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这本小书面前,数十年来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不禁有些黯然失色了。《笑谈大先生》收录陈丹青有关鲁迅的七次演讲,虽不过数万言,却在浩瀚的鲁迅研究的边上,辟出新的境界。
作者将鲁迅重新放置回“民国的风景”中,与其说是“还原”了鲁迅,不如说是为一个人、一个时代重新注入灵光。
《笑谈大先生》由陈丹青亲手设计,收录照片、插图数十幅,精印精装,堪称不容错过的收藏级版本。
内容简介
《笑谈大先生》收录作者近年来关于鲁迅的七次演讲文稿。虽不过数万言,却在浩瀚的鲁迅研究的边上,辟出新的境界。论者或称它“还原”了鲁迅,或称它“唤回”了鲁迅;而对于作者,这样的公开谈论大先生,或许更类似于一种还愿。作者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著名油画家、作家,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者之一。 2000年回国,任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7年卸去教职。其间,因辞职事件及公开批评教育现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舆论一时焦点,更被媒体推崇为影响中国的五十位知识分子之一。除了教育,他对城市、影像、传媒等文化领域的诸多现象亦有独到见解和批评。 著有《纽约琐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等。目录
序笑谈大先生
鲁迅与死亡
鲁迅是谁?
上海的选择
民国的文人
文学与拯救
鲁迅与美术
漫长的补记
附录 鲁迅的墓园
精彩书摘
民国的文人——长沙谈鲁迅(部分)
鲁迅交友之广,也是这个演讲中提到了的,但后人在照例的宣传中,只知道他有共产党朋友。鲁迅一生在对待朋友、与朋友相处方面,大致是怎样的性情?
陈:除了不可能查证核实的隐私,没有一位中国作家像鲁迅那样被详详细细暴露在公众面前。由于长期独尊鲁迅,他生前的所有生活记录——日记、书信、大量回忆和旁证——不但全都出版,而且重复出版。诸位如果真要了解鲁迅,可能要比了解任何其他中国作家更方便。这些资料中充满鲁迅对待朋友的故事和细节,诸位有兴趣,很方便查证。
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鲁迅资料中丰富翔实的日常细节,后人视而不见,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今日的文艺中青年多半不愿了解他,因为怎样看待鲁迅早已被强行规定,以致几代人对威权的厌烦、冷漠和敷衍,也变成对鲁迅的厌烦、冷漠和敷衍。敷衍一位历史人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简化他,给他一个脸谱,很不幸,鲁迅正是一个早已被简化的脸谱。
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然而还是中国人的老办法:要么骂,要么捧,总不能平实地面对一个人,了解一种学说,看待一段历史。
“兄弟失和是他最难释怀的内伤”,这几乎也可算鲁迅生涯中的一桩超级情感公案。而且,尤具戏剧性的是,他与周作人在进入历史书写中所处的境地,甚至都可以用“神鬼”之别来描述。这个方面,除了失和内情的悬疑,周氏兄弟在对待亲情方面,性格有很大的不同吗?就鲁迅的作品来讲,有涉及这些的吗?
陈:鲁迅不是神,周作人也不是鬼。周作人曾在早年说,自己心中有一个“绅士鬼”,一个“流氓鬼”,这是文学的说法,修辞的巧妙,我们就此说周作人是鬼,那是不懂修辞,不懂文学,别说当不成绅士,恐怕还不如流氓,中国从前的流氓,有性情,会说话,用词很别致。如果因为周作人当过汉奸,就说他是鬼,更不应该。你是陈独秀,是胡适,是周作人的同辈,你或许有资格骂他一句,贬他一贬,到了我们这一代,有什么资格呢?我不认为我有资格责难前辈,看不出我们有什么道德的高度可以遥远地责难一位五四时期的文人——那是多么轻佻的道德姿态。诸位请看看今日中国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黑矿主、王八蛋,那才真是妖魔鬼怪啊。
至于周家兄弟的情感关系,哥哥弟弟都写过。中国从前的规矩,母亲死了,大姐在家就是母亲,父亲死了,大哥就是父亲,担当权威,负起责任。鲁迅的父亲早死,此后一生,他一直是位好哥哥,不摆权威,尽责任。他留学回来,接母亲到北京,给弟弟在北大安排教职,北京两处房产是他的薪水盖起来。弟弟得病,他比弟弟还急,后来写在《兄弟》这篇小说里。但是彼此失和,直到去世,在可见的文字中,两兄弟都很得体,即便在大观点大是非上有所暗示,有所表达,也十分厚道,十分守度。从前有句话,叫作“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何况兄弟失和。大家要知道,他们周家兄弟在当时是极端新派的、前卫的文人,但他们的行为大致遵行旧道德,不但他们,英美派海归的为人处世也谨守旧道德的规范。胡适在台湾去世后,蒋介石挽联就说出这层意思,我记不得原话,大致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我们再回头看看从1949年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之间、师生之间、朋友和亲人之间,发生多少卑鄙丑恶、乖张惨痛的故事,像周家兄弟那般失和,像五四文人那种有教养的绝交关系,在今天,寥若晨星。
据说周作人晚景很凄凉,他一生是不是都对鲁迅怀了怨恨之心?
陈:周作人晚年不是凄凉,而是孤立和悲惨。说他孤立,因为建国后他被提前释放,毛泽东批示将他养起来,写回忆,弄翻译,月薪两百元,相当高。但他不再有朋友,不再有社会地位。说他悲惨,是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多年,到“文革”,他就被红卫兵折磨,撵到破屋子里,有个老婆子偷偷伺候他,有一天他在炕上喝完一碗粥,当天就死了。
周作人晚年有一方印章叫作“寿则多辱”,说的是实话。但他刻这方印时,还想不到会领教“文革”时期的侮辱。他因汉奸罪被审判,坐监牢,属于惩罚,不是受辱。
至于他一生是否对鲁迅怨恨,我以为不要随便揣测。即便有怨恨,那也并非是错,因他是鲁迅的弟弟。而像这样的兄弟恩怨,不是外人可以任意揣测的。在座诸位可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但有父母、亲人、好朋友,外人公开揣测议论你们的私人感情关系,你们会同意、会接受吗?
“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个意思,就是事实上的鲁迅并不只是诅咒万恶的旧中国,他诅咒之外的东西,可以简要介绍一下吗?
陈:“吃人”的“礼教”,顽劣的“国民性”,军阀统治,国民政府的压迫,等等等等——这些主题,是鲁迅一代知识分子全都诅咒的事物。陈独秀、胡适,当年就是发起反礼教、主张文学革命、呼吁改造国民性的先锋人物。
可是为什么大家只知道鲁迅一个人在“诅咒”呢?就因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和知识遗产,被高度政治化——胡适的知识背景是英美那一套,后来又和国民政府合作,所以他的革命性全部不算,变成反动派;陈独秀因为二十年代末不服苏联的管制,既被共产国际抛弃,又被中共党内打击,所以他的革命性也全部不算,连创建共产党的大功劳也不算。鲁迅死得早,没有介入国民政府,也不是共产党员,而他的“诅咒”具有高度的文学性,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其他新兴知识分子比不上,所以鲁迅在建国后最有利用价值,最方便被以一种极不道德的方式树立为一个道德的,甚至超道德的形象,来压迫大家。
在这一场巨大的阳谋中,真正被利用的是我们几代人。独尊鲁迅的真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无知,不怀疑,盲从意识形态教条。我应该说,我们几代人被成功地利用了。现在一部分人知道被利用,于是掉过头来诅咒鲁迅。
那么鲁迅是否“诅咒”过其他事物呢?第一,鲁迅固然诅咒过古文、礼教之类,但对其他事物,他不是诅咒,而是怀疑、讽刺、批评;第二,他议论过的事物,太多了,譬如文人相轻问题,翻译问题,美术问题,小孩子和妇女问题,留胡子和拍照问题,书籍封面设计和毛笔钢笔问题,等等等等。但他怀疑批判的方式多种多样,有轻重,有曲直,亦庄亦谐,即便他被引述最多的批判命题,也不像长期宣传的那么极端、片面、简单。所以第三,今天议论鲁迅的年轻人,阅读过几本鲁迅的书?阅读过多少其他五四文本?假如阅读过,应该不会有以上问题,不会问鲁迅时代的其他文人是什么状况,鲁迅怎样对待他的朋友或兄弟,尤其不该问鲁迅是否还诅咒过其他事物。为什么呢?因为只要阅读鲁迅,阅读那个时代的作品,就不会有以上疑问,即便有,也不是这么问法。
总之,半个世纪的洗脑,弄得本来应该知道的事情,变得不知道,本来蛮清楚的是非,变得不清楚,本来很普通的常识,变得很稀罕。独尊鲁迅的后果,不是我们只知道鲁迅,不知道其他人,而是我们连鲁迅也不知道,也要来问。
我今天回答的,其实都不该是问题,结果都变成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很简单,请阅读鲁迅。可我从来不劝告别人读鲁迅,因为几代人被逼着读鲁迅,读了等于没读,或者,还不如不读——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扭曲鲁迅,就是我们的被扭曲。
……
前言/序言
自序 (节选)七回讲演讲下来,我久已存心写写这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胡适,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我不是指国家的统一。我也不相信穿越时间的历史人物居然一如当初——孔夫子或曹孟德果然是经文戏出里的那个人么——鲁迅与胡适离我们实在并不远,倘若文化中国不割离,五四传统不裂变,则胡适鲁迅不该在两岸此消彼长的历史剧情中,忽而被禁绝,忽而成显学,忽而当圣人,忽而作恶魔……面见海婴先生的一刻,我确认鲁迅是一位人父,是阜成门外与山阴路底的居民,是那些手稿与著作的主人。当我结结巴巴试图描述我所望见的鲁迅,我是在说出我的相信与不相信,是在为自己的判断,娓娓辩护。在这辩护过程中,我想象鲁迅与他的敌友们活在众声喧哗的民国。
所以我很少很少谈及鲁迅的文章:他无须辩护。他的自供词与辩护状,就是他写的书。
说来奇怪:自从公开讲过鲁迅后,近年,我竟不很经常念及老先生了。什么缘故呢?而近日校稿,逐篇一过,又发现我关于大先生想要说的话,其实并没说出来。集子里末一篇《鲁迅的墓园》,写在2000年,当时就算借此还了爱敬鲁迅的愿。现在选作附录,顺便再补几句闲话吧:那一次,我在虹口公园注意到毛泽东手书的鲁迅墓碑给两侧的美树遮没了,及后见到海婴先生,他就说,他曾几度向上海市政府申请作修剪,迄今没下落。我暗想:花木无心,遮没了,岂不也好。记得鲁迅初葬的那块碑,字体拙朴,笔锋转折竟有鲁迅手书的圆润而内敛,谁写的呢,动问海婴,原来竟是他七岁丧父时,由母亲扶持着,一字一字亲手写成的。
呜呼!愿有关鲁迅的想象汇聚到1936年吧,那一年,因为弟弟的几句话,雏儿的几个字,鲁迅之为鲁迅,算是有一份平实的交代与存证在,纵然兄弟失和,父子永隔。
2010年12月31日写在北京
在线试读
《笑谈大先生》相关信息在这本小书面前,数十年来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不禁有些黯然失色了。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很有意思,一种复古的油画风格,色彩浓郁却不失质感,让人一看就觉得有故事。翻开书页,纸张的触感也很舒服,带着一种淡淡的油墨香,这对于一个喜欢纸质书的人来说,简直是享受。我一直对那种能够穿越时光、展现历史细节的作品情有独钟,而这本书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很有可能做到了这一点。故事的主人公,听名字就透着一股不凡的气质,总觉得他身上承载着很多时代的印记和不为人知的经历。我特别期待他在人生的某个节点,是如何做出那些影响深远的决定的,又是如何面对那些命运的跌宕起伏。作者在人物的塑造上,似乎有着深厚的功力,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一个鲜活的灵魂。我喜欢那些有血有肉、有缺点也有闪光点的人物,他们才更贴近真实的人生。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让我笑出声来,或者让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如何,我已经迫不及待想 dive into 这个故事的世界了。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惊喜远不止于此。随着故事的深入,我发现它在探讨的不仅是个人命运,更是在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思潮的涌动。那些历史背景的铺陈,并非生硬的教科书式讲解,而是巧妙地融入到人物的经历和对话之中,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复杂。我尤其喜欢作者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反思,那些对人性的洞察,既尖锐又温情,让人在读到某些地方时,会不自觉地对号入座,或者引发对自身经历的共鸣。我想,这大概就是一本优秀作品的魅力所在吧,它能够超越时空,触及到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和思考。我会在读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反复回味书中的每一个字句,试图从中汲取更多的智慧和力量。这本书让我感到,我不仅仅是在阅读一个故事,更是在参与一场深刻的思想交流,在拓展自己对世界的认知边界。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语言的运用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遣词造句既精准又富有表现力,时而如涓涓细流,细腻婉转,时而如惊涛拍岸,掷地有声。我特别喜欢那些富有诗意的段落,它们像是点缀在故事中的璀璨明珠,让整个文本更加生动和富有感染力。同时,作者在幽默感的把握上,也做得相当出色。那些“笑谈”的部分,并非粗俗的打诨,而是透着一种智慧的幽默,一种对生活辛辣而又温和的调侃,让人在会心一笑之余,也能品味出其中的深意。这本书让我体会到,语言的力量可以如此强大,它可以塑造人物,可以渲染气氛,可以引发情感,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我甚至会尝试模仿作者的某些句子结构,来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这本书无疑是语言艺术的一次精彩呈现。
评分总的来说,这本书是一次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它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在多个层面触动了我。我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所吸引,被作者的叙事技巧所折服,被作品所蕴含的深刻思考所启发,也被精妙的语言所打动。它让我看到了历史的缩影,也让我反思了当下的人生。这本书就像一位睿智的长者,用他的人生经验和洞察,与我进行了一场意味深长的对话。我从中获得了很多乐趣,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毫不犹豫地会将这本书推荐给我的朋友们,我相信他们也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与收获。它是一本值得反复品味、值得珍藏的好书。
评分读到一半,我发现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人觉得拖沓,也不会过于仓促。故事仿佛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时而平静舒缓,时而激流勇进,将我带入一个又一个精心编织的情节之中。我特别欣赏作者对细节的刻画,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却能精准地勾勒出当时的人物心境和环境氛围。比如,书中对某个场景的光影变化、人物细微的面部表情、甚至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身临其境。我总觉得,一个好的故事,不仅仅是情节的堆砌,更是对生活细微之处的捕捉和提炼。这本书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甚至会停下来,反复咀嚼某些句子,体会其中蕴含的深意。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找到这些“珍珠”的,又是如何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如此动人的篇章。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到,阅读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更是一种与作者灵魂对话的过程,一种体验不同人生、不同时代的奇妙旅程。
评分帮妈妈买的书,不知道好不好看。
评分通过这本书开始了解鲁迅,喜爱鲁迅,推荐
评分京东商城,速度很快。
评分好书,内容精彩,书籍装帧精美。
评分《笑谈大先生》收录陈丹青有关鲁迅的七次演讲,虽不过数万言,却在浩瀚的鲁迅研究的边上,辟出新的境界。
评分《笑谈大先生》收录作者近年来关于鲁迅的七次演讲文稿。虽不过数万言,却在浩瀚的鲁迅研究的边上,辟出新的境界。论者或称它“还原”了鲁迅,或称它“唤回”了鲁迅;而对于作者,这样的公开谈论大先生,或许更类似于一种还愿。
评分双十一期间 本人在这买了两百元的书(十本) 收到货后甚是“湿 A s望 ” 首先 作为网络售书巨头之一 其包装甚是/汉 D臣/ 用一张牛皮纸加以包装 直接造成了书籍在快递过程中的 “ 模 M 笋” 与“亚 M麻F 训” 相较而言 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敝人曾在“亚H麻E训”买书 只要你的书超过一定重量或数量都是用专业的箱子给你包装 这一点与“亚 f麻 训” G查的不是一点半点 其次 书的质量除了基本专业书籍质量尚A可 《名作细读》《我们仨》《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华阳国志研究》等书籍真是让人“物N语 ” 书籍与“正H版”有天壤之 别 可能连“正M版”书籍也不是 退一步说 即便不是“正M版” 书籍你们怎么也弄个精装“;倒F板”;来啊 镜拿着倒板书籍“ 户 D 浓” 人 对于《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修订版)》一书 已经不能用“师 p 望”来形容 书中多页有油印之灰迹 甚至连薄膜封皮都没有 封面上的三个指印是你们的“化D 吖”吗 灰黄纸业与白纸形成夹层 多页文字有重F影 请问你们是从哪家作坊进的书 太让人湿M望了 尤其是《华阳国志研究》一书 请问京东 你们是把书放在“h u i” 里半年又拿出来的吗 其中本人特意挑选了一本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这个本书内里几页有纸面有“凹 H 陷” 请问这就是力透纸背吗 《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更帅 纸质之D茶令人“湿 K 望” 你们以为双十一打折就可以维F所玉维的”户D 浓“人吗
评分看到有推荐,所以买了看看。
评分太薄了 都是演讲 访问啥的 内容少 其它都还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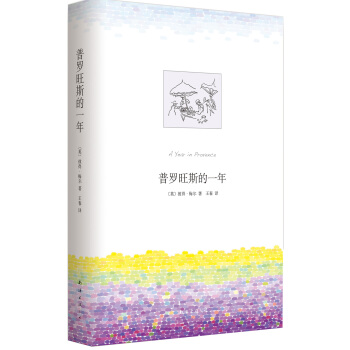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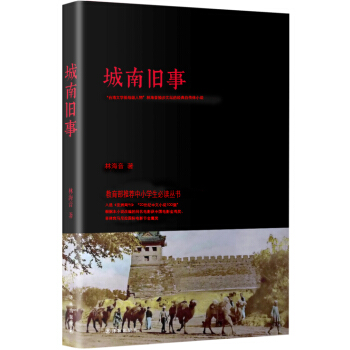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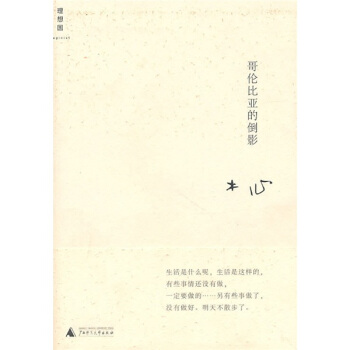
![泥步修行(余秋雨新作)[荐书联盟推荐]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79071/592932f2Nde0b83b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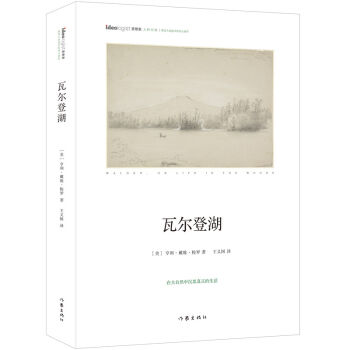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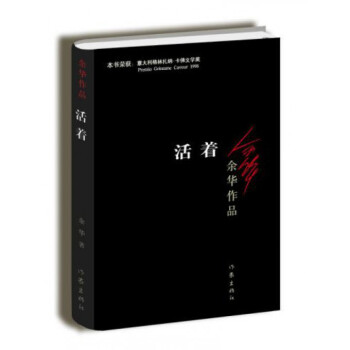
![国内大奖书系-小巴掌童话5(注音·全彩·美绘)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41193/568495fbN759b88ef.jpg)




![女孩版-蒋多多日记(第1辑):我是你的好朋友 [8-12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66915/56d015e4Nfe6134b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