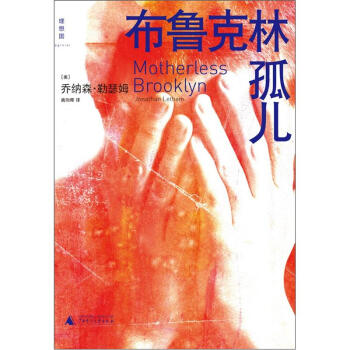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 获得众多大奖的经典小说--本书在美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好评。不仅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单,还获得美国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美国国家书评奖,同时也是《时尚先生》年度最佳小说,沙龙图书奖获奖作品,金匕首最佳犯罪小说奖获奖作品,还入选了《卫报》评选的“死前必读的1000本小说”,集众多奖项为一身,足以证明其经典小说的地位。2、美国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作品首次引介到国内--乔纳森·勒瑟姆是美国当代最具创造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杂糅了科幻、推理的元素,又能推陈出新,突破类型小说的限制,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被评论家称之为“类型小说的突破者”,不仅时常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也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世界奇幻奖、金匕首奖、麦克阿瑟奖等众多大奖。如今,乔纳森·勒瑟姆一有新书出版便会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纽约,他的作品几乎是纽约文艺青年的最爱,几乎人手一册。
3、好莱坞天才影星爱德华·诺顿推崇的作品--1999年《布鲁克林孤儿》出版后不久,爱德华·诺顿便买下了本书的电影版权。此后爱德华·诺顿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改编这部作品,他不仅将导演这部电影,还将参与演出书中患有妥瑞氏症患者的主角莱诺尔。这部电影的上映日期一再推延,影迷们也越来越期待这部电影。据IMDB网站提供的最新消息,这部备受期待的电影大作2013年公映。
4、不同寻常的叙事视角--本书是以患有妥瑞氏症患者、这个不同寻常的人物来讲述整个小说,看待整个世界。不仅好看,而且趣味十足。对此,蔡康永在“周二不读书”栏目推荐本书时便说,“透过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会看到一些平常所谓健全的人看不到的,尤其是像纽约这么一个有趣的地方,从这样的一个主角眼中看出来,的确充满了我们平常所看不到的光泽、看不到的颜色。”
内容简介
莱诺尔是布鲁克林圣文森孤儿院的孤儿,从小就患有罕见的妥瑞氏症,这个疾病使得他产生狂吠、拍打、自言自语等异常行为。被视为怪胎的他和另外三个男孩被挑选出来,为敏纳·弗兰克的出租车行兼侦探社工作。那种异于其他孤儿的优越感,让这四个男孩成为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忠心耿耿地效忠于敏纳·弗兰克。有一天,弗兰克被杀,莱诺尔这四个孤儿的世界也被整个翻转过来。一连串问题接连发生,各种各样的人物、黑人侦探、禅堂里的老师、日本黑帮等相继出现,他们四个人之间不断发生磨擦。莱诺尔这个怪胎开始不顾一切地游走在各种人物之间,发誓要解开谜团。作者简介
乔纳森·勒瑟姆(Jonathan Lethem,1964- ),1964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年少时,他沉迷于鲍勃·迪伦的音乐,钟情于《星球大战》,读过菲利普·迪克的全部小说。1982年,勒瑟姆从本宁顿学院退学,怀揣四十美元,从科罗拉多搭便车穿越一千多里的荒漠与山岭,来到加利福尼亚。在加利福尼亚,他为一家二手书店工作,同时开始了他的文学写作。乔纳森·勒瑟姆是美国当代最具创造力、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杂糅了科幻、推理的元素,又能推陈出新,突破类型小说的限制,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不仅深受读者欢迎,时常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也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世界奇幻奖、金匕首奖、麦克阿瑟奖等众多大奖。
主要作品有《枪,偶尔有音乐》、《布鲁克林孤儿》、《孤独堡垒》、《久病之城》等。
精彩书评
透过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会看到一些平常所谓健全的人看不到的,尤其是像纽约这么一个有趣的地方,从这样的一个主角眼中看出来,的确充满了我们平常所看不到的光泽、看不到的颜色,我在阅读《布鲁克林孤儿》的过程中,得到很大的乐趣。——蔡康永(“周二不读书”中推荐)
年度最佳小说,十分新颖,让人深深感动。
——《时尚先生》杂志
充满了机智的对话和情节转折……一次引人入胜的历险。
——《卫报》
一个侦探故事,一幅敏锐的布鲁克林图景,一部重新讲述的《雾都孤儿》。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是个妥瑞氏症患者,他的讲述如此具有巴洛克风格,就连菲利普·马洛也会感到羞愧,向他致敬。
——《新闻周刊》
目录
走进布鲁克林孤儿
拷问的眼睛
(妥瑞氏症的梦境)
坏曲奇
一心
自作主张的身体
曾经相识
好三明治
精彩书摘
第二章 布鲁克林孤儿我在圣文森特男孤儿院的图书室长大,这所孤儿院位于布鲁克林下城区,还没有哪个开发商有兴趣把这一片翻新为上等社区;这里既不算是布鲁克林高地,也不属于科布尔山,甚至都不在波伦山的范围内。大体而言,孤儿院坐落在布鲁克林桥的出口匝道上,但看不见曼哈顿或大桥本身,底下的八条车道总是车流滚滚;车道旁耸立着毫无特色的民事法庭,法院大楼尽管看起来冷峻灰暗,但我们孤儿院里的不少孩子都见识过里面的样子;还有布鲁克林邮局的分拣中心,彻夜嗡嗡哼哼,灯火闪烁,大门呻吟着打开,卡车运来堆积如山的名为“信件”的神秘物品;还有伯顿机修专科学校,受过磨砺的学生在那里努力着让自己过上无聊的正常人生活,他们每天两次蜂拥而出,趁着休息时间喝啤酒吃三明治,把隔壁的破旧酒馆挤得满满当当,乖戾的暴徒气焰让过路人胆战心惊,让我们这些孤儿院的孩子心驰神往;还有一排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公园长椅,头顶上是拉法耶的大理石胸像,标出他在布鲁克林战役中的介入地点;还有一处停车场,周围的高篱笆顶上镶有宽阔的铁丝网和迎风抽打的荧光警示旗;还有一幢红砖盖的贵格派礼拜堂,附近还是农田的时候大概就有它了。简而言之,这些乱七八糟的货色把守着一个古老而破落的行政区的臃肿入口,是货真价实的蛮荒之地,从这里经过前往他处的人们会将它刻意遗忘。在被弗兰克·敏纳拯救之前,正像我之前所说的,我就生活在图书室里。
我决心读完那坟墓般的图书室里的每一本书,每一册编目入库又被遗忘的惨淡捐赠品--我在圣文森特时恐惧和无聊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是妥瑞氏式症的早期迹象之一,让我强迫性地计数、排序、探查。蜷缩在窗台上,翻着干燥的书页,看着尘埃跌撞着穿过成束的阳光,我在西奥多·德莱塞、肯尼斯·罗伯茨、J.B.普里斯特利的著作和 《大众机械》的过刊中寻找正在萌芽的古怪自我,但都没找到,没找到属于我的那种语言。与此相仿的是我无法看电视。《家有仙妻》、《太空仙女恋》、《我爱露西》、《盖里甘》和《脱线家族》①没完没了地重播,那些缺乏运动细胞的书呆子借此打发了无数个下午的时光,凑到屏幕近旁观赏女人的滑稽表演--女人!多么陌生的存在,和信件一样,和电话一样,和森林一样,都是与我们孤儿无缘的东西--模仿女性角色的丈夫,但我在电视里找不到自己,德西·阿纳兹、迪克·约克、拉里·海格曼②,那些饱受折磨的飞向地球的太空人,他们没有展示出我需要看到的东西,无法帮助我找到我的语言。我与周六早晨稍微亲近些,尤其是达菲鸭能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前提是我能忍受想象自己长大后成了一只挨过炸弹、嘴巴七零八落的鸭子。《蜜月中人》里的亚特·卡尼也让我有所触动,特别是他扭动脖子的模样,不过这需要管事的允许我们晚睡才行,否则就没法看见他了。但是带给我语言的是敏纳,是敏纳和法院街让我说话的。
我们四个那天之所以被选走,只因为我们是圣文森特仅有的五个白种男孩中的四个,第五个名叫斯蒂芬·格罗斯曼,肥如其名。斯蒂芬要是瘦些的话,凯赛尔先生恐怕就会把我扔回废物堆里了。我无疑是个滞销货,又抽搐,又抠鼻子,是从图书馆里挖出来的,而非来自操场,怎么看都像个弱智,显然是谁买谁后悔的劣等品。凯赛尔先生是圣文森特的老师,他跟弗兰克·敏纳熟得跟邻居似的,他建议敏纳借用我们一个下午,这让我初次窥见了在敏纳周围闪闪发亮的那个由“承情”和“偏袒”构成的光环--“认得谁谁谁”是一种生存条件。敏纳与我们恰好位于两个极端,我们不认识任何人,即便认得也无法从中获益。
敏纳只要白种孩子,是为了迎合雇主或许抱有的偏见--和他必然抱有的偏见。也许他的脑子里那时就有了改造我们的幻想。当然我无从得知。在他第一天对待我们的态度中无疑没有显露半分。那是八月一个闷热的工作日,下午的课程结束后,街道像是黑色的口香糖,慢速爬行的车辆在烟霾中仿佛成像不清的自然课幻灯片。他打开厢式货车的后门,车身遍布凹痕和涂鸦,尺寸和深夜送信的邮政卡车差不多,他吩咐我们进去,然后砰的一声摔上门,上了锁,既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问我们叫什么。我们四个人大眼瞪小眼,为脱离樊笼感到震惊、晕眩。我们不知道这代表什么,其实也不需要知道。另外三个人,托尼、吉尔伯特和丹尼都愿意跟我搭伙,愿意假装我与他们很合拍,只需这样他们就能被外部世界拎出孤儿院,摸黑坐在肮脏的金属地板上,听凭车厢震颤着驶向圣文森特以外的某个地方。我当然也在震颤,敏纳集拢我们几人之前我就在震颤,我的内里永远在震颤,我用尽力气不让它表露出来。我没有亲吻另外三个男孩,但我很想,于是我发出了亲吻般的啁啾声,类似鸟儿的叫声,一遍又一遍:“嘁喳,嘁喳,嘁喳。”
托尼叫我闭上他妈的臭嘴,但他的心思并不在这儿,特别是今天,人生的秘密正在徐徐展开。对于托尼来说尤其如此,他的命运找上门来了。他从一开始就在敏纳身上看见了更多的东西,因为他让自己做好了这个准备。托尼·佛蒙蒂因其流露的自信在圣文森特小有名气,他坚信自己进孤儿院肯定是出了差错,相信自己并不属于这里。身为一名意大利人,他优于我们这些不知道出身的家伙(艾斯罗格是什么玩意儿?)。他的父亲不是黑帮就是条子--托尼不认为这有什么矛盾,所以我们也一样。意大利人将会伪装成这个那个身份回来找他,他正是这样看待敏纳的。
托尼出名还有别的原因。他比同在敏纳车厢中的我们其他几人都年长,他十五岁,我和吉尔伯特十三,丹尼·芬特尔十四(圣文森特孤儿院的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去别处念高中,从此很少再露面,但托尼却想办法留了下来),他的年龄让他显得无比时髦和世故,即便他没有离开过孤儿院,在外面生活了一段时间再回来也是这样。事实上,他是我们的经验之神,总在唠叨香烟和其他方面的暗示。两年前,街对面礼拜堂的某个贵格派人家把托尼带了回去,想给他一个永久的家。收拾衣服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抒发他对这家人的不齿了。他们不是意大利人。话虽如此,托尼还是和他们生活了几个月,也许挺开心,但他始终不肯承认。他们安排托尼进了“布鲁克林之友”,一家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的私立学校。大多数日子里,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托尼会在圣文森特的围栏外逗留,跟我们讲他如何抚摸私立学校的姑娘们,有时还要搞上一两回,私立学校的男生都很娘娘腔,懂得怎么游泳和踢足球,但上了篮球场只有挨他羞辱的份儿,而篮球都不算是托尼的专长。后来有一天,他的继父母发现高大黑发的托尼和一个姑娘上床,但这次太过分了,那女孩是他们十六岁的亲生女儿。反正据说如此,但消息的源头只有一个。总而言之,第二天他被送回了圣文森特,他轻而易举地回到了原先的生活方式:每隔一天,就轮流殴打我和斯蒂芬·格罗斯曼,然后又对我们示好,这样我们俩就永远不可能同时受他照应,也无法彼此信任,就像我们不信任托尼一样。
托尼是我们的“嘲笑之星”,当然也是他首先吸引了敏纳的注意力,激发了我们这位未来老板的想象力,叫他在我们这群渴望栽培的心中窥见了日后的敏纳帮。或许托尼,连同他对意大利救星的热望,甚至还帮助敏纳做出了构想,最终令敏纳侦探所应运而生;托尼那份渴求的力度激发了敏纳的特定灵感,让他第一次有了找几个帮手供其差遣的念头。
敏纳当时也只勉强算是成年,但在我们眼中却无疑是个男人了。那年夏天,他二十五岁,瘦长身材,略有点小肚子,穿有口袋的T恤衫,还尽心尽力地把头发梳成油光水滑的大背头,这种卡罗尔花园式的发型与七九年格格不入,而像是投射自某个弗兰克·辛纳屈唱主角的年代,那一刻仿佛一粒琥珀或摄影师的滤镜,紧紧包裹住了弗兰克·敏纳和他钟爱的所有事物。
敏纳那辆货车的车厢里,除了我和托尼之外,还有吉尔伯特·科尼和丹尼·芬克尔。吉尔伯特当时是托尼的左膀右臂,身材矮壮,性格阴沉,称之为“硬朗”也不为过--听见你叫他暴徒,他也许会对你露出笑容。吉尔伯特对斯蒂芬·格罗斯曼格外不好,要我说是因为后者的肥胖,对他而言是一面引人不快的镜子,但他待我很宽容。我们甚至一起守着几样古怪的秘密。两年前,孤儿院组织去曼哈顿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和吉尔伯特脱离大部队,不约而同地返回了一个展厅,天花板上垂吊着的巨大塑料蓝鲸主宰着整个房间,它是正式参观的焦点展品。然而,蓝鲸身下还有一道双面展墙,是黑暗而神秘的深海生物立体布景,打了灯光,排列整齐,你必须凑到玻璃前才能发现隐藏在拐角处的种种奇景。其中有抹香鲸大战巨乌贼,还有杀人鲸破冰而出。我和吉尔伯特深深着迷,流连于一面又一面的展窗之前。等一班三年级或四年级的小孩被带出展厅以后,我们发觉这个巨大的房间尽归我们所有,连说话时我们的声音都被博物馆里超乎自然的寂静磨去了棱角。吉尔伯特把他的发现指给我看:企鹅布景旁有一扇孩童尺寸的黄铜门扉,没有上锁。打开门,我们发现它既通向企鹅布景背后,也通向布景内部。
“艾斯罗格,进去。”吉尔伯特说。
如果我不愿意,这大概就是仗势欺人了,但事实上我想进去都想得发疯了。展厅里空无他人的每一分钟都极其宝贵。那扇门的上缘只有我的膝盖高。我爬了进去,打开充当展览边墙的海蓝色背景板上的活门,接着滑进了画面之中。碗形的海底长而平缓,是涂抹过颜色的石膏,我弯着膝盖沿坡跑了下去,望着玻璃另一侧目瞪口呆的吉尔伯特。游泳的企鹅或是固定在从后墙上伸出的长杆上,或是悬挂在海面的塑料波浪下,海面此刻已是我头顶上低矮的天花板了。我爱抚着最近的一只企鹅,这只企鹅吊得很低,正在潜水追捕美味鲜鱼。我拍拍企鹅的脑袋,揉揉它的咽喉,像是在帮它吞咽药丸。吉尔伯特笑得直打滚,以为我在向他表演喜剧,但事实上我被一阵温柔而又躁动的冲动所征服,必须去爱抚那只僵硬悲哀的企鹅。接下来,我必须去触摸每一只企鹅,至少是我够得到的每一只--有几只我够不到,它们站在浮冰上,被海面挡在了另外一侧。我跪在地上四处移动,满怀爱意地挨个抚摸那些游泳的鸟儿,最后才穿过铜门逃了出来。吉尔伯特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我看得出来。我成了他心中无所不能的小子,敢肆意妄为的小子。当然了,他既对也错,因为摸到第一只企鹅之后,我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不知为何,这引出了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他越来越信任我。我很疯狂,但又很温顺,很容易受到胁迫,这让我成了吉尔伯特理想中的仓库,用来存放他认为是疯狂念头的东西。吉尔伯特比别人早熟,喜欢打手枪,正在寻找介于其个人经验和一般校园常识之间的三角测量基准物。我做那档子事吗?有多频繁?一只手还是两只手?这样还是那样握?闭不闭上眼睛?有没有动过摩擦床垫的念头?我很认真地对待他的询问,但却无法提供他需要的信息--当时还不行。我的愚钝刚开始让吉尔伯特好生不爽,他有一两个星期假装从未提过那些问题,甚至压根儿不认识我,对我投来凶恶的目光,叫我晓得要是胆敢说出去就将有极大的痛苦等在前头。然后他会突然回来,比之前更急切。试试看吧,他这样说,没那么难。我会看着,如果你弄错了我就纠正你。和博物馆那次一样,我听从了他的话,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无法用对待企鹅的那种温柔对待自己,至少当着吉尔伯特的面做不到(尽管事实上他催动了我对自己的私密探索,这很快就变得相当耗费精力),吉尔伯特又不高兴了,把我吓得魂不附体。两三个回合以后,这个论题就被永远搁置了。然而,暴露隐私的影响却留存了下来,成为我们之间宛若幽魂的维系。
敏纳这辆货车里的最后一个男孩是丹尼·芬克尔,他是个赝品,只不过肤色很白而已。丹尼欢欢喜喜、轻松自在、发自肺腑地融入了圣文森特的大部分人中。他以自己的方式赢取了不亚于托尼的尊重(自然也得到了托尼的尊敬),既没有吹牛说大话,也不需要惺惺作态,大体而言连嘴巴都不用张开。他真正通晓的语言是篮球,可这位运动健将精神太过紧绷,动作太过流畅,在屋内、教室里就显得分外憋屈。他一开口就要嘲笑我们的热情、我们显露的“不酷”,但总有些心不在焉,仿佛他的脑子另有盘算,还在琢磨怎么换手过人,怎么优化步法。他听“放克疯”,听“浮雕宝石”,听“扎普”①,和孤儿院的其他孩子一样,也飞快投入了饶舌乐的怀抱,但每逢他钟爱的音乐奏响,他从不会跳起舞步,而是抱着胳膊站在那里,随着节拍瞪眼撅嘴,富有表现力的臀部一动也不动。丹尼生活在半空中,他既不黑也不白,既不挨揍也不打人;帅归帅,但不受女孩这个念头侵扰;功课一塌糊涂,但每门课都能蒙混过关;偶尔挣脱地球引力的束缚,漂浮在圣文森特的篮球框上那堆烂铁链和人行道之间。折磨托尼的是自幼失散的意大利家庭,他坚信他们会回来找他;丹尼却像是七八岁就离家出走,加入了街头篮球比赛,一气打到十四岁,直到敏纳开着货车来的那一天为止。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说实话,拿到这本书时,我对它的期待值其实是比较低的,毕竟近年来关于城市边缘人物的题材似乎有些泛滥。然而,翻开第一页后,我立刻被那种独特的叙事腔调所吸引。作者的语言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干净利落地剖开了现代人看似光鲜外表下的那层易碎的保护膜。它没有刻意去煽情,却在平铺直叙中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张力。故事中角色的选择,那些艰难的取舍,让我反复思考“何为归属”的哲学命题。更令人称道的是,作者对时代背景的把握非常精准,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和当下的疏离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它不是那种读完让人拍案叫绝的爽文,而是一种需要你静下心来,细细品味其间留白与暗示的作品。每次合上书页,都会忍不住回味那些对话,它们就像散落在记忆深处的碎片,拼凑出一个关于“漂泊”的完整肖像。
评分这部小说读完后,脑海里久久无法散去的是那种特有的、混合着怀旧与迷茫的都市气息。它细腻地捕捉了那些在人潮汹涌中努力寻找自己立足之地的灵魂的挣扎。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入木三分,仿佛能透过文字直接感受到角色在面对生活变故时的那种无助与坚韧。故事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时而急促如纽约的地铁高峰,时而又慢得如同老式胶卷播放的影像,充满了光影的流转。我尤其欣赏作者在环境描写上的功力,那些街道的转角、公寓楼里的微光、街边小店的喧闹,都成为了人物情绪的延伸和注脚,让整个阅读体验如同沉浸在一部精心制作的独立电影之中,充满了那种不易察觉的、却又直击人心的力量。它并非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一个个微小的、真实到令人心痛的瞬间,让你不得不反思自己与周遭世界的关系。读完之后,那种久违的、被深刻触动的感觉,让我好久才从故事中抽离出来。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非常巧妙,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节点,但它们又通过无形的根系紧密相连,共同支撑起一个复杂而又统一的世界观。我个人对这种多线叙事的能力感到非常佩服,它没有让故事线变得混乱,反而让人物的命运彼此映照,互相折射出不同的光芒。特别是几处关键的转折点,处理得极其含蓄而有力,没有使用任何戏剧化的夸张手法,仅仅是通过人物一个眼神的闪躲或是一次沉默的对望,就完成了情绪的爆发。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叙事功力,是很多新手作者难以企及的。我不得不承认,在阅读过程中,我好几次停下来,只是为了重新阅读前几段文字,去捕捉那些之前可能忽略掉的细节伏笔。这绝对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每一次都能发现新层次的佳作。
评分这部作品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对“寻找”这一行为本身的探讨。它不是简单地讲述一个角色找到了什么,而是深入挖掘了“寻找”过程中的消耗、希望与幻灭。书中的场景切换非常流畅,仿佛导演的镜头在不同场景间自由穿梭,却总能精准地锚定在人物的内心活动上。我特别喜欢那种略带荒诞感的幽默,它不是用来逗乐读者的,而是作为一种自我解嘲的保护色,让角色的悲剧性显得更为立体和真实。你甚至会觉得,那些故事里的街道、咖啡馆,都仿佛拥有了生命和记忆。它成功地将宏大的社会议题,内化为一个个鲜活个体最私密的挣扎,读起来毫不费力,却在心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让人在喧嚣中反思自己是否也成为了一个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孤儿”。
评分我很少遇到能让我产生强烈代入感的书籍,但这本书做到了。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或明确的救赎,而是诚实地呈现了生活本来的面貌——充满了不确定性与灰色地带。作者对白描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寥寥数语,人物的性格、背景乃至当时的处境便跃然纸上。这种简洁的力量,比起冗长的心理描写更为有效。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与一位老朋友进行一次深夜的倾诉,坦诚、直接,不加修饰。它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情感空间,让读者得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桎梏,进入一个可以直面内心脆弱角落的世界。看完后,我的情绪是平静的,但内心却像是经过了一场洗礼,对生活中的微小善意和不期而遇的温暖,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珍惜。这是一部需要用心去感受,而非仅仅用眼睛去“看”完的小说。
评分作者简介
评分布鲁克林孤儿 hao
评分我不得不感叹,那时候的小说家还有雄心,敢于着手疑难问题。大革命在雨果看来,是人民站起来了,虽然在《悲惨世界》里,谁才算“人民”相当含混。如果特权阶级因为罪恶累累不配做人民,那么受压者是否就一定双手干净?谁赋予一个人剥夺另一个人性命的权力?“雅克”们摇身一变成了大群,拥有断头台就有力量,这从血泊里成长起来的新的施暴者,他们还是人民吗?雨果把革命看成扫荡黑暗的力量,而在狄更斯笔下,大革命则是“人类的想象力创造出无数贪得无厌、不知餍足的妖魔鬼怪”中之一,象征大革命的东西是断头台,有意思的是,对此狄更斯并没有展开论述,而只是轻轻说一句:“它取代了十字架。”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如果我不愿意,这大概就是仗势欺人了,但事实上我想进去都想得发疯了。展厅里空无他人的每一分钟都极其宝贵。那扇门的上缘只有我的膝盖高。我爬了进去,打开充当展览边墙的海蓝色背景板上的活门,接着滑进了画面之中。碗形的海底长而平缓,是涂抹过颜色的石膏,我弯着膝盖沿坡跑了下去,望着玻璃另一侧目瞪口呆的吉尔伯特。游泳的企鹅或是固定在从后墙上伸出的长杆上,或是悬挂在海面的塑料波浪下,海面此刻已是我头顶上低矮的天花板了。我爱抚着最近的一只企鹅,这只企鹅吊得很低,正在潜水追捕美味鲜鱼。我拍拍企鹅的脑袋,揉揉它的咽喉,像是在帮它吞咽药丸。吉尔伯特笑得直打滚,以为我在向他表演喜剧,但事实上我被一阵温柔而又躁动的冲动所征服,必须去爱抚那只僵硬悲哀的企鹅。接下来,我必须去触摸每一只企鹅,至少是我够得到的每一只--有几只我够不到,它们站在浮冰上,被海面挡在了另外一侧。我跪在地上四处移动,满怀爱意地挨个抚摸那些游泳的鸟儿,最后才穿过铜门逃了出来。吉尔伯特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我看得出来。我成了他心中无所不能的小子,敢肆意妄为的小子。当然了,他既对也错,因为摸到第一只企鹅之后,我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不知为何,这引出了一连串的事件,使得他越来越信任我。我很疯狂,但又很温顺,很容易受到胁迫,这让我成了吉尔伯特理想中的仓库,用来存放他认为是疯狂念头的东西。吉尔伯特比别人早熟,喜欢打手枪,正在寻找介于其个人经验和一般校园常识之间的三角测量基准物。我做那档子事吗?有多频繁?一只手还是两只手?这样还是那样握?闭不闭上眼睛?有没有动过摩擦床垫的念头?我很认真地对待他的询问,但却无法提供他需要的信息--当时还不行。我的愚钝刚开始让吉尔伯特好生不爽,他有一两个星期假装从未提过那些问题,甚至压根儿不认识我,对我投来凶恶的目光,叫我晓得要是胆敢说出去就将有极大的痛苦等在前头。然后他会突然回来,比之前更急切。试试看吧,他这样说,没那么难。我会看着,如果你弄错了我就纠正你。和博物馆那次一样,我听从了他的话,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我无法用对待企鹅的那种温柔对待自己,至少当着吉尔伯特的面做不到(尽管事实上他催动了我对自己的私密探索,这很快就变得相当耗费精力),吉尔伯特又不高兴了,把我吓得魂不附体。两三个回合以后,这个论题就被永远搁置了。然而,暴露隐私的影响却留存了下来,成为我们之间宛若幽魂的维系。 敏纳这辆货车里的最后一个男孩是丹尼·芬克尔,他是个赝品,只不过肤色很白而已。丹尼欢欢喜喜、轻松自在、发自肺腑地融入了圣文森特的大部分人中。他以自己的方式赢取了不亚于托尼的尊重(自然也得到了托尼的尊敬),既没有吹牛说大话,也不需要惺惺作态,大体而言连嘴巴都不用张开。他真正通晓的语言是篮球,可这位运动健将精神太过紧绷,动作太过流畅,在屋内、教室里就显得分外憋屈。他一开口就要嘲笑我们的热情、我们显露的“不酷”,但总有些心不在焉,仿佛他的脑子另有盘算,还在琢磨怎么换手过人,怎么优化步法。他听“放克疯”,听“浮雕宝石”,听“扎普”①,和孤儿院的其他孩子一样,也飞快投入了饶舌乐的怀抱,但每逢他钟爱的音乐奏响,他从不会跳起舞步,而是抱着胳膊站在那里,随着节拍瞪眼撅嘴,富有表现力的臀部一动也不动。丹尼生活在半空中,他既不黑也不白,既不挨揍也不打人;帅归帅,但不受女孩这个念头侵扰;功课一塌糊涂,但每门课都能蒙混过关;偶尔挣脱地球引力的束缚,漂浮在圣文森特的篮球框上那堆烂铁链和人行道之间。折磨托尼的是自幼失散的意大利家庭,他坚信他们会回来找他;丹尼却像是七八岁就离家出走,加入了街头篮球比赛,一气打到十四岁,直到敏纳开着货车来的那一天为止。 莱诺尔是布鲁克林圣文森孤儿院的孤儿,从小就患有罕见的妥瑞氏症,这个疾病使得他产生狂吠、拍打、自言自语等异常行为。被视为怪胎的他和另外三个男孩被挑选出来,为敏纳·弗兰克的出租车行兼侦探社工作。那种异于其他孤儿的优越感,让这四个男孩成为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忠心耿耿地效忠于敏纳·弗兰克。有一天,弗兰克被杀,莱诺尔这四个孤儿的世界也被整个翻转过来。一连串问题接连发生,各种各样的人物、黑人侦探、禅堂里的老师、日本黑帮等相继出现,他们四个人之间不断发生磨擦。莱诺尔这个怪胎开始不顾一切地游走在各种人物之间,发誓要解开谜团。
评分帮别人买的,当时在做活动,又有一张满200减100的券。三百几的书只花了一百几就买到了...
评分书挺好,印刷纸张都不错。内容不赘述。
评分对这次的包装相当不满意,几本书就放在一个纸盒子里面寄过来了,里面一点填充物都没有。塑封薄膜有破损,其他尚可。
评分运输保存比较好,书没的说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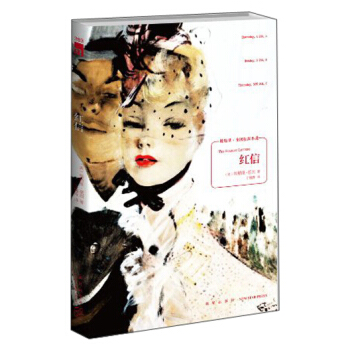
![召唤死者 [Call For The Dea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99821/53ce2092Nc44f128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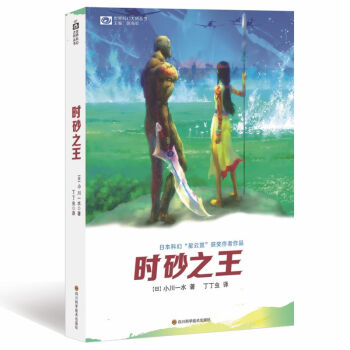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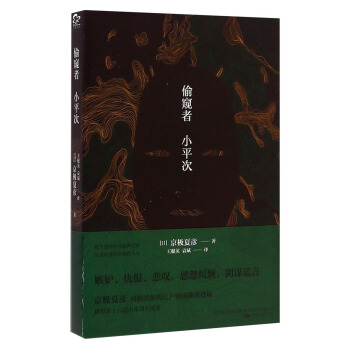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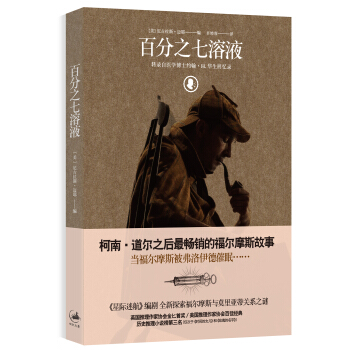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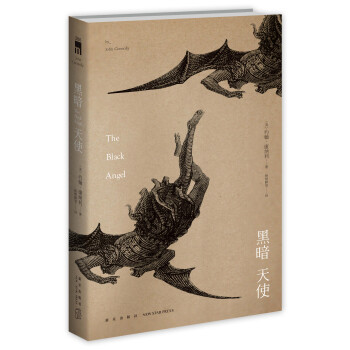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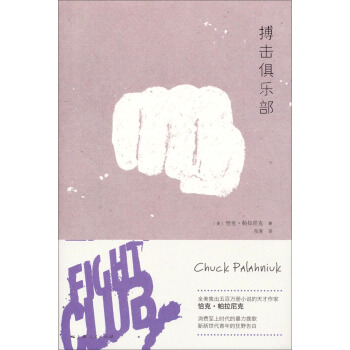
![首席女法医19:红雾杀人事件 [Red Mist]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8662/555557c1Nb209ad6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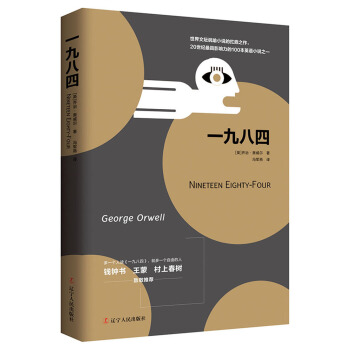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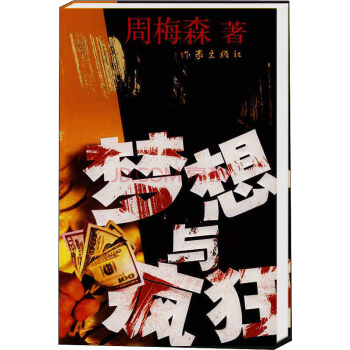

![纳尼亚传奇(套装共7册 英汉双语典藏版)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05435/58573400Nc18a005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