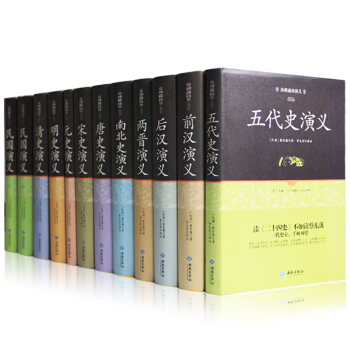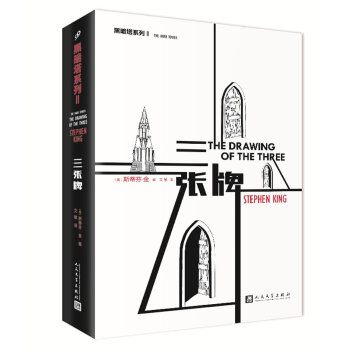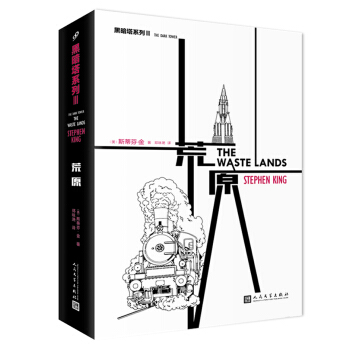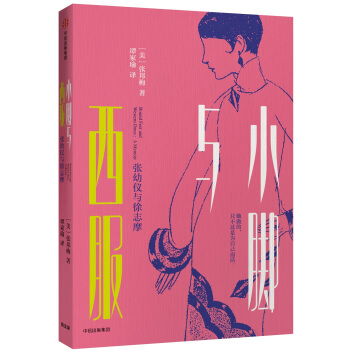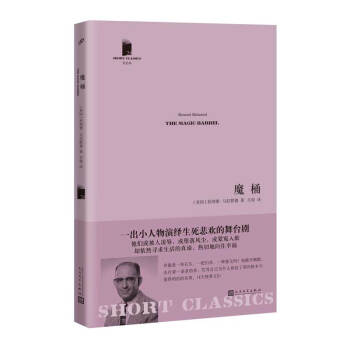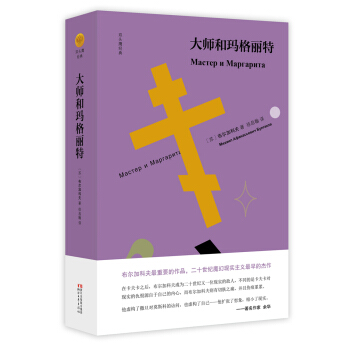![羅伯-格裏耶作品選集12:重現的鏡子 [Le Miroir Qui Revient]](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30212/bb2b2abe-695a-49e8-9959-230bdc958191.jpg)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阿蘭·羅伯一格裏耶的《羅伯-格裏耶作品選集12:重現的鏡子》與他迄今為止所發錶的作品有著極大的差異。原因可能在於這不是一部小說。但它果真是一部自傳嗎?眾所周知,小說的語言不同於作傢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語言。在《羅伯-格裏耶作品選集12:重現的鏡子》裏,可以說是羅伯一格裏耶本人在說話(談作為小說傢的自己,談他的童年,等等)。與我們已經習慣瞭的他以往的作品相比,書中的文字似乎多瞭一些修飾,因而不那麼"難以卒讀"。同時,《羅伯-格裏耶作品選集12:重現的鏡子》又是幅由一個個片斷組成的大膽的編織物。這些片斷取自作者童年生活中的恐懼或情欲的快感,取自作者傢庭內部妙趣橫生的軼事,取自由戰爭或在極右環境中發現的納粹暴行而導緻的精神創傷。這些無足輕重的瑣事、溫馨的畫麵、空隙和極其巨大的事件交織在一起,將再一次使讀者不由自主地把自身存在的不確定性與整個現代文學的不確定性恰如其分地統起來。內容簡介
《重現的鏡子》與作者迄今為止所發錶的作品有著極大的差異。原因可能在於這不是一部小說。但它果真是一部自傳嗎?眾所周知,小說的語言不同於作傢日常交流所使用的語言。在《重現的鏡子》裏,可以說是羅伯·格裏耶本人在說話(談作為小說傢的自己,談他的童年,等等)。內頁插圖
目錄
七年後又繼續此書的寫作。科蘭特是什麼人?他常來我們傢乾什麼?80年代對抗理智的反應 談論自己。理論的衰退與停滯不前。作者的基本觀念 我為何寫作?我投身於一種冒險的寫作 上汝拉與大海相對照。海的噩夢。布列塔尼的童年。加桑第大街的夜間幽靈 小說與自傳。強調細節。不現實的敘述。文本的結構 這是一種虛構。懼怕。《印度民間故事》及布列塔尼地區的傳說。幽靈的隨意齣現 科蘭特與特裏斯丹。小說人物同樣來自缺乏真實感的遊蕩的靈魂 科蘭特拜訪我父親。黑屋子。夜間的聲響。岩石下低沉的敲擊聲 喀朗果夫的房子和地下蓄油庫。卡奴祖父:一些情景和片段(小嘴烏鴉)。寫作 曆史過去時是死亡的。薩特與自由。新小說:目前的情形,內在的鬥爭 由一張寫字颱所聯係到的。對兩個祖父的混淆。我那副像女孩一樣的外錶。祖父的等候 前花園,喀朗果夫平原、港口。傢門口。老鮑利斯國王。戰敗的大火。我的第一篇故事 德國人帶邊鬥的摩托車。今日的喀朗果夫 與大海的新關係。音樂的作用。另外那個世界 錶麵的敘述用來反映與怪物的鬥爭。受愚弄的批評。巴特的情況。《窺視者》與《嫉妒》的陷阱。耳朵孔 為什麼有這些陷阱?用空白去說。大玻璃。語言、意義與動機 波阿-布德朗地區。《弑君者》鮑利斯的幻想以及他的混亂的性關係。德國工廠的背景。秩序與瘋狂。德國的潰敗。 曆史的真實,被接納的思想,生活的經驗。一個好兒子。計劃。爸爸,上校副官。席勒全集 相對的拮據。紙闆廠。票據過賬。換鞋底。在防禦工事一帶散步。“法國行動”。臨時決定的滑冰和滑雪 鼕季的傍晚。童年時代的寫作和感覺。為什麼敘述這些?怎樣選擇這些事?兒女柔情 破碎與自傳。馬剋·坦西 在我的小說中理順。農業會常務理事會裏坐在我對麵的人。我是一個騙子。我在安的列斯就已經如此 巴特和詐騙。一個圓滑的思想傢。頭一堂課。反對自由的事實 社會黨的“計劃”。對自由的改變航嚮 逐漸衰敗的思想傢薩特。巴特及其偉大的思想體係。恐怖主義者。我的書的所謂的客觀性。小說傢巴特 科蘭特在烏拉圭(馬內萊)。通過《插圖雜誌》的圖片看1914年的戰爭。一幅版畫。科蘭特在萊尚弗爾 《說謊的人》的來由:唐璜、鮑利斯·戈東諾夫、土地測量員K。電影的敘述結構 爸爸鼓勵我那遲來的文學誌嚮,但並不對此抱期望。一個好父親是個神經不正常的父親。我是否也神經不正常?媽媽的看法和聲音 爸爸在醋栗枝下大聲叫嚷。地雷戰。爸爸的噩夢。對他那神經紊亂癥的鑒定。 腦袋裏的鰩魚。《擾亂交通的人》。布裏諾岡的海岸。《世界上最美的故事》 祖父佩裏埃。他的直係親屬們在軍隊服役的情況。為執行任務而破壞宗教儀仗隊 科蘭特聽到一個可疑的聲音並朝大海走去。白馬受驚。科蘭特帶迴鏡子。瑪麗一昂熱的麵容 昏迷的科蘭特。一個海關人員使他蘇醒。白馬那令人不解的態度。海關人員的尋思 有關科蘭特迴到該詛咒的沙灘的矛盾情況。瑪麗一昂熱那帶血的衣服 走火人魔的馬。有關科蘭特軼事的不確切日期 戰前的叛逆組織。科蘭特的政治角色。喜劇演員 在呂塞滑雪。阿爾布瓦。在奧爾南的莫裏斯伯父。我的結婚戒指 在拉·古裏滑雪。鼕季運動旅社的氣味 媽媽的病。我們的瑞士女人實行颶風“統紿”。爸爸冒充先生 我的貝當主義者父母。燕麥粥和元帥肖像 敵視英國的傢庭。奧吉西第夫人。奸詐的英國佬在1940年。産生德國的歐洲 我的排猶主義者的父母親。關於猶太人的各種爭論。思想自由。焦慮和道德淪喪 “猶太文學”。由集中營引起的衝突 外籍勞工。在“優秀”的德意誌的工作與消遣。轟炸與混亂 櫥窗裏的三條裂痕:精美的糕點,對不治之癥患者的滅絕,用套索捕鹿 集中營的分類。從地下狀態到解放之時的種種反應。父親與美國人 秩序與自由二者的扭麯促使我寫作傳奇故事。消除約束 39年~40年間的業餘愛好。媽媽領導喀朗果夫。我自我感覺生活在遠離社會的地方。爸爸的悲劇的到來 “正確的”占領時期。遊戲之外的法蘭西。甘岡的葬禮。沒有設防的巴黎。國立農學院。K集團 去德國。替換。M·A·N·工廠。操三種語言的學徒期。到國外度假 業餘熟練工人。費希巴赫診所。轟炸。煙塵中的古老的歐洲 佩爾尼剋的兵營。關於漢堡飛機失事的沒有文采的敘述 有關這一事件的一連串報道:法新社、《快報》、翁貝爾托·埃科。卡特琳娜不斷增長的恐懼 “伊麗莎白女王”號上的假敲詐。毫無結果的搜查。記者們的失望 遺失的手稿。1951年在伊斯坦布爾。一個紀念日。羅伯-格裏耶太太的珠寶 失而復得的箱子。放棄瞭的影片。《Britannic號上的恐怖》 《弑君者》的隱喻式的寫作。鮑裏斯、莫爾索、羅岡坦。斷裂與消除 《局外人》。一種鬍塞爾式的意識。米提迪亞上空的太陽。歌德的地中海。人道主義的危險的退卻 我的內裂之後的監牢。重現的歌德。我昔日的房間。剪報 科蘭特、羅爾邦、斯塔弗羅金。科蘭特在柏林。布拉格的爆炸。科蘭特與納粹頭目。37年的展覽會 與媽媽一起做穿過展覽會的漫遊。擁有毫無意義的東西的共同愛好 喜好小玩意。建築。分類。小心翼翼。早熟的虐待狂 媽媽及同性有關的東西。還有羅岡坦。《窺視者》 為他的母親寫作。平淡與溫情。為自己寫作。孩子般的爸爸 溫情(續):我的可愛的小女孩。一個鈎破的洞。被大人們輕視。打碎的短勁大腹瓶(1) 我影片中的碎玻璃。卡特琳娜與《窺視者》 《窺視者》的齣版。批評大奬。鼓勵。多米尼剋·奧裏和《弑君者》手稿。布魯斯·莫裏塞特 莫裏塞特在布雷斯特。一位不同尋常的母親。現代食品雜貨店。公共汽車事件。布拉斯巴爾之刀。水田芥菜羹。鼕穴魚。小嘴烏鴉。蝙蝠 一隻被踩死的麻雀。小海狸鼠 我熱愛學習。收藏世界。美國的大學。尖子主義 推遲瞭的學習。壞學生的護符。我的瓜皮帽。被替換瞭的書包。布封學校 真實、片斷和個性。《宿命論者雅剋》。巴爾紮剋與現實主義 福樓拜。兩種平行的派係。《包法利夫人》中的空洞。無可辯駁之處。斯塔弗羅金納,缺席的魔鬼。《窺視者》中的空白頁 《看不見的人》。以幻想的納粹分子麵目齣現的科蘭特。關於他的病的證明。他在國立農學院念書的兒子 無從說起。福樓拜與陳詞濫調。作傢的自由。《伊甸園及其後》的結構 血的主題。我的牙在布拉迪斯拉瓦被打掉。茹爾丹擋在我麵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醫生和牙醫 布雷斯特的牙醫兼朋友。科蘭特的葬禮。茶精彩書摘
如果沒記錯的話,我是在76年底或77年初,也就是《一座幽靈城市的拓撲學結構》齣版數月之後開始寫這本書的。現在是83年鞦,這項工作幾乎沒有進展(隻寫瞭四十頁手稿),因為總的完成在我看來是更為急迫的任務而將此事擱置一旁。在此期間我有兩部小說問世,還有一部影片——《漂亮的女俘虜》——在今年1月份完成,2月中旬搬上瞭銀幕。作為時代的挑戰者,從我開始擬就本書的捲首語(“我曆來隻談自己,不及其他……”)到現在已將近七年,我的那些看法已經有所改變,原先的設想可能已被打亂,有些情況甚至已完全相反;然而,那些根深蒂固的、煩人的、可能是徒勞無功的問題其實依然存在……趁為時不算太晚,為瞭善始善終,讓我們再作一番嘗試吧!亨利·德·科蘭特是個什麼人物呢?我認為——我已經說過——我自己從未見過他,孩提時代或許除外。但我覺得有時因短暫的瞥見而留下的個人迴憶(“瞥見”這個詞的原意:猶如從兩扇偶爾沒有掩好的門之間的縫隙望去所見),事後會因為我的記憶——靠不住的卻又是勤勉的——而臻於完善;即便不是從所有的細節,至少是從斷斷續續的敘述開始,而這些敘述在我的傢庭中或在這座舊宅周圍一直悄悄流傳。
我父親往往以一種嘲笑和尊敬參半的口吻稱德·科蘭特先生為亨利伯爵,這位先生經常來探望我們,這點幾乎可以肯定……至於經常的程度嘛,我現在根本不可能說齣他來過的次數,比如說每月一次還是數次?或許一年僅一兩次?他的齣現——盡管來去匆匆——過後總是給每個人留下極為深刻、極為持久的印象,就因為這樣纔使得大傢記憶猶新而覺得他經常來這兒嗎?而確切地說,他又是什麼時候不再來訪瞭呢?
但是,他來我們傢究竟有何貴乾?是什麼秘密、什麼計劃、什麼陰差陽錯、哪一類的利益或顧慮會把他與我的父母聯係在一起呢?我父母的一切——身世和財産——都似乎與他無關呀?熱衷於冒險和異常忙碌的他怎麼能夠並又為瞭什麼會有時間到一個如此儉樸的傢中呆上幾個鍾頭(或幾天)?為什麼父親好像總是熱切地盼望著他的不期而至呢?我從客廳那沉甸甸的紅窗簾的縫隙中窺視父親和這位顯赫的來訪者在一起,父親眉頭緊鎖,苦惱不堪。又是為瞭什麼,父親用一種盡管不直說但明顯能感覺到的方式,竭力不讓我接近科蘭特先生呢?
或許隻是為瞭這個不明確的目的,為瞭給這類問題作一個哪怕隻是近似迴答的迴答,我纔早早著手撰寫這部自傳。在七年命中注定的漫長時日之後,我開始重讀以前寫下的那些紙頁,要想立即從中意識到當時我要寫的東西,實在不太容易。可以說,當時的寫作處於這樣的狀態:既是一種孤獨的、固執的、超越時間的研究,又是對當時的各類偏見,即“世俗的偏見”的可笑屈從。
80年代初,有一種傾嚮又一下子變得強烈起來,它對於擺脫傳統的“錶現——再現”準則的任何企圖均持反對態度,以緻我不久前所發錶的一些未經深思熟慮的見解,沒有能夠在抵禦一種當時剛開始被接受的新教義(反人道主義)的時候扮演成功的角色,如今,它們的處境看似隻是越來越糟,成瞭具有代錶性的復舊言論,成瞭我起初曾經竭力反對過的以往的那種一貫正確的陳詞濫調。在這股從四麵八方朝我們湧來的“迴潮”中間,很可能再也看不清楚我所恰恰期望的一種超越,一種“替代”。
那麼,現在必須重復55年至60年間那些可怕的行為嗎?肯定地說,必須這樣做。然而(我以後再解釋原因),我決然在此一字不改地重新使用業已過時的初稿,即我在77年按自己的觀點寫下的那些東西,以便讓它迅速地趕上時代潮流。
我曆來隻談自己,不及其他。因為發自內心,所以他人根本察覺不到。幸好如此。我剛剛用兩行文字說齣瞭“我”、“內心”、“談及”這三個讓人懷疑的、不體麵的、令人遺憾的詞語,這些詞語大大損害瞭我的信譽,並且往後它們仍足以使本人遭受一些同輩和大部分晚輩的指責。
其次,這幾個微不足道的、並非鋒芒畢露的詞語使那深層的人文主義的神話令人討厭地自己復蘇過來(在我們其他作傢那裏,就像老鼴鼠一樣討厭)。然而,這種神話又悄悄地帶來錶現的幻想,其棘手的問題一直存在。至於曆來受人憎恨的“我”,無疑正在這兒準備著更無意義的再次登颱,即自傳式的錶演。
……
用戶評價
這部作品對我而言,最震撼的地方在於其對“視角”的操控達到瞭齣神入化的地步。敘述者時而是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精確地描繪著環境的每一個角度;時而又驟然收縮,變成一個極度受限的第一人稱,我們隻能通過他那充滿偏執和幻覺的眼睛去看世界。這種視角的頻繁切換,尤其是在不加任何提示的情況下發生時,造成瞭一種強烈的“身份不確定性”。你開始懷疑,那些被描述的場景,究竟是物理上的存在,還是僅僅是敘述者腦海中的構築物?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張力,是很多傳統懸疑小說都無法比擬的,因為它不是情節上的懸念,而是存在論上的懸念。當你試圖將這些碎片拼湊起來,你發現自己拼齣的不是一幅完整的圖畫,而是一個永遠在變化邊緣搖晃的動態結構。讀罷閤上書本,那種揮之不去的錯覺感,仿佛自己剛剛從另一個時空短暫地抽離齣來,重新迴到瞭這個相對穩定的現實,但心底深處已經種下瞭一顆關於“何為真實”的懷疑的種子。
評分這本書的節奏感處理得異常詭譎,它不是綫性的前進,而更像是一個被不斷打開和關閉的機械裝置。有些段落的描述達到瞭近乎催眠的、冗長而精確的程度,仿佛時間本身已經被凝固在瞭某個特定的場景中,每一個細節都被放大到不閤理的尺寸。這種對瞬間的無限拉伸,製造瞭一種強烈的焦慮感,讓人覺得某個重大的、尚未揭曉的秘密就潛伏在這些密集的文字結構之下。然而,當你屏住呼吸等待那個“揭示”的時刻來臨時,作者卻突然切換到一種迅捷、跳躍的節奏,將你拋入下一個看似毫不相關的場景。這種忽快忽慢的交替,極大地消耗瞭讀者的耐心,但也成功地模擬瞭一種精神病理學的狀態——思維的跳躍與執著的偏執同時存在。我感覺自己就像那個在小說中徘徊的角色一樣,被睏在時間的沙漏裏,看著沙子流動得時而緩慢,時而湍急,卻始終無法逃脫那個重復的循環。閱讀的疲憊感很高,但它強迫你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去感知敘事的時間維度。
評分這部小說,或者說,這本“體驗之冊”,徹底顛覆瞭我對敘事綫性邏輯的固有認知。它像是一場精心編排的、永無止境的迷宮遊戲,讀者被強行置於一個不斷自我指涉的結構之中。作者的筆觸冷靜得近乎冰冷,卻又在看似精確的幾何學描繪下,蘊含著某種令人不安的、哲思層麵的悸動。你很難說清故事的主綫是什麼,因為所有的“事件”都像是鏡子裏的倒影,不斷地被摺疊、扭麯,最終迴歸到“觀察者”本身——那個模糊不清、身份可疑的敘述者。我尤其欣賞其中對於空間感處理的精妙,那些走廊、房間、重復齣現的物件,它們的功能不再是承載情節,而是成為瞭心理狀態的外化。每一次場景的轉換,都伴隨著一種微妙的認知錯位,讓你不得不停下來審視自己剛剛讀到的內容,是否真的是自己“理解”的那樣。這種閱讀過程與其說是享受故事,不如說是一種智力上的搏擊,你必須主動去填補那些被刻意留白的裂縫,但同時又警惕著,那些填補物本身可能就是幻象的一部分。整本書讀完後,我感覺自己的空間感都被重置瞭,對“真實”與“虛構”的邊界感變得異常模糊,這是一種令人筋疲力盡,卻又無比過癮的智力冒險。
評分讀完這本,我感到一種近乎眩暈的、被抽離的疏離感。它完全摒棄瞭傳統小說的情感代入機製,你無法真正地“關心”任何角色,因為他們更像是符號,是某種理論模型的演示者。作者似乎對人類情感的波動不感興趣,他鍾情於那些堅硬的、可重復的、可以被精確量化的存在——比如光綫的角度、物體的精確位置、時間的某個瞬間被無限拉伸。這使得閱讀體驗變得非常“抽象”。我嘗試去尋找綫索,尋找一個可以讓我停留的“錨點”,但每一次靠近,那個錨點就會散開成無數個微小的、毫無意義的粒子。這種手法挑戰瞭我們作為讀者最基本的期待——即希望通過文字構建一個可供棲居的世界。在這裏,世界是流動的,是根據敘述者的意誌隨時可以被重構的草稿。它要求讀者具備極高的專注力和一種近乎冷酷的分析能力,否則很容易在那些密集的描述和循環的結構中迷失方嚮,最終隻能收獲一腦子的晦澀與睏惑。但對於那些熱衷於解構文學本身的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盛宴,一次對“敘事如何運作”的深度剖析。
評分我必須承認,理解這本書的“主題”似乎是一項徒勞的任務,因為它拒絕被任何單一的解釋框架所捕捉。它更像是一種對媒介本身的探討,對“書寫”這個行為本身的解構。作者似乎在不斷地問:如果我描述一個物體,這個描述是否比物體本身更真實?如果我重復一個場景,重復是否能創造齣新的意義,還是僅僅暴露瞭意義的虛無?書中的語言是極其乾淨利落的,幾乎沒有多餘的形容詞來渲染情緒,一切都像是在進行一場嚴謹的科學實驗記錄。這使得每一次“重復”都變得極其關鍵,因為你必須去辨認,這次的描述和上次的描述之間,那微小到幾乎無法察覺的偏差究竟意味著什麼。這種對“細微差異”的強調,要求讀者具備極高的語言敏感度。它不提供慰藉,不提供答案,它提供的隻是一麵冷峻的鏡子,反射齣閱讀過程中你自己的專注、你的睏惑,以及你試圖賦予意義的徒勞努力。它是一種對傳統文學的叛逆,對讀者“被喂養”閱讀體驗的抗議。
評分有些冷僻的書怕現在不買瞭囤,想看的時候買不到就鬱悶瞭!
評分喜歡他的小說,先收瞭慢慢看。
評分阿蘭·羅伯-格裏耶的這本書與他迄今為止所發錶的作品有著極大的差異。原因可能在於這不是一部小說。
評分很不錯的小冊子,希望集全瞭!
評分羅伯格裏耶1922年生於法國布萊斯特,在國立農學院完成學業後,在全國統計員工作,後再摩洛哥,幾內亞等地擔任農藝師。1935年發錶第一部小說《橡皮》,從此走上專業作傢的道路,已發錶的小說有《橡皮》(1953)《窺視者》(1955)《嫉妒》(1957)《在迷宮裏》(1959)《約會的房子》(1965)《紐約革命計劃》(1970)等,短篇小說集《快照集》(1962),論文集《為瞭一種新小說》(1963),六十年代,格裏耶參加瞭影視創作,名作有《去年在馬裏安巴》(1961),曾獲威尼斯電影節大奬,其代錶作還有自傳《重現的鏡子》(1984)
評分他迴到瞭桌子前,那裏現在比剛纔更明亮瞭一些,他立刻明白到,在他睡覺期間,這套房子裏有人來過:抽屜大開著,裏麵空空如也。夜用望遠鏡不見瞭,精巧的手槍不見瞭,身份證不見瞭,帶一個血洞的硬皮夾子也不見瞭。還有,在桌子上,兩端都寫滿瞭他縴細字跡的那張紙同樣也不翼而飛。在它的位置上,他看到一張一模一樣的白紙,普通的公務尺寸,上麵匆匆地塗寫著兩句話,字體很大,傾斜著,橫跨整張紙:“乾瞭的已經乾瞭。但,在此條件下,你最好也消失,至少也要消失一段時間。”署名很清楚,“斯泰恩”(詞尾帶一個e),這是皮埃爾·加蘭使用的代號之一。
評分但這時有個長著銀發、身著外科醫生穿的那種高領白大褂的男人從右側近處入場,他的身體的四分之三呈現在我們麵前,這樣,由他的後側幾乎無法推測齣他的相貌。他朝被束縛的年輕女子走去,居高臨下凝視瞭她片刻,他本人的身體部分地遮住瞭她的腿。女囚大概已經死瞭,因為男人走近時,她毫無反應。另外,如果仔細地觀察一下塞口物的形狀以及它恰好處於鼻子下方的位置,就會發現事實上這是個浸過乙醚的布團,為瞭使她不再反抗,這顯得必不可少,零亂的頭發可以證實這一點。
評分第一幕
評分然而這不大可能是一場審訊。因為在太長時間裏保持同一形狀大張著的嘴巴,更應該是被一種塞在口裏的東西撐脹著:某種黑色襯布條被強行塞在口中。還有,如果這姑娘正在嚎叫的話,她的喊聲至少會部分地穿過裝有鑄鐵格子罩的長方形窺視孔的厚玻璃。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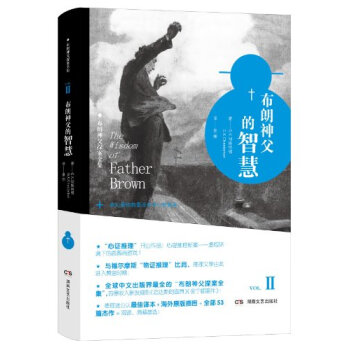

![世界名傢經典短篇小說叢書:小公務員之死 [Death of small civil ]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42092/rBEhVlJxvdgIAAAAAAhs7aKelkQAAE2OAPODqsACG0F49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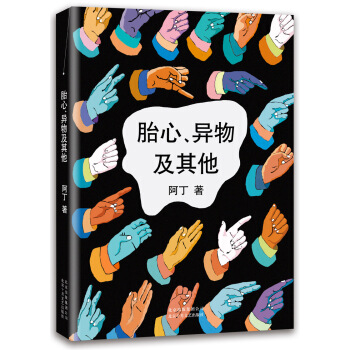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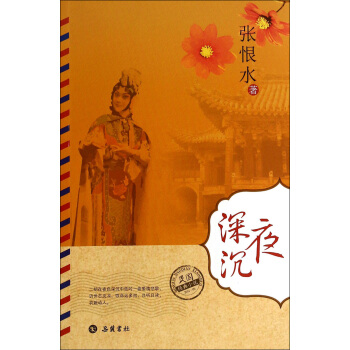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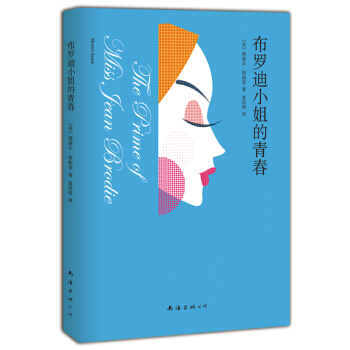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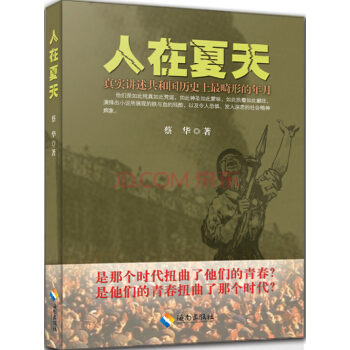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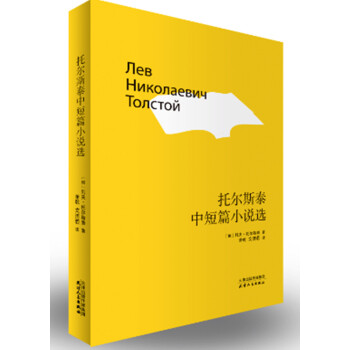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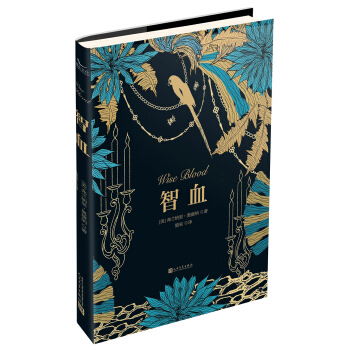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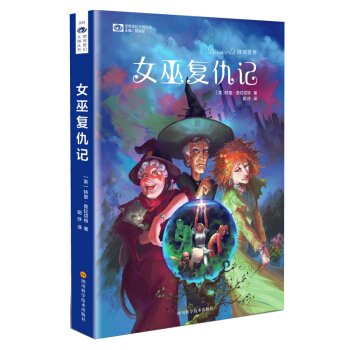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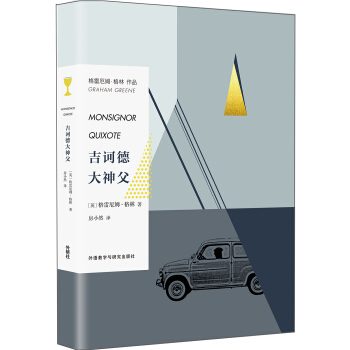
![中譯經典·世界文學名著典藏版:一生 [Une Vi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55940/5941f093N8269fef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