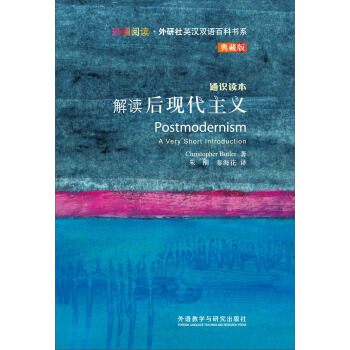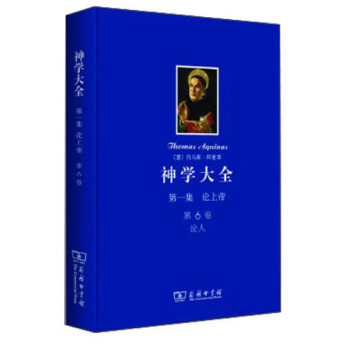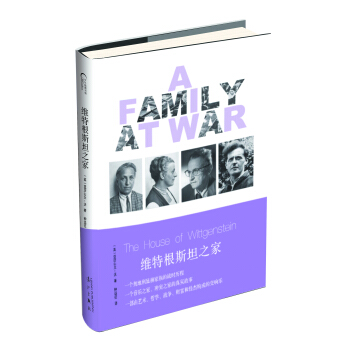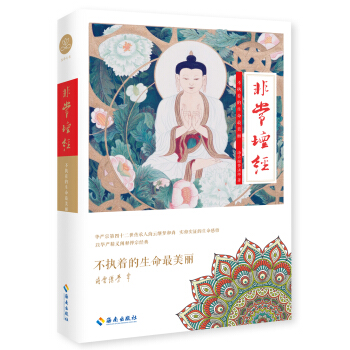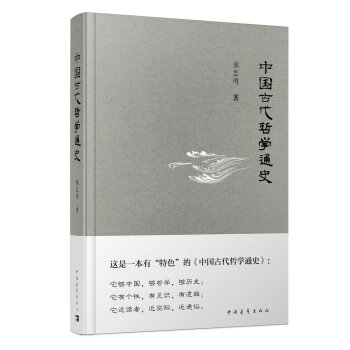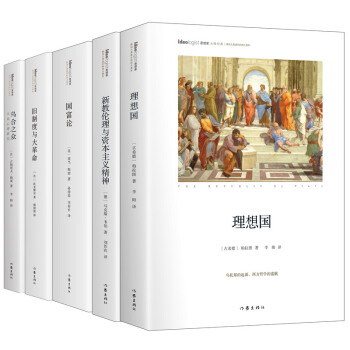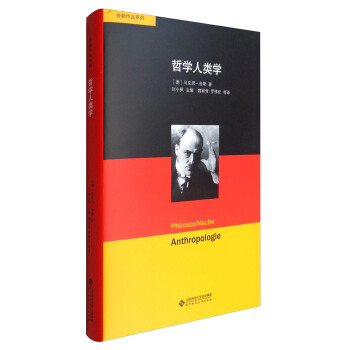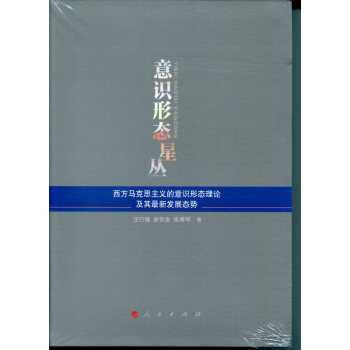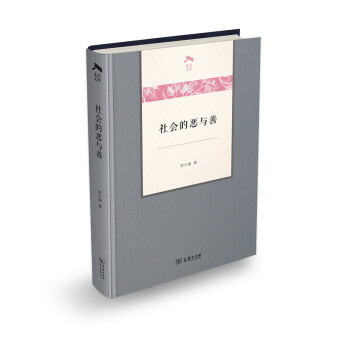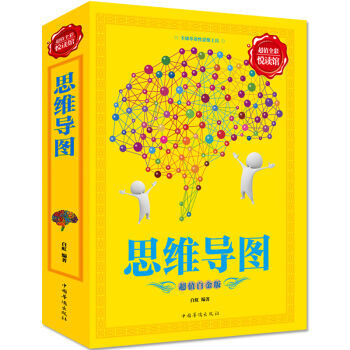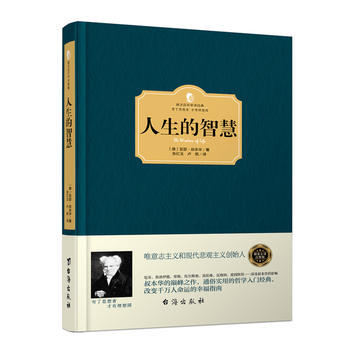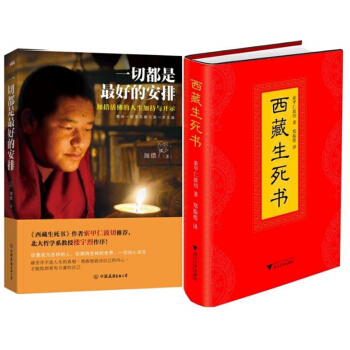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是作者杜维明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最后一部,记录了已界不惑之年的作者在生命旅途经历巨大转变的关头时的所思所想。书中所收都是1983一1985年作者从伯克利回到哈佛任教期间吐露的心声。内容简介
《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是作者早期学术生涯中的三部随笔作品中的最后一部,记录了已界不惑之年的作者在生命旅途经历巨大转变的关头时的所思所想。《杜维明著作系列·现龙在田: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1983-1985)》中所收都是1983一1985年作者从伯克利回到哈佛任教期间吐露的心声,所关怀的范围变成广义上的“文化中国”而不是地理、族群或政治定义下的狭义中国,所了解的儒家也是包括了东亚各国在内的“儒家文化圈”。
作者简介
杜维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曾应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的邀请参加为推动文明对话而组建的“世界杰出人士小组”。先后求学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8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目录
西樵偶语从认识、了解到批评、创造
一阳来复
建立自我的体上工夫
该学哪一样
沉默
观画断想
听的艺术
从祭祀涌现的艺术
——正餐酒会
爱那看不见而不死的事物
百寿人瑞
——为萧太夫人百年高寿而作
又见到了利科
苏黎士午餐
从异乡到失落
美国阳光带的兴起
以道德实践对治“共识”破产
寒流下的暖流
——高标理想的美国研究生
探讨“轴心时代”
从“轴心时代”看儒学兴起
站在“大家”这边的劳心者
伊尹之“任”
“实学”的含义
妻者齐也
儒家的女性主义
儒学在美国的初机
儒家伦理和东方企业精神有关吗?
介绍《海岳文集》
儒家的动力
——为纪念陆彬教授而作
一阳来复的儒学
——为纪念一位文化巨人而作
徐复观先生的胸怀
——为纪念一位体现了忧患意识的儒学思想家而作
孤往探寻宇宙的真实
——重印《尊闻录》
儒学访谈
工业东亚与儒家精神
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
儒家的现阶段发展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
——有关在中国大陆推展儒学的访谈
精彩书摘
从认识、了解到批评、创造最近常在报章杂志上看到“创造转化”这个醒目的名词。在美国的重点大学中,加州的伯克利是特别强调创造性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伯克利的研究成绩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常常有崭新的见地。和美国东岸传统深厚的学府相比,伯克利因为敢想敢做,往往出奇制胜,在尖端科技方面傲视群伦。然而,真能持久的创见绝非一时灵感所导致的突破;过分夸张独创的重要性,有时反而会斫丧引发洞见的真机。在伯克利任教的10年中,我亲炙过好几位神解卓特的师友之间的人物,但也接触到不少自己以为前无古人,其实不过靠廉价的怪论来提高个人声誉的投机分子。落实地说,创造转化是站在文化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把探索真理的视野更加扩展所作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是以知己知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和不顾学术及知识界已经达到的水准而自己闭门造车的做法大不相同。因此,体现创造精神,发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层的转化功能,必须从认识自己和了解对象两处起步。
“认识自己”是苏格拉底和孔子都重视的教学宗旨。苏格拉底以理性作用的阐明为训练学生的权法和孔子由德教启发后进的潜移默化代表轴心时代两种精神取向歧异而自成体系的思想,不过他们主张为己之学的意愿却是相通的。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并不容易;要想达到自知之明的境地,更需要长期不断的反省。这种应该在自家身心上贴切用功的学问是终身大事,比获得一技之长要难得多。可是,如果连认识自己的意愿都没有,那么在起步处就有偏差,将来即使侥幸有所建树,根基不坚固的危险则永远不能去除,更谈不上什么创造的转化了。
有了认识自己的能力,还须培养了解对象的工夫。这就牵涉到如何奋勉精进,以开放的心灵自勉自励的问题了。专靠骇人听闻的怪论来抬高身价的趋时者,常患律己甚宽而责人极苛的通病。他们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气势颇为雄壮,好像有一股真理都在这里荡漾的信念;到了抨击不太合口味的学说时,却摇身一变成为挑剔的能手,坚持论敌一无是处的立场。他们多半能说善道,但却和听的艺术了无关涉。在伯克利时,一位专攻日本思想史的同事曾对我说,要想评断一个知识分子是否拥有开放的心灵,最好的测验是看他对自己所厌恶的思潮有没有听的耐心。其实,在我所接触的同事中,有些连听的意愿和能力都丧失了,还说什么耐心!了解对象不是以自己主观的限制,对选定为目标的人物或思想作无理的要求。美国学术界对所谓强人策略,也就是虚构敌人的幼稚可笑,以显示自己的威风,已有警觉。如果一个学人宁愿采取这种无法提升智性交通的下策,明眼人一望即知,而且多半只从特殊心理的层次去理会,绝不轻易辩解,免得每况愈下成为莎翁所谓“全是音响和愤怒,毫无所指”的混乱。另一种借题发挥的策略,也可作为不能或不愿了解对象的例证。我曾深受其苦,不妨把自己的经验提供大家参考。加州大学出版社在1976年刊行了我所写的专门分析阳明少年时代的论文。在那本不到200页的小书里,我明确地指出研究阳明“知行合一”这一观念的哲学心理背景是我撰稿的目的所在。一位兴致勃勃的读者写了一篇数千言的书评,完全不顾我的立言宗旨,更不讨论我运思途径的得失,却把他自己积年累月想要倾吐的学术意见和盘托出。编者要我回应,我拒绝了,但心里不免有些哑巴吃黄连的滋味。
其实,认识自己和了解对象是相辅相成的两条管道,都是滋养开放心灵不可或缺的命脉。儒家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不仅表示成人之美的恕道,也是为了尽己的忠道而发。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为了体谅别人才提出了解对象的价值。
……
前言/序言
《三年的畜艾》(志文出版社,1970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龙鹰之旅:从哈佛回归东海的认同和感悟(1966—1970)》——编者注)宣泄了20世纪60年代旅美求学的情怀,《人文心灵的震荡》(时报书系,1976年;本次再版书名改为《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伯克利十年(1971一1981)》——编者注)吐露了20世纪70年代浅尝施教滋味的感触。这里所收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自觉地为儒学创造生机所作的反思。其实,30多年前在建国中学读书的时期,就因受周文杰老师的启蒙,而有志于儒学探究;1957年考进东海大学,跟随牟宗三及徐复观两位老师一窥孔孟堂奥,也是为成全这意趣而作的存在抉择。可是,在北美求学任教的28年,虽然童心未泯,所走的思想道路却很曲折。
《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联经,1989年)刊行之后,面临海内外各种论说的挑战,笔者开发传统的精神资源,让儒家的源头活水流向世界的意愿更强,而且更迫切地感到重新认识和了解儒家是为“文化中国”创造崭新的价值领域所不可或缺的思想事业。在这种心境里校读以“西樵偶语”为标签的30篇文字,便觉得每篇都只点题而已,都有重新起步“详为之说”,以阐明主旨的必要。但既然是副刊短篇,点题的笔法是难免的。在这里我只希望读者谅解:设法从有限的文字去捕捉那多元多样但又坚守凝定的自我意识吧!“儒学访谈”所收的四篇,因为是根据对话的实录,而且通过删节或摘要的形式见诸海峡两岸的报章杂志,应该算是“儒学论说”(Confuciandiscourse)的公产了。不过,必须申明,“访谈”是严肃的课题;即使空口腾说不必像笔耕那样句句皆辛苦,其困难度却常常超过书写文字,因为出口的声浪必须经过“入人耳”而且还能“心通”之后才成为真正的信息。让自己珍爱的信息通过知音者的“听德”传播给广庭大众不仅要靠信念,也要有几分勇气。我希望读者正视“访谈”所提出的构想,充分利用这份公产并积极参与论说。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如同老练的酿酒师在精心调配风味各异的佳酿,每一章的笔触和侧重点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韵味。有些篇章结构严谨,逻辑推演如同精密的钟表运作,每一个论点都环环相扣,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构建宏大理论体系的功力。而另一些章节则更为灵动,仿佛是学术研讨会上的精彩辩论实录,充满了活力和即兴的智慧火花,这种鲜明的对比,极大地丰富了阅读的层次感。我特别欣赏作者在阐释艰深概念时所采取的耐心和清晰度,他从不傲慢地将读者撇在一边,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邀请我们一同进入他构建的思想迷宫,并细心地提供地图。这种对读者心智的尊重,是很多当代学术著作所欠缺的宝贵品质。
评分这套书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其强烈的“在场感”。它不是一本沉睡在书架上的历史陈迹,而是仿佛作者正坐在你对面,用他那富有穿透力的目光,与你进行一场关于人文精神核心价值的深度对话。那些关于“选择”与“坚守”的论述,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位学者在特定历史关口所必须承受的重量与责任感。能够感受到作者在学术道路上所经历的挣扎、坚持与最终的释然,这种情感的真实性,使得冰冷的理论探讨也充满了人性光辉。它让我们意识到,每一次学术的推进,都凝聚着个体生命的努力与抉择,这远比纯粹的知识堆砌更具感染力。
评分从整体的阅读感受来看,这套文集更像是一部“方法论的教科书”,它教我们如何“看”世界,而非仅仅教我们“看什么”。作者对不同学派思想的吸收与批判性转化过程,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治学示范课。他巧妙地将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学术传统熔于一炉,形成了一种既根植传统又不泥古不化的独特声音。我发现自己被引导去重新审视一些过去看似板上钉钉的结论,并开始质疑那些被普遍接受的简化叙事。这种由内而外的颠覆性体验,是阅读高水平学术著作最令人兴奋的部分。它挑战了读者的舒适区,迫使我们在思想上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校准”。
评分品味这套文集,我体会到了一种难得的“学术的韧性”。它所涉及的议题,无一不是关乎文化身份、知识传承的根本性问题,它们穿越时空,至今仍未有终极答案。作者在处理这些“大问题”时,展现出的那种不急于求成、不满足于表层解答的求索精神,着实令人敬佩。他似乎深知,真正的智慧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在不断的打磨、修正与迭代中缓缓显影。因此,即便是那些略显晦涩的段落,也蕴含着深厚的思考积淀,需要读者静下心来,一同参与到这场没有终点的思想探险中去。这是一套值得反复阅读、常读常新的宝典。
评分读完这本厚重的文集,我仿佛跟随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漫步。书中的论述,无论是对古典文本的细致剖析,还是对当代文化现象的深刻反思,都展现出一种罕见的学识深度与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一些关于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如何重塑与转化的观点,更是激发了我极大的思考兴趣。作者在处理复杂议题时,那种游刃有余的思辨过程,让人不禁为之折服。他并非简单地复述前人观点,而是总能从中提炼出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切入点,构建起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知识桥梁。这种跨越代际的对话能力,使得这部作品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像是对我们当下精神困境的一剂良方。阅读体验中,时不时会有茅塞顿开之感,仿佛被引领至一片思想的旷野,自由呼吸。
评分京东一如既往的好用,希望更多活动
评分犯罪片本来是商业电影的重要类型,因为它最方便营造正邪之间的戏剧冲突,将人物命运置于激烈的环境里,在跌宕起伏的剧情中满足观众暴力宣泄的心态。但是犯罪片一遇到中国的现实,就成为死路一条,被套上笼子,举步维艰地前进。所以,一旦遇到这类题材,创作者就赶紧跑回民国时期的上海滩去寻找隐身衣。但问题是,这种时代的跨越容易造成布景和美术的困难,如果不了解当初的时代面貌,就很容易闹笑话。《给野兽献花》一开始就用字幕交代这是1946年的上海,但是人物穿的格子衬衫、女人的筒靴、贴罚单的警察、歌舞厅里一口京腔的老板等细节,明显就是我们当下的城市景象。这种环境的错乱造成了陌生化效果,就像穿着西装唱京剧一样,总有别扭的感觉。
评分这本书所收的31篇曾以“西樵偶语”发表的散文和4次访谈记录,都是1983—1985年在哈佛任教时吐露的心声。
评分在康桥耕耘儒学论述的抉择
评分你要对伴在你身边的那个人说爱。你多久没对他说爱了?你多久没有像热恋中一样,为讨他的欢喜,而精心准备一份礼物?你模糊了他的生日。你忽略了他的喜好。你不记得他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裳。他添了皱纹没?他有白发了吗?他最近的心情好不好?这些你统统不知道。你对风对月说爱,却懒于对他说。你们本有多少良辰美景好度,你生生弄丢了。因为亲近,所以漠视。现在,你想起他,心忽然很疼痛。
评分我没有别的意思,其实,我只是想说,我们中国自己应该拍一部真实的万历援朝战争实录,也可以和韩国人一起拍,但前提是最大程度地接近历史。如果不能,就自己拍,而真正的历史是:朝鲜在大明的帮助下,终于没有灭国,并严重地挫伤了日本人在朝的一次次战争企图,最后,丰臣秀吉死了,露梁海战中,中朝两国将士齐心戮力共同阻击了想要逃跑的日寇。这场战争涌现出了一批时代英雄,是他们挽救的朝鲜,这其中包括中国的李如松、陈璘、麻贵、邓子龙,还有朝鲜的李舜臣。
评分假如生命明天结束
评分如果去掉影像细节上的粗糙,单纯从故事本身来看,《给野兽献花》其实是非常精彩的。电影铺展了两条斗智线索,一条是警察与黑帮的“卧底与反卧底”的斗争,一条是堂主与夺权者的“利用与反利用”的斗争。这样便形成了三股势力,李光辉既要面对警察的调查,同时还要面对熊五(高捷)的算计。由于电影对警察形象进行了很大的丑化和戏谑,他们既呆傻又胆怯,所以李光辉最大的敌人其实是熊五以及想要夺位的胜虎。这样的故事架构非常有意思,如果再进行一些细腻加工,增强复杂性,就能成为一部完整的剧情片。但这毕竟是一个新导演的作品,气势和手段还不成熟。
评分老公买的,他说不错,书不错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