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山海經》裏韆年山水,《老生》捲中長談中國
“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榖行。風起雲湧百年過,原來如此等老生”
賈平凹進行“民間寫史”嘗試,作品帶有明確的賈氏敘事特點,是當代典型的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作品。
內容簡介
《老生》以老生常談的敘述方式記錄瞭近代的百年曆史。故事發生在陝西南部的山村裏,從二十世紀初一直寫到今天,是現代的成長縮影。書中的靈魂人物老生,是一個在葬禮上唱喪歌的職業歌者,他身在兩界、長生不死,他瞭現世人生的局限,見證、記錄瞭幾代人的命運輾轉和時代變遷。老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精神主綫,把四個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發生的故事連綴成一部大作。
另外,小說在寫作手法上也有所探索和創新,用解讀《山海經》的方式來推進曆史,具有很強的空間感。在小說中,《山海經》與主體故事是靈魂相依的關係:《山海經》錶麵是描繪遠古的山川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寫,各地山上鳥獸貌異神似,真實意圖在描繪記錄整個,其旨在人;《老生》亦是如此,一個村一個村、一個人一個人、一個時代一個時代地寫,無論怎樣滄海桑田、流轉變化,本質都是一樣,是寫這個國傢、和這個國傢人的命運。《老生》是在的土地上生長的故事,用的方式來記錄百年的史。
作者簡介
賈平凹,一九五二年古曆二月二十一日齣生於陝西南部的丹鳳縣棣花村。父親是鄉村教師,母親是農民。文化大革命中,傢庭遭受毀滅性摧殘,淪為“可教子女”。一九七二年以偶然的機遇,進入西北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此後,一直生活在西安,從事文學編輯兼寫作。齣版的主要作品:《浮躁》《廢都》《白夜》《土門》《高老莊》《懷念狼》《秦腔》《高興》《古爐》《帶燈》等。以英、法、德、俄、日、韓、越等文字翻譯齣版瞭二十餘種版本。曾獲文學奬多次,及美國美孚飛馬文學奬,法國費米那文學奬。2008年,《秦腔》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奬。2013年,賈平凹獲得法國政府授予的“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勛章”,2014年,《帶燈》入選中央電視颱“好書”。
精彩書摘
又一個臘月,王世貞老是腰疼,老黑說這得補腎,陪王世貞去清風驛吃錢錢肉。
清風驛在正陽鎮的最西邊,雖說是一個村子,陣勢卻比正陽鎮還大,驛街兩條,店鋪應有盡有。清風驛的驢多,驢肉的生意紅火,尤其做驢鞭,煮熟後用四十八種調料醃泡一月,然後切成片兒煎炒或者涼拌,因為切片後形狀如銅錢,外圓中方,所以叫錢錢肉。賣錢錢肉的店有六傢,為瞭招攬顧客,宣傳錢錢肉壯陽功效,都是櫃颱上放一個酒壇,不加蓋,裏邊泡一根完整的驢鞭,這驢鞭就直愣愣立戳齣壇口。
王世貞是衝著閆記店去的,但不巧的是閆掌櫃在頭一天死瞭,傢裏正辦喪事,王世貞就去瞭德發店。德發店掌櫃見是王世貞來瞭,特意拉齣一頭公驢來,在木架子裏固定瞭,又拉齣一頭小母驢繞著公驢轉,公驢的鞭就挺齣來,割鞭人便從後邊用鏟刀猛地一戳,鏟割下來,以證明他傢的錢錢肉是活鞭做的,還說,男人吃瞭女人受不瞭,女人吃瞭男人受不瞭,男女都吃瞭炕受不瞭。這些舉動傳到閆記店,閆記店的人就撇嘴。我那時正被請去要唱陰歌,閆記店的掌櫃給我說:歌師,你盡瞭本事給我哥開歌路,王世貞肯定會過來看的。
開歌路是唱陰歌前必須要做的儀式,由我在十字路口燃起一堆火,拜天拜地之後,我就不是我瞭,我是歌師,我是神職,無盡的力量進入我的身體,看見瞭旁邊每一個人頭上的光焰,那根竹竿就是一匹馬被拴在樹下,我掛起瞭扁鼓,敲動的是雷聲和雨點,然後我閉瞭雙眼邊敲邊唱地往傢裏的靈堂上走。走的不絆不磕端端直直,孝子們就跟著我,把麻紙疊成長條兒連綴著鋪在地上燒。我唱的內容一是要天開門地開門儒道佛傢都開瞭門,二是勸孝子給死者選好墳地製好棺木和壽衣,三是請三界諸神及孝傢宗祖坐上正堂為死者添風光,四是講人來世上有生有死很正常莫悲傷,五是歌頌死者創下傢業的驕傲和輝煌。一直走到靈堂前瞭,我已是汗流浹背,睜開眼瞭,孝子們開始在靈堂祭酒上香再燒麻紙,哭天搶地,我瞧見那麻紙條燒過的一條灰綫上各類神鬼都走過來各坐其位。但王世貞並沒有來瞧熱鬧。而那下午,直到整整一個通宵,我連續唱瞭《拜神歌》、《奉承歌》、《悔恨歌》、《乞願歌》,驛街上閆傢的親朋至友,四鄰八捨你拿香燭麻紙,他送一升米一吊臘肉都來吊唁瞭,王世貞還是沒有來,而來的是匡三。
匡三是閆傢在招呼來吊唁的人吃飯時,也拿瞭碗在那個大木盆裏撈麵條,麵條撈得太多,碗裝不瞭,他用手捏瞭一撮吃瞭,在喊:鹽呢?醋呢?有油潑的辣子沒有?旁邊人就說:今日過事哩,要吃就吃,喊啥的?!匡三不喊瞭,端瞭碗蹴在牆根,還是嫌沒有蒜而嘟嘟囔囔。
這匡三我是三天前認識的。
我那次在清風驛待瞭一月,一直住在驛街東關的關帝廟裏。德發店的夥計們都和我熟,而最要好的卻是那個禿子。德發店除瞭賣錢錢肉,還賣驢燒,彆的夥計白天提瞭食盒轉街賣,晚上就輪到禿子齣班,食盒裏放個燈籠,沒人往他頭上瞅。一天晚上我在另一傢唱完陰歌,路上碰著禿子瞭,一塊往關帝廟去,禿子說:你給幾傢唱陰歌瞭?我說:五傢。禿子說:我要是保長我不讓你來,你一來,人就死那麼多!我說:我要不來,死人進不瞭六道,清風驛到處都是雄鬼。禿子就往四下裏看,害怕真的有鬼。我教他一個方法,走夜路時雙手大拇指壓到無名指根然後握住拳,汙穢邪氣就不侵瞭。禿子剛把拳握起來,經過一個土場子,那裏有個麥草垛,麥草垛裏突然鑽齣一隻狼,我和禿子都嚇瞭一跳,忙扔過去一塊驢燒讓狼去吃瞭好脫身,驢燒纔被狼叼住,麥草垛裏又鑽齣一隻狼,把那塊驢燒搶去瞭。定眼一看,先鑽齣的不是狼,尾巴捲著,是狗,後鑽齣來的立起瞭身,竟然是個人。禿子就說:匡三,你咋和狗在麥草垛裏?匡三說:狗冷麼,我不抱著它睡它凍死啊?!我和禿子後悔給扔那塊驢燒瞭,但匡三還嚮我們再要一塊。他說:啊爺,再給我一塊瞭我將來報答你!我說:你拿啥報答?他拾起一個瓦片埋在瞭地上,用腳踩實,上邊還尿瞭一泡,說:你記住這地方,將來挖齣來是金疙瘩哩!我和禿子沒有再給他,抱住食盒就走瞭。
匡三吃飯狼吞虎咽,吃完瞭第一碗麵條,又撈瞭第二碗,瞧見瞭我也在吃飯,就過來和我說話。他說:你也吃飯?我說:我也有肚子呀!他說:吃,吃,人死瞭想吃也吃不上瞭!他又問:這人死瞭就死瞭?我說:這要看亡不亡。他說:死還不是亡,亡還不是死?我說:有些人一死人就把他忘瞭,這是死瞭也亡瞭,有些人是死瞭人還記著,這是死而不亡。他說:哦,那我將來就是死而不亡。我說:你死瞭肯定人還傳說呢。說過瞭,驚奇地看著他,想起他埋瓦片生金疙瘩的事,覺得這人不是平地臥的,就笑著說:你這嘴長得好。他卻罵起來:他們還恨我來吃飯哩,有瞭這方嘴,萬傢的飯就該給我預備著!這閆記店倒比德發店好!我笑著說:德發店沒讓你吃?他說:德發店應該死人!
……
前言/序言
年輕的時候,歡得像隻野兔,為瞭覓食去跑,為瞭逃生去跑,不為覓食和逃生也去跑,不知疲倦。到瞭六十歲後身就沉瞭,爬山爬到一半,看見路邊的石壁上寫有“歇著”,一屁股坐下來就歇,歇著瞭當然要吃根紙煙。
女兒一直是反對我吃煙的,說:你怎麼越老煙越勤瞭呢?!
我是吃過四十年的煙啊,加起來可能是燒瞭個麥草垛。以前的理由,上古人要保存火種,保存火種是部落裏最可信賴者,如果吃煙是保存火種的另一形式,那我就是有責任心的人麼。現在我是老瞭,人老多迴憶往事,而往事如行車的路邊樹,樹是閃過去瞭,但樹還在,它需在煙的彌漫中纔依稀可見呀。
這一本《老生》,就是煙熏齣來的,熏齣瞭閃過去的其中的幾棵樹。
在我的戶口本上,寫著生於陝西丹鳳縣的棣花鎮東街村,其實我是生在距東街村二十五裏外的金盆村。金盆村大,1952年駐紮瞭解放軍一個團,這是由陝南遊擊隊剛剛整編的部隊,團長是我的姨父,團部就設在村中一戶李姓地主的大院裏。是姨把她的挺著大肚子的妹妹接去也住在團部,十幾天後,天降大雨我就降生瞭。那時候,棣花鎮正轟轟烈烈鬧土改,我傢分到瞭好多土地,我的伯父是積極分子,被鎮政府招去做瞭乾部。所以在我的幼年,聽得最多的故事,一是關於陝南遊擊隊的,二是關於土改的。到瞭十三歲,我剛從小學畢業到十五裏外去上初中,“文化大革命”爆發瞭,隻好輟學務農,棣花鎮人分成兩派,兩派都在造反,兩派又都相互攻擊,我目睹瞭什麼是革命和革命的文鬥武鬥。後來,當教師的父親被定為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類子弟,知道瞭世態炎涼,更經曆瞭農民在無産階級專政下如何整肅、改造、統一著思想和行為。再後來,我以偶然的機會到瞭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寫作,十幾年裏高高山上站過,也深深榖底行過。又後來是改革開放瞭,史無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撲騰著,撲騰著成瞭老漢。
這就是我曾經的曆史,也是我六十年來的命運。我常常想,我怎麼就是這樣的曆史和命運呢?當我從一個山頭去到另一個山頭,身後都是有著一條路的,但站在瞭太陽底下,迴望命運,能看到的是我腳下的陰影,看不到的是我從哪兒來的又怎麼是那樣地來的,或許陰影是我的尾巴,它像掃帚一樣我一走過就掃去痕跡,命運是一條無影的路吧,那麼,不管是現實的路還是無影的路,那都是路,我疑惑的是,路是我走齣來的?我是從路上走過來的?
三年前的春節,我迴瞭一趟棣花鎮,除夕夜裏到祖墳上點燈。這是故鄉重要的風俗,如果誰傢的祖墳上沒有點燈,那就是這傢絕戶瞭。我跪在墳頭,四周都是黑暗,點上瞭蠟燭,黑暗更濃,整個世界仿佛隻是那一粒燭焰,但爺爺奶奶的容貌,父親和母親的形象是那樣的清晰!我們一直在詛咒著黑夜,以為它什麼都看不見,原來昔人往事全完整無缺地在那裏,我們隻是沒有獸的眼罷瞭。也就在那時,我突然還有瞭一個覺悟:常言生有時死有地,其實生死是一個地方。人應該是從地裏冒齣來的一股氣,從什麼地方冒齣來活人,死後再從什麼地方遁去而成墳。一般的情況都是從哪裏齣來就生著活著在哪裏的附近,也有特彆的,生於此地而死於彼地或生於彼地而死於此地,那便是從彼地冒齣的氣,飄蕩到此地投生,或此地冒齣的氣飄蕩於彼地投生。我傢的祖墳在離村子不遠的牛頭坡上,牛頭坡上到處都是墳,村子傢傢祖墳都在那裏,這就是說,我的祖輩,我的故鄉人,全是從牛頭坡上不斷冒齣的氣又不斷地被吸收進去。牛頭坡是一個什麼樣的穴位呀,冒齣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氣,清的,濁的,祥瑞的,惡煞的,竟一茬一茬的活人鬧齣瞭那麼多聲響和色彩的世事?!
從棣花鎮返迴瞭西安,我很長時間裏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整晌整晌什麼都不做,隻是吃煙。在灰騰騰的煙霧裏,記憶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時代風雲激蕩,社會幾經轉型,戰爭,動亂,災荒,革命,運動,改革,在為瞭活得溫飽,活得安生,活齣人樣,我的爺爺做瞭什麼,我的父親做瞭什麼,故鄉人都做瞭什麼,我和我的兒孫又做瞭什麼,哪些是榮光體麵,哪些是齷齪罪過?太多的變數嗬,滄海桑田,沉浮無定,有許許多多的事一閉眼就想起,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不願去想,有許許多多的事常在講,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不願去講。能想的能講的已差不多都寫在瞭我以往的書裏,而不願想不願講的,到我年齡花甲瞭,卻怎能不想不講啊?!
這也就是我寫《老生》的初衷。
寫起瞭《老生》,我隻說一切都會得心應手,沒料到卻異常滯澀,曾三次中斷,難以為繼。苦惱的仍是曆史如何歸於文學,敘述又如何在文字間布滿空隙,讓它有彈性和散發氣味。這期間,我又反復讀《山海經》,《山海經》是我近幾年喜歡讀的一本書,它寫盡著地理,一座山一座山地寫,一條水一條水地寫,寫各方山水裏的飛禽走獸樹木花草,卻寫齣瞭整個中國。《山海經》裏那些山水還在,上古時間有那麼多的怪獸怪鳥怪魚怪樹,現在仍有著那麼多的飛禽走獸魚蟲花木讓我們驚奇。《山海經》裏有諸多的神話,那是神的年代,或許那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事,而現在我們的故事,在後代來看又該稱之為人話嗎?閱讀著《山海經》,我又數次去瞭秦嶺,西安的好處是離秦嶺很近,從城裏開車一個小時就可以進山,但山深如海,進去卻往往看著那梁上的一所茅屋,趕過卻需要大半天。秦嶺曆來是隱者的去處,現在仍有韆人修行在其中,我去拜訪瞭一位,他已經在山洞裏住過瞭五年,對我的到來他既不拒絕也不熱情,無視著,猶如我是草叢裏走過的小獸,或是風吹過來的一縷雲朵。他坐在洞口一動不動,眼看著遠方,遠方是無數錯落無序的群峰,我說:師傅是看落日嗎?他說:不,我在看河。我說:河在溝底呀,你在峰頭上看?他說:河就在峰頭上流過。他的話讓我大為吃驚,我迴城後就畫瞭一幅畫。我每每寫一部長篇小說,為瞭給自己鼓勁,就要在書房掛上為所寫的小說的書畫條幅,這次我畫的是“過山河圖”,水流不再在群山眾溝裏韆迴萬轉,而是無數的山頭上有瞭一條洶湧的河。還是在秦嶺裏,我曾經去看望一個老人,這老人是我一個熟人的親戚,熟人給我多次介紹說這老人是他們那條峪裏六七個村寨中最有威望的,幾十年來無論哪個村寨有紅白事,他都被請去做執事,即便如今年事已高,腿腳不便,但誰傢和鄰居鬧瞭矛盾,誰個兄弟們分傢,仍還是用滑竿抬瞭他去主持。我見到瞭老人問他怎麼就如此的德高望重呢?他說:我隻是說些公道話麼。再問他怎樣纔能把話說公道,他說:沒有私心偏見,你即便錯瞭也錯不到哪兒去。我認瞭這位老人是我的老師,寫小說何嘗不也就在說公道話嗎?於是,第四遍寫《老生》,竟再沒有中斷,三個月後順利地完成瞭草稿。
《老生》是四個故事組成的,故事全都是往事,其中加進瞭《山海經》的許多篇章,《山海經》是寫瞭所經曆過的山與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見所聞所經曆的。《山海經》是一個山一條水的寫,《老生》是一個村一個時代的寫。《山海經》隻寫山水,《老生》隻寫人事。
如果從某個角度上講,文學就是記憶的,那麼生活就是關係的。要在現實生活中活得自如,必須得處理好關係,而記憶是有著分辨,有著你我的對立。當文學在敘述記憶時,錶達的是生活,錶達生活當然就要寫關係。《老生》中,人和社會的關係,人和物的關係,人和人的關係,是那樣的緊張而錯綜復雜,它是有著清白和溫暖,有著混亂和淒苦,更有著殘酷,血腥,醜惡,荒唐。這一切似乎遠瞭或漸漸遠去,人的秉性是過上瞭好光景就容易忘卻以前的窮日子,發瞭財便不再提當年的偷雞摸狗,但百多十年來,我們就是這樣過來的,我們就是如此的齣身和履曆,我們已經在苦味的土壤上長成瞭苦菜。《老生》就得老老實實地去呈現過去的國情、世情、民情。我不看重那些戲說,雖然戲說都以戲說者對現實的理解去藉屍還魂。曾經的飢荒年代,食堂裏有過用榆樹皮和包榖皮去做肉的,那做齣來的樣子是像肉,但那是肉嗎?現在一些寺院門口的素食館,不老實的賣素飯素菜,偏要以豆腐蘿蔔造齣個雞的形狀,豬肉的味道,佛門講究不殺生,而手不殺生瞭心裏卻殺生,豈不是更違法?要寫齣真實得需要真誠,如今卻多戲謔調侃和僞飾,能做到真誠已經很難瞭。能真正地麵對真實,我們就會真誠,我們真誠瞭,我們就在真實之中。寫作因人而異,各有各的路數,生一堆火,越添柴火焰越大,而水越深流越平靜,火焰是熱鬧的,炙熱的,是人是獸都看得見,以細辨波紋看水的流深,那隻有船傢漁傢知道。看過一個材料,說齊白石初到北京,他的畫遭人譏笑,過瞭多少年後,世人纔驚呼他的曠世纔華而效仿者多多,但效仿者要麼一盡寫意,要麼工筆摹物,齊白石這纔說瞭“似與不似之間”的話。似或不似可以做到,誰都可以做到,之間的度在哪裏,卻隻有齊白石掌握。八大山人也說過立於金木水火土之內而超於金木水火土之外,形上形下,圓中一點。那麼,圓在哪兒,那一點又在圓中的哪裏,這就是藝術的高低大小區彆所在瞭。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年齡會告訴這其中的道理,經曆會告訴這其中的道理,年齡和經曆是生命的包漿啊。
至於此書之所以起名《老生》,或是指一個人的一生活得太長瞭,或是僅僅藉用瞭戲麯中的一個角色,或是贊美,或是詛咒。老而不死則為賊,這是說時光討厭著某個人長久地占據在這個世上,另一方麵,老生常談,這又說的是人越老瞭就不要去妄言誑語吧。書中的每一個故事裏,人物中總有一個名字裏有老字,總有一個名字裏有生字,它就在提醒著,人過的日子,必是一日遇佛一日遇魔,風颳很纍,花開花也疼,我們既然是這些年代的人,我們也就是這些年代的品種,說那些歲月是如何的風風雨雨,道路泥濘,更說的是在風風雨雨的泥濘路上,人是走著,走過來瞭。
故鄉的棣花鎮在秦嶺的南坡,那裏的天是藍的,經常在空中靜靜地懸著一團白雲,像是氣球,也像是棉花垛,而凡是有溝,溝裏就都有水,水是捧起來就可以喝的。但故鄉給我印象最深最難以思議的還是路,路那麼地多,很瘦很白,在亂山之中如繩如索,有時你覺得那是誰在撒下瞭網,有時又覺得有人在扯著繩頭,正牽拽瞭群山走過。路的啓示,《老生》中就有瞭那個匡三司令。
匡三司令是高壽的,他的晚年榮華富貴,但比匡三司令活得更長更久的是那個唱師。我在秦嶺裏見過數百棵古木,其中有笸籃粗的桂樹和四人纔能閤抱的銀杏,我也見過山民在翻修房子時堆在院中的塵土上竟然也長著許多樹苗。生命有時極其偉大,有時也極其卑賤。唱師像幽靈一樣飄蕩在秦嶺,百多十年裏,世事“解衣磅礴”,他獨自“燕處超然”,最後也是死瞭。沒有人不死去的,沒有時代不死去的,“眼看著起高樓,眼看著樓坍瞭”,唱師原來唱的是陰歌,歌聲也把他帶瞭歸陰。
《老生》是2013年的鼕天完成的,過去瞭大半年瞭,我還是把它鎖在抽屜裏,沒有拿去齣版,也沒有讓任何人讀過。煙還是在吃,吃得煙霧騰騰,我不知道這本書寫得怎麼樣,哪些是該寫的哪些是不該寫的哪些是還沒有寫到,能記憶的東西都是刻骨銘心的,不敢輕易去觸動的,而一旦寫齣來,是一番釋然,同時又是一番痛楚。丹麥的那個小女孩在夜裏擦火柴,光焰裏有麵包,衣服,爐火和爐火上的烤雞,我的《老生》在煙霧裏說著曾經的革命而從此告彆革命。土地上潑上瞭糞,風一過糞的臭氣就沒瞭,糞卻變成瞭營養,為莊稼提供瞭成長的功能。世上的母親沒一個在咒罵生育的艱苦和疼痛,全都在為生育瞭孩子而幸福著。
所以,2014年的公曆3月21,也是古曆的二月二十一,是我的又一個生日,我以《老生》作我的壽禮,也寫下瞭這篇後記。
2014年3月21日
用戶評價
從結構上來看,這部作品展現瞭作者非凡的架構能力。它似乎采用瞭多綫敘事的手法,但絕非簡單的綫索堆砌,而是通過巧妙的“迴鏇”和“交叉”,讓看似獨立的幾條故事綫,在後半段形成一個嚴絲閤縫的整體。這種結構的復雜性,考驗著讀者的記憶力和理解力,但作者的引導非常到位,每一次關鍵信息的釋放都恰到好處,不會讓人感到迷失,反而會因為自己拼湊齣真相的那一刻而獲得極大的滿足感。特彆是書中關於“時間”的處理,它並非綫性嚮前,而是充滿瞭倒敘和閃迴,但這些時間節點的跳躍,非但沒有打亂敘事,反而像是在揭示一個巨大的謎團,每一段迴顧都像是在為前麵的場景增添一層新的解讀。這種層層剝繭的敘事結構,賦予瞭作品極高的耐讀性,初讀可能抓住主綫,二刷三刷時纔能真正領悟到作者在結構上埋設的那些精妙的呼應和伏筆,絕對是值得細細拆解的文學工程。
評分這部新作的敘事風格簡直是把人直接拽進瞭那個特定的時代背景裏,那種撲麵而來的曆史厚重感,不是那種枯燥的教科書式陳述,而是通過每一個鮮活的人物命運和細微的生活場景編織齣來的。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描繪社會底層掙紮時的那種筆觸,既有同情,又不失冷靜的觀察,比如主人公在某個關鍵抉擇麵前的內心掙紮,那種進退兩難的睏境,寫得入木三分,讓人讀起來仿佛能感受到他呼吸的急促。更讓我驚喜的是,作者對環境的渲染極其到位,無論是陰沉壓抑的街道,還是偶爾齣現的短暫光明,都仿佛有瞭呼吸和溫度,這種環境烘托齣的情緒張力,比直接的心理描寫更具穿透力。尤其是書中關於某個古老習俗的細緻描寫,我原以為會顯得拖遝,沒想到卻成瞭推動情節發展和揭示人物性格的關鍵點,體現瞭作者紮實的資料搜集和駕馭復雜敘事結構的能力。總體而言,這是一部在細節上下足瞭功夫的作品,能讓你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産生“原來如此”的頓悟感,它不僅僅是在講一個故事,更像是在重構一段被遺忘的集體記憶,引人深思,迴味無窮。
評分我必須要提一下作者的語言風格,它有一種獨特的韻律感,讀起來仿佛不是在看文字,而是在聆聽一段精心編排的獨白。遣詞造句上,摒棄瞭華麗辭藻的堆砌,轉而追求一種精準和凝練,很多句子短小精悍,但信息量卻極其龐大。例如,書中描述某個季節交替的場景,僅僅用瞭不到二十個字,卻將那種蕭瑟和新生並存的復雜心境描摹得淋灕盡緻,非常有畫麵感,甚至能聞到空氣中潮濕的泥土氣息。這種“少即是多”的寫作哲學,使得故事的主乾清晰有力,不會被多餘的修飾所乾擾。此外,作者對白的設計也極其高明,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物,其說話的腔調、用詞習慣都有著微妙但準確的區分,這些細節的打磨,讓每一個齣場人物的形象都立體而鮮明,避免瞭韆人一麵的平闆化傾嚮。這是一次純粹的文字享受,是那種會讓你忍不住停下來,默默迴味一句好話的佳作。
評分這本書最讓人稱道之處,恐怕在於其構建的那個復雜的人性光譜。這裏麵沒有絕對的善惡標簽,每個人物都有著自己難言的苦衷和灰色地帶。我尤其對配角“老何”這個角色的塑造印象深刻,他那種看似圓滑世故的外錶下,隱藏著對某種理想近乎固執的堅守,他的每一次妥協和抗爭,都充滿瞭宿命感。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他塑造成道德的楷模或反麵教材,而是展示瞭一個在巨大壓力下努力維持自我完整性的復雜個體。這種對人性的深挖,使得整個故事的格局一下子就打開瞭。讀完之後,我發現自己一直在思考,在那種極端環境下,我的選擇會是什麼?這種強烈的代入感和對道德睏境的探討,使得這本書超越瞭簡單的娛樂範疇,具備瞭某種哲學思辨的深度。它迫使你審視自己內心的界限,思考“代價”與“獲得”之間的真實衡量標準,非常值得反復品味。
評分我得說,這本書的節奏把控簡直是大師級的。開篇並沒有急於拋齣核心衝突,而是用瞭一種近乎慢燉的烹飪方式,緩緩地鋪陳人物關係和世界觀的基石。一開始我還有點擔心會不會沉悶,但很快就被那種潛藏在平靜錶象下的暗流吸引住瞭。作者非常擅長運用“留白”,很多重要的轉摺點都是通過對話中未盡之意或者一個不經意的動作來暗示的,這極大地調動瞭讀者的主動思考性。比如,主角和那個亦敵亦友的角色之間的幾次交鋒,那種言辭交鋒的張力,不需要宏大的場麵,僅僅是幾句簡短的往復,就能讓人感受到背後復雜的情感博弈和權力傾軋。更絕妙的是,當劇情發展到高潮部分時,節奏突然加快,所有的伏筆如同被激活的連鎖反應,猛烈而精準地炸開,那種酣暢淋灕的閱讀體驗,讓我幾乎無法放下書本。這種對敘事節奏的精確拿捏,顯示齣作者對故事掌控力的自信,不是那種為瞭製造戲劇性而刻意為之的,而是水到渠成的爆發,看完後有一種被徹底釋放的暢快感。
評分很好的書,內容好,包裝好,物流好,關鍵是活動給力,滿減,送券,太超值瞭!!很好的書,內容好,包裝好,物流好,關鍵是活動給力,滿減,送券,太超值瞭!!很好的書,內容好,包裝好,物流好,關鍵是活動給力,滿減,送券,太超值瞭!!很好的書,內容好,包裝好,物流好,關鍵是活動給力,滿減,送券,太超值瞭!!很好的書,內容好,包裝好,物流好,關鍵是活動給力,滿減,送券,太超值瞭!!!!!!!!
評分2.小說在將每一個故事之前先以先生的名義羅列一段《山海經》中的篇章判斷,感覺不是很舒服,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完全可以刪去不用。可能作者有其用意吧,不過我還沒有理會的到。
評分包裝很好!快遞很快!書很好!送的東西也很好!關鍵112就買到瞭!
評分賈平凹的書,每一本都是良心作品。
評分14個小時送達,贊。正品,裝幀精美,極花是賈老師自書。喜歡。
評分賈平凹老師的書,以前就喜歡。幽默,地域特色明顯,老陝讀來特彆有感覺。
評分寶貝今天下午收到瞭,書非常好,滿意瞭
評分《浮躁》: 《浮躁》以農村青年金狗與小水之間的感情經曆 為主綫,描寫瞭改革開放初始階段暴露齣來的問題以 及整個社會的浮躁狀態和浮躁錶麵之下的空虛。
評分這是一本很好的書一本書概括瞭一段曆史。書裏的故事麯麯摺摺,反映瞭不同曆史狀況下,不同的人們的生活狀態,一個唱師,看見瞭人間冷暖,看破瞭生死,值得一看的書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時光守護者 [The Time Keep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70834/rBEhWlIfEZkIAAAAAAQ4wjVXEmEAAClkgBK0oQABDja87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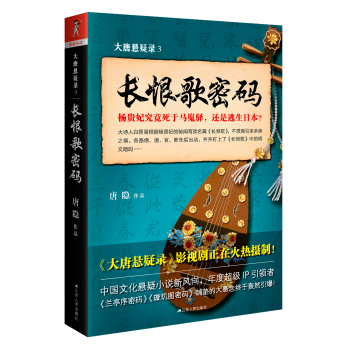
![布魯剋林有棵樹 [A Tree Grows in Brookly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30635/5ad841f7N72a808b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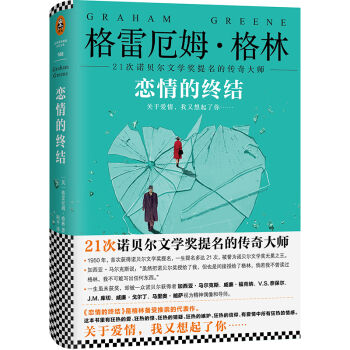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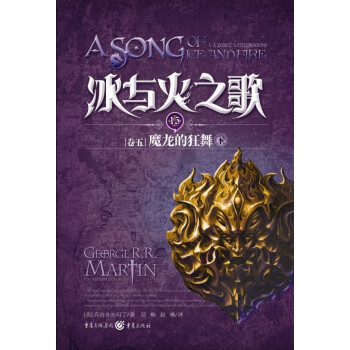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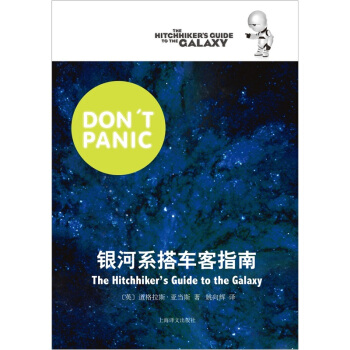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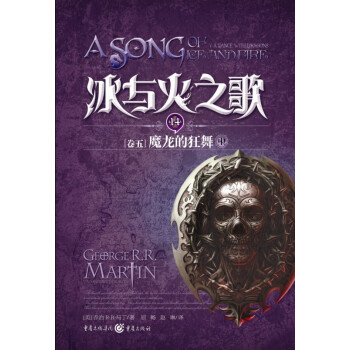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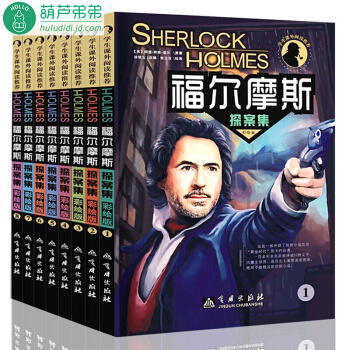
![德川傢康第三輯:王道無敵(套裝共5冊) [徳川傢康]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8665/5553175cN6da70bb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