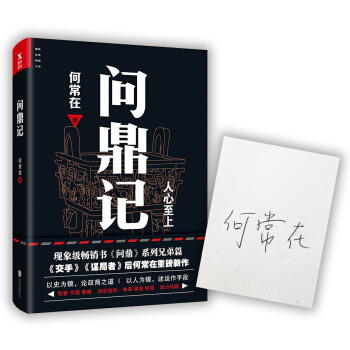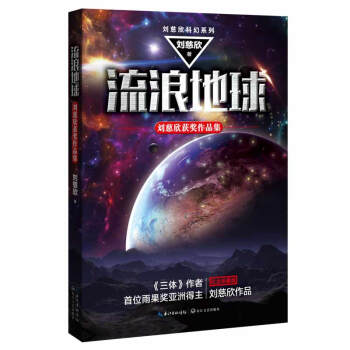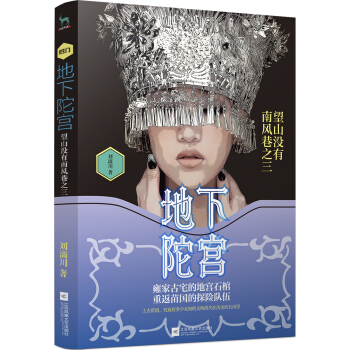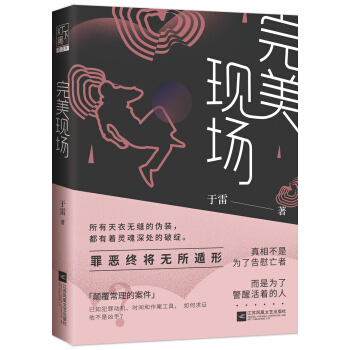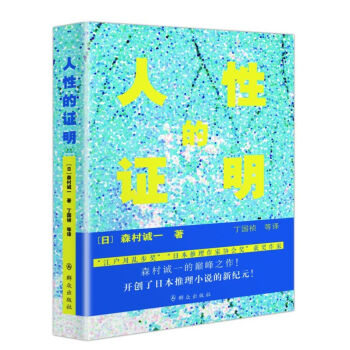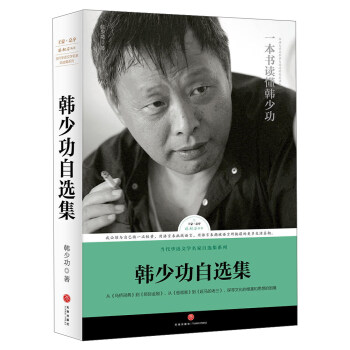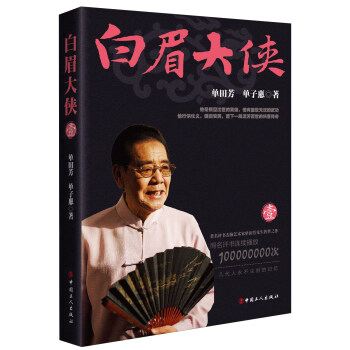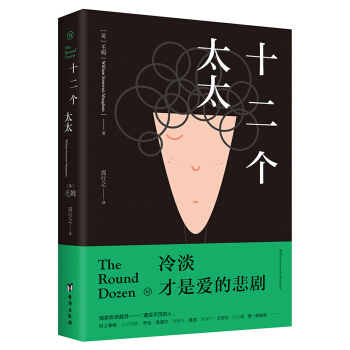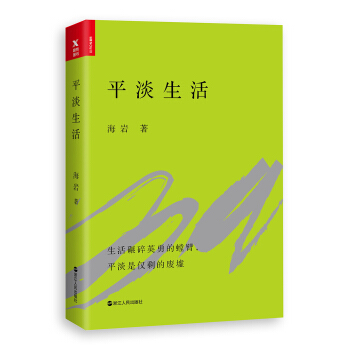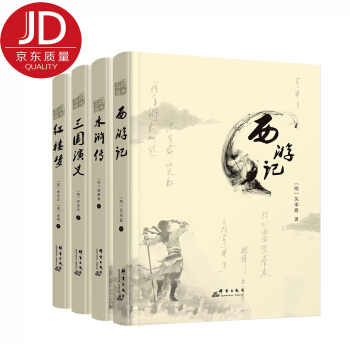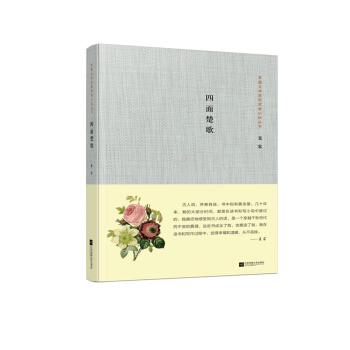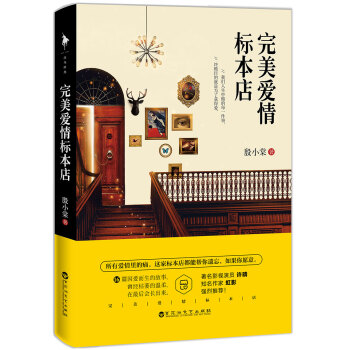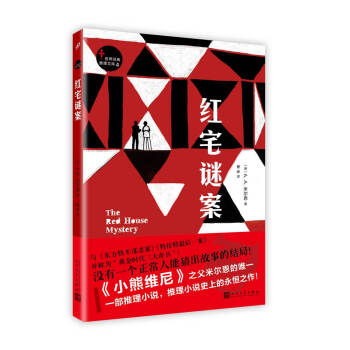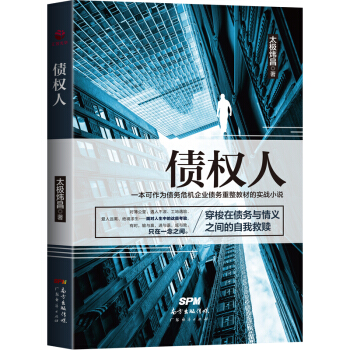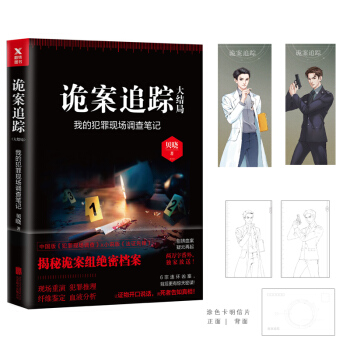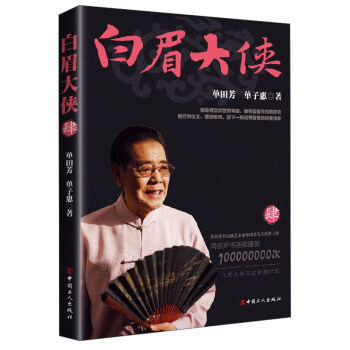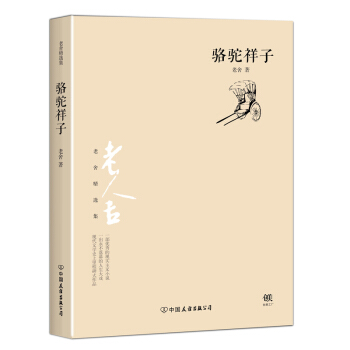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人间的真话本来不多,一个女子的脸红胜过一大片话;连祥子也明白了她的意思。——《骆驼祥子》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骆驼祥子》
内容简介
《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以北平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北京市民的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深刻揭露了一个时代对普通大众生存境况的挤压,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向人们展示了底层贫苦市民积极努力致力于改变命运,却四处碰壁的图景。《骆驼祥子》是三十年代中国极为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奠定了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骆驼祥子》是他个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作者简介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老舍一生勤勉,著述颇丰,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二马》《猫城记》;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剧本《茶馆》《龙须沟》等。精彩书评
我们都觉得他(老舍)是我们朋友中爽朗、幽默、质朴、热情的一个。——冰心
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了。
——茅盾
目录
骆驼祥子/1断魂枪/217
八太爷/225
敌与友/235
老字号/241
精彩书摘
一我们所要介绍的是祥子,不是骆驼,因为“骆驼”只是个外号;那么,我们就先说祥子,随手儿把骆驼与祥子那点关系说过去,也就算了。
北平的洋车夫有许多派:年轻力壮,腿脚灵利的,讲究赁漂亮的车,拉“整天儿”,爱什么时候出车与收车都有自由;拉出车来,在固定的“车口”或宅门一放,专等坐快车的主儿;弄好了,也许一下子弄个一块两块的;碰巧了,也许白耗一天,连“车份儿”也没着落,但也不在乎。这一派哥儿们的希望大概有两个:或是拉包车;或是自己买上辆车,有了自己的车,再去拉包月或散座就没大关系了,反正车是自己的。
比这一派岁数稍大的,或因身体的关系而跑得稍差点劲的,或因家庭的关系而不敢白耗一天的,大概就多数的拉八成新的车;人与车都有相当的漂亮,所以在要价儿的时候也还能保持住相当的尊严。这派的车夫,也许拉“整天”,也许拉“半天”。在后者的情形下,因为还有相当的精气神,所以无论冬天夏天总是“拉晚儿”。夜间,当然比白天需要更多的留神与本事;钱自然也多挣一些。
年纪在四十以上,二十以下的,恐怕就不易在前两派里有个地位了。他们的车破,又不敢“拉晚儿”,所以只能早早的出车,希望能从清晨转到午后三四点钟,拉出“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他们的车破,跑得慢,所以得多走路,少要钱。到瓜市,果市,菜市,去拉货物,都是他们;钱少,可是无须快跑呢。
在这里,二十岁以下的——有的从十一二岁就干这行儿——很少能到二十岁以后改变成漂亮的车夫的,因为在幼年受了伤,很难健壮起来。他们也许拉一辈子洋车,而一辈子连拉车也没出过风头。那四十以上的人,有的是已拉了十年八年的车,筋肉的衰损使他们甘居人后,他们渐渐知道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而用鼻翅儿扇着那些后起之辈。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他们自己也因此在擦着汗的时节常常微叹。不过,以他们比较另一些四十上下岁的车夫,他们还似乎没有苦到了家。这一些是以前决没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或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此外,因环境与知识的特异,又使一部分车夫另成派别。生于西苑海甸的自然以走西山,燕京,清华,较比方便;同样,在安定门外的走清河,北苑;在永定门外的走南苑……这是跑长趟的。不愿拉零座;因为拉一趟便是一趟,不屑于三五个铜子的穷凑了。可是他们还不如东交民巷的车夫的气儿长,这些专拉洋买卖的讲究一气儿由交民巷拉到玉泉山,颐和园或西山。气长也还算小事,一般车夫万不能争这项生意的原因,大半还是因为这些吃洋饭的有点与众不同的知识,他们会说外国话。英国兵,法国兵,所说的万寿山,雍和宫,“八大胡同”,他们都晓得。他们自己有一套外国话,不传授给别人。他们的跑法也特别,四六步儿不快不慢,低着头,目不旁视的,贴着马路边儿走,带出与世无争,而自有专长的神气。因为拉着洋人,他们可以不穿号坎,而一律的是长袖小白褂,白的或黑的裤子,裤筒特别肥,脚腕上系着细带;脚上是宽双脸千层底青布鞋;干净,利落,神气。一见这样的服装,别的车夫不会再过来争座与赛车,他们似乎是属于另一行业的。
有了这点简单的分析,我们再说祥子的地位,就像说——我们希望——一盘机器上的某种钉子那么准确了。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这就是说,他是属于年轻力壮,而且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车,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
这可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年,二年,至少有三四年;一滴汗,两滴汗,不知道多少万滴汗,才挣出那辆车。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的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像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在他赁人家的车的时候,他从早到晚,由东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家抽着转的陀螺;他没有自己。可是在这种旋转之中,他的眼并没有花,心并没有乱,他老想着远远的一辆车,可以使他自由,独立,像自己的手脚的那么一辆车。有了自己的车,他可以不再受拴车的人们的气,也无须敷衍别人;有自己的力气与洋车,睁开眼就可以有饭吃。
他不怕吃苦,也没有一般洋车夫的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他的聪明和努力都足以使他的志愿成为事实。假若他的环境好一些,或多受着点教育,他一定不会落在“胶皮团”里,而且无论是干什么,他总不会辜负了他的机会。不幸,他必须拉洋车;好,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作过了。可是,不久他就看出来,拉车是件更容易挣钱的事;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与地点就会遇到一些多于所希望的报酬。自然,他也晓得这样的机遇不完全出于偶然,而必须人与车都得漂亮精神,有货可卖才能遇到识货的人。想了一想,他相信自己有那个资格:他有力气,年纪正轻;所差的是他还没有跑过,与不敢一上手就拉漂亮的车。但这不是不能胜过的困难,有他的身体与力气作基础,他只要试验个十天半月的,就一定能跑得有个样子,然后去赁辆新车,说不定很快的就能拉上包车,然后省吃俭用的一年二年,即使是三四年,他必能自己打上一辆车,顶漂亮的车!看着自己的青年的肌肉,他以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必能达到的一个志愿与目的,绝不是梦想!
他的身量与筋肉都发展到年岁前边去;二十来的岁,他已经很大很高,虽然肢体还没被年月铸成一定的格局,可是已经像个成人了——一个脸上身上都带出天真淘气的样子的大人。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他不甚注意他的模样,他爱自己的脸正如同他爱自己的身体,都那么结实硬棒;他把脸仿佛算在四肢之内,只要硬棒就好。是的,到城里以后,他还能头朝下,倒着立半天。这样立着,他觉得,他就很像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
他确乎有点像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有自己的打算,有些心眼,但不好向别人讲论。在洋车夫里,个人的委屈与困难是公众的话料,“车口儿”上,小茶馆中,大杂院里,每人报告着形容着或吵嚷着自己的事,而后这些事成为大家的财产,像民歌似的由一处传到一处。祥子是乡下人,口齿没有城里人那么灵便;设若口齿灵利是出于天才,他天生来的不愿多说话,所以也不愿学着城里人的贫嘴恶舌。他的事他知道,不喜欢和别人讨论。因为嘴常闲着,所以他有工夫去思想,他的眼仿佛是老看着自己的心。只要他的主意打定,他便随着心中所开开的那条路儿走;假若走不通的话,他能一两天不出一声,咬着牙,好似咬着自己的心!
他决定去拉车,就拉车去了。赁了辆破车,他先练练腿。第一天没拉着什么钱。第二天的生意不错,可是躺了两天,他的脚脖子肿得像两条瓠子似的,再也抬不起来。他忍受着,不管是怎样的疼痛。他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这是拉车必须经过的一关。非过了这一关,他不能放胆的去跑。
脚好了之后,他敢跑了。这使他非常的痛快,因为别的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地名他很熟习,即使有时候绕点远也没大关系,好在自己有的是力气。拉车的方法,以他干过的那些推,拉,扛,挑的经验来领会,也不算十分难。况且他有他的主意:多留神,少争胜,大概总不会出了毛病。至于讲价争座,他的嘴慢气盛,弄不过那些老油子们。知道这个短处,他干脆不大到“车口儿”上去;哪里没车,他放在哪里。在这僻静的地点,他可以从容的讲价,而且有时候不肯要价,只说声:“坐上吧,瞧着给!”他的样子是那么诚实,脸上是那么简单可爱,人们好像只好信任他,不敢想这个傻大个子是会敲人的。即使人们疑心,也只能怀疑他是新到城里来的乡下老儿,大概不认识路,所以讲不出价钱来。及至人们问到,“认识呀?”他就又像装傻,又像耍俏的那么一笑,使人们不知怎样才好。
两三个星期的工夫,他把腿溜出来了。他晓得自己的跑法很好看。跑法是车夫的能力与资格的证据。那撇着脚,像一对蒲扇在地上扇乎的,无疑的是刚由乡间上来的新手。那头低得很深,双脚蹭地,跑和走的速度差不多,而颇有跑的表示的,是那些五十岁以上的老者们。那经验十足而没什么力气的却另有一种方法:胸向内含,度数很深;腿抬得很高;一走一探头;这样,他们就带出跑得很用力的样子,而在事实上一点也不比别人快;他们仗着“作派”去维持自己的尊严。祥子当然决不采取这几种姿态。他的腿长步大,腰里非常的稳,跑起来没有多少响声,步步都有些伸缩,车把不动,使座儿觉到安全,舒服。说站住,不论在跑得多么快的时候,大脚在地上轻蹭两蹭,就站住了;他的力气似乎能达到车的各部分。脊背微俯。双手松松拢住车把,他活动,利落,准确;看不出急促而跑得很快,快而没有危险。就是在拉包车的里面,这也得算很名贵的。
他换了新车。从一换车那天,他就打听明白了,像他赁的那辆——弓子软,铜活地道,雨布大帘,双灯,细脖大铜喇叭——值一百出头;若是漆工与铜活含糊一点呢,一百元便可以打住。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第一步他应当,他想好了,去拉包车。遇上交际多,饭局多的主儿,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钱。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头五块的,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这样,他的希望就近便多多了。他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没有任何嗜好,没有家庭的累赘,只要他自己肯咬牙,事儿就没有个不成。他对自己起下了誓,一年半的工夫,他——祥子——非打成自己的车不可!是现打的,不要旧车见过新的。
……
用户评价
老实讲,这本书的基调是相当压抑的,读完整本书后,我感到了一种深刻的疲惫,但这种疲惫并非源于内容枯燥,而是源于情感上的过度投入。作者似乎毫不留情地撕开了生活的温情面纱,将人性的自私、环境的冷漠,以及理想在现实面前的脆弱,暴露无遗。我欣赏这种不妥协的真实,它拒绝给我们廉价的希望,而是将残酷的真相摆在我们面前,逼迫我们直视。书中的一些转折点设计得极为巧妙,它们不是戏剧化的意外,而是逻辑上必然导致的结果,这种宿命感让人感到无力,却又无比真实,仿佛那就是生活本来的面目。我忍不住思考,如果我置身于那个情境,是否能做出不同的选择?恐怕不能。这种代入感,便是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它让你感同身受,并因此而震撼。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在于它对“努力”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义。它没有简单地歌颂勤奋的价值,而是深入探讨了努力与环境、努力与回报之间的复杂关系,甚至是两者之间的悖论。书中人物的奋斗轨迹,充满了悲剧性的讽刺,让人不禁要去反思,我们所信奉的那些朴素真理,在宏大的社会机器面前,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作者的笔触是冷静的,带着一种近乎科学的观察角度,记录着个体意志的消磨过程。我喜欢这种不加粉饰的记录方式,它避免了说教的风险,而是让事实本身去说话。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奋斗”这个词有了更审慎、更成熟的理解,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充满变数的、需要审时度势的策略。
评分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极其独特,初读时略感晦涩,但一旦适应了那种独特的韵律,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美感。作者的遣词造句充满了古典的张力和现代的锐利,很多句子仿佛是精心打磨过的诗句,每一字都恰到好处地承载着重量。情节的推进并非采用传统线性叙事,而是充满了跳跃感和象征意义,这要求读者必须投入百分之百的专注力去捕捉那些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深意。其中几段关于内心独白的描写,简直是心理学的教科书,将人物那份矛盾、挣扎、自我欺骗与清醒之间的拉扯,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拍案叫绝。我甚至停下来,对照着字典查阅了几个生僻的词汇,那份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因为它们是构建整个情感基调的关键。这本书挑战了我的阅读习惯,也极大地拓宽了我对文学表达边界的认知。它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出更深刻的问题。
评分这本新近读完的书,带给我一种久违的、沉甸甸的触动。它不像那些快餐式的读物,翻几页就忘了,而是像一块磨人的石头,在你心头反复摩擦,留下清晰的印记。书中的世界观构建得异常扎实,作者似乎对人性的复杂性有着近乎残酷的洞察力。我尤其欣赏它对环境描摹的细腻,那些文字仿佛拥有气味和温度,能让你真切地感受到人物所处的困境——无论是烈日下扬起的尘土,还是阴冷巷子里透出的寒意,都刻画得入木三分。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陷入一种沉思,思考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挣扎的小人物,他们看似微不足道的抗争,实则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张力。叙事节奏的把控也十分老道,张弛有度,高潮迭起却又不显刻意煽情,真正的高级感往往体现在不动声色的力量上。这本书,在我看来,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深层的肌理和个体在命运面前的无力和坚韧。它不仅仅是讲了一个故事,更是在探讨一种生存的哲学,值得反复咀嚼。
评分从结构布局来看,这本书的布局宛如一座精密的钟表,每一个齿轮、每一个发条都紧密咬合,缺少任何一环都会导致整个系统停摆。作者在篇幅的分配上展现了非凡的控制力,有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配角或场景,在后文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写作功力。我特别留意了不同章节之间的过渡处理,它们衔接得天衣无缝,即便时间跨度很大,读起来也不会有断裂感。这使得整个故事的内在逻辑无比坚固,没有丝毫的注水或为了凑字数而存在的段落。对于喜爱研究叙事技巧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份极好的范本。它证明了精妙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叙事力量。
评分是真品,比书店便宜,非常好
评分价格优惠,大师作品值得拥有。
评分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好书
评分书不错,值得细细品读。买书容易读书难啊。
评分东西不错,物流很快,很棒!
评分挺厚的一本,纸张是带有淡淡黄色的,比较护眼。很不错。。
评分经典,一直没看,慢慢看啦
评分物流快书正版。
评分今年618的第一弹,期待更多优惠,多多买书,大爱京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