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郑振铎被遗忘的杰作,生命力经久不衰的新词史
内容简介
本书是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计划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之一部分,作者将词的起源与汉唐的乐府挂钩,按照中晚唐词、五代词、敦煌卷子中所见词和变文、北宋词、南宋词的顺序,梳理了词作为文学形式的产生、发展、极盛乃至最终形成固定体例的过程。每讲一个时代,郑振铎都会引用大量词作,以形象细致的语言阐明各时期词风的不同,以及词在当时取得了怎样的新发展。由于郑氏有纵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雄心,又有不凡同时侪辈的眼光,他在这部词史中提出了很多创见,有些观点至今仍有学术价值。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原因,本书被学术界长期遗忘,甚至连作者本人及亲属也不复记忆。直至本次整理出版,这部杰出的文学史著作才得以重新与读者见面,可谓难得的机缘。
作者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福建长乐人,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收藏家,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等职。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曾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等职。郑氏生平著作甚多,文学史领域的专著有《文学大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多种,另著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等。
目录
第一章词的起源(1)第二章五代文学(31)
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92)
第四章北宋词人(154)
第五章南宋词人(243)
后记(339)
精彩书摘
第一章词的起源一
六朝乐府的生命自经了晋隋至唐中叶的一个长时期之后,便盛极而衰。到了五代之时,歌唱者皆尚“词”。欧阳炯所谓“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正足以见当时的盛况。至宋则流传更广,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娴雅如文人学士,豪迈如武夫走卒,无不解歌者。词的流行真可谓“至矣,甚矣,蔑以复加矣”。但到了后来,词也渐渐成为不可歌了。仅足资纸上之唱和,不复供宴前的清歌,仅足为文人学士的专业,不复为民间俗子所领悟;语益文,辞益丽,离民间日益远,于是遂有“曲”代之而兴,而词的黄金时代便也一去而不复回。
二
在未说到本文之前,有一点是不可不先说明白的,即词与五七言诗之间是不发生什么关系的。她的发展,也并不妨碍到五七言诗的发展。她与五七言并没有相继承的统系。这正与六朝时代的乐府一样。乐府也是与五言诗平行发展起来的。他们各走着一条路,各不相干,也各不相妨。在文体的统系上说起来,词乃是六朝乐府的同类,却不是五七言的代替者。我们晓得,诗歌有两种。一种是可歌的,一种是不可歌的。可歌的便是乐府,便是词,便是曲;不可歌的便是五七六言的古律诗。不可歌的诗歌,系出于不必有音乐素养的文人之手,只以抒情达意为主,并没有另外的目的;可歌的诗曲,其目的,一方面是抒写情意,一方面却是有了一种自娱或娱人的应用目的的。他们有的为宗庙朝廷的大乐章,有的为文人学士家宴春集的新词曲,有的则为妓女阶级娱乐顾客的工具。因此,不可歌的诗歌,其发展是一条线下去的;可歌的诗歌,其发展便跟随了音乐的发展而共同进行着。音乐有了变迁,他们便也有了变迁。汉人乐府不可歌了,便有六朝乐府代之而起,六朝乐府不可歌了,便有词代之而起,词不可歌了,便有南北曲代之而起。虽然在乐府词曲已成为不可歌之物之时,仍有人在写乐府词曲,那却是昧于本意,迷恋于古物的文人们所做的不聪明的事。例如,许多人以词为“诗余”,便是一个构成这种错误的实证。沈括的《梦溪笔谈》说: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如曰“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朱熹也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
——《朱子语类》百四十他们这个主张影响很大。《全唐诗》第十二函第十册,在“词”之题下,亦注道: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歌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方成培的《香研居词麈》也这样的主张着:“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也。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这几个人的见解都是以词为“诗余”,为由五七言诗蜕变而成的。这种见解,其主要的来因,乃误在以唐人所歌者胥为五七言诗。我们且看,唐人所歌者果尽为五七言诗乎?王灼的《碧鸡漫志》说:“唐史称李贺乐章数十篇,诸工皆合之管弦。又称李益诗每一篇成,乐工慕名者争以赂取之,被诸声歌,供奉天子。旧史亦称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见于乐府。开元中,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画壁,伶官招妓聚宴。以此知唐之伶妓以当时名士诗词入歌曲,皆常事也。”然既云“合之管弦”,既云“往往见之乐府”,则可见五七言诗的入乐乃是偶然的事,并不是必然的事。文人既以诗篇入乐为可夸耀的事,则五七言诗篇之不常入乐,更为可知。按崔令钦的《教坊记》,共录曲名三百二十五;又《词律》所录者凡六百六十余体;又《钦定词谱》所录者凡八百二十六调。在这许多曲调中,据《苕溪渔隐丛话》,则在宋时“所存者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而统唐、宋能歌与否的词体而总计之,也只有《怨回纥》《纥那》《南柯子》《三台令》《清平调》《欸乃曲》《小秦王》《瑞鹧鸪》《阿那》《竹枝》《柳枝》《八拍蛮》诸曲而已。以这许多绝非五七六言古律绝诗的词调,乃因了偶有寥寥几首的合于五七六言古律绝诗的词式,便以为她是出于五七六言诗的,真是未免太过武断了。《旧唐书·音乐志》说:“太常旧相传,有宫商角徵羽宴乐五调歌词各一卷。或云贞观中侍中杨仁恭妾赵方等所诠集。词多郑、卫,皆近代词人杂诗。至縚(韦縚)又令太乐令孙玄成更加整比为七卷。”但他们所集的,“工人多不能通”。工人所通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新的曲调,崭新的曲调;这种崭新的曲调便是词,便是代替六朝乐府而起的新歌曲的词。成肇麐说:十五国风息而乐府兴,乐府微而歌词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为范也。抑扬抗坠之音,短修之节,连转于不自已,以蕲适歌者之吻。而终乃上跻于雅颂,下衍为文章之流别。诗余名词,盖非其朔也。唐人之诗未能胥被弦管,而词无不可歌者。
——《七家词选序》他这话确能看出词的真正来源来。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有寥寥的几句话:“古乐府者,诗之旁行也;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这几句话也恰是我们所要说的。但“乐府之末造”一语,却颇有语病。词是代替乐府而起的可歌之诗歌,却不是乐府的末造,也不是乐府的蜕变。她是另有其来源的。
……
前言/序言
导言陈福康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郑振铎是发出“要求一本比较完备些的中国文学史”呼吁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很早就从事中国文学史的撰著工作。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共出版过四种中国文学史(或与中国文学史有关的)专著:一是《文学大纲》四大册的中国部分(按,《文学大纲》实际是史上第一部真正的世界文学通史,其中约四分之一篇幅写的是中国,已有学者指出,《文学大纲》中国部分若独立出来,实是一部体系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如此,我认为此书的中国文学部分,实际还是一九二○年代国内最优秀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二是《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按即本书原书名。——编者一册,为断代史性质;三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四册,为通史性质;四是《中国俗文学史》二册,为分类史性质。总计字数约一百五十万字(《文学大纲》外国文学部分以及各书插图所占篇幅均不算在内),又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在新文学工作者中,以一人之力做出如上成绩的,没有第二个人。
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三部书,几十年来被众多出版社多次重印,学界几乎无人不知。而那本《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知道的人就很少了。那是怎样的一本书呢?须从头道来。
郑振铎于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文学大纲》。边写边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其中有些补充章节则发表于《一般》等刊物上),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册于一九二六年底出版,接着郑振铎因大革命失败而避难欧洲,全书的跋即作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赴法国的远洋轮上。最后的第四册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出版的。应该说,在《文学大纲》写成和出版以后,郑振铎就产生了再撰著一部详尽的《中国文学史》的念头。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从西欧回国,应上海复旦大学等校之聘,讲授中国文学史。同时,继续主编《小说月报》。一开始,他已经公布要撰写一部《西洋艺术史》以供《小说月报》连载,但后来撰写《中国文学史》的欲望超过了写《西洋艺术史》,以至后者终于未能写出,而从一九二九年三月号《小说月报》起,开始发表《中国文学史》的“中世卷第三篇”。至年底,共发表了五章。最早发表的是第三章《敦煌的俗文学》,文末有郑振铎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写的附记,说明此章是“去年九月间匆促写成”,可知他回国不久就开始《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了。
这五章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后,郑振铎经过少许修订,于一九三○年五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书名为《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作者在同年三月一日写的该书《后记》中说:“全书告竣,不知何日,姑以已成的几章,刊为此册。我颇希望此书每年能出版二册以上,则全书或可于五六年后完成。”从这里我们已可窥知原书计划之宏大。但是,这个“中世卷第三篇上”是什么意思呢?原书共拟分几册?由于全书仅出版此一册,后来作者在北平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计划已有更改,因此人们一直无从详知。一直到我在郑振铎遗稿中幸运地看见了他在一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此时该书已经付印)修订的《中国文学史草目》,方才解开了这个哑谜。
根据这个《草目》,我们知道郑振铎当时拟写的《中国文学史》,上下五千年,自上古(公元前三千年)至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夕。共分“古代卷”“中世卷”“近代卷”三卷。从上古至西晋末年为古代卷,共分三篇,每篇各一册;从东晋初至明中期正德年间为中世卷,共分四篇,每篇各二册;明嘉靖初至“五四”前为近代卷,共分三篇,第一篇三册,后二篇各二册。这样,全书共有十篇,约一百章,拟分十八册出版。大致估计,全书完成将有三百万字左右。这是何等气势磅礴的前无古人的文学史撰写计划!可惜的是,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完成。而其“中世卷第三篇”,内容是五代、两宋期间的文学史,计划分上下两册,已出的此书即为上册。上册共五章,题目为:《词的启源》《五代文学》《敦煌的俗文学》《北宋词人》《南宋词人》。除了敦煌文学及五代文学中涉及的诗、散文等以外,主要讲的都是有关“词”的历史,正如作者在此书《后记》中说的,“这一册所叙者以‘词’为主体”。因此,尽管此书作为断代文学史(五代两宋文学史)也仅成半部,令人不无遗憾;但却颇有单独存在的价值——可以当作一部词史来读。(宋以后,“词”仍有一定的发展,但已趋衰落,影响小了。)
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已经提出,中古时期中国诗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即诗(近体、律体)的时期与词的时期,并将“自五代时‘词’之一体的开始发展起,至宋元之间此种诗体之衰落为止”,称作中世“第二诗人时代”。必须指出的是,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学大纲》的有关章节,对词史作了简明的论述后,关于这一特殊诗体的发展史的研究,几年来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在本书之前出版的其他各种文学史中,虽然也提到了词,但都很简略。曾在报上指出《文学大纲》几处小误,并称也对宋词研究深有兴趣的胡云翼,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了专著《宋词研究》,书中明确说明:“本书行世前,尚无此类专著”。胡氏此书约十万来字,除了通论部分外,主要是作家评传。胡氏此书有一定学术价值,但作为通论、评传尚可,却显然不是一本“词史”。因为它主要是鉴赏、评述性质,而缺少历史观念。要论“词史”的话,我们其实不能不推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为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在郑著此书问世后,有关词史的专著才开始多了起来,如一九三一年出版了刘毓盘的《词史》此书在一九二○年代曾作为北京大学讲义,内部少量印行,约八万余字。,王易的《词曲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其第三册专论词与曲),一九三三年出版了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中国词史大纲》、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其下册专谈词),等等。但是,从史料的丰富性与立论的正确性等方面看,一九三○年代出版的一些词史似均未能超过郑振铎这本书。
此书约有十七万字,其中专论词的部分有十四万字。(而《文学大纲》有关词的部分的文字,不及这一字数的十分之一。)本书论及词作者近二百名,引录词作约三百七十首,即使将这些词作单独抽出作为一本“词选”,也是相当丰富的了。由此可见本书的内容是相当详赡的。而在见解上,书中更有不少独创。
例如,关于词的来源,《文学大纲》未及论述,本书则认为有“两个大来源”,即“胡夷之曲”与“里巷之曲”,一个是西域来的,一个是取之民间的。作者不同意历来认为词是“诗余”的说法,也不同意词是“古乐府的末造”的说法,认为这些说法“是完全违背了文体的生长与演变之原则的”,也是不符合史实的。他指出:“词自有它的来历、它的发源、它的生命。”“它不是旧诗体的借尸还魂,也不是旧诗体的枯杨生稊,更不是旧诗体的改头换面。新诗体是一种崭新的东西。”它新就新在敢于大胆摄取域外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养料,因此就“与五七言诗大异其面目与性质”。关于中国文学接受外来影响与民间养料的问题,是当时的很多研究者所讳言或忽视的。郑振铎强调指出这些,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很有意义。本书第一章《词的启源》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时,著名词学家、郑振铎的小学同学夏承焘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夏承焘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日记:“阅《小说月报》二六六号郑振铎《词的启源》,谓词与五、七言诗不发生关系。据《旧唐书·音乐志》‘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句,谓‘里巷与胡夷之曲,乃词之二大来源’。又谓依腔填词,始于裴谈、温庭筠。以绝细腻之笔,写无可奈何之相思离绪,始为文人之恋歌,而非民间之情曲。余所见郑君文字,此篇最不苟者矣。”近年,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精选编集了一本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的《词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即收入郑振铎《词的启源》,并置于全书首篇。亦可见其学术价值。
关于词的发展,书中认为大致可分为四期。一是胚胎期,即“引入了胡夷里巷之曲而融冶为己有”的时期,这时的词是有曲而未必有辞的。二是形成期,即“利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以及皇族豪家的创制,作为新词”的时期,“曲旧而词则新创”。三是创作期,即词作家“进一步而自创新调,以谱自作的新词,不欲常常袭用旧调旧曲”,这时的曲与词(辞)有一部分均是新创的。四是模拟期,即作家“只知墨守旧规,依腔填词,因无别创新调之能力,也少另辟蹊径的野心”,“词的活动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唐初至开元天宝时为词史发展的第一期,开元天宝至唐末为第二期,五代至南宋末为第三期,元初至清末为第四期。这是发前人未发的见解,与鲁迅后来关于词从兴起到衰落的宏观见解在精神上颇为一致。郑振铎不仅从宏观上将词史分为四个发展期,在具体分析时他又将北宋词的发展与南宋词的发展分别分为三个阶段。他认为北宋词经历了从清隽健朴,到奔放雄奇,到循规蹈矩这样三个阶段;南宋词则经历了奔放,改进,凝固(雅正)这样三个阶段。他指出,这些变化跟词这一文体本身的发展规律、文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等有关;而且也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有关。例如,南宋词第二阶段以后渐趋僵化,就因为这时它“不仅与民众绝缘,也且与妓女阶级绝缘”,成为“差不多已不是民间所能了解的东西了”;这时的词失去豪迈的气概,也是当时统治阶级“升平已久”“晏安享乐”的社会现象的反映。郑振铎的这些分析与见解,体现了卓越的史识,已可略见唯物史观的星星光芒了。
书中通过独立思考,对胡适有关学术观点作了争鸣。例如,胡适据《杜阳杂编》,以为《菩萨蛮》调出于大中初,因此断定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决非真品。但郑振铎指出,《菩萨蛮》一调实已见诸《教坊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亦提到开元时即有此调,因此李白当然有填写此词的可能。虽然,这到底是不是李白所作,至今尚无定论,郑振铎也没有绝对肯定;但他强调指出不能用孤证来推翻一切他证,这显然比胡适要慎重得多。胡适还认为五代的词都是无题的,因为其内容都很简单,不是相思便是离别,不是绮语便是醉歌,所以用不着什么标题。郑振铎不同意这种皮相的看法,指出:“花间词人的作品,诚多咏离情闺思之作。然离情闺思之作,原是一切抒情诗中最多的东西,不独花间词为然。且这一期中,也不完全是离情闺思、宴席歌曲之作。”那么,为什么“无题”呢?他认为,这是词创作初期的一种现象,“大多数的词牌名,已是它们的题目了,它们的内容也和词牌名往往是相合的,所以更无需乎另立什么题目。”例如,当时《更漏子》写的便大多与更漏声有关,《杨柳枝》便与杨柳有关,《天仙子》便与仙女有关,等等。发展了一段时间后,词的内容与词牌不大切合了,但尚未完全离开词牌所含的意思,例如《渔父》,填词者未必直接歌咏渔家生活,但仍含有该词牌原有的鄙薄功名、甘隐江湖的意味。再发展到后来,内容与词牌没有必然的联系了,这时才必须另外再有一个题目。郑振铎的这些论述,显微烛隐,无疑比胡适高出一筹。
在具体作家作品分析评论中,书中也时有新见。例如,关于王安石在宋词史上的地位,前人均无特别的好评,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也不过附带一说而已。但此书中不仅肯定他在政治上变法图强的精神,而且认为他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其词“宜乎气格与别的词人们不同”,盛赞其“脱尽了《花间》的习气,推翻尽了温、韦的格调、遗规,另有一种桀傲不群的气韵”,“无论在格式上,在情调上”,都“大胆无忌的排斥尽旧日的束缚”。因此,郑振铎认为,王安石在词史上的地位是“为苏、辛作先驱,为第二期的词的黄金时代作先驱”。这是非常独到的创见,郑振铎自己也指出,这是“很少人注意及之”的。书中对柳永的词作了十分细致的艺术分析,并将其与《花间集》作了艺术上的比较,指出《花间集》的风格在于“不尽”,“有余韵”;而柳永则在于“尽”,在于“铺叙展衍,备足无余”。他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境界,不好随便评其优劣;“但这第二种的境界,却是耆卿(柳永)所始创的,却是北宋词的黄金时代的特色,却是北宋词的黄金期作品之所以有异于五代词,有异于第一期作品的地方。所以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含蓄二字,其词不得不短隽;北宋第二期的词,其特点全在奔放二字,其词不得不铺叙展衍,成为长篇大作。当时虽有几个以短隽之作见长的作家,然大多数的词人,则皆趋于奔放之一途而莫能自止。这个端乃开自耆卿。”这样精辟的分析,在当时其他论著中极为少见。不仅说透了柳永词的艺术特点,而且更进一步阐明了词从前期到黄金时期转化之际艺术风格上的变化脉络,以及柳永在其间所起的作用等。
除了关于词史以外,本书关于敦煌文学的论述在当时也是开创性的。陈子展对此就有高度评价。陈子展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第八章《敦煌俗文学的发见和民间文艺的研究(上)》之后,特地专门加了一段附记,指出郑振铎此书《敦煌的俗文学》一章,“是介绍敦煌发见的俗文学最详实而又最有见解的一篇文字”。并深为遗憾地说:“可惜我作文时不曾得着这篇文字作为参考材料,现在又来不及改动前稿了。”在《文学大纲》中,有关敦煌文学只是极简单地提到了一句;虽然这是在文学史著作上较早的记载,但毕竟过于简略了。(这当然是与当时很多材料流失至国外后尚未整理与公开有关的。)而本书中却有近三万字的论述。对于敦煌抄本的整理与研究,郑振铎并不是国内外最早的学者;但他无疑是迅速吸取当时敦煌学研究最新成果,并较早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评价的人,而且他还是我国较早亲赴法、英等国去查阅有关原件的人。书中指出,敦煌写本中“在文学上最可注意者则为俚曲、小说及俗文、变文、古代文学的钞本等等”。(按,所谓“俗文”的称呼,后郑振铎作了纠正,详见下述。)并认为:“就宗教而论,就历史而论,就考古学而论,就古书的校勘而论,这个古代写本的宝库自各有它的重要的贡献,而就文学而论,则其价值似乎更大。”因为,第一,发现了许多已佚的杰作,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很多诗等;第二,发现了大量的俗文学作品,使人们知道了小说、弹词、宝卷及很多民间小曲的来源。“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绝大的消息,可以因这个发现而推翻了古来无数的传统见解”。而推翻传统旧说,正是靠像郑振铎这样的研究者,用敏锐的史识对这批材料进行研究后取得的。
书中分别介绍与评述了敦煌发现的诗歌(包括民间杂曲、民间叙事诗和最初的词调)和散文(包括民间通俗小说),但认为:“敦煌抄本的最大珍宝,乃是两种诗歌与散文联缀成文的体制,所谓‘变文’与‘俗文’者是。”(按,“俗文”其实是变文的误称。)郑振铎强调指出变文是敦煌抄本中最可珍贵的发现,这很有眼力。他强调“它们本身既是伟大的作品,而其对于后来的影响,又绝为伟大。我们对于它们决不应该忽视!”他认为,变文对于后来中国文学的影响,可分为四个方面,即对宝卷与弹词的直接影响,和对小说与戏剧的间接的影响。这些论述可以说是自有中国文学史著作以来,第一次将这批封存了一千多年而又大多流失至国外的中国民间俗文学,公然抬到了文学殿堂的高座,其意义非同一般。这对于我国一九三○年代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是很有促进作用的。
在论述具体作品时,书中也有不少精彩见解。例如,关于《目连救母变文》,他在《文学大纲》中已简单地提及,并把它与但丁《神曲》并提,但当时他误以为它是小说;在本书中,他指出这是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叙述周历地狱的情况的,并把它与古希腊荷马的《奥特赛》、古罗马维吉尔的《阿尼尔》、但丁的《神曲》等相比较,指出:“在中国,本土的地狱,或第二世界的情形,则古代的作家绝少提起,仅有《招魂》《大招》二文略略的说起其可怖之景色人物而已。(那里所指的并不是地狱,不过是第二世界,即灵魂所住的地方而已。)直到了佛教输入之后,于是印度的‘地狱’便整个儿的也搬入了中国。”而这以前的地狱描写还不够详细。直到这本《目连救母变文》出现,我们才知道在唐代已有了这样详细的描写。郑振铎的这一精辟分析,对读者是深有启发的。
当然,本书亦略有不足之处。首先是作为断代史还缺少下半篇,作为“词史”则尚缺第四期(元初至清末)。其次是有些论述还不够精当,这或因当时史料缺乏所限,或因考订不周所致。例如,书中将敦煌发现的民间讲唱文学区别为“变文”与“俗文”两种,并试图指出其间的几点差异,但其实“俗文”是今人给这些作品编目或引用时自取的名称,其原本的名称就只有“变文”一词。后来,由于几种重要的首尾完备的变文写本的公布,才使郑振铎了解了这一点,并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及《中国俗文学史》等书中作了郑重的纠正。再如,本书中谈到有人怀疑五代时《花间集》中的词作家张泌与《全唐诗》中南唐的张泌不是一个人,但又认为“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姑从旧说”,仍以其为一人。其实这是两个人,后来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作了有力的考辨,纠正了此书中的说法。另外,我认为书中对变文的评价也略嫌过高。但是,这些不足之处显然是微瑕,而不足以蔽其美玉之光华的。
最后必须指出,本书又是一本命运非常不幸、非常寂寞的书。出版后不久,商务印书馆就惨遭日本侵略军轰炸,它的印刷纸版和仓库里的存书就都被烧毁了。因此,本书流传于世的很少,以后也从来没有再版过。因此,读过它的人也很少,也几乎没有人评论和引用过,连现在一些专门研究和评论词史的学者也不知有此书。甚至连一九九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全集》也没有收入。我曾呼吁出版社影印此书,可惜未果。我一直认为,本书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的,即使残缺也像断臂维纳斯一样具有特殊的“残缺美”,而且重新出版还具有抗议和铭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意义。我的这些想法对“民间出版家”黄曙辉兄说了,得到他高度赞同,多方联系,终于获得北京出版社领导的支持,重印有望。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近年来重印的出版社很多,而我觉得北京出版社出的那本校勘最为认真,因此,此书由他们重印是令我非常高兴的。
用户评价
坦率地说,初拿到这本书时,我有些担心其内容的艰深程度,毕竟涉及唐五代到两宋这么长一段历史跨度,学术门槛想必不低。然而,深入阅读后发现,作者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对一些复杂的理论和流派演变进行了极富创意的阐释。比如,书中对苏辛豪放词风形成的环境因素的剖析,引入了当时政治气候和社会思潮的分析,而非仅仅停留在文本细读层面,这种宏观视野令人耳目一新。再者,作者对于词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审美取向变化,有着独到的见解,将词从单纯的“艳科”提升到可以承载厚重历史感的艺术形式的转变过程,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本书的好处在于,它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入门者可以从中窥见宋词的概貌,而专业人士则能从中汲取新的研究灵感。它成功地架设起了一座沟通古典文学与现代读者的桥梁,让那些沉睡在故纸堆中的文字,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评分我个人对这类梳理古代文学史的著作一直抱有敬畏之心,因为这需要耗费研究者大量的精力去钩沉索隐,去辨析细微的差别。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在于其对“变化”二字的深刻把握。词史并非一条平滑的直线,而是充满了转折与张力。作者非常善于捕捉那些关键的转折点,比如北宋中后期词风的转向,以及南渡之后词人情感基调的剧烈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被历史的大潮所裹挟,又是如何被个体才情所塑造的,书中都有精彩的论述。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对比不同时期词人的作品,感受那种时代烙印带来的风格差异,不得不佩服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可以将如此庞杂的文献资料组织得井井有条,条理清晰,没有丝毫的芜杂感。它展现的不仅是词的发展史,更是一部中国士人心灵史的侧影,沉重而又壮阔。
评分读罢这本厚厚的史学著作,我内心激动不已。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仿佛带领我们穿越回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亲眼见证了词这种文学体裁的萌芽、成长与鼎盛。书中对唐五代到两宋词坛的梳理,并非简单的年代罗列,而是融入了深刻的社会背景分析。那些词人的命运沉浮,他们的创作心路历程,都被作者抽丝剥茧般地呈现出来。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词人风格差异的对比研究,构建了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宋词图景。阅读过程中,我时常停下来,掩卷沉思,想象着昔日词人面对的那些山河故土,那些家国情怀。这本书无疑是文学史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它不仅仅是一部学术专著,更是一场与古代文人的深度对话。每一次翻阅,都有新的感悟,仿佛每一次都有新的风景映入眼帘,那种发现的乐趣,是其他读物难以比拟的。它要求读者投入极大的耐心和思考,但回报是丰厚的,知识的海洋在眼前缓缓铺陈开来,令人心驰神往。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功底,简直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虽然是严肃的学术探讨,但叙事流畅自然,没有一般史书的晦涩难懂,反而充满了文学的韵味。作者对词史脉络的把握极为精准,从词的早期形态到格律的定型,再到不同流派的兴衰,逻辑清晰得如同手术刀般精准,让人想不深究都难。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论证观点时所引用的那些旁征博引的例证,那些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打捞出来的珍贵材料,被巧妙地嵌入到论述之中,使得每一个论断都有坚实的根基。阅读时,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学术探索的激情在字里行间跳跃。这已经超出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历史书”,它更像是一部由顶尖学者精心酿造的文学美酒,初品可能觉其醇厚,细品方知其回甘悠长,每一次啜饮都带来不一样的体悟。对于想要深入了解宋词发展史的同好来说,这本书绝对是案头必备的“圣经”级别存在,不读此书,实为憾事。
评分这本书的体例编排和论述视角,都体现了扎实的学问功底和创新的研究精神。它不是那种老生常谈的综述性文字,而是充满了辩证的思辨色彩。书中对一些传统上存在争议的词人归属或风格划分,作者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并且都提供了详实的论据支撑,让人读来心服口服,或者至少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尤其在对“词史”的定义上,作者似乎也在进行着一次重新的界定,将词的兴衰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了一个宏大且精密的叙事框架。我尤其欣赏那种在细节中见宏大,在宏大中不失细节的叙事手法。读完之后,感觉自己对宋词的认识不再是零散的篇章或个别名家,而是一个完整、有机的、不断演进的文学体系。这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反复研读的佳作,其价值绝非一蹴而就的阅读体验所能完全概括。
评分书很好,质量也不错,点赞。
评分大家小书,都是精华。
评分大家小书 唐五代两宋词史稿
评分书很好,质量也不错,点赞。
评分书不错,活动价格很优惠。
评分质量好,包装好,品质有保障,推荐购买。
评分为什么在运输之前没有给书籍提供海绵亦或泡沫等保护措施?
评分书很好,质量也不错,点赞。
评分大家小书,都是精华。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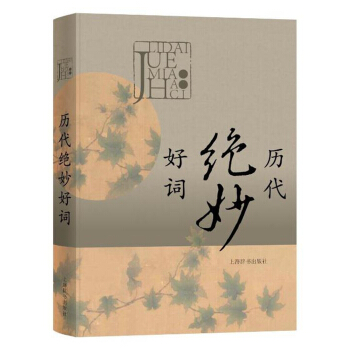


![绝佳拍档·消失的请假条 [小学中低年级]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95946/5923cf41N3127a2e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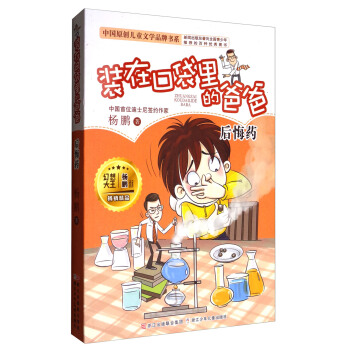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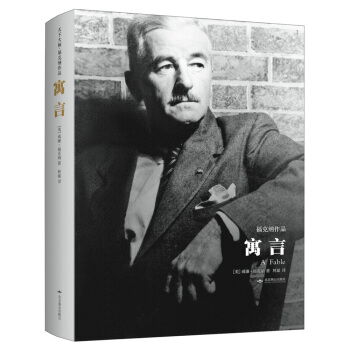



![学前经典阅读书系·世界童话精选(套装全16册) [3~6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98223/59e6faf1N12c6375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