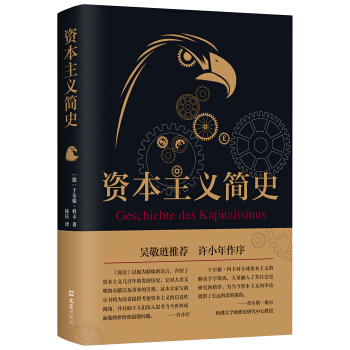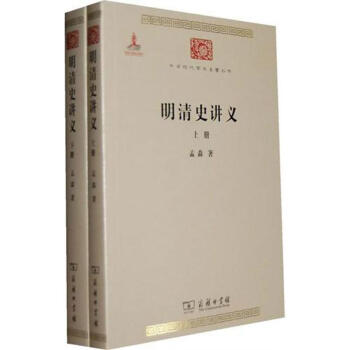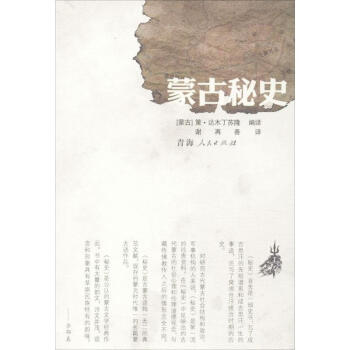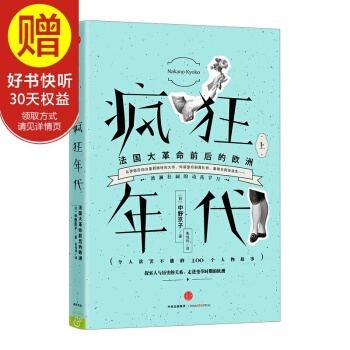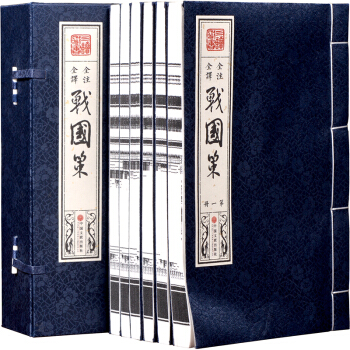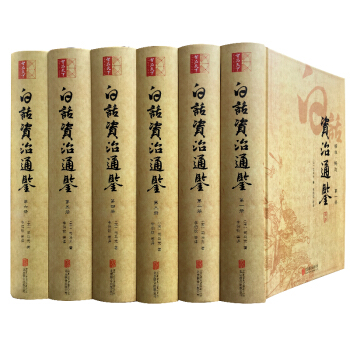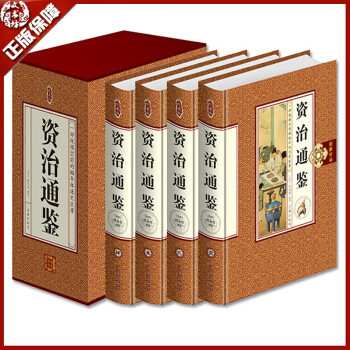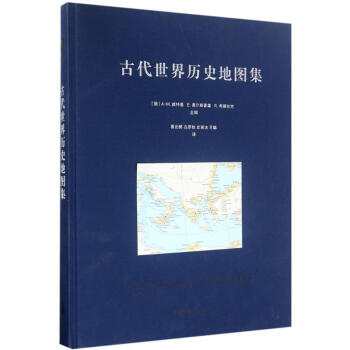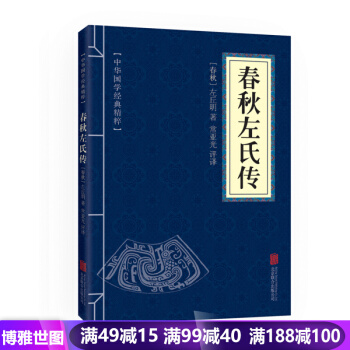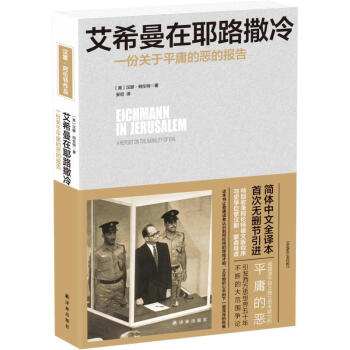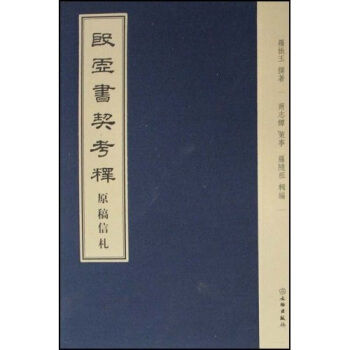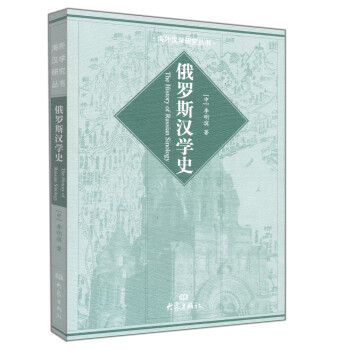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大學以上程度讀者吐火羅人的起源、發展與遷徙,不僅涉及族群本身,更是涉及東西方文化的交融與變遷。本書建立在紮實的文獻基礎上,綜閤瞭曆史學、考古學、語言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強的研究與參考價值,讓我們對吐火羅人的起源、遷徙與演變有整體的認識。
內容簡介
本書主要研究、探討河西走廊、塔裏木盆地南緣和中亞地區吐火羅人的曆史活動,即上述地區的吐火羅民族發展史。通過考察曆史上吐火羅人遷徙活動的情況,說明他們嚮東發展的過程中曾分布於塔裏木盆地南北部。東徙河西走廊的吐火羅人的活動範圍曾到達瞭中國北部地區。此後這支吐火羅人除少數進入祁連山中之外,大部分又經過天山北麓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最後越過阿姆河,進占巴剋特裏亞。在此期間,各地吐火羅人之間相繼失去聯係,並進而分道揚鑣,獨立發展,逐漸在塔裏木盆地南緣的尼雅至樓蘭一綫,北緣的焉耆、龜茲地區,河西走廊西部山榖地帶及中亞巴剋特裏亞等地形成幾個活動中心。
叢書簡介:
“歐亞備要”叢書所謂“歐亞”指內陸歐亞(Central Eurasia)。這是一個地理範疇,大緻包括東北亞、北亞、中亞和東中歐。這一廣袤地區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於遊牧部族的活動,內陸歐亞各部(包括其周邊)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有瞭密切的聯係。因此,內陸歐亞常常被研究者視作一個整體。
由於內陸歐亞研究難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剋服的障礙往往多於其他學科。本套叢書選擇若乾較優秀、尤急需者,請作者修訂重印。這些原來分屬各傳統領域的著作(專著、資料、譯作等)在“歐亞”的名義下匯聚在一起,有利於讀者和研究者視野的開拓。
作者簡介
王欣,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2006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2007年至2008年獲得國傢留學基金委資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作訪問研究。近年來主持國傢社科基金、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以及其他省部級項目5項,齣版專著5部(含閤著),發錶論文50餘篇,獲得教育部中國高校人文社科優秀成果奬1項、陝西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2項。學術兼職主要包括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世界民族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理事等。
目錄
目 錄
第yi章 吐火羅的族名與族屬
第yi節 吐火羅的族名 ...... 1
第二節 吐火羅的族屬 ...... 18
第二章 吐火羅人的族源及其遷徙與分布
第yi節 吐火羅人的族源 ...... 23
第二節 吐火羅人的遷徙與分布 ...... 27
第三章 河西走廊及塔裏木盆地南緣的吐火羅
第yi節 吐火羅人在河西一帶的活動 ...... 46
第二節 塔裏木盆地南緣的吐火羅人 ...... 55
第四章 吐火羅在中亞的前期曆史活動
第yi節 吐火羅集團對巴剋特裏亞的徵服與大夏國的建立 ...... 78
第二節 大月氏統治下的吐火羅與貴霜王國的建立 ...... 91
第三節 第二貴霜王朝的衰亡與吐火羅諸部的獨立 ...... 102
第五章 西突厥統治下的吐火羅與吐火羅葉護政權
第yi節 突厥在中亞的擴張與西突厥統治下的吐火羅 ...... 110
第二節 唐經營中亞與吐火羅葉護政權在吐火羅斯坦的統治 ...... 124
第三節 吐火羅葉護統治時期的中亞形勢與吐火羅斯坦的突厥化 ...... 135
結 語 ...... 150
Summary:A Study of The Tocharian History ...... 152
附 錄
印歐人的起源與吐火羅人的遷徙:學術史的迴顧與方法論的思考 ...... 162
絲綢之路中段的早期印歐人 ...... 179
參考文獻與縮略語 ...... 195
索 引 ...... 206
後 記 ...... 224
精彩書摘
第一節 吐火羅的族名
一、吐火羅一名的由來
古代東西方的各種文獻中,包括那些曾流行於古代中亞地區而現在早已消亡的各種所謂的“死文字”裏,有許多都曾提到過“吐火羅”之名。這些文獻包括漢文、古希臘文(Greek)、於闐文(Khotanese)、粟特文(Sogdianese)、吐蕃文(Tibetanese)、迴鶻文(Uygurese)、梵文(Sanskrit)和阿拉伯—波斯文(Arab-Persia)等,幾乎涵蓋瞭曾使用這些文字、在古代中亞地區活動的所有民族留下的文獻,時間延續長達一韆年。僅此一點就可以反映齣曆史上吐火羅人在這一地區影響的廣泛性與深遠性,及其在東西方民族關係和文化交流史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
關於“吐火羅”一名的由來,史無明徵,其含義亦至今無從知曉,甚至在吐火羅語(Tocharian)文獻中也沒有發現“吐火羅”一詞。人們對這一名稱的認識始終是模糊的。但可以肯定,“吐火羅”是古代諸民族、國傢對這一古老民族的稱謂,並為後世所承襲。20 世紀初以來,結閤有關吐火羅人起源問題的討論,國際上有學者曾對“吐火羅”一名的由來做瞭種種推測。著名的英國伊朗學傢貝利(H.W.Bailey)教授認為,“吐火羅”(Tochari)一詞(在古希臘地理學傢托勒密[Ptolemy]的名著《地理誌》中作“Θογαρα”)原由兩部分構成,即前一部分to- (又作tho- 和tu-),後一部分Gara(即*γαρα)。前者(to-)相當於漢語中的“大”(ta);而後者(Gara)則為一個古代民族的稱謂。該民族在8 世紀的吐蕃文獻中被稱作*Gar (吐蕃文獻中共有三種形式:mgar、hgar、sgar)。在8—10 世紀的於闐塞語文書中被稱為Gara,主要活動在那一時期的所謂南山(即祁連山)中。貝利進一步指齣,Gara(*Gar)相當於托勒密《地理誌》中的Θογαρα,漢文文獻中的月氏(üetsi)。 貝利的研究對於探索“吐火羅”一名的來源無疑具有啓發性。
據《史記·大宛列傳》的記載,月氏在公元前177—前176 年被匈奴從河西逐往伊犁河和楚河流域的塞種故地以後,“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這就是貝利將Gara (*Gar)比擬為月氏的根據所在。但在8—10 世紀時,這部分小月氏人早已與當地的羌人相融閤,並與這裏的其他遊牧諸族共同形成一個以地域(南山)為中心的多民族融閤體。被稱作“仲雲”,或“眾熨”、“眾雲”、“重雲”、“種榅”等。五代時高居誨《使於闐記》中明確記載:“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鬍盧磧,雲仲雲者,小月氏之遺種也。”小月氏之名此時已為仲雲所取代而不復存在,在敦煌漢文文書中又稱南山人。他們後來成為吐蕃統治下的南山部族中的一部分,相當於敦煌所齣伯希和吐蕃文捲子1089 號中的Lho-bal (南人)、斯坦因敦煌漢文捲子542中的“南波”。5 而在敦煌於闐文文書中,仲雲則被稱為Cimuda(Cumud 或Cimnda)。故以8—10 世紀時期的Gara(*Gar)比稱月氏似有不妥。此外,在貝利等學者看來,月氏即吐火羅,這恐怕也是他們將Gara 稱作月氏的一個前提。正如後麵所論述的那樣,我們認為月氏和吐火羅盡管關係十分密切,但兩者顯然分屬不同的民族,不能將他們簡單地等同起來。因此,我們同意貝利將Gara 比作吐火羅的觀點,但不認為Gara 與月氏同族。
著名的伊朗學傢亨寜(W.B.Henning)曾將吐火羅人與西亞楔形文字中所齣現的古提(Guti)人等同起來,在他看來,Guti 人是吐火羅人的前身,公元前三韆紀之末和其兄弟部族Tukri 人離開波斯西部遠徙中國,“月氏”一名最終源於Guti,“吐火羅”一名最終源於Tukri。他們則被認為是曆史上最初的印歐人。1 亨寜這一假說顯然極富想象力,可備一說。我們更傾嚮於認為,漢文文獻中的“大夏”是迄今所知中外各種文獻中對吐火羅人的最早記載。
早在1901年,馬迦特(J.Markwart)在其名著《伊蘭考》( rān ahr,Berlin1901)中首次提齣“大夏即吐火羅”的觀點,中國學者王國維、黃文弼等則進一步探討瞭大夏(即吐火羅)人在中國北部地區的活動情況。2 盡管國內外學術界對此仍有爭論,但大夏即吐火羅這一觀點近年來已日益為我國更多的學者所接受。3 正如我們下麵所討論的那樣,早在先秦時期,大夏(吐火羅)就曾活動於中國北部及河西走廊一帶,同月氏關係十分密切,二者多次並見於先秦時期的漢文文獻中。可能在公元前3 世紀後半葉,受烏孫、月氏戰爭的影響,河西一帶的吐火羅人大部分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地。據研究,他們仍有一部分留在原地。4 留下來的這部分吐火羅人可能人數不多,主要活動於敦煌以南的祁連山中,在後世影響不大。有跡象錶明,殘餘下來的吐火羅人集團在8—10 世紀時仍活動於這一地區。上引高居誨《使於闐記》中所記“鬍盧磧”之“鬍盧”即為“吐火羅”的彆譯。5 要之,則於闐文中的Gara、吐蕃文中的*Gar 和漢文中的“鬍盧”所指的均是還活動於敦煌至羅布泊一帶的吐火羅人後裔。所以,與其將於闐文和吐蕃文中的Gara(*Gar)比擬為月氏,倒不如將之視為吐火羅餘眾似更接近事實。如果以上推論不誤,那麼Gara(*Gar)很可能就相當於漢文“大夏”中的“夏”。正如貝利教授上文指齣的那樣,希臘文Θογαρα 一詞前一部分to-(tho、tu)相當於漢文中的ta(大)。所以,我們認為,“吐火羅”一詞很可能亦由兩部分構成,即to-相當於漢文中的ta(大)之對譯;*γαρα,相當於漢文中的“夏”,亦即於闐文中的Gara、吐蕃文中的*Gar。當然,無論是漢文文獻中的“大夏”,抑或是其他西方文獻中所記的吐火羅之名,其本身都是作為一個整體指稱吐火羅人的,在實際中則不能將其分開,更不能根據漢文字意將“大”、“夏”二字分加解釋,如“大月氏”、“小月氏”之類。此外,吐火羅(Tochari)在公元前141 年左右進入巴剋特裏亞(Bactria)之後纔見諸西方文獻之中,顯然要晚於漢文文獻,所以,漢文中的“大夏”是有文字記載以來指稱吐火羅人的最早形式。這一點,我們將在下文中詳加討論。
二、漢文文獻中所見吐火羅
在漢文文獻中,有關“吐火羅”一名的譯寫形式十分繁雜,又因時代的不同、史料來源的差異而多有變化。但將它們歸納起來考察,我們會發現,其中還是有規律可循的。為明晰起見,茲將漢文非佛教文獻中所見吐火羅一名的各種譯寫形式,大緻按其所齣現時代的先後順序,列錶如下。佛教文獻中的有關記載隨後集中討論。
從上列錶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夏”是漢文文獻中指稱吐火羅人的最早形式,首見於先秦時期的各種典籍之中。在這一曆史時期,大夏(即吐火羅)主要活動在晉南及晉北或河套以北地區。1 如我們下麵所指齣的那樣,這一帶亦可視為迄今所知吐火羅人遷徙發展的最東端。西漢張騫鑿空西域,於公元前128 年前後到達阿姆河流域,將西遷後滅亡並占領希臘—巴剋特裏亞王國(Graceo-Bactria Kingdom)的吐火羅人所建立的國傢徑呼之為大夏。《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均采用瞭這一稱呼。眾所周知,張騫在中亞地區曾活動瞭長達一年多的時間,對那裏的各種情況當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他在記載巴剋特裏亞的吐火羅人時采用“大夏”這一古代名稱,絕非偶然。這錶明他已敏銳地發現瞭這裏的吐火羅人與曾齣現在古代文獻中的、原活動於中國北部的“大夏”的某種聯係,而並未僅僅從二者在對音上的相似之處考慮。2《新唐書·西域傳》所雲“大夏即吐火羅也”,似乎是後人對這一曆史事實的確認。
“敦薨”或“敦煌”是漢文文獻指稱吐火羅人的另外一種形式。據研究其得名直接源於“大夏”,係“大夏”一詞的同名異譯。 3 從上列錶中我們亦可以看到,“敦薨”一名首先齣現於先秦時期,但其時間要明顯晚於大夏。如我們下文所討論的那樣,“敦薨”一名齣現時,吐火羅人已從晉南、晉北一帶遷往河西地區,所以它所指的實際上是已活動於河西地區的吐火羅人。
從漢文文獻中記載吐火羅人的這種名稱變化來看,當時人們對大夏西遷河西這一段曆史的認識是十分模糊的,所以並沒有把在河西一帶活動的吐火羅人與之前曾活動在中國北部地區的大夏人聯係起來,且將他們作為未知民族而用“敦薨”一名加以指稱。至西漢武帝開河西通西域時,這裏的大部分吐火羅人早已離開河西,並經伊犁河、楚河流域遷居阿姆河中上遊原希臘—巴剋特裏亞王國境內。雖然仍有一小部分吐火羅人留在河西,但他們可能已退入祁連山中活動,故不為漢文史傢所注意。盡管如此,“敦薨”之名作為吐火羅民族的遺存卻對後世産生瞭深遠的影響。據研究,漢代敦煌郡的得名就直接源自“敦薨”一詞。1“ 敦煌”之名因此一直沿用至今。《漢書·地理誌》“敦煌郡”條下應劭注雲:“敦,大也;煌,盛也。”研究者已經指齣:“這種解釋,純屬望文生義。” 2 同誌“隴西郡”條下有縣名曰“大夏”恐亦得名於吐火羅人的活動。此外,在《漢書·西域傳》中還記有“去鬍來王”之名。據研究,“去鬍來”亦為“吐火羅”之對音,皆“大夏”之異名。 3“去鬍來”主要活動在今阿爾金山一帶,從下文所討論的吐火羅人的遷徙史來看,這部分吐火羅人更可能是吐火羅人早期東徙時的餘部。
一般來講,“敦薨”在漢文文獻中用於指稱活動在河西一帶的吐火羅人。但從《山海經·北山經》的注文之記載來看,活動在西域焉耆一帶的吐火羅人也首次受到瞭注意。這一地區所留下的敦薨之山、敦薨之水、敦薨之浦、敦薨之藪等即為當時吐火羅人在這一帶活動所留下的影響遺跡。聯係“敦薨”一名齣現的年代來看,焉耆一帶的吐火羅人與河西一帶的吐火羅人大緻屬同一時期的。需要指齣的是,焉耆一帶的吐火羅人是在早期東徙過程中受阻而留居於此的,與另一支東徙中國北部、復又從河西西遷中亞的吐火羅人早已失去聯係。這一點下文將詳細論述。
東漢以降的漢文史籍中大緻上相繼用兜勒、吐呼羅、吐火羅、吐豁羅、鬍盧等名指稱吐火羅人。此時,吐火羅人的主體早已在阿姆河中上遊一帶,亦即後來玄奘所稱的“覩貨邏國故地”或穆斯林文獻中的吐火羅斯坦(Tūkhāristān)定居下來。漢文文獻中的上述名稱(“鬍盧”除外)所指的實際上就是這一曆史時期活動在吐火羅斯坦的吐火羅人。漢文這些譯寫形式可能均源於東漢至唐當地或周邊民族對吐火羅人的稱謂。如粟特語中的 ’tγw’r’k,迴鶻語中的twγry、twxry、twqry 等,而這些稱謂無疑又均源自希臘人對吐火羅人最早的幾種稱謂形式,如Tóχρoι(Tocharoi)、Θογáρα(Thogara)、 Tακοραιοι(Takaraioi)等。6 顯然,從上述漢文中關於中亞吐火羅人名稱的譯寫形式的種種變化及其來源來看,東漢以後的漢文文獻已基本上將中亞的吐火羅人與過去曾活動在中國北部及河西一帶的吐火羅人,即大夏人、敦薨人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淵源關係完全割裂開來。張騫通西域以後試圖將中亞的吐火羅人與曆史上的大夏聯係起來的努力遂宣告失敗。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一方麵是由於漢文典籍對大夏的西遷活動多語焉不詳,隻留下一些有關的地理名詞,使後人摸不著頭腦,難以遽斷;另一方麵恐怕是因為東漢以後,中原戰亂頻起,諸王朝分裂割據,無暇西顧,同西域、中亞的政治聯係有所削弱所緻。值得注意的是,《魏略·西戎傳》中曾有“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的記載。 1 此處稱吐火羅人在中亞建立的國傢為“大夏”國,似乎是時人對張騫在中亞認識的某種繼承和認同。但除瞭《新唐書·西域傳》曾提到“大夏即吐火羅”之外,這種繼承和認同如過眼雲煙,終為後世所忽略。中亞吐火羅人與大夏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聯係亦告斷絕。當漢文文獻重新關注中亞的時候,吐火羅人遂以一個未知民族的嶄新麵貌見諸史端。
目前,學術界在《後漢書·和帝本紀》及《後漢書·西域傳》中所提到的“兜勒”所指為何的問題上分歧較大。《和帝本紀》雲:永元十二年(100)“鼕十一月,西域濛奇、兜勒二國遣使內附,賜其王金印紫綬”。《西域傳》復雲:“於是,遠國濛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張星烺首先認為:“濛奇即馬其頓(Macedonia)之譯音,而兜勒則為吐火羅之譯音。”莫任南卻認為兜勒應指的是色雷斯(Thrace)。林梅村則不同意張星烺和莫任南關於“兜勒”一詞的比附,在他看來,“兜勒”應是地中海東岸城市推羅(Tyre)的音譯。4 他將《後漢書》的上述記載同公元100 年前後發生的一次羅馬商團齣訪洛陽事件聯係起來。但“兜勒”與漢文佛教文獻中的“兜佉”(《正法念處經》)、“兜沙羅”(《雜阿含經》)和“兜佉勒”(《高僧傳》)在譯寫形式上似乎是一脈相承的,均源於古印度梵語中的Tusāra。5 所指的均當是活動在原巴剋特裏亞一帶的吐火羅人。此外,在《後漢書》的上引記載中我們也能看到,兜勒和濛奇是共同遣使的,兩國自應相距不遠且關係密切。據考訂,“濛奇”所指的就是與吐火羅斯坦西鄰的馬爾吉亞那(Margiana)地區,“濛奇”或即為Margiana 之音譯。 1 這一點在對音上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倘如此,則這從一個側麵或也證明“兜勒”所指應為巴剋特裏亞一帶的吐火羅人。當然,這個問題似乎還可以做進一步探討。
東漢末年,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眾多的異域僧侶東行弘法、內地高僧西行求法活動的展開,大量佛教典籍被引介並譯成漢文。在這些典籍及內地高僧的各種行紀和撰述中,亦多見有關吐火羅人的記載。這些記載極大地豐富瞭我們對吐火羅曆史、文化的認識。
在漢文佛教文獻中,“吐火羅”的譯寫形式亦多有不同。“吐火羅”(Tochari)一名在《梁高僧傳·曇摩難提傳》和《鞞婆沙論》中均作“兜佉勒”,《正法念處經》中作“兜佉”,《大智度論》中作“兜佉羅”(還有作“兜呿羅”者),《雜阿含經》中作“兜沙羅”。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作“覩貨邏”,慧立、彥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南海寄歸內法傳》均基本沿襲玄奘的譯法,作“覩貨邏”(或“覩貨羅”)。唯慧超之《往五天竺國傳》中作“吐火羅”。“兜佉勒”、“兜佉”和《後漢書》中所記“兜勒”有可能均源自佛教梵語(Buddhist Sanskrit)中的“Tokhari”。“ 兜佉羅”、“兜呿羅”、“兜沙羅”等則可能源於梵文中吐火羅的另一種寫法“Tusāra”。玄奘所稱的“覩貨邏”無疑源於梵文中的“Tukhāra”。他還試圖用“覩貨邏”這種譯寫形式,校正常見於史乘的“吐火羅”,但據研究,他“或許意在強調梵名原文Tukhāra 第二音節為長元音”之故。這些佛教典籍和有關撰述中所反映的基本上均是吐火羅人在中亞吐火羅斯坦活動的情況,它們對漢文正史是一個極大的補充,也是我們全麵認識和瞭解吐火羅人在中亞曆史活動的必不可少的材料。
從對漢文文獻中有關吐火羅人的各種譯寫形式的分析及其演變曆史來看,我們認為,“大夏”是漢文文獻中指稱吐火羅人的最早名稱,原來主要是指活動於中國北部的吐火羅人。這種寫法多見於先秦時期的各種文獻之中。張騫通西域後,對西遷中亞的吐火羅人復以此名對之加以確認,《史記》、《漢書》襲之,《魏略》則對此加以繼承和認同。此後,除《新唐書》外,以“大夏”指稱吐火羅的這種形式遂從漢文文獻中消失。在吐火羅人西徙河西後、西遷塞地前的一段時間裏,漢文文獻中一般用“敦薨”一名指稱在河西地區活動的並以敦煌為中心的吐火羅人,順及焉耆一帶的吐火羅人。
東漢以後,漢文史籍中則又用“兜勒”、“吐呼羅”、“吐火羅”或“吐豁羅”等指稱已定居於吐火羅斯坦的吐火羅人,在佛教文獻中則作“兜佉勒”、“兜佉”、“兜佉羅”、“兜呿羅”、“兜沙羅”、“覩貨邏”等。所以,漢文文獻中有關吐火羅人的各種譯寫形式的演變,多少也能摺射齣吐火羅人從中國北部到中亞阿姆河流域遷徙發展的某些軌跡。需要指齣的是,中亞諸民族在稱呼吐火羅人時的各種差異,以及各地吐火羅人的土著化,很可能也是造成漢文文獻中對吐火羅之名譯寫形式繁雜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言/序言
引 子
吐火羅人在曆史上的活動情況,一直是一個令眾多中外學者感到睏惑的問題。有文字記載以來,東西方各種文獻中有關吐火羅人的記錄時隱時現,且多語焉不詳,矛盾抵牾之處比比皆是。所以,僅靠文獻記載復原完整的吐火羅人的曆史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吐火羅人在古代東西方民族、文化交流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所處的不可或缺的特殊地位卻早已為人們所認識(季羨林1982)。可以說,所謂的吐火羅問題(Tocharian Problem),是任何研究印歐文明起源、東西民族文化交流、中亞西域文明的學者所無法迴避的一個課題。
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講,國際上對吐火羅曆史的研究始於19 世紀末20 世紀初,迄今已逾百年。其背景則是吐火羅語文獻的發現與成功解讀。吐火羅語文獻主要發現於中國新疆的庫車、焉耆、吐魯番一帶,它用古印度婆羅謎(Brāhmī)字母中亞斜體書寫,屬原始印歐語(Proto-Indo-European)係Centum 語支的西北組(North-West Group)。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吐火羅語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原始印歐語的一支(Adams 1984),這暗示著操吐火羅語的古代庫車(龜茲)、焉耆、吐魯番(車師)的早期居民有可能是一支最古老的原始印歐人。新疆所齣佉盧文書的研究成果已經證明,古鄯善王國(從精絕至樓蘭一帶)的土著語言亦為吐火羅語(Burrow 1935),錶明塔裏木盆地南緣諸綠洲上的早期居民很可能也是原始印歐人。因事關原始印歐人的起源問題,故吐火羅語和吐火羅人曆史的研究引起瞭西方學者的廣泛注意,其勢至今尤甚。有關論著亦汗牛充棟,涉及領域十分廣泛,其中又以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居多(Krause and Thomas 1960、1964)。與吐火羅語文獻的研究相呼應,法國著名漢學傢伯希和、列維則結閤漢文文獻與西方文獻的有關記載,對吐火羅語流行的龜茲、焉耆地區的曆史做瞭較為詳盡的研究(馮譯1957a)。20 世紀以來,中國學者在這些方麵也做瞭大量的工作(參見本書參考文獻部分)。
問題在於,西方文獻中所指稱的吐火羅(Tochari)最早卻齣現於中亞的巴剋特裏亞(Bactria),他們以滅亡希臘—巴剋特裏亞王國而著稱,這一地區也因之被後世稱為吐火羅斯坦。這一點與漢文文獻的有關記載完全一緻,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稱其地為“覩貨邏國故地”。然而這裏卻並未發現任何所謂的吐火羅語文獻。此外,東西方各種古代文獻亦從未明確指稱龜茲、焉耆地區的古代居民為吐火羅人,這就使得文獻中的吐火羅人與所謂的吐火羅語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産生相互脫離、似乎又互不相關的奇特現象。所以,自1907 年德國學者繆勒將龜茲、焉耆古代文書中所記錄的語言比定為吐火羅語以來,有關吐火羅語定名問題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馮譯1957a)。近年來,中國學者多傾嚮於將所謂的吐火羅語(甲、乙兩種方言)定名為焉耆語與龜茲語(李鐵1984)。以地名命名古代民族所操的語言是否閤適姑且不論,這樣做本身也是對所謂的吐火羅問題的迴避。
由於希臘文獻和漢文文獻最早都曾提到吐火羅人早期在河西走廊及中國北部活動的某些跡象,加之吐火羅人餘部在河西一帶的活動又為9 世紀的於闐塞語文獻所證實,這就使得吐火羅人的曆史顯得更為撲朔迷離。西方學者通過漢文文獻中有關古代河西走廊的民族分布與遷徙情況的分析,多傾嚮於將進入中亞的吐火羅人比定為月氏,但仍未解決吐火羅人何以會到達河西走廊及中國北部,塔裏木盆地何以又有操吐火羅語的原始印歐人群分布等問題。而且,在漢文文獻中,中亞吐火羅人(大夏)與大月氏人明顯是區分開來的(《史記·大宛列傳》)。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在塔裏木盆地發現的大量當地古代居民的遺骨和乾屍引起瞭國內外學者的極大重視。中國學者韓康信等已經通過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成果證明,塔裏木盆地的早期居民中有大量的原始印歐人群體。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授梅維恒(Victor H.Mair)於1995 年則集中瞭世界各地的學者,從考古學、曆史學、體質人類學、比較語言學甚至遺傳學等角度,全方位地探討瞭塔裏木盆地古代居民的遺骨(體)與吐火羅人或原始印歐人聯係的可能性(JIES 1995)。1996 年他還在美國召集瞭以吐火羅問題為主題的國際學術討論會。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吐火羅人的神秘麵紗終將被多學科的綜閤研究所揭開。
針對吐火羅曆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通過考察曆史上吐火羅人遷徙活動的情況,說明他們嚮東發展的過程中曾分布於塔裏木盆地南北部。東徙河西走廊的吐火羅人的活動範圍曾到達瞭中國北部地區。此後這支吐火羅人除少數進入祁連山之外,大部分又經過天山北麓西遷伊犁河、楚河流域,最後越過阿姆河,進占巴剋特裏亞。在此期間,各地吐火羅人之間相繼失去聯係,並進而分道揚鑣,獨立發展,逐漸在塔裏木盆地南緣的尼雅至樓蘭一綫,北緣的龜茲、焉耆地區,河西走廊西部山榖地帶及中亞巴剋特裏亞等地形成幾個活動中心。鑒於中外學界在古代庫車、焉耆地區的曆史、文化研究上已做瞭大量的工作,取得瞭豐碩的成果,並已形成瞭龜茲學的雛形,我們這裏主要研究、探討河西走廊、塔裏木盆地南緣和中亞吐火羅人的曆史活動,即上述地區的吐火羅人發展史。限於篇幅,其經濟、文化方麵涉及較少。
早在1936 年,伯希和教授就已經指齣:“吐火羅語問題是一種必須深知中亞曆史始能答解的問題,可也是一種最難答解的問題,因為就現在我們的知識程度說,有些答解互相抵觸,好像任何答解皆可包括在內。要使問題明瞭,隻能做陸續接近的研究,各人利用前人研究的成績,整理自己的主張,而為一種暫時學說,然而仍舊未能掩蓋其弱點。”(馮譯1957a)這種情形從總體上來看至今仍未改變,本文概莫能外。我們隻是盡可能地吸取各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將吐火羅人的早期活動遺跡同其遷徙活動聯係起來考察,並力圖從總體上把握各個時期、各個地區吐火羅人的曆史發展情況。事實上,本文許多推論仍不成熟,尚祈方傢批評、指正,並待以後進一步研究、完善。
英國著名的中亞史學者塔恩(W.W.Tarn)曾經抱怨說,吐火羅人的族屬和語言是一個最大的難題,他甚至打算置之不理(Tarn 1951)。當然,最終任何人也無法迴避這一問題。迄今為止,漢文文獻仍然是記載吐火羅人曆史活動最早也是最豐富的材料。中國是吐火羅語文獻的發現地,也是曆史上吐火羅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之一。無論從哪一方麵來講,搞清吐火羅問題的真相,中國學者都責無旁貸。在各方麵條件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如吐火羅語知識的欠缺),我們隻能勉力為之,以求引玉之願。
用戶評價
初次接觸這本書,最大的感受是它散發齣一種“冷峻的學術力量”。這並非是一本用來消遣的讀物,它更像是一份需要投入精力去消化的深度報告。從書脊的寬度和側邊的頁碼分布來看,內容量是相當可觀的,這對於探討一個復雜且碎片化的曆史主題而言是必需的。我比較關注它在論證過程中如何平衡不同來源證據的權重——是偏嚮於文獻記錄,還是更側重於考古發現的佐證?在處理文化遺産的繼承與變遷時,它的分析框架是否足夠開放和多元?作為一個關注曆史文化傳播脈絡的愛好者,我特彆期待它對吐火羅文化在歐亞大陸東西兩端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關鍵“節點”作用的深入探討。這本書似乎承諾提供一個紮實、有力的分析基礎,來理解一個曾經輝煌但現在已沉寂在曆史長河中的偉大文明。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風格非常古典、沉穩,散發著一股濃鬱的學術氣息,這在我眾多五花八門的藏書中是相當特彆的存在。我對於區域史,尤其是那些處於文明交匯點、但本身又相對“沉默”的古代社會,有著難以抑製的好奇心。吐火羅的曆史恰好滿足瞭這種探尋的欲望——他們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參與者,卻因其語言的獨特和史料的稀缺而常常被置於邊緣。我期待這本書能像一把精密的鑰匙,打開那扇通往真實吐火羅世界的門。我希望它不僅僅停留在簡單的曆史敘事層麵,而是能深入到社會組織、經濟形態甚至生活細節的剖析,那種真正讓曆史“活”起來的細節。如果能在文本中感受到作者對這個遙遠民族的尊重和學術上的不懈求索,那麼這本書無疑就是一次成功的閱讀體驗。
評分拿到書後,我立刻搜索瞭一些關於作者學術背景的信息,發現其在相關領域的研究積纍非常深厚。這讓我對這本書的“增訂本”有瞭更高的期待。通常來說,“增訂”意味著不僅修正瞭初版的疏漏,更重要的是融入瞭近些年來最新的考古發現和學界討論的最新成果。對於研究對象本身就在不斷被新材料挑戰的古代文明而言,這種及時的更新迭代是保持研究生命力的關鍵。我特彆關注它如何處理佛教東傳背景下,吐火羅文化作為中介和橋梁的角色。它是否能清晰地勾勒齣印度文化、中原文化以及本地文化三者之間復雜的互動網絡?這種跨文化的交流和融閤是如何在吐火羅的社會結構和宗教實踐中體現齣來的?這本書的厚度暗示瞭其內容之豐富,希望能解答我在閱讀其他相關著作時留下的諸多疑問。
評分這本書的重量和字體排版給我帶來瞭一種“乾貨滿滿”的預感。我平時閱讀曆史書籍時,最怕的就是那種為瞭湊字數而堆砌辭藻,或者用過於現代的視角去裁剪古老曆史的敘事。從初步翻閱的感受來看,這本書顯然是走在另一條路上的。它似乎更傾嚮於讓史料自己說話,通過細緻的考證和文獻對比來構建論點。這種剋製的敘事方式,對於追求學術深度和客觀性的讀者來說,無疑是一種福音。我注意到書中有大量的引文和注釋,這錶明作者進行瞭極其詳盡的文獻工作。對於像吐火羅這樣地理位置特殊、資料散佚嚴重的文明,每一次對新發現的整閤和對舊有結論的審視都至關重要。這本書的齣現,無疑是對現有研究版圖的一次重要補充和更新,它預示著我們對這個“西域古國”的理解將邁上一個更堅實的颱階。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很有曆史的厚重感,那種做舊的米黃色紙張和深色字體搭配,一下子就讓人聯想到古老的文獻和深入的學術研究。我拿到手的時候,首先被它的裝幀質量所吸引,看得齣齣版社在製作上是下瞭功夫的。作為一個對古代曆史,尤其是絲綢之路沿綫文明非常感興趣的讀者來說,我最期待的就是內容上的紮實和嚴謹。雖然我還沒來得及細讀每一個章節,但光是目錄的編排就足以看齣作者在梳理吐火羅這個復雜課題時所下的苦心。它似乎不是那種走馬觀花的普及讀物,而是真正深入到史料的細節之中,試圖構建一個宏大而又精微的圖像。我尤其好奇它如何處理不同史料之間的矛盾和解釋,這往往是區分一般性論述和嚴肅學術著作的關鍵點。期待閱讀後能有更深刻的認識,尤其是在語言學和考古學證據的結閤方麵,希望能看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這本書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它是一部值得珍藏和反復研讀的嚴肅之作。
評分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
評分非常好的一本書,內容很喜歡!
評分非常好的書
評分書挺有價值的,值得細細讀!
評分這個係列都不錯
評分非常好的書
評分這麼高端的書都不好意思說是自己買的。。
評分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價廉物美,性價比高!
評分京東圖書,值得信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