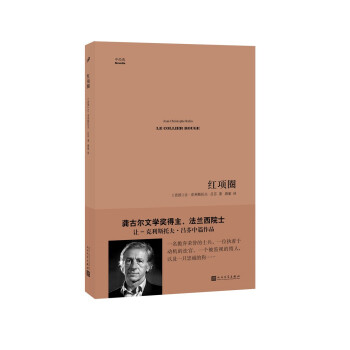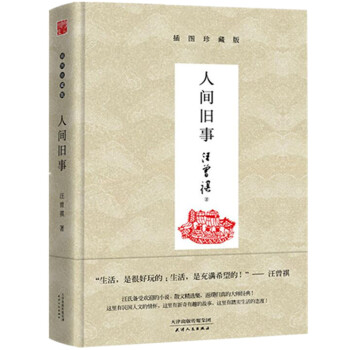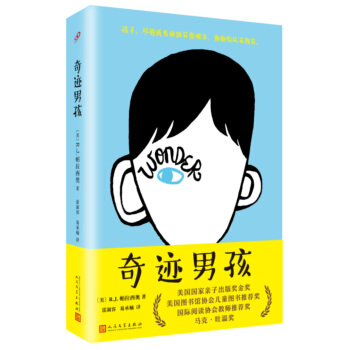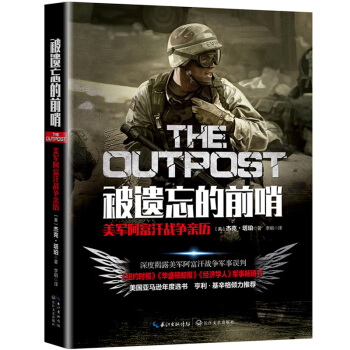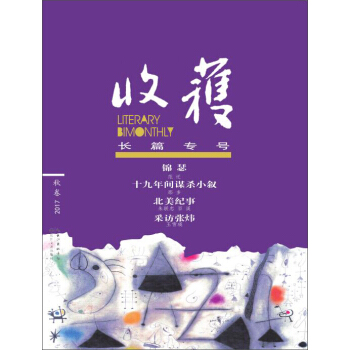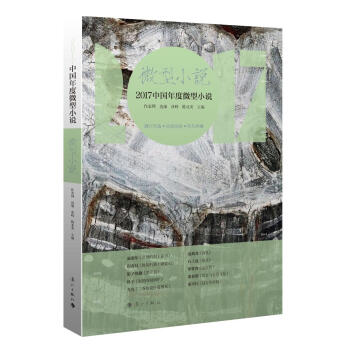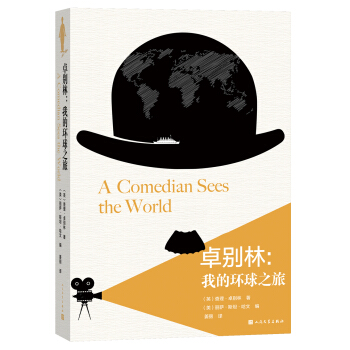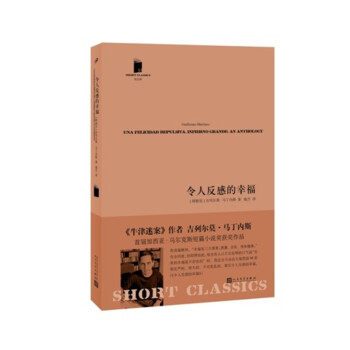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牛津迷案》作者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继博尔赫斯后第二位在《纽约客》上刊登短篇小说的阿根廷作家
首届加西亚·马尔克斯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本书是阿根廷当代著名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包含十九篇短篇小说,皆出自两部集子:《大地狱》和《令人反感的幸福》。《大地狱》出版于1989年,是马丁内斯的第一部作品,此书让他在文坛崭露头角,被评论为具潜力的阿根廷当代作家;2009年,同名短篇《大地狱》的英译文在美国《纽约客》刊登,他成为继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后第二位登上此杂志的阿根廷作家,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令人反感的幸福》出版于2013年,翌年荣获首届加西亚?马尔克斯短篇小说奖。全书语义微妙,视角独特,整体和谐统一。
内容简介
本书是阿根廷当代著名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的短篇小说自选集,包含十九篇短篇小说,皆出自两部集子:《大地狱》和《令人反感的幸福》。《大地狱》出版于1989年,是马丁内斯的第一部作品,此书让他在文坛崭露头角,被评论为具潜力的阿根廷当代作家;2009年,同名短篇《大地狱》的英译文在美国《纽约客》刊登,他成为继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后第二位登上此杂志的阿根廷作家,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令人反感的幸福》出版于2013年,翌年荣获首届加西亚?马尔克斯短篇小说奖。全书语义微妙,视角独特,整体和谐统一。作者简介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1962— ),阿根廷当代著名作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数学系教授。生于阿根廷中部港口城市白湾。在布宜斯艾利斯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他曾赴牛津大学数学研究所进行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由此受到启发,创作小说《牛津迷案》。该书于2003年出版后即获得当年度西语文坛大奖——阿根廷行星文学奖。2007年,马丁内斯推出长篇小说《露西亚娜?B的缓慢死亡》,被翻译成二十种文字,并入选当年西班牙年度十大好书。此外,马丁内斯还著有专著《博尔赫斯与数学》、长篇小说《象棋少年》,以及两部短篇小说集。精彩书评
《令人反感的幸福》通过一种奇特的视角,将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恐怖、幻想和奇特一一展现出来,技艺娴熟。——首届加西亚·马尔克斯短篇小说奖颁奖词
在我造访过的许多“地狱”里,马丁内斯的《大地狱》是我喜欢的。这本集子里的每一个故事都揭示了一个独特而杰出的讲故事的人,展现了他迷人和令人惊奇的声音。
——胡安·马尔塞(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奖获得者)
目录
001大地狱010与维托尔德干杯
014玛尔科内大酒店的舞厅
026补考
032帽力的快乐与惊吓
045一次极难的考试
057皮普金教授无法战胜的羞怯
064千元纸币
069被害者
077一个养鱼者的肖像
087令人反感的幸福
103《易经》与纸男人
114疲惫的眼
117一只死猫
142上帝的阴沟
144理发师会来的
147秘密
151救命!
158护犊之母
精彩书摘
《易经》与纸男人男人从梦中惊醒。他是睡在椅子上的,整个背都麻了。几秒钟后他才想起自己在哪儿;这已经是第二晚了,安置着一排病床的大厅以及连接着导管的小脑袋们也变得熟悉起来。空气中有浓重的消毒水和古龙水味,从高处传来风扇扇叶转动的嗡嗡声。他一条腿抽筋了;揉眼睛时,手背感觉到了胡子粗糙的摩擦。他试着回忆那场噩梦,但最后的残迹无可追觅,他合计着,也许这样更好。他站起来,于黑暗中俯身查看第一张病床。毫无变化。被单盖到了脖子,包裹着那段瘦小的身躯;一绺金发黏在汗湿的脸上;头纹丝不动,仍僵直在那个角度,就像被那根从鼻孔通出的胶管残忍地扯向了上方。晚上有谁来换过血清了,额头上的湿毛巾也是新的。睡着前,他听着三床的女婴撕裂的哭声,之后于睡梦中,则有戴呼吸机的那小子如即将溺毙的游泳者一般剧烈的哮喘,他慨叹身体应对死亡的战略竟是如此不同,自问他女儿沉沉的昏睡——那固若金汤的静默——是否也算是种自负的顽抗,抑或预示着最终的放弃?
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他看了眼时间:妻子来换他了。开门的一瞬间,光扇照在其他床位上:三床,之前属于那个女孩的,此刻空着。他心想,睡着太危险:夜里有悄无声息的失踪,不可预见的更替。他感觉到肩膀上妻子的手以及她的唇在脸颊上一掠。他们站着,像两个陌生人,一动不动,观看着同样一动不动的、陌生的景象。
“没什么,是吧?”她说,伸手摸了摸额上的湿巾,“又该换了。”
她走出房间;透过走廊,他听见小饭厅里水龙头的声音,护士们都在那儿打盹。当她回来,探着孩子前额的温度时,他在她因恐惧而放大的瞳孔中看见了他们谁都还没敢说出口的东西。
“医生什么时候再来?”
“过两个小时。”
“他还说了什么吗?”
他摇摇头。
“只能等了。”
“有点不对劲,你不觉得?应该半个小时就从手术室里出来的,照他们所说。可能不是阑尾炎。说不定有并发症。”
“我问过他,他说没有。可到了晚上他又跟另外一个医生一起来看了一次。他们说还得等二十四个小时。”
“上课前你不要睡会儿吗?”
“嗯,我会试试睡会儿。”
“你会记得帮我找《易经》的吧?”
话音听着像卑微的乞求,他在她眼里读到了与失去第一个孩子时相同的无助,好像海难者高举着的手臂,周围一切都已沉了下去,她再也不去顾及他的想法。他告诉她,所有箱子都检查过一遍,但他会再好好找找。
“还有硬币,”她说,“别忘了硬币。得有一阴一阳两个头像。我以前用的是英镑,十便士的,一面是狮子,一面是女王①。应该都在她那个红色的储蓄罐里。”
男人点点头,弯腰在她唇上吻了一下。她始料未及地抱住他,大哭起来,痉挛而破碎的抽咽伴着沙哑而绝望的呻吟。他感觉她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脸和脖颈。他们好久没有拥抱了。
她放开手,再次望着他,下意识地帮他把衬衫领子立好。
“你会记得的吧?”
男人旋转钥匙进了门。气味已与之前有些微的不同,是荒弃之家的味道。他听见指甲抓挠院门的声音,从玻璃中看见了他的狗潮湿的口鼻。老婆在厨房里给他留了橙汁和几片吐司。他掰了些吐司给那条狗。天还没亮。他踱过昏暗的过道,摸进女儿的房间,打开灯。他发现他妻子一整天都待在了那里。一切都整理停当了,似乎她每将一个玩具放回柜子前都先拿起来看过摸过;那张床——半夜里,他们就是从这儿把女儿抱走的——也铺好了,维尼熊的床罩过分精细地箍着床垫。他看见床头柜上摆着一张妻子跟他的合照,两人笑着,躺在沙滩上,脸被太阳晒得通红:某年夏天女儿在海边给他们照的,那会儿她还只有四五岁。他在一箱玩具中找到了那个储蓄罐,马口铁制的红色邮筒,一次旅行时买回来的。他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床上,从各国钱币中挑出了他要找的那三枚放进兜里。他关了灯,上楼去了书房。
搬家时海运过来的十几个书箱还在昨晚的老地方,盖子开着,三三两两地摆在地上。这套房子不带书柜;刚搬进来时总有比这更紧急的事需要解决,日子过着过着又忘了这茬,仿佛两人都明白,这已经不再重要,反正他总是要走的。他蹲下去,翻开第一个纸箱,把书一摞摞地搬出来。他在脑中估算着这些书将在屋子里占用多少空间。他决定把所有箱子重新检查一遍。他在找的书是黑色的,很厚,书名是用中文写的,书脊的一头绽了线。他确信自己不会看漏。说不定就在哪个他一直没有翻到的箱子里。那本书让他想到她,想到两人刚结婚的日子,那时她整晚整晚无法入睡。尤其令他记忆深刻的是硬币的敲击声——他在黑暗中醒来,身边是冰冷的床铺,他循着那有节奏的响声寻过去,发现她散着发,身穿睡衣,餐桌上摊着本《易经》,旁边放着张一折为二的纸,纸上无休无止地画着横道,就像用古怪的摩尔斯电码发出的求援信号。还记得他煮着咖啡,而她长久讲述着为于大君之武人、左次之师、贞女、老妇、文王、牧羊、厥宗噬肤、泣血涟如②。他想起自己对她的万般取笑以及她冷静微笑着给出的回应,好比一张常胜的王牌:《易经》预言了他,纸男人,将会进入她的生活。我的纸男人。以前每到意乱情迷时她总会这么叫他。
男人打开第二个箱子,一线日光从窗口洒了进来,如抚上脸颊的一只意外温热的手。一阵剧烈的疼痛从腰间升上背脊。他把身子往后抻了抻,干脆躺倒在镶木地板上,眯着眼睛,看着在光锥中悬浮着的闪亮的流尘。他睡了过去,那么沉,都没有发觉那条狗悄悄爬上楼梯,坏了规矩,在他身边蜷成了一团。
底楼的电话响了。一声,两声。男人醒了,得以在自动答录机启动前赶到了楼梯的底端。
“我想着你可能要睡着。”是妻子打来的,背景音有点嘈杂,像是打的公用电话。“你几点的课?”
男人看了看表。
“还来得及冲个澡。有什么新情况吗?”
“他们刚带她去拍了个片子。医生说还要做别的检查。他说得等到今晚十二点;他也不肯告诉我,万一到时她还是没有反应的话……”她一时哽咽了,而后,就像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似的,她问他是不是上完课就直接去医院。
“对,当然。”
“那你别忘了把《易经》一起带到系里去。”
她一再提醒他该做什么。他不觉得自己的记性有她常说的那么差。一开始两人都把这当作玩笑,后来——在暴风骤雨的日子里——却成了她唯一能跟他搭上话的机会。他的记忆里确实有些游移的因子,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坚固而不可撼动的场景。他每晚都会忆起他儿子的垂死,想起她——那时她还那么年轻——一边掷着硬币,一边喃喃自语,被金属的叮当声催眠着,魔怔般地意图从书里翻出另一个解释。他还记得那一天,葬礼之后,放在饭厅搁板上的那本《易经》不见了,他什么都不敢问;就是那一天,她开始服药——如今她仍靠它们安眠整晚。
男人打开淋浴喷头,快速脱下衣服。他的身体修长健壮,自加入大学游泳队起就一直保持这样。现在他还能游,毫不费力,仰泳一百米是他的日常项目。在与身体签订的秘密协议里,他感觉,“别太关注它”就是他要尽的那部分义务。他走出浴室,套上短袖衬衫,又看了看表,确定没有时间刮胡子了。他再次上到书房,拿起统计书和几页笔记,拖着狗脖子把它拽下楼,重新将它扔回院子里。确认过口袋里的三枚钱币,他在玄关的台面上找到了车钥匙。他朝大学的方向行驶着,却拐上某条大街,在一爿书店前停了下来。店员耐心听他讲完,慢慢摇头。他们只有《易经》的缩略版。他说的那本黑色封皮的特别厚的书,有荣格作序的,很久以前就卖完了,他不觉得在本城的任何一家书店还有可能找到它。男人踱回车中。他低头看表,复又驶上大道,略微超了点速。跑进教室的时候,学生都已在座位上了,他听到一阵交头接耳。他从未迟到过,或许,他想着,所有人都以为他不会来了。男人的长腿迈过教室,登上讲台;他讲起病理学、怪症和畸形。各位有没有发现,他问道,最初的病例总是发生在中国?难道中国人特别容易变异,特别容易生出怪异之物?还是说,只是因为他们人口众多?到底怎样的病才算是罕见病呢?我们说,它的发生率必须小于千万分之一。可中国人口超过了十亿,以至于在任何一个国家都算得上罕见的病症,在中国可能并不稀有。那现在,男人说,让我们想想先兆之梦。我们所有人都梦见过某个近亲的死亡,所以我们不妨假设,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都至少做过一次这样的梦。
他停了下来,好像思路断了:他灾难般地清晰记起了清晨在医院里的那场噩梦。他朝黑板转过身去,假装在寻找粉笔,平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面对课堂。以下这种情况并不常见,他说,第二天,那位亲人真的死了。但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句话,什么叫“并不常见”呢?我们的亲人也和所有人一样,终有一死。
男人在黑板上写了一个五位数。这是一个人寿命的极限,以天表示。我们的亲人可以在其中的任意一天死去,预兆之梦也可以发生在其中的任意一个晚上。那么好,梦境应验的几率也就是以上两个独立事件——做梦的那晚和死亡的那天——同时发生的几率。这个数我们都会算。
男人写了个等式,在画上等号的时候顿了顿,似乎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心算,接着他记下了一个几乎两倍长的数字。这个数很大,但也不是那么大,他说。在东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纽约,按照惯例,每晚都会有人在梦里杀掉一位至亲。这个人自然会无比惊悚,我们没法用这个算式或者其他理性的推断来说服他;他一定不会相信,这里面没有奥秘,没有预兆,只有平庸的统计学,它如此必然,就好比每回彩票总会有人中奖。
他颇为精神地擦了黑板,随后,以同样冷漠而讽刺的语调,将秘术、星象和塔罗奥义在他的统计课上逐一击溃。学生们全未发觉这天的课与其他任何一堂课有什么两样。他只是比平日里多了些恍惚,且尚未拿出他那令人难以觉察的冷笑话。第一次课间休息,他没离开讲台,教室渐空,坐在前排的一个女生带着存疑的微笑走了上来。
“您刚才所说的,包括大数定律③,是不是对《易经》都不适用?因为《易经》预言的是未来的事件……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了,不能简单解释为掷骰子。”
每个学期,但凡他讲到这堂课,讲到偶然性,总会有人抱着这般警觉的姿态来找他,仿佛他挑战了一种信仰,比一切宗教更值得维护的信仰。一般都是星象,他会听到天真而激烈的辩护、关于星座与星盘的长篇大论。也有时是塔罗。大体上他做不了什么能让他们明白,是的,我很遗憾,它们都一样,都是事物盲目的不确定性使然。但直至今日,还没有谁提到《易经》。
“你那书每测必中么?”男人问道,女生似乎未听出话中的讥嘲。
“从不落空,”她很认真地说,“所有对我的预言都应验了。但只有确实重要的事我才用它来占卜。”
“大概你那本特别神奇。”
“你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那女孩有点受伤。
男人打量着她。女孩的目光清澄通透;她脸上有股特殊的神采,极端稚气,似乎未经人事。他发觉,是的,就这一次,他愿意相信。
“神奇的书,”他听见自己讲述着,“就像神奇的硬币一样,是统计学中被仔细研究过的一个案例。我们设想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住户同时开始扔硬币,把一枚硬币连续扔二十次,那么所有人中很可能有这么一个,他的硬币接连二十次都是同一面朝上。接连二十次。这人一定会觉得,他的硬币是有魔力的,可是当然了,这并非硬币的固有属性,只是偶然的一种可能表现形式罢了。同理,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个世界上所有拥有《易经》的人。我们假设在每次占卦后,预测落空的人都不再相信这本书了,只留下灵验的继续占卜;我们说,只剩下一半人。而在第二次占卜过后,留下的是一半的一半,依此类推。即便《易经》是像硬币那样没主见的东西,只要放到一个大城市里,也很有可能存在这么一本——它永远正确:说不定就是你那本。它是哪版的?”男人忽然问起来。
“你说版本?应该跟这没关系吧?就是最普通的,黑色封面。”
“上面有烫金的汉字?”
“对,就是这个。”
“能不能借我用一下?就今天。”
“今天?可那本书在家呢。”
“对,一定要今天。上完课我可以送你过去。”
女孩脸上掠过一丝狐疑,她在戒备,像在适应一段新的对话,或在揣度他的话语背后是否另有深意。但她仍在摇摆,因为从他的表情里看不出其他的征兆——没有半个笑容,语调没有丝毫变化,没有心怀鬼胎的目光——好让她确定他的真实目的。她紧张地摸着头发,弱弱地笑了笑。
“但您不是不相信《易经》的么?”她的笑容中闪出一抹轻浮,或许是在怂恿他越过那条无形的界线,好让她明白,她要接受或拒绝的究竟是什么。男人做了个疲累的表情。
“对,总体来说是不信的。也不是我自己用。主要是……”
他停了下来,仿佛选错了路。“说来话长了,”他换了种说法,“但确实是件重要的事,就像你说的。所以最好能用你那本来占卜。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小忙?我明天就还你。”
“当然,当然可以。”女孩困惑地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谢谢,”男人说道,“那我们下课见。”
女生的家在新建的学生社区里,公园的后边。几分钟的路程中,两人没讲几句话。他知道了她的名字,而她根据车后座的玩具判断他有个女儿。他在一栋独户公寓前停下,女孩不好意思地请他下车;当她为屋中的凌乱说着抱歉,在架子上翻找那本书时,站在门口的他顿时觉得回到了学生时代,回到了自己凌乱的寝室——只需注意每个细节,她的一切尽皆了然。回来时,女孩把书递给了他。他的食指拂过金色的文字;把书转过来看着书脊的时候,他感觉到了它的分量。男人想起来,这还是他第一次捧起这本书。
“就是最普通的版本。”她说道,就好像一件早已提醒过对方的事,她仍怕男人会失望。
“太棒了,”男人回应道,“神奇的书是一本最普通的版本的最普通的书。”
男人踏上医院的石阶,兜里的硬币逢单便响。他穿过内院,在诊室的迷宫中寻找女儿的病房。开门前,一个认得他的护士在走廊里把他拦下;她伸手扶住他的胳膊,告诉他,他女儿被送去手术室了:她得再次接受手术,他妻子正在那儿等他。男人迈向回廊尽头,登上另一段阶梯,大理石的,磨损已经很严重,边缘带着锯齿,终点即是等候室。妻子站起来拥抱了他,他在她脸上看到了泪痕。
“刚进去,”她说,“就在那扇门后面。不知她怎么了。他们只说要再给她动手术,可都没法告诉我她到底怎么了。”她迷离的目光定在了男人手中的书上;他把《易经》递给她,她将它抱在胸口:“所以你还是找到了。”
“不是你那本。”男人说,“我又找了一遍,到处都没有。这本是借的。”
“那硬币呢?你没忘吧。”
等候室里没有别人。男人从兜里掏出那三枚硬币交给她。女人拿着书坐到第一级台阶上。他转头望向一排排座椅:他不愿见她这样,埋头书本,像阴暗的邪神,仿佛过去又原封不动地转回来了。但他的儿子和女儿,他心想,是完全独立的事件。他听见硬币撞在大理石上的声音。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决定六爻的六次投掷。他不可避免地抬起头,恐惧地看见那只手将那本永无失误的书翻到了其中一页。
……
用户评价
这本精装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那种略带复古的墨绿色封皮,配上烫金的字体,散发着一种低调而深沉的质感。初拿到手时,厚度适中,重量也刚刚好,握在手里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我尤其喜欢扉页上那几行小小的引文,虽然内容本身我没有去深究,但那种排版上的匠心,足以看出出版方在细节上的用心。它放在书架上,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那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知识的重量感扑面而来,让人忍不住想去翻阅它,感受纸张的纹理和油墨的芬芳。每次翻开它,都能感受到一股莫名的仪式感,仿佛自己正在开启一段不寻常的阅读旅程。这种对实体书的尊重,在这个充斥着电子屏幕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评分对于喜欢深度思考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我个人体验是,它像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心理导师,通过讲述旁人的故事,巧妙地折射出我们自身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和未被正视的挣扎。很多情节的转折点,都蕴含着极高的人生智慧,并非那种空洞的说教,而是植根于真实人性挣扎中的提炼。每次合上书,我总会发现自己对某些日常现象的看法有微妙的改变,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比任何直接的指导都来得深刻和持久。它不是一本读完就束之高阁的书,更像是一个值得反复咀嚼、时常拿出来重温的智者之言。
评分从文学技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语言运用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些长句的铺陈,节奏感把握得极好,时而如涓涓细流,温和地渗透进读者的内心;时而又如惊涛骇浪,在关键时刻爆发,直击人心最脆弱的地方。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对环境和场景的描写,那些画面感极强的文字,让人仿佛身临其境,空气中的气味、光线的变化,甚至微风拂面的触感,都能清晰地感知到。这种“可见的文字”和“可感的氛围”,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即便是描述一些抽象的情感和概念时,作者也总能找到一个具象化的载体来承载,使得复杂的内心情感变得触手可及。
评分这次阅读体验,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探险,它挑战了我对既有世界观的一些固有认知。作者的叙述方式非常独特,常常采用一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暗藏玄机的叙事手法,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入他构建的逻辑迷宫。我得承认,有好几次我不得不停下来,合上书本,花上几分钟时间去梳理刚才读到的那些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哲学思辨。它不是那种可以让你轻松消遣的作品,更像是一块需要耐心打磨的璞玉,需要读者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挖掘其深层的内涵。这种需要“用力”去读的书,反而更能带来一种成就感,读完后,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仿佛自己的认知边界又被拓宽了一寸。
评分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急于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或道德评判。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开放的讨论空间,让读者自己去填充那些留白之处。我发现,在阅读不同章节的时候,我对自己先前形成的一些观点又产生了动摇,这种持续的自我审视和怀疑,正是优秀作品的魅力所在。它不试图取悦任何人,也不迎合任何主流思潮,它只是冷静、甚至略带嘲讽地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处境的荒谬性。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感,虽然有时令人感到不安,却也是它最真实的力量源泉。它迫使我直面那些我通常倾向于回避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清醒的视角。
评分不错,慢慢看,书买多了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评分以奇特的视角,展现日常。
评分一如既往的快,回头细读再评价。。
评分帮同事买的。现在能踏实读书的人不少了……
评分拉美作家,领军人物之一
评分继续收短经典,真是凑单神器……
评分tststshjtstshfshjfdgdj
评分hao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