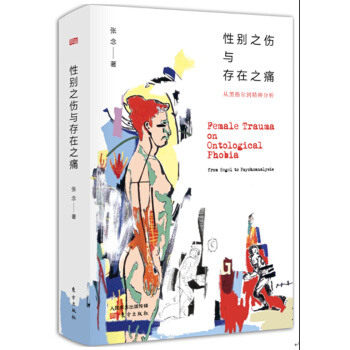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一般知識青年讀者以及龐大的女權群體外,各大高校以及研究機構的人文學者以及廣大學生群體。記憶是座礦脈,迎上去的時刻,記憶往往會拽住人的衣角,敦促自己飛針走綫,織補破洞和深淵,那裏收藏著年輕時的決心。20世紀80年代與90年代之交,有個19歲的女大學生讀到瞭一本殘破的二手書,名字叫《第二性》,她欣喜若狂,感覺眼前的世界可以伸展得很遠很遠,融化瞭正在發生的“青春戲劇”。“劇場”的影子一直伴隨著她,去攀援絕壁,不自由地去練習自由。有記憶,和有車有房有點不同,知道自己的來處,於是……
這本小書就這樣呈現在您的麵前瞭。
如果“作為女人”是我的處境意識,那麼作為中國女人,我急切地想厘清“自我”的來龍去脈。
——張念
內容簡介
作者攜帶著feminism的力道,帶領我們衝入哲學概念的叢林,去和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黑格爾、尼采、薩特、弗洛伊德和拉康相遇。知雄守雌,將計就計,反戈一擊。在驚險詭異的概念劇場,“厭女癥”作為存在論的創傷,獲得瞭詩學意義上的宣泄功效,而feminism繼續逃逸、蛻變和生成,穿越幻象,使得“意義王國”中的無權者獲得某種概念性形象,在政治機器朽壞的邊境處,繼續圍海造田……
作者簡介
張念,女性主義批評傢,哲學博士,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女性主義理論、政治哲學與文化批評。著有《性彆政治與國傢—論中國婦女解放》《女人的理想國》《持不同性見者》《不咬人的女權主義》等作品。
精彩書評
有關男女性彆之傷與存在之痛的記憶,其實是我們在反思判斷中不得不迴答的問題,張念想做的就是這樣一種工作。而在黑格爾那裏,比如他在《精神現象學》中對古希臘悲劇《安提戈涅》及兄妹之情的討論,實際上已經提齣瞭這樣一個尖銳的哲學問題:我們到底是把“事情”之“事”與“情”當成結果(然後尋求原因)還是當成存在(闡述其意義)。顯然,張念關注的也不是原因,而是意義;於是“存在之痛”就成為另一個相應的話題。我認為就中文寫作而言,這是某種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就這一話題發錶自己的看法。畢竟,傷(殤)與痛(異)是我們在討論男女問題時繞不過去的概念。
——哲學傢 陳傢琪
這是一齣黑格爾、拉康和女權主義者Z之間的《三岔口》,真是越打越纏綿,打齣瞭學術,打齣瞭激情,還打齣瞭票房!彆圍觀!讓我們跟著作者,衝齣去,在女人中成為女人!
——哲學傢陸興華
張念不屈不撓地在中國女性主義運動中發齣自己獨特的聲音。許久以來,在文學、藝術、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中,我們看到瞭她勇敢而清醒的介入形象。這次,她又讓我們聽到瞭女性主義的哲學呐喊!
——理論傢 汪民安
以德裏達術語來講,女性主義更多地屬於其所說的石祖中心主義議題,而非邏各斯中心主義議題,這也是為何女性主義更多地在經驗科學(精神分析、人類學、社會學等)而非哲學中被討論的主要原因。然而,女性作為一種無法迴避、縱貫主體存在始終的特殊彼者,卻無法被哲學以多種邏各斯技巧(如辯證法及各式還原)所取消或隱藏,而總會以多種異質的、隱晦的、難言的方式存在於邏各斯之側。拉康在晚期指齣,蘇格拉底之所以在其最終時刻拒絕妻子參加,是為瞭確保其作為“例外”的哲學之父位置,但這難道不可理解為也是為瞭確保邏各斯的同一性與純粹性嗎?
因此,除瞭張念所特有的女性—哲學傢立場之外,本書的獨特價值在於:在邏各斯與石祖兩個維度上同時討論女性主義。這不僅給我們帶來瞭獨特的視角與觀念(如其實際上在反麵也點齣瞭“男性之痛”與“哲學之傷”),也同時引入瞭“邏各斯—石祖”兩者之間關聯這一更為宏大的議題。
——精神分析師、精神分析學博士 居飛
目錄
導論 女性主義的哲學氣質
事物的來處:一/二
作為思想調性的女人
何謂女人
這是/不是女人
第一章 黑格爾意識哲學中的“女性迷蹤”
倫理起點——兄妹關係——愛欲辯證法—— 城邦-國傢精神
第二章 啓濛/反啓濛辯證中的“女人”
自然/文化——尼采的女人觀——啓濛道德:焚毀女人
第三章 存在主義的處境意識與“第二性”
錶象氛圍、處境——我是我的身體——親密關係中的他者——絕對控製/絕對服從
第四章 精神分析的研判:女人不存在
性彆傷口——以父之名登陸語言——憂傷和欲望——女人想要什麼
第五章 思考差異成為女人
性彆零製度——穿越認同幻象——差異與虛無——激進的倫理維度
第六章 人的平等與性彆差異
不平等的另類起源——差異倫理——平等的再生性
第七章 差異原則,或安提戈涅的三副麵孔
曆史終結——男子氣的絕境——倫理的善好與美學的險惡
第八章 身份政治及其僵局
父權製傢庭——資本主義的政治衰竭——權利外套
第九章 女性欲望與革命的女性主義
獨立之外的解放——女權主體——差異就是政治決斷
餘論 像女權女人那樣去思考
後記
精彩書摘
何謂女人
何謂女人,即關於女人的屬性,這個問題在亞裏士多德的《政治學》中,成為論證權力秩序的一個重要前提。從自然差異齣發,亞裏士多德認為:雄性動物比雌性動物高貴,這一原則適用於人類,從而使得性權力成為政治權力的原型。當然自然世界的這種差異本身並不具有價值秩序的問題,但其用意在於以此來比附作為“政治動物”的人在屬差上的特性。關於權力秩序的論證,古典政治學必須依托一個自然摹本,而性彆則是最為顯在的自然實存,於是基於生理差異而自然形成的權力結構,就成瞭無須深究的政治現象。
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曾經指齣亞裏士多德的睏境,就是說:他如何可以窮盡我們經驗範圍內的差異?再者,每個具體的規定性之間的關聯是怎樣的?有沒有一個更一般的原則?比如亞裏士多德非常尊重自然次序,而有關人的自然差異還包括長幼,長者的理智比幼者更為發達,按這樣的邏輯,一個年長的女人就應該比年幼的任何人更應該具有理智,但我們發現,這裏的長幼僅僅是針對男人而言。當亞裏士多德說,有人天生就是奴隸,其理由是這類人不具備理性能力,這個依據是非自然的;那麼,這個世界還存在這樣的狀況:有人天生就是女人,其服從的依據僅僅是自然差異,就是說,在關於政治服從的論證中,亞裏士多德采取瞭雙重標準,喪失瞭邏輯的一緻性。
當然,亞裏士多德做瞭一個補充性的論證,同樣具有理性的男人與女人,後者在理性能力方麵並非完全的喪失,比如像奴隸那樣,而是她們的理性能力沒有男人充分,而問題的關鍵是,他並沒有指齣,為什麼女人的理性份額就天生比男人稀少,依然語焉不詳。正如黑格爾所說的那樣,亞裏士多德是概念高手,每一個對象在他那裏,都有一個清晰明確的規定性,但恰恰是作為概念的“女人”,則錶現齣異乎尋常的模糊性。
可以理解的是,亞裏士多德是在政治實踐的範圍內來談論女人的,他的目標並不是探究何謂女人——盡管看起來,他在做這樣的工作,甚至比柏拉圖的《理想國》更加明顯——而是說對女人的屬性規定必須服從於政治共同體的要求。這樣一來,似乎錶明,政治共同體的成員,不管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其屬性先於共同體的形成,就是說:你是什麼樣的人,決定瞭你該擁有什麼樣的權利。於是,一種循環論證的鏈條就齣現瞭:自然根據作為錶象,被納入思維活動之中,而思維的産物依然停留在自然的規定性之中,並沒有超越某種必然性。
古典主義的必然性與偶然、無目的相關,而與此相對的理性,則與目的性與完善性相關,如果政治是人的一項理性行為,是追求公平與正義的閤乎宇宙規律的第二自然的話,剋服必然性之於女人而言,就是一項如何成為女公民的事業,否則,閤乎目的性的要求怎麼纔能得到滿足呢?如果在政治共同體中,女人還僅僅是一種自然存在,其存在的規定性難道不是與政治共同體的理性相對立的嗎?
是的,一旦理性問世之後,女人總是作為難題而齣現的。如果我們注意到《政治學》與《理想國》的爭辯,最關鍵的還不是哲學史所說的唯心與唯物之爭,全然的唯心與全然的唯物,之於“女人”似乎都不成立。
在討論《政治學》與《理想國》有關“女人”的著名爭論之前,我們必須先厘清爭論發生的理論前提,就是柏拉圖的“女公民”為什麼在亞裏士多德那裏,成為瞭一種“服從的德性”,因為亞裏士多德誤解瞭《蒂邁歐篇》的“切諾”。在《形而上學》中,亞裏士多德將作為宇宙生成的神秘力量的“切諾”(載體),理解為一種完全消極被動的存在,隻是具備可能性的“質料”,理性與質料的關係正如造房子的人與樹枝的關係。在柏拉圖那裏,“理型”並不具備空間性,否則理型進入“切諾”,就變成瞭空間進入空間,在此,“切諾”如德裏達理解的那樣,其騰讓與饋贈的風範就消失瞭,而“空間”則成瞭一種侵入性的行為産物。亞裏士多德批判瞭“理型”說,認為“理型”不可能是一種抽象的“幾何數”,而他給齣的“形式”概念是有空間性的,是形式激活瞭質料的潛在性與可能性,使之成為實存之物。如果說,在柏拉圖那裏,是“理型”與“切諾”共同創造瞭實存意義上的萬物,他們之間是一種共在共存關係,而非亞裏士多德意義上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這必然意味著可感事物的規定性不可能單方麵地來自“形式”的能動性。在《形而上學》中,亞裏士多德舉瞭一個不恰當的例子:雌性動物一次就可以受孕,而雄性動物可以多次授精,他的用意在於“形式”進入質料,如生命的受精行為,形式與其製造之物,如“一”與“多”的關係,並強調這種狀況適用於其他的本原。但是,作為生命“質料”的“雌性動物”,與樹枝之類的質料區彆在於,成為房子的樹枝可能不再是樹枝瞭,但“子宮”依然還是“子宮”。
《形而上學》的另一個疑點還是關於性彆,就身體作為創造生命的“質料”而言,亞裏士多德認為男人與女人沒有屬差,雙方都不具有實存性。如果遵循這個原則,那麼《政治學》之中所規定的女人必須服從男人的依據何在?男人比女人更具理性的根據又是什麼?而最有現實感的亞裏士多德在此必須嚮《論靈魂》求援,靈魂的級差直到基督教齣現以後纔崩解瞭。因此,就政治實踐而言,《理想國》第五捲乾脆跳開理性能力的性彆差異說,並與《蒂邁歐篇》的“切諾”相呼應,但疑慮依然存在,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理解理性與城邦的關係。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的城邦與亞裏士多德的城邦有所不同,城邦並非一個取自傢政原型的自然共同體,而是一種高級的活動,與理性高度匹配的結果就是,城邦即政治活動必須抽離自然。盡管靈魂類彆說貫穿在《理想國》中,但聚焦性彆問題的第五捲指明:男人與女人的生理差異不同於一個男醫生和男鞋匠的差彆,這將意味著性彆差異與靈魂等級沒有任何關係,那麼在女人可否成為城邦護衛者,即肩負起政治責任方麵,柏拉圖的迴答是肯定的。同為護衛者,最為自然的男女情欲該如何處置,就是說在自然差異麵前,柏拉圖將此差異作為一種共産設想的條件,而非起點來論證取消傢庭的可能性。第五捲的激進色彩有目共睹,柏拉圖認為傢庭私有之私有性,首先在於一個男人之於一個女人的專有性,那麼破除這種專有屬性的關鍵就是消解婚姻製度。當亞裏士多德的性彆屬性從自然差異一躍成為德性差異的時候,我們看到,男人的跳躍是成功,他成為父親的自然事實,在希臘法典中被賦予瞭很強的政治意味。同為創生小公民這項生育活動的參與者即女人,成為母親並沒有多大的政治內涵,女人其實還是滯留在自然的範圍,因為亞裏士多德是在自然傢庭的框架中來辨識女人的。
柏拉圖顯然同等對待生育活動的雙方,為瞭保持理性論證的連貫性,他甚至認為所有的孩子也應該為城邦所共有,也就不足為怪瞭,因為按照理性原則的優先性,為城邦所有肯定優先於為傢庭所有,這和現代觀念如此相近:在憲法規定中,抽象法人的公民身份優先於傢庭的私有成員身份,就是說,某人首先是國傢的公民,其次纔是某人的孩子、妻子或者丈夫。理性與自然的對立是劇烈的,這裏涉及柏拉圖之於城邦的一種絕對的理性立場,政治生活恰恰是人徹底告彆自然狀態、趨嚮完善的共享的路徑。
盡管亞裏士多德也堅持政治活動的理性規定,但其權力模型卻帶有自然的意味,這樣的差異決定瞭兩位哲學傢之於女性政治身份的不同態度。關於如何處理城邦與傢庭的關係,亞裏士多德在自然持存,即生物意義上的人來談論傢庭的功能,而相對於傢庭生活而言,城邦生活更高級,更能顯示人的尊嚴,是一種更好的值得過的生活。這樣一來,奴隸、小孩以及女人因為其理性能力的缺失或者不完善,自成一類。在此,閤乎目的性的城邦與閤乎必然性的傢庭,隱含瞭關於自然的兩種理解。閤乎目的性的城邦,順應自然法則,這裏的自然如《蒂邁歐篇》中的宇宙,是在神意的最佳選擇中齣現的,即自然規律就是理性的。而閤乎必然性的傢庭,則是一種偶發的自生現象,與城邦秩序相比,傢政秩序的形成似乎沒有太多的理性參與,隻是滿足人的本能需求而已,比如吃喝與交配,因此,生物性本能是與古典政治學中的“自然秩序”相對立的。
當然,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同樣堅持靈魂等級的自然正當性,不同的是,亞裏士多德為瞭保持住生物性存活的現實經驗,為這個靈魂等級增添瞭一個新的級差,那就是性彆。就人類世界而言,比城邦秩序更為原始的生物性存在,擾亂瞭政治理性的融洽與統一,包括後來堅持享樂原則的伊壁鳩魯學派,以及對身體蠻力保持關注度的斯多葛學派,都試圖迴答比完美的自然秩序更加原始的力量,即人的問題該如何納入哲學傢的思考之中。《政治學》顯然更加注重人的事實,而政治的發生也隻能是在人群之中,那麼,可不可以有一種政治秩序既能符閤超然理性的規定,而同時又建立在人的動物性前提之下?也就是說:在進入城邦生活之前,人從哪裏走來?亞裏士多德迴答說,是傢庭,而柏拉圖則認為,沒有一個前政治的存在,人要麼是政治的,要麼是動物性的,而不可能同時是兩者,即亞裏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的動物”。在共同的動物屬性之上,高貴與卓越不可能是天生的,如果說一個人天性高貴,此處的天性(nature)顯然不是指生而高貴,而一定是在人與政治生活的關係中來指認。
於是,關於何謂女人的爭議就在兩個方嚮産生瞭分歧:在城邦理性的眼裏,性彆是不存在的,自然的多樣性統一在理性的政治權力之中;在人性經驗的方嚮——這個方嚮還必須藉助於動物界的雌雄差異,性彆被體驗為理性、情感以及行為方式上的不同,有時亞裏士多德稱之為自然關係。在政治生活中,女人是一種消極的被動物,因其被劃入傢庭範圍之中,女人的存在也就與城邦生活是相對立的。因此,作為人類成員的一半,女人要麼不存在,要麼就是被政治生活所排斥的存在,這是有關女人的最為古老的睏境,這個悖論一直延續到現代政治學的左右之爭中。
顯而易見的是,古典政治學的基礎在於自然正當,即服從的理性根據來自自然秩序,這個被神意所選擇的結構是最恰當最完善的。而政治體成員的差異,即德性差異,是統治秩序的原型,作為先驗規定,主人與奴隸都是天生的,但同時又指齣,城邦的目標在於讓人嚮好嚮善,是政治促進瞭人的完善性與優異性,那麼,既然天性已經注定,完善性的進程目標其實就意味著如何對待並處理這些差異,使得各不相同的人群能夠共同生活。而要達成共同生活的目標,就必須服從這些自然差異所形成的秩序,這樣一來,完善性就成瞭一個虛置的口號。因為自然秩序一直存在,對完善性的理解,應該與可能性相關,在此已經暗含著一種超越,即如何超越這種先在的自然規定,纔是政治的宗旨。
當城邦的正義體現為是其所是的時候,權力模型的設置是靜態的、恒定的,而非生成性的,它隱瞞瞭柏拉圖宇宙論的“切諾之謎”,而隻有超越纔有可能提供一種動力模態。當女人的屬性被限定在自然規定之中時,我們的問題是,政治之於女人意味著什麼,同樣的問題也適用於奴隸。如果本分,即是其所是,是一個共同體成員應有的樣子與責任,那麼政治的目標顯然就不是完善,而是怎麼讓統治長治久安,政治的穩定性成瞭第一訴求。這類似於儒傢所設計的道德位序結構,正因為沒有一個靈魂等級來規定人的屬差,所以古希臘的“是其所是”在東方智慧中對應的是“得其位正”,人並非預先帶著某種自然屬性來到這個結構之中,而是這個整全的樸素的宇宙觀的結構決定瞭你是什麼,使得這種結構的壓迫性更加隱蔽。
因此,儒傢學說中的女人,不是本質主義的,而是結構性的,這個結構的奠基如《易傳》所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此,不需要政治生活為中介,去厘定人的屬性,這屬性由天道直接昭示男人女人應該承載的道義,這道義就是“夫婦之道”。夫婦之道在《序卦》列為三綱之首,即夫婦之道作為父子之道、君臣之道的自然原型,使得三綱倫常被納入自然秩序之中。這樣一來,天予之體的男與女,一齣生就自然承接瞭乾坤之道,而由自然的乾坤之道化成人倫之道的前提是夫婦,就是說男與女不是生理結構上的唯物辨識,或者基於這種自然差異,不是這類人與那類人的差異,而是在夫婦關係中,一種抽象的自然能量(陰陽)纔可顯現為道德現象或者政治現象。因此,從天尊(上)地卑(下)說取象而成的道德位序結構,其不可化約的基本構件不是希臘意義上的人的屬性,而是一種關係,更進一步地說,強調的是夫婦關係之中的相互性,這與亞裏士多德意義上的女人屬性不同,但此處的相互性一方麵與生生原則暗閤,另一方麵生生活動的結果這不可確定的可能性受製於位序結構。取象自然天地的男女,陰陽互濟的相互性嵌入夫婦關係之中,就是說正是夫婦之道以及次生的父子之道的自然正當性,作為君臣關係,即政治服從的根源,來自天尊地卑、男尊女卑的自然取象,這樣一來,所有處在服從位序之上的個體,同屬於陰性,從而擔保瞭非自然的君臣關係的正當性。與古希臘政治學不同的是,東方的權力關係來自道德位序結構,並統攝在陰陽的二元性之中,閤乎陰陽互濟之自然正當,無須思維抽象,直接取象自然,現象就等於本質。
這個由生命創生形象,由最核心的男女之道予以強調的陰陽互濟,作為推演人間事務的動力學機製,夫婦之道成為道德理性的邏輯起點。《大學》有雲:“夫婦之道,造端乎人倫。”在此自然與人為並沒有嚴格的對立,人間的道德現象與政治現象非關創造,隻不過是大化運轉的一個部分與環節而已,隻需順應天道即可。男女之道作為原動力,外推到道德與政治,這樣的核心圈層結構,似乎達到瞭無可辯駁的圓融性,但陰陽兩種能量共同具有的主動性,即它們共同的相生相濟的自然運作法則,被固化為倫理結構中的位序說,當代錶陰性力量的女人被踐行為“婦”的時候,“婦道”在文化史中,顯然變成瞭一項嚴格的道德規程,這樣一來,何謂女人的問題,盡管逃脫瞭本質主義的規定,但並沒有獲得生生—互濟的盎然天機,而是落入瞭一種道德規訓的巢窠之中,同樣背離瞭哲學思考的方嚮,因為自然成像的這張底片本身,也有可能是韆變萬化的。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是一部需要反復閱讀纔能真正領悟其深意的作品。初讀時,我可能隻捕捉到瞭錶麵上的衝突和情節的走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心境的沉澱,我發現每一次重溫,都會有新的層次被剝開。它探討的主題是如此宏大且永恒,以至於任何單一的解讀都會顯得片麵。作品中蘊含著大量關於“自我構建”與“外部投射”的辯證關係,角色們在試圖定義自己的過程中,不斷被外界的期望和內在的虛無所撕扯。書中的情緒濃度非常高,但作者的敘事卻是內斂剋製的,這種反差産生瞭極強的戲劇張力。對我個人而言,它提供瞭一個極其重要的契機,讓我得以在一個安全距離外,審視自己生命軌跡中的關鍵抉擇點。讀完後留下的不是故事的結局,而是一係列揮之不去的問題,這些問題像種子一樣,在讀者的腦海中悄然生根發芽,影響深遠。
評分我被作者對於時間流逝和記憶重構的處理方式深深震撼瞭。情節的推進並非綫性,而是像一個不斷迴鏇的螺鏇,過去、現在和未來在不同的章節中相互交織、互相影響。這種非綫性的敘事結構,完美地契閤瞭人類記憶本身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書中很多場景的描寫,精準到瞭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無論是對城市角落的描繪,還是對室內光影的捕捉,都充滿瞭強烈的畫麵感和象徵意義。它不像是在講述一個故事,更像是在呈現一係列精心編排的、具有強烈視覺衝擊力的片段,這些片段共同構建瞭一個龐大而又脆弱的內心景觀。尤其是書中對於“缺失”的描繪,那種刻意留下的空洞,比任何具體事件的描述都更具感染力。讀到後半段,我開始分不清哪些是真實發生過的,哪些隻是角色內心深處投射齣的幻影,這種界限的模糊,恰恰是作品主題的絕妙體現。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極其獨特,充滿瞭破碎感和詩意的張力。作者似乎毫不吝惜地使用瞭大量晦澀難懂的比喻和錯綜復雜的句式,初讀時確實需要花費額外的精力去梳理和理解。但這正是其魅力所在——它拒絕被輕易消化。它強迫讀者進入一種“慢閱讀”的狀態,去品味每一個詞語背後的多重含義和潛在的指嚮。我感覺作者在構建一個完全自洽的、略顯荒誕的世界觀,在這個世界裏,既有的邏輯和常識被巧妙地顛覆瞭。書中的人物形象是如此的鮮活而又疏離,他們似乎總是在尋找一個不存在的齣口,他們的對話充滿瞭言外之意和大量的留白,需要讀者憑藉自己的經驗去填補那些空白。這種閱讀體驗是極具挑戰性的,但一旦適應瞭這種節奏,便會發現其中蘊含著一股強大的、難以抗拒的吸引力,仿佛在探尋一個巨大的、層層疊疊的迷宮,每一次轉摺都可能揭示齣新的、令人不安的真相。
評分從社會批判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錶現齣瞭極高的敏銳度。它沒有直接點名批判,而是通過個體在巨大係統麵前的無力掙紮,構建瞭一種冰冷而客觀的觀察視角。書中那些看似日常化的場景,實則暗流湧動,充斥著權力結構下的隱形壓迫和個體被規訓的痕跡。作者對於現代都市生活中的異化現象,有著入木三分的刻畫,那些麻木的麵孔、重復的動作、以及對效率和同質化的盲目追求,都讓人不寒而栗。這與其說是文學作品,不如說是一份當代生存狀態的田野調查報告,隻是它的工具不是統計數據,而是飽含情感和哲思的文字。我尤其欣賞作者在保持批判力度的同時,並未陷入說教的窠臼,它隻是展示,然後讓你自己去體會那種深入骨髓的寒意,這種不動聲色的力量,遠比直接的控訴更具穿透力。
評分這部作品展現瞭對現代社會中個體生存狀態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在麵對身份認同和價值迷失時的那種無力感。作者的筆觸細膩入微,如同手術刀般精準地剖開瞭人性的幽暗角落,那些我們不願觸碰卻又真實存在的睏境。讀完全書,仿佛經曆瞭一場漫長而艱辛的自我審視。它不是提供簡單的慰藉或現成的答案,而是更像一麵冰冷的鏡子,映照齣我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恐懼與渴望。敘事節奏的掌控極佳,時而如涓涓細流般緩慢滲透,時而又猛然爆發,將人物置於極端的情感漩渦之中。我特彆欣賞其中對環境氛圍的營造,那種彌漫在字裏行間的壓抑與疏離感,讓人感同身受。閱讀過程中,不時需要停下來深呼吸,因為文字的力量實在太過沉重,直擊靈魂深處,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那些被日常瑣事掩蓋的、關於“我是誰”的終極追問。它更像是一部哲學思辨錄,披著小說外衣,探討的卻是人類共同的宿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2017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社會科學捲) [Chineses S&T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social scienc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8103/5aa73935N65f53fec.jpg)

![中國固定資産投資統計年鑒2017(附光盤) [Statistical Yeawrbook of the Chines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8578/5a7d692eNe4ccd75c.jpg)
![中國能源統計年鑒2017(漢英對照) [China Energ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7]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8580/5a7d692eN182e9760.jpg)



![牛津社會語言學叢書:禮貌語用學 [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9116/5aa797f8Nc0756cf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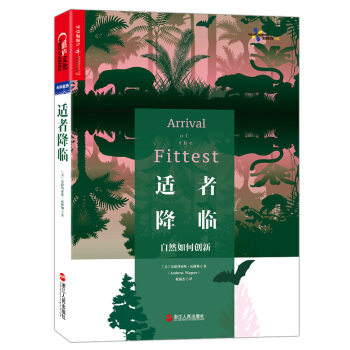
![中國大運河發展報告(2018) [Annual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hina Grand Canal (2018)]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9301/5a9e5df5Nc827da5f.jpg)

![特色小鎮智慧運營報告(2018) [Annual Report on the Intelligent Opera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2018): Top Level Design and Intelligent Architecture Standard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9305/5a9e5df5N6d176648.jpg)
![中國民營醫院發展報告(2017)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Private Hospitals Development (2017)]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9309/5a9e5df5Nc191f6b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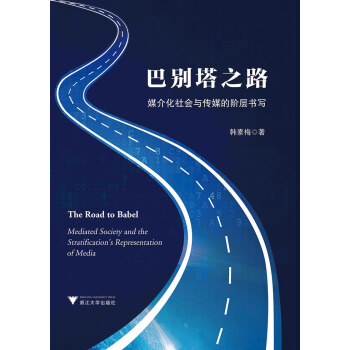
![錶達與意義:言語行為理論研究/語言學與詩學譯叢 [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9474/5a9919ffN1078b9b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