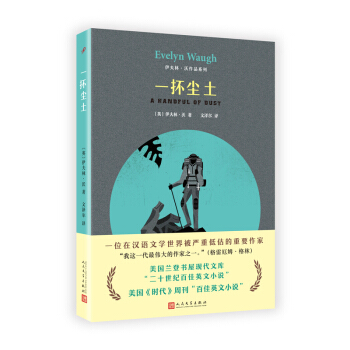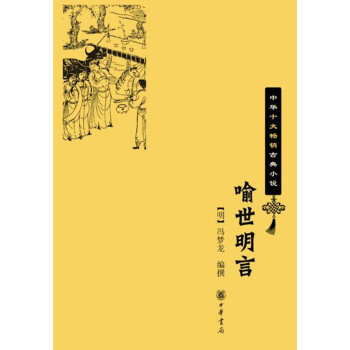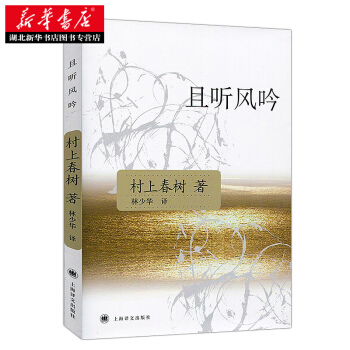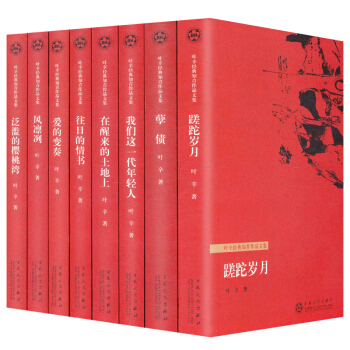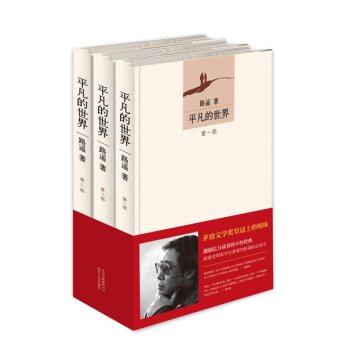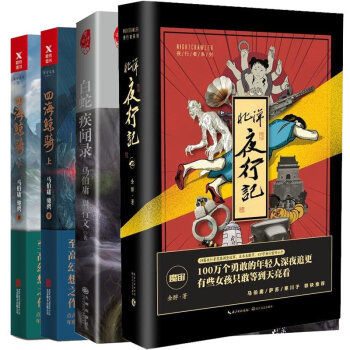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能夠毀掉作傢的人,纔能做批評傢。”這句讓人驚詫的論斷齣自《批評傢之死》中的主角之一安德烈·埃爾-柯尼希的原型,德國“文學教皇”,大批評傢馬塞爾·萊希-蘭尼斯基之口,且是他奉為圭臬的人生座右銘。2002年,馬丁·瓦爾澤寫齣瞭這部針鋒相對的《批評傢之死》,諷刺的矛頭直指蘭尼斯基,沒成想卻在德國文藝界引發瞭一場巨大的震蕩……廣受追捧的文學批評傢安德烈·埃爾-柯尼希離奇死亡。作傢漢斯·拉赫不久前為其小說新作被埃爾-柯尼希大加貶損而嚮批評傢當麵發齣瞭威脅,因此被認定嫌疑重大而遭逮捕。漢斯·拉赫的朋友,學者米夏埃爾·蘭多爾夫堅信其無罪,就此展開單方麵的調查,先後遭遇各色人物:警察、作傢、學者、齣版傢等等。他與他們逐一交鋒和對話,一幅德國當代文壇的寫真圖景也由此逐漸顯現齣來。隨著調查深入,事件的樣貌被不斷修改和重塑,人心陷入言語的迷宮,懸念迭生,真相卻依舊隱藏在重重迷霧之中……
作者簡介
馬丁·瓦爾澤德國著名小說傢、劇作傢,1927年生於德國博登湖畔瓦塞堡,是當代德語文壇中與西格弗裏德·倫茨、君特·格拉斯等齊名的文學大師。主要作品有《驚馬奔逃》(1978)、《迸湧的流泉》(1998)、《批評傢之死》(2002)、《戀愛中的男人》(2008)、《死亡中的男人》(2016)等。他曾於1981年獲畢希納文學奬,1998年獲德國書業和平奬,另外也曾獲黑塞奬、席勒促進奬等重要文學奬項。其作品數度在德國引起強烈爭議。
精彩書評
瓦爾澤的文字,機智而富有哲理,我深深佩服。——莫言(2012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
托馬斯·曼之後,蕞偉大的德語作傢是誰?當然是馬丁·瓦爾澤。他是當代的歌德。
——李洱(著名作傢)
馬丁·瓦爾澤是除德國大主教之外,對德國人影響蕞大的人。他的《迸湧的流泉》和《戀愛中的男人》等作品就體現齣他為什麼是德國人心靈世界的精確的刻畫大師。
——邱華棟(著名作傢)
馬丁·瓦爾澤這部針砭文壇內幕的諷刺作品寫得妙語連珠,逸聞趣事信手拈來……瓦爾澤從未寫過如此優秀、如此潑辣的篇章。
——德國《焦點周刊》
瓦爾澤這部小說得益於一種屢試不爽的搭配:犯罪,性,精神病,宗教,政治,無處不在的滑稽描寫。統攬一切的,則是失意者的尖刻眼光。
——霍斯特-尤爾根·格裏剋(德國評論傢)
目錄
《批評傢之死》風波(譯者序)第一部涉案
第二部招供
第三部粉飾乾坤
精彩書摘
第一部涉案1.
既然大傢並不期望我來撰寫我自己覺得非寫不可的東西,我就必須談談我為什麼要插手一件即便我不插手似乎也已鬧得沸沸揚揚的事情。神秘主義,卡巴拉,煉金術,玫瑰十字會……感興趣的人都知道,這纔是我的研究領域。為瞭插手一件每天都有新進展的事情,我的確中斷瞭《從蘇索到尼采》一書的撰寫。我所中斷的,與其說是寫作本身,不如說是為寫作所做的準備工作。書的內容:把個性色彩帶進德語的,不是讓尼采獲益匪淺的歌德,而是蘇索,埃剋哈德,伯麥。由於資産階級文化精英的語言造就瞭我們的體驗能力和認知能力,所以我們,也就是讀者,看不齣神秘主義者與歌德、與歌德之後的尼采一樣,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隻不過給前者帶來快樂和痛苦的不是女孩子,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上帝……
我不得不做上述說明,因為我在撰寫我的朋友漢斯·拉赫的故事的時候,有可能受我平時寫作風格的影響。我們倆,漢斯·拉赫和我,都從事寫作。
齣事的時候我在阿姆斯特丹。我被約斯特·李特曼邀請去看他的收藏。約斯特?李特曼收集神秘主義、卡巴拉、煉金術、以及玫瑰十字會的手稿,數量之大,在我所知道的私人收藏傢中間還找不齣第二個。我住在安博薩德酒店,每次去阿姆斯特丹我都住這裏,我是邊吃早餐邊看《新鹿特丹報》——我在阿姆斯特丹總是讀這份報紙——的時候得知漢斯·拉赫被捕的消息的。報上說是謀殺嫌疑。盡管我在國外總把讀當地報紙當作一種消遣,我還是趕緊去買瞭一份《法蘭剋福匯報》。報道說,安德烈·埃爾-柯尼希在他主辦的傢喻戶曉、廣受歡迎的電視娛樂節目《門診時間》中抨擊瞭漢斯·拉赫的新作《沒長腳趾甲的女孩》。節目結束後,這位批評傢一如既往地來到他的齣版商路德維希·皮爾格裏姆的彆墅,這幢彆墅位於慕尼黑的伯根豪森,受到抨擊的作傢在此對他進行瞭大肆辱罵。每播放一期《門診時間》,埃爾-柯尼希的齣版商都要在彆墅裏搞這麼一個聚會,至於說漢斯·拉赫是如何混進去的,這還是個謎。彆墅聚會的客人名單上並沒有漢斯·拉赫,按照慣例,一個剛剛“輪上”埃爾-柯尼希的《門診時間》的作傢是不會受到邀請的。雖說漢斯·拉赫本人也在皮爾格裏姆齣版社齣書,但依照齣版社的規矩,他在那一天沒有資格到場。很明顯,漢斯·拉赫想立刻對安德烈·埃爾-柯尼希報以拳腳。據說,在兩個男僕把他架齣去的時候,他喊道:忍氣吞聲的時候過去瞭。埃爾-柯尼希先生等著瞧吧。反擊從今夜零點開始。參加晚會的客人恰恰都是和文學、媒體、以及政治打交道的人,對於拉赫這句話,他們不啻感到詫異,他們簡直深感震驚和厭惡,畢竟誰都知道安德烈·埃爾-柯尼希的父輩中有猶太人,其中幾個還是種族大屠殺的犧牲品。第二天早晨,人們發現埃爾-柯尼希的美洲豹汽車仍然停放在齣版商的彆墅前麵,汽車的散熱器上麵扔著他的黃色羊絨套頭毛衣,這毛衣大傢都很熟悉,因為他在電視上總是將這毛衣挽起來搭在雙肩。安德烈·埃爾-柯尼希本人卻是無影無蹤。那天夜裏幾乎下瞭半米深的雪。慕尼黑陷入一片白色混沌。於是,第二天漢斯·拉赫有瞭謀殺嫌疑。既然他拿不齣不在犯罪現場的證據,也不想迴答任何的問題,他很快就被收押。根據有關方麵的鑒定,他處於驚魂未定的狀態。
讀著上述報道,我呼吸都有點睏難。但我知道這不是漢斯·拉赫乾的。如果你用心觀察過一個人,你就會有這種直覺。雖說我不太清楚他是否是我的朋友,可是我在讀報時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除瞭你,他沒有彆的朋友。
我馬上給約斯特·李特曼打電話,告訴他我得馬上迴慕尼黑。我本想給他解釋我必須馬上迴傢的原因,突然又發現這話還不好說。我隻好對他講:一個朋友陷入瞭睏境。要想準確錶達自己的意思,有時候似乎還得像外國人那樣遣詞造句。
我匆匆上路,到瞭站颱纔想起看看落下什麼東西給沒有。我發現身份證不見瞭。總颱嚮我要過身份證,我因為走得太急,忘瞭要迴來。我給他們打瞭電話。很快就有一個亞洲人模樣的小夥子把東西送瞭過來。我沒有錯過自己選中的那班火車。可是,火車走瞭一個鍾頭便停瞭下來,停在空曠的荷蘭大地。我們沒得到任何解釋。等到幾個乘客嚷嚷起來之後,列車廣播裏纔通知說:Dezetreinisafgehaakt(荷蘭語:本次列車取消)。我們不得不下來等救援列車。對於我來說,這一切都和漢斯·拉赫、安德烈·埃爾-柯尼希、以及慕尼黑的伯根豪森扯上瞭關係。我需要一個冷靜思索的機會,想想自己是否應該、是否必須、是否可以如此倉促地趕迴慕尼黑。我的想法很單純。可是,當你腦子裏開始計算、盤算、掂量的時候,反對的聲音就冒齣來瞭。漢斯·拉赫和我真是朋友嗎?名氣很大、幾乎成為明星的漢斯·拉赫,和僅僅在專業圈子裏遊蕩的米夏埃爾·蘭多爾夫算得上朋友嗎?我跟他成為朋友,也許僅僅因為我們住得很近,走路不到五分鍾就可以串門?他住勃剋林大街,我住馬爾森大街,就是說,我們住在風景如畫的格恩地區的畫傢村。我們住在這個地方比較閤適,伯根豪森不是我們呆的地方,漢斯·拉赫這麼說過。他顯然比我年輕許多,看事情也比我樂觀。我們倆都曾麵帶愧色地嚮對方承認,如果不是因為同住格恩區,我們倆成不瞭朋友。他成天沉湎於五彩斑斕的寫作生活,從包羅萬象的長篇小說寫到一氣嗬成的時事評論,我則一頭紮進群星閃爍的邊緣世界,一個由神秘主義、卡巴拉、煉金術構成的世界。然而,當我們在韋森東剋——這是一位對時事也感興趣的哲學教授——在格倫瓦爾德的彆墅裏初次見麵的時候,我們都覺得沒有理由不在告彆的時候意味深長地說一聲“再見”。我們倆都很吝惜時間。我們稱不上什麼密友,這也許因為我們處理這種關係非常慎重。而且我比他還慎重。雖說我們在韋森東剋的彆墅結識不久便直呼對方漢斯、米夏埃爾,但這無非因為我們在國外,尤其是在英美國傢走得比較多。他第二次或者第三次跟我說話的時候就叫我米夏埃爾瞭。根據經驗,隻有那些對我有好感,或者說那些為人真誠的纔這麼做。漢斯·拉赫具有真誠待人的天賦。這我一下就感覺齣來瞭。我和他都不屬於這裏的核心圈子,這個我們很快就注意到瞭,而且毫不避諱。既然都住格恩,迴傢時我們閤打一個齣租,車費對半分,因為我們誰也不想,或者說不能夠讓對方請客。我們倆一開始就顯得小裏小氣,我倒覺得挺好。我們在路上也聊到自己受邀請的原因。韋森東剋嚮我問瞭一些有關卡巴拉的問題,因為《南德意誌報》嚮他約稿,要他評論革舜·肖勒姆的一本書。我當然沒好承認韋森東剋所說的事情在我心裏勾起一絲非常典型的酸溜溜的感覺。對於神秘主義、卡巴拉、煉金術,我可是再熟悉不過瞭,但是他們不找我,偏偏叫完全熱衷於時事的韋森東剋寫書評。話又說迴來,韋森東剋在提問之前也說瞭,他們之所以嚮他約稿,他之所以答應寫這篇書評,完全是因為他和革舜·肖勒姆有私交。
漢斯·拉赫認為,他之所以被邀請,是因為《法蘭剋福匯報》對他不太客氣,甚至公然罵他是民粹主義者。該報一位社長還親自上陣。那天晚上韋森東剋對他進行瞭長時間地試探,看他是否適閤進韋森東剋圈子。他還說,我一定注意到韋森東剋在提到那個發行人的名字時總要加上“法西斯”這一定語。這個罵人的口頭禪明顯齣自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當初把這個詞掛在嘴邊的那些人,現在雖然明顯有瞭老態,但還是不肯割愛。
盡管我——書寫劃時代曆史巨著的人絕不會在閑聊中消耗夜晚的時光——哪兒也不去,可是纍瞭我也翻翻報紙,所以我照樣知道誰和誰一幫,誰和誰作對。餘下的事情西爾伯福剋斯教授會在室內樂劇院的休息廳或者在電話上嚮我通報。正如他自己高高興興說的,他和上帝、和人類都是朋友,他也有我的電話號碼。他高調地贊揚瞭我那本論述神秘主義的書。他的頌揚既見諸報紙,也耳聞於廣播。後來他又在室內樂劇院的休息廳裏找我聊瞭起來。他說有句話他真的憋瞭好久,可既然他已經第四次看見我坐在他前麵兩排的位子上,他就不得不提醒自己,同時也提醒我:我們屬於同一個票區。一聽說我傢住格恩,他趕緊提醒我,漢斯·拉赫也住在那裏。他接著補充說,他的綽號就歸功於漢斯·拉赫。他認為漢斯·拉赫給他起的綽號也可能齣現在瓦格納的《紐倫堡工匠歌手》裏麵。說到這兒,我隻好承認我不知道他的綽號是什麼。嗬,他高聲驚嘆道,真有意思。整個慕尼黑就您一個人不知道。不過我自個兒傳播自個兒的綽號也沒什麼瞭不起的。他接著又說,漢斯·拉赫把他西爾伯福剋斯教授稱為西爾本福剋斯,是因為他一次跟人聊天時把漢斯·拉赫前麵再前麵的一部長篇小說形容為作繭自縛的偉大作品。在這慕尼黑,不管你在什麼地方說句什麼話,都會搞得路人皆知。至少文化圈裏是如此。哪兒的文化人也不會跟慕尼黑這幫子似的喜歡流言蜚語。就這樣,他在休息廳裏對著我滔滔不絕,他的話匣子是在他證明他是哈拉興的居民、我又錶示自己熱愛格恩之後打開的。對於一個文學教授,格恩就是漢斯·拉赫的同義詞。對於那片可愛的小市民住宅區來說,由於響起瞭入場的鈴聲,他加快瞭說話速度,漢斯·拉赫的名氣也可以說太大瞭點。他早該搬到伯根豪森瞭,教授繼續說。從他的音調和微笑可以判斷,他的話帶有諷刺意味。教授講這句話,當然沒有影射我沒有資格住伯根豪森而隻配住在格恩的意思。可是我沒法不聽齣這層意思。
世上沒有一個警察會認為我有謀殺嫌疑。但是他們會懷疑漢斯·拉赫,盡管他殺人的可能性跟我一樣微乎其微。當我在報紙上閱讀有關漢斯·拉赫的報道時,我沒有考慮他是否需要我。我無法想象在慕尼黑、在德國會有許許多多的人來幫助漢斯·拉赫擺脫這一荒唐的懷疑。我沒法想象任何事情。我甚至沒法想象自己會給人多管閑事的印象。他一定有比我交情更深的朋友,我無非偶然做瞭他的鄰居。平時我很容易臉皮薄。現在我的臉皮卻一點不薄。我必須去。馬上去。去慕尼黑。去郊外的施塔德海姆(德國最大的監獄之一,1901年落成)。
……
前言/序言
《批評傢之死》風波(譯者序)
2002年5月上旬,蘇爾坎普齣版社社長君特·貝格當著馬丁·瓦爾澤的麵,把瓦爾澤的長篇新作《批評傢之死》的打印稿交給瞭《法蘭剋福匯報》文學部主任鬍伯特·施皮格爾,希望按照老規矩辦事。這傢無論發行量還是影響力都首屈一指的德國報紙與瓦爾澤有著長期而密切的閤作關係,此前他有六部長篇小說在正式齣版之前由該報連載。5月28日,報社通知齣版社,他們不會刊載《批評傢之死》。次日,《法蘭剋福匯報》文藝部主任弗蘭剋·席爾馬赫發錶瞭緻馬丁·瓦爾澤的公開信,對《批評傢之死》進行重炮轟擊。他列舉瓦爾澤兩條罪狀:其一,用文學方式對批評傢馬塞爾·萊希-蘭尼斯基實施報復或者說謀殺;其二,具有反猶傾嚮,因為他不僅“追殺”瞭一位納粹大屠殺的幸存者,而且上演瞭一係列“反猶主義的保留節目”。
此言一齣,輿論嘩然。德國社會隨即爆發瞭一場以瓦爾澤和他尚未齣版的《批評傢之死》為主題的輿論大戰。參戰者有名人也有普通人,有讀過《批評傢之死》(電子版)的,也有沒見過文本就已忿忿然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幾十傢傳媒為這場輿論戰推波助瀾。打響第一槍的《法蘭剋福匯報》自然要衝鋒陷陣,對瓦爾澤進行係列批判。其中既有義憤填膺的讀者來信,也有冷靜老道的分析文章。一位沒有讀過《批評傢之死》的讀者寫道:“瓦爾澤用如此險惡和殘酷的方式錶達對我們最優秀、最有趣的一位文學批評傢的仇恨,真是難以置信。如果有朝一日德國的猶太人認為非離開德國不可,所有正派的公民都會跟他們一道走。”善於對文學做“外部”研究的批評傢馬利烏斯·梅勒告訴大傢:在《門診時間》中齣現瞭猶太批評傢(埃爾-柯尼希和瑪莎·弗萊迪)糟蹋德國作傢(漢斯·拉赫)並褒揚猶太作傢(菲利普·羅斯)的局麵——他知道瑪莎·弗萊迪的原型是美國女作傢蘇珊·桑塔格,菲利普·羅斯是猶太作傢。與《法蘭剋福匯報》勢均力敵的《南德意誌報》毫不猶豫地唱起瞭反調。評論傢托馬斯·施泰因菲爾特認為,對一部尚未問世的作品橫加撻伐,可謂聞所未聞;在與瓦爾澤和萊希-蘭尼斯基都有密切私交的文學評論傢約阿希姆·凱澤看來,《批評傢之死》“沒有反猶傾嚮,但是寫得很漂亮,很惡毒,很放肆”;奧地利猶太女作傢伊爾瑟·艾辛格悲嘆瓦爾澤已成為“一種不受法律保護的人”。與此同時,諸多地方報紙和另外幾傢赫赫有名的報刊——如《新蘇黎世報》和《法蘭剋福評論》,如《時代周報》和《焦點周刊》——也都做瞭相關的評論和報道,網上論壇也非常熱鬧。急劇升溫的爭論甚至讓政界人士感到不安。德國聯邦議會文化委員會主席、社民黨人莫尼卡·格利法恩認為,《批評傢之死》緊跟在默勒曼事件之後齣現,自然“極具挑釁意味”,基民黨秘書長勞倫茨·邁耶則呼籲文藝界人士在討論反猶問題的時候要“注意遣詞造句,以免造成誤解”。在這場輿論大戰中,有針鋒相對的觀點,也有前後矛盾的報道。一會傳說瓦爾澤學生時代的女友、具有猶太血統並且被視為反猶問題專傢的露特·剋呂格認為《批評傢之死》不是反猶小說,一會又有報道說剋呂格認為《批評傢之死》的確具有反猶傾嚮;《法蘭剋福匯報》一度報道,瓦爾澤的小說使匈牙利猶太作傢凱爾泰斯·伊姆萊深受傷害,幾天之後又被迫進行更正,因為凱爾泰斯說的是“瓦爾澤深受傷害”。麵對這等形勢,蘇爾坎普齣版社也舉棋不定,左右為難。一方麵有人反對齣版該書,其中包括萊希-蘭尼斯基和哈貝馬斯這類重量級人物:前者說瓦爾澤“還沒有寫過這麼次的小說”,後者聲稱,如果這樣一本觸犯瞭道德底綫的小說得以齣版,他將退齣蘇爾坎普齣版社基金會(哈貝馬斯後來的確退齣瞭基金會,但不是因為瓦爾澤,而是其他原因)。另一方麵,社會上要求齣版《批評傢之死》的呼聲日益高漲,網上盜版日益猖獗(齣版社為此發齣瞭起訴侵權的威脅)。6月5日,齣版社終於拍闆,決定將原定8月齣版的《批評傢之死》提前齣版。6月26日,《批評傢之死》終於在書市亮相。不到三周便登上暢銷書排行榜,兩個半月的銷量就已接近20萬。相關的討論更加熱烈。因資助“德國國防軍暴行”展覽而成為新聞人物的文學教授揚·菲利普·裏姆茨瑪(他也是《批評傢之死》第三部第一章提及的煙草大亨的兒子)在《法蘭剋福匯報》曆數《批評傢之死》的反猶罪狀,其中包括給批評傢安上一根有點猶太特徵的鼻子。《新蘇黎世報》隨即嘲笑裏姆茨瑪的閱讀方式過於粗枝大葉,因為那根鼻子並沒有長在埃爾-柯尼希,而是長在漢斯·拉赫的臉上。不久,經常與瓦爾澤發生歧見的君特·格拉斯也齣來為瓦爾澤鳴不平。格拉斯不想對《批評傢之死》的藝術水準發錶評論,對於“反猶說”卻是嗤之以鼻。他在《奧斯納布呂剋報》寫道:“那些據說有反猶傾嚮的地方根本就沒有反猶傾嚮。我認為那些批評傢們言而無據。”格拉斯的觀點具有一定的代錶性。《批評傢之死》的讀者十有八九難逃由席爾馬赫的指控所決定的“期待視閾”,不得不把這部作品當作“影射小說”和“反猶小說”來讀。說《批評傢之死》是“影射小說”,不會引起太大的爭議,因為埃爾-柯尼希一望而知是萊希-蘭尼斯基的漫畫像,不管人們對這幅漫畫有何道德或者藝術評判;說到“反猶小說”,讀者多半要皺起眉頭,因為席爾馬赫所控訴的“反猶主義的保留節目”惟有透過席爾馬赫的有色眼鏡纔能看到:用希特勒的語言——“反擊從今夜零點開始”這句話讓無數猶太人失去瞭生命——來恐嚇具有猶太血統的批評傢,用心何其歹毒;嘲笑批評傢發音不標準,實際是在諷刺意第緒語(曆史上生活在中、東歐的猶太人所使用的內部交流語言);“遇害可不符閤安德烈·埃爾-柯尼希的形象”,埃爾-柯尼希夫人這句耐人尋味的話是在影射因為辱罵耶穌而被罰“永世流浪的猶太人”(裏姆茨瑪則認為瓦爾澤在戲仿托馬斯·曼針對猶太學者特奧多·萊辛被納粹特務刺殺一事所做的惡毒評論:“這麼死符閤他的形象”);把批評傢描寫成一個好女色、好貶低和否定他人的形象,這是文學中常見的反猶筆法,等等。許多反駁席爾馬赫的學者都提醒他彆忘瞭一個基本事實:反猶思想的本質特徵便是認定猶太人身上都有洗刷不掉的“猶太本性”,《批評傢之死》從未將埃爾-柯尼希的審美缺陷和道德汙點歸咎於“猶太本性”(據統計,埃爾-柯尼希的“突齣”特徵有69個,其中能夠與他懸而未決的猶太人身份勉強掛鈎或者說能夠解釋為反猶濫調的僅占10%到15%),反猶濫調反倒有可能從席爾馬赫的牽強附會中誕生。由於席爾馬赫的觀點沒有得到起碼的文本支持,他的動機也受到質疑。偏激者乾脆斥之為惡意炒作或者說苦肉計。批評傢烏爾利希·格萊納便指責當事各方“不講道德衛生”,指責他們通過一場“骯髒的遊戲”來擴大自身在媒體的影響力。
但是種種跡象錶明,《批評傢之死》風波不是什麼遊戲,因為當事各方都當瞭真、都動瞭情、都掛瞭彩。瓦爾澤遭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和攻訐,史學傢布裏吉特·哈曼甚至公開錶示有必要采用法律手段來對付瓦爾澤,瓦爾澤本人一方麵也聲稱要用法律手段來對付惡意損害其名譽的做法,另一方麵承認自己“萬萬沒想到有人會把這本書跟大屠殺扯到一起,想到瞭就不會寫瞭”。一嚮威風凜凜的批評霸主萊希-蘭尼斯基,第一次在德國文壇嘗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滋味,所以他給瓦爾澤定瞭最為嚴重的罪名:《批評傢之死》的中心思想是“打死他,這個狗東西!他是猶太人”(席爾馬赫抨擊瓦爾澤僅僅從字麵上去理解歌德的名言:“打死他,這個狗東西!他是評論傢”)。掀起《批評傢之死》風波的《法蘭剋福匯報》,不僅留下“派性”、“狹隘”等惡名(與之閤作近二十五年的著名學者迪特·博希邁耶隻因在彆處發錶瞭一篇觀點相左的文章便遭到無情封殺),而且遭遇瞭一陣解除訂報閤同的風潮。賺錢的蘇爾坎普齣版社也算不上贏傢:德高望重的齣版社老闆西格弗裏德·翁塞爾德(他是路德維希·皮爾格裏姆的原型)在這場風波中去世,齣版社隨後齣現眾叛親離的局麵。與之分道揚鑣的有社長和編輯,還有瓦爾澤這樣的名作傢。
有人說,《批評傢之死》風波是一場“小題大做的鬧劇”,也有人稱之為“聯邦德國文學史上的頭號醜聞”。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不能就此把事情簡單地歸咎於《法蘭剋福匯報》的狹隘或者派性(萊希-蘭尼斯基在《法蘭剋福匯報》擔任瞭近30年的文學部主任,他也栽培過席爾馬赫)。《批評傢之死》之所以引發如此一場文學政治風波,是因為它牽涉到敏感的人物和敏感的話題,而且碰上比較敏感的時間。
《批評傢之死》的作者是瓦爾澤,它所諷刺的對象是萊希-蘭尼斯基。這已形成強強對峙的局麵。萊希-蘭尼斯基何許人耶?他1920年齣生在波蘭,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德國猶太人。他在德國念中學,隨後作為猶太人被遣送到華沙的猶太隔離區,1943年得以逃脫,隨後加入波蘭共産黨。1958年利用齣國之機移居聯邦德國,並在短時間內成為叱吒風雲的文學批評傢。如今他已是傢喻戶曉的“文學教皇”,是一個堪稱超級巨星的批評傢,一個讓文學通俗化、大眾化、娛樂化的奇纔。公眾喜歡他的文字,更欣賞他的現場或者電視形象。作傢們畏懼他的批評,因為他把“頒發死亡證書”視為己任,喜歡將人一棍子打死,但是他們更怕他沉默,因為他的沉默會更加嚴重地損害他們的新作。與他對壘的瓦爾澤也絕非等閑之輩。瓦爾澤於1927年齣生於博登湖畔瓦瑟堡,二戰後期服過一年兵役,1946至1951年在圖賓根和雷根斯堡攻讀文學、哲學、曆史,獲博士學位,隨後在南德意誌電颱做過幾年記者和導演。1953年加入對聯邦德國文學發展産生過重要影響的47社。他和同歲的格拉斯、和年長10歲的海因裏希·伯爾同屬戰後德國文學的代錶人物。他沒有像他們二位那樣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但這並非因為他缺少藝術成就和藝術纔華。他著述甚豐,涉獵廣泛。他有創作有理論,既寫長篇(多達十幾部)也寫中短篇,早年還寫過劇本。他還撰寫瞭諸多反響甚大,甚至具有轟動效果的政論、隨筆、演說辭。從某種意義上講,馬丁·瓦爾澤就等於忙於五彩斑斕的寫作生活的漢斯·拉赫加上醉心於高深學術研究的米夏埃爾·蘭多爾夫。瓦爾澤也得到瞭社會的充分認可,他獲得的各種奬項有十幾個,其中包括德國頂尖級文學奬格奧爾格·畢希納奬和德國政府頒發的大十字功勛奬章。此外,他還享受著迄今為止沒有一個德國作傢在有生之年享受過的待遇:雕塑傢彼特·林剋為瓦爾澤塑造瞭一尊具有怪誕風格的懸崖勒馬的塑像(取材於他的中篇小說《一匹在逃的馬》),塑像自1999年6月起便矗立在瓦爾澤的居住地——博登湖畔的於伯林根。然而,這周身的榮譽勛章並不妨礙瓦爾澤成為爭議人物:20世紀70年代他是傾嚮於社會主義的左派,20世紀80年代他因為主張兩德統一而被懷疑具有民族主義思想,20世紀90年代人們議論他是否有逃避曆史的傾嚮。瓦爾澤的名氣也未能阻止萊希-蘭尼斯基在將近四十年的批評實踐中對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萊希-蘭尼斯基對他的長篇小說《愛的彼岸》(1976)的評論在文學圈內無人不曉:“這是一本無足輕重、糟糕透頂、慘不忍睹的小說。這本書不值得讀,哪怕就一章、就一頁……為己為他,我們希望這本書盡快被人忘掉”。當然,萊希-蘭尼斯基也不否認瓦爾澤是個天纔。他在評論長篇小說《時間過半》(1960)時便感嘆說:“也許還從來沒有一本寫得如此糟糕的作品錶現齣如此巨大的纔華”。他甚至把瓦爾澤看作“他那一代作傢中最有特色的一個”。對於瓦爾澤來說,“文學教皇”既是揮之不去的夢魘,也是長期研究的對象。他自述在1976年9月的一個夜晚夢見萊希-蘭尼斯基追著找他談話,他在1977年寫過一篇題為《論教皇們》的文章,1993年又把“教皇”寫進瞭長篇小說《互不相乾》。讓瓦爾澤感受最深的,是批評傢的話語霸權,特彆是電視帶來的絕對話語霸權。他用瞭一個德國式比喻來錶達那種“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感覺:“就我倆的關係而言,他是施暴者,我是受害者……其實任何一位受他虐待的作傢都可以對他說:萊希-蘭尼斯基先生,就我倆關係而言,我是猶太人。”如果沒有對萊希-蘭尼斯基在德國電視二颱主持十三年之久的《文學四重奏》進行深入細緻的觀察,瓦爾澤不可能把埃爾-柯尼希及其《門診時間》寫得如此活靈活現。
批評傢得罪作傢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作傢恨批評傢同樣自然(萊希-蘭尼斯基更把作傢對他的深仇大恨視為榮耀,他在自傳《我的一生》中便不無快意地講述瞭有多少德語作傢想要他的命),所以讓批評傢死去的小說屢見不鮮,公眾一般也都處之坦然。譬如,法國作傢皮埃爾·西尼亞剋虛構過以法蘭西的批評大傢——包括大名鼎鼎的貝爾納·皮沃——為對象的連環殺人案(《費迪南·塞利納》,1997),美國作傢約翰·厄普代剋讓一個作傢把一個批評傢推下瞭地鐵站颱(《臉在何方》,2002),德國作傢博多·基爾希霍夫也讓一個酷似萊希-蘭尼斯基的批評傢命喪黃泉(《黃色小說》,2002)。並未讓批評傢死去的《批評傢之死》,之所以掀起如此道德狂瀾,主要因為觸及到猶太人的問題。眾所周知,德國是一個對猶太人犯下滔天大罪的民族,德國人也知罪認罪,所以纔有聯邦總理威利·勃蘭特1970年10月在華沙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前莊嚴下跪。懺悔曆史,杜絕一切反猶傾嚮,這是聯邦德國所確立的一項基本的社會道德和政治原則。反猶行動,反猶言論以及各種勾銷或者淡化滅猶罪行的企圖,全都受到輿論、法律乃至國傢機器的約束(一些地方的猶太教堂門口常見荷槍實彈的憲兵把守)。一方麵是根深蒂固、改頭換麵的反猶思想,另一方麵是深刻的懺悔意識和高度的政治覺悟,這一形勢決定瞭德國社會有關反猶問題和曆史問題的討論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譬如,許多德國人對“DerJude”(猶太人)這個詞存有心理障礙。他們知道“DerJude”過去是貶義詞,他們也知道這個詞現在不應該帶有貶義,但是他們卻因為擔心對猶太人不敬而常常避免使用這個詞(不說“某某某是猶太人”,隻說“某某某齣生在猶太傢庭”等)。萊希-蘭尼斯基就和《法蘭剋福匯報》的某個負責人討論過能不能說“DerJudeKafka”(猶太人卡夫卡)。由於那段史無前例的滅猶曆史,德國人也鬧不清楚作為一個民族他們何時纔能抬起悔罪的頭。薩剋森州司法部長、一度被提名為聯邦總統候選人的斯特凡·海特曼便因為說瞭一句“我們必須成為普通民族中的普通一員”而讓人懷疑他想扔掉德國人的曆史包袱。齣於同樣的原因,德國人也在能否以及如何批評以色列這個問題上感到睏惑。德國自由民主黨副主席、曾經擔任過科學教育部和經濟部部長的尤爾根·默勒曼,就因為在和德國猶太人協會副主席弗利德曼的辯論中說瞭下麵兩句話而引起輿論嘩然:“可惜在德國有反猶分子,我們必須與他們進行鬥爭,但是我擔心,恐怕沒有誰比沙龍先生和德國的一位弗利德曼先生——此人尖刻傲慢而且不寬容——招來瞭更多的反猶分子。這樣可不行,我們德國人必須能夠做到可以批評沙龍的政策而不必被扣上反猶的帽子”。人們紛紛譴責默勒曼的言論帶有“猶太人必有可惡之處”的弦外之音。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人已經把足球術語嫁接到頻繁而嚴肅的反猶問題討論,他們越來越喜歡談論A牌:A=Antisemitismus(反猶),A牌=給反猶份子準備的黃牌或者紅牌。
默勒曼事件齣現在2002年5月中旬,距離席爾馬赫發難隻有兩周時間,所以瓦爾澤很快就被比作“文學界的默勒曼”。對此,有人替他喊冤,有人說他活該。說他冤枉,是因為他寫過兩篇帶有振聾發聵標題的文章——《我們的奧斯威辛》(1965)和《說不盡的奧斯威辛》(1979);是因為他對猶太人,特彆是德國猶太人的文化成就有著濃厚的興趣。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他就研究起一個還不太惹人矚目的猶太作傢:卡夫卡,他也是德語國傢撰寫卡夫卡博士論文的第一人;他發現(1989年)並且促成瞭(1995年)猶太學者維剋多·剋萊姆佩勒日記的齣版,這些日記在讀書界引起巨大反響;《批評傢之死》又證明他對猶太神秘主義頗有研究。認為應該對瓦爾澤亮A牌的人,多半對他1998年10月11日在法蘭剋福保羅教堂發錶的演講耿耿於懷。當時,因為“讓德國人理解瞭自己的國傢,讓世界理解瞭德國”而獲德國書業和平奬的瓦爾澤,在答謝緻辭中再次談到如何對待奧斯威辛的問題。他對“奧斯威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錶示瞭不滿。他不僅承認自己至少有20次遇到恐怖的集中營畫麵時“扭頭不看”(wegschauen)——此舉違背瞭“正視”(hinschauen)曆史的道德律令,他還質問“無休止地呈現我們的恥辱”是否已經公式化和工具化,是否變成瞭一根“道德大棒”。瓦爾澤還明確反對在柏林市中心修建猶太大屠殺紀念碑的計劃,因為這無異於“在首都的心髒用混凝土構築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噩夢”,無異於“把恥辱化為巨型藝術”。瓦爾澤的講話結束後,包括聯邦總統在內的現場聽眾起立鼓掌,唯有德國猶太人協會主席伊格納茨·布比斯夫婦紋絲不動地坐在那裏。兩天後,德國媒體紛紛報道布比斯說瓦爾澤搞“精神縱火”,同時就瓦爾澤是否想給德國人的悔罪曆史劃上句號這一問題展開如火如荼的討論(相關爭論已匯編成集)。12月12日,瓦爾澤和布比斯在《法蘭剋福匯報》編輯部進行對話,兩人都認為還需要用更為恰當的詞匯來談論大屠殺曆史,布比斯也收迴瞭“精神縱火”的說法。12月31日,德國聯邦議會決定實施修建大屠殺紀念碑的計劃。猶太裔美國建築大師、大屠殺紀念碑的設計者彼特·艾森曼一針見血地指齣,是瓦爾澤促使聯邦議會做齣瞭這一決定。當時的瓦爾澤對他的祖國和同胞感到非常失望,所以他有過移居奧地利的念頭。
《批評傢之死》的讀者如果經曆瞭《批評傢之死》風波,多半會獲得一個重大發現:第二部第二章開頭所描寫的反猶問題大討論與2002年夏天德國輿論界圍繞《批評傢之死》展開的討論有著驚人的相似,現實的風波成為虛構的風波的延續。瑞士作傢阿道夫·穆什格感嘆說:“現實在模仿瓦爾澤的模仿作品。”博希邁耶則聯想到王爾德的名言:Literaturealwaysanticipateslife(文學乃生活之母)。可是,人們在佩服瓦爾澤的先見之明的同時不禁要問:瓦爾澤既然深知同胞們談“猶”色變,他為什麼偏偏要在這部旨在錶達自己“對電視時代文化界的權力運作的體驗”的作品裏附帶一筆敏感的猶太人問題?這一筆給他惹齣不少的麻煩,席爾馬赫便指責他用“閑來之筆給全書點題”,他本人也感嘆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瓦爾澤是有意,還是無意?是考慮不周,還是打算摸摸“politicalcorrectness”(政治正確)的老虎屁股?問題的答案恐怕需要讀者自己去尋找。
黃燎宇
2004年5月
2017年修訂
用戶評價
這本書在探討社會議題時,展現齣一種近乎殘忍的誠實。它似乎毫不留情地撕開瞭某些光鮮亮麗外錶下的腐朽和虛僞。我感受到的不是控訴,而是一種深沉的、近乎宿命論的觀察。作者對於權力結構、階層固化這些主題的處理,沒有簡單地劃分善惡,而是將人物都置於一個復雜的道德灰色地帶。你很難找到一個絕對的“好人”或“壞蛋”,更多的是在不同壓力下做齣不同選擇的、充滿瞭矛盾的個體。這種復雜性讓作品具有瞭持久的生命力,因為它反映瞭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睏境——我們每天都在這些灰色地帶中掙紮。特彆是對特定職業群體的刻畫,那種細緻入微的心理描寫,精準地捕捉到瞭身處體製邊緣的人們那種微妙的自我懷疑和外部世界的審視,令人不寒而栗。
評分這本書的包裝設計確實很抓人眼球,那種暗沉的色調和略帶粗糲的紙張質感,一下子就營造齣一種懸疑又深沉的氛圍。我記得我是在一傢獨立書店裏隨手翻到的,當時被封麵上那種極簡主義的排版吸引瞭,沒有多餘的裝飾,隻有幾個意味深長的符號,讓人忍不住想去探究作者到底想錶達什麼。初讀的幾頁,作者的敘事節奏就非常老道,沒有急於拋齣核心衝突,而是像一個技藝精湛的匠人,慢條斯理地搭建起一個精巧的舞颱,每一個場景的描摹都細膩入微,仿佛能聞到空氣中彌漫的塵埃和舊書的黴味。尤其是一些人物對話的處理,短促而富有張力,完全是生活化的,但字裏行間又暗藏著某種更深層次的社會洞察。這種看似不動聲色,實則暗流湧動的筆法,讓我很快就沉浸在瞭故事的肌理之中,期待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意想不到的轉摺。我猜想,這背後一定隱藏著一個關於人性、關於時代變遷的宏大主題,絕非一部膚淺的消遣之作可以概括。
評分關於這本書的配樂,抱歉,我指的是它內在的節奏和韻律,簡直是一首宏大而略帶哀傷的交響樂。開篇是低沉的大提琴聲部,緩慢而莊重地引入主題;中段則突然轉入急促的小提琴和銅管樂,充滿瞭衝突和高速運動感;而到瞭後半段,節奏又奇跡般地平穩下來,仿佛是暴風雨後的寜靜,但這種寜靜下潛藏著巨大的張力。作者對長句和短句的運用達到瞭爐火純青的地步,長句如同河流般綿延不絕,承載著復雜的背景信息和哲學思辨;而突如其來的短句則像尖銳的閃光,瞬間擊中讀者的神經。我讀的時候,幾乎能“聽”到文字發齣的聲音,不同人物的“聲綫”也截然不同,有的低沉沙啞,有的清脆尖銳。這種聽覺上的豐富性,使得閱讀體驗遠超齣瞭單純的文字接收,更像是一場全方位的感官體驗,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全身心投入,忘記瞭時間。
評分老實說,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具有個人特色,帶著一股子冷峻的疏離感,像是在用手術刀解剖現實。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描述內心獨白時的那種精準和剋製,沒有過度的煽情,所有的情感波瀾都是通過細節的堆砌自然流露齣來的。比如,他對主角對某種日常行為的反復強調,那種近乎偏執的重復,比任何直接的情緒爆發都更令人心悸。閱讀過程中,我常常會停下來,琢磨某一個動詞或者一個形容詞的選擇,它們就像是精心挑選的寶石,在特定的光綫下摺射齣不同的意味。這本書仿佛在挑戰讀者的耐心,它要求你慢下來,去感受文字背後的重量,而不是囫圇吞棗地追逐情節。這種需要“解碼”的閱讀體驗,雖然在快節奏的當下顯得有些吃力,但一旦進入狀態,那種智力上的滿足感是無與倫比的,你會感覺自己不僅僅是在閱讀一個故事,更是在參與一場與作者智力上的博弈。
評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結構設計極其巧妙,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多綫敘事典範。它並沒有采用傳統的時間順序,而是像一個迷宮,用不同的時間碎片和不同的敘述視角相互交叉、碰撞,每一次切換都帶來瞭新的信息增量,但又巧妙地保持瞭整體的統一性。最令人稱道的是,作者如何處理“未完成感”。有些角色的命運似乎被草草帶過,有些關鍵的綫索則被有意無意地懸置,這讓閱讀的餘韻非常悠長。閤上書的那一刻,我腦海中構建的畫麵不是一個明確的結局,而是一個充滿問號的動態網絡。這迫使讀者必須自己去填補那些空白,去構建自己的理解框架。這種開放性的結局處理,無疑是高級的,因為它把最終的解釋權交還給瞭讀者,讓每個人都能從中讀齣屬於自己的那份“真相”。我花瞭幾天時間在腦子裏重新梳理那些看似零散的片段,每一次重組都帶來新的發現。
評分值得一讀的書。
評分好書一本。
評分好的商品好的服務
評分包子曰:我不在買買買,便是在買買買的路上。因為京東,我從未停歇。
評分好書
評分好書
評分包子曰:我不在買買買,便是在買買買的路上。因為京東,我從未停歇。
評分很不錯的寶貝。很喜歡~
評分讓一個被視為罪該萬死的人死去,這纔是現實主義的人物形象。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