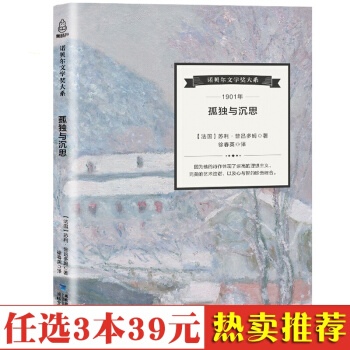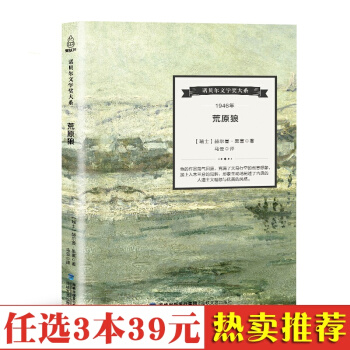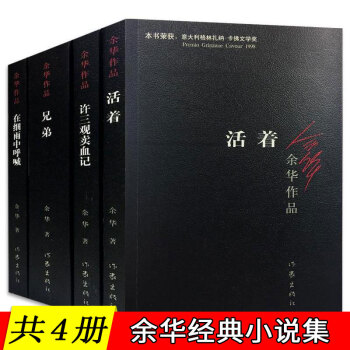具体描述
商品参数
| 被掩埋的巨人/浮世画家/远山淡影/无可慰藉/小夜曲(上海译文)5册 | ||
| 定价 | 179.00 | |
| 出版社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次 | 1 | |
| 出版时间 | 2011年05月 | |
| 开本 | 32 | |
| 作者 | 石黑一雄 | |
| 装帧 | 精装 | |
| 页数 | 0 | |
| 字数 | 0 | |
| ISBN编码 | 9787532753451 | |
内容介绍
内容简介:
《小夜曲》是石黑一雄的diyi部短篇集,全书以音乐为线索,由五个看似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故事的主要人物都同音乐情牵相关:郁郁不得志的餐厅乐手,风光不再的过气歌星,孤芳自赏的大提琴手,为求成功被迫整容的萨克斯手等等,多是对音乐一往情深,对生活却满腹牢骚。情节或荒诞不经,或令人唏嘘,借音乐人生这个主题,表现了作者一贯的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反思: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命运的嘲弄,才华的折磨,以及庞大社会机器控制下被压抑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小夜曲》中大量出现的音乐家、歌手、歌名,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令人仿若置身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当红歌手和经典曲目之中;而音乐,恰是作者年轻时曾经涉足,并浸淫于其中,乃至立志从事的。
作者简介: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1989年获得“布克奖”,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英国文坛移民三雄”。被英国皇室授勋为文学骑士,并获授法国艺术文学骑士勋章。
2017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为“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石黑一雄文体以细腻优美著称,几乎每部小说都被提名或得奖,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八种语言。
虽然拥有日本和英国双重的文化背景,但石黑一雄却是极为少数的、不专以移民或是国族认同作为小说题材的亚裔作家之一。他致力于写出一本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于是,石黑一雄的每一本小说几乎都在开创一个新的格局,横跨了欧洲的贵族文化、现代中国、日本,乃至于1990年代晚期的英国生物科技实验,而屡屡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惊喜。
目录
作品系列:
[ 石黑一雄作品 ]
远山淡影
浮世画家
长日将尽
无可慰藉
我辈孤雏
莫失莫忘
小夜曲
被掩埋的巨人
评论:
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瑞典学院
作品谦逊得近乎无形,犹如隐藏着惊涛骇浪的平静湖面。
——《洛杉矶时报》
精彩书摘:
伤心情歌手
我发现托尼·加德纳坐在游客当中的那天早上,春天刚刚降临威尼斯这里。我们搬到外面广场上来刚好一个星期——跟你说,真是松了口气,在咖啡厅的zui里面演奏又闷又挡着要用楼梯的客人的路。那天早上微风习习,崭新的帐篷在我们身边啪啪作响,我们都觉得比平时更加愉悦和精神,我想这种心情一定反映在我们的音乐里了。
瞧我说得好像我是乐队的固定成员似的。事实上,我只是那些个“吉卜赛人”中的一个,别的乐手这么称呼我们,我只是那些个奔走于广场、三个咖啡厅的管弦乐队里哪个缺人,就去哪里帮忙的人中的一个。我主要在这家拉弗娜咖啡厅演奏,但若遇上忙碌的下午,我就要先和夸德里的小伙子们演奏一组,然后到弗洛里安去,再穿过广场回到拉弗娜。我和这三支乐队都相处得很好——和咖啡厅的服务生们也是——在别的哪个城市,我早就有固定职位了。可是在这里,传统和历史根深蒂固,事情都倒过来了。在其他地方,吉他手可是受人欢迎的。可是在这里?吉他手!咖啡厅的经理们不自在了。吉他太现代了,游客不会喜欢的。去年秋天,我弄来了一把老式椭圆形音孔的爵士吉他,像强哥·莱恩哈特二十世纪欧洲爵士吉他巨匠,吉卜赛人,出生于比利时。弹的那种,这样大家就不会把我当成摇滚乐手了。事情容易了些,可经理们还是不喜欢。总之,实话告诉你吧: 倘若你是个吉他手,就算你是吉他大师乔·帕斯,也甭想在这个广场找到一份固定工作。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原因: 我不是意大利人,更别说是威尼斯人。那个吹中音萨克斯风的捷克大个子情况和我一样。大伙儿都喜欢我们,乐队需要我们,可我们就是不符合正式要求。咖啡厅的经理们总是告诉你: 闭上你的嘴,只管演奏就是了。这样游客们就不会知道你不是意大利人了。穿上你的制服,戴上你的太阳镜,头发往后梳,没有人看得出来,只要别开口说话。
可是我混得还不错。三支乐队都需要吉他手,特别是当他们与竞争对手同时演奏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个轻柔、纯净,但是传得远的声音作背景和弦。我猜你会想: 三支乐队同时在一个广场上演奏,听起来多混乱啊。可是圣马可广场很大,没有问题。在广场上溜达的游客会听见一个曲子渐渐消失,另一个曲子渐渐大声,就好像他在调收音机的台。会让游客们受不了的是你演奏太多古典的东西,这些乐器演奏版的著名咏叹调。得了,这里是圣马可,游客们不想听zui新的流行音乐。可是他们时不时要一些他们认得的东西,比如朱莉·安德鲁斯英国著名电影和舞台剧演员、歌唱家。的老歌,或者某个著名电影的主题曲。我记得去年夏天有一次,我奔走于各个乐队间,一个下午演奏了九遍《教父》。
总之就是在这样一个春天的早晨,当我们在一大群游客面前演出的时候,我突然看见托尼·加德纳,独自一人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杯咖啡,差不多就在我们的正前方,离我们的帐篷大概只有六米远。广场上总是能看见名人,我们从来不大惊小怪。只在演奏完一曲后,乐队成员间私下小声说几句。看,是沃伦·比蒂美国著名演员、导演。。看,是基辛格。那个女人就是在讲两个男人变脸的电影里出现过的那个。我们对此习以为常。毕竟这里是圣马可广场。可是当我发现坐在那里的是托尼·加德纳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激动极了。
托尼·加德纳是我母亲zui喜爱的歌手。在我离开家之前,在那个共产主义时代,那样的唱片是很难弄到的,可我母亲有他几乎所有的唱片。小时候我刮坏过一张母亲的珍贵收藏。我们住的公寓很挤,可像我那个年纪的男孩子有时就是好动,尤其是在冬天不能出去的时候。所以我就从家里的小沙发跳到扶手椅上这样玩,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了唱片机。唱针“嗞”的一声划过唱片——那时还没有CD——母亲从厨房里出来,冲我大声嚷嚷。我很伤心,不是因为她冲我大声嚷嚷,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托尼·加德纳的唱片,我知道那张唱片对她来说多么重要。我还知道从此以后,当加德纳轻声吟唱那些美国歌曲时,唱片就会发出“嗞嗞”的声音。多年以后,我在华沙工作时得知了黑市唱片,我给母亲买了所有的托尼·加德纳的唱片,代替旧的那些,包括我刮坏的那一张。我花了三年才买齐,可我坚持不懈地买,一张张地买,每次回去看望她都带回去一张。
现在你知道当我认出托尼·加德纳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了吧,就在六米以外啊。起初我不敢相信,我换一个和弦时一定慢了一拍。是托尼·加德纳!我亲爱的母亲要是知道了会说什么啊!为了她,为了她的回忆,我一定要去跟托尼·加德纳说句话,才不管其他乐手会不会笑话我,说我像个小听差。
但是我当然不可能推开桌椅,朝他冲过去。我还得把演出演完。跟你说,真是痛苦极了,还有三四首歌,每一秒钟我都以为他要起身离开了。可是他一直坐在那里,独自一人,盯着眼前的咖啡,搅呀搅,好像搞不清楚服务生给他端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的装扮与一般的美国游客一样,浅蓝色的套头运动衫、宽松的灰裤子。以前唱片封面上又黑又亮的头发如今几乎都白了,但还挺浓密,而且梳得整整齐齐,发型也没有变。我刚认出他时,他把墨镜拿在手里——他要是戴着墨镜我不一定能认出来——但是后来我一边演奏一边盯着他,他一会儿把墨镜戴上,一会儿拿下来,一会儿又戴上。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而且没有认真在听我们演奏,让我很是失望。
这组歌曲终于演完了。我什么也没有对其他人说,匆匆走出帐篷,朝托尼·加德纳的桌子走去,突然想到不知如何与他攀谈,心里紧张了一下。我站在他的身后,他的第六感却让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想这是出于多年来有歌迷来找他的习惯——接着我就介绍自己,告诉他我多么崇拜他,我在他刚刚听的那个乐队里,我母亲是他热情的歌迷等等,一古脑儿全都说了。他表情严肃地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好像他是我的医生。我不停地讲,他只偶尔说一声:“是吗?”过了一会儿我想我该走了,转身要离开,突然听见他说:
“你说你是从波兰来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
“都过去了。”我笑笑,耸了耸肩。“如今我们是个自由的国家了。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太好了。那就是刚刚为我们演奏的你的同仁吧。坐下。来杯咖啡?”
我说我不想叨扰他,可是加德纳先生的语气里有丝丝温和的坚持。“不会,不会,坐下。你刚才说你母亲喜欢我的唱片。”
于是我就坐了下来,接着说。说我的母亲、我们住的公寓、黑市上的唱片。我记不得那些唱片的名字,但我能够描述我印象中那些唱片套子的样子,每当我这么做时,他就会举起一根手指说“哦,那张是《duyiwuer》。《duyiwuer的托尼·加德纳》”之类的。我觉得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游戏,突然我注意到加德纳先生的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转过头去,刚好看见一个女人朝我们走来。
她是那种非常优雅的美国女人,头发优美,衣服漂亮,身材姣好,不仔细看的话不会发现她们已经不年轻了。远远地看,我还以为是从光鲜的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儿呢。可是当她在加德纳先生身旁坐下,把墨镜推到额头上去时,我发现她至少五十了,甚至不止。加德纳先生对我说:“这位是我的妻子琳迪。”
加德纳太太朝我敷衍地笑了笑,问她丈夫:“这位是谁?你交了个朋友。”
“是的,亲爱的。我们聊得正欢呢,我和……抱歉,朋友,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扬,”我立刻答道。“但朋友们都叫我雅内克。”
琳迪·加德纳说:“你是说你的小名比真名长?怎么会这样呢?”
“别对人家无礼,亲爱的。”
“我没有无礼。”
“别取笑人家的名字,亲爱的。这样才是好姑娘。”
琳迪·加德纳无助地转向我说:“你瞧瞧他说些什么?我冒犯你了吗?”
“不,不,”我说,“一点也没有,加德纳太太。”
“他总是说我对歌迷无礼。可是我没有无礼。我刚刚对你无礼了吗?”然后她转向加德纳先生,“我很正常地在跟歌迷讲话,亲爱的。我就是这样讲话的。我从来没有无礼。”
“好了,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别小题大做了。而且,这位先生也不是什么歌迷。”
“哦,他不是歌迷?那他是谁?失散多年的侄子?”
“别这么说话,亲爱的。这位先生是我的同行。一位职业乐手。刚刚他在为我们演奏呢。”他指了指我们的帐篷。
“哦,对!”琳迪·加德纳再次转向我,“刚刚你在那里演奏来着?啊,很好听。你是拉手风琴的?拉得真好!”
“谢谢。其实我是弹吉他的。”
“弹吉他的?少来了。一分钟之前我还在看着你呢。就坐在那里,坐在那个拉低音提琴的旁边,手风琴拉得真好。”
“抱歉,拉手风琴的是卡洛。秃头、个大的……”
“真的?你不是在骗我?”
“亲爱的,我说了,别对人家无礼。”
加德纳先生并没有提高音量,可是他的声音突然变得严厉和气愤,接着,出现了一阵异样的沉默。zui后,是加德纳先生自己打破了沉默,温柔地说: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是有意要训你的。”
他伸出一只手去拉妻子的手。我本以为加德纳太太会推开他,没想到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子,好靠近加德纳先生一点,然后把另一只手搭在他们握紧的手上。一时间他们就那么坐着,加德纳先生低着头,他妻子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出神地看着广场那头的大教堂。她的眼睛虽然看着那里,但却好像并没有真的在看什么。那几秒钟,他们好像不仅忘了同桌的我,甚至忘了整个广场的人。zui后加德纳太太轻声说:
“没关系,亲爱的。是我错了。惹你生气了。”
他们又这样手拉着手对坐了一会儿。zui后她叹了口气,放开加德纳先生的手,看着我。这次她看我的样子和之前不一样。这次我能感觉到她的魅力,就好像她心里有这么个刻度盘,从一到十,此时,对我,她决定拨到六或七,可我已经觉得够强烈的了,如果此时她叫我为她做些什么——比如说到广场对面帮她买花——我会欣然从命。
“你说你叫雅内克,是吗?”她说。“对不起,雅内克。托尼说得对。我不应该那样子跟你说话。”
“加德纳太太,您真的不用担心……”
“我还打扰了你们的谈话。音乐家之间的谈话,我想。好吧,我走了,你们继续聊。”
“你用不着离开,亲爱的,”加德纳先生说。
“用得着,亲爱的。我很想去那家普拉达专卖店看看。我刚刚过来就是要跟你说我会晚一点。”
“好,亲爱的。”托尼·加德纳diyi次直了直身子,深吸了一口气。“只要你喜欢就好。”
“我在那家店里会过得很愉快的。你们俩,好好聊吧。”她站起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保重,雅内克。”
我们看着她走远,接着加德纳先生问了我一些在威尼斯当乐手的事情,特别是夸德里乐队的事,因为他们刚好开始演出。他好像不是特别认真在听我回答,我正准备告辞时,他突然说道:
“我要跟你说一些事,朋友。我想说说我心里的事,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了。”他俯过身来,降低了音量。“事情是这样。我和琳迪diyi次到威尼斯来是我们蜜月的时候。二十七年前。为了那些美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再回到这里来过,没有一起回来过。所以当我们计划这次旅行,这次特别的旅行时,我们对自己说我们一定要来威尼斯住几天。”
“是你们的结婚周年纪念啊,加德纳先生?”
“周年纪念?”他很吃惊的样子。
“抱歉,”我说。“我以为,因为您说是特别的旅行。”
他还是吃惊地看着我,突然大笑起来,高声、响亮的笑。我突然想起我母亲以前经常放的一首歌,在那首歌里加德纳先生有一段独白,说什么不在乎恋人已经离他而去之类的,中间就有这种冷笑。现在同样的笑声回荡在广场上。他接着说道:
“周年纪念?不,不,不是我们的周年纪念。可是我正在酝酿的这件事,也差不离。因为我要做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我要给她唱小夜曲。地地道道威尼斯式的。这就需要你的帮助。你弹吉他,我唱歌。我们租条刚朵拉,划到她的窗户下,我在底下唱给她听。我们在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卧室的窗户就临着运河。天黑以后就万事俱备了,有墙上的灯把景物照亮。我和你乘着刚朵拉,她来到窗前。所有她喜欢的歌。我们用不着唱很久,夜里还是有点冷。三四首歌就好,这些就是我心里想的。我会给你优厚的报酬。你觉得呢?”
“加德纳先生,我荣幸至极。正如我对您说的,您是我心中的一个大人物。您想什么时候进行呢?”
“如果不下雨,就今晚如何?八点半左右?我们晚饭吃得早,那会儿就已经回去了。我找个借口离开房间,来找你。我安排好刚朵拉,我们沿着运河划回来,停在窗户下。不会有问题的。你觉得呢?”
你或许可以想象: 这就像美梦成真一样。而且这主意多甜蜜啊,这对夫妇——一个六十几岁,一个五十几岁——还像热恋中的年轻人似的。这甜蜜的想法差点儿让我忘了刚才所见的那一幕。可我没忘,因为即便在那时,我心里深知事情一定不完全像加德纳先生说的那样。
接下来我和加德纳先生坐在那里讨论所有的细节——他想唱哪些歌,要什么音高,等等之类。后来时间到了,我该回帐篷去进行下一场演出了。我站起来,和他握了握手,告诉他今天晚上他完全可以信任我。
*
那天晚上我去见加德纳先生时,漆黑的街道十分安静。那个时候,一到离圣马可广场较远的地方我就会迷路,所以尽管我早早出发,尽管我知道加德纳先生告诉我的那座小桥,我还是晚了几分钟。
加德纳先生站在路灯底下,穿着一件皱皱的深色西装,衬衫敞到第三四个扣子处,所以能看见胸口的毛。我为迟到的事向他道歉,他说道:
“几分钟算什么?我和琳迪已经结婚二十七年了。几分钟算什么?”
他没有生气,但似乎心情沉重——一点儿也不浪漫。他身后的刚朵拉轻轻地在水里摇晃,我看见刚朵拉上的船夫是维托里奥,我很讨厌的一个人。他当着我的面总是一副友好的样子,可是我知道——我知道在我背后——他到处说些难听的话,说像我一样的人的闲话,他把我们这种人称为“新国家来的外地人”。所以那天晚上,当他像兄弟似的跟我打招呼时,我只是点点头,静静地看着他扶加德纳先生上船。然后我把我的吉他递给他——我带了一把西班牙吉他,而不是有椭圆形音孔的那把——自己上了船。
加德纳先生在船头不停变换着姿势,然后突然用力地坐下去,船差点翻了。可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开船了,他一直盯着水面。
我们静静地在水上漂着,经过黑色的建筑,穿过低矮的小桥。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加德纳先生从沉思中回过神来,说道:
“听着,朋友。我知道下午我们已经说好了今晚要唱哪几首歌。但是我在想,琳迪喜欢《当我到达凤凰城的时候》这首歌。我很久以前录的一首歌。”
“我知道,加德纳先生。以前我母亲总说你唱的版本比辛纳特拉② 均为二十世纪享有盛誉的美国流行歌手。的,或者那个家喻户晓的格伦·坎贝尔②版的都好听。”
加德纳先生点点头,接着有一小会儿我看不见他的脸。维托里奥吆喝了一声,船转弯了,吆喝声在墙壁间回响。
“以前我经常唱给她听,”加德纳先生说。“所以我想今晚她一定乐意听到这首歌。你记得调子吗?”
此时我已经把吉他拿出来了,我就弹了几小节。
“高一点,”他说。“升到降E调。我在唱片里就是这么唱的。”
于是我就用降E调弹了起来,弹了差不多整个主歌的部分以后,加德纳先生唱了起来,很轻很柔地,像是只记得一部分歌词。可是他的声音还是清晰地回响在安静的运河上。而且真是太好听了。一时间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那个公寓,躺在地毯上,而我母亲坐在沙发上,筋疲力尽,或者伤心无比地听着托尼·加德纳的唱片在房间的角落里旋转着。
加德纳先生突然停下来,说道:“很好。《凤凰城》我们就用降E调。然后是《我太易坠入爱河》,如我们计划的那样。zui后是《给我的宝贝》。这样就够了。她不会想听再多的了。”
说完,加德纳先生又陷入了沉思,我们在黑暗中慢慢地往前漂去,只听见维托里奥轻轻泼溅起的水声。
“加德纳先生,”我终于忍不住问道,“希望您别介意我这么问,可是加德纳太太知道今晚的表演吗?还是说这会是个惊喜?”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我想应该是属于惊喜这一类的。”他停了一下,又说道,“天晓得她会有什么反应。兴许我们唱不到《给我的宝贝》。”
维托里奥又转了一个弯,突然传来了音乐声和笑声,我们正漂过一家灯火通明的大餐厅。好像客满了,侍者忙碌地穿梭其间,食客们都很开心的样子,尽管那时运河边上还不是非常暖和。我们刚刚一直在宁静和黑暗中行驶,现在看见餐厅显得有些纷乱。感觉好像我们是静止不动的,站在码头上,看着这只闪闪发光的开着派对的船驶过。我注意到有几张脸朝我们这里看了看,可是没有人太在意我们。把餐厅甩在身后以后,我说道:
“真有意思。要是那些游客发现一条载着著名的托尼·加德纳的船刚刚开了过去,不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维托里奥英语懂的不多,但是他听懂了这句话的大意,笑了一下。而加德纳先生却没有反应。直到我们又驶入黑暗,驶进一条狭窄的河道,驶过沿岸灯光昏暗的门口时,他才说道:
“我的朋友,你是从波兰来的,所以你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加德纳先生,”我说,“我的祖国现在是自由的民族了。”
“抱歉。我没有侮辱你们国家的意思。你们是勇敢的民族。我希望你们赢得和平和繁荣。可是朋友,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想说的是从你来的地方,自然还有很多东西是你不明白的。正如在你们国家也有很多事情我不会明白。”
“我想是这样的,加德纳先生。”
“我们刚刚经过的那些人。要是你过去问他们:‘嘿,你们还有人记得托尼·加德纳吗?’也许当中一些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会说记得。谁知道呢?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子经过,就算他们认出了我,他们会兴奋不已吗?我想不会。他们不会放下他们的叉子,不会停下他们的烛光晚餐。为什么要呢?只不过是一个已经过时了的歌手。”
“我不相信,加德纳先生。您是经典。就像辛纳特拉或者迪安·马丁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歌手、演员。一样。一些一流的大师是不会过时的。不像那些流行歌星。”
“谢谢你这么说,朋友。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唯独今晚,不要开我的玩笑。”
我正想反驳,但加德纳先生举止里的某些东西让我放开了这个话题。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没有人说话。说实话,我开始纳闷自己是不是搅和进了一件什么事,这整个小夜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毕竟是美国人啊。说不定当加德纳先生开始唱时,加德纳太太会拿着枪走到窗前,朝我们开火。
也许维托里奥跟我想到了一块儿,因为当我们驶过一面墙上的路灯下时,他朝我递了个眼色,像是在说:“他真是个怪人,不是吗,朋友?”可是我没有理他。我不会跟他那种人一起反对加德纳先生的。在维托里奥看来,像我这种外地人,成天敲诈游客,弄脏河水,总之就是破坏了这座该死的城市。哪天遇上他心情不好,他会说我们是强盗——甚至是强奸犯。有一次,我当面问他是不是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他赌誓说全是一派胡言。他有一个他敬如母亲的阿姨是犹太人,他怎么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呢?可是一天下午幕间休息的时候,我靠在多尔索杜罗的一座桥上打发时间,一条刚朵拉从桥下经过。船上有三名游客,维托里奥摇着桨站在他们身后,高谈阔论,讲的正是这些垃圾。所以他尽可以看着我,但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伙伴情谊。
“我来教你一个秘诀,”加德纳先生突然说道。“一个表演的小秘诀。给同行的你。很简单。你要多少了解你的观众,不管是哪个方面,你得知道一点儿。一件让你心里觉得今晚的观众跟昨晚的不同的事。比如说你在密尔沃基演出。你就得问问自己,有什么不同,密尔沃基的观众有何特别之处?他们跟麦迪逊的观众有何不同?想不出来也要一直想,直到想到为止。密尔沃基,密尔沃基。密尔沃基有上好的猪排。这就行了,当你走上台时心里就想着这个。不用说出来让观众知道,你唱歌的时候心里知道就行。你面前的这些人吃上好的猪排。他们对猪排非常讲究。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观众就成了你知道的人了,成了你可以为之演出的人。这就是我的秘诀。给同行的你。”
“谢谢,加德纳先生。我以前从没这样想过。像您这样的人的指点,我永生难忘。”
“那么今晚,”他接着说,“我们是为琳迪表演。琳迪是我们的观众。所以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琳迪的事情。你想听吗?”
“当然,加德纳先生,”我说。“我很想听听她的事情。”
*
接下来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坐在刚朵拉里,顺着水流漂,听加德纳先生讲。他的声音时而低得近乎耳语,像是在自言自语。而当路灯或者沿途窗户的灯光照到船上时,他就会突然想起我,提高音量,然后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朋友?”之类的。
他说,他妻子来自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中学时,学校的老师让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因为她老看电影明星的杂志,不学习。
“老师们不知道琳迪有远大的计划。看看现在的她。富有、美丽、周游世界。而那些学校里的老师呢,他们如今有什么成就?过得怎么样呢?他们要是多看些电影杂志,多些梦想,也许也能够拥有一些琳迪今日的成就。”
十九岁时,她搭便车到了加州,想进好莱坞,却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家路边餐厅当起了服务生。
“意想不到啊,”加德纳先生说。“这家餐厅,这个高速公路旁不起眼的小地方,却成了她zui好的去处。因为这里是所有野心勃勃的姑娘来的地方,从早到晚。她们在这里见面,七个、八个、十来个。她们吃啊喝啊,坐在那里聊上好几个钟头。”
这些姑娘都比琳迪大一些,来自美国的四面八方,在洛杉矶待了至少两三年了。她们聚在餐厅里聊八卦,聊倒霉事,讨论计策,汇报大家的进展。可是这里zui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叫梅格的女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招待。
“梅格是这群姑娘的大姐头,智囊袋。因为以前她就和她们一样。你得明白,她们是一群正经的姑娘,野心勃勃、意志坚定的姑娘。她们是不是和其他女孩子一样谈论衣服、鞋子、化妆品?是,她们也谈这些。但是她们只关心哪些衣服、鞋子、化妆品能帮助她们嫁给明星。她们谈不谈论电影?她们谈不谈论歌坛?当然了。但是她们谈的是哪个电影明星或者歌星还是单身,哪个婚姻不幸,哪个离了婚。而所有这些,梅格都能告诉她们,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东西。梅格走过她们要走的路。她知道钓到大腕的所有规矩和门道。琳迪和她们坐在一起,一字不落地听着。这家小小的热狗店就是她的哈佛、她的耶鲁。明尼苏达来的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现在想想她可能会变成什么样,都让我哆嗦。可是她是走运的。”
“加德纳先生,”我说道,“请原谅我打断您。可要是这个梅格这么神通广大,她干吗不自己嫁个明星?她干吗还在餐厅里端盘子?”
“问得好,可你不太明白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位女士,梅格,她自己没有成功。可是重点是,她看过别人是怎么成功的。你明白吗,朋友?她曾经和这些姑娘一样,她目睹谁成功了,谁失败了。她见过圈套陷阱,也见过阳关大道。她把所有的故事都讲给她们听,而其中一些人学进去了。琳迪就是其中一个。就像我说的,这里是她的哈佛。这里成就了后来的她。这里给了她日后需要的力量,天啊,她确实需要。她等了六年才交了diyi次好运。你想象得到吗?六年的处心积虑,六年的如履薄冰。一次次地遇到挫折。可是就跟我们的事业一样。你不能因为zui初的一些小挫折就打退堂鼓。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的姑娘随处可见,在默默无闻的地方嫁给默默无闻的人。而有一些人,有一些像琳迪这样的人,她们从每一次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变得越来越坚强,她们屡败屡战,却越战越勇。你以为琳迪没有蒙过羞?像她这么漂亮,这么有魅力的人?人们不明白美丽不是zui主要的,一半都不到。用得不对,人们就视你为娼妇。总之,六年之后,琳迪终于有了好运。”
“她遇到您了是吗,加德纳先生?”
“我?不,不是。我没有这么快出现。她嫁给了迪诺·哈特曼。没听说过迪诺?”说到这里加德纳先生微微冷笑了一下。“可怜的迪诺。我想他的唱片没有流传到共产主义国家去。不过那时他很有些名气。当时他频频在维加斯演出,出了几张金唱片。我刚才说了,琳迪交了好运。我初次见到琳迪时,她是迪诺的妻子。这种情况老梅格早跟她们解释过了。诚然有的姑娘能diyi次就撞了大运,一步登天,钓上辛纳特拉或者白兰度这样的人。可是这种事情并不多见。姑娘们得准备好在二楼就出电梯,走出来。她得习惯二楼的空气。也许将来有一天,她会在二楼这里遇见一个从顶楼公寓下来的人,也许是下来取一下东西。这人对她说,嘿,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一起上顶楼去。琳迪清楚游戏规则。她的战斗力没有因为嫁给了迪诺而减退,她的雄心也没有因此而大打折扣。迪诺是个正派人。我一直都喜欢他。所以虽然我diyi次见到琳迪就深深地爱上了她,但我没有采取行动。我是个绝对的绅士。后来我得知琳迪因此而更加下定决心。啊,你应该钦佩这样的姑娘!我得告诉你,朋友,我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红。我猜你母亲就是在那个时期听我的歌的。然而迪诺却开始迅速走下坡路。那段时期很多歌手的日子都不好过。时代变了。孩子们都听披头士、滚石。可怜的迪诺,他的歌太像平·克劳斯贝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歌手、演员。了。他尝试做了一张巴萨诺瓦一种融合巴西桑巴节奏与美国酷派爵士乐的新派音乐,被视为拉丁爵士乐的一种。的唱片,却被大家耻笑。这时琳迪肯定不能再跟着他了。当时的情况没有人能指责我们。我想就是迪诺也没有真的责怪我们。所以我行动了。她就这样到了顶楼公寓。
“我们在维加斯结了婚,我们把酒店的浴缸装满香槟。今晚我们要唱的那首《我太易坠入爱河》,知道我为什么选这首歌吗?想知道吗?新婚后不久,有一次我们在伦敦。吃完早饭以后我们回到客房,女佣正在打扫我们的套房。可是我们欲火烧身。于是我们进了房间,我们可以听见女佣在用吸尘器打扫客厅的声音,可是我们看不见她,隔着隔板墙。我们踮着脚尖偷偷地溜进去,像孩子似的,你瞧。我们悄悄地溜回卧室,把门关上。我们看得出卧室已经打扫完了,所以女佣应该不用再回到卧室来了,但我们也不是很肯定。管他呢,我们才不在乎。我们脱掉衣服,在床上大干起来,女佣一直都在隔壁,在套房里走来走去,不晓得我们已经回来了。我说了,我们欲火烧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突然觉得整件事情太好玩了,我们开始笑个不停。后来我们完事了,躺在床上拥抱着对方,女佣还在外面,你知道吗,她居然唱起歌来了!她用完吸尘器,开始放声高歌,天啊,她的声音太难听了!我们笑个不停,当然是尽量不发出声音。你猜接下来怎么着,她不唱了,打开收音机。我们突然听见切特·贝克美国爵士乐号手、歌手。的声音,在唱《我太易坠入爱河》,优美、舒缓、柔和。我和琳迪躺在床上,听着切特的歌声。过了一会儿,我也唱了起来,很轻地,跟着收音机里的切特·贝克唱,琳迪偎依在我怀里。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今晚我选了这首歌。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想起这件事。天晓得。”
加德纳先生不说了,我看见他擦去眼泪。船又转了个弯,我发现我们第二次经过那家餐厅了。餐厅似乎比先前更加热闹,有个人,我知道他叫安德烈亚,正在角落里弹钢琴。
当我们再次驶入黑暗之中时,我说道:“加德纳先生,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我看得出眼下您和加德纳太太的关系不是很好。我想让您知道我是明白这些事的。以前我母亲经常悲伤,大概就和您现在一样。她以为这次她找到了一个好人,她高兴极了,告诉我这个人要做我的新爸爸了。头
用户评价
这套石黑一雄作品集,在我看来,是近十年文学界最重要的收藏之一。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处理“怀旧”主题时的独特视角。他笔下的怀旧,不是简单的对过去的赞美,而是一种带着宿命感的、对逝去美好事物无可挽回的哀悼。这种哀悼是如此的优雅和克制,以至于你阅读时几乎感受不到廉价的煽情,只有一种高贵的悲剧性。每看完一个故事,我都会在脑海中默默构建出那个时代的影像,那些穿着特定服饰、恪守特定礼仪的人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助与坚韧。装帧的质感也让人爱不释手,书脊的设计典雅大气,放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提升整个房间的格调。这套书带来的,是一种“精神食粮”的极大满足,它不是提供逃避现实的途径,而是提供了一个更深邃的、更诚实的维度去重新审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甚至会刻意放慢速度,试图让这些精妙的句子在脑中多停留一会儿,生怕太快地读完就辜负了作者的心血。
评分说实话,刚开始接触石黑一雄的作品时,我有点不太适应他那种冷峻的叙事腔调。那种不紧不慢,甚至有些疏离感的讲述方式,差点让我中途放弃。但坚持下来后,我才明白,这种“慢”正是他最厉害的武器。他不是在急着告诉你故事的结局,而是在精心编织一个陷阱,让你一步步沉浸其中,直到最后猛然发现,原来自己早就被他牵着鼻子走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构建的那种“半真半假”的现实感,你很难用“科幻”或“现实主义”来简单定义,它介于两者之间,充满了哲学思辨的味道。阅读的时候,我经常会停下来,反思自己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理解。他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只是温柔地把这些问题抛给你,让你自己去消化、去承担。这种阅读体验,比那些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要来得更持久、更耐人寻味。这五本书,就像是五面不同的镜子,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和时代的变迁,值得反复翻阅,每次都会有新的感悟。
评分这套全集带来的,是一种知识分子式的阅读满足感。石黑一雄的文字功力,在我看来,已经臻于化境了。他用最朴素的词汇,构建出最宏大、最微妙的情感景观。特别是在处理那种“未尽之言”和“心照不宣”的场景时,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示范。那些人物之间微妙的眼神交汇、欲言又止的停顿,比任何直白的表白都更有力量。读他的书,仿佛你必须调动自己所有的感官和想象力,去填补那些看似空缺的地方。这不仅仅是阅读,更像是一场需要高度参与感的智力游戏。我特别欣赏他那种对社会阶层和集体无意识的犀利观察,尤其是在处理那些历史遗留问题时,他总是能找到一个独特的、不落俗套的切入点,既保持了文学的温度,又避免了说教的沉闷。对于追求精神深度和文学性的读者来说,这套书绝对是案头的必备良品,那种对文字精致打磨的痕迹,随便翻开一页就能感受到。
评分终于把这套厚厚的书读完了,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又迷人的旅行。石黑一雄的文字,总是带着一种特有的、挥之不去的忧郁和克制,像是在一层薄薄的雾气后观察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他笔下的人物,很少有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更多的是内心的挣扎与沉淀。我特别喜欢他在叙事中那种对“记忆”和“身份”的反复叩问,仿佛在提醒我们,我们所坚信的过往,究竟有多少是真实,又有多少是自我构建的慰藉。每一次翻页,都像是被拉入一个既熟悉又疏离的世界,那里有我们都曾有过的遗憾,但表达方式却新奇得让人拍案叫绝。这本书的装帧设计也十分典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感,让人觉得这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虽然阅读过程偶尔需要放慢脚步,去细细品味那些看似平淡却蕴含深意的对话,但最终收获的,是那种被深刻触动后,久久不能平息的共鸣感。这套书放在书架上,本身就是一种气质的体现,低调,但内涵丰富。
评分坦率地说,这套书的阅读门槛稍微高了一点,不是那种可以一口气读完的“爽文”。它更像是一杯需要慢慢品鉴的陈年威士忌,初尝可能觉得辛辣,但回味却悠长。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他那种近乎冥想般的叙事节奏。其中有几篇作品的氛围非常压抑,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读完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从情绪中抽离出来。但正是这种挑战性,让阅读过程充满了意义。它强迫你去面对那些我们通常在日常生活中会刻意回避的痛苦真相——比如生命的短暂、爱意的错失、以及我们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而不得不做出的那些“美丽”的谎言。这套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获得信息或消磨时间,它更像是一次深层次的自我对话。我个人认为,它对提升一个人的共情能力和对生活复杂性的理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强烈推荐给那些不满足于表面故事,渴望挖掘人性幽微之处的读者。
评分质量不错,正在看
评分很好,准备开始看书了
评分质量很好
评分送货速度快,书的质量不错,相信京东!
评分经典
评分物流很快很给力,以为会等一段时间,点个赞!
评分收到了
评分慢。
评分第一次读石黑一雄的作品,希望有所收获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