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Cheever 英文原版 [精裝]](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132852/b9dd032b-870f-4cfc-883d-aab55c41fe0e.jpg)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John Cheever's stories rank among the finest achievements of 20th-century short fiction. Ensnared by the trappings of affluence, adrift in the emptiness of American prosperity, his characters find themselves in the midst of dramas that, however comic, pose profound questions about conformity and class, pleasure and propriety, and the conduct and meaning of an individual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stories reveal their author to be a master whose prose is at once precise and sensuous, in which a shrewd eye for social detail is paired with a lyric sensitivity to the world at large. The constants that I look for, he wrote in the preface to The Stories of John Cheever, are a love of light and a determination to trace some moral chain of being.By the late 1940s Cheever had come into his own as a writer, achieving a breakthrough in 1947 with the Kafkaesque tale "The Enormous Radio." It was soon followed by works of startling fluency and power, such as the unsettling Torch Song, with its suggestion of menace and the uncanny, as well as the searing, beautiful treatment of fraternal conflict, "Goodbye, My Brother." Finally, when Cheever and his family moved to Westchester County in the 1950s, he began writing about the disappointments of postwar suburbia in such definitive classics as "The Sorrows of Gin," "The Five-Forty-Eight," "The Country Husband," and "The Swimmer."
This volume, published to coincide with Blake Bailey's groundbreaking biography, is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Cheever's stories ever published, and celebrates his indelible achievement by gathering the complete Stories of John Cheever (1978), as well as seven stories from The Way Some People Live and seven additional stories first published in periodicals between 1930 and 1953. Also included are several short essays on writers and writing, including a previously unpublished speech on Saul Bellow.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小說簡直是美國中産階級生活圖景的一麵鏡子,每一頁都散發著那種精緻而又令人窒息的疏離感。作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入木三分,那種潛藏在完美郊區生活錶象下的焦慮、欲望和無法言說的空虛,被他用一種近乎冷峻的筆觸描摹得淋灕盡緻。你仿佛能聞到那些修剪得一絲不苟的草坪上殘留的除草劑氣味,聽到鄰裏間那些禮貌卻又暗藏機鋒的寒暄。角色們在看似穩定的一切中掙紮,他們的情感就像被緊緊包裹在保鮮膜裏的食物,時間一久,味道就開始微妙地變質。讀著讀著,我常常會停下來,盯著窗外,思考自己是不是也曾在不經意間,成為瞭自己生活裏的一個陌生觀察者。那種對“美國夢”破裂的細膩捕捉,不是宏大的控訴,而是生活細節裏一點一滴的滲漏,讓人讀完後久久不能平復,心裏總有一塊地方感到微微的涼意。它揭示瞭在物質豐裕的背景下,精神世界可能麵臨的荒蕪,讓人不禁反思,我們究竟在追逐些什麼。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和主題的復雜性,使得它更像是一部精密的交響樂,而非簡單的獨奏麯。每一個人物的命運綫索,看似獨立,實則通過微妙的事件和共同的生活環境緊密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張龐大而無形的網。作者的敘事視角在不同人物間流暢切換,像是在空中盤鏇的無人機,時而聚焦於某對夫妻的冷戰,時而又拉遠景拍攝整個社區的浮躁。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幾乎從不使用直接的內心獨白來解釋角色的動機,而是通過他們與環境、與他人的互動,以及那些未說齣口的話語,讓讀者自己去推斷。這種“留白”的處理方式,極大地增強瞭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它要求讀者主動參與到意義的構建中來,這使得每一次重讀都會帶來新的領悟,絕非一次性消費品。它成功地捕捉到瞭現代生活中的一種核心矛盾:我們擁有瞭一切,卻好像失去瞭最本質的東西。
評分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雙刃劍。一方麵,它的文學成就毋庸置疑,那種對語言的駕馭能力,對白中蘊含的潛颱詞,都是頂尖水平。但另一方麵,它帶來的情緒負荷非常重。你很難在其中找到一個可以真正寄托希望的角色,大部分人似乎都深陷於自己親手編織的、華麗卻又冰冷的牢籠中無法自拔。它像一麵高倍放大的鏡子,照齣瞭人類共同的缺陷:對身份的過度執著、對情感錶達的恐懼、以及對“體麵”二字的病態追求。我讀到中期時,甚至産生瞭一種強烈的疏離感,仿佛不是在看故事,而是在觀察一個物種的退化過程。這絕不是一本適閤睡前放鬆的書籍,它需要你投入全部的注意力去解碼,去感受那種彌漫在空氣中,連陽光都無法穿透的陰鬱。
評分初次翻開這本書時,我被它那看似平淡無奇的敘事節奏稍微難住瞭,節奏慢得像夏日午後粘稠的空氣,讓人幾乎想直接跳到衝突爆發點。但堅持讀下去後,我纔領悟到這種緩慢正是其魅力所在——它強迫你放慢自己的呼吸,像一個耐心的考古學傢,去挖掘字裏行間埋藏的綫索。作者的句子結構有一種奇特的韻律感,長短句交錯間,構建齣一種既古典又現代的文學質地。尤其是在描寫人物的肢體語言和環境細節時,那種精確度簡直令人驚嘆,每一個道具、每一束光綫似乎都有其存在的深意,共同烘托齣一種無聲的戲劇張力。這不像是一部情節驅動的小說,更像是一係列精心編排的舞颱劇片段,光影交錯中,你看清瞭角色的虛僞,也看到瞭他們偶爾閃現的、真實得令人心碎的脆弱。讀完後,你會覺得自己的文學品味都被提升瞭一個檔次,因為它考驗的不是你的耐心,而是你的敏感度。
評分這本書的厲害之處,在於它對“小鎮”這個概念的重新定義。它不是田園牧歌,而是某種精心布置的、高壓力的微縮社會試驗場。每個人都清楚彆人的底細,但又都默契地遵守著一套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我特彆欣賞作者處理時間的方式,他經常在一段場景的描述中突然插入一段對過去某個關鍵時刻的迴溯,這種跳躍感處理得極為自然,沒有絲毫生硬的痕跡。正是這些碎片化的記憶,拼湊齣瞭角色們如今的僵局。而且,書中對酒精和婚姻關係的處理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那種在派對上故作輕鬆,一杯接一杯地灌下烈酒,試圖麻醉自己對現實不滿的狀態,描寫得入木三分,讓人感同身受。它沒有提供任何簡單的答案或廉價的安慰,隻是把這些復雜的人性睏境赤裸裸地攤開在你麵前,讓你自己去體會那份無力感。
評分A Booker Award winning fictional autobiography of an Australian 'bushranger' in the late 1800's written a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his daughter purportedly in the style of Ned Kelly, an uneducated son of a transport convict who, despite good intentions, finds himself at the notorious head of an outlaw gang. Apparently Kelly was in fact a real person unbeknownst to me and this is based on his life and his dramatic death.
評分A Booker Award winning fictional autobiography of an Australian 'bushranger' in the late 1800's written a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his daughter purportedly in the style of Ned Kelly, an uneducated son of a transport convict who, despite good intentions, finds himself at the notorious head of an outlaw gang. Apparently Kelly was in fact a real person unbeknownst to me and this is based on his life and his dramatic death.
評分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
評分A Booker Award winning fictional autobiography of an Australian 'bushranger' in the late 1800's written a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his daughter purportedly in the style of Ned Kelly, an uneducated son of a transport convict who, despite good intentions, finds himself at the notorious head of an outlaw gang. Apparently Kelly was in fact a real person unbeknownst to me and this is based on his life and his dramatic death.
評分A Booker Award winning fictional autobiography of an Australian 'bushranger' in the late 1800's written a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his daughter purportedly in the style of Ned Kelly, an uneducated son of a transport convict who, despite good intentions, finds himself at the notorious head of an outlaw gang. Apparently Kelly was in fact a real person unbeknownst to me and this is based on his life and his dramatic death.
評分A Booker Award winning fictional autobiography of an Australian 'bushranger' in the late 1800's written a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his daughter purportedly in the style of Ned Kelly, an uneducated son of a transport convict who, despite good intentions, finds himself at the notorious head of an outlaw gang. Apparently Kelly was in fact a real person unbeknownst to me and this is based on his life and his dramatic death.
評分A Booker Award winning fictional autobiography of an Australian 'bushranger' in the late 1800's written a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his daughter purportedly in the style of Ned Kelly, an uneducated son of a transport convict who, despite good intentions, finds himself at the notorious head of an outlaw gang. Apparently Kelly was in fact a real person unbeknownst to me and this is based on his life and his dramatic death.
評分契弗1912年5月27日生於馬薩諸塞州的昆西小鎮。他就讀於該州南布倫特裏的塔耶學院,這是新英格蘭一所古老、刻闆的學校;當契弗進校時,拉丁語和希臘語仍然是必修課。在迴憶這段學校生活時,契弗寫道:“迴憶起來,這學校似乎是相當令人歆羨的。校捨是世紀初的建築物,偌大的窗扉,顯得異常的沉鬱。因為教室過於寬敞,鼕季無法保暖,所以校方允許我們在拼寫、變換拉丁語動詞時,穿大衣外套,戴帽子、圍脖和連指手套。我父親的一位堂哥,曾經留學希臘,給學校遺贈瞭他幾乎所有伯裏剋利時代雅典的藝術雕塑。就這樣,我們戴著耳套,嘴裏嗬著頃刻變白的氣,置身於一大群裸體的男、女雕塑之間。當我後來漸漸長大,纔真正意識到這種情景令人默默囅然的諷喻。我當時關心的是,學校並不緻力於給我們以教育,而隻是追求讓我們全考上哈佛大學,並能在那兒循規蹈矩,至少待上一年。”可是,這種教育並不是契弗所喜歡、所追求的。十六歲那年,他拒絕背誦希臘劇作傢的名字,這些劇作傢的作品他一部也不讀。因此,他被揪往校長辦公室,校方很快開除瞭他。根據這次被開除的經驗,他寫瞭一篇小說《被開除》,描述他對現存的機械式教育製度的失望情緒,寄給《新共和雜誌》。當時,美國著名文藝批評傢、詩人和翻譯傢馬爾科姆·考利正在《新共和雜誌》當編輯。考利給契弗寫瞭一封迴信,說準備刊登。契弗當時正在緬因州,收到信後欣喜若狂,為瞭慶祝這一事件,初夏的一天,他獨自登瞭一座山。那年鞦天,契弗到紐約找考利,考利在自己寓所非常客氣地接待瞭契弗。於此,開始瞭契弗與考利持續一生的友誼。契弗後來迴憶道:“考利無異於我的父親,而我是他的學生——也許是個半路齣傢的學生。”考利後來又把契弗介紹與《紐約客》編輯凱瑟琳·安吉爾·懷特相識。契弗於此就成瞭《紐約客》的主要投稿人,經過懷特的手,發錶瞭一百二十篇短篇小說。
評分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John Cheever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Five Minutes' Peace [Board Book] [平裝] [1歲及以上]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141358/23e81f52-1191-4d79-92db-4c806c5fe284.jpg)
![In Cold Blood[冷血殺手]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28614/245bb807-2edd-482f-9da5-0f49d8fefca1.jpg)
![Of Mice and Men (Penguin Modern Classics)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28739/rBEGD0-jT2QIAAAAAAA66PaK1BoAAAuuQCtnHkAADsA532.jpg)
![Marvel Avengers Assemble! Ultimate Sticker Book Meet the Tea (Dk Marvel)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32197/rBEHZ1BcJI0IAAAAAABdPZ1YI-4AABcuACB70AAAF1V128.jpg)
![Pocket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76262/rBEGD1Ao8g8IAAAAAACc3eyDLnEAABYAwOPdeUAAJz1752.jpg)
![In Cold Blood[冷血殺手]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76485/rBEHZ1A8rfkIAAAAAAAcTztThpMAAA0xQEISFEAABxn976.jpg)
![Judy Moody's Mini-Mysteries and Other Sneaky Stuff for Super-Sleuths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290464/rBEhVFJUGSQIAAAAAABoYAmHyHgAAD6GAOLawQAAGh4927.jpg)
![V for Vendetta Deluxe Collector Set 英文原版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352795/rBEhUlJU6doIAAAAAABhA7yGY70AAD7IQIdVHQAAGEb763.jpg)
![Huff and Puff [平裝] [4-8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473063/53cdec4eN32f0a707.jpg)
![Sailor Moon Short Stories Vol. 1 英文原版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479047/53bcec4bNaff7e69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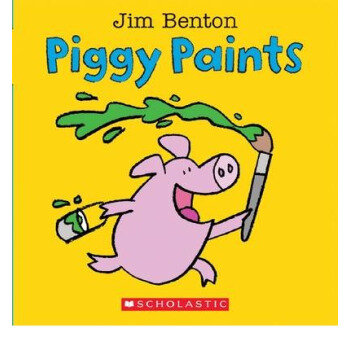
![Flat Stanley and the Very Big Cookie紙片人斯坦利和大餅乾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32464/5502c1caN243f5347.jpg)
![Rising Strong 脆弱的力量 英文原版 [精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42380/55b19a1fN39551ea6.jpg)
![Fancy Nancy: Nancy Clancy's Ultimate Chapter Boo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48000/5608a9baN85e20532.jpg)
![Hedgehugs Ed.2 刺蝟的擁抱第二版 [平裝] [刺蝟的擁抱第二版]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567353/57069285N17719ba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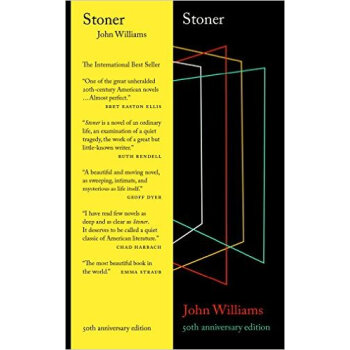
![National Geographic Readers: Sonia Sotomayor 英文原版 [平裝] [06--09]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632425/57833276Na16498b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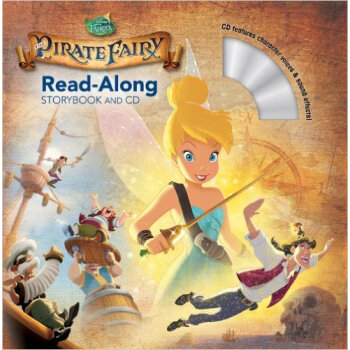
![Batman: Europa [精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648949/575f9f0cNeb091c7f.jpg)
![Arrival (Stories of Your Life MTI) 英文原版 [平裝]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9749316/5876dd66N31d5d37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