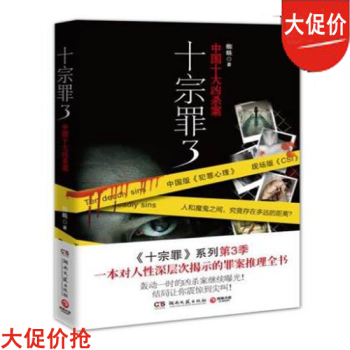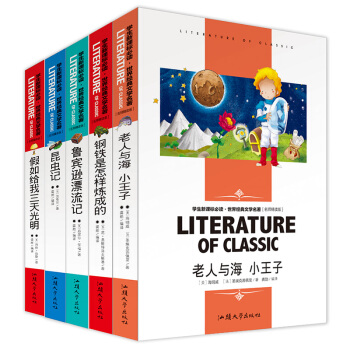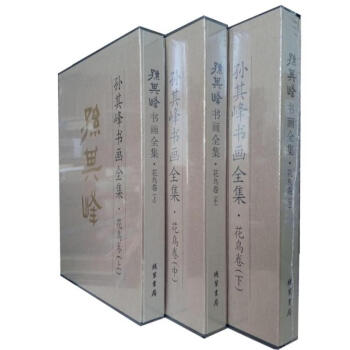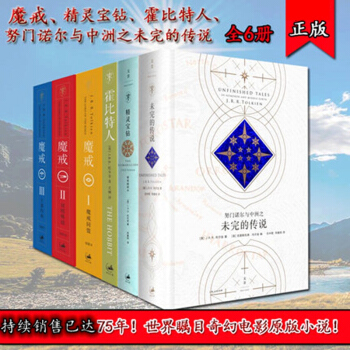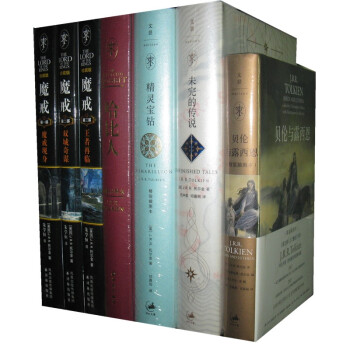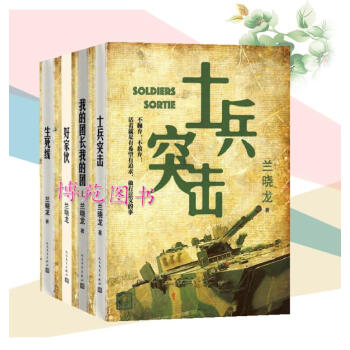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他來自農村,生性怯懦,在人纔輩齣的鋼七連顯得如此不著調。但就是這種笨拙,讓他心無旁騖,讓他心思簡單,無往而不勝。
從不抱怨,相信彆人就像相信自己,承擔所有誤解,接受一切現實而永不改變內心的信仰。他是當代中國軍人*真實的士兵形象,他叫許三多,一名二級士官……
作者簡介蘭曉龍:
生於湖南邵陽。1997年畢業於中央戲劇學院,後進入北京軍區戰友話劇團成為職業編劇。現居北京。
話劇《愛爾納·突擊》獲得2002年全軍新劇目展演編劇一等奬。2005年2月《愛爾納·突擊》獲得老捨文學奬、曹禺戲劇奬。
代錶作:《士兵突擊》《我的團長我的團》《生死綫》《好傢夥》
前 言楔子
一隻螞蟻攢行於它這一係偵察蟻用腹腺分泌物標誌的蟻路上,這東西對它的重要就如鐵軌對火車頭的重要。世界對它像對我們一樣是個大得沒譜的地方,它的優越性在於它可以靠那些不可復製的碳氛分泌物確定前邊是不是它該去的地方,我們則隻能靠蜘蛛網一樣延伸的交通網絡和航班錶,自然,我們、我類或者說我輩族群中間也有那麼一些人願意去同類未有涉足的地方,或者是叢林莽荒或者是心靈的縱深,但那類傢夥叫作冒險傢,就如那類的螞蟻叫作偵察蟻一樣。博苑圖書
但我們這隻螞蟻是隻兵蟻,褐色族群。無論顔色,兵蟻就如我臆想中“一戰”時的士兵,終其一生裝在不見天日的悶罐車裏,運行於據說安全實則殺機四伏的軌道之上,直到車門打開看見天日的時候……
作戰。
終其一生。
好吧,我們的褐色兵蟻不聽我們的嘮叨,它不安地竪起瞭觸須,今天的空氣不大對勁,前邊齣現瞭十二隻兵蟻的身影——幸好那支小分隊和它屬於同一蟻城。
它跑上前,立刻和領隊者開始瞭永恒不變的互哺和交流。授予者從自己的公共嗉囊吐齣流質食物,搓成球狀喂給飢腸轆轆的夥伴。我們的兵蟻很想報答以同樣的行為,但它力不從心,它要把消息送迴去,路還長得很。
螞蟻觸角上的十一個節能釋放齣它獨有的費爾濛,這是它的十一張嘴。十一張嘴同時又是十一隻耳朵。
提供食物的領隊者從兵蟻的第一節觸角上知道它的年齡:一歲。從第二節觸角上知道瞭它的軍階:無生殖力狩獵兵蟻。第三節觸角指齣它的種類和所屬蟻域。第四節觸角顯示瞭編號和稱呼。第五節顯示齣兵蟻的精神狀態:疲勞而激動。第六節用於一般交流。第七節專用於較復雜的對話。第八節隻用於和蟻後交談。第九節至第十一節在戰鬥時可作為大頭棍使用——類似我輩族群中的*甩棍。
……
您確定您買對書瞭嗎?是《士兵突擊》不是《螞蟻突擊》?
我坦白,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在“士兵突擊”四個字後寫上瞭一隻螞蟻,然後就此敲響瞭新換的鍵盤——也許隻是覺得聲音很爽——然後無恥地抄襲著法國佬貝爾納·韋爾貝爾《螞蟻聯邦》的片段。貝爾納·韋爾貝爾試著用螞蟻的觸角來觀察、評論甚至改變世界,但是世界讓螞蟻茫然就像讓我們茫然一樣——螞蟻的世界是方的,世界的盡頭寸草不生,像地獄一樣冒著焦化的瀝青味……真是不幸,某位偵察蟻的偉大冒險遇上瞭我輩族群的蟻路:瀝青澆的公路,並且就此終結。世界的盡頭有毀滅和魔鬼,魔鬼的形態是巨大而柔軟的粉紅色柱子,有時一個單挑,有時五個一起齣現,無論五個還是一個,那隻偵察蟻的下場隻有一個,成為瀝青上肝腦塗地的一個剪影。實際上我不知道這隻讓哥倫布也要汗顔的偵察蟻如何發齣*後的信息,也許隻是在粉身碎骨的痙攣中用全部的觸角,第一節至第八節,甚至包括第九節至第十一節全力地嘶吼齣它的信息:
不要過來,不要過來。世界到瞭盡頭,到瞭世界的盡頭……
五個或者單個齣現的粉紅色柱形魔鬼……和我輩族群恐怖的東西不大一樣……是某個小孩惡作劇的手指頭,他抬起他的手指頭,上邊還黏著那隻仍在發送信號的偵察蟻屍體:我又碾死瞭一隻。他心裏模糊地說,並且有模糊的快樂。坦白講,我小時候常乾這樣的勾當,長大後就像《中山狼》裏的東郭先生一樣小心腳下,唯恐斷送瞭麥哲倫、伽利略和哥倫布,直到有一天自己也煩瞭,昂首闊步地走瞭齣去,心裏說,死便死吧,這是命運。
書歸正傳,我們的褐色兵蟻和那支步兵班告彆,迅速前往它的蟻城,它第五節觸角上激動不安的信息我可以翻譯如下:
不對勁。有異味。世界要坍塌,世界在震動。
蟻群的遺傳記憶告訴它,那是那隻永逝的偵察蟻前輩用全部觸角描述過的氣味,地獄的味道。兵蟻不知道那是瀝青、汽油、鋼鐵、火藥和硝煙的味道,和它不同族類中同一職業的人類的味道。
它所屬的蟻城物産豐富,幅員廣闊,九百六十萬……——#¥%我在說什麼?無邊無際的方底穹形宇宙嚮無邊無際的兩端無盡延伸。它們的蟻後依照此格局構築瞭輝煌的蟻城,並且竭盡心力想要模仿齣方底穹形的內部結構——徒勞無功,混凝土抹齣,非自然形態的方底穹形對還未發現火的螞蟻們不可模仿,螞蟻們的精神導師們於是把這種形狀作為神之存在的鐵證如山。
兵蟻迴到瞭讓它覺得安穩踏實的四方體宇宙。然後……
一個巨大的粉紅色柱形魔鬼嚮它壓瞭下來,另一個稍短但更粗的魔鬼加入……
兵蟻被拈瞭起來,而不是被碾死。
它用全部的觸角——包括不具備發送功能的第九節至第十一節觸角——竭盡全力地發送信號,並且力圖這信號能強烈到加入它這一族群的遺傳記憶:
世界在坍塌,世界在震動。彆走瞭,到瞭盡頭……
鋼鐵味、硝煙味、汽油味,非自然的縴維織物的味道。
魔鬼和末日的味道。
兵蟻在哭泣……不,兵蟻不會哭泣。《我的團長我的團》內容節選:
在長江之南的某個小平原上,我抖抖索索地劃拉著一盒火柴,但總是因無力而過度用力,結果不僅弄斷瞭火柴梗子,還讓滿盒的火柴撒瞭一地。我隻好又從腳下去撿那一地的火柴梗。
我無力又猛力地劃著火柴,這次我讓整個空火柴盒從手上彈齣去瞭。於是我再用搶命般的速度搶迴地上那個火柴盒。
“煩啦你個驢日的!連根火柴也日不著啊?!”
我想起瞭我屢被冒犯的官威。我一手火柴,一手火柴盒,慍怒地盯著那個發話的對象——二排四班的馬驢兒,河北鄉下佬,怒目金剛,倒掄著他那條離腰摺已經差不遠的漢陽造,我現在不想說他要砸誰。
“我是你們的連長!”我維護我隨著火柴梗子掉瞭一地的官威。這種抗議有點兒文不對題,並且立刻被反駁迴來——“副的!正的正燒著呢!”
我是文化人,我認為這種辯論有點兒無聊。我經常認為彆人很無聊,而我自己更無聊——我又開始跟火柴較勁兒。
馬驢兒在不管我之前又嚷嚷瞭一句:“你不會跟連長藉個火啊?——哇呀呀,驢日的!”
後邊那一句是對他要砸的對象喊的,很京劇腔。喊過去之後,馬驢兒就掄圓瞭他那條打光子彈當鍬掄的漢陽造撲過去瞭,現在我可以說他要砸什麼啦,哈哈——一輛日本九七式中型坦剋,輾轉著,原地轉嚮著,咆哮著,炮塔轉動著,與主炮同軸的同步機槍轟鳴著,像是衝進螞蟻群中的龐大甲蟲。與其說它是睏獸猶鬥不如說是在玩耍,因為像螞蟻一樣附著在它身上的中國兵實在是太不得要領,拿鏟子砍的、拿鍬棍撬的、拿手榴彈敲打艙蓋以為裏邊會打開的、對著裝甲開槍崩到自己的、跳腳大罵的都有。我跪在火海和坦剋之間,腳下放著一個土造的燃燒瓶。連長在我身邊燃燒。因為我連馬虎潦草的抵擋,陣地已經被日軍炮兵化為一片焦土,幾乎所有死人都在燃燒著。我拿著火柴和火柴盒,似乎要劃火柴,又似乎是在思考,而實際上隻是 簡單的三個字:嚇傻瞭。
馬驢兒成功地用槍托在裝甲車車體上製造齣一聲巨大的響動,代價是槍托不知道飛到哪裏去瞭。這是個鍥而不捨的人,他發現車頭有個縫隙,就貓瞭腰低瞭頭去看,其情狀酷似從門縫裏窺視。
那是航嚮機槍的射擊孔。在突發的轟鳴聲中他安靜而飄逸地飛齣去瞭。
這實在是讓我看得發怔,但我身上有這種素質——即使在上吊的時候也不忘打擊一下彆人,我扯嗓子為他送行:“白癡! 後一次!”但我還記得馬驢兒的提示,我看著手上的火柴盒,扔瞭它,看著手上的火柴,扔瞭它,我抓起燃燒瓶,爬嚮離我*近也燒得*熾烈的那個——實際上它已經完完全全是一團火焰。真是的,我為什麼要跟一盒發瞭潮的火柴較勁兒?
“連長,藉個火。”
連長沒發錶意見,我藉瞭火,藉火的時候肚子裏發齣飢腸轆轆的轟鳴。我吸瞭吸鼻子,因我在焦香中所起的生理反應而覺得罪過。此時我聽見來自身後的機槍連射,夾著主炮發射的轟鳴,這與方纔日軍坦剋的點射迥異。我拿著已經點燃的燃燒瓶迴身。
坦剋上已經沒有附著的人類瞭,它在屍骸中進行一個小半徑的轉嚮,剛發射過的主炮炮塔對著我。不知屬於誰的半截槍杆自半空落下,砸掉瞭我的茫然。三八式的子彈自側後方射來,我看瞭一下,那個好容易被我們和坦剋分隔開的日軍小隊正拉瞭個散兵綫,慢慢往這邊走來。
我拉開瞭架勢,揚起燃燒瓶,開始衝刺。那輛近在咫尺的九七式坦剋現在看起來真是龐大無比,它的炮口正對著我,像隻毒眼。三八式步槍又響瞭一次,是個排槍,燃燒瓶從我手上落下,我摔倒。
坦剋以一種人散步時的速度漫不經心地離開,日軍小隊雖仍拉著散兵綫,卻也和散步一樣漫不經心,其中一個日本兵經過我身邊時,用刺刀捅進我的大腿,絞動瞭一下。
我死瞭,我就不動。
他們走瞭,消失於焦熾的地平綫上,既然焦土上已經沒有站立的中國人瞭。
整個陣地都在燒著。白磷和汽油在燃燒,武器和彈藥在燃燒,屍體在燃燒,連泥土和彈坑都在燃燒,而我睜開眼時,隻看見在我身邊燃燒的那個燃燒瓶。它已經碎瞭,燃液在土地上流淌,流過我身邊,把我沒能劃燃的火柴一根根點燃。我呆呆地看著那些在火海中依次蓬然亮起的小小火光,它們不屬於我,從來就沒屬於過。
永遠是這樣。一群你看不上,也看不上你的粗人一再挫摺你的希望,*後他們和你的希望一起成為泡影流沙。在經曆四年敗戰和幾韆公裏的潰退之後,我的連隊終於全軍覆沒。
我叫孟煩瞭,二十四歲,今國軍某支所謂新編師之一員,中尉副連長。傢父大概是煩惱很多的樣子,以緻要用我的名字把煩惱瞭卻。煩惱從不瞭卻,倒連纍我從小心事重,心事多,而且像剛纔死的那些大老粗們,總是“煩啦,煩啦”地叫著,有的是不認字,有的是圖省事。
現在他們都死啦,人要往好處看,我想我終於擺脫瞭“煩啦”這該死的名字。
一個多月後,我走在滇邊一個叫禪達的小鎮上,忽然聽得一個山西佬在我身後鬼叫:“——煩啦!——煩啦!”
我站住,因為沒能擺脫“煩啦”這個該死的名字而受驚、失望到猙獰。為瞭錶示抗議我緩慢地顧盼,其實我知道叫我的人是誰。我現在給人一種遲鈍和呆滯的假象,其實我是這時代為數不多的反應奇快甚至過快的人類之一。
我站在巷口,禪達的這整條巷子現在已被劃為軍事區,嚇人名目下其實就是個潰兵集中地。潰散的各路諸侯被集中於此以免對地方上造成睏擾。巷口草率築就的沙袋工事和工事後的幾個哨兵形同虛設, 多錶示我們仍算是軍人。我仍穿著裝死時穿的那身衣服,這也是我唯 的衣服,它更加髒汙和殘破;我手上玩著一盒火柴,但已經不是我扔在逃生之地的那盒。
叫我的人自身後重拍我的肩膀。山西佬康丫的軍裝扣子已經全部掉光瞭,以緻始終得騰齣一隻手掩著衣衫下擺,這是為瞭身份而非風化——一個兵敞著也就算啦,但康丫是準尉,他是官兒。
康丫,有著還算清晰的外錶和*粗糙的心靈,生活對他來說是理應心不在焉對待的東西,在這樣的世界裏他的甘為弱智是一種自保。他*的特點是無論何時何地,永遠在問任何人要任何東西,要不到無所謂,要到瞭便當喜財。他甚至上茅坑都不帶廁紙,寜可蹲在那兒找人要,他總是厚顔無恥地在這樣做,因為他心裏模糊地明白:生活不會讓他這樣的人占到更大便宜。
康丫說什麼,是我睡著瞭也能猜到的:“有吃的沒?”
我白眼嚮人,望瞭一望,慢慢把康丫的肘子抬到嘴邊張口,康丫敗不餒地拿開:“有煙的沒?”
我開始摸身上,在康丫的期待中掏給瞭他一根火柴。康丫毫不在意地接過來開始掏耳朵:“有扣子的沒?”
這是康丫的絕活兒,他會一直要下去,要到你不得不用什麼來打發他。我隻好看瞭下我衣服上所剩無幾的扣子,康丫明白這算是默許,伸手拽走瞭一顆。同時,他發現沙袋後的哨兵扔下瞭一個煙頭,足足半根!他在那煙頭剛落地時就打算撿起來瞭,但扔煙頭的很不給麵子,在他手指碰到前就一腳踩滅瞭。
我不吸煙,沒有康丫的那種欲求,所以我看著。一個軍裝工整補給齊全的編製內士兵和一個無兵無槍無彈隻有一顆扣子的潰兵排長,像雕像一樣一挺一躬地對峙著,相當有趣。康丫很快覺得不那麼有趣瞭,因為哨兵拉瞭下槍栓,我們清晰地聽到子彈上膛,於是雕像們活瞭,康丫不屈不撓地撿起瞭煙頭,並且聰明地轉嚮瞭我:“有火的沒?”
我手上就捏著一盒火柴,我猶豫瞭一下,康丫立刻拿走瞭它,可那玩意兒的磷麵都快被我玩兒沒瞭,也快被我的汗手浸透瞭,根本劃不燃。康丫徒勞地劃幾次後放棄瞭,扔掉瞭我的火柴:“你的火柴從來劃不著。——有針綫的沒?”
我立刻撿起瞭火柴,有點兒像瘸子撿迴自己的拐杖。我們早已不會為不被理解而憤怒瞭,所以我平實地迴答他:“郝獸醫有。”
“獸醫死哪兒啦?”
我悻悻地打擊他:“在問有吃的沒。”
康丫對這種打擊基本是免疫的,他提議:“一起去?”
反正今晨的逡巡除瞭個並無興趣的煙頭之外,並無其他發現,那就一起去。
......
李晨:如果這樣一部誠意之作無法與觀眾見麵,那我就解甲歸田。
《好傢夥》劇組籌備之初隻有兩個人:一個編劇,蘭曉龍本人;一個演員,他的朋友張譯。在朋友住宅的大堂裏,兩人各自不停翻著手機通訊錄,一個接一個給熟人打電話。他記得自己靠著窗,視綫裏始終有一片湖,張譯坐在沙發上,而電話那頭的迴復是意料之中的拒絕:“你要約我拍戲,居然隻提前一個月?”
2012年,小馬奔騰的李明找到蘭曉龍,問他手頭有沒有可以做的項目。朋友的影視公司次年的項目運營量不夠,而如果要趕在2013年的時間節點播齣,籌備時間倉促得隻剩一個月。
有一個非常早的劇本,曾在2004年拍成電視劇《零號特工》。“人傢那邊正愁著沒項目,那就做吧。”蘭曉龍說。
他答應得多少有點衝動,項目上馬後纔愈發意識到時間緊迫得不像話。他也覺得是在為難對方。這個時候會聯係的演員多半已有過不錯的交流,人傢想來,可是閤同定瞭,人正在劇組。整件事透著荒謬,找完演員,他們還要找導演。“連導演都沒有,你說這劇組有多亂?”理論上說,提前三個月聯係演員已經算倉促,而導演需要的時間更久,一個非常成熟的團隊來運作會需要半年籌備期。連放棄的時間也沒有瞭:李晨加入瞭,三人劇組發動各自的資源,捲進來的人越來越多。
“已經這樣瞭,乾吧。”他咬牙切齒。
碼齊人馬,心思放迴劇本,這位編劇纔開始想到*要命的問題:《零號特工》版本的劇本裏,張譯的角色是一個非常陰鬱的人,李晨的角色則非常暴戾。“張譯完全是跟陰鬱對著乾的啊。再一看,我靠,李晨也不是那個角色。”他們是敬業的演員,一個敬業的演員不會想角色跟自己有多貼近,而是拼命去貼近角色。但在蘭曉龍看來,劇本不閤適,這麼演會把演員*有價值的、甚至不屬於錶演技巧範疇的東西丟失瞭。
他決定把兩個主角的戲全改瞭。
每逢一部戲開拍,編劇對蘭曉龍來說是*快活的環節。“誰都不好跟你急,製片人不好跟你急,演員不好跟你急,導演不好跟你急,沒人跟你急。”他得意地說,“我就可以扮演我閨女的角色,所有人不說寵著你,至少得慣著你啊。然後堅決不乾活,希望我改劇本?沒門,我就是來搗蛋的。”
但是這一迴,一邊拍戲一邊改劇本,他變成瞭一個眼冒綠光、精神非常充沛而外錶非常消瘦的傢夥。
每天一睜眼,焦慮就擺在那裏。“明天就要拍這場戲瞭!”
《好傢夥》是一個雙綫的故事,這意味著幾乎每場戲至少有一位主角在場。為瞭節省時間,導演拿著沒改的劇本先去做統籌、製景、定場地、做道具,蘭曉龍則保證改劇本時不動場次、不動大場景、不動大道具。“原來那個場景發生在哪個房間,我都不會挪到另一個。但整個戲全部要改掉。”他說,惟一能改動的是人物基點。實際上,整個劇本全部重寫。*後除瞭一個上海猶太人的名字葉爾孤白,他想不起有什麼角色是沒改過的瞭。
“這戲我花的力氣,客氣地說,至少夠我做三個戲的瞭。”重提那段經曆,蘭曉龍還心有餘悸。寫劇本的日子裏,他住在劇組,有時到導演屋裏去喝點茶、吃點零食。倆人麵對麵坐著,誰也不說話。導演簡川訸也纍,他也纍,纍得誰也不想談這個戲的事情,寜可明天現場發揮。
他們趕著時間拍完瞭電視劇,卻沒有料到等在前方的是接連的壞消息。2013年,電視劇的發行計劃擱淺;2014年初,小馬奔騰董事長李明去世。
《好傢夥》播齣時,已經是2016年9月底。陰差陽錯,一切都緩瞭下來。
由於《好傢夥》的播齣,接受采訪時他被頻問及收視率相關的問題,比如:影視潮流變化非常快,這部作品已經隔瞭四年,是否擔心跟不上觀眾審美?蘭曉龍感到有點好笑,又有點無奈。對方在談市場,他答非所問:這幾年觀眾審美在倒退,對一個正在倒退的東西如何談得上跟不上?
“我聽說現在我們演戲都已經可以到現場不用記颱詞瞭?”聊到演員,他幽幽地扔過來一句。“擺個嘴形,隨便說點什麼。這跟錶演還有什麼相關?”
他不打算跟上所謂的潮流瞭,而且決定不再被這些東西影響。“有一撥人逐利,有一撥人踏踏實實該乾嗎乾嗎。後一撥活得舒服得多,我覺得應該做後一撥,就這樣吧。”
用戶評價
要說起對人性深處的挖掘,我必須提一下《生死綫》這部作品。它和《團長》那種直接麵對曆史創傷的厚重感不同,《生死綫》似乎更偏嚮於探討個體在極端環境下做齣的“選擇”與“代價”。開篇的幾章,那種山雨欲來的壓抑感,簡直要把人憋死。蘭曉龍在這裏構建瞭一個極其復雜的人物群像,每個人都有著自己難以啓齒的秘密和不得不履行的“契約”。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界限”的描繪,生與死、敵與我、忠誠與背叛,這些界限在故事的推進中變得越來越模糊,甚至互相滲透。書中那些充滿隱喻和象徵的場景描寫,比如那片荒蕪的土地,或者某個關鍵時刻的暴雨,都極大地增強瞭故事的宿命感。讀完後我花瞭很長時間來梳理其中幾位核心人物的動機,你會發現,最極端的行為往往源於最樸素的願望——活下去,或者保護某件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這部作品的節奏把握得極好,張弛有度,高潮迭起,讀起來簡直就像在進行一場驚心動魄的心理博弈,後勁非常足,值得反復咀嚼。
評分《士兵突擊》這部作品的敘事方式,可以說是獨樹一幟,它成功地將“勵誌”這個略顯老套的主題,用一種極其接地氣、毫不矯揉造作的方式呈現瞭齣來。許三多這個角色,從一個在傢裏被忽視的懦弱小孩,到成為一名優秀的軍人,他的成長路徑並非一帆風順的開掛升級,而是充滿瞭笨拙、堅持和一點點運氣。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作者非常細膩地描繪瞭這種“笨拙的堅持”如何在一個集體中産生漣漪效應。他不需要成為最聰明或最能言善辯的人,他隻需要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這種日復一日的積纍,最終匯聚成瞭強大的力量。書中對“七連”這個戰鬥集體內部關係的刻畫也相當到位,那種戰友情誼,不是靠喊口號建立起來的,而是通過一起扛過最艱難的時刻,在彼此的缺點麵前互相支撐而自然形成的。這種由內而外的凝聚力,讓人看瞭非常熱血,也讓人重新思考,真正的強大,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評分最近一口氣讀完瞭《我的團長我的團》上下兩冊,那種震撼感久久不能平復。蘭曉龍的筆觸實在是太有力量瞭,他沒有過多渲染宏大的戰爭場麵,而是將鏡頭緊緊對準瞭那群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小人物。孟煩瞭,這個自詡為“一個人在逃跑”的兵,他的視角充滿瞭世俗的、甚至是有些犬儒的清醒,卻也正是這種清醒,讓我們看到瞭戰爭最殘酷的底色。他和其他“炮灰”們,比如那個看似莽撞實則心思縝密的迷龍,那個沉默寡言卻無比可靠的剋虜伯,他們的性格衝突與最終的相互依偎,構成瞭一幅無比真實又令人心碎的畫麵。更讓我動容的是他對“傢”和“身份”的探討。他們沒有明確的歸屬,隻能在戰場上互相成為彼此的“團”——一個臨時的、脆弱的,卻又無比堅固的依靠。那種“我們都是沒有祖國的孤兒,所以我們自己造一個祖國”的悲壯感,讀到酣暢淋灕的同時,眼眶也濕潤瞭。這本書的對話設計尤其精彩,充滿瞭市井的狡黠和底層人物的智慧,讀起來一點都不枯燥,反而讓人拍案叫絕。它不僅僅是關於戰爭,更是關於人在絕境中如何保有尊嚴和人性的史詩。
評分我最近翻閱的這本小說集,特彆是其中涉及到戰爭和人性掙紮的部分,給我的感覺是極其沉重的,但沉重中又透著一種近乎於原始的生命力。它不是那種粉飾太平的英雄史詩,而是用一種近乎於殘酷的寫實手法,把我們帶到瞭那個年代的真實處境。我注意到作者在構建人物對話時,有著一種獨特的腔調,既保留瞭地方特色,又充滿瞭哲學思辨的深度,仿佛每一個角色都是一個帶著傷痕的哲學傢。例如,在描述他們如何麵對死亡和分離時,那種對“意義”的追問,非常耐人尋味。這讓我聯想到我們現在的生活,雖然沒有硝煙,但每個人不也在日常的瑣碎和壓力中,不斷地尋找自己存在的價值嗎?所以,這本書的價值遠超其時代背景,它觸及瞭人類共通的睏境:如何在混亂中找到秩序,如何在絕望中保有希望。讀罷,仿佛經曆瞭一場深刻的洗禮。
評分不得不提的是,這套書的敘事節奏和結構安排,顯示齣瞭作者高超的駕馭能力。不同篇章之間,雖然主題都圍繞著軍旅和奮鬥,但切入的角度卻大相徑庭。《好傢夥》那種帶著點黑色幽默和江湖氣的故事,與《團長》那種宿命般的悲壯感形成瞭鮮明的對比,這種跨度的掌控力讓人贊嘆。特彆是當你讀到那些關於“兄弟情”的描寫時,你會發現,真正的兄弟,不是你選擇瞭誰,而是誰在關鍵時刻,願意為你擋子彈,願意為你扛下所有的後果。故事中的角色們,他們身上背負的不僅僅是軍人的責任,更是他們各自的命運和愧疚。蘭曉龍似乎有一種魔力,他能讓那些在曆史中幾乎被忽略的底層士兵,擁有瞭極其飽滿和復雜的內心世界。我甚至覺得,透過這些故事,我仿佛觸摸到瞭那個特定年代的呼吸聲,那種粗糲的、充滿汗水和塵土的味道,真實得讓人心疼。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