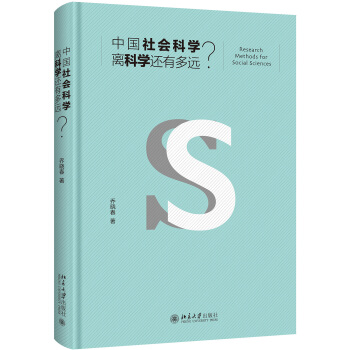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王叔岷的《校雠学》一书,广为中外学者引用。此补订本是在此基础上,将可以修订的问题及条例进行补充,例证太多的则进行删减。因此,《校雠学 校雠别录》更为严谨与充实。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整体架构和论证过程,展现了一种罕见的宏大视野和精微分析相结合的特点。作者似乎从一个非常高远的维度审视了所探讨的主题,然后逐步深入到最细微的结构和案例分析中去。每一次论点的展开,都建立在扎实的前期铺垫之上,使得后续的推导显得水到渠成,无可辩驳。我注意到,作者在处理历史脉络和理论发展时,总能清晰地勾勒出不同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了传统研究中常见的片段化和孤立化倾向。这种结构上的严密性,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强烈的“全景图”的把握感,不会感到迷失在细节的泥淖中。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揭开了一层新的帷幕,看到更广阔的图景,这种逻辑上的层层递进和结构上的完美闭环,是极其难得的。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深切感受是其蕴含的批判性思维的光芒。作者并非简单地复述已有的观点或知识,而是在不断地提问、质疑和挑战既有的范式。尤其是在对一些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理论进行审视时,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提出的反思角度往往直击要害,发人深省。这种思想的锋芒,让人在阅读时时刻保持一种警觉和活跃的状态,不断地在脑中进行着与作者观点的对话与碰撞。它不是一本提供标准答案的教科书,而更像是一面映照我们认知局限的镜子。很多我过去习以为常的看法,在这本书的冲击下,不得不被重新审视和解构,这种思想上的“震荡”与重塑,才是阅读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评分我对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行文节奏感到非常惊喜,它巧妙地在学术深度与通俗易懂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遣词造句既准确又富有韵味,即便是在论述一些复杂的问题时,也能用生动的比喻和清晰的结构将复杂的思想娓娓道来。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沉稳而又充满洞察力的笔触,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带领读者穿越迷雾,直抵核心。阅读过程中,我几乎能感受到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对所研究领域的热爱与执着。有些段落,读完后甚至会让人停下来,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哲理,那种知识的甘醇仿佛在舌尖久久不散。这种行文的流畅度和思想的穿透力,使得阅读过程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封面采用了一种典雅的深蓝色调,纹理细腻,仿佛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尘埃。书页的纸张质感也相当不错,厚实而不失韧性,油墨的印刷清晰锐利,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初次翻阅时,我注意到作者在章节编排上的用心良苦,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让人很容易跟随其思路深入探索。特别是一些关键概念的提出,作者似乎总能找到一个非常精妙的角度去阐述,既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文采,读起来丝毫没有那种枯燥乏味的学究气。装帧上的细节处理,比如书脊的烫金工艺,都体现了出版方对这部作品的重视,让人觉得手捧的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对于注重阅读体验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在物理层面的呈现,无疑是加分良多,极大地提升了阅读过程中的愉悦感和仪式感。
评分从内容广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涉猎范围之广令人称奇,它仿佛搭建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平台。作者在论证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融入了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乃至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使得单一主题的探讨拥有了丰富的维度和更深厚的土壤。这种跨领域的融会贯通,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让它能够吸引到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从中获得许多启发。例如,当讨论某一核心概念时,作者能够迅速地将其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对比分析,这种多维度的切入,让原本可能略显单薄的议题变得丰满立体起来。整体而言,这本书在知识的广度、深度的结合上,以及思想的穿透力上,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是一部让人受益匪浅的佳作。
评分好书,品相好,内容更佳。期待更多好活动!
评分王叔岷 这本书不错,值得拥有值得一看值得入手!
评分好书,品相好,内容更佳。期待更多好活动!
评分挺好的书,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
评分挺不错的书,质量和配送都好
评分此书为“王叔岷著作集”之一种,将王叔岷的《校雠学(补订本)》与《校雠别录》两书合为一册。 王叔岷的《校雠学》一书,广为中外学者引用。此补订本,是在此基础上,将可以修订的问题及条例进行补充,例证太多的则进行删减。因此,更为严谨与充实。 《校雠别录》为王叔岷在数十年进行庄子、史记、刘子等古籍的校证过程中,清理出的有关校雠的心得之作八篇的合集。 校雠形成理论,作为一项独立的学问,始于西汉。根据《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风俗通义》:“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由此可见,“雠”是核对之意。梁代以后校雠亦称“校勘”,指同一本书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校正讹误。 此外,校雠学亦包含编制目录之意,章学诚《校雠通义·叙》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记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一十焉。”这就明确指出校雠学作为一门学问,和狭义的目录学不同,其任务不仅是要甲乙丙丁地排列书的目录,更重要的是“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1] 由此,编者认为可以这样说:从范围角度而言,校雠大于校勘,校勘大于校对。 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说的校雠,包括校勘和校对两者;有时也单指古籍整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校勘,或者单指新著(包括原创初版本和新的古籍整理本)复制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校对。这在具体语境中是不难区分的。 概括地说,因为校勘与校对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性和共同点,而且校勘在中国出版史中的成就之大和经验之丰,又远非校对所能及。这就决定了中国校对的“细胞”中有着校勘大量的“遗传基因”。因此,在中国,一向是校对从校勘中继承了丰富的宝贵遗产。这正是本文较多地论及校勘的原因所在。 关于校勘与校对的关联性和共同点,从两千多年前刘向的校雠实践中就能够窥见端倪。刘向在《别录》中告诉我们:他整理好每一种古籍后,总要提出,“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杀青”的本义是烘干竹简,以便于书写,引申为定稿。“书可缮写”,就是可以依照 定稿缮写在帛素(丝织品)上,使之成书。在这两个过程中,都需要“比勘图文”,以纠正 讹误,也就是都需要校雠。后人通常称前者为校勘,后者为校对。由此可见两者的关联性和共同点。至于两者的不同点主要是:校勘所纠正的是祖本或底本中的讹误,包括原著作者有悖于客观事实、事理的讹误和以往的整理者、复制者有违于原著本意的讹误。清代校雠学者段玉裁称前者为“作者之是非”,称后者为“本子之是非”,后者实即原著本与复制本之间的“异同”(详见后)。而校对所纠正的,则侧重于当前的复制样本中有“异”于定稿的讹误。也可以说,校勘一般是校是非和校异同并重,而校对侧重于校异同。 汉文字校雠源远流长,承先启后,连绵不断。要追溯其源头,就必须与中国的文字史和文明史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中国的文字史和文明史的发生和发展是平行的和同步的,至今已有不下千年的历程。中国校事的源头、流向和传承,也大致与此相当。
评分确实经典。
评分校雠别录
评分体验入微,洞见迭出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写作指南(第2版) [Guidance to Professional Master′s Dissert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04494/54a12f07Nd072f394.jpg)
![初识传播学:在信息社会正确认知自我、他人及世界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20995/573a838bNb199483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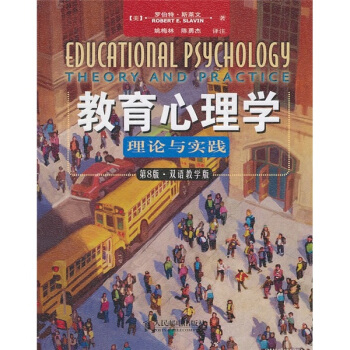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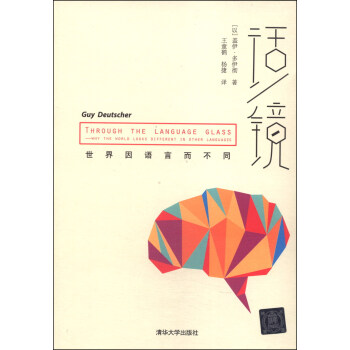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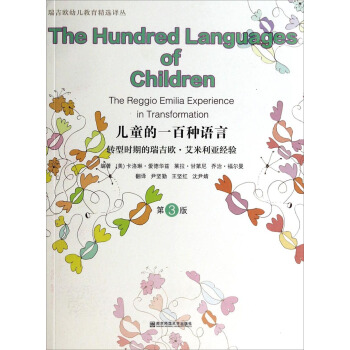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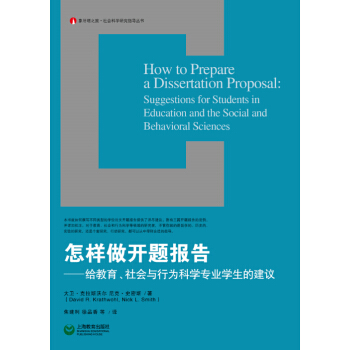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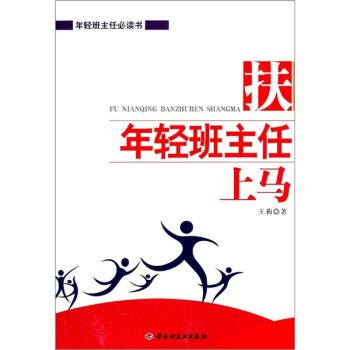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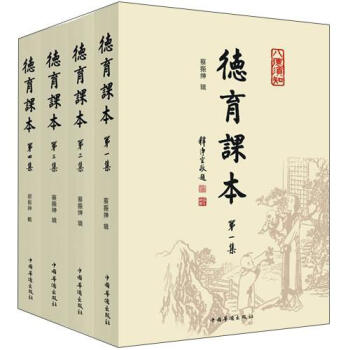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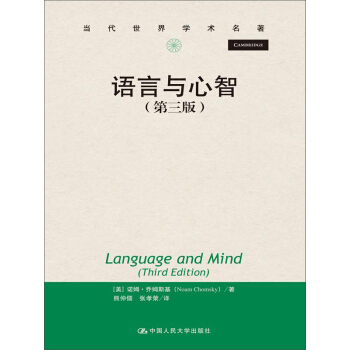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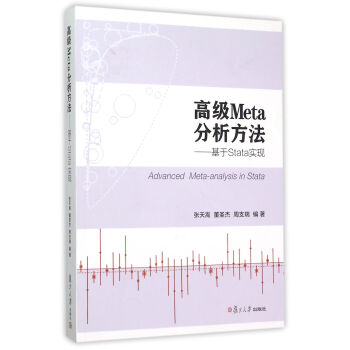
![哈佛医学生的历练 [White Coat: Becoming A Doctor At Harvard Medical 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08388/570d333bN124d7fa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