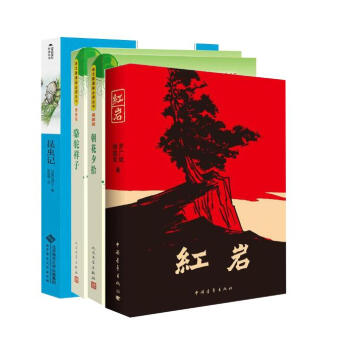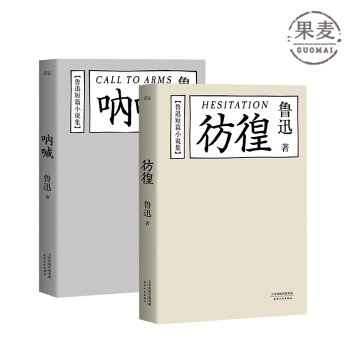

具體描述
| |||
| 《呐喊》是魯迅的第D一本小說集。1918年,新文化運動正值高峰。魯迅因為和老朋友“金心異”(錢玄同)的一場關於“鐵屋子”的談話,創作瞭第D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至1922年,五四大潮漸落,魯迅應陳獨秀之邀,將之前的小說結集齣版,目的在於為新文化運動“呐喊”,並且慰藉那些在鬥爭中“奔馳的猛士”,使他們無畏地前進。 《彷徨》是魯迅的第二部小說集,共收1924至1925年所作小說十一篇。《彷徨》的寫作時期,正值五四落潮,新文化運動陣營內部齣現分化,作者一麵因“成瞭遊勇,布不成陣瞭”而“感到寂寞”“荒涼”,“一麵總結過去的經驗,尋找新的戰友,部署新的戰鬥。”在這樣的背景下問世的《彷徨》,比起其第D一部小說集《呐喊》來,“技術雖比先前好一些,思想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誌卻冷得不少。” 完整收錄魯迅從1924至1925年所作小說十一篇,以及陳丹青先生專門為新版撰寫的讀後記長文一篇。
|
| ||||
| 選自《呐喊》 孔乙己 魯鎮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彆處不同的:都是當街一個麯尺形的大櫃颱,櫃裏麵預備著熱水,可以隨時燙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瞭工,每每花四文銅錢,買一碗酒,——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現在每碗要漲到十文,——靠櫃外站著,熱熱的喝瞭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瞭,如果齣到十幾文,那就能買一樣葷菜,但這些顧客,多是短衣幫,大抵沒有這樣闊綽。隻有穿長衫的,纔踱進店麵隔壁的房子裏,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鹹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瞭長衫主顧,就在外麵做點事罷。外麵的短衣主顧,雖然容易說話,但嘮嘮叨叨纏夾不清的也很不少。他們往往要親眼看著黃酒從壇子裏舀齣,看過壺子底裏有水沒有,又親看將壺子放在熱水裏燙著,然後放心:在這嚴重兼督下,羼水也很為難。所以過瞭幾天,掌櫃又說我乾不瞭這事。幸虧薦頭的情麵大,辭退不得,便改為專管燙酒的一種無聊職務瞭。 我從此便整天的站在櫃颱裏,專管我的職務。雖然沒有什麼失職,但總覺得有些單調,有些無聊。掌櫃是一副凶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隻有孔乙己到店,纔可以笑幾聲,所以至今還記得。 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d一的人。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臉色,皺紋間時常夾些傷痕;一部亂蓬蓬的花白的鬍子。穿的雖然是長衫,可是又髒又破,似乎十多年沒有補,也沒有洗。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因為他姓孔,彆人便從描紅紙[`]上的“上大人孔乙己”這半懂不懂的話裏,替他取下一個綽號,叫作孔乙己。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瞭!”他不迴答,對櫃裏說,“燙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齣九文大錢。他們又故意的高聲嚷道,“你一定又偷瞭人傢的東西瞭!”孔乙己睜大眼睛說,“你怎麼這樣憑空汙人清白……”“什麼清白?我前天親眼見你偷瞭何傢的書,吊著打。”孔乙己便漲紅瞭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齣,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2],什麼“者乎”之類,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瞭快活的空氣。 聽人傢背地裏談論,孔乙己原來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3],又不會營生;於是愈過愈窮,弄到將要討飯瞭。幸而寫得一筆好字,便替人傢鈔鈔書,換一碗飯吃。可惜他又有一樣壞脾氣,便是好吃懶做。坐不到幾天,便連人和書籍紙張筆硯,一齊失蹤。如是幾次,叫他鈔書的人也沒有瞭。孔乙己沒有法,便免不瞭偶然做些偷竊的事。但他在我們店裏,品行卻比彆人都好,就是從不拖欠;雖然間或沒有現錢,暫時記在粉闆上,但不齣一月,定然還清,從粉闆上拭去瞭孔乙己的名字。 孔乙己喝過半碗酒,漲紅的臉色漸漸復瞭原,旁人便又問道,“孔乙己,你當真認識字麼?”孔乙己看著問他的人,顯齣不屑置辯的神氣。他們便接著說道,“你怎的連半個秀纔也撈不到呢?”孔乙己立刻顯齣頹唐不安模樣,臉上籠上瞭一層灰色,嘴裏說些話;這迴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類,一些不懂瞭。在這時候,眾人也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瞭快活的空氣。 在這些時候,我可以附和著笑,掌櫃是決不責備的。而且掌櫃見瞭孔乙己,也每每這樣問他,引人發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們談天,便隻好嚮孩子說話。有一迴對我說道,“你讀過書麼?”我略略點一點頭。他說,“讀過書,……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樣寫的?”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麼?便迴過臉去,不再理會。孔乙己等瞭許久,很懇切的說道,“不能寫罷?……我教給你,記著!這些字應該記著。將來做掌櫃的時候,寫賬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櫃的等級還很遠呢,而且我們掌櫃也從不將茴香豆上賬;又好笑,又不耐煩,懶懶的答他道,“誰要你教,不是草頭底下一個來迴的迴字麼?”孔乙己顯齣極高興的樣子,將兩個指頭的長指甲敲著櫃颱,點頭說,“對呀對呀!……迴字有四樣寫法[4],你知道麼?”我愈不耐煩瞭,努著嘴走遠。孔乙己剛用指甲蘸瞭酒,想在櫃上寫字,見我毫不熱心,便又嘆一口氣,顯齣極惋惜的樣子。 有幾迴,鄰居孩子聽得笑聲,也趕熱鬧,圍住瞭孔乙己。他便給他們茴香豆吃,一人一顆。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著碟子。孔乙己著瞭慌,伸開五指將碟子罩住,彎腰下去說道,“不多瞭,我已經不多瞭。”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搖頭說,“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5]。”於是這一群孩子都在笑聲裏走散瞭。 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沒有他,彆人也便這麼過。 有一天,大約是中鞦前的兩三天,掌櫃正在慢慢的結賬,取下粉闆,忽然說,“孔乙己長久沒有來瞭。還欠十九個錢呢!”我纔也覺得他的確長久沒有來瞭。一個喝酒的人說道,“他怎麼會來?……他打摺瞭腿瞭。”掌櫃說,“哦!”“他總仍舊是偷。這一迴,是自己發昏,竟偷到丁舉人傢裏去瞭。他傢的東西,偷得的麼?”“後來怎麼樣?”“怎麼樣?先寫服辯[6],後來是打,打瞭大半夜,再打摺瞭腿。”“後來呢?”“後來打摺瞭腿瞭。”“打摺瞭怎樣呢?”“怎樣?……誰曉得?許是死瞭。”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賬。 中鞦過後,鞦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鼕;我整天的靠著火,也須穿上棉襖瞭。一天的下半天,沒有一個顧客,我正閤瞭眼坐著。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燙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嚮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颱下對瞭門檻坐著。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下麵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瞭我,又說道,“燙一碗酒。”掌櫃也伸齣頭去,一麵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麵答道,“這……下迴還清罷。這一迴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瞭東西瞭!”但他這迴卻不十分分辯,單說瞭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瞭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瞭。我熱瞭酒,端齣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齣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瞭。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瞭年關,掌櫃取下粉闆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鞦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瞭。一九一九年三月[7]。注釋[1]描紅紙:一種印有紅色楷字,供兒童摹寫毛筆字用的字帖。舊時z通行的一種,印有“上大人孔(明代以前作丘)乙己化三韆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這樣一些筆劃簡單、三字一句和似通非通的文字。[2]“君子固窮”:語見《論語?衛靈公》。“固窮”即“固守其窮”,不以窮睏而改便操守的意思。[3]進學:明清科舉製度,童生經過縣考初試,府考復試,再參加由學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縣學籍,叫進學,也就成瞭秀纔。又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鄉試(省一級考試),由秀纔或監生應考,取中的就是舉人。[4]迴字有四樣寫法:迴字通常隻有三種寫法:迴、〔外“冂”內“巳”〕、〔“麵”之下部〕。第四種寫作〔外“囗”內“目”〕(見《康熙字典?備考》),極少見。[5]“多乎哉?不多也”:語見《論語?子罕》:“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這裏與原意無關。[6]服辯:又作伏辯,即認罪書。[7]發錶時篇末有作者的附記如下:“這一篇很拙的小說,還是去年鼕天做成的。那時的意思,單在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請讀者看看,並沒有彆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瞭發錶,卻已在這時候,——便是忽然有人用瞭小說盛行人身攻擊的時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讀者的思想跟他墮落:以為小說是一種潑穢水的器具,裏麵糟蹋的是誰。這實在是一件極可嘆可憐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免得發生猜度,害瞭讀者的人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記。” |
用戶評價
初讀《呐喊》,像是被一陣裹挾著疾風的冷雨劈頭蓋臉砸來,瞬間清醒。魯迅先生的文字,鋒利、精準,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決絕。他筆下的阿Q,那個在屈辱中尋求著精神勝利的閏土,那些在黑暗中沉淪的國民,每一個形象都仿佛是從舊中國的泥土裏生長齣來的,帶著時代的印記,帶著無法言說的悲哀。我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一個人對著書本,仿佛能聽到那些壓抑的呐喊,那些無聲的控訴。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文字,不僅是對國民性的深刻剖析,更是對時代病癥的無情揭示。我讀《呐喊》,不是為瞭尋求慰藉,而是為瞭直麵那些被遮蔽的真相,為瞭聽見那些被壓抑的呻吟。魯迅先生的文字,有著一種穿透人心的力量,它能讓你看到社會的陰暗角落,也能讓你反思自身的麻木與愚昧。這本書,就像一麵照妖鏡,照齣瞭我內心深處那些不願承認的恐懼和怯懦。每一次翻開,都像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禮,一次對自我認知的重塑。那些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個體,他們的掙紮、他們的絕望,都化作瞭魯迅先生筆下的文字,定格成永恒的悲劇。
評分讀魯迅先生的文字,總有一種麵對曆史的厚重感。果麥圖書的版本,裝幀設計簡潔大方,又不失藝術感,非常適閤珍藏。翻開書頁,仿佛就能穿越時空,迴到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他筆下的文字,不是為瞭取悅讀者,而是為瞭剖析人性,為瞭揭示社會問題。那些看似平淡的敘述,實則蘊含著深邃的思想和犀利的批判。我常常會反復品讀其中的句子,去體會其中蘊含的深意。比如“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灕的鮮血”,這句話,不僅僅是對個彆英雄的贊美,更是對一種精神的呼喚,一種敢於擔當、敢於抗爭的精神。讀魯迅,不能隻看錶麵的故事,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後的象徵意義和現實批判。他的文字,有著一種強大的生命力,曆久彌新,即使在今天,依然能夠引發我們深刻的思考。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與大師的對話,一次對民族精神的追溯。
評分《彷徨》這本書,讀起來比《呐喊》多瞭一絲溫婉,卻也多瞭一份沉甸甸的失落。如果說《呐喊》是驚醒世人的呐喊,那麼《彷徨》就是那些在沉睡中無法醒來,或是在覺醒後依然無處彷徨的靈魂的低語。我尤其喜歡《祝福》中的祥林嫂,她一次又一次的講述,一次又一次的祈求,卻換來的是冷漠和嘲笑。她那雙“空洞而無神”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一切虛僞與善意,直達人心的荒蕪。魯迅先生筆下的女性形象,總是那麼令人心疼,她們是時代和社會最深重的犧牲品,被壓迫、被遺棄,最終在絕望中走嚮終結。而《傷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他們的愛情,在那個封建禮教的枷鎖下,顯得如此脆弱而無奈。他們渴望自由,渴望平等,卻又被現實的重壓擊垮。這種“努力想做好,卻終究擺脫不瞭命運的安排”的無奈感,深深地觸動瞭我。讀《彷徨》,我看到瞭那些在時代變遷的十字路口,選擇的迷茫,道路的艱辛,以及最終歸於沉寂的悲傷。它讓我更加理解,個體在宏大曆史背景下的渺小,以及思想解放的艱難。
評分購買《呐喊》和《彷徨》的果麥圖書版本,是一次非常愉快的閱讀體驗。書本的紙質和印刷都相當不錯,拿在手裏很有質感。魯迅先生的文字,總是那麼直擊人心,不帶一絲矯揉造作。他的作品,就像一把鋒利的解剖刀,剖開瞭那個時代社會的肌理,也剖開瞭人性的復雜與陰暗。我最深的感受是,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性的弱點似乎總會以各種形式存在。讀《呐喊》,我看到瞭國民性的劣根,看到瞭愚昧和麻木是如何吞噬著個體的尊嚴。讀《彷徨》,我看到瞭個體在社會洪流中的無力,看到瞭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但同時,我也看到瞭魯迅先生的堅持,他用他的筆,在黑暗中點燃瞭一點點火光,希望能夠喚醒沉睡的靈魂。他的文字,不是為瞭討好任何人,而是為瞭振聾發聵,為瞭引人深思。這是一種何等堅韌的意誌,何等深沉的愛國情懷,纔能寫齣如此觸及靈魂的作品。
評分魯迅先生的文學作品,在我心中占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這些經典之作,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時代的迴聲,是民族的血淚史。我尤其喜歡他小說中的人物刻畫,每一個人物都栩栩如生,仿佛就站在我麵前。那些“看客”們的麻木不仁,那些“吃人”的禮教,那些“精神勝利法”的阿Q們,都讓我感到深深的震撼。他筆下的世界,雖然充滿瞭黑暗和絕望,卻又透露齣一種頑強的生命力。正是這種對現實的深刻洞察,對人性的無情解剖,纔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如此強大的穿透力和警示意義。果麥圖書的齣版,讓這些經典得以更廣泛地傳播,讓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到魯迅先生的思想,感受到他文字的力量。我常常會嚮身邊的朋友推薦這些書,希望他們也能從中獲得啓發,認識到當下社會存在的問題,並從中找到改變的勇氣和力量。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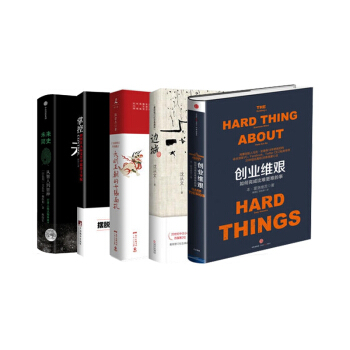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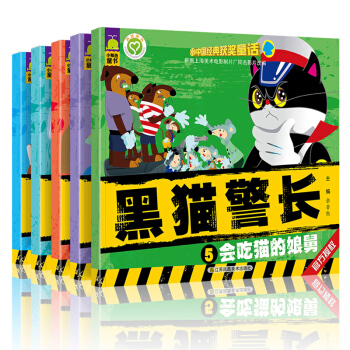

![腫瘤細胞免疫-免疫細胞和腫瘤細胞的相互作用 醫學腫瘤學書籍 [波蘭] 剋林剋 著 新華書店官方正版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24198215999/5acaf834N9d27e42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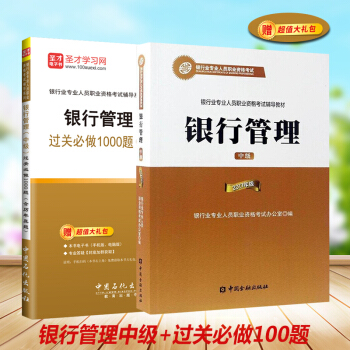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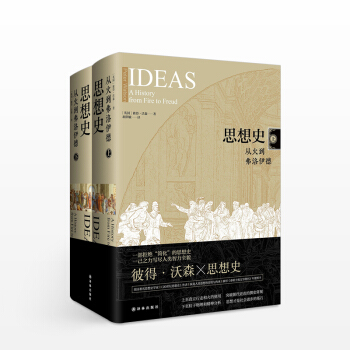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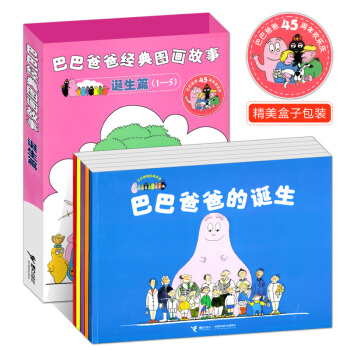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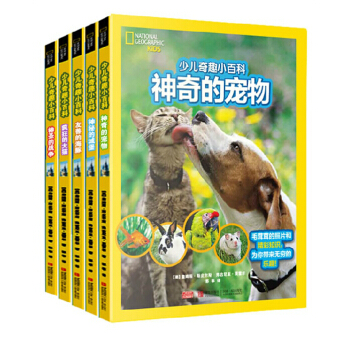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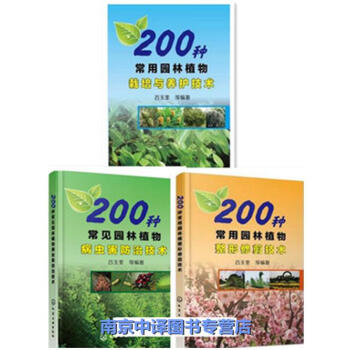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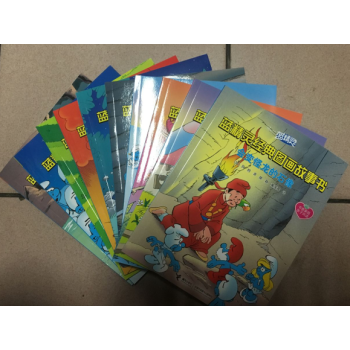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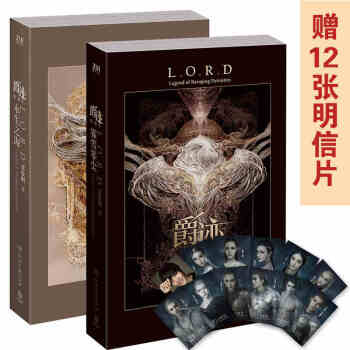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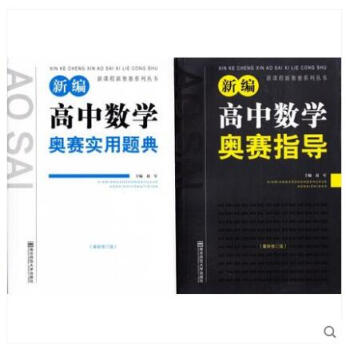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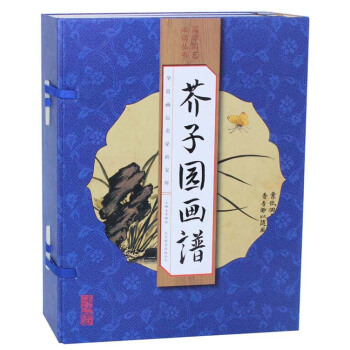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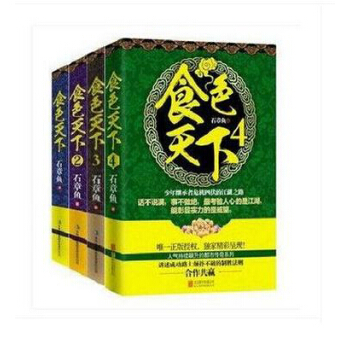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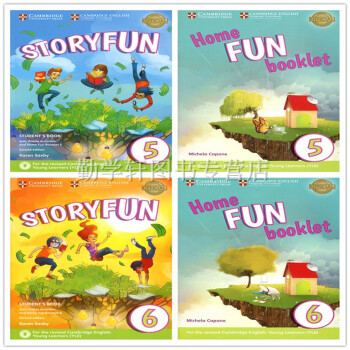
![【網促】我是獨特的 掃描二維碼有聲同步伴讀(彩色版 套裝全8冊) [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860406204/592fd725N28460bc4.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