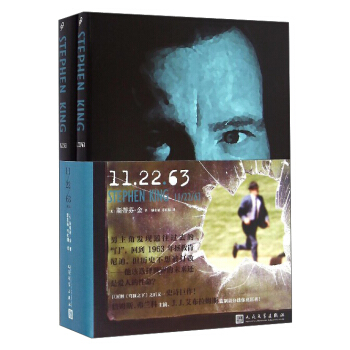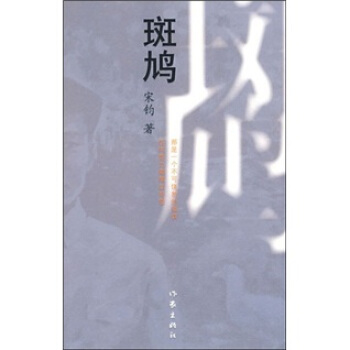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1950年代的另类生活传奇!一个北方乡村青年的忏悔录!鸠占鹊巢,一个人以另一个人的身份和名义活着。他得到了一大堆东西,但把自己弄丢了,倾其一生,他再没能让自己的名字复活……
故事如此曲折、跌宕,充满悬念,叙述却如此从容、节制,毫无夸怖,那是叙述者历尽沧桑之后的淡定。
内容简介
那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任何努力都难以补偿……故事如此曲折、跌宕,充满悬念,叙述却如此从容、节制,毫无夸怖,那是叙述者历尽沧桑之后的淡定。宁静的河面下暗潮汹涌,平和的语调难掩彻骨的忧伤,这只“斑鸠”的命运让人不能释怀。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一个人对自己生命成长的追寻,却被卷入了历史的皱褶。这部作品在个人的生命选择与历史的宿命之间,建立起一种奇特的紧张关系。就在历史宿命之侧,主人公的形象一步步清晰:那是一个富有文化气息、带有感伤气质的乡村青年形象,其敏感和内秀甚至远远超出中国文学中惯常的农村青年形象。他甚至有些诗意气质,他身上有着五四青年的某些禀赋,那是未能投身革命而误入歧途的乡村知识青年。——陈晓明
一部相当出色的小说。从叙述即小说语言的角度,堪称当代小说中不多见的精品,不惟从容、节制,而且简洁、精准,凸现了现代汉语文学作品可能的钻石品格。对节奏的把握尤其高超,将结构和布局上的虚实、简繁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
——唐晓渡
目录
第一章孤城驿
李广武
小家伙
贼船
第二章
形形色色的客人
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
张望唐河镇
第三章
孙晋的朋友
笑面韦驮
风从北方来
女生、女生
第四章
李叔叔
网撒出去了,小鱼还在欢快地游动
不要仇恨
第五章
是谁炸伤了李广武
唐河支队
焦土·雪野
第六章
凯旋
我的幸福时光
第七章
我们家的新人
在河边
诱捕
最初的清算
第八章
女客人
正仁街号
唐河苏武
第九章
阴影
邮差
我能给你什么
给孩子们
第十章
致本城居民的公开信
梦魇
等待台风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孤城驿关于我的故事,还是从五○年开始说起吧。五○年春节刚过,我从烟台搭乘一艘双桅机帆船去安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行。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算起来距离不太远,但隔着海峡,又分属两省,因此在安东下船的时候,心里也“异乡异客”地怅惘了一回。我从安东坐上开往唐河的长途公共汽车,沿海边公路西行约两个小时,中途在孤城驿下车,这是我此行的终点。我来孤城驿是投奔一个叫李秉义的人,他是我的一个本家叔叔,在孤城驿来亨贸易货栈做店员。在海峡另一面的山东老家,李秉义算是一个体面人,乡亲们管他叫“二掌柜”。李秉义回乡的时候穿着长袍,戴一顶呢礼帽,举止彬彬有礼,浑身透着生意人的谦和劲儿。有一个阶段,父亲曾打算让我跟李秉义出来学生意,那时候我在县城上中学,心气很高,说到生意人,第一个印象就是低眉顺眼打算盘,或点头哈腰招徕顾客,自然是看不上眼。我最感兴趣的是当军官,有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国军里做到师长,所以当时很多同学都想从军,除了当兵,那时候我从未起过别的念头。当我在家里待不下去的时候,自然就想到了李秉义,当年李秉义曾经很赏识我,如果那时候跟他出来,估计这阵子我也该戴上呢礼帽了。
孤城驿是一个背山.临海的小镇,一片青灰的瓦屋顶,看起来和我们子午山的集镇差不多。打听了几个人,很快找到来亨贸易货栈。
焦土?雪野
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接触过高句丽、百济和新罗这些古国名词。自安东都护府以来,鸭绿江东岸这块土地似乎总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为它搭进了多少条性命,连自己都难以计数,我们有一百条理由为它着迷,到头来却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到岳宝瑞的爷爷岳振邦逃走那时候起,我们终于离开了这个咝咝作响的炮仗,但仅仅隔了几十年,在它炸得遍地开花的时候,我们又回来了。
沿X号公路往南开,恶战的迹象随处可见,沿途看不到一个完好的村庄,所过之处,满眼都是废墟,炸断的大树横在路边,甚至连岩石都被烟火熏成黑色。路上,不断能遇见队形不整的朝鲜人民军向北撤退,即使遇见我们这样一支骡马车队,他们也会谦恭地等候在路边,让我们先过。
每当中途休息的时候,支队都要抓紧时间进行防空演习,警务连的人安插在各分队指导训练,我们被告知:听到号声,须立即就地卧倒,双手掩住耳朵,嘴张开。队员们没经历过轰炸,觉得这种姿势挺滑稽,他们说这是“旱地扎猛”,每当训练结束,大家嘻嘻哈哈地互相取笑。第一次经历轰炸是在龟城南面,车队正走在一片低山地区,忽然响起了防空号声,我们刚隐蔽到公路边的树林里,便有两架飞机低空飞过来,巨大的轰鸣声夹带着哨音呼啸而过,像从地皮上碾压过去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或许是试探,那两架飞机往公路上投了几颗炸弹,有一挂马车受了惊吓,从隐蔽处狂奔而出,笔直地冲下公路。那两架飞机有了目标,依次俯冲下来,又投下两颗炸弹。在腾空而起的烟雾中,眼见车轮像风筝一样斜飞到山那面去了。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岳宝瑞也冲出树林子,他的黑斗篷高高地飘起来。像一只黑色的大鸟展翅欲飞。只见他冲到一片开阔地上,指天画地声讨空中强盗。在我旁边的警务连丁连长骂了一声:“这是哪儿冒出来的活宝!”有好几个声音大喊岳宝瑞,但他像没听见一样。丁连长迅速冲出去,拉了岳宝瑞一把,岳宝瑞顾自大喊大叫,梗着脖子作岿然状,后来还是老丁用了擒拿功夫才把他放倒。
这天晚上,各分队都分到了马肉,丢了马车的车老板伤心得直哭,数叨说那是三匹好牲口,其中一匹稞马刚配了种,还花了一斗高梁的料钱,现在可好,齐根都炸掉了。卜政委耐心劝了他半天,说这是他的光荣,何况按规定还可以得到赔偿。车老板好歹不哭了,但他坚决不吃马肉。
晚饭后召开了分队以上干部会议,孙晋一反常态,声色俱厉地强调说隐蔽是头等大事,据他观察,今天被炸毁的那挂马车根本就没闸。我注意到孙晋的语气也不像以前了,他再没像以往那样强调要把人都好好带回去,而是说要把伤亡降到最低限度。这是一个不祥的变化,是身临其境的人才有的一种直觉。孙晋还对丁连长的果断行为表示感谢,说要建议军分区给丁连长记功。至于岳宝瑞,经研究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没收黑斗篷,并责令写出书面检查。
散会后我在队部拿了一件棉衣,来到城关区分队。岳宝瑞的黑斗篷已被收缴,他瑟缩着身子,一个人坐在树下,膝盖上垫着小本子,眼神直勾勾的,看样子又在构思了。我把棉衣给他披在身上,岳宝瑞一下又来了精神,说今天很不错,至少有两首新诗,都是以前没体验过的,待在家里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意境。说着便站起来,背着手走了两步,随之抬头望着夜空吟出两句。我打断他,说你把诗先放一放,今天晚上还要写一份检讨书交到队部。岳宝瑞一听便火了,他拍拍身上,说:“不是把斗篷拿走了吗,还写什么检讨!”
我说:“对你的处分是队部研究决定的,不能更改。你今天的行为非常愚蠢,要不是丁连长,还不知会闹出什么后果,你不怕死,图一时痛快,可你想过没有,在你身旁还有三千人的车队。”
“他们都说我傻,”岳宝瑞说,“我骂飞机,飞机在天上,它听不见,我知道它听不见,听见了也听不懂,那是美国飞机,美国飞机能听懂中国话吗!”
……
前言/序言
后记若干年后,在北满林区一个地窨里,我开始追述自己的经历。那时候外面冰天雪地,气温是零下三十几度,从外兴安岭吹过来的西北风挟带着雪雾在树梢上呼啸,地下则是另一个世界,炕洞里燃着劈柴,空气中弥漫着松树凝子的气味,肆虐的风雪和彻骨的严寒都被挡在外面。喧嚣中的宁静,能让人想起很多往事,由大风搅起的思绪,仿佛都在风吹不到的地方沉淀下来,积成厚厚的一堆——
“关于我的故事,还是从五。年开始说起吧。”我对着跳荡的油灯说,然后,我把这句话记在摊开的稿纸上。
把自己的经历当作故事讲出来,我认为这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使如实复述,也难免矫饰的嫌疑,这有悖我的某些准则。好在我并不认为那就是我,叙述者是一个叫李满仓的人,我可以想象,李满仓以第一人称叙述另一个人的故事,那个人叫李广举,或者叫李广武。如今唐河的李广武被埋在数千里外的一个公墓里,而李广举也早已丢失在漂泊的路上,李满仓知道他们的全部底细,他要拿他们来打发漫长的冬夜。
我住的地方离国境线只有二十公里,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嘹望塔上能清楚看到北面的界河,这里是林场的一处观测点,在场部绘制的地图上,我的观测点代号是511。大雪封山之后,林场撤走了另一名观测员,此后的几个月里,只有我一个人守候着方圆百里的莽莽林区。我每天三次从栖身的地窨里走出来,登上圆木搭的嘹望塔,八十倍军用望远镜把远处的景物都拉到眼前。暴风雪过后,四周一片死寂,仿佛连空气和声音都在眼前凝住了,厚厚的积雪掩埋了地面的棱角,近处远处的景物都变得浑圆起来,大地就像一幅八卦图,仿佛又回到了遥远的混沌时期。偶尔,镜头里面会出现觅食的松鼠或是野鸡,这时候我通常会兴奋起来,如果它们找到浆果,我会一直看着它们饱食之后离开。我还发现过两处树洞,洞口挂着厚厚的白霜,据说那里面住着蹲仓的黑熊。我把眼前的一切生物都看作是我的邻居,我和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到来年冰雪消融之前,我完全是一个自然的人。松鼠和黑熊住在树洞里,野鸡在草丛中,而我的巢穴在地下,只有当另一个人到来的时候,这里才有了社会,有时候我想这一次真他妈的完全彻底,简直就是逃离了社会。嘹望塔是一个过时了的景物,每当我在上面凝目远眺,望着密密层层的冷杉梢头在风中涌动,仿佛青风岬的海浪正在向我涌来。在灯塔的时候,我对生活还抱有某种期望,而现在,我只是一双眼睛,我想我活在这世界上注定是一个守望者。
我比较喜欢李满仓这个名字,它很平常,像大田里的一棵高粱,永远不会惹人注意。它能让人想起土地、农作和收成,有一种可以触摸的质感,自从我赋予它生命以来,很少有人提起它(对于一个刻意要隐姓埋名的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只是静静地睡在林场职工的花名册里,也许场部领导在某一次会议上,偶尔会站在地图前,指着我的观测点说:这里就是511,有我们一个观测员。他们没见过这个观测员,不知道他的过去,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叫李满仓。
我的搭档是个快乐的小伙子,他有一个秀气的名字,叫杨秀玲,人长得也秀气,他来511不到三年,是顶替前一个退休的老观测员。杨秀玲刚来的时候,耐不住旷日持久的寂寞,动辄爬到嘹望塔上,拍着栏杆大声吼叫。闲暇时他便缠着我不停地说话,比如我的家庭以及来林场前的经历,我自然又得编造身世,这次我是胶东的农民,已婚,生有一个女儿,老婆叫杨舸,是春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我编造谎言很平常,有一种事务性的认真态度,由于过于认真,有时候连自己也迷惑了,仿佛那本来就是我。长年呆在林子里,可干的事毕竟不多,我花很多时间侍弄土地,住处周围的空地都被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和谷物,还有一片大烟。我的农活手艺让杨秀玲大开眼界,不过据他说,我的行为举止更像干部或是教员。
每年春季杨秀玲回来,第一件事便是给我理发,这时候我的头发通常都长到齐肩,杨秀玲管我叫“女干部”。雨季来临的时候,我照例要休一个月的假,既然我是有家的人,总该回家看看。每次临行前,杨秀玲都会说:“这回该给我姐留个儿子了。”或者说:“快走吧,去年你气色挺好,我看能种上,没准回家就能赶上抱儿子了。” 我步行穿过森林,向南走一百多里地,那里有一个伐木场,从伐木场乘小火车往东二百里,是场部所在地,那是一个四等小站,具有文明社会的一切特点,旅馆、饭店、澡堂和电影院一应俱全。我从场部领了一年的薪水,通常会在那里适度消费一下,感受一下作为现代人的种种便利,然后改乘公共汽车继续向东,约有六个小时的车程,在日暮时分到达另一座小城(由于种种原因,我不便说出地名,姑且叫它s城吧,如果说我还有家可回的话,这大概就算回家了)。离开唐河这些年,家的概念已经很淡漠了,像一个陈年的梦。我能够理智地看待自己,对我来说,唐河是另一个世界,比如阴阳阻隔,我从不奢望能起死回生,我可以千遍万遍默念杨舸和小午的名字,但我没有丝毫理由再去搅扰她们那已经平静的生活。对妻子女儿的思念驱使着我,我就像固执的候鸟那样准时,每年一度来到S城,在这里,我能辗转得到一点妻子女儿的讯息,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毗邻国境线的S城颇具异国情调,远远望去,一片漆成灰色或是天蓝色的铁皮屋顶,铁路线穿城而过,消失在远处的森林中。城里也有一座小教堂,和唐河不同的是教友们可以做礼拜,可见这里比内地要宽松一些。当年我从唐河出来,先在北方转悠了两年,给人放过马,下过煤窑,在林场当过伐木工人。那是一段近于流浪的日子,为了不惹人注意,我把制服收进提包里,换上对襟袄和抿裆裤,尽量让自己土气一些,那时候我是一个老成笨拙的胶东农民。后来风声渐紧,不断有逃亡者被查获,我不得不一再向北边迁移,最后来到S城,大凡在南面能有一点办法,我想我是不会利用程天佩提供的投奔地址。记得火车是在下午到达S城,照程天佩给我的地址,找到城北一处小旅馆,接待我的,居然就是在程天佩家看见的那个老顾(也许是老景),现在他姓金,人们都叫他金掌柜。初次看见金掌柜简直让我瞠目结舌,当年在唐河河堤上,我曾经试图对他使用暴力手段,还扬言要把他扔进河里,但金掌柜并不特别注意我,仿佛他已经忘记了。金掌柜是一个有规矩的人,对我的款待周到又有分寸,我们很少说话,偶尔碰见,只是点头而已。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金掌柜的小旅馆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这里住着一些神秘的客人,他们谨慎而又收敛,悄无声息地呆在各自的房间里,很少互相走动,只有吃饭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起,但没有人说话,一个个满腹心事的样子,那些怀表、金牙、平光镜以及陈旧的三接头皮鞋和礼服呢外套,无不散发着一股陈年的霉味。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由于不合时宜,他们不得不离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前些年他们应该往南走,在孤城驿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登船,去寻找适于他们生存的地方,如今海路被堵死了,于是他们又一股脑拥向北方,这里地旷人稀,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身,他们在这里集结等待,像逆流而上的鱼群寻找源头。和他们比起来,我还是一个新手,我还不太适应阳光下的黑暗,但从今往后,我将和他们一样,我想逐渐会适应的。在小旅店住了半月左右,每天就是睡觉、吃饭、看书,据程天佩说,金老板会给我找一份工作,所以也不是很着急。终于有一天金老板告诉我,工作已经联系好了,去林场当护林员,他并没问我是否同意,只说那面一切都办妥了。“是一份好差事,挺安全的,”他说,“你看,林业局那面需要登记一下,你得有个名字。”他谦和地望着我,仿佛我从来就没有过名字。那时候我脱口就说出了李满仓这个名字,金老板让我写在一张纸条上,然后收起来揣进衣兜,临走的时候他像是忽然想起来,说:“对了,这里还有你一个熟人,今天下午会来看你。”见我诧异的样子,他轻声说请李同志放心,这件事非常稳妥。不等我再问,他便轻轻关上门,悄无声息地走了。这天下午我忐忑不安地呆在房间里,我实在想不起有谁会来看我,老实说,现在我还没到被人“看”的时候。不难想象,这时候唐河的我早已埋在屏风山革命公墓里,墓碑前摆着褪色的花圈,真切的或事务性的哀伤已逐渐平复,都被厚厚的黄土掩埋在地下,而这时候竟会有一个人戏剧般地越过阴阳阻隔,要来看我了。我了解程天佩,他绝不会把如此性命攸关的秘密泄露出去,那么,这个人是怎么知道我还活着?他想干什么,是显示知情者的能耐还是要来“验明正身”?我站在窗前,望着街上往来的行人,心里反复揣摩着可能出现的面孔。午后的阳光斜照在街上,风中已夹带着秋天的凉意,街两旁的杨树叶已经泛黄,一群大雁横着从天上飞过去,急匆匆飞向南方,大概在立冬前后,它们会准时到达唐河,在那里稍事休整,然后飞过海峡,飞过子午山。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是上行列车,小站的广播响起来,播音员的声音懒洋洋的。这时候有人轻轻敲门,我走到镜子前,做作地拢了拢头发,样子还不算太狼狈,我想既然要来看,那就看吧。仿佛是一个幻觉,站在门外的竟是罗苏维!几年不见,罗苏维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原先的发辫剪成了短发,但热情的眼神还在,依稀还能感觉出咄咄逼人的样子。 “没想到会是你!”我说不上惊喜还是惊慌,拉过椅子让罗苏维坐。“听金老板说,今天下午会有人来。” “刚知道你在这儿,”罗苏维说,“两年前程天佩来过一封信,说你能过来,这两年你去哪了?” “海阔天空,”我说,“离开唐河后一直在北方转悠,其实咱们隔得不远。” “我家就在附近,”罗苏维把手里拎的背兜背到肩上,“你收拾一下,咱们走。” 路上罗苏维不停地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仿佛我是来旅游的。我想罗苏维已经习惯了用平和宽容的眼光看我,即使我变成一条毛毛虫也不会让她惊讶。在朋友眼里能混到这步田地,我说不准是幸运还是悲哀。我问罗苏维现在怎么样,她说在中学教美术。提起当年离开唐河那件事,罗苏维迟疑了片刻,说她不得不走。“我有一个儿子,今年三岁,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罗苏维笑了一下,“我没有勇气把孩子生在唐河。” 罗苏维家是三间红砖房,铁皮屋顶漆成天蓝色,院里种了很多向日葵,中间一条方砖铺的甬道,甬道两边是荆条插的篱笆墙,墙根混种着秋菊和鸡冠花。进门是厨房,西屋是客厅兼工作室,几幅未完成的油画随意摆放在地上。罗苏维把画架推到一边,搬了把椅子给我坐。摆在地上的画有一幅静物,两幅风景,其中一幅画的是海湾,显然是以前未完成的画稿,我说:“你终于能沉下心画画了。” “我喜欢做美术教员,也算物尽其用吧。我们有几个学生很有才气,今年有四个考上美院了。” 这时候外面有人喊罗老师,罗苏维迎出去,一会儿拉着一个男孩走进来。“阿图,叫叔叔,”她俯下身指着我说,“这是阿图的李叔叔。”阿图喊了声叔叔,就鼓着劲儿去搬椅子。罗苏维说:“妈妈要做饭去了,看叔叔能不能抱得动,我们阿图可沉了。”阿图站在地上做岿然状,我故作吃力的样子抱起阿图,说:“阿图真沉!领叔叔出去玩好不好?”阿图兴奋起来,拉着我的手往外使劲儿:“叔叔捉蚂蚱。” 阿图是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黑头发、灰蓝色的眼睛、翘鼻子、白里透红的胖脸蛋儿,隐约能看出那个苏联中尉哈达耶夫的影子。我想罗苏维当年不顾一切要生这个孩子,除了对界河北面那片广袤土地的向往,也有对哈达耶夫的真实情感。公道地说,哈达耶夫这个人不错,在情感方面,罗苏维不会作假,为此她失去了一些东西,阿图是一个回报,是一个抚慰,我想如果不是北面那条界河的阻隔,罗苏维会毫不犹豫地为孩子去寻找父亲,为自己去寻找所爱的人。我给阿图抓了两只蚂蚱,用罐头盒装起来,阿图捧着罐头盒看了一会儿,又掏出来一只放在地上。我问阿图为什么要把蚂蚱放走,阿图严肃地说:“它们打架了。” 甬道东侧的篱笆有两处缺口,我找来荆条给重新修补起来。罗苏维的院子很大,约有一亩地,土质黝黑,除了种一点向日葵,其余的土地就那么闲置着,如果是在春天,我想我会把它变成一片菜地,尽管罗苏维生活能力很强,但还是能看出独身女人的拮据。这时候便想到杨舸,正仁街93号现在也有一个单身女人,也有一个失去父亲的孩子,那些不眠之夜,深长的叹息,坚定的面孔下面,掩藏着难以言说的凄苦无助,而我只能站在远处,无能为力地看着这一切。与我相近的几个女人,仿佛都难以逃脱命运的作弄,我见过郭兰,见过罗苏维,更是一手制造了杨舸的悲剧命运。回顾这些年,我在即将崩塌的雪崖边缘窜跳,雪崖终于崩塌,我被它裹卷着呼啸而下,回头望望,身后一片狼藉。晚饭的时候,我和罗苏维谈起孙晋,温丽新去世后,杨舸曾和我说过她的想法,那是一个很实际的安排,不乏女人式的体贴和周到,只是我们没来得及办这件事。罗苏维知道温丽新已经不在了,也为孙晋惋惜,又问起孙晋的儿子,我告诉她现在由杨舸抚养,罗苏维说杨舸心细,有责任感,孙晋把孩子交给她,也该放心了。我说这边气候毕竟和辽南不一样,记得孙晋说过,唐河人到了外地都会不习惯,如果有机会,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回唐河。罗苏维正在给阿图喂饭,她看看我,似乎已经听懂了我的意思。“那怎么可能,”她说,“我个人怎么样无所谓,我得为阿图考虑,唐河放不下阿图,不用说你也明白。” “唐河小吗?”阿图仰脸望着妈妈。 “唐河很大。”罗苏维说。 “比椅子大吗?”阿图认真起来。 “唐河啊……”罗苏维说,“都让人住满了,没有咱们阿图的地方了,阿图生在北方,这里才是阿图的家,”罗苏维舀了一勺汤喂给阿图,“黑土地,大森林,阿图的家多好啊!” 去林区那天,罗苏维送我到车站,临上车的时候她说:“我会注意南面的消息,休假了就回来,希望你能把我这里当自己的家一样。” 即使罗苏维不说,我也会把S城看做是一个家,那是我与过去的最后一线联系,没有那条线,我会像无主的野狗一样彷徨无着。我很幸运,在这种时候遇上了我和我妻子的朋友,S城是一个不容选择的归属,是漂泊的心灵唯一赖以凭藉的地方,有了那个坐标,我才没有让自己迷失在荒山野林里。此后,每年我都要回到S城,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来,我需要得到唐河方面的消息,当然,我同样看重和罗苏维母子的团聚,S城弥补了我的某种缺憾,让我重新感受到家庭的氛围。我和阿图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我总是在夏天来到S城,阿图便叫我“夏天的叔叔”。李秉义教给我的那个童谣,又被我传给阿图,看着阿图一年年长大,我就想小午也该长高了,还有孙晋的儿子留纪,他一直由杨舸抚养。杨舸还在实验小学教书。孙晋在专署工作两年后,回唐河当了副县长。这些都是罗苏维告诉我的,消息自然还是程天佩传过来的。程天佩还让罗苏维转告我,李秉义的后事是子午山那边来人办的,按照李秉义个人的意愿,那一提包东北币和他埋在一起。程天佩已经出徒,仍在拖船上,据罗苏维说,这小子一直过得逍遥自在。都说思想的人是草食动物,行动的人是肉食动物,程天佩是吃肉的,特殊的经历让他自小就磨砺出一副尖牙利齿,该出手的时候迅疾准确,绝不拖泥带水。离开唐河这件事,让我真正领略了他周密的头脑和过人的胆识。我不知道他如今是不是还在继续干那桩非法买卖,但贯穿东北的那条通道还在,他随时都可以利用,坦率说,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一般来说,当一个人从某种勾当中得到好处的时候,他自然就变成了同谋,比如我和金老板,当年我要把他扔进唐河,但现在我们成了朋友。由黑到白不容易,而由白到黑再便当不过了,只要你有足够的承受能力。金老板对我特别照顾,连食宿带介绍工作,只收了我一百元,而据我所知,由于风声太紧,后来他们每弄走一个人至少要四百,我想再给补一百元,但金老板不干,他说你是程天佩的人,交一点食宿费就行了。初听这句话很不受用,仿佛我是给程天佩跟班的,但后来也就想通了,金老板没说错,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仅有的这条命还是程天佩给的。离开唐河的时候程天佩给我准备了一点钱,加上以前借的,合计有一千三百元,这笔钱逐渐都还给程天佩了。我发现待在林子里,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攒钱,每年夏天出来,都能在场部财务科领到厚厚一沓薪水,尽管由运输科长到护林员,薪水降了不少,但一年当中,至少有十一个月没地方花钱,攒起来也是挺可观的一笔。后来又有消息说杨舸和孙晋生活在一起,他们又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消息并不让我意外,即使怀着褊狭的念头,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我的朋友和我的妻子,他们碰到了一个机会,他们没有放弃那个机会,各自做了适度的变通,我妻子又有了新丈夫,女儿又有了父亲,此后我可以了无牵挂了。感谢程天佩,他还给我传来了子午山老家的消息:父亲已经作古,李广武在子午山人民公社当主任,郭兰在县里工作。我想父亲临终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某种期望,期望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教我念《增广贤文》,但是父亲在茫茫冥路上找不到我,他老人家知道我还“健在”吗?罗苏维后来也结婚了,她嫁给了林场技术员彭秀深。老彭是扬州人,业余时间爱弄弄书画,对西禅的墨竹佩服得不行,闲暇时便临摹西禅,罗苏维总说老彭的竹子就和他的人一样呆板笨拙。彭秀深并不在意他妻子的冷嘲热讽,一如既往地画,罗苏维家挂得满墙都是,也送人。这时候我已经是个平和而又收敛的老鳏夫,除了每年与罗苏维一家的例行团聚,我几乎再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我不大能和人交谈,由于长年呆在林子里,我的舌头似乎总也不能和思维同步。当我和罗苏维夫妇闲坐的时候,罗苏维动辄会对老彭说:“当年老李对我是有些意思的,如果我们再多走一步,就没你什么事了。”老彭也会反唇相讥:“我看是你对老李有些意思吧,是不是要旧情复萌啊。”我在罗苏维夫妇面前没有秘密,这部手稿便是罗苏维整理抄写的,彭秀深也看过我的手稿。我始终珍藏着女儿七岁时的照片,那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有我们老李家人的特征,女儿是我和唐河的最后一线联系。或许是由于女儿的缘故,每想到唐河,我的心都会温暖一下,我总觉得我对唐河负有某种责任。不用说,唐河是我人生的一段歧路,我走错了,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但歧路风景是如此瑰丽,我已经不想自责了,我情愿用一生去守望它。再不能回唐河了,也不能回子午山,我已经习惯了林子里的生活,习惯了一个人独处的日子,当山前山后响起布谷鸟的叫声,在511嘹望塔上,会有一双眼睛长久地望着南方。
在线试读
《斑鸠》第一部分即使现在——在我写这部手稿的时候,回头审视最初的行为,我也认为离家是明智的选择。某些时候,你的存在会使当事各方陷入尴尬境地,这时候你最好还是离开。在遭遇尴尬的时候,有些人躲出去了,说得体面一点叫回避,在我老家子午山,有一种更直接的说法——跑了。五〇年春节后某一天,子午川前街李秉生家的次子李广举突然“跑了”。我离家的时候颜面扫地(这一节我会在后面写到),一个人偷偷溜出来,只是想走得越远越好,我走出去了,一走就是多年。
用户评价
坦白说,这本书的开篇略显缓慢,角色的介绍和背景铺陈占用了不少篇幅,对于追求快节奏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有一段需要耐心的适应期。然而,一旦故事的主线真正展开,那种古典小说的气韵和宏大的格局便展现无遗。作者仿佛在用一种古典的、史诗般的笔调来描绘一个现代的困境,这种跨越时代的张力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它的情节推进虽然稳健,但每一步都充满了宿命感,人物的命运仿佛早就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牵引。最让我感到惊艳的是其对“时间”这一概念的处理,它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让人深刻体会到个体生命在漫长历史洪流面前的渺小与无力。这是一部需要沉下心来,细细品味的佳作,它用扎实的文学功底,构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微观宇宙。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如同品尝一杯层次极其丰富的陈年威士忌,初入口时,可能只觉辛辣或略带苦涩,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后劲和复杂的回甘才逐渐显现出来。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功力深厚,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有在特定环境下被逼无奈的选择和挣扎。我尤其着迷于主人公面对绝境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近乎本能的韧性与狡黠,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活生生的、有缺陷的、充满人性光辉的个体。叙事中穿插的一些历史背景的细致考据,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坚实可信的基石,让虚构的情节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触手可及的过去。我常常会因为某个细节的真实感而感到震撼,仿佛作者并非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整理一份尘封已久的历史档案,其严谨度令人赞叹。
评分这本小说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仿佛一位经验老到的制片人在掌控着镜头,时而快速推进,让人屏息凝神,时而又慢下来,给予关键的情感和场景以充分的展现空间。作者对环境的描摹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那些细腻入微的笔触,构建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世界。无论是北方寒风凛冽的雪原,还是南方潮湿闷热的密林,都能让人身临其境,甚至能嗅到空气中特有的气味。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人物内心挣扎的刻画,那些潜藏在角色日常言行之下、复杂纠结的情绪,通过零散的内心独白和不经意的肢体语言被巧妙地揭示出来。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反而比直白的宣泄更具冲击力,让读者需要主动参与到对人物动机的解读中去,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参与感和回味空间。整体而言,这是一次非常愉悦的阅读体验,它不只是提供了一个故事,更像是一次深入的、多维度的感官探索。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需要时间来整理脑海中那些纷乱的思绪,因为它绝不是那种可以轻松翻过一页的书。作者在构建故事结构上展现了一种近乎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处理手法,大量的非线性叙事和多重视角交替,初读时可能会让人感到些许迷失,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迷宫。然而,一旦适应了这种叙事节奏,你会发现每个看似不相关的片段最终都会像拼图一样,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契合在一起,揭示出一个宏大而令人深思的主题。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其语言的驾驭能力,那种充满哲思的、略带疏离感的书面语,时常会抛出一些直击人心的诘问,迫使我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对某些既有观念的看法。这本书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而不是单纯的消遣,它要求读者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意义的追寻之中,收获的不仅仅是故事的结局,更是思维层面的拓展。
评分我对这本书的感情是复杂的,它成功地营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幽闭的氛围,这种氛围像一张无形的网,紧紧地裹挟着故事中的人物,也裹挟着屏幕前的我。书中对社会结构和权力运作的剖析,尖锐而毫不留情,揭示了那些隐藏在光鲜外表下的腐朽与压抑。作者对白的处理堪称一绝,那些对话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充满了潜台词和未说出口的威胁,仿佛每一次交流都是一场步步为营的博弈。我尤其欣赏作者敢于触碰那些敏感和禁忌的议题,并且不提供廉价的安慰或明确的答案,而是让读者在阅读结束后依然感到那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感。这本书无疑是那种“让人不舒服但又不得不读”的作品,它提供了一个观察人性阴暗面的独特窗口,非常适合喜欢探讨严肃主题的读者。
评分"[SM]和描述的一样,好评! 上周周六,闲来无事,上午上了一个上午网,想起好久没买书了,似乎我买书有点上瘾,一段时间不逛书店就周身不爽,难道男人逛书店就象女人逛商场似的上瘾?于是下楼吃了碗面,这段时间非常冷,还下这雨,到书店主要目的是买一大堆书,上次专程去买却被告知缺货,这次应该可以买到了吧。可是到一楼的查询处问,小姐却说昨天刚到的一批又卖完了!晕!为什么不多进点货,于是上京东挑选书。好了,废话不说。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它是一个人特有的形式,或者工具;不这么说,不这么写,就会别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腔调有时候就是“器”,有时候又是“事”,对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说,器就是事,事就是器。这本书,的确是用他特有的腔调表达了对“腔调”本身的赞美。|发货真是出乎意料的快,昨天下午订的货,第二天一早就收到了,赞一个,书质量很好,正版。独立包装,每一本有购物清单,让人放心。帮人家买的书,周五买的书,周天就收到了,快递很好也很快,包装很完整,跟同学一起买的两本,我们都很喜欢,谢谢!了解京东:2013年3月30日晚间,京东商城正式将原域名360buy更换为jd,并同步推出名为“joy”的吉祥物形象,其首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改版。此外,用户在输入jingdong域名后,网页也自动跳转至jd。对于更换域名,京东方面表示,相对于原域名360buy,新切换的域名jd更符合中国用户语言习惯,简洁明了,使全球消费者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访问京东。同时,作为“京东”二字的拼音首字母拼写,jd也更易于和京东品牌产生联想,有利于京东品牌形象的传播和提升。京东在进步,京东越做越大。||||好了,现在给大家介绍两本本好书:《谢谢你离开我》是张小娴在《想念》后时隔两年推出的新散文集。从拿到文稿到把它送到读者面前,几个月的时间,欣喜与不舍交杂。这是张小娴最美的散文。美在每个充满灵性的文字,美在细细道来的倾诉话语。美在作者书写时真实饱满的情绪,更美在打动人心的厚重情感。从装祯到设计前所未有的突破,每个精致跳动的文字,不再只是黑白配,而是有了鲜艳的色彩,首次全彩印刷,法国著名唯美派插画大师,亲绘插图。|两年的等待加最美的文字,就是你面前这本最值得期待的新作。《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当今世界最高明的思想控制与精神绑架,政治、宗教、信仰给我们的终极启示。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一次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从国家、宗教信仰的层面透析“思维的真相”。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神经生物学、医学、犯罪学、传播学适用于:读心、攻心、高端谈判、公关危机、企业管理、情感对话……洗脑是所有公司不愿意承认,却是真实存在的公司潜规则。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无孔不入。阅读本书,你将获悉:怎样快速说服别人,让人无条件相信你?如何给人完美的第一印象,培养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如何走进他人的大脑,控制他们的思想?怎样引导他人的情绪,并将你的意志灌输给他们?如何构建一种信仰,为别人造梦?[SZ]"
评分京东图书还是不错的,物美价廉,希望京东多多搞活动,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评分凑单 因为促销 京东快递已经慢递了 哎 现在作家可真廉价
评分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评分挺好
评分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评分图书勋章日,价格比平时便宜点
评分京东图书还是不错的,物美价廉,希望京东多多搞活动,让消费者得到实惠!
评分3、帛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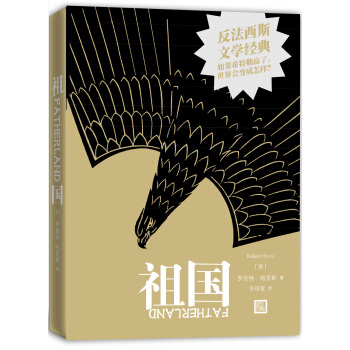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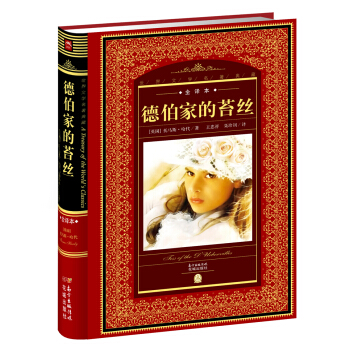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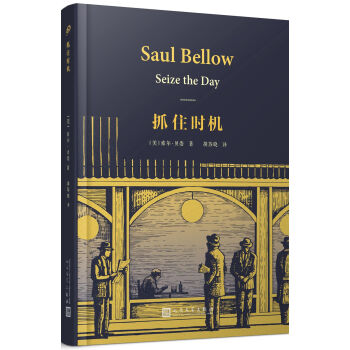

![浮世畸零人 [Ben, in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75629/56cd0eedNa367e43f.jpg)

![世界最险恶之旅(2) [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88071/57231496N3ce7c2d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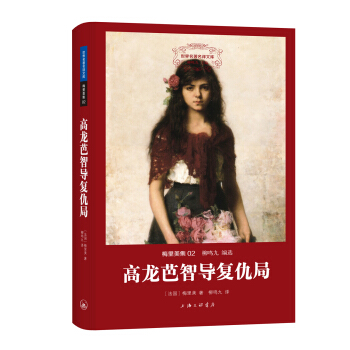



![异乡人.5:遥远的重逢(全二册) [Voyg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42783/58acff5dN13da56f2.jpg)
![破碎帝国:荆棘国王 [ KING OF THOR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62440/5823ececN7456502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