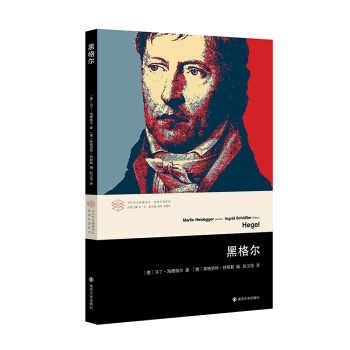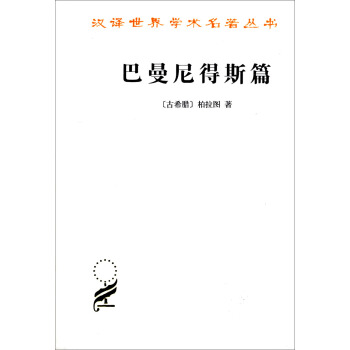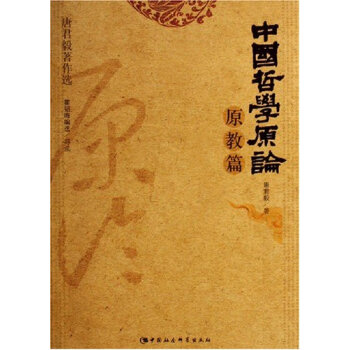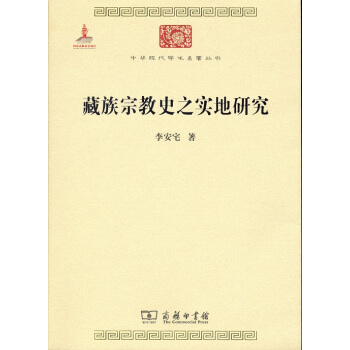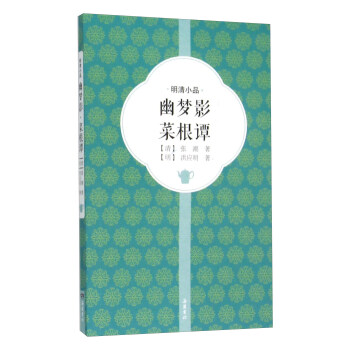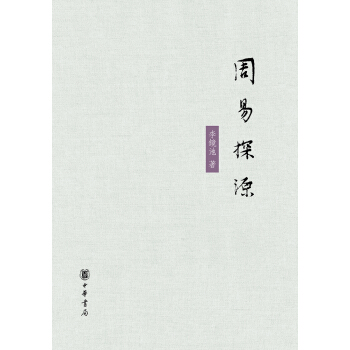![伯林谈话录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571157/93dfa568-c034-40ac-8c8e-af38bcb98d9a.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伯林谈话录包括:从波罗到海到泰晤士河、现代政治学的诞生等内容。从《伯林谈话录(新编版)》精彩纷呈的谈话中,读者可以分享他对自由主义与宽容的信念,可以分享他对音乐与文学的激情,也可以对他的生活与个性获得一种独特的认知。
作者简介
拉明•贾汉贝格鲁(1961— ) 伊朗哲学家,1974年迁居法国,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现执教于多伦多大学。主要著作有《甘地:非暴力之源》、《黑格尔与法国革命》、《现代人》,以及与以赛亚•伯林、乔治•斯坦纳等人的谈话录。他也是法国《精神》、《生长》、《研究》等杂志的重要撰稿人。精彩书评
他(伯林)像苏格拉底一样很少发表作品,但他的思考与言论对我们的时代有莫大影响。
——莫里斯·布瓦拉
对我来说,在这一代人中,以赛亚·伯林对生活的阐释是最为真实的和最为动人的。
——诺埃尔·安南
他(伯林)睿智而不显浮夸,风趣而不显琐屑,充满温情而不显伤感。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目录
序
第一次对话 从波罗的海到泰晤士河
两次俄国革命
20世纪30年代的牛津
卡尔·马克思:我的第一次接受委托
维也纳小组
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
奥斯威辛的发现
哲学家还是思想史家?
没有哲学家的哲学?
列奥·施特劳斯的“魔眼”
关于文化的差异
文化相对主义和人权
两种自由概念
关于多元论的争论
理想的追求
通向欧洲大陆的桥梁
第二次对话 现代政治学的诞生
马基雅维里:政治的自律性
国家与托马斯·霍布斯
斯宾诺莎和一元论
反启蒙运动:约瑟夫·德·迈斯特和埃德蒙·柏克
维柯或一种新科学
关于汉娜·阿伦特
身为今日之犹太人
赫尔德和社会观
思想史:一个寂寞的学科
第三次对话 政治思想:时间的检验
接受委托或候车
德国人的耻辱感
赫尔德、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18世纪的相对主义
道德与宗教
休谟和英国哲学
人权
威尔第、斯特拉文斯基、瓦格纳
摩西·赫斯:犹太复国主义者
马克思和19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
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第四次对话 自由哲学
斯蒂芬·斯彭德:60年的友谊
哲学的目标
多元论与民主
平等和自由
牛津哲学和实证主义
柏格森、谢林和浪漫主义
第五次对话 个人印象
19世纪的俄国思想
涅恰耶夫和虚无主义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赫尔岑
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1848年
刺猬和狐狸
别林斯基
从帕斯捷尔纳克到布罗茨基
丘吉尔、魏茨曼和尼赫鲁
乔治·索雷尔和伯纳德·拉扎尔
精彩书摘
贾汉贝格鲁(以下简称贾):首先,我要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如果可能,我想向您提出一些传记性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您以往的种种经历和它们如何影响了您的思想,以此作为我们讨论的开端。您于1909年6月6日生于里加,10岁时便随双亲离开俄国。关于这个时期您还有些记忆吧,尤其是移民的情况怎么样?
伯林(以下简称伯):我于1915年随父母离开里加前往彼得格勒[1],我们是1919年离开彼得格勒的。在那里,8岁那年,我目睹了俄国的两次革命。头一次革命我记得很清楚。到处是集会、旗帜,街道上拥挤着人群,人们激动万分,广告上画着李沃夫新政府部长们的头像[2],立宪会议的二十多个党派在做宣传。人们关于战争的议论倒不太多,至少在我们家生活的小圈子里3很少谈论。自由党人的革命主要得到犹太人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欢迎,而这种状况持续不久。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11月爆发,我们——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们——几乎都不知道。第一个信号是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总罢工。各种各样的报纸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家自由党人的报纸名字叫做《白天》,后来改名为《傍晚》,又改为《夜》,再改为《子夜》,最后改为《黑夜》,再过四五天吧,它终于被查封了。那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有枪声。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以为暴动最多能持续两三个星期。如果您翻阅那些日子的《泰晤士报》,会读到俄国驻巴黎大使写的报告,他预言暴动(putsch)会很快结束。在《泰晤士报》上,布尔什维克被称为“最高纲领派”,不算是主要的力量。列宁和托洛茨基逐渐作为革命领袖人物崭露头角。我父母属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以为列宁要创造一个让资产阶级不能生存的社会。他们把列宁看作一个危险的狂人,但又是一个纯粹的信徒,正直而清廉,在政治上热烈追求某种理想的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物,而把托洛茨基看作一个邪恶的机会主义者。只有八岁大的我不明白父母为什么对这两个人有如此不同的感觉。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名字连在一块,人们常常一口气说着,好像一个公司的名称那样。现在想来,当时仍旧忠于沙皇政府的人就只有警察了。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不够。人们管街道上的警察叫“法老”——民众的压迫者。有些警察在顶楼或房顶上向革命者射击。我记得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着,脸色苍白,挣扎着,显然快死了。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4可怕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
[1] 圣彼得堡。该城为彼得大帝于1703年所建,1914年改称彼得格勒,1924年又改称列宁格勒,1991年复称圣彼得堡。
[2] 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是短命的(1917年3月14日至7月25日)。继他之后的克伦斯基于5月5日便夺取了全部政权。
贾:您在革命后离开俄国有没有麻烦?
伯:没有。我家是从里加来的,里加当时已经成了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3]。如果你能证明你是拉脱维亚人,他们便让你走。我们离开俄国到达拉脱维亚。我父亲是一个木材商人,给俄国铁路供应枕木。他继续为新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工作了两年,最后显然是没法再做下去了。我们从未受过触动,不论是我父亲还是哪一个亲人都没有被捕或受到任何形式的骚扰。我记得人们排成长队购买面包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我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四五个小时才能买到东西。我们家邻近有个救济贫民的施粥所,那里有些食品供应。还有个小电影院,放映有关19世纪沙皇政府迫害革命者的社会主义影片(当时还没有共产主义的影片),一些憔悴的歌手演唱莫扎特和罗西尼的选段。那都是当时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所特有的记忆。我们全家挤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因为只有一个火炉。但是我不害怕,我没有压抑感——也许因为我太小而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我父母也很少跟我说。
[3] 拉脱维亚在1918年11月宣布独立,1920年8月11日苏联承认其独立(《里加条约》)。
贾:你们怎么来到英国的?
伯:我们先来到英格兰乡下,然后才搬到伦敦。开头,我上伦敦郊区一所预备学校,那时我很少说英语,我父母互相之间都说英语。从那以后我们很少看见俄国人。我父母不怀念里加,5不怀念俄国。我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崇英派的人,而我是在英国人不会干坏事这样的信念中成长的。我还没丢俄语,我想主要是阅读俄国的古典名著的缘故。结果我的俄语说得很流利,我每次访问苏联都被看作老乡亲。在我们学校有个男同学是俄国人,名字叫比利宾。他父亲是一个著名的俄国画家。他的儿子至今仍然是一个虔诚的俄国保皇派。我偶然跟他说说俄语,此外就极少碰上说俄语的人了,我的俄语水平主要归功于阅读以及在儿童时期扎下的根基。
……
前言/序言
我第一次会见以赛亚·伯林爵士是在1988年6月6日,他70岁生日那天,在他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寓所。欧洲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之一《自由四论》的法译本已经获得法国广大读者青睐。因此,我决定在《精神》杂志总部每周一次的文献研讨会上向我的同事介绍伯林的思想。这次研讨会的积极结果,是使我拿定主意通过一次由《精神》杂志同意发表的访谈来更深刻地展示伯林的思想。经过简短的电话交谈和迅速的信件往来,我们便决定在他寓所会见。自1976年1月一个寒冷的雨天我在伦敦佛勒书店发现《自由四论》之后,十多年来我一直对伯林爵士很敬仰,要拜会这么一位名人的念头确实使我感到有点紧张。但是,一见面他就带着友好的微笑热情地迎接我,话还没说我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消失了。谈话开始时,我不仅听他说什么,也留意他的仪表怎么样。虽然我见过他许多照片,而实地看到他我还是有点惊奇。他的面容乍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出生在里加的人。他的声音听上去准确而有力,但吐词缓慢。轻重分明的牛津口音极有节奏地流贯谈话过程,使我觉得我仿佛是获准受到一位极为尊贵的英国绅士的召见。这是温文尔雅、最谦恭的一个人,说话慢条斯理而热情厚道,毫不装腔作势。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他详细地告诉我俄国革命时期他的童年情况以及20世纪30年代他在牛津大学的情况。我很惊讶他对俄国文化有着非常亲密的感觉,毕竟他在10岁时就离开那里了。那天告别的时候我就希望能有机会再次见到他,但我不知道有一天还有可能以书本形式发表对他的访谈。
我回到巴黎以后,有个编辑跟我联系,他要求我继续这样的访问,并且写成一本书。很高兴我有机会再次会见伯林。我们是1988年12月于伦敦再次见面的。这次我有幸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跟他谈话。每个场合他都热情、友好地欢迎我。我得以就他在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向他提出了三百多个问题,分门别类,并逐一讨论。他要我将谈话记录整理成文,我把定稿交给了他。该书1991年在法国出版。
显然,这本书不奢望成为伯林的正式传记,但是,对于一切有待进行的伯林研究,这本书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有时候,有一种倾向,过高地估计思想史家的重要性,而对于伯林这么杰出的人物却不会是这样,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单是他对英语世界过去50年来各种智性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影响就足以使理解他的著作和分析他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他在著作中的论述和洞见有助于我们对形成当代史的各种事件和概念树立一种富有批判性的看法。因此,不可否认,伯林的思想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毫无疑问,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他那代人中典型的杰出牛津哲学家。他的牛津哲学背景(使他成为休谟哲学的真正崇拜者),他的思想的明亮清晰,他对晦涩术语的极端疏远,使他成为当代英国哲学的一个真正的代表。可是,在某些方面伯林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又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全部哲学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反抗传统信念的理论战斗来审视,那种信念认为,纵贯古今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原则上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真理性的正确回答。因此,他反对那种以为可以依据科学的、政治的、甚至美学的价值在人世间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主张。鉴于人类历史实际上是各种经常相互碰撞的价值和思想的产生地及其变化发展的实验场所这一事实,伯林追溯多元论在伦理学、政治学和美学等领域的出现。明白了这一点,人们就可以充分理解为什么50年来伯林选择思想史作为他的兴趣中心。在他看来,研究思想史无疑是弄清楚自孩提时代经历俄国革命以来,就深深地烦恼着他的某些严酷的难题的唯一途径。这项研究的成果便是关于民众生活和思想的措辞优美、具备了一部小说的全部文学品质的研究论文,同时也是对历史上各种观念的透彻的批判性的考察报告。伯林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吸引人,是因为他的全部写作都是从非教条的观点出发,以便向读者揭示作者全神贯注的某些持久不断的哲学问题。伯林不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决定论者,即使我们可以以为他是某种西方意识的现象学家。黑格尔主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发展的逻辑的和本体论的过程,经过先定的历史阶段,终结于现实与理性的某种调和。与这种观点不同,伯林的研究探讨了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个人责任的各个层面,这就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必然性的枷锁。因此,伯林对那些以最终解决为目标的一般的态度和观点都不感兴趣。在他最近出版的《扭曲的人性之材》那本书中有一篇论文谈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我说的不错,不光最终解决这个概念本身是不切实际的,而且,各种价值之间也不可避免地是相互碰撞的、不可协调的。最终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忘记了这个词组带有希特勒时期的恐怖感)会制造出一种幻觉,一种非常危险的幻觉。因为,如果人们真的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的,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付出多少都绝不为过:为了使人类永远公正、幸福、富于创造性以及和谐协调,有什么不可以为此付出的呢?为了做成这样的蛋卷,我们可以打破无限数量的鸡蛋,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我们所了解的波尔布特的信念。既然我知道通向社会问题最终解决的唯一正确道路,我也就知道人类车队必须沿着什么路线走;因为你没有我这种知识,你就不能有选择自由,哪怕是最低限度的选择自由,否则你就达不到目的地。你声明采取某种方针将使你更幸福、更自由,或将使你有自由呼吸的空间,而我知道你这样想是错误的。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人民大众需要什么。如果出现由于无知或恶意而酿成的反抗,那就必须镇压下去,为了大多数人永远幸福,消灭成千上万人也许是必要的。除了心甘情愿地将他们全都牺牲掉,我们,明白此中道理的我们,又有什么选择?”
人们了解了伯林的哲学背景就会更好地懂得为什么他劝告我们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赫尔岑和伯林的思想中,“选择”这个概念都处于关键地位。伯林批判柏拉图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认为它是西方思想传统中一元论的主要特征。这时他与声称“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该是认清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充满着偶发的和无意义的事件、充满着愚蠢和糊弄行为的时候了”的赫尔岑何其相似。因此,伯林笔下的主人公总是那些拒绝把世界看作单纯的、合理的、和谐的整体。主要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伯林接近于以法国哲人(Philosophes)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的思想“潮流”,但决不会妨碍他去弄清楚那些反对这一“潮流”的思想家的生活和思想。在思想史的工作中,伯林研究了那些勇敢地、公开地跟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体系作斗争的思想家,赞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他特别重视这些思想家的自由思想。正是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由思想的肯定和褒赏,显示了他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他的研究工作,伯林向我们宣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绝对的价值,而且,人类历史与众多悲剧性后果相伴,充满着那些企图通过坚信最终绝对真理而避免做出悲剧性选择的人们的困苦。
拉明·贾汉贝格鲁
1991年7月于巴黎
用户评价
这本书,坦白说,第一次翻开时我有些犯怵。那些厚重的名字和高深的议题,总让人觉得需要一个哲学专业的背景才能窥其堂奥。然而,一旦真正沉浸进去,那种扑面而来的智识的活力和思想的穿透力,却让人欲罢不能。它不像一本教科书那样冷冰冰地罗列观点,更像是一场发生在温暖的壁炉旁,两位思想巨匠之间,时而优雅时而激烈的辩论现场录音。你几乎能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的烟味,以及他们对知识的纯粹热爱。特别是当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和政治哲学的解读时,那种从不同文化和时代背景出发,相互碰撞、相互激发的火花,令人拍案叫绝。你会发现,许多你过去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在他们的对话中被抽丝剥茧,暴露出了内在的矛盾和细微的差别。那种感觉,就像是有人突然为你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思想世界的窗户,窗外是风云变幻的人类历史,而你正站在一个可以俯瞰全局的制高点。这绝不是那种读完就可以束之高阁的书,它更像是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在你接下来的思考旅程中,会不断地提醒你,去质疑,去深入,去以更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
评分阅读这卷记录的体验,简直像经历了一次密集而精妙的心灵按摩。那些对“自由”与“必然”之间永恒张力的探讨,不再是晦涩的学术术语堆砌,而是化为了极其生动的语言交锋。我尤其欣赏这种“谈话录”的形式所带来的松弛感,它允许思想在不那么拘谨的语境下自然流淌,没有论文那样必须严丝合缝的逻辑链条,却在整体上构建了一个更为丰满、更具人性温度的知识体系。你会看到,即使是最高深的议题,在两位智者你来我往的提问和反驳中,也逐渐变得可触可感。它教会我的最重要一课,也许是认识到“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陷阱。真正的智慧,可能恰恰存在于那些尚未解决的、充满张力的灰色地带。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它展示了思想是如何“生成”的,而非仅仅是“呈现”结果。那种思维的敏捷度,那种对细微语境的把握,简直让人叹为观止。读完后,我开始反思自己日常交流中的表达方式,那种追求清晰但常常流于表面的沟通,与书中那种层层递进、步步为营的深度对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评分这本书带来的震撼,更多是结构性的,而非内容的堆砌。它没有给我提供一套现成的“答案”,但却提供了一套极富洞察力的“提问工具箱”。我之所以如此推崇,是因为它直击了现代人知识焦虑的核心——我们阅读了太多碎片化的信息,却失去了构建宏大叙事框架的能力。而这卷谈话录,恰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多维度的框架,用以审视政治、历史、艺术乃至个体命运的复杂性。想象一下,如果用电影语言来描述,它不是一部叙事流畅的剧情片,而是一部由无数个精彩特写和富有深意的远景交织而成的蒙太奇作品。每一次转折,每一次对既有观念的颠覆,都伴随着一种强烈的智力愉悦感。对于那些对二十世纪欧洲思想史抱有好奇心,却又畏惧于官方学术著作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份绝佳的“入门密钥”,它在保持严肃性的同时,完美地平衡了可读性。它让我明白,伟大的思想,是可以充满人情味和生命力的。
评分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阅读时的感受,那一定是“精神的拓宽”。这本书并非那种读完就能立刻运用到工作汇报中的实用指南,它的价值在于其深远的潜移默化作用。我的世界观在某些关键的锚点上被轻轻地撬动了。它没有直接告诉我应该做什么,而是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复杂性。那些关于人性的弱点、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探讨,都以一种极其成熟和克制的语调被表达出来。我特别留意到作者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鸿沟的处理方式,那种既不完全悲观的犬儒主义,也不天真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基于深刻理解之上的审慎前行。这种平衡感极其难得,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容易陷入极端情绪的时代。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两位思想家的面孔,更有我们自身在面对宏大历史命题时的局限与潜力。阅读完毕后,我发现自己对新闻报道中的某些断言开始保持警惕,多了一层思考的缓冲垫。
评分我常常思考,何为真正的“经典”?在我看来,那些能够跨越时代、激发后续思考的作品,方能当此殊荣。这本记录,便具备了这种特质。它不仅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总结,更像是一份关于“如何进行高质量的思考”的示范文本。文字的韵律感和对话的节奏感,构建了一个令人沉醉的智力空间。它让我深刻体会到,知识的积累是必要的,但知识的连接与重构才是真正的智慧所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的观点碰撞,使得任何一个单一的论断都无法轻易站稳脚跟,这迫使读者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世界的多元和内在的张力。这本书没有给我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但它提供了一种极为宝贵的、近乎奢侈的智力挑战。对于任何渴望提升思维深度、追求思想自洽的读者而言,这绝不是一本可以跳过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将陪伴我很久,如同一个沉默但时刻在场的智者,在我迷茫时提供一种思考的参照系。
评分不错的好书,值得看看!!
评分听说作家的第一本书是写他自己,最后一本书也是写他自己。 “第一本书”指自传式的小说,“最后一本书”指作家的回忆录。 我曾经想写“第一本书”,始终没写出来。现在,我想写“最后一本书”了。 我向不热衷歌颂名利,虽然在我举目所及之处也曾出现雍正乾隆。 竞逐名利是向前看,恋念情义是向后看。 人,从情义中过来,向名利中走去。有些人再回情义,有些人掉头不顾。 这是一本向后看的书。所谓情义,内容广泛,支持帮助是情义,安慰勉励也是情义。潜移默化是情义,棒喝告诫也是情义。嘉言懿行是情义,趣事轶话也是情义。 这“最后一本书”为生平所见的情义立传,是对情义的回报。无情义处也涂抹几笔,烘云托月。 我并不是写历史。历史如江河,我的书只是江河外侧的池泊。不错,池泊和江河之间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调节。一位历史学者说,“历史是个小姑娘,任人打扮。”这也没什么,小姑娘尽管穿衣戴帽,而出水当风,体态宛然。 也许,历史是一架钢琴,任人弹奏乐曲。因此才有书,才有第一本书和最后一本书。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与孤鹜齐飞”何以成为千古名句。 我以为都不是。人的一生只能是一部回忆录,是长长的散文。诗、剧、小说,都有形式问题,都要求你把人生照着它们的样子削足适履。而回忆录不预设规格,不预谋效果。回忆录是一种平淡的文章,“由绚烂归于平淡”。诗、剧、小说,都岂容你平淡?西谚有云:“退休的人说实话。”退休的人退出名利的竞技场,退出是非旋涡,他说话不必再存心和人家交换什么或是间接为自己争取什么。有些机构为退休的人安排一场退休演讲,可以听到许多真心话。古代的帝王“询于刍荛”,向打柴割草的人问长问短,正为这些人没有政治目的,肯说实话。所以回忆录要退休以后过若干年抄写,这时他已没资格参说谎俱乐部。回忆录的无上要件是真实,个人主观上的真实。这是一所独家博物馆,有些东西与人“不得不同,不敢苟同”,或是与人“不得不异,不敢立异”。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岂舍诸。”“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诗人痖弦的名句。白云苍狗,变幻无常而有常,否则如何能下“苍狗”二字?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这“最后一本书”不是两三百页能够写完的,它将若断若续,飘去飘来。
评分显然,这本书不奢望成为伯林的正式传记,但是,对于一切有待进行的伯林研究,这本书不失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有时候,有一种倾向,过高地估计思想史家的重要性,而对于伯林这么杰出的人物却不会是这样,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单是他对英语世界过去50年来各种智性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影响就足以使理解他的著作和分析他的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他在著作中的论述和洞见有助于我们对形成当代史的各种事件和概念树立一种富有批判性的看法。因此,不可否认,伯林的思想向我们提出了挑战。毫无疑问,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他那代人中典型的杰出牛津哲学家。他的牛津哲学背景(使他成为休谟哲学的真正崇拜者),他的思想的明亮清晰
评分好东西,(我在刷分)好东西,(我在刷分)
评分据说以赛亚柏林因此书闻名,正在看。
评分3,适合耐心的人读。
评分伯林谈话录伯林谈话录
评分新版贵了几块钱,封面大片空白的装帧与前版各有千秋
评分不错的书籍,不错的服务。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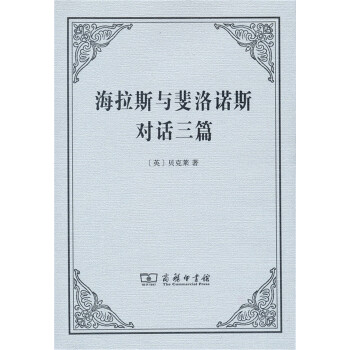

![牛津通识读本:无神论(中英双语) [Atheis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42093/5ae1cd05N7e3d3fc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