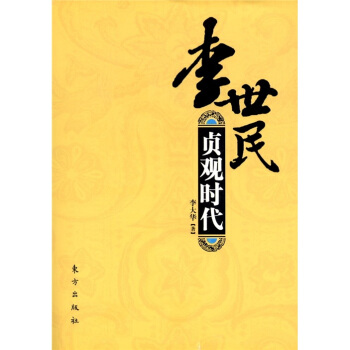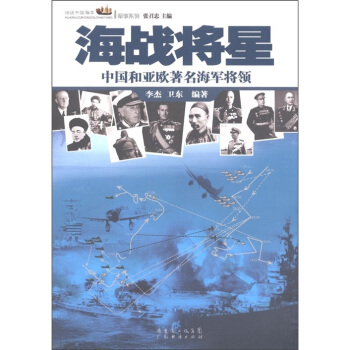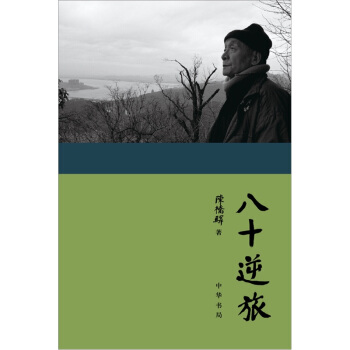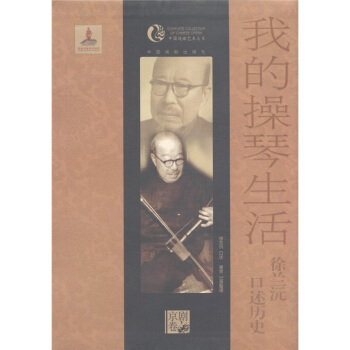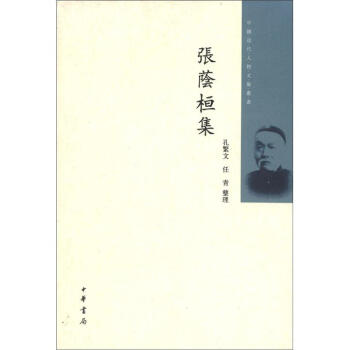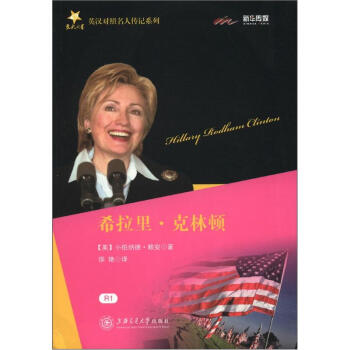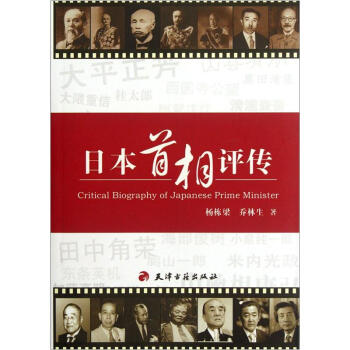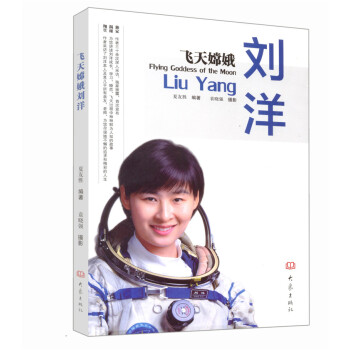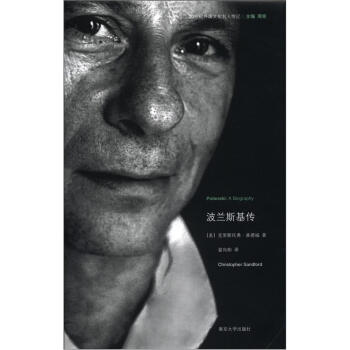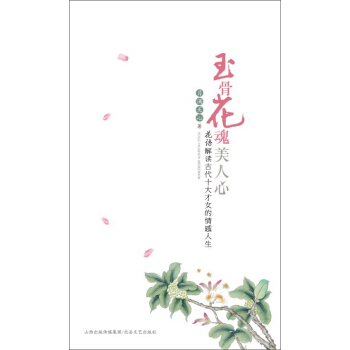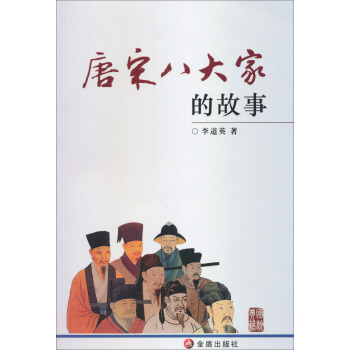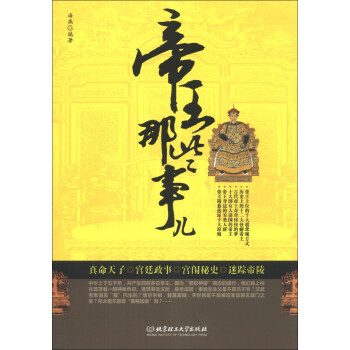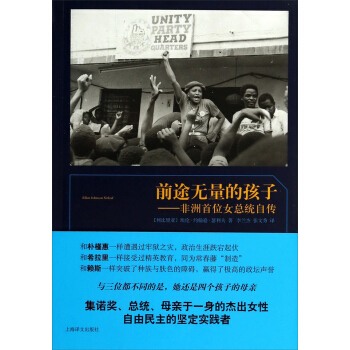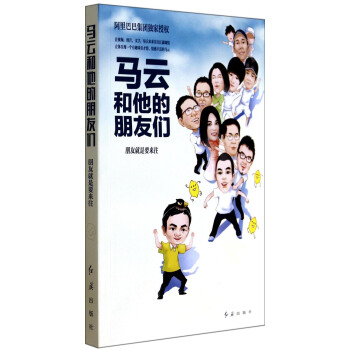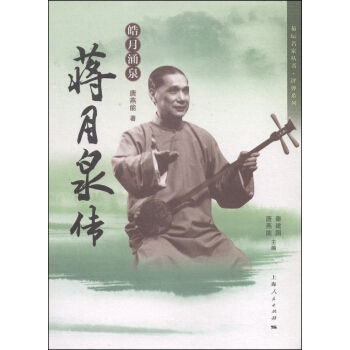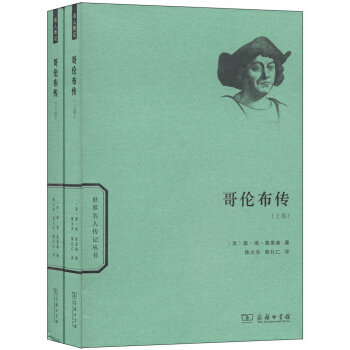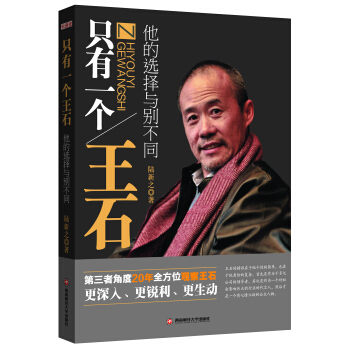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清朝会试共举行112科(正科84、加科2、恩科26),录取进士两万余名(不包括武科进士),然而现存各种“题名碑录”还有大量的问题,如姓氏错误、人名错误、籍贯错误及遗漏未收等情况,至今也没有学者对此作一番系统之整理。此次编纂校订,作者以《国朝进士题名碑录》为底本,然后根据国子监所刻题名碑的全部拓本、各种履历表齿录如《清代朱卷集成》、地方志中的“选举志”、专题文献如《词林辑略》《清秘述闻》以及相关传记史料如行状、墓志、年谱、家谱、档案等文献中的有关内容,逐一校核,隶定正确的人物资料,凡有异同,写出校记。《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下)》分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按科年著录清朝全部进士,未参加当年殿试者附于相应科年之后。每一进士为一条,依次注明籍贯、甲第、名次,有关考证资料附于相应科年后。第二部分为《人名索引》,将书中所有进士按四角号码编制索引,查检方便。《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下)》横排繁体字。
目录
上册清朝进士题名文献概述
凡例
清朝进士题名录
顺治三年丙戌科(1646)
顺治四年丁亥科(1647)
顺治六年己丑科(1649)
顺治九年壬辰科(1652)
顺治九年策试满洲进士壬辰科(1652)
顺治十二年乙未科(1655)
顺治十二年策试满洲进士乙未科(1655)
顺治十五年戊戌科(1658)
顺治十六年己亥科(1659)
顺治十八年辛丑科(1661)
康熙三年甲辰科(1664)
康熙六年丁未科(1667)
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
康熙十二年癸丑科(1673)
康熙十五年丙辰科(1676)
康熙十八年己未科(1679)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1682)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科(1685)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1688)
康熙三十年辛未科(1691)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1694)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1697)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1700)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1703)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1706)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1709)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1712)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1713)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1715)
……
中册
下册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清朝进士题名录(套装全3册)》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我总觉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奋斗、关于荣耀、关于命运的故事。我想象着,当年那些被选中的学子,他们是何等意气风发,他们的人生将由此发生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本书,就像是一面照妖镜,映照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映照出知识阶层在整个国家机器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希望能够通过阅读它,去了解清朝官员的选拔机制,去探究不同朝代、不同时期,进士的数量和质量有何变化,甚至去揣测那些榜上有名者,他们的仕途之路是否都一帆风顺。它不仅仅是一份名单,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研究数据库。我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对这些名字进行深入的家族谱系梳理,是否能发现一些关于中国古代大家族发展的线索?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充满魅力的挑战,一份引人入胜的历史侦探游戏。
评分看到《清朝进士题名录(套装全3册)》这个书名,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无数个生动的画面。想象一下,在那个等级森严、文风鼎盛的时代,多少寒窗苦读的学子,在考场上挥汗如雨,只为金榜题名,光耀门楣。这套书,就像是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那些被镌刻在功名簿上的名字,以及他们背后可能隐藏的传奇故事。我不禁要问,在这厚重的卷册中,有多少名字最终成为了叱咤风云的大臣,又有多少默默无闻,却也曾饱读诗书,怀揣着对国家社会的理想?我尤其好奇,那些在科举制度下,出身寒微却能凭借才学跃升至高位的“寒门贵子”,他们的经历又是如何?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份客观的记录,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解读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流动、人才选拔机制的独特视角。它让我开始思考,在那个讲究“学而优则仕”的年代,知识与权力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而科举制度本身,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塑造了怎样的社会风貌。这本书,简直就是一座宝藏,等待着我去一点一点地挖掘,去感受历史的温度,去体味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
评分当我得知有《清朝进士题名录(套装全3册)》的存在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它有多么详实和珍贵。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情有独钟,觉得它既是那个时代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也承载了无数人的梦想与命运。这套书,无疑是研究这一制度最直接、最权威的资料之一。我想要知道,这3000多位进士,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的家庭背景如何?他们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巅峰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如果能够深入研究其中的一些人物,挖掘他们的传记,对照他们的科举经历,是否能描绘出更加生动、立体的人物画像?这本书的价值,绝不仅仅停留在“名单”层面,它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网络的缩影,是连接着个人命运与国家政治的纽带。我尤其期待,通过对这些进士的籍贯、年龄、考中年份等信息的分析,能否发现一些有趣的、不为人知的规律?它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期待,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历史迷宫,等着我去探索其中的奥秘。
评分读到《清朝进士题名录(套装全3册)》这个书名,我便立刻想到了那个曾经辉煌而又复杂的清朝。对于我这样一个历史爱好者来说,这份名录简直就像是一座宝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它,去看看那些曾经的名字,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我尤其好奇,在漫长的清朝历史中,哪些年份的进士数量最多?哪些地区涌现出的进士最多?这些进士最终都担任了什么样的官职?他们的命运又如何?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份冰冷的名单,它更像是一张巨大的社会网,连接着无数个家族、无数段人生。我希望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有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比如,在哪个时期,科举考试的竞争最为激烈?哪些家族能够长期在科举中占据优势?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和理解清朝的政治生态、社会结构,甚至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变迁。它不仅仅是历史事实的堆砌,更是解读历史、理解人生的钥匙。
评分这套《清朝进士题名录(套装全3册)》的出现,让我觉得仿佛触碰到了历史的脉搏。它不仅仅是一份名录,更是一份沉甸甸的集体记忆。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名字代表着什么?是家族的荣耀,是个人奋斗的结晶,还是国家机器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脑海中会不自觉地勾勒出这些进士们的人生轨迹:他们或许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仕途;他们或许在朝堂之上,与同僚们唇枪舌剑,为国事操劳;他们或许也曾经历过政治的风波,宦海沉浮,最终归于平静。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研究清朝社会结构、官员任职体系、甚至是民间家族发展史的绝佳素材。我甚至可以想象,通过对比不同年份、不同省份的进士名录,去分析当时的人才分布、地域差异,以及政策对教育和仕途的影响。它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清朝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大门。读这样一本书,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更需要一份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一份想要深入探究的求知欲。
评分活泼开朗、乐观向上、兴趣广泛、适应
评分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品学兼优,连续三年获得学院奖学金。
评分中国古代虽无“文献学”一词,但许多学者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进行了大量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历代文献收藏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中国古代文献研究的情况来看,其内涵比较广泛,除研究一般的文献发展史外,还涉及文字的校订,版本的鉴别,对内容得失的评品及目录的编制等。如汉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制《别录》、《七略》是整理文献;郑玄为群经作注,也属整理文献。最早以专著形式系统讨论文献学的是南宋的郑樵。他在《通志·校雠略》中从理论上阐述了文献工作中的文献收集、鉴别真伪、分类编目、流通利用等问题。郑樵以后,系统研究文献学理论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著名观点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要求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要明确反映并细致剖析各种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相互关系等。但他和郑樵一样,都把这些工作称为“校雠学”。最早以“文献学”作为书名的著作是郑鹤声、郑鹤春合著的《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书中认为: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是文献的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和刻印。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1982)和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1986)则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专著,二书认为文献学就是版本学、校勘学(见校雠学)和目录学三者的结合。其中张舜徽还认为文献学就是校雠学。由于“文献” 这一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特定涵义,所以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献学实际上是以考证典籍源流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由于文献数量、内容、形式和载体的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文献工作的复杂性,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文献的实际和揭示其发展规律。因此,作为现代文献学,还必须研究现代文献及其规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文献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计量学方法,丰富了文献学的内容。80年代中期以后,专科文献学受到重视,专科文献检索与利用方面的著述大量问世。
评分百年后有价之书宜藏, 两三年寿命之书宜借, 明星传记宜在书店站着翻, 朋友送书宜收不宜看, 自己赶职称之书宜扔不宜送。 读论语宜曲阜音, 读孟子宜滕州调, 读老庄宜河南腔。 林中宜读王维, 舟中宜读曾祺。 读陆游宜舞剑, 读黄裳宜听戏。 读老夫子杂文宜佐辣, 读小女人随笔宜蘸醋。 读丰子恺宜饮花雕, 读梁实秋宜饮咖啡。 办公室宜读参考消息, 卫生间宜读地摊小报, 出差途中宜读武侠小说。 读李白宜长啸, 读杜甫宜泪流。 春读雪莱,夏读拜伦。 秋读波德莱尔, 冬读艾略特。 读美国书宜随随便便, 读德国书宜正正经经。 读法国书宜情感丰沛, 读俄国书宜思虑清淅。 哪个男子不钟情, 哪个女子不怀春。 晨与妻子宜读纪伯伦, 暮与情人宜读泰戈尔。 少年恋爱读《维特》, 中年情外读《廊桥》, 老年多情读《歌德传》。 读莱蒙托夫要喝酒, 读海涅宜高歌。 读海明威宜舞剑, 读卡夫卡宜流泪。 读雨果宜沉思, 读凡高须流血。 黑格尔宜读精要, 尼采宜诵全文。 大仲马宜一目十行, 昆德拉宜反复回味。 读茨威格宜一气呵成, 并马上重读一遍, 读陀氏宜心智平衡, 并每三年读一遍。 忙里偷闲略读华莱士`, 闲来无事细读托翁。 催眠宜读海德格尔, 失眠宜读福尔摩斯。 讲课前宜读培根, 讲演前宜读沙翁。 峰会前宜读杜拉克, 总结后宜读韦尔奇。 回首往事宜读《忏悔录》, 展望未来宜读托夫勒。 研究世界文明宜读亨廷顿, 反思中国精神宜读费正清。 历史入门宜读汤因比, 哲学入门宜罗素。 艺术入门宜读丹纳, 文学评论入门宜读韦克勒, 美学入门宜读鲍葵尔, 戏剧入门宜读布莱希特, 经济入门必须读凯恩斯, 军事入门宜读《战争论》, 计算机入门宜读比尔。盖茨。 了解资本主义宜读布罗代尔。 解剖自我宜读弗罗依德, 磋磨他人宜读弗洛姆。 分析群体宜读荣格, 现代禅学宜读铃木大拙, 认知人类宜读列维。斯特劳斯。 受伤后读毛姆, 得意处读惠特曼。 忧郁时读川端康成, 寂寞时读《鲁宾逊》。 清理思路宜读维特根斯坦, 智力训练宜读波普尔。 玄之又玄读胡塞尔, 清之又清读德里达。 如想做世界第七读《相对论》, 爱因斯坦说:懂得它的只有六人。 如还不满意,宜读霍金。 如想试试能否成为作家,宜读《百年孤独》。 两种结论:一是“我也能这么写”, 一是 “算了,让老马独步”。 与女学生谈话,宜谈《简爱》, 如她不知,正好讲与她听,以示多情; 与男青年谈话,宜谈希罗多德, 这是唯一机会,以炫博学。 三岁宜读拼音, 十岁宜读西游, 二十宜读红楼, 三十宜读水浒, 四十宜读金瓶, 五十宜读三国, 六十宜读六记。
评分活泼开朗、乐观向上、兴趣广泛、适应
评分2
评分百年后有价之书宜藏, 两三年寿命之书宜借, 明星传记宜在书店站着翻, 朋友送书宜收不宜看, 自己赶职称之书宜扔不宜送。 读论语宜曲阜音, 读孟子宜滕州调, 读老庄宜河南腔。 林中宜读王维, 舟中宜读曾祺。 读陆游宜舞剑, 读黄裳宜听戏。 读老夫子杂文宜佐辣, 读小女人随笔宜蘸醋。 读丰子恺宜饮花雕, 读梁实秋宜饮咖啡。 办公室宜读参考消息, 卫生间宜读地摊小报, 出差途中宜读武侠小说。 读李白宜长啸, 读杜甫宜泪流。 春读雪莱,夏读拜伦。 秋读波德莱尔, 冬读艾略特。 读美国书宜随随便便, 读德国书宜正正经经。 读法国书宜情感丰沛, 读俄国书宜思虑清淅。 哪个男子不钟情, 哪个女子不怀春。 晨与妻子宜读纪伯伦, 暮与情人宜读泰戈尔。 少年恋爱读《维特》, 中年情外读《廊桥》, 老年多情读《歌德传》。 读莱蒙托夫要喝酒, 读海涅宜高歌。 读海明威宜舞剑, 读卡夫卡宜流泪。 读雨果宜沉思, 读凡高须流血。 黑格尔宜读精要, 尼采宜诵全文。 大仲马宜一目十行, 昆德拉宜反复回味。 读茨威格宜一气呵成, 并马上重读一遍, 读陀氏宜心智平衡, 并每三年读一遍。 忙里偷闲略读华莱士`, 闲来无事细读托翁。 催眠宜读海德格尔, 失眠宜读福尔摩斯。 讲课前宜读培根, 讲演前宜读沙翁。 峰会前宜读杜拉克, 总结后宜读韦尔奇。 回首往事宜读《忏悔录》, 展望未来宜读托夫勒。 研究世界文明宜读亨廷顿, 反思中国精神宜读费正清。 历史入门宜读汤因比, 哲学入门宜罗素。 艺术入门宜读丹纳, 文学评论入门宜读韦克勒, 美学入门宜读鲍葵尔, 戏剧入门宜读布莱希特, 经济入门必须读凯恩斯, 军事入门宜读《战争论》, 计算机入门宜读比尔。盖茨。 了解资本主义宜读布罗代尔。 解剖自我宜读弗罗依德, 磋磨他人宜读弗洛姆。 分析群体宜读荣格, 现代禅学宜读铃木大拙, 认知人类宜读列维。斯特劳斯。 受伤后读毛姆, 得意处读惠特曼。 忧郁时读川端康成, 寂寞时读《鲁宾逊》。 清理思路宜读维特根斯坦, 智力训练宜读波普尔。 玄之又玄读胡塞尔, 清之又清读德里达。 如想做世界第七读《相对论》, 爱因斯坦说:懂得它的只有六人。 如还不满意,宜读霍金。 如想试试能否成为作家,宜读《百年孤独》。 两种结论:一是“我也能这么写”, 一是 “算了,让老马独步”。 与女学生谈话,宜谈《简爱》, 如她不知,正好讲与她听,以示多情; 与男青年谈话,宜谈希罗多德, 这是唯一机会,以炫博学。 三岁宜读拼音, 十岁宜读西游, 二十宜读红楼, 三十宜读水浒, 四十宜读金瓶, 五十宜读三国, 六十宜读六记。
评分清朝会试共举行112科(正科84、加科2、恩科26),录取进士两万余名(不包括武科进士),然而现存各种“题名碑录”还有大量的问题,如姓氏错误、人名错误、籍贯错误及遗漏未收等情况,至今也没有学者对此作一番系统之整理。此次编纂校订,作者以《国朝进士题名碑录》为底本,然后根据国子监所刻题名碑的全部拓本、各种履历表齿录如《清代朱卷集成》、地方志中的“选举志”、专题文献如《词林辑略》《清秘述闻》以及相关传记史料如行状、墓志、年谱、家谱、档案等文献中的有关内容,逐一校核,隶定正确的人物资料,凡有异同,写出校记。《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下)》分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按科年著录清朝全部进士,未参加当年殿试者附于相应科年之后。每一进士为一条,依次注明籍贯、甲第、名次,有关考证资料附于相应科年后。第二部分为《人名索引》,将书中所有进士按四角号码编制索引,查检方便。《清朝进士题名录(上中下)》横排繁体字。此书很好,值得购买。
评分这本书可以与其他工具书配合使用,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