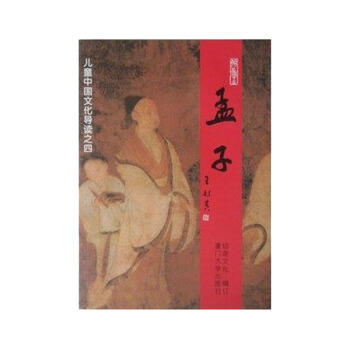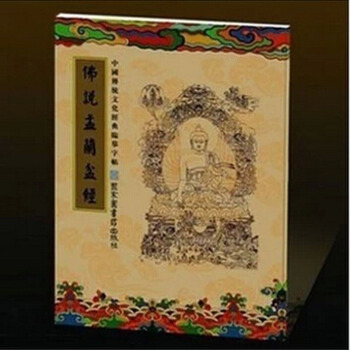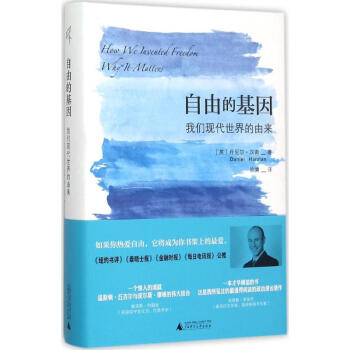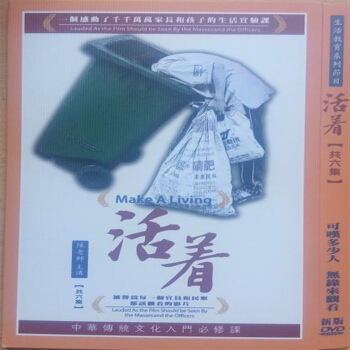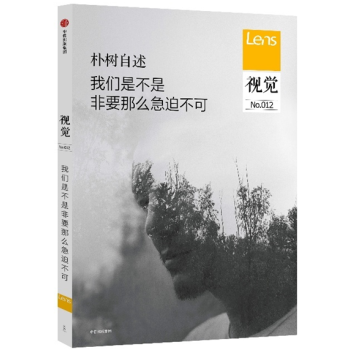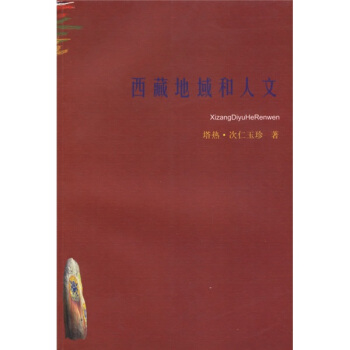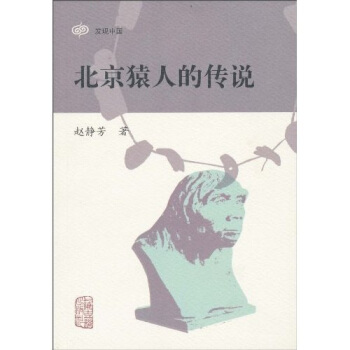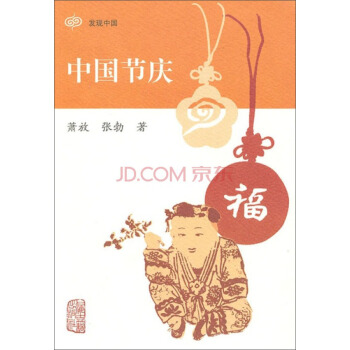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思享家丛书:草色连云》是知名作家高尔泰最新力作,《重返家园》后唯一一部新作。一针见血,锋芒毕露,尽显高式风格像一幅画卷:一个旅美学者对自己生命和文学艺术的深刻感悟,一个作家对生存的反思,一个典型“右派”的文革回忆……内容简介
《草色连云》是高尔泰先生的散文随笔集,内容涉猎丰富,有对历史的真实回忆,有对人性的深层揭示,也有对灵魂的深度挖掘。他用文字还原了许多琐碎小事和日常感觉,也丰富了大历史。其文充满了生命的真诚与情感的赤诚,以及时代的沧桑感,随时随地能引发读者的共鸣,触动读者的情感。作者简介
高尔泰,著名美学家、画家、作家,旅美学者。1935年生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早年就读于江苏师范学院美术系,后因发表《论美》被打成右派,发往夹边沟,睹尽人间酷烈事,劫后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任职,后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兰州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处工作。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著有《寻找家园》、《美是自由的象征》等。目录
隔膜山路崎岖
佛缘
馀生偶记
白头有约
吕无咎先生
纪念洪毅然先生
弱者的胜利
跨越代沟
文盲的悲哀
哪敢论清白
陈迹飘零读故宫
从敦煌经变说起
在场主义文学奖答谢辞
艺术与人文
寻找家园,就是寻找意义
山路崎岖
佛缘
馀生偶记
白头有约
吕无咎先生
纪念洪毅然先生
弱者的胜利
跨越代沟
文盲的悲哀
哪敢论清白
陈迹飘零读故宫
从敦煌经变说起
在场主义文学奖答谢辞
艺术与人文
寻找家园,就是寻找意义
前言
我这辈子,和沙漠有缘。青年夹边沟,中年敦煌,晚年拉斯维加斯。
拉城是沙漠中的华都,万紫千红相幻,纸醉金迷。就精神生活而言,单一唯物一如城外风景。
收入本书的文字,都是在这个双重沙漠中写的。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麻黄、骆驼刺、仙人掌,或者芨芨草,在连天砂石中渺小。
渺小,惨淡,但绿着。绿是普世草色,故起“连云”之想。
精彩书摘
隔膜百年人生,有许多维度,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有许多空洞。比如在时间这个维度上,一场“反右”挖掉你二十年,一场“文革”挖掉你十年,算是大空洞。一场感冒挖掉你一星期,一次塞车挖掉你半小时,算是小空洞。有些维度无名,但是都有空洞。有的空洞大到无边,这个维度就算没了。
没了这个维度,还有别的维度,还有人生。维度欠缺的人生,不一定是没有价值的人生。瞎子阿炳的琴声,是人类文化的珍品。活在轮椅上说不出话的霍金,是科学界无与伦比的巨星。虽如此,毕竟遗恨。
平凡微贱如我辈,生存努力的成败得失之外,也有思想感情、性格倾向和人生体验的维度。这些主观维度,同样有其空洞。其中之一,就是隔膜。未进入意识的、意识到了跨不过去的,和事后发现已成心殇的隔膜之洞,多到不可言说。这里略说数则,不辞挂一漏万。
一、知更鸟飞走了
刚搬到新泽西海边那栋老旧小屋时,我在廊檐下栽了一株忍冬。长得极快,几年就爬上和覆盖了大片屋顶。纵横交错的藤蔓枝叶,从栏杆到屋檐织成了一幅帷幕。春夏之交,花期很长,老远都闻得见清淡的幽香。
那年在廊檐下,发现了一个知更鸟的窝,很精致。里面有两个橄榄大小的蛋,翠绿色,点缀着一些大小不同带着金色的黑点,很美。经常地,有一只鸟在里面孵蛋,另一只鸟出去找吃食,时不时回来喂它。有时候也一起飞走,丢下两只蛋,在春天的阳光里晒着。我们非常庆幸,有了这两个可爱的邻居。
不幸的是,这个窝的位置,恰恰在廊檐的正下方。一旦下雨,檐溜如注,纵不冲散,也会泡烂,更不用说在里面孵蛋了。海边林带,多风多雨,迟早要来。我趁它们不在,把鸟窝所在的那一丛藤蔓,稍稍拉了一拉,绑在靠里面的粗枝上。鸟窝离开了廊檐,大约三公分左右。
我干得非常小心,枝叶的向背,都力求保持原样。鸟窝端正稳当如初,连里面的蛋,都没有丝毫滚动。
但是鸟儿回来,不像往常那样直接飞进窝里,而是停在离窝不远的枝丫上,侧着头朝窝里看。一忽儿跳上另一根枝丫,从另一边侧着头朝窝里看,看一看窝里,又看一看四边。显然是发现了变化,相信变化就是危险。就这样,两只小鸟绕着窝,上下左右跳跃,很久很久,都不敢进去。
终于,呼啦一声,同时飞走了。从此没再回来。
记得有谁,好像是尼采说过,信仰掩盖真理,有甚于谎言。如果世俗一些,把迷信、成见、经验主义之类都纳入广义的信仰范畴,起码这两只鸟儿,还有我,可以为此做证。
二、爱之罪
我小时候,视父亲比母亲更亲。原因是,我怕管。比如不洗脚不准上床上了床要揪着耳朵拽下来洗的是母亲;带我出去登山穿林爬树游泳擦破了衣服皮肤说没关系它自己会好的是父亲。后来上村学,父亲是校长又是教师,教我和别的孩子读书,严格而有耐心。爱之外,加上敬。我因他而自豪。
家乡解放时,我上初中二年级。因为喜欢山野,假期里常到山乡去玩。“山乡”是湖那边深山老林里的一些小村,抗战时期我们家曾在其中一个村里避难,一住八年,满村乡亲。
那次我去,村里在“土改”,来了些外地人。其中一个,我认识,叫刘法言,是我在县立中学上学时的学长。比我高两班,大十几岁。我常和他同打篮球。他人高马大,我却能抢得到他的球,总觉得他大而无当,很是瞧不起。后来我留级,他毕业,没再见过。
村里见了,他很热情。笑着迎过来,说我长高了。说那时只到我这里(指胸口),现在到我这里了(指下巴)。问高老师(我父亲)好吗?又说见了你爸,代我问个好。我说,嗯。心里纳闷儿:他来干吗?
回到家里,在饭桌上随便地说到,看见刘法言了。不料父亲一听,显出紧张恐惧的神色。放低了声音,鬼祟地问道,他的态度,怎么样啊?
这表情和声音,使我感到羞辱,气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没觉得我的反应,小心翼翼地又问,他同你,说话了吗?
我不答,他又问,说什么了吗?
我更气了,粗暴地说,没说什么。放下碗筷,跑出去了。
母亲和二姐追出来,一把抓住我,恶狠狠地说,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我们家在山乡有五亩半地,出租,要是被划为地主,不得了啊。我还在气头上,说,“有什么不得了的”,扭头就走。母亲又一把抓住,说,刘法言是土改工作队队长,他说什么了?你倒是说呀。
我不说,姐姐捧住我的脸,问,是不是教你要划清阶级界限了?
我大叫道,见鬼了!挣脱,跑掉。
几十天后,消息传来,山乡划成分,我们家是“小土地出租”。全家庆幸,很是欢喜。但是一年后,城里搞土改,父亲还是被弄成了地主,后来又加上“右派”,批斗劳改惨死——他怕得有理。
三、无赖的盛宴
当年在外地上学,想家想得要命,不敢回去。毕业后当了“右派”,不能回去。一别十几年,很少通信。来往信件,都要经过检查。为了安全,也为了不让对方担心,信上互相都说,自己一切很好。
十几年后第一次回家省亲,家中已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
一个“地主婆”,一个“右派”。给鱼行剖鱼,给工程队削旧砖头……都是脏活累活,时受训斥。工资是象征性的,几近于无。
上工前,收工后,她们在后院种了些瓜菜、养了些鸡鸭,贴补生活。但又舍不得吃,粗茶淡饭,一点儿一点儿地省下,晒干留着,等我回来。
在我到达以前,她们清理和修补了两间老旧小屋,收拾得干净整齐。回到家里,看见窗明几净,地板光亮。床底下满坛满罐的黄豆蚕豆红豆青豆花生芝麻,屋梁上悬挂着腌鱼腊肉和风干的鸡鸭,很宽慰。说,看到你们过得这样好,我在外面也就放心了!
短短一个月假期,我把她们所有的储存,包括几只养着下蛋的鸡鸭,都吃得精光。吃着,感觉到她们看我吃东西的快乐,有甚于她们自己吃东西的快乐。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让她们如此快乐。
走的时候,我容光焕发。想都没想过,我把家里吃空了。她们俩又将从零开始,重新苦巴巴地,对付那饥饿残酷的年代。居然一直没想,直到母亲过世30多年、二姐也已经85岁的现在。
人在美国,很偶然地,和小雨说起那一段往事。小雨狠狠骂了我一顿。说我没心没肺,简直像个无赖。说你怎么就没想到,那是她们多少年来,一点儿一点儿从自己嘴里克扣下来的积蓄?怎么就没想到,要给她们留下一些?还心安理得?!还乐?!
四、田园诗的境界
老家的住房被没收后,院子变成了繁忙的砂石公路,从留给母亲和二姐居住的两间原先堆放杂物的老屋门前通过。
老屋全天候笼罩在卡车拖拉机的烟尘轰响里。沿路家家如此,日久习以为常。“文革”后期,有些人家还在门口摆个煤炉,卖起茶水茶叶蛋来。常有运煤的车子经过,一跳一跳的,撒落下一路煤块,大家抢着捡,欢乐紧张。交通局要拓宽马路,没人搬迁,似乎很愿意这样下去。
二姐早已被下放农村。为了照顾母亲、我的孩子高林和她的两个孩子能够上学,回来和母亲同住。被人指控为“黑人黑户”,要她回农村去。除了交通局的动员拆迁,还有派出所、居委会时不时地上门驱赶。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五七干校,每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假期里,在车声市声烟尘的旋涡里同各路人马纠缠,紧张得天旋地转。直到回了西北,才能松一口气。
但是一想到家里那样,总是揪心。再次回去,到二姐的下放地秦溪去了一下。是一个湖边小村,蓼屿荻花掩映,洲头竹篱茅舍。给二姐的草屋,位在一条长满老杨柳树的防波堤上,原是放舴艋舢板的公屋。为安置下放人员,清空了隔为互通三间,盘了炉灶,架了床,颇整齐。树甚粗壮,有的长在堤上,有的长在堤岸,有的长在堤岸下芦苇丛生、菰蒲杂乱的水中,弯曲横斜。
透过绿色的喧哗,看湖上白鸟追飞,我斩钉截铁地想,这才是人住的地方。回去后,力劝母亲二姐搬到这里居住。加上外界的压力,她们终于依了我,从交通局手里,接下二百块钱的拆迁费。邻居都说太少,我说这个亏吃得值得。那时年轻力壮,搬家举重若轻。用得着的东西,连同十来块搬得动的青石板,加上老小六口,一船运到了秦溪。
下放劳动的岁月,学会了一点儿做泥活和木活的手艺,斧头菜刀对付着,加固了墙壁门窗,平整了内外地面。在通往水边的斜坡上,砌了十几级石板台阶,以便潮涨潮落,都可以淘米洗菜。母亲和二姐收拾家里,孩子们也帮了大忙。村上人很热情,送来各种菜苗,还就近选了一块阳光充足的地面,帮开垦出来种上,算是队里给的自留地,异常肥沃……安顿刚就绪,假期就完了。
上路时十分疲劳,但是欢喜安心。翌夏省亲,下车时大风大雨,叫不到船。赤脚打伞,冒雨上路。湖堤上泥泞深滑,伞一闪就飞了。背包浸透,贼沉。湖上白茫茫一片,浪打石堤,飞溅如鞭。十几里路,走了半天,到家已是深夜。
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她说村学很少上课,孩子们还是得到城里上学。在城郊租了一间农舍,二姐在那边照看。母亲在这边,养了一只狗,一群鸡鸭鹅。狗叫阿年,母亲说它懂话,她常和它说话。过几天放暑假,路也干了,他们回来了,带你过去看看。
那些年我严重失眠,百药无效。回到母亲身边,竟天天睡得很香。长夏江村,万树鸣蝉。搬张小桌子,拖两把竹椅,在浓荫下一起喝茶,恍如梦寐。来自湖上的清风,带着荷叶的清香和菱花的微腥,闻着闻着就想沉沉入睡。偶尔也说些很小的事情,某一天阿年的表现之类。阿年躺在母亲脚边,在提到它的名字时,抬起头摇几下尾巴。
火红的年代,人们活得潦草疲累。从那股铁流中出来,面对这份清寂祥和,有太虚幻境之感,一再说这里真好。母亲说你这是三天新鲜,天天这样就会烦。我问她是不是烦了,她说没有,这里很好。二姐带孩子们回来,明显黑了瘦了,也说这里很好。
但是童言无忌,同孩子们奔跑、游泳,把他们无心提到的许多零碎小事拼凑起来,才知道我的荒谬,给大家带来了多大的灾难。
母亲的户口和高林的临时户口都在淳溪镇,农村不供应口粮。二姐每个月要拿着她们的户口本,到淳溪镇粮站,按照配额买了粮食和煤球挑回来。二姐一家三口是农村户口,队里给的工分粮是稻子,得挑到公社加工厂,舂成米再挑回来。从城郊到学校很远,孩子们上学,得起早摸黑。午饭自己带。高林最小,跟着跑,每逢下雨,常要滑倒。有好几次,到家时像个泥人。
二姐那边照顾孩子们,这边还要照顾母亲。隔几天必来一次秦溪,把水缸挑满,把马桶倒净,从阁楼上取下烧饭用的稻草,到自留地采来足够的蔬菜……匆匆再回去给孩子们做饭。来回二十几里,无辞顶风冒雨。
母亲年近八十,独住村野。没人说话,时或同阿年念叨,赢得摇几下尾巴。门外只两丈平地,然后就斜下去直到水边。有苇茬处扎脚,没苇茬处滑溜。虽有石板台阶,日久生苔,仍很难走。每天,她颤巍巍拄着藤杖,下到水边淘米、洗菜、唤鸭,都特别特别小心。最是黑夜里起夜,更加小心,生怕摔倒了,起不来,没人扶。
小时候,母亲常笑说,父亲是书呆子。我相信她必然认为,我也是书呆子。
在母亲艰难的一生中,心甘情愿地,吃够了父亲和我,两个书呆子的苦。但她从不抱怨,也从不说苦。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安心。
在母亲去世很多年以后,我垂老忆旧,才猛然惊觉,自己的罪孽,有多么深重。
……
用户评价
《思享家系列第四辑:草色连云》这个书名,让我感觉非常亲切。它不像是一些过于晦涩或生僻的书名,而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自然的美感。“草色连云”,这不正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一种与天地万物相连接的和谐景象吗?我一直很欣赏《思享家系列》的选书眼光,总是能发掘出那些能够引发思考,带来启发的作品。中信出版社的名字,也足以证明这本书在内容和装帧上的高品质。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一种舒缓而深刻的阅读体验,让我在其中找到一种心灵的慰藉,一种思想的滋养。我希望它能够像春天的草一样,一点点滋长,然后在我的脑海中凝聚成像云朵一样的广阔思考。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通过文字,将这种“草色连云”的意境,转化为深刻的思想,并最终触动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评分当我看到《思享家系列第四辑:草色连云》时,我的心立刻被这个名字所吸引。它勾勒出了一幅壮丽而又宁静的画面,仿佛能将人带入一个辽阔的世界。“草色连云”,这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更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象征。它或许代表着一种广阔的胸怀,一种对生命无限可能性的探索,又或许是一种随遇而安的洒脱,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我一直是《思享家系列》的忠实粉丝,这个系列总是能够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火花。中信出版社的名字,更是让我对这本书的品质有了信心。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春天蓬勃的草木一样,在我心中激起思想的涟漪,又像无边无际的云朵一样,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记。我希望它能够带给我深刻的启示,让我能够以更成熟、更智慧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让我心生向往。“思享家系列”本身就带有了一种探索精神和思想深度,而“草色连云”这个副标题,更是赋予了它一种诗意和辽远的意境。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样一幅画面:绿意盎然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天边,与连绵的云朵融为一体,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也蕴含着一种无垠的思考空间。中信出版社作为国内优秀的出版机构,其出版的书籍向来质量上乘,内容精良,这让我对这本书的期待值又提高了不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像它名字所描绘的那样,为我带来思想上的滋养,让我能够在这片“草色连云”的文字世界里,获得片刻的宁静与启迪。我渴望它能够带给我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以更开阔的眼界去审视生活,去感悟生命的意义。
评分这本书的出现,对我来说,就像是久旱逢甘霖。我最近一直处于一种比较迷茫的状态,感觉生活就像一潭死水,缺乏波澜,也缺乏动力。偶然间看到了《思享家系列第四辑:草色连云》这本书,名字就很有意思。“草色连云”,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种生机勃勃、无边无际的景象,仿佛一切都有可能,充满希望。我一直认为,阅读是最好的充电方式,而“思享家系列”更是我心中的宝藏。这个系列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每一本书都像是心灵的鸡汤,又像是思想的启迪。中信出版社的名字也让我对这本书的品质有了十足的信心。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像春草一样,在我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让我重新感受到生命的活力。我希望它能够带我走出迷茫,看到更广阔的天地,就像那连绵的云朵一样,包容万象。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草色连云”这种意象,融入到深刻的思想之中,又是如何用文字,点燃我内心的激情,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宁静致远的感觉。“草色连云”,这不仅仅是自然的描绘,更是一种心境的写照。我常常在想,生活究竟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思享家系列》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挖掘那些触及灵魂的思考,而“草色连云”这个意象,恰好传递出一种辽阔、包容,但又不失细腻的哲学韵味。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缕清风,拂去我内心的尘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生活。中信出版社的书籍,我一直都很信任,他们的出版物往往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和严谨的学术态度,相信《草色连云》也不会例外。我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以更开阔的胸怀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我更希望,它能够像连绵的云朵一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让我时常回味,从中汲取力量。我期待着,能够在这本书中,找到那些能够引领我走向更深刻思考的火花。
评分刚看到《思享家系列第四辑:草色连云》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立刻闪过一幅画面:春天里,嫩绿的草色一直延伸到远方的云层,那种生机勃勃、无边无际的感觉扑面而来。我一直很喜欢“思享家”这个名字,因为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对思想的追求和分享,而“草色连云”这个副标题,更是增添了几分诗意和哲学色彩。我常常在想,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应该像这草色一样,充满生机,又像云朵一样,能够包容一切,不断向前?中信出版社的质量,我一直都很信赖,他们出版的书籍,往往都充满了智慧和深度。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一些新的启发,一些关于生活,关于人生的感悟。我希望它能够像春风一样,吹拂我的心灵,让我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和希望。我希望它能够像连绵的云朵一样,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让我在日后的生活中,能够不断地回味和思考。
评分一直以来,我都是《思享家系列》的忠实读者,这个系列总是能够带给我不同于寻常的阅读体验。这次的第四辑,名为《草色连云》,光是这个名字,就足够让我心生向往。在我看来,“草色连云”不仅仅是一种自然景象,更是一种境界,一种开阔、绵延、生生不息的意境。它仿佛在诉说着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一种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我非常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进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空间,让我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思考不一样的哲学。中信出版社作为国内知名的出版社,其出版的书籍一向以品质精良、内容深刻而著称,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对这本书的信心。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像它名字所描绘的那样,为我带来一片思想的绿洲,让我的心灵在其中得到滋养和升华。我希望它能够像春天的草芽一样,坚韧而充满生命力,又像悠远的云朵一样,能够容纳百川,包容万物。我渴望在这本书中,找到一些能够改变我思维方式、提升我人生境界的内容。
评分我一直对《思享家系列》情有独钟,这个系列总是能够触及到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引发我最深刻的思考。《思享家系列第四辑:草色连云》这个名字,更是让我眼前一亮。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那种广袤无垠的绿色,一直延伸到与天相接的云层,充满了生命的张力和诗意的想象。“草色连云”,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景象,更是一种人生哲学的隐喻,它象征着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一种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中信出版社的名字,也为这本书增添了品质的保证。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春天的草一样,在我心中播下思想的种子,然后像云朵一样,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记。我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以更广阔的胸怀去理解世界,去感悟生活。我渴望在这本书中,找到那些能够启迪我心灵,让我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积极向上的智慧。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足够吸引我了,那种淡淡的青绿色调,带着一丝朦胧的质感,仿佛真的能将人带入“草色连云”的意境之中。拿到书的那一刻,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仿佛遇到了久违的老友。我一直对“思享家系列”很感兴趣,这个系列总能发掘出一些触动人心的思想火花,而第四辑的这个名字,更是让我充满期待。我常常在想,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我们有多少时间能够停下来,去感受身边的美好?有多少时间能够静下心来,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草色连云”这个意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广阔与深邃,既有自然的生机盎然,又有那种“天连五岭皆兵已,岭南从此不姓李”的壮阔。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看看作者是如何将这份意境融入到文字之中的,是否能够带领我在文字的海洋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与思考的空间。中信出版社的名字也让我对这本书的品质有了初步的信心,他们总是能出版一些有深度、有格调的书籍,相信这次也不会让我失望。我特别期待它能够给我带来一些新的视角,一些能够启发我思考生活、思考世界的新观点。
评分初拿到《思享家系列第四辑:草色连云》时,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幅幅画面:远山如黛,近水含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田园牧歌,或是小桥流水人家,炊烟袅袅的江南水乡。这种联想,源于书名本身所带来的诗意和画面感。我对于“草色连云”的理解,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草木与云彩的相接,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意象。它可能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视野,一种连接天地万物的胸怀,也可能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温柔力量。在我看来,一个好的书名,就如同一个引人入胜的序曲,能够勾起读者无尽的好奇和想象。而《思享家系列》这个名字,本身就带有了一种思想的深度和探索的意愿。我尤其欣赏中信出版社在选择书籍内容和打磨书籍品质上的用心,他们出版的书籍往往都能够引发读者深思,提供有价值的阅读体验。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春日里的嫩草一样,悄悄地滋长,带来勃勃生机,又如同连绵的云朵,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记。我渴望在这本书中,找到关于生活、关于成长、关于人生的智慧,能够帮助我在纷繁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清晰方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