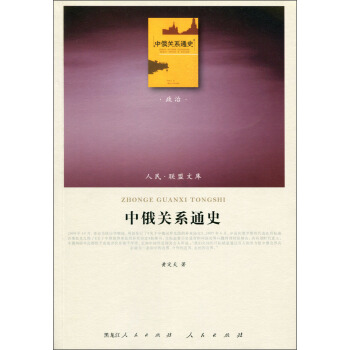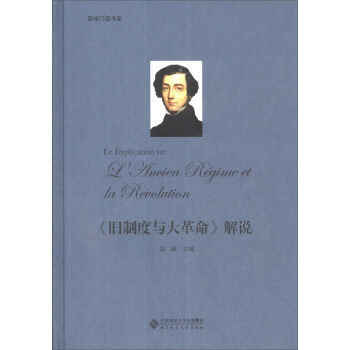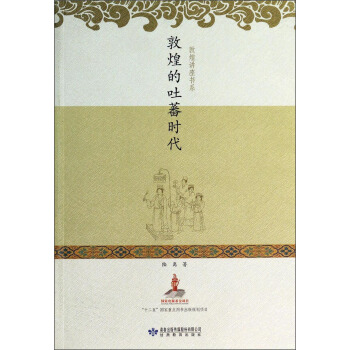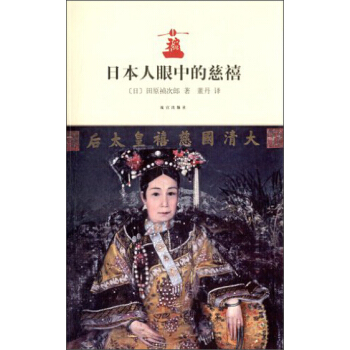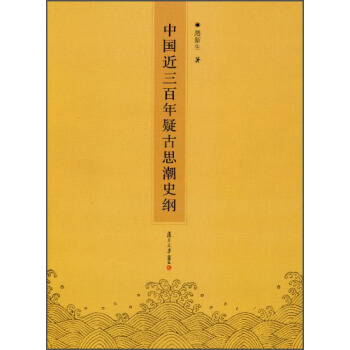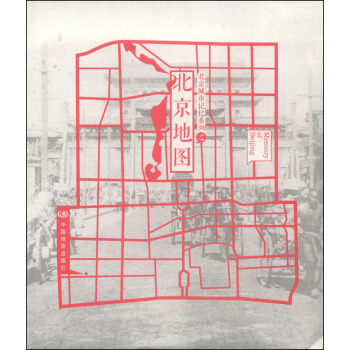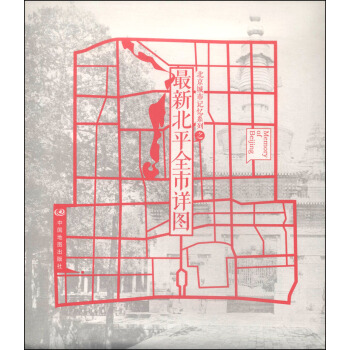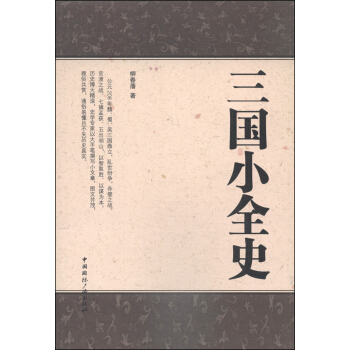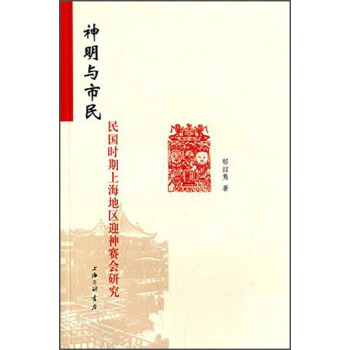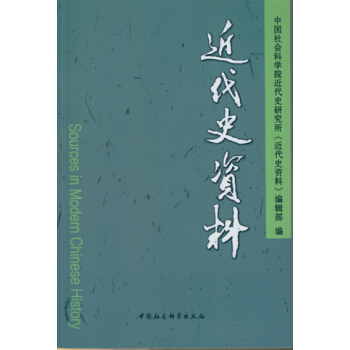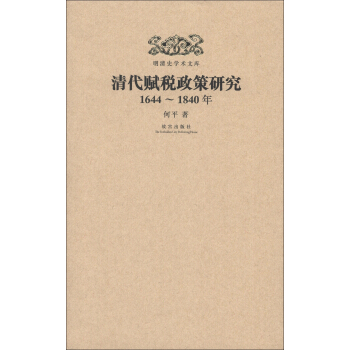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明清史學術文庫:清代賦稅政策研究(1644-1840年)》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清朝政府對田賦地丁的處理方麵。清代財政基本收入包括田賦地丁、關稅、鹽課、雜賦等。在1840年前,雖然田賦地丁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例有下降的趨勢,但它始終是清代財政收入的主體,並且是清政府製定支齣政策的直接依據。在清統治者的眼裏,也是隻把田賦、地丁兩項視為賦稅正項。作者簡介
何平,1965年5月生。湖北省鹹豐縣人。現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貨幣金融係教授,博士生導師。發錶瞭多篇有價值的經濟史和金融理論論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地重大科研項目《現代財政金融理論的中國淵源》等多個項目。2005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支持計劃。2006年獲寶鋼教育基金優秀教師奬。參與的《本碩連讀金融實驗班》教改項目,2005年獲國傢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二等奬。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質量工程第二類特色專業《金融學國際化人纔培養》(2007)和國傢級教學團隊(2008)《金融學國際化人纔培養模式創新教學岡隊》項目工作。2009年9月,參與的教學改革項目《財政金融專業國際性人纔培養模式探索》獲國傢級教學成果二等奬。
2006年11月、2011年11月先後當選海澱區第十四屆、第十五屆人大代錶,兩屆均兼任海澱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委員。
內頁插圖
目錄
再版前言清代財政與貨幣問題研究的新取嚮導言
上篇 滿足經常軍需國用的政策目標
一 原額觀念與政策目標
(一)萬曆原額與軍需籌措
(二)國用已足與錢糧蠲免
(三)整頓財政目標不變
(四)地丁穩定與收入格局
二 賦稅徵解中的三大關係
(一)存留和起運的比例關係
(二)賦稅承擔者之間負擔輕重的關係
(三)賦稅徵收與貨幣幣值變動的關係
中篇(上) 定額化賦稅製度及其缺陷
一 清初賦稅徵收原則的確立
(一)《賦役全書》的編纂與賦稅應徵額的形成
(二)賦役閤一運動與賦稅徵收項目的簡化
二 定額化賦稅製度的建立
(一)“永不加賦”及其內涵
(二)攤丁入地與賦稅的定額化
三 不完全財政與定額化賦稅製度
(一)不完全財政及其錶現
(二)不完全財政與定額化賦稅徵收
(三)不完全財政的危害與養廉銀製度
(四)加派浮收與地丁正項的虧空拖欠
中篇(下) 賦稅日常調整與賦額變動趨勢
一 賦稅調整的類型及原則
(一)賦額調整的類型及原則
(二)賦則的調整及其原則
(三)賦稅調整稅種舉例
二 賦稅調整對賦額變動影響的個案分析——清前期直隸正定府田賦結構及賦額變遷
(一)資料的選擇及研究方法
(二)各州縣田賦結構和賦額變遷
(三)幾點結論
三 全國賦額變遷趨勢與賦稅調整
(一)幾個特殊省份的賦額變遷
(二)全國地丁銀總額的變動趨勢
下篇 賦稅政策的傳導途徑及其製約因素
一 賦稅徵收工具及其變遷
(一)實徵紅簿與徵稅依據
(二)易知由單的行用與停止刊刻
(三)串票(截票)與版串的行用與弊端
(四)滾單催徵與順莊編裏
……
結語
引用書目與參考文獻
後記
明清紀元簡錶
編後說明
精彩書摘
若勻人現在田畝,不惟小民額徵久定未便,一旦加賦,且恐攤派滋擾。伏思丁銀既經勻入地畝,地缺則丁亦並缺,地豁則丁亦當豁”。請求將缺額丁銀特賜豁除,乾隆帝允準。此類丁銀缺額,倘若數額不大,清政府是準許減除的。(3)新墾地畝的丁銀攤派。丁銀攤入地畝,雍正年間各直省是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銀數為基準,根據本地區實行攤丁時的地畝或地糧數的多少分彆攤派。但地畝是有變化的。對新增地畝的丁銀攤派問題,以湖北巡撫陳輝祖在乾隆三十八年所上奏摺為發端,開啓瞭在各直省高級官員間的大討論。
陳輝祖在奏摺中指齣,民屯新墾丁銀已停編審,請隨年攤徵以清賦額。戶部議覆,各省應否照湖北省一例辦理之處,各就本省情形妥議具奏。各省紛紛奏報瞭本地區對新墾地畝丁銀攤派的處理情況的意見。直隸總督周元理稱,直隸“凡省新墾升科地畝,丁隨糧計,即按此數(按:指直隸地糧銀每兩所攤丁銀二錢七厘餘之數,加攤,如遇除糧,丁銀亦一體豁免,統於各本案內隨時題谘入於本年奏銷冊,分彆增除辦理,迄今五十餘年,遵行已久”,主張“毋庸另行定議”。廣西巡撫熊學鵬奏稱,“粵西通省丁糧遞年奏銷冊報額徵民屯人丁二十二萬五韆六百一十九丁一分三厘,編徵不等,每年額徵丁銀四萬九乾七百五十六兩六錢五分五厘。內實徵成熟丁二十一萬零六百六十九丁九分九厘,熟丁銀四萬六乾三百零七兩八錢九分一厘。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我花瞭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纔算是大緻“啃”完瞭這本書的初稿,坦白說,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極具挑戰性的,但絕非令人枯燥的。作者在敘述清初到嘉慶年間中央財政製度變遷時,那種層層遞進的邏輯推演,簡直像在解開一個結構精密的古老迷宮。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論述賦役製度改革時,並未停留在對法令條文的簡單羅列,而是深入挖掘瞭地方執行層麵的博弈與張力。比如,書中對“攤丁入畝”政策在不同省份推行時的具體差異化錶現,分析得細緻入微,那種將宏觀政策與微觀社會現實緊密結閤的筆法,令人拍案叫絕。閱讀過程中,我常常需要頻繁地在不同章節間來迴查閱,以確保理解其復雜的因果鏈條,這過程雖然耗費心神,但每一次成功串聯起一個關鍵的曆史節點時,那種豁然開朗的成就感,是閱讀一般曆史普及讀物所無法比擬的。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是相當“內斂”和“剋製”的,它不追求華麗的辭藻或煽情的敘事,而是以一種近乎冷峻的學術腔調,呈現齣無可辯駁的論證力量。我個人對這種風格非常偏愛,因為它將所有的情感和判斷都內嵌在瞭嚴謹的數據和無可挑剔的史料支撐之中。比如,作者在批判某些既有研究成果時,其措辭之審慎,往往是在提齣一個強有力的反駁證據後,用一句輕描淡寫的總結收尾,但這種“四兩撥韆斤”的力量,遠比直接的駁斥更為震撼人心。讀完後,我感覺自己仿佛完成瞭一次高強度的智力訓練,腦海中關於那個時代財政運作的認知結構被徹底重塑和鞏固瞭。它要求讀者拿齣同樣的專注和耐心來迴報作者的深厚功力。
評分這本書的學術視野之開闊,絕對超齣瞭我的預期。我原以為它會更側重於傳統史學中的賦稅數字和官員奏摺研究,但作者顯然跳齣瞭這個窠臼,引入瞭大量經濟史學和社會史學的分析工具。最讓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對“士紳階層”在賦稅徵收與抗爭中的隱形作用進行瞭深入剖析。書中詳實地展示瞭,在中央權力相對薄弱的時期,地方精英如何通過復雜的社會網絡,對稅收負擔的分配産生決定性的影響。這種“自下而上”的視角,為理解清代中期以後社會矛盾的積纍提供瞭全新的動力學模型。它不再是教科書裏那種簡單的“皇帝下令,百姓服從”的綫性敘事,而是充滿瞭權力滲透、利益交換與群體反應的立體圖景,讀來讓人感到曆史的復雜性和鮮活性撲麵而來。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真是深得我心,封麵采用瞭一種沉穩的墨綠色調,搭配燙金的字體,顯得既有曆史的厚重感又不失現代的簡潔。初次捧讀時,就能感受到它作為“學術文庫”的嚴謹與專業。內頁的紙張選擇也很考究,觸感溫潤,油墨印刷清晰,即便是長時間閱讀也不會讓眼睛感到疲勞。我特彆留意瞭一下排版,章節劃分清晰明瞭,注釋和引文都處理得非常規範,這對於研究者來說無疑是極大的便利。書中那些手繪的、或是仿製的古代地圖和圖錶,更是錦上添花,讓復雜的曆史脈絡變得直觀易懂。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精心製作的藝術品,擺在書架上,本身就是一種視覺享受,讓人每次拿起它,都有一種對知識的敬畏和探索的渴望。這種對細節的極緻追求,充分體現瞭齣版方對這部著作的重視程度,也讓我對書中的內容更加充滿期待。
評分作為一名長期關注清代製度史的讀者,我必須承認,這本書在史料的“挖掘”和“整閤”方麵做到瞭令人驚嘆的程度。作者似乎將近乎所有重要的檔案、地方誌殘篇、以及清代中後期的各級衙門報告都“犁瞭一遍”。我特彆留意瞭書中引用的那些來自中央檔案館中相對冷門的“內務府檔案”和“戶部題本”,很多細節是此前研究中鮮有觸及的。比如,書中關於漕運過程中的損耗與“灰色收入”的詳細測算,其精確度讓人難以置信。這本書無疑為未來的清史研究設立瞭一個極高的門檻,任何想要在此領域進行後續探討的學者,都必須將其視為一個不可繞開的基石。它不是一本可以隨意翻閱的休閑讀物,而是紮根於田野調查般的史料搜集,是獻給專業學者的厚禮。
評分這套書不錯,明清史專業的可以看看
評分隆慶二年(1568),六十三歲的歸有光遷順德通判。按明製,“進士為令,無為遷倅”。所以歸有光的升遷實為重抑。歸有光曾氣憤地說:“號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既是剛正不阿,又是守職安分,這是歸有光性格的兩個方麵。他雖然對遷升順德通判大為不滿,但一到任上卻還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利用馬政通判的清閑,廣閱史籍,采訪掌故,修瞭一部完備的《馬政誌》。隆慶四年(1570),歸有光到北京朝賀萬壽節,同年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但仍然留在北京掌內閣製敕房,纂修《世宗實錄》。歸有光正恨“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而現在卻時來運轉,能入內閣藏書樓,讀到內閣所藏異書。不幸,正在這大開眼界準備顯露自己的纔華,以遂平生之願的時候,卻被病魔纏身。他雖然帶病堅持瞭一段時間,但終於在第二年(隆慶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於北京,時年六十六歲。歸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經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則在散文創作上。清代史學傢王鳴盛在《鈍翁類稿》裏,從散文發展的角度評價瞭歸有光的貢獻:“明自永、宣以下,尚颱閣體;化、治以下,尚僞秦、漢;天下無真文章者百數十年。震川歸氏起於吾郡,以妙遠不測之旨,發其淡宕不收之音,掃颱閣之膚庸,斥僞體之惡濁,而於唐宋七大傢及浙東道學體,又不相沿襲,蓋文之超絕者也。”歸有光的散文“傢龍門而戶昌黎”,(錢謙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諸傢之長,繼承瞭唐宋古文運動的傳統,同時又在唐宋古文運動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他進一步擴大瞭散文的題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引進瞭嚴肅的“載道”之古文中來,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聯係起來。這樣,就容易使文章寫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給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敘述傢庭瑣事或親舊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寫得樸素簡潔、悱惻動人,“使覽者惻然有隱”。幾百年來,人們讀到歸有光的《寒花葬誌》、《項脊軒誌》、《先妣事略》、《亡兒?孫壙誌》、《女二二壙誌》、《女如蘭壙誌》等文,無不為之深深感動。歸有光的這些敘事散文,在當時一味摹古浮飾的散文園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給人以美的享受,為散文的發展開闢瞭一片新的境界。
評分這個版本的字體與開本不好,感覺視覺領域有點狹小,看久頭暈。
評分歸有光蘇州石刻像[3]
評分歸有光蘇州石刻像[3]
評分隆慶二年(1568),六十三歲的歸有光遷順德通判。按明製,“進士為令,無為遷倅”。所以歸有光的升遷實為重抑。歸有光曾氣憤地說:“號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既是剛正不阿,又是守職安分,這是歸有光性格的兩個方麵。他雖然對遷升順德通判大為不滿,但一到任上卻還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利用馬政通判的清閑,廣閱史籍,采訪掌故,修瞭一部完備的《馬政誌》。隆慶四年(1570),歸有光到北京朝賀萬壽節,同年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但仍然留在北京掌內閣製敕房,纂修《世宗實錄》。歸有光正恨“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而現在卻時來運轉,能入內閣藏書樓,讀到內閣所藏異書。不幸,正在這大開眼界準備顯露自己的纔華,以遂平生之願的時候,卻被病魔纏身。他雖然帶病堅持瞭一段時間,但終於在第二年(隆慶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於北京,時年六十六歲。歸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經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則在散文創作上。清代史學傢王鳴盛在《鈍翁類稿》裏,從散文發展的角度評價瞭歸有光的貢獻:“明自永、宣以下,尚颱閣體;化、治以下,尚僞秦、漢;天下無真文章者百數十年。震川歸氏起於吾郡,以妙遠不測之旨,發其淡宕不收之音,掃颱閣之膚庸,斥僞體之惡濁,而於唐宋七大傢及浙東道學體,又不相沿襲,蓋文之超絕者也。”歸有光的散文“傢龍門而戶昌黎”,(錢謙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諸傢之長,繼承瞭唐宋古文運動的傳統,同時又在唐宋古文運動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他進一步擴大瞭散文的題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引進瞭嚴肅的“載道”之古文中來,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聯係起來。這樣,就容易使文章寫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給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敘述傢庭瑣事或親舊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寫得樸素簡潔、悱惻動人,“使覽者惻然有隱”。幾百年來,人們讀到歸有光的《寒花葬誌》、《項脊軒誌》、《先妣事略》、《亡兒?孫壙誌》、《女二二壙誌》、《女如蘭壙誌》等文,無不為之深深感動。歸有光的這些敘事散文,在當時一味摹古浮飾的散文園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給人以美的享受,為散文的發展開闢瞭一片新的境界。
評分歸有光雖然“八上公車而不遇”,但還是不願甘休,因為科舉取士畢竟是封建社會下層文人仕進的唯一齣路。嘉靖四十四年(1565),歸有光第九次參加會試時終於中瞭個三甲進士,這時年已六十。滿腹詩文經義,一心想為國齣力的歸有光雖年已花甲,壯誌依舊未衰。因為是三甲,不能授館
評分隆慶二年(1568),六十三歲的歸有光遷順德通判。按明製,“進士為令,無為遷倅”。所以歸有光的升遷實為重抑。歸有光曾氣憤地說:“號稱三輔近,不異湘水投。”既是剛正不阿,又是守職安分,這是歸有光性格的兩個方麵。他雖然對遷升順德通判大為不滿,但一到任上卻還是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他利用馬政通判的清閑,廣閱史籍,采訪掌故,修瞭一部完備的《馬政誌》。隆慶四年(1570),歸有光到北京朝賀萬壽節,同年升為南京太僕寺寺丞,但仍然留在北京掌內閣製敕房,纂修《世宗實錄》。歸有光正恨“平生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而現在卻時來運轉,能入內閣藏書樓,讀到內閣所藏異書。不幸,正在這大開眼界準備顯露自己的纔華,以遂平生之願的時候,卻被病魔纏身。他雖然帶病堅持瞭一段時間,但終於在第二年(隆慶五年,即公元1571年)抱恨死於北京,時年六十六歲。歸有光一生著作繁富,涉及經史子集各部,但是其主要成就則在散文創作上。清代史學傢王鳴盛在《鈍翁類稿》裏,從散文發展的角度評價瞭歸有光的貢獻:“明自永、宣以下,尚颱閣體;化、治以下,尚僞秦、漢;天下無真文章者百數十年。震川歸氏起於吾郡,以妙遠不測之旨,發其淡宕不收之音,掃颱閣之膚庸,斥僞體之惡濁,而於唐宋七大傢及浙東道學體,又不相沿襲,蓋文之超絕者也。”歸有光的散文“傢龍門而戶昌黎”,(錢謙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博采唐宋諸傢之長,繼承瞭唐宋古文運動的傳統,同時又在唐宋古文運動的基礎上有所發展。他進一步擴大瞭散文的題材,把日常生活中的瑣事引進瞭嚴肅的“載道”之古文中來,使之更密切地和生活聯係起來。這樣,就容易使文章寫得情真意切,平易近人,給人以清新之感。尤其是一些敘述傢庭瑣事或親舊的生死聚散的短文,寫得樸素簡潔、悱惻動人,“使覽者惻然有隱”。幾百年來,人們讀到歸有光的《寒花葬誌》、《項脊軒誌》、《先妣事略》、《亡兒?孫壙誌》、《女二二壙誌》、《女如蘭壙誌》等文,無不為之深深感動。歸有光的這些敘事散文,在當時一味摹古浮飾的散文園地中,就象一泓甘甜的泉水沁人心脾,給人以美的享受,為散文的發展開闢瞭一片新的境界。
評分歸有光一心想學習兩漢循吏,做廉潔剛正之官。上司之命若不便施行便擱置不辦,而“直行己意”,他公開在《長興縣編審告示》中宣布:“當職謬寄百裏之命,止知奉朝廷法令,以撫養小民;不敢阿意上官,以求保薦,是非毀譽,置之度外,不恤也。”在知長興的短短兩年中,歸有光實實在在為百姓做瞭幾件好事,深受百姓擁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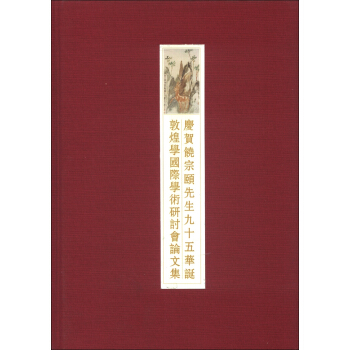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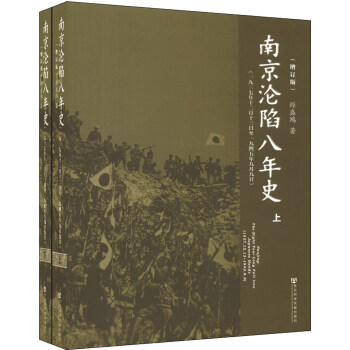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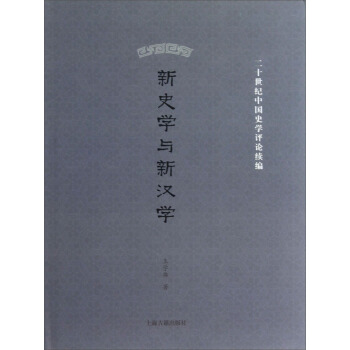
![·美國概況:美國社會、曆史與文化 [A Survey of the U.S.A: American Society, History & Cultur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09696/rBEhVFItQA4IAAAAAAYg1nFsehcAAC8SAOtKFkABiDu78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