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柏拉图注疏集·立法者的神学:柏拉图《法义》卷十绎读 [The Theology of thef Legislator]](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20694/rBEQWVF8lUYIAAAAAAe0TMLdzJAAAFMOAAv1zgAB7Rk511.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理解灵魂就是理解诸神:最终,灵魂学等同于神学。城邦及其诸神能够成为心智的家,就此而言,它们可以成为哲学的家。这如何可能?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城邦如何并在何种程度上能“将心智作为助手”?这些问题更多显示在雅典异方人的行动中,而非言辞中。《法义》的戏剧而非论证,才是柏拉图的神学。——潘戈
内容简介
《法义》以神开篇,这在柏拉图的对话中仅有,卷十还专门探讨了“神学”,为不虔敬之罪制定了法律。不过,在制定这一法律前,柏拉图先拟制了整部《法义》中“高贵和好的序曲”,也是长的法律序曲,其目的在于驳斥诗人的三个“神学”观点:诸神不存在,或存在却不关心人类,或关心人类但可用献祭和祈祷求情。内页插图
目录
编者前言路易斯城邦诸神及其超越
潘戈《法义》中的政治与宗教
潘戈《法义》中的宗教政治灵魂学
尤尼斯基本宗教信仰和虔敬态度的构建
卡罗内 恶的起因和根源
维特克不宽容之福
普兰尼克心智的运动
梅修《法义》卷十中的劝谕与强制
精彩书摘
因此,机运决定了万物的起源。一旦机运决定这一切东西,如元素和物理定律,那么,人们就可以说,“宇宙”自行稳步运行着。那就是人们所谓的自然:这个宇宙系统的作品。这个包含诸元素和定律的系统,产生出更加复杂的形式——分子、行星、有机物、植物、动物,最终是人类。机运及其后裔自然创造了这一切事物。而人类一旦存在,人们就开始独立制作东西。那就是技艺。人类制作了工具和茅屋,建立了朋友、家庭、氏族,最后还有政治共同体。这一切都是人工制作的。最重要的是,人类创造了诸神。诸神本身是人类技艺的产物。诸神是造出来让人信仰的。无论人类创造诸神的目的是安慰自己还是威吓其他每个人,诸神都是人类技艺的产物。要不是人类的创造,诸神不会存在。大体可以说,这就是雅典异方人列举的深邃的无神论。这个论证的前提很清楚:首要的是机运,其次是无机的自然——诸元素和物理定律。其他一切东西都源于这些事物。还会有其他什么东西呢?
雅典异方人列举的另一种伟大选择是灵魂。他问,“在这幅图景中,灵魂的位置在哪里?”(892a)。根据深邃的无神论,灵魂似乎是物质的产物(因此也是机运的产物)。灵魂只是诸多概念之一,是DNA或荷尔蒙之类的产物。这正是雅典异方人要挑战的观点。他试图证明,事实上,灵魂是首要的,在万物中最早(892c)。结果表明,对于他论证诸神存在且不仅仅是人类的发明,这一证明至关重要。
此刻,我们已行至雅典异方人的论证最艰深的部分(参892d-899c)。这个最艰深的部分涉及运动。雅典异方人从一个很稳靠的前提切入:显而易见,一些事物运动,另一些则静止。尽管诸如前苏格拉底的帕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激烈争论过这点,但看起来,这一看法是个适宜的起点。随后,雅典异方人考虑了运动的事物。他列举的十种运动,不需要分别考虑,但看起来确实合理。
……
前言/序言
在太阳直射大地最久、阳气最盛的夏至日,三位来自不同城邦的老人漫步在前往宙斯神社的林荫大道上。他们边走边讨论政制和礼法,虽然路途遥远、天气炎热,但引人人胜(圣)的话题,让他们倍感惬意,忘却了年迈和艰辛。他们的谈话始于“神”:“神还是某个人”,可归为制定礼法的起因?柏拉图的《法义》由此开启了立法的征程,在神人之间摇摇曳曳。《法义》以神开篇,这在柏拉图的对话中绝无仅有,卷十还专门探讨了“神学”,为不虔敬之罪制定了法律。不过,在制定这一法律前,柏拉图先拟制了整部《法义》中“最高贵和最好的序曲”,也是最长的法律序曲,其目的在于驳斥诗人的三个“神学”观点:诸神不存在,或存在却不关心人类,或关心人类但可用献祭和祈祷求情。《法义》开篇就谈到神,为什么直到卷十才真正开始讨论“神学”呢?要弄清“神学”在《法义》中的位置,必须先考虑卷九和卷十一这前后两卷。卷九的主题是刑法,涉及的罪行包括抢劫庙宇、颠覆政制、叛变城邦、盗窃、杀人、伤害等等,最后一个话题是殴打父母,这些罪行主要由血气驱动。
用户评价
坦白讲,我更倾向于那些观点鲜明、论证直接的现代哲学著作,这种对古代经典进行层层剥茧的“注疏”式阅读,对我来说,挑战性极大。它要求读者不仅要理解眼前的文字,还要预设其背后的历史语境、亚里士多德的诘难、新柏拉图主义的回响,乃至中世纪神学家对它的引用。这本书的厚度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屏障,它提醒你,这里面没有速成的捷径,每一步都需要脚踏实地。我总觉得,当我拿起这样一部作品时,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一个需要小心翼翼穿行在历史长河中的考古学家,生怕弄坏了任何一片脆弱的陶片。它需要的不是快速翻阅,而是沉浸式的冥想,需要你在阅读完一句话后,停下来,望着窗外,问自己:“柏拉图到底想说什么?”这种对耐心的极限考验,正是这类书籍的魅力所在,也是其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原因。
评分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绝对是为那些真正热爱思想的“硬核”读者准备的。从装帧到字体,都透着一股子学院派的严谨,丝毫没有迎合大众读者的痕迹,这挺好的,至少说明作者和出版方是抱着对经典应有的尊重来对待这部作品的。我不是柏拉图研究的专家,坦白说,我对《法义》的熟悉程度可能仅限于教科书上那几段著名的引用。所以,当我看到“绎读”这个词时,我心里有点打鼓。这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导读,而是要深入到文本的肌理,去剖析那些可能被无数代学者反复咀嚼过的细微差别和语境。这本书的重量感不仅仅是物理上的,更是思想上的。我甚至在想,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是不是每天晚上都要和柏拉图的灵魂进行一番严肃的辩论。对于我这样的普通爱好者来说,阅读这本书,更像是一次“朝圣”——去探访那位古希腊巨匠思想深处的秘密花园,哪怕迷路了,也心甘情愿。
评分天哪,光是看着这书名就觉得压力山大,简直就是一场智力上的马拉松。《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柏拉图注疏集·立法者的神学:柏拉图<法义>卷十绎读》,这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古老而深邃的气息,仿佛一下子把你拽回了那个雅典的广场,耳边是柏拉图掷地有声的诘问。我这人吧,平时看书比较追求那种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这本书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光是“注疏集”这三个字就让人心生敬畏,我知道,这绝不是那种可以捧着咖啡在沙发上随意翻阅的闲书,它需要的是全神贯注,需要的是带着一本厚厚的词典和一本空白笔记本才能勉强跟上思路。我光是想象一下要消化“立法者的神学”这个概念,就已经觉得脑细胞在燃烧了。这本书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座需要攀登的高峰,而不是一片可以漫步的田园。它散发出的那种学术的严谨和思想的厚重感,让我对自己的阅读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但同时也激起了我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我得做好心理准备,这可能是一次艰辛但绝对值得的智力冒险。
评分这本关于《法义》卷十的解读,光是看名字,就暗示了它对“立法”和“神性”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在我的想象中,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一定充满了不断地自我修正和推翻。你以为你抓住了作者的意图,下一页,他又用一个更精妙的脚注把你拉回到更深层次的文本分析中。它不是告诉你一个结论,而是带你走一遍从提出问题到构建理论的完整路径。我预感,阅读过程中,我可能需要准备多份笔记——一份记录我自己的困惑,一份记录作者对柏拉图文本的精准定位,还有一份记录那些被引用但尚未被我消化的其他哲学家的观点。这是一本“重型装备”式的书籍,它要求你的思维保持高度的敏锐和警觉,拒绝任何形式的敷衍了事。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你对古典智慧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评分对我而言,能拥有这样一本专著在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富足。它代表着学术界对核心文本持久而深刻的投入。我或许永远无法达到作者那样深厚的学识,但我可以从他/她构建的分析框架中,窥见一斑那座宏伟思想殿堂的构造。它不是一本让你“读完就忘”的书,它更像是放置在书架上的一位沉默的导师。当你每次路过它,都会被它所承载的沉甸甸的学术重量所吸引。即使只是偶尔翻开其中一页,看看那些密集的注释和引文,也能感受到那种穿越时空而来的思想冲击力。这本书散发出的那种“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是任何通俗读物都无法比拟的。它让你相信,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总有一些灯塔是永恒的,而这本书,无疑就是指向其中一座灯塔的精确航标。
评分引言
评分前言
评分非常满意,五星
评分本书是一本为柏拉图《法义》所作的导读。全书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柏拉图的《法义》结构、文风、义理在他整个作品织体中的位置;第二部分分五章分析性地概括了《法义》全书的文脉;第三部分是附录,按内在的论题结构提供原书关键段落的今译,并附有相当细致的注释。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对全书的文学形式和思想意蕴形成概观性的把握,而且可以对原作的关键段落产生切实的阅读感。
评分《法义》的辩证结构和进路
评分柏拉图注疏系列很不错。
评分本书是一本为柏拉图《法义》所作的导读。全书结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柏拉图的《法义》结构、文风、义理在他整个作品织体中的位置;第二部分分五章分析性地概括了《法义》全书的文脉;第三部分是附录,按内在的论题结构提供原书关键段落的今译,并附有相当细致的注释。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可以对全书的文学形式和思想意蕴形成概观性的把握,而且可以对原作的关键段落产生切实的阅读感。
评分柏拉图注疏系列很不错。
评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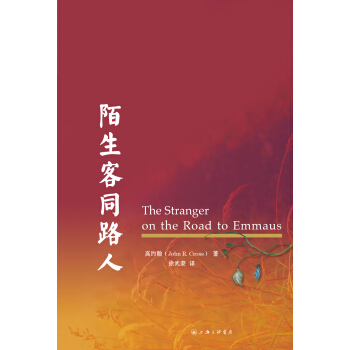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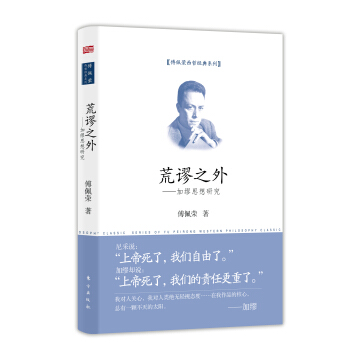
![《清真释疑》研究 [Studies on Qingzhen Shiyi]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69455/rBEhWFKpECoIAAAAAAGFv3k0dkMAAGqgQHHLccAAYXX20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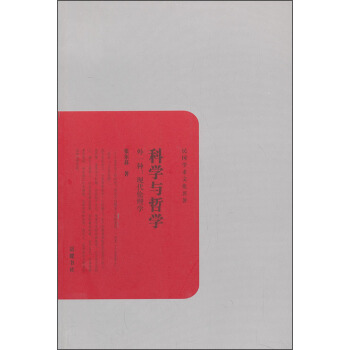
![趣味系列08:趣味美学(修订本) [Interesting Aesthetic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68783/53894cdaN27ebd52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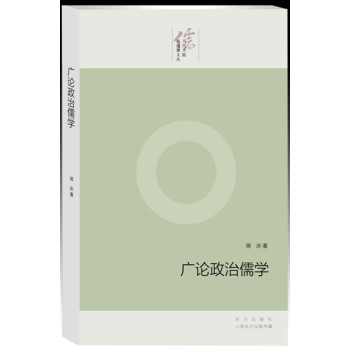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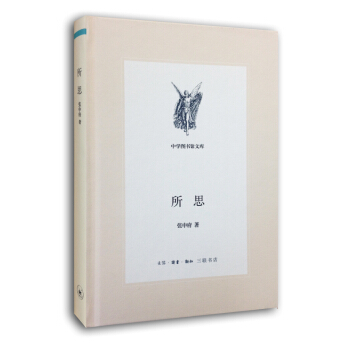
![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的挑战 [Politische Philosophie und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Offenbarungsrelig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71592/545c80b1N03bfee1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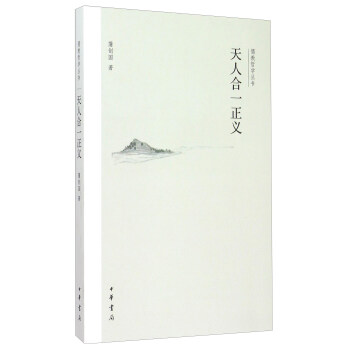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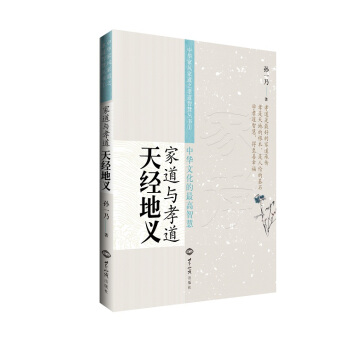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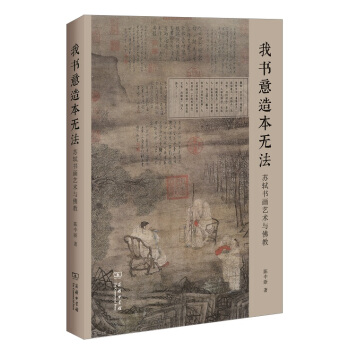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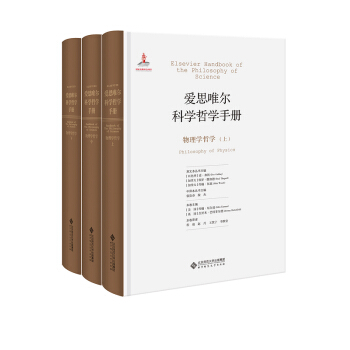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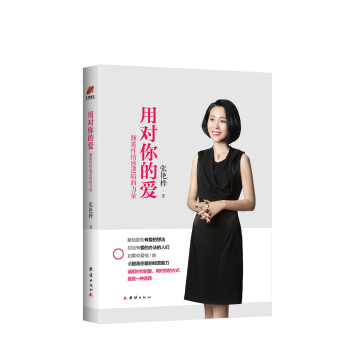
![品格的力量 [The Strength of Charact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86572/586cc024N93e6d1e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