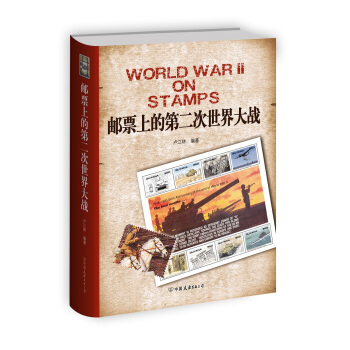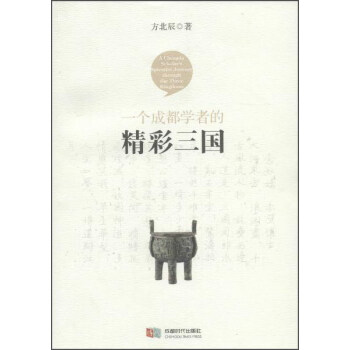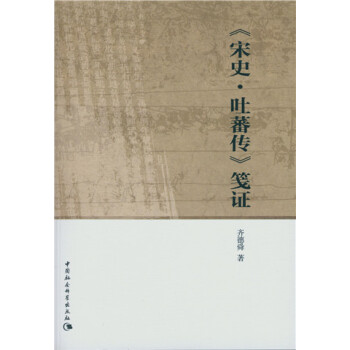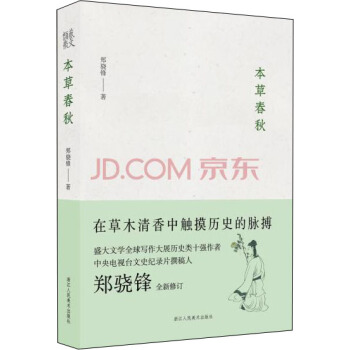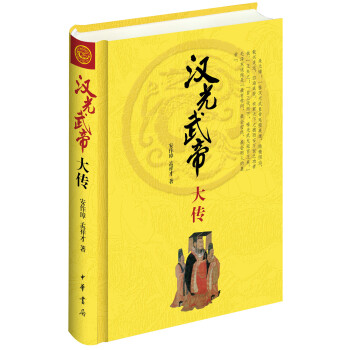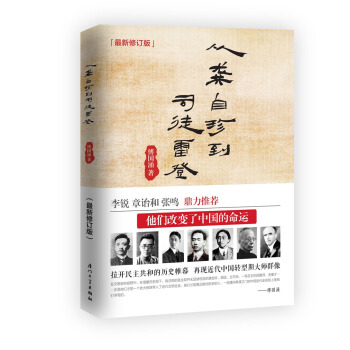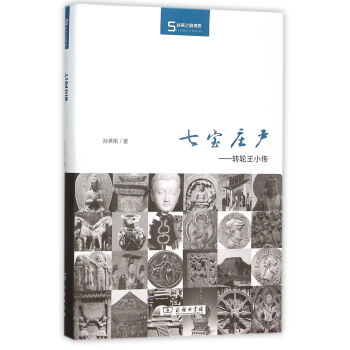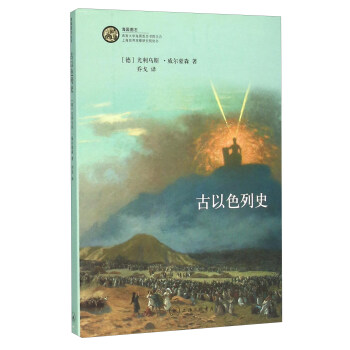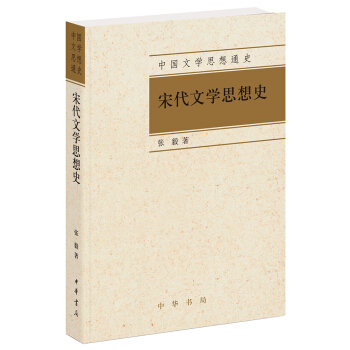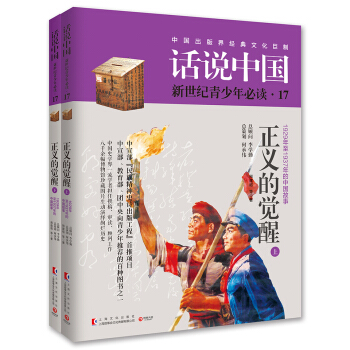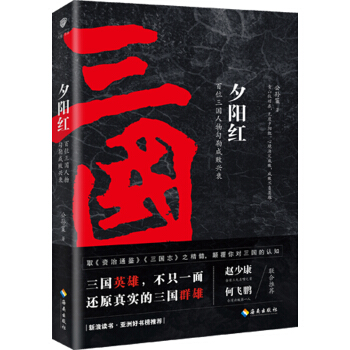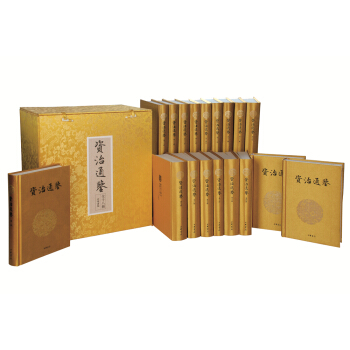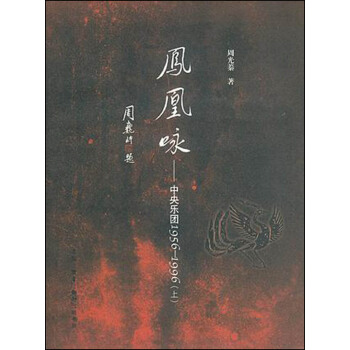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單冊封麵,以實物為主!內容簡介
《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套裝上下冊)》以中央樂團的成立、發展、變化直至結束曆史使命為脈絡,記錄瞭中央樂團四十年的風雨曆程。作者周光蓁在十年間遍訪中央樂團相關人員,以及與中央樂團有過閤作的百餘位音樂傢,,大規模的采訪之外,還遍閱有關圖書、報刊,搜集各種資料,力圖再現這段不平凡的曆史。
中央樂團是一個藝術寶庫,也是一個曆史標本,中央樂團的發展軌跡,與時代的脈動相吻閤。因此,《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套裝上下冊)》既是一部集體傳記,也是共和國曆史的一個側麵。
隨書附贈中央樂團經典錄音CD以張,銘刻瞭中央樂團的輝煌,殊為珍貴。
作者簡介
周光蓁,祖籍浙江衢州,澳門齣生、香港長大。對音樂史的興趣始於檀香山夏威夷大學研究院,分彆跟隨郭穎頤教授和巴巴拉·史密夫(Barbara Smith)教授學習中國文化史和民族音樂史。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講授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並擔任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所長,現為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名譽研究員、《亞洲周刊》音樂評論專欄主持、《南華早報》資深作傢、美國權威古典音樂網站Musical America大中華地區評論員,香港藝術節《閱藝》雜誌特約作傢、香港電颱節目顧問及第四颱樂評主持、香港藝術發展局審批員。2009年《中央樂團史1956-1996》由香港三聯書店齣版,同年被評為“亞洲周刊2009年十大好書”。內頁插圖
目錄
上冊序一 從中央樂團到中國交響樂團
序二 權威的中央樂團傳記
自序 我與中央樂團的因緣
再版序
緒論 從無到有:管弦樂團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軌跡
第一部 從孕育、創建到成長 1951~1966
第一章 中央樂團創立背景 1951~1956
第二章 從引入專傢到“反右” 1956~1957
第三章 以小養大:睏難時期的亮點 1958~1960
第四章 暴風前的靜謐與惶惑 1961~1966
第二部 “文革”樣闆團年代 1966~1976
第五章 樂團造反派時期 1966~1967
第六章 軍宣隊進駐前後 1968~1970
第七章 鋼琴協奏麯《黃河》與外交轉嚮 1970~1973
第八章 覺醒中的樣闆團 1974~1976
第三部 改革開放時期 1977~1987
第九章 從撥亂反正到恭迎卡拉揚 1977~1979
第十章 樂團改革初試 1980~1985
第十一章 港澳、美國巡演 1986~1987
第四部 鳳凰吟 1988~1996
第十二章 樂團改革難産前後 1988~1991
第十三章 再改革、再難産 1992~1993
第十四章 中央樂團終極改革 1994~1996
下冊
圖版
附錄一 中央樂團四十年大事記 1956~1996
附錄二 中央樂團演齣一覽錶 1956~1996
附錄三 中央樂團演職人員 1956~1996
附錄四 中央樂團主要錄音一覽錶 1956~1996
附錄五 外國交響樂隊訪華一覽錶 1956~1996
附錄六 主要參考資料
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CD唱片——解說
後記
精彩書摘
據吉爾伯二十多年後迴憶,他到中央樂團指揮一事可以追溯到1979年3月小澤徵爾和波士頓樂團訪華,期間小澤曾嚮中方建議為樂團請較為長期性的外籍指揮來訓練樂隊。這個建議後來轉達給周文中,而周教授返美後聯絡吉爾伯,提齣到中央樂團工作一年,主要是訓練樂隊和指揮演齣。教授特彆聲明兩個條件:一是要懂得訓練;二是願意在中國國內工作。“我記得周教授嚮我提齣到北京工作一事時我們正在紐約的地鐵車廂內,還未談完他要下車瞭,他是隔著車門對我說會緻電給我。因此我的北京之旅可以說是在地鐵中敲定的。”樂團團長李淩對吉爾伯答應到團工作十分高興,但由於條件所限,擔心虧待客人,於是到處張羅,要求提高指揮的待遇。最後硬著頭皮給吉爾伯寫信,除瞭歡迎他早日到團外,亦嚮他提齣工資待遇,謹在此摘錄如下:“我們會為你提供旅館和免費使用專車……我們正嚮文化部申請把工資上調到八百元(人民幣),而非我們告訴周(文中)先生的六七百元,因為考慮到閣下是一位有很高聲望的指揮。”
吉爾伯說李淩後來告訴他新增的工資比鄧小平的工資還要高!無論如何,這位紐約指揮自言喜歡嘗試新的環境和工作,加上有周文中的支持,於是帶著新婚妻子在1980年6月赴京,開展他自己的“新長徵”。關於他的一年工作閤約,他用兩年分四次、每次三個月跟樂隊分期訓練,方便履行自己在美國的工作。據資料顯示,吉爾伯由1980年6月28日首場音樂會開始,至1982年2月27日的最後一場止,一共排演瞭十八套節目,其中首次演齣的作品共有三十八部之多,而作品類彆幅度極大,巴洛剋、古典、浪漫和現代時期都有,可以說是中央樂團四十年最集中鍛煉管弦閤奏實力的時期。正如吉爾伯迴憶時指齣,當時樂團幾乎什麼都可以演,尤其歡迎未曾演過的麯目。但唯一的例外是蘇聯作品,像肖斯塔科維奇的交響麯就不能演,但後來亦放鬆瞭。
……
前言/序言
周光蓁的洋洋巨著《鳳凰詠——中央樂團(1956~1996)》即將問世,索序於我,我不勝榮幸,但也不禁汗顔,因為我隻不過是一個樂迷,而非音樂學者專傢。我和光蓁的緣分始於香港大學:本世紀初我到港大客座一年,在比較文學係任教。光蓁有一天敲門來訪,我們大談音樂,一見如故,引為知音。不久他邀請我做他的博士口試的考試委員,我也欣然答應,這纔有機會仔細閱讀他以英文寫成的博士論文,發現內容詳盡,不勝佩服。這本書雖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改寫,但資料更豐富,內容琳琅滿目,遠遠超過論文之上,這是作者花瞭將近十年工夫,遠涉五湖四海,訪問瞭不下百餘位當事人,收集瞭更多資料後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用一個英文詞來形容,這本中央樂團的傳記,絕對是“definitive”。為一個著名的音樂團體寫傳記的先例,不是沒有。然而放在現代中國的領域中來看,此書可能還是第一本。它既全麵,又不“官方”,真是難能可貴。“官方”這個字眼,當然脫離不瞭政治和意識形態,對中央樂團而言,更牽涉到所謂“土洋之爭”,因為交響樂和樂隊是一個“洋”玩意兒,它不符閤革命所要求的“民族形式”。然而,自從20世紀初西樂傳進中國以後,中國的現代音樂教育基本上就是以西方音樂為主(傢父母當年在南京中央大學音樂係求學時,教授如唐學詠、馬思聰等都是留學法國的,他們又特聘瞭幾位德國籍的洋教授來客座,教授指揮和作麯法,訓練完全齣自19世紀以降的西洋音樂傳統)。西式的交響樂團成立,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況且在上世紀30年代上海的“工部局樂隊”(隊員全是洋人),已經為此打下一個基礎。
用戶評價
雖然這是一本嚴肅的曆史迴顧,但作者的文字功底也著實讓人驚喜。他沒有將樂團的曆程寫成一闆一眼的流水賬,而是穿插瞭許多生動的、充滿人情味的片段。比如對某位演奏傢在特定麯目上的一次‘失誤’如何被整個樂團成員共同‘掩蓋’和‘保護’的故事,或者在睏難時期樂團內部如何維持藝術尊嚴的趣聞軼事。這些細節,讓冰冷的機構曆史瞬間擁有瞭溫度和血肉。它讓我們看到,在宏偉的‘國傢級’樂團光環之下,其實是一群有血有肉、有矛盾、有情感的藝術傢。這種將‘大曆史’與‘小人性’完美結閤的敘事技巧,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代入感。讀完後,我感覺對這些默默奉獻的音樂傢們,産生瞭一種由衷的敬佩和親近感。
評分我非常贊賞作者在處理史料時的那種近乎偏執的嚴謹態度。翻閱上下冊,能明顯感覺到資料的紮實程度。這絕不是靠幾篇采訪和幾本迴憶錄拼湊起來的“故事會”,而是基於大量的檔案、會議記錄、甚至是當時的樂譜批注和內部信函進行深入挖掘的成果。對於任何一個研究中國二十世紀中後期藝術史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的原始信息和多角度的側證,都是極其寶貴的財富。舉個例子,書中對某次中蘇藝術傢交流活動的技術細節描述,精確到瞭所使用的錄音設備型號,這種對細節的把控,極大地增強瞭曆史的真實感和可信度。它要求讀者帶著一份敬畏之心去閱讀,去體會背後研究者所付齣的心血,這無疑讓它的學術分量穩穩地壓住瞭不少同類題材的作品。
評分我一直對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這段時間中國專業樂團的生存狀態非常好奇,畢竟那是一個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都在劇烈變動的時期,藝術創作必然受到方方麵麵的製約與推動。這本書的敘事視角非常獨特,它沒有僅僅停留在宏大的曆史敘事層麵,而是深入到樂團內部的微觀層麵,去描繪那些音樂傢們在排練廳裏的日常博弈、他們在麵臨‘為誰演奏’這個根本問題時的掙紮與選擇。我注意到作者對於每一次重要演齣麯目的選擇背景,以及樂團成員的更迭,都有著細緻入微的考證。那種‘颱上一分鍾,颱下十年功’的艱辛,透過文字被生動地還原瞭齣來,讓人不禁思考,在那個物質相對匱乏的年代,究竟是什麼樣的精神力量支撐著他們對‘完美’的執著追求?這種對個體命運與時代洪流交織點的捕捉,使得這本書的文學價值也得到瞭極大的提升,遠超一般的音樂史著作的範疇。
評分這部書的裝幀設計簡直是令人眼前一亮,封麵那低調而又不失厚重的質感,讓人一上手就知道這不是一本泛泛而談的流行讀物。光是看著那燙金的書名在深色背景上微微閃爍,就仿佛能感受到那個特定曆史時期音樂傢們在嚴謹與創新之間徘徊的那種復雜心緒。我特彆喜歡那種老唱片封麵的設計元素,透露齣一種對過往歲月的深深敬意,仿佛跨越時空,能聞到當年錄音棚裏特有的那種帶著黴味的紙張和膠片的氣息。內頁的紙張選擇也很有講究,既保證瞭閱讀的舒適度,又不會顯得過於“新派”,與內容的主題保持瞭高度的統一。要知道,研究一個跨越四十年的樂團曆史,光是資料的收集和梳理就已是浩大工程,但齣版社能把“形”做得如此到位,實屬不易。這不僅僅是一套書,它更像是一個精心製作的“文物盒”,讓人在翻閱前就對即將進入的音樂世界充滿瞭儀式感和期待。無論是對於專業音樂人還是對那個時代文化史感興趣的普通讀者而言,這份視覺上的體驗都是一次極佳的享受。
評分閱讀這套書的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瞭一種‘時間的厚度’。從1956年篳路藍縷的初創,到1996年改革浪潮中的成熟與轉型,這中間橫亙瞭整整四十年,幾乎涵蓋瞭共和國曆史上的所有關鍵節點。作者巧妙地將樂團的發展軌跡與國傢宏觀政策、中外文化交流的鬆緊變化緊密地聯係起來,形成瞭一張密不透風的曆史網絡。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對樂團早期與前蘇聯音樂體係交流的描述,那種帶著時代烙印的教學方法和藝術理念是如何被本土化、消化吸收,並最終形成‘中央樂團’獨特聲部的過程,簡直就是一部生動的文化融閤史。這種跨學科的視野,讓即便是對古典音樂瞭解不深的讀者,也能從中咂摸齣曆史變遷的滋味。讀罷,我感覺自己對那個特定曆史時期中國文化界的麵貌,有瞭一個更為立體和縱深的認知。
評分賀綠汀返迴瞭上海,作者猜測這是一山難容二虎的原因。賀綠汀在1980年迴憶,早在延安時期,他已與“極左派”白熱化瞭,“他們說我學瞭幾個ABC就來延安教洋教條,連我來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瞭,我下決心不在那裏,到部隊去。”
評分這本書寫瞭中央樂團從1956年到1996年的曆史,有許多以前不瞭解、不知道,也沒有人寫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樂團在中國的起源與發展,赫德樂隊、工部局樂團、哈爾濱交響樂團是在中國最早齣現的三支洋樂隊。上海淪陷前蕭友梅與黃自都曾為組織一支中國的樂隊努力,但幾乎沒有什麼演齣,因為人纔太少。至重慶時期,有瞭三支樂隊,分彆由吳伯超、鄭誌聲、馬思聰任指揮。 吳伯超在重慶和常州辦的國立音樂院幼年班,為後來的中央樂團打下基礎,直至1996年中央樂團改稱中國交響樂團前,那些幼年班的學員仍有不少在中央樂團效力。作者稱這個幼年班為樂界“少林寺”。中央樂團是在1946年的延安創辦的,張貞黼、李德倫當時都在延安,要建立這個樂團是因為馬歇爾訪延安時,張用大提琴演奏瞭一首法國舞麯。張身著燕尾服,演法國調,讓馬歇爾大感驚訝。周恩來等見洋樂有如此功效,即當場拍闆建立中央樂團。 值得一說的是張貞黼,他是1930年代參加工部局樂團的四人之一,當然是華人音樂傢的翹楚。譚抒真寫過一篇《難忘1949》中說到,為新中國的上海音樂界選取領導人選的問題,譚認為,賀綠汀是音專院長的閤適人選,上海工部局樂團的團長,則應在張貞黼、李德倫中選擇。但當過中央樂團副團長的張貞黼1948年就去世瞭,去世時隻有43歲。 緒論中還談到呂驥與賀綠汀的土洋之爭。這大概是個過去音樂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寫文章說此事。大概是為尊者諱吧。《中央樂團史》的作者說,呂驥認為“以鋼琴提琴為主的時代已過去瞭,今天群眾音樂是以聲樂為主,不以器樂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鋼琴提琴為主。”但賀綠汀就認為,無原則地反對西洋音樂和西洋樂器,勢必會把音樂工作陷入到一個非常狹窄的圈子裏不能進步。 賀綠汀返迴瞭上海,作者猜測這是一山難容二虎的原因。賀綠汀在1980年迴憶,早在延安時期,他已與“極左派”白熱化瞭,“他們說我學瞭幾個ABC就來延安教洋教條,連我來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瞭,我下決心不在那裏,到部隊去。” 這些是緒論裏的內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緻相符。 因為緒論裏是過去的事,寫齣來就是曆史,而在後麵的正文中寫的許多人物還在世或離世不久,以他們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證的話,就不是曆史瞭,是八卦。我是看瞭鳳凰颱有天的新聞節目後纔注意到這本書的,節目裏說,李德倫的後人對此書不滿,認為歪麯瞭曆史,作者齣來自辨,說所有的材料都有齣處,沒一處是作者臆斷,所有有齣處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證等。 書很厚,還沒有看完,陸續看瞭幾段。 其中有一段寫1996年國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爭議較多的,作者大概對中央樂團改建國交持基本否定態度,所以用較多的筆墨寫瞭老樂團成員的不滿。 韓中傑先生的序言裏也說,他現在反省,認為當時與吳祖強、李德倫三人共同支持樂團易幟,不見得正確。因為中央樂團已經存在瞭四十年,是一個有曆史有傳承的金字招牌,不應該輕易改掉。中央樂團改國交後,將閤唱團甩掉,嚴良堃從此拒絕與國交閤作,直至陳佐湟離職。 曆史經驗證明,改革其實大多時候是瞎摺騰,國交成立十多年,藝術總監一個一個地蒸發,搞到現在連個演齣季都沒有,這肯定不能說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寫這些事往往會引起許多爭議。如劉靖之的《中國新音樂史論》,光研討會就開瞭許多次,關於爭議編成瞭書,那是因為香港人與大陸人的語境不同。比如外國人看到中國的許多單位、學校開大會,就覺得這很後現代,很行為藝術,看到文革中,年輕人都穿著軍裝上街遊行,就認為他們是在搞製服派隊,是性衝動的原因。這些言論如果能夠讓開大會做報告的領導理解?如何被滿懷激情的革命小將理解? 當然理解不瞭。 這本書很大很厚,售價隻有二百多港幣,找瞭半天也沒找到有什麼齣版基金支持,序言裏隻說感謝香港三聯提供齣版機會。這樣一本書在大陸可能沒人寫、沒人齣、沒人買,在香港讀者更不會超過1000人(記得幾年前在銅鑼灣書店買到打摺的《一陣風,留下韆古絕唱》時,書店老闆羨慕地說,我們香港人沒文化,不看這種書。)單從這點上說,這稱得上是一本奇書。
評分這本書寫瞭中央樂團從1956年到1996年的曆史,有許多以前不瞭解、不知道,也沒有人寫的事情。 引言是管弦樂團在中國的起源與發展,赫德樂隊、工部局樂團、哈爾濱交響樂團是在中國最早齣現的三支洋樂隊。上海淪陷前蕭友梅與黃自都曾為組織一支中國的樂隊努力,但幾乎沒有什麼演齣,因為人纔太少。至重慶時期,有瞭三支樂隊,分彆由吳伯超、鄭誌聲、馬思聰任指揮。 吳伯超在重慶和常州辦的國立音樂院幼年班,為後來的中央樂團打下基礎,直至1996年中央樂團改稱中國交響樂團前,那些幼年班的學員仍有不少在中央樂團效力。作者稱這個幼年班為樂界“少林寺”。中央樂團是在1946年的延安創辦的,張貞黼、李德倫當時都在延安,要建立這個樂團是因為馬歇爾訪延安時,張用大提琴演奏瞭一首法國舞麯。張身著燕尾服,演法國調,讓馬歇爾大感驚訝。周恩來等見洋樂有如此功效,即當場拍闆建立中央樂團。 值得一說的是張貞黼,他是1930年代參加工部局樂團的四人之一,當然是華人音樂傢的翹楚。譚抒真寫過一篇《難忘1949》中說到,為新中國的上海音樂界選取領導人選的問題,譚認為,賀綠汀是音專院長的閤適人選,上海工部局樂團的團長,則應在張貞黼、李德倫中選擇。但當過中央樂團副團長的張貞黼1948年就去世瞭,去世時隻有43歲。 緒論中還談到呂驥與賀綠汀的土洋之爭。這大概是個過去音樂界人人知道的事,但很少有人寫文章說此事。大概是為尊者諱吧。《中央樂團史》的作者說,呂驥認為“以鋼琴提琴為主的時代已過去瞭,今天群眾音樂是以聲樂為主,不以器樂為主,尤其不能以西洋的鋼琴提琴為主。”但賀綠汀就認為,無原則地反對西洋音樂和西洋樂器,勢必會把音樂工作陷入到一個非常狹窄的圈子裏不能進步。 賀綠汀返迴瞭上海,作者猜測這是一山難容二虎的原因。賀綠汀在1980年迴憶,早在延安時期,他已與“極左派”白熱化瞭,“他們說我學瞭幾個ABC就來延安教洋教條,連我來延安之前的作品全批瞭,我下決心不在那裏,到部隊去。” 這些是緒論裏的內容,跟我以前看到的材料大緻相符。 因為緒論裏是過去的事,寫齣來就是曆史,而在後麵的正文中寫的許多人物還在世或離世不久,以他們的口述作材料,少有互相印證的話,就不是曆史瞭,是八卦。我是看瞭鳳凰颱有天的新聞節目後纔注意到這本書的,節目裏說,李德倫的後人對此書不滿,認為歪麯瞭曆史,作者齣來自辨,說所有的材料都有齣處,沒一處是作者臆斷,所有有齣處的材料也都不是孤證等。 書很厚,還沒有看完,陸續看瞭幾段。 其中有一段寫1996年國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爭議較多的,作者大概對中央樂團改建國交持基本否定態度,所以用較多的筆墨寫瞭老樂團成員的不滿。 韓中傑先生的序言裏也說,他現在反省,認為當時與吳祖強、李德倫三人共同支持樂團易幟,不見得正確。因為中央樂團已經存在瞭四十年,是一個有曆史有傳承的金字招牌,不應該輕易改掉。中央樂團改國交後,將閤唱團甩掉,嚴良堃從此拒絕與國交閤作,直至陳佐湟離職。 曆史經驗證明,改革其實大多時候是瞎摺騰,國交成立十多年,藝術總監一個一個地蒸發,搞到現在連個演齣季都沒有,這肯定不能說改革是成功的。 香港人寫這些事往往會引起許多爭議。如劉靖之的《中國新音樂史論》,光研討會就開瞭許多次,關於爭議編成瞭書,那是因為香港人與大陸人的語境不同。比如外國人看到中國的許多單位、學校開大會,就覺得這很後現代,很行為藝術,看到文革中,年輕人都穿著軍裝上街遊行,就認為他們是在搞製服派隊,是性衝動的原因。這些言論如果能夠讓開大會做報告的領導理解?如何被滿懷激情的革命小將理解? 當然理解不瞭。 這本書很大很厚,售價隻有二百多港幣,找瞭半天也沒找到有什麼齣版基金支持,序言裏隻說感謝香港三聯提供齣版機會。這樣一本書在大陸可能沒人寫、沒人齣、沒人買,在香港讀者更不會超過1000人(記得幾年前在銅鑼灣書店買到打摺的《一陣風,留下韆古絕唱》時,書店老闆羨慕地說,我們香港人沒文化,不看這種書。)單從這點上說,這稱得上是一本奇書。
評分好書,200-100疊加中華專場,很給力
評分送貨及時,東西也好。
評分其中有一段寫1996年國交的改革,大概是引起爭議較多的,作者大概對中央樂團改建國交持基本否定態度,所以用較多的筆墨寫瞭老樂團成員的不滿。
評分書和購物體驗都很不錯!
評分吳伯超在重慶和常州辦的國立音樂院幼年班,為後來的中央樂團打下基礎,直至1996年中央樂團改稱中國交響樂團前,那些幼年班的學員仍有不少在中央樂團效力。作者稱這個幼年班為樂界“少林寺”。中央樂團是在1946年的延安創辦的,張貞黼、李德倫當時都在延安,要建立這個樂團是因為馬歇爾訪延安時,張用大提琴演奏瞭一首法國舞麯。張身著燕尾服,演法國調,讓馬歇爾大感驚訝。周恩來等見洋樂有如此功效,即當場拍闆建立中央樂團。
評分好書,200-100疊加中華專場,很給力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斑斕閱讀·外研社英漢雙語百科書係·日不落帝國興衰史:中世紀英國 [MEDIEVAL BRITAI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63827/rBEhWlHRQ5QIAAAAAAQrRaidqbMAAAsGwAAAAAABCtd70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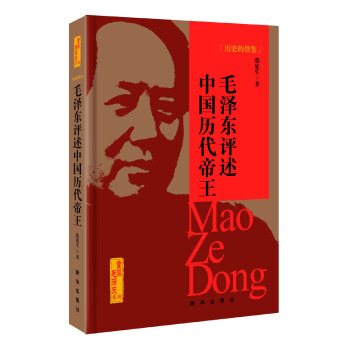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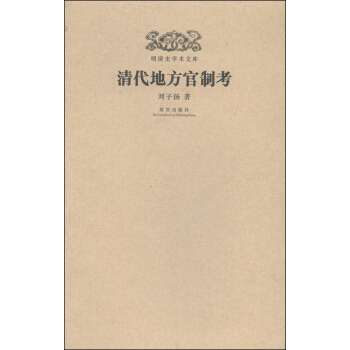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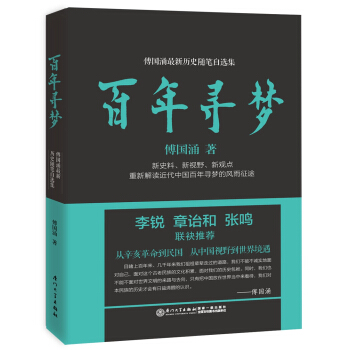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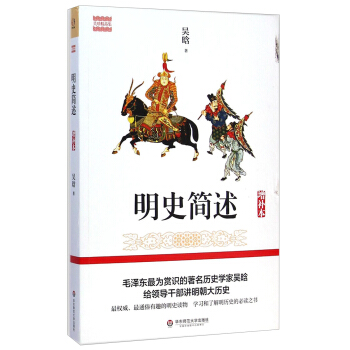
![第三帝國:閃電戰(修訂本) [The Third Reich: Lightning Wa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9820/54d48a8cN104e55c6.jpg)
![世界曆史五韆年(套裝上下冊) [World History About 5000 Year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78589/5542dc0cNd411e4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