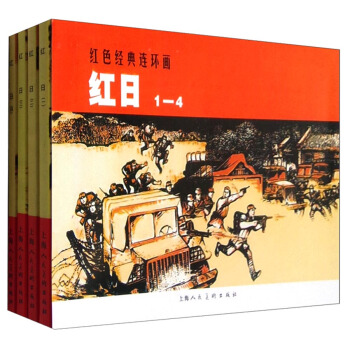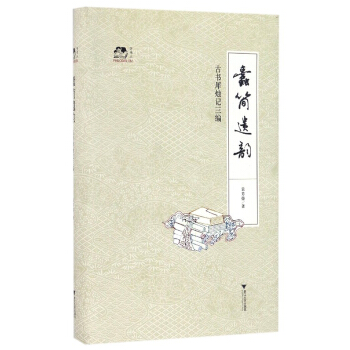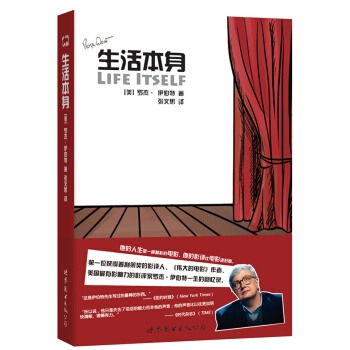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体察艺术百态,不过是一场“欢喜的空无”。陈丹青、何多苓、曾梵志、徐冰……有关具代表性的二十余位艺术家冷静剖析;画谎、炒作、假拍、抱团……着眼浮华背后作弊艺术的假象与不堪。
百余幅当代艺术完美展示,千万级市价画作首次披露《新周刊》副主编胡赳赳,犀利点评当代艺术:别把艺术当神,别拿艺术当真。
内容简介
《空,欢喜:扯一扯当代艺术》为《新周刊》副主编胡赳赳一本系统论述当代艺术的批评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似引非引、万象、众生。其中“似引非引”向大众解释“何为当代艺术”以及“如何欣赏当代艺术”的问题;“万象”将对三十年来的当代艺术种种行状进行剖析和深入思考;“众生”则遴选了具代表性的二十余位当代艺术家肖像、作品及重要评论。语言犀利,见解中肯,分享艺术心得,思索生命和时空感悟。意在完成当代艺术从圈子化向大众化的转移,让白领、精英阶层能够鉴赏、批判、参与到中国的当代艺术进程中来。
作者简介
胡赳赳,《新周刊》副主编,著名媒体人。著有《北京的腔调》《北京的味道》《理想不死》等畅销书。文风老辣,性情单纯,眼明心亮。半颓废半激进的才情令人叫绝。精彩书评
艺术家是狂的,自得其乐的一种动物。
——陈丹青
赳赳的文字灵动,才情高蹈……他的言路和思路是我们社会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异数。
——余世存
为人不识胡赳赳,到过京城也枉然。
——百晓妹
目录
似引非引——这就是当代艺术
万象——
艺术批评的尺度
89美术大展反思-重估“中国现代艺术展”价值
当代艺术是看中国的最好角度
发现丹托
三代知识分子的美学语境
写给青年艺术家的一封信
作弊的艺术
疗伤系艺术家的诞生
艺术家简单点好
艺术家攒人品
谎 画
本质主义绘画:一个假想的流派
刍狗的艺术
黄桷坪艺术区“黄”了吗?
如何去看一幅画?
诗人画派:一个流派的诞生
文人与版画
停电了还搞不搞艺术?
意派论
中国力量
作为玄学的抽象艺术
众生——
陈丹青:我只是在画画
陈鱼:自己的方法
曾梵志:我不是沉默的羔羊
傅榆翔:动物山水的当代表征
傅榆翔的二手漫游
傅榆翔的诸相非相
杨宏伟:复数艺术的焦虑
彭薇的国画新思维
中国美术史上的枪响——枪手肖鲁
毛同强:1360张地契“契入”当代艺术
何多苓:消极是个积极的词汇
郭海平:中国“精神病艺术之父”
冯梦波:停电了就不做艺术吗?
徐冰:左脑毛泽东,右脑科学家
纽约大都会街540号探访徐冰工作室
金锋的迷惘
论康璨
康璨创作手记
冰逸其人
傅文俊:一切历史都是走过场
苏新平的末世风景
黄敏:面对风景的内心修炼
马军:穿越中西之壁的崂山道士
孙初:回到初心
徐弘:中产迷津
张世英:油画抢夺照相术
王子:一个人的美术新编
艺术我不懂
精彩书摘
当代艺术是看中国的最好角度从“理想主义的样板”到“消费主义的狂欢”,当代艺术提供了看中国的最好视角,“艺术眼”看到的是中国病痛和幸福的根源,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与怕”。
学者李陀对当代艺术有个“烂西红柿理论”:“当代艺术好比一筐西红柿,有的是好的,有的是烂的;有的看着是烂的,擦擦看原来是好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好西红柿从筐里摘出来,不受烂西红柿的传染。”
当代艺术有价、有市、有标准;亦有滥竽充数、混水摸鱼、插科打诨。有人说:“粗糙和混乱才有活力。”这正是当代艺术的现状:不完善、未完成、有活力。
当代艺术三十年,前半程是“理想主义的样板”——高名潞主持黄山会议;艺术家们搞达达主义;肖鲁在中国美术馆开枪;叶永青在重庆开火锅大会——当诗人芒克和北岛等人在白洋淀放歌时,艺术家们没闲着,从文革绘画、苏联绘画的时代中醒悟,画《西藏组画》、《春风已经苏醒》等,美术和诗歌,充当了时代变革前沿的发令枪。
后半程,艺术家桥归桥、路归路,各奔前程:能出国的出国,不能出国的聚居——圆明园、东村乃至后来的宋庄、798以及八大美术院校的周边。艺术分化也逐渐开始:学术、商业,也有人在寻找学术和商业的平衡点。当单一的收藏模式被打破时,媒介、网络、画廊构成的网状收藏模式为艺术家的作品打开通路,一个艺术家只要有三、五个收藏家认可和“供养”,便能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很好。与《新周刊》创刊15年一路走来,中国当代艺术的后半程可谓是“消费主义的狂欢”。
无论是“理想主义的样板”,还是“消费主义的狂欢”,中国当代艺术有力佐证了当代中国(一个大时代)的变革,并且充当了显而易见的当代历史的说明书,中国人的一切心态、状态、生态都能从艺术家的作品中找到答案。急吼吼、闹哄哄、乱糟糟,作品中有;急中求慢、闹中取静、乱中从容,作品中也有。正如了解西方历史,读美术史和看美术馆,是一个最易进入的切口,要了解当代中国正在行进中的历史,当代艺术也提供了一个看中国现场的独特视角。
艺术家徐冰说:“在没搞清楚什么是艺术的时候,做做环保、慈善总不会有错。”所以他做了《木林森》作品。一个大艺术家尚不敢说他搞懂了“艺术是什么”,对于众多艺术家而言,也只是老老实实的“艺术的学徒”而已。艺术,真不是艺术史论专家们能说清的。
当代艺术可供利用的资源:一类是传统文化;一类是现行社会;一类是媒介理论;一类是消费理论;一类是后现代理论;一类是全球化理论;一类是体制异见。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世道人心”,是“通感”——感染别人。艺术家的手、艺术家的眼,决定了作品是否成立。
而当代中国,提供了这样多的素材,对艺术家而言真是幸事。有人说:“回国最兴奋的事,是一闭眼,第二天醒来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新闻。”
本世纪初,一股海外艺术家回归浪潮涌起,在“不发生事”的西方,艺术家呆不住了,搭着飞机回来,发觉“中国像个大工地”,每天都在变化,一个新鲜而问题多多的中国,等待艺术家发声。
最多时,北京一天有30个展览同时开幕。极盛时,30家艺术杂志创刊。牛逼时,最顶级的MOMA策展人会来找私人收藏家管艺借作品。而拍卖会更是十年三级跳,从百万俱乐部到千万俱乐部,再到近期齐白石作品拍出4个亿、杭州也花5个亿打包购买了包豪斯藏品。“亿元俱乐部”指日可待。
有钱者投奔艺术,有学问的人也投奔艺术。这是精英荟萃的场合,在艺术社交场,没有娱乐界的尖叫,却比娱乐界更加VIP。
都在投奔艺术,这是必然的。由富而贵,由GDP而中国形象,由硬实力而软实力,当代艺术和当代中国的关系搅在一起,既参与又旁观,既享受快感又目睹灾难,既得意又失落——西方人只有人性,中国人除了人性之外,还有中国性。
陈丹青:我只是在画画
艺术家需要一个隐蔽的地点,这个地点或许是宇宙的“奇点”,或许是时空中的“虫洞”。一旦找到,那么,“创世纪”的那一刻来临了,或者,从“虫洞”中穿越到另外一个异想的平行的世界中去,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地点起初是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有着布尔乔亚气氛,一个少年画着自己的自画像,这种稍带自恋的勾勒正是画家身份的最初确立,虽然它的指向还不那么明晰。窗外是一片红色的世界,资产阶级在变卖自己的家产,或被充公,即便被驱赶住进杂乱的弄堂里,也依然保持着喝下午茶的习惯。一种民国时代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了,传统的斯文扫地,而西洋的花花世界和洋玩艺仅仅是一种地下流通的、带有臆想成分的渴望。
这显然是个美少年,艺术家精心的描摹,使人联想到那卡索斯盯着湖水中自己的倒影——在一张未曾营养不良的脸上,嘴巴倔强地挺着,头发和服饰甚至使人看不出来种族与国别。苦难并未侵袭到画面上来,多年之后,《西藏组画》暴风骤雨般的“红色雕塑”画风则迥异(他一方面受苏联画法的影响太大,另一方面,内心却一直迷恋欧洲的精致圆润的美)。美少年可以享受宁静的烛光,以及私下里偷听到贝多芬或莫扎特的愉悦。
在他的绘画作品中,近五十年来一直未变的是饱满与纤细两样事物能够叠加在一起,“我内心里住着一个女人”,他自己这样讲。他手上吸着烟,嘴上骂骂咧咧,但又会在电影院里、在四顾无人的漆黑的夜晚,任泪水打湿枕畔。如果翻捡他的那些迅疾、准确却又充满个人趣味(他总能打量出不一样的效果来)的速写,这大概有满满几箱子的笔记本,其中的笔意或者说笔法,始终是盘旋的、迂回的、曲意承欢的。他喜欢用曲线,这区别于生硬的、人工的直线。这与学院派的方法是多么不一样,在包豪斯风格一路影响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中,这个顽固的家伙,依然守旧般的在色彩、块面、光影和内心世界里旅行。有时他也叹息,用柏林的话来警示自己“不要有太多的热忱”;更多时候则忘了教条,听从于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后天历练起来的“教养”。
而“跑江湖”(跑江湖的本意是到江西、湖南寻访禅宗大师)的智慧则起源于一种生存斗争,17岁到25岁间,他不得不去上海周边省份的农村插队,这是中国的1970年代——一个全民政治运动的时代就要轰然坍塌了,原教旨的左派路线在欧洲已经只是思潮中的余渍,伟大的国产领袖即将挥手自兹去,哪管人民眼泪滔天。
而在时代变局之前,一切都是殷红、匮乏、艰难的,自我的生存、前途与命运、诗意内心与现实的冲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与国歌的声音重叠在一起,最后化成苏北乡村少女的浅浅的笑——当她出现在速写本上时,世界依然是美好的,就像15岁时临摹哈尔拉莫夫的作品《意大利女孩》所获得的那种印象——而到他55岁坐在北京明亮宽敞、布景如同欧洲某个别致房间的工作室时,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场景:临摹维拉斯开支的小小《宫娥》女孩,获得的却是一种壮士暮年的心境。当他的寿眉长过了两寸时,面对他人惊异的目光,他笑称这让自己看起来像蟋蟀。
这个时期,他更能与董其昌、八大、李世民、文徵明结为心灵上的盟友。尤其是李世民和董其昌,简直可以化身做这位“老夫”了。有一次,在深圳大梅沙的海边,他推开酒店的窗户,说:“看哪,这简直是董其昌。”一块海岛浮现在天际线上,颇有中国画的山水意境。多少次,他被传统文化灵魂附体,而又不甘心承认,在他写字用的桌上,凌乱地摆着他的一些书法习作,这些练习不仅使他在用油画绘制“书册”时,能用油画笔活灵活现、一笔而成地将毛笔书法显现出来(此时,是临摹还是写生呢?),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与古人心慕手追、潜心求道、期待感应降临的方式是一样的。他骨子里是个书生,虽然常常,他嘲笑那些带有“书生气”、“文艺腔”的人。而在他的论敌或是好朋友私下的谈话里,恰恰认为他是另一种“书生气”和“文艺腔”。没错,他是一个“仁”者,骨子里没跑离儒家传统。无论他如何入世,入世如何之深,他对待父母,对待木心,对待朋友(他从未背后说朋友坏话),以及对待陌生人,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礼义仁智信”的传统在支撑。
这样一个书生,身上要是没有“江湖气”,是难能立足的。他构成了自我所批判的一部分。归国十年来(2000年至2011年),他常常跑出画室,面向公众事物发声,既批判一些事物,也吹捧另一些事物。这是容易惹来非议的。在艺术圈内,他获得了不安心画画的“恶名”。好在,在他批判的事物和吹捧的事物中,大部分都立住脚跟了,这使得他能够从容许多。也使得他猛然觉得某些言说实在是多余,而一头扎进新的绘画场域中。
《泪水洒满丰收田》时期的陈丹青,与在纽约绘制并置与三联画风格的陈丹青,以及与归国时期的陈丹青,判若三人。前一个阶段上,他的时空是要在远方,去体验未曾体验过的世界和想像中的事物;而在后一个阶段,他历经了中国的巨大变革,从逃逸者成为回归者,带来了鲜活的经验和急智的话语,而此时,他似乎更愿意怀想他的童年、他的少年和他的青年,他无数次想从绘画中、从写生中,找到当年的记忆,但这已不复存在了。他想安安心心地在绘画中体会笔意与真理,但又总是心潮起伏,容易被媒体煽动。你可以说他骨子里是不安分的,他渴望有个模特坐在对面,哪怕不说话;他渴望一篇文章获得他人的赞赏;他珍惜这种渴望。
有时候,他与老朋友们坐在画室里,一聊就是一个晚上,他们检点过去的记忆,为连环画绘制的插图,或欣赏彼此少岁时的作品。更多时,是对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位大师的画片发呆,长久地响亮着啧啧的赞语声,“真好呀”,然后又是长久地发呆。屋子里烟雾缭绕。
有时候,有两位年轻人作伴,这多少有点鲁迅当年的样子。只是鲁迅没有这样幸运,除了在三味书屋临摹过绣像插图外,只能以指导年轻版画家遣怀。
而陈丹青除了获得了艺术家应有的声名之外,他仍然在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一丝不苟画画,这一点大像刚刚逝世的画家弗洛尹德。即便有时候,别人赏赐借用的带天窗的画室不一定尽如人意,他不接电话,有时也接,一边接一边调颜色,点两下,看看,形准了,色对了。颇像他少年日记所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自由,我终于学会像说话一样画画。”
要问在一个数字时代,连胶片照相机都变成古典工具的时间里,绘制静物、表现摄像术一样的逼真效果,有什么用处
——然而,艺术不正是无用的吗?陈丹青说:“我只是在画画。”
中国美术史上的枪响
——枪手肖鲁
肖鲁坐在她新搬的工作室里面。此前,她收拾了一周,晚上,一班朋友将过来吃饭。
“从机场辅路第二个东营牌子右拐,第一条土路左拐,到东营艺术区,第一排房子最后一间。”肖鲁在电话里这样指路。今年上半年的某一天,她通过艺术批评家高名潞,要到了《新周刊》的电话:“你们的《始于1980》那一期,能递给我一本吗?”
这期杂志在她的新工作室里摆放着,一个显眼的位置。新工作室空空荡荡,她自己设计的一组尚未起名字的装置作品成为“家具”:一个大得离谱的放图片的工作台,有五个抽屉在进门的右侧;进门的左侧是两个书架一样的搁物架,上面搁着新买的葡萄酒、青梅酒,和一堆书籍资料,这两个呈梯形放置的搁物架高矮不一、互相倚靠,肖鲁没有明说,但有着情感上的隐寓;二楼像是这个工作室的后台,后台总是稍显凌乱,肖鲁未来得及细加收拾,一张办公桌上放着电源坏掉的笔记本电脑;从办公桌墙边的长方形窗户望出去,就是北京机场路附近的田地,几棵树的枝叶在墙外的夏日里轻轻摇动;二楼同样有五件装置作品,一字排开,分别呈长方形和梯形,是由金属框架和木头拼接而成的,有评论家戏言说“是一组起伏的人体”,这组从外面看有着刚硬线条、夺人眼目的作品,却是肖鲁自己的穿衣柜、书架和梳妆台——她的作品都是阳性的,但她的内在首先是一个女人。
参观完毕,她笑指着说:“你们杂志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这期杂志上,梳理1980年代的宏大事件时,将在1989年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对话》“枪击事件”署名为肖鲁、唐宋——这与外界多年来的认识是一样的。
“那是我一个人的作品。”肖鲁说:“开枪的是我。”
“这个女人有点疯狂。”我在肖鲁工作室里看到她的行为作品《精子》的图片,心里不禁暗想。
2006年5月,延安抗大宾馆,一个名为《长征计划-延安“延安艺术教育座谈会”》的会议正在举行。
肖鲁的作品《精子》在这里展出,《精子》的材料为架子、12个存放精子的小瓶和1台存放精子所用的控温冰箱。肖鲁向四十多位与会艺术家和专家学者以及参观者中的男性现场征集“精子”。
两天后,肖鲁宣布:第一次征精失败。她笑称:“去延安的男人都没精子了。”
这些男性艺术家的想法可能跟我一样,他们觉得肖鲁有点疯狂。包括费大为、蔡国强、刘小东在内的许多艺术家们在经过肖鲁的作品《精子》时,全都摆着手、绕着走。有的以“我已经结扎了”搪塞过去,有的则开玩笑说“瓶口太小”。
网络上有一段当时会议的视频,镜头最后,肖鲁坐在后排发笑。
“这实际上是对男人的一个心理测试。”肖鲁坐在对面,她身着的绿色吊带裙袍,正好是《精子》图片中的那件。“在这件作品中,男人变得完全被动,他甚至连接近女人都不可能。而男人在两性关系中一直是占主动地位的。”
在第一次征集中,也有男性表示“瓶子是个冷冰冰的东西”,不如“面对一个大活人”,提出可以通过身体接触的方式“捐精”。但为肖鲁拒绝。
肖鲁后来解释她1989年枪击电话亭事件的缘由时说:“打枪的恐惧被更大的恐惧支配着”。她说这就像人不会害怕自杀一样,后面有个更大的恐惧存在。
在《精子》中,肖鲁不顾一切征精,缘于一个更大的恐惧:她44岁了,她从书中看到,女人到这个年龄离不能生育的时间已经不远了。
“我所有的作品都来源于我的情感,我的个人感觉。”肖鲁说,“它的源发点是自我意识。”
作品是一个人身上长出来的东西,这是肖鲁的创作观。“我想要一个归宿,我想结婚,我想要个孩子。”这是肖鲁的人生观。她足足要了15年。
肖鲁配合着摄影师,拿着一把仿真手枪,很自然地伸展、瞄准、凝视。她冷静地说:“但是那个男人不给我。”
她指的男人是唐宋。
“他很会调情,很会生活的。”肖鲁念念不忘“1989打枪”之后,他去了香港,而自己去了澳大利亚,一年半的时间,他们之间情书往来,情浓意稠。
“我用生命爱过你。”这是唐宋在两人关系发生危机时,会不断提及的一句话。每到这个时候,肖鲁就心软了。一晃就15年,肖鲁从26岁大学毕业,到2003年分手时,已经是41岁。
在香港呆了一年半,唐宋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去了澳大利亚,与肖鲁生活在了一起。这次偷渡是他用生命爱过的“明证”。
他们在澳大利亚最初是难民,1992年澳洲“大赫”,四年后他们取得了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才能回国。此后,在唐宋的动议下,他们一起回到了杭州。
1989年,肖鲁和唐宋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附近的一间酒吧经人介绍认识,当时肖鲁在上海油画雕塑院上班一年,唐宋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新一届毕业生。肖鲁向唐宋谈到了向作品开枪的想法,唐宋问她,敢不敢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开枪,肖鲁说敢。
她在中国美术学院的本科毕业作品《对话》被选中,参加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现代大展,这个装置作品由两个电话亭组成,有男女分别在打电话,但中间搁着的话筒在空中悬着,并不在话机上。
在中国现代艺术展前,肖鲁再次碰见了唐宋,唐宋建议将作品用红布铺底,铺上后肖鲁并不满意,把红布撤了下来——这是唐宋与这件作品的唯一关系。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开幕那天,肖鲁向自己的作品开了两枪。当天下午,她回到中国美术馆向警察自首,三天后,被释放。此后,她就离开了北京,从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消失了。
在枪击现场,站在肖鲁旁边的唐宋曾被便衣警察误抓,也许,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枪手是个男的。
“我走出审讯室,这时,唐宋正好从另一间审讯室出来。”肖鲁后来在回忆中写道:“他冲我微微一笑,特定状态下,一种浪漫情怀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唐宋此后作了这件作品的解说者,他跟栗宪庭在中国美术报的编辑部聊了一个通宵。次日,又向高名潞出具了一份文字说明,署名为“唐宋、肖鲁”。
在所有媒体报道和评论中,“唐宋、肖鲁”成为这件作品的共同作者。
“他挺喜欢这一枪的。”肖鲁淡淡地说。她为了与唐宋在一起,每次谈论到这个作品时,都不发一声,全由唐宋来说。这个白羊座的女人认为情感就是女性唯一的追求,其它的一概可以放弃、无原则。
到了澳大利亚之后,唐宋和她确定了一种合作模式,创作由他来控制,署两个人的名字。
装置作品《火柴燃烧的旗帜》就是这样诞生的,肖鲁完全不喜欢,但署的是两个人的名字。“他的作品是阴性的,我的作品是阳性的。”
在澳大利亚接受过几次展出邀请,但展出的效果都反响平平。
肖鲁唯一承认的合作作品是《我们在纽约》。2002年,唐宋给在纽约旅行的肖鲁寄来了一个不锈钢装置,是唐宋自己的塑形。唐宋让她带着这个装置去旅馆呆一晚上、带它逛超市、给它买一套衣服,以此代他逛逛纽约。
肖鲁对这个没感觉,但心里“既感动又别扭”。她电话告诉唐宋说,她在纽约的创作部分由她自己作主,她最后选择了三个地点实施行为艺术:“9?11”纪念地,布鲁克林大桥,纽约时代广场。
回到杭州后,二人大吵一场。
男:“你现在变了,变得很有主见了。”
女:“如果什么都以你的意志做作品,那不是合作,我只是一个你意志的执行者。真正的合作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意志。”
男:“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是你听我的。”
“为什么?”
男停了一下,掏出香烟点上抽了几口,然后一脚把它灭了。男走到女面前,“别人都说唐宋、肖鲁是一道菜,我们是不能分开的。”
二人于2003年在北京分手,以情感和个人体验为全部主题的肖鲁完全自闭起来。她在香港写小说的朋友陈漪珊飞到北京来陪了她三天。听她讲述了三天。最后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肖鲁被传授的写作经验是:真实、细节。她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完成了这本12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除了人名是虚构之外,一概真实的事件历历在目。
肖鲁并不打算出中文版,写完这部小说的好处是“拔毒”。
“我必须真正面对这一枪。”肖鲁说:“本以为抹上一个爱情药会管用,但治表,不治本。”
现代艺术展开幕的前一天晚上,26岁的肖鲁思考到晚上10点钟,到底要不要开这一枪。然后,一种恐惧被另一种更大的恐惧的支配着,通过打枪向自己少年时期被伤害过(两次?抑或三次?)的情感状态决裂。
她知道北京的朋友李松松家里有一把手枪,她打电话让李松松借给她用,第二天带到中国美术馆。
作为筹备现代艺术展三年的负责人,高名潞回忆那天说:“我正在楼上去一个展间,听到楼下传来砰砰两下,没当回事,以为是在布展弄地响,很快就听说,有人开枪了。”
李松松把肖鲁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第一次教她怎么开枪。随后他们来到《对话》装置作品电话亭前,肖鲁低头、举枪、抬头,砰的一声,站在左侧的唐宋叫道:“再来一枪”,又是砰的一声。
这个展区此后被封,再也没开放过,因靠得近被“株连”的还有挂在两边墙上的两幅画作品被撤,它们是谷文达和另一个解析小组作者王鲁炎、顾德新、陈少平、曹友廉、吴讯、李强的作品。
这一枪被赋予了太多的解读和意义:历史的、政治的、社会学的、开端的、谢幕的、巧合的、震惊的。但没有想到,这一枪真实的动因是一个女人内心的情感投射。
这一枪给了唐宋太多的压力,他一直活在这一枪的阴影下,以致于找不到自己的艺术之路。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出色的代言人。
她的原作《对话》早已被当作废铜烂铁卖掉,她复制了《对话》,就连电话亭中男性穿着的雪花石牛仔服,也复制得一模一样,这幅复制的装置作品在嘉德拍卖中以231万人民币成交。一件复制品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令人们吃惊。它在美术史上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
15年后,肖鲁开始了清算。她从游离于艺术圈的状态重新回到艺术圈中,她的爱情生命被抛弃了,作为一个单身重新开始自己的艺术生命——她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个艺术家。
她重新定义作品《对话》的署名权,她解释说:“当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困惑之中,如此大的突发事件的发生,一时使我这个真正的作者失语了。”
2004年2月,她分别给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和高名潞写信。用书面的方式还原了那段真实,佐以当年的录像资料。
她创作了一副幅新作品《十五枪……从1989到2003》,又一次举起枪。一年一枪,整整十五枪。十五年的青春岁月,失去的是年华,而得到的却是一个女人敢于面对过去的勇气和再生的力量。如果不是艺术的自救手段,也许她真会选择毁灭。
2006年,她又一次举起了枪,将原有的《十五枪》作品重新冲洗、装框,运至北京靶场,在那里连击15枪,然后在曼谷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展览开幕式现场完成了第16枪枪击。
她还会开枪吗?这是一个谜。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阅读此书的过程,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之旅。作者巧妙地设置了一些开放性的提问,这些问题常常不是指向艺术作品本身,而是指向“为什么我们会对它产生这种反应?”以及“我们的观看方式是不是受到了太多时代局限?”。这种哲学层面的引导,迫使我不断审视自己固有的文化偏见和审美惯性。书中关于“在场性”和“缺席”的讨论,让我对虚拟世界的艺术呈现有了全新的理解——原来我们所观看的“真实”,往往是经过精心过滤和建构的产物。这种对观看主体和观看行为的持续追问,让这本书的价值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评论范畴,上升到了对现代人存在状态的哲学探讨。读完之后,感觉看待日常事物的方式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那种感觉,就像是戴上了某种矫正视力的眼镜,世界突然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复杂了。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控得炉火纯青,完全不是那种枯燥的学院派论述。作者仿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导游,他没有直接把我们丢进晦涩难懂的理论迷宫,而是采取了一种非常平易近人的“闲聊”模式。开篇时,他会用极其生活化的语言,引出一个你我可能都曾困惑的艺术现象,让你瞬间感觉“对,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话锋一转,便巧妙地将这个日常观察引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脉络和历史背景。这种叙事策略使得原本高冷的当代艺术瞬间变得“接地气”。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复杂观念时所展现出的灵活的句式变化,时而是排比句的层层递进,时而是短促有力的反问,极大地增强了文字的张力和感染力,让阅读体验充满了节奏感和互动性。读完一个章节,常常会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像是刚刚和一位知识渊博的朋友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辩论,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灌输。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一场视觉盛宴。封面采用了哑光处理,手感细腻,那种温润的触感让人忍不住想反复摩挲。大胆的留白和精致的字体排版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让人对内部的内容充满了好奇与敬畏。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十分考究,厚度适中,墨色印刷清晰锐利,即便是高密度的文字段落,阅读起来也毫无压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插图的印刷质量,那些色彩斑斓的当代艺术作品,在专业的印刷技术下,几乎还原了原作的肌理和光影,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对“艺术品”应有的尊重。装帧的整体风格既有现代的简约感,又不失古典的沉稳,仿佛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让人在翻开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一次美好的感官体验。翻阅的过程本身,就像是欣赏一场精心策划的展览,从入口处的序言到章节的过渡页,每一个细节都在无声地引导着读者的心绪,为接下来的深度阅读做足了铺垫。
评分从内容的广度来看,这本书的视野无疑是宏大的,但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它对“小切口”的深入挖掘能力。它不仅仅停留在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大师作品进行宏观描述,而是将聚光灯投射到了那些常常被主流话语忽略的边缘议题和新兴媒介上。比如,书中对于特定国家或地域的艺术生态演变,以及某种特定材料(如新媒体、行为艺术的现场记录)在当代语境下的意义变迁,都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作者似乎拥有某种“X射线”般的洞察力,能够穿透作品表面的喧嚣,直抵其创作意图与社会语境的交汇点。这种细致入微的解构,让读者得以跳脱出既定的审美框架,去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艺术定义。这种在广阔背景下聚焦微观细节的平衡感,使得整本书既有学术的厚度,又不失探索的乐趣。
评分书中引用和穿插的那些非传统文献和跨界资源,无疑是本书的一大亮点,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维度。我注意到,作者不仅仅依赖于艺术史的典籍,还大量引入了社会学、符号学甚至是一些前沿的科技报告中的观点。例如,他在分析某个特定装置艺术的生命周期时,竟然引用了关于材料降解速率的化学数据,这种学科间的无缝对接,展现了作者深厚的跨学科功底。更令人惊叹的是,书中对某些关键概念的阐释,似乎是从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文化母题中提炼而来,这种思维的跳跃性和原创性,让人拍案叫绝。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艺术的书,它更像是一个知识网络的中心节点,将艺术、科技、社会变迁以及人类心理等看似不相关的领域,用一种极具逻辑美感的方式编织到了一起,构建了一个丰富立体的知识图景。
评分塞缪尔·贝克特因为“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荣获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但在中国,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只限于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
评分非常不满意,这次买的书全部有折痕,心疼呐。
评分[ZZ]写的的书都写得很好,[sm]还是朋友推荐我看的,后来就非非常喜欢,他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我家小孩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他们的书我觉得都写得很好。[SM],很值得看,价格也非常便宜,比实体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 书的内容直得一读[BJTJ],阅读了一下,写得很好,[NRJJ],内容也很丰富。[QY],一本书多读几次,[SZ]。 快递送货也很快。还送货上楼。非常好。 [SM],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BJTJ],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书是非常明智的。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抹杀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 中国人讲“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思想,“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从而获得对于“道”的体悟,“唯道集虚”。这在传统的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中国古代的绘画,提倡“留白”、“布白”,用空白来表现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和广博深广的人生意味,体现了包纳万物、吞吐一切的胸襟和情怀。让我得到了一种生活情趣和审美方式,伴着笔墨的清香,细细体味,那自由孤寂的灵魂,高尚清真的人格魅力,在寻求美的道路上指引着我,让我抛弃浮躁的世俗,向美学丛林的深处迈进。合上书,闭上眼,书的余香犹存,而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缀叶如雨”的冲淡清幽境界。愿我们身边多一些主教般光明的使者,有更多人能加入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我们的生活,[NRJJ]希望下次还呢继续购买这里的书籍,这里的书籍很好,非常的不错,。给我带来了不错的现实享受。希望下次还呢继续购买这里的书籍,这里的书籍很好,非常的不错,。给我带来了不错的现实享受。
评分我看了这本书籍很好,有不错的感想。认真学习了这本书,给我几个感受
评分书很好 签名了当代艺术是看中国的最好角度
评分塞缪尔·贝克特因为“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荣获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但在中国,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只限于他的成名作《等待戈多》。
评分《空,欢喜:扯一扯当代艺术》为《新周刊》副主编胡赳赳第一本系统论述当代艺术的批评文集。分为三个部分:似引非引、万象、众生。其中“似引非引”向大众解释“何为当代艺术”以及“如何欣赏当代艺术”的问题;“万象”将对三十年来的当代艺术种种行状进行剖析和深入思考;“众生”则遴选了最具代表性的二十余位当代艺术家肖像、作品及重要评论。
评分沟通中达成共识。
评分不错比荣宝斋的强不错比荣宝斋的强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