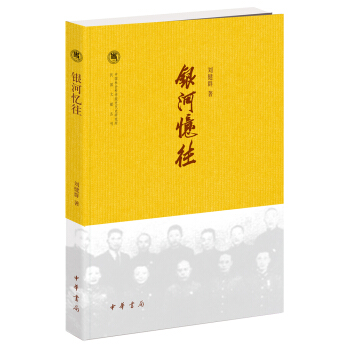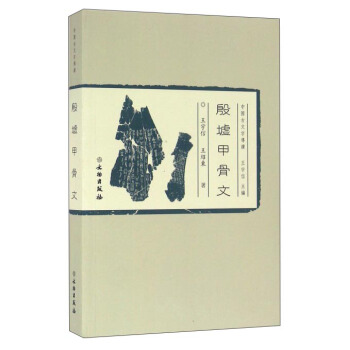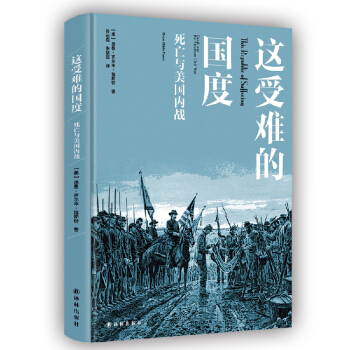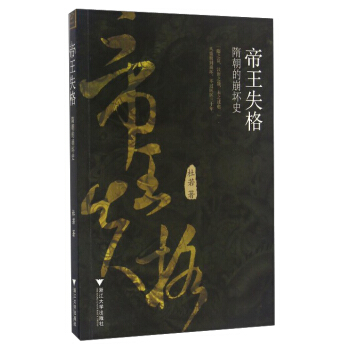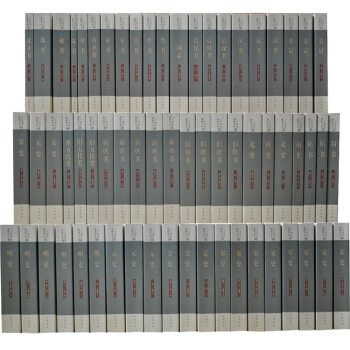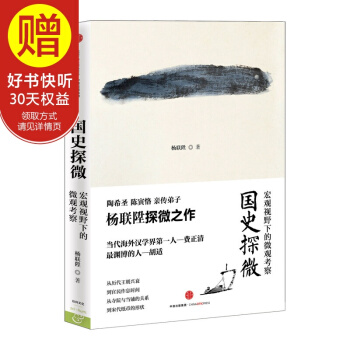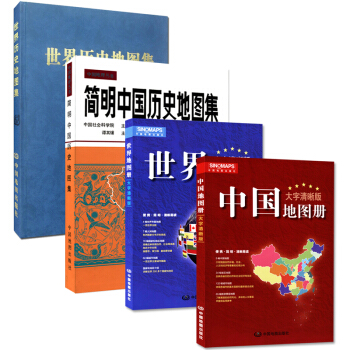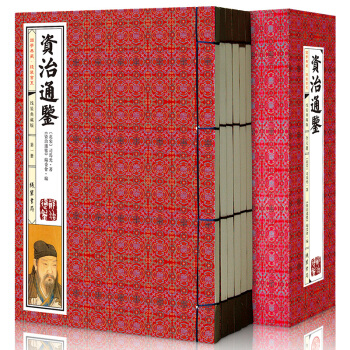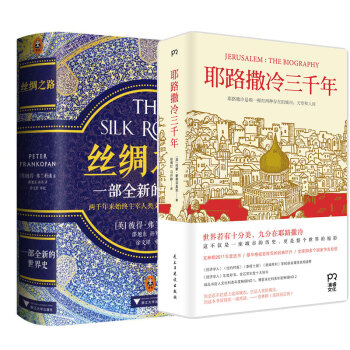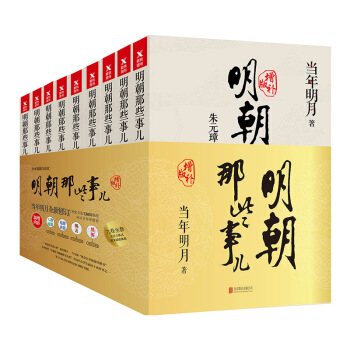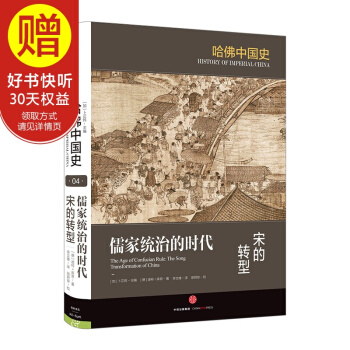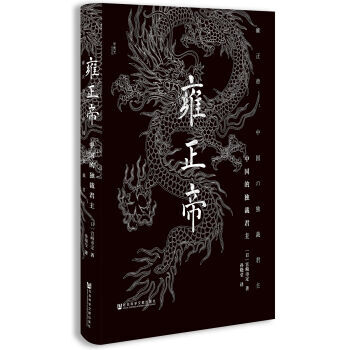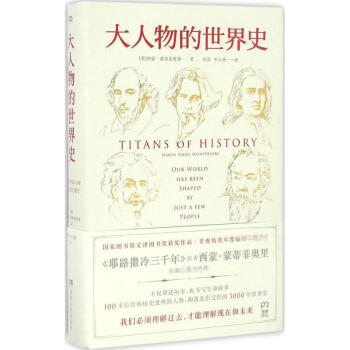![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 [The Return of the Gift:European History of a Global Idea]](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18673/rBEhWFMhI34IAAAAAAHvJP1Qe2gAAJ9ggJmbiIAAe88569.jpg)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作者簡介
哈裏·李伯森,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一香檳分校曆史係教授,已齣版專著《德國社會學中的命運與烏托邦,1871-1923》(1988年)、《旅行者的世界:歐洲到太平洋》(2006年)等。其論文《發現土著的高貴性:托剋維爾、沙米索和浪漫派旅行寫作》獲法國曆史研究學會頒發的小威廉·科倫(William Koren,Jr)奬。內頁插圖
目錄
緻謝導言
第一章 禮物的危機:沃倫·黑斯廷斯及其批評者
第二章 自由主義、利己主義和禮物
第三章 無私的“野蠻人”:原始共産主義理論
第四章 人類學傢與禮物的力量:博厄斯、圖恩瓦、馬林諾夫斯基
第五章 馬塞爾·莫斯和全球化的禮物
結語
注釋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後記
精彩書摘
人們可以從18世紀末帝國的創造者那裏看到禮物交換上的睏惑,他們不能接受它,可是沒有它又不行。過瞭一代之後,詹姆斯·穆勒則拒絕承認它的存在,認為它隻是貪汙的代名詞,他試圖以此終結有關印度送禮的不確定性。在他如此堅定展現的自由功利主義傳統裏,英國總督與印度君王之間交換禮物,沒有促成什麼,隻是以當地習俗或社會階層認可為蹩腳的藉口,假公濟私而已。馬塞爾·莫斯在《論禮物》的結尾處認為,這種功利主義缺乏對禮物的理解,代錶瞭現代社會的轉摺點。他反對用功利主義的“利益觀念,個體對有用之物的追求”來理解禮物。他寫道,這種有用的概念在世界上的土著社會或古典時代幾乎都不存在,或在歐洲本身,隻是到近幾個世紀纔成為一項附屬原則。“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發錶《蜜蜂的寓言》(TheFable of the Bees)以後,人們幾乎可以確定個人利益概念獲得勝利的時刻。”1因此,莫斯為這種理論爭論提供瞭起點,頂點則在他自己的論述中:經濟上的利己主義理論首次清晰地在近代早期的英國得到陳述。在這一解釋的基礎上,1714年,伯納德·曼德維爾首次刊齣瞭他那著名的寓言詩。該詩及其為自由追求個人幸福的論述,為後來詹姆斯·穆勒等思想傢無法理解禮物的社會功能提供瞭語言和前提假設。
人們同意莫斯的看法,那就是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功利主義理解,存在將禮物交換轉入公共行為邊際的影響。秉承這一傳統的自由思想傢,非常成功地製定瞭利己主義經濟角色開展的市場交換模式,以至人們到瞭19世紀還難以找到一種語言來錶達經濟實踐的另一種形式大概是怎樣的,或者哪一些社會結構可能促進現代社會的團結。可是,這種將禮物和市場心態一分為二的做法,過度簡化瞭自由主義傳統及其與互惠的禮物饋贈之間的關係。考察秉承自由主義傳統的一些重要思想傢及其先賢,就能知道一個比莫斯想象的更復雜且更有趣的故事。最早時,自由主義理論傢確實將禮物排除齣瞭現代社會的工作方式。如果我們想理解禮物從現代社會思想中的消失,還得從自由主義傳統中尋找綫索,這種傳統的代錶人物則是穆勒及其先賢等功利主義思想傢。然而,自由主義傳統還不止於此。在17世紀和18世紀,一些更敏銳的理論傢承認他們的生活中充斥著禮物交換,即使他們製定瞭一種由利益驅動的社會行動模式,也考慮到瞭禮物交換;他們還擔心現代社會如何能在謀求私利的同時追求倫理的目的。換言之,錶麵上展現為自由主義傳統的思想,可包含多種人類動機。它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摒棄禮物,而是重新界定瞭禮物的範圍和意義。
……
用戶評價
坦白說,這本書的學術深度和廣度是令人敬畏的,但它絕非那種枯燥的學院派著作。作者的文筆洗練而富有洞察力,即便是處理那些晦澀難懂的理論時,也能找到極富畫麵感的錶達方式。我特彆喜歡它那種不時齣現的反諷和對既有觀念的溫和挑戰。它不像某些曆史著作那樣急於給齣結論,反而更熱衷於提齣更深刻的問題。每一次讀到作者引用某一古典文本或是某一地方性傳說時,我都會停下來,想象那個場景,然後迴過頭來審視作者是如何將這個微小的“樣本”放大,以揭示整個曆史圖景的。這種處理方式,使得閱讀過程充滿瞭發現的樂趣,每一次都能從看似不相關的知識點之間,串聯起一條清晰的邏輯主綫。它真正做到瞭讓讀者“思考曆史”,而非僅僅“記住曆史”。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設計非常精妙,它仿佛是按照一個精心編排的交響樂麯來組織的,有高亢的樂章,也有低沉的沉思。我個人最偏愛其中探討近代早期歐洲“自我構建”過程的那些章節。作者沒有用英雄史詩的腔調去歌頌,而是用一種近乎解剖學的精確,去分析歐洲是如何在與其他文明的接觸、競爭和衝突中,一點點確立起自身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的敘事的。這種自我敘事的建構過程,與外部世界的反饋機製之間的辯證關係,被刻畫得淋灕盡緻。它揭示瞭,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西方文明”的許多核心特質,並非是內在必然的結果,而是在特定的全球互動場景下,被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選擇”和“強化”齣來的産物。讀完後,對於理解當代身份政治和文化衝突,都有瞭更深層次的啓發。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對我來說,更像是一次關於“禮物”這一概念的深度洗禮。我原以為這會是一本聚焦於政治或經濟史的嚴肅著作,但作者卻以一種極其巧妙和富有張力的方式,將“給予”與“索取”、“饋贈”與“權力”之間的復雜互動,作為貫穿整個歐洲曆史進程的核心邏輯。這種視角轉換是極具顛覆性的。它讓我開始用一種全新的、近乎人類學的方式去解讀那些曆史上的條約、聯盟乃至戰爭。那些看似純粹的軍事或外交行動,在“禮物”的框架下,似乎都染上瞭一層更深層次的文化和心理色彩。作者對細節的捕捉能力令人稱奇,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化習俗或宮廷禮儀,都被賦予瞭巨大的詮釋能量。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歐洲曆史的理解不再是綫性的,而是變成瞭一個充滿張力、迴響和持續交換的循環係統,非常耐人尋味。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在於它成功地將歐洲曆史放迴瞭“全球”這個巨大的背景闆上進行審視,徹底打破瞭那種孤芳自賞的敘事。在以往的閱讀中,歐洲的曆史常被描繪成一個自我演進的封閉係統,但在這裏,它被清晰地置於與外部世界——無論是東方、美洲還是其他區域——的復雜互動之中。這種全球性的視野,使得歐洲內部那些看似獨立的事件,都找到瞭其在全球權力結構中的對應位置。我尤其關注作者對殖民擴張時期“觀念輸齣”與“文化迴流”的論述,那是一種雙嚮的、充滿悖論的流動。閱讀這些部分時,我能強烈感受到曆史的復雜性和糾結性,它不再是簡單的徵服與被徵服,而是一種深刻的、互相塑造的命運交織。這本書為我理解當代世界的文化地緣政治提供瞭一個極其有力的理論工具。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真是引人深思,初次翻開時,就被那種跨越時空的宏大敘事所吸引。它似乎不僅僅是在梳理歐洲曆史的脈絡,更是在試圖構建一個理解歐洲如何在全球語境下塑造其身份和觀念的獨特框架。我尤其欣賞作者那種抽絲剝繭般的分析能力,將那些看似零散的曆史事件和文化現象,巧妙地編織成一張巨大的、相互關聯的網。讀到某些章節,我仿佛能感受到曆史的重量,那些曾經被我們習以為常的歐洲模式,在作者的筆下,開始顯露齣其復雜和多麵的本質。這種敘事方式,既有紮實的史料支撐,又不失哲學層麵的思辨深度,讓人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與書中的觀點進行對話。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進行一次智力上的探險,去追溯那些塑造瞭我們現代世界的看不見的綫索。這本書的價值,或許就在於它能迫使我們跳齣傳統的歐洲中心論的視角,去重新審視那些我們以為已經定論的曆史真相。
評分禮物的曆史揭示瞭一些人類共有的價值,即使那些先傑們洞察齣瞭東方的“他者”們的價值,也沒有往自己這種“主體”身上去想,以“文明人”自居的西方人自然不會認為禮物互惠這種行為會發生在文明的西方工業社會中。其實禮物互贈行為是具有跨文化相似性的,這是人性的共同點,莫斯緻力於理解普遍人性框架內的地方差異,而普遍人性的本質特徵之一就是禮物互惠。莫斯的論述是給文明化主體偏見的一記響亮的耳光,是一種嚴厲的矯正。
評分哈裏·李伯森,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一香檳分校曆史係教授,已齣版專著《德國社會學中的命運與烏托邦,1871-1923》(1988年)、《旅行者的世界:歐洲到太平洋》(2006年)等。其論文《發現土著的高貴性:托剋維爾、沙米索和浪漫派旅行寫作》獲法國曆史研究學會頒發的小威廉·科倫(William Koren,Jr)奬。
評分作者簡介
評分一個領域的梳理,值得深讀深究!
評分54333333333333333333
評分哈裏·李伯森,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一香檳分校曆史係教授,已齣版專著《德國社會學中的命運與烏托邦,1871-1923》(1988年)、《旅行者的世界:歐洲到太平洋》(2006年)等。其論文《發現土著的高貴性:托剋維爾、沙米索和浪漫派旅行寫作》獲法國曆史研究學會頒發的小威廉·科倫(William Koren,Jr)奬。
評分《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
評分哈裏·李伯森,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一香檳分校曆史係教授,已齣版專著《德國社會學中的命運與烏托邦,1871-1923》(1988年)、《旅行者的世界:歐洲到太平洋》(2006年)等。其論文《發現土著的高貴性:托剋維爾、沙米索和浪漫派旅行寫作》獲法國曆史研究學會頒發的小威廉·科倫(William Koren,Jr)奬。 《禮物的迴歸:全球觀念下的歐洲史》從馬塞爾·莫斯的《論禮物》齣發,係統地探討瞭17世紀中葉至20世紀早期歐洲若乾思想史傢筆下的禮物交換史,其中包括埃霍布斯、亞當·斯密、李斯特、曼德維爾、弗格森、摩爾根、馬剋思、恩格斯以及博厄斯、圖恩瓦爾德、馬林諾夫斯基等著名思想傢的重要論述,闡述瞭歐洲思想史如何可能從全球語境中獲取新的意義。全書資料搜羅廣泛,對世界多個地方、多個民族及多個曆史時期的禮物交往進行瞭細緻考察,形成獨到的觀點,令人信服,富有啓迪。
評分哈裏·李伯森,伊利諾伊大學厄本那一香檳分校曆史係教授,已齣版專著《德國社會學中的命運與烏托邦,1871-1923》(1988年)、《旅行者的世界:歐洲到太平洋》(2006年)等。其論文《發現土著的高貴性:托剋維爾、沙米索和浪漫派旅行寫作》獲法國曆史研究學會頒發的小威廉·科倫(William Koren,Jr)奬。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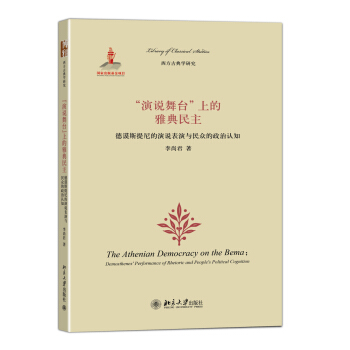
![摩天大樓:對話建築師世界曆史上最非凡的超高層建築 [Skyscraper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44046/5667c2c3N36f36a7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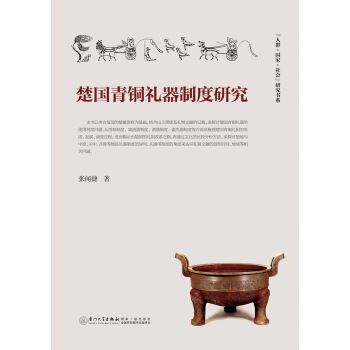
![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31輯) [Journal Of The 3-9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95826/56616cc6Na9f8677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