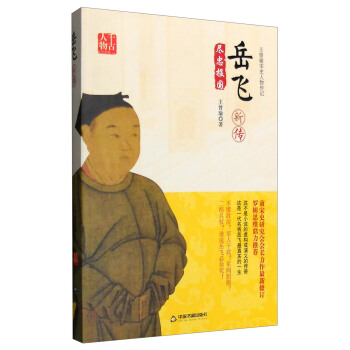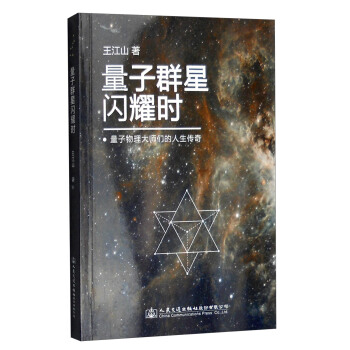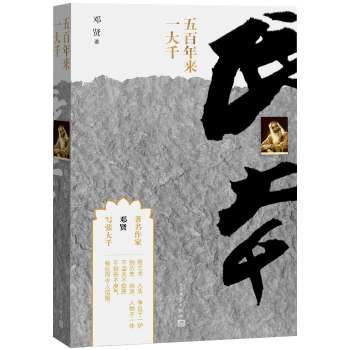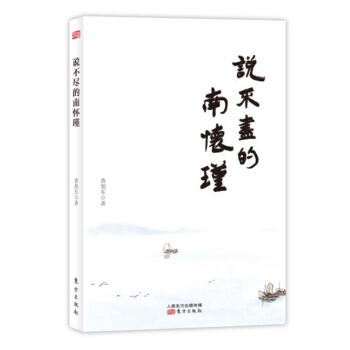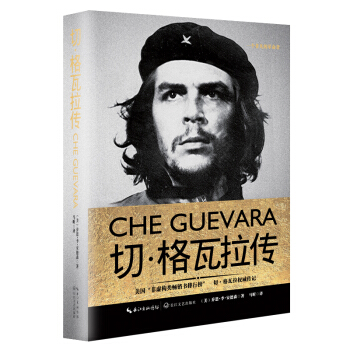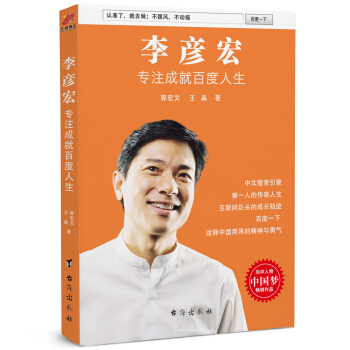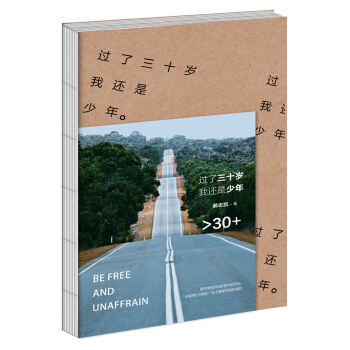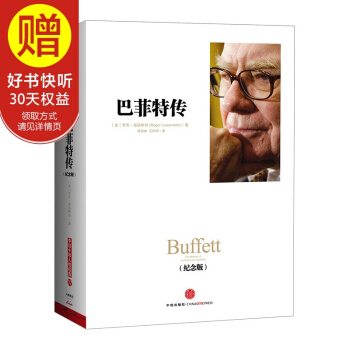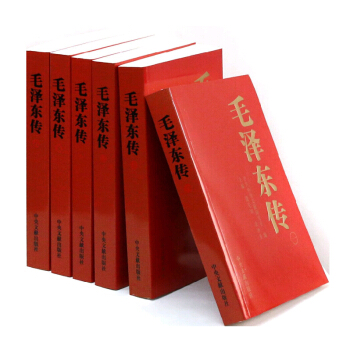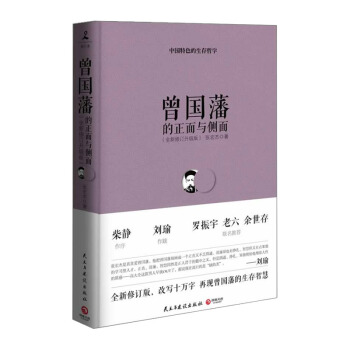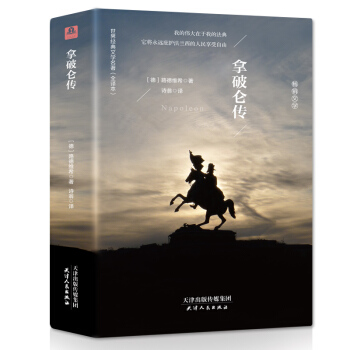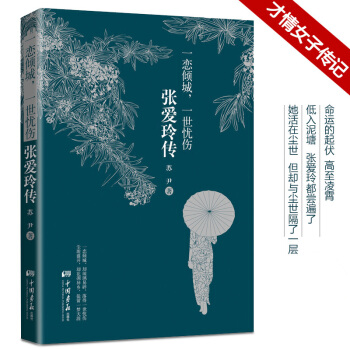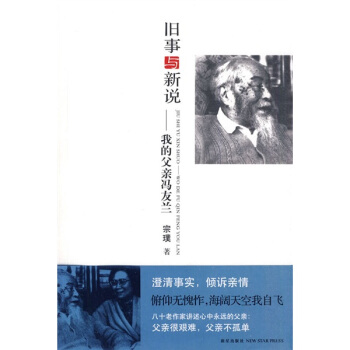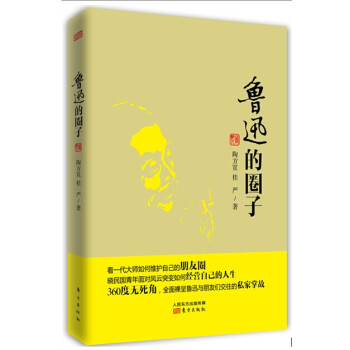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或许你徘徊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独自哀伤
升职,加薪,房子,爱情,婚姻,未来……
一切都那么迷茫……
现实便是历史的写照
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生活在民国的动乱里,迷茫并徘徊……
他们和你一样
但他们和你又不一样
他们挤进了鲁迅的圈子……
生活有了别样的光芒
所以他们名留青史
所以我们也透过他们
看见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
内容简介
胡 适 蔡元培 章太炎 林语堂 郁达夫 陈寅恪陈独秀 许广平 瞿秋白 萧 红 钱玄同 茅 盾
梁实秋 许寿裳 刘半农 许羡苏 废 名 丁 玲
这些鲜活的名字,一个个活跃在鲁迅的朋友圈,他们关系不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都曾在一起。
通过鲁迅的会客厅,我们知道了他们的故事
通过他们与鲁迅的交往,我们也认识了生活中的鲁迅……
作者简介
陶方宣,中国作协会员,出生于安徽,居住于上海。曾任政府机关公务员多年,现为专业编剧、作家。出版著作有《今生今世张爱玲》、《西装与小脚》等20余部。部分作品在香港出版,发行海外。创作有长篇电视连续剧《江郎山下》。
精彩书评
文笔优美,故事逗趣,知道了很多民国时期的文人中间的趣闻趣事,真心值得一读。——喝咖啡的猫
—— 《新闻出版报》 编辑
——会飞的猪
目录
序 言:随着时代的消失而消失
第一章 绍兴会馆(1912—1919)
1.许寿裳:拖在身后的“老虎尾巴”
2.钱玄同:爬来爬去的肥猪头
3.孙伏园:催生阿Q的茶童
4.蔡元培:气味不相投的“此公”
5.胡 适:不打不成交的冤家
6.刘半农:演双簧戏的半侬
7.陈寅恪:贪吃爱玩的胡同串子
8.章太炎:装疯卖傻的狂徒
9.章士钊:穿长衫的士大夫
第二章 八道湾(1919—1923)
1.郁达夫:飘来飘去的虎皮笺
2.林语堂:糊里糊涂的愣小子
3.陈独秀:爱发火的总司令
4.许广平:住三楼的乖姑
5.许羡苏:留短头发的令弟
第三章 阜成门三条(1924—1926)
1.韦素园:瘦小的守寨者
2.废 名:把月亮闩在门外的王老大
3.高长虹:黑夜里的太阳
4.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5.台静农:人缘极好的未名社员
第四章 景云里(1927—1930)
1.瞿秋白:会耕田的犬
2.冯雪峰:长得很丑的乡巴佬
3.内山完造:讨厌蚊子的书商
4.曹聚仁:赤膊打仗的六安人
5.茅 盾:沉默寡言的编者
6.柔 石:讲宁波话的旁听生
7.潘汉年:瓦窑堡来的小潘
8.史沫特莱:并不漂亮的舞伴
9.胡 风:卖苦力的牛
10.白 薇:生肺病的仙女
11.苏雪林:脾气不好的徽州姑娘
12.陈西滢:外冷内热的正人君子
第五章 大陆新村(1931—1936)
1.萧 红:狼狈不堪的小母亲
2.萧 军:东北来的“土匪”
3.丁 玲:被嘲弄的“休芸芸”
4.邵洵美:富翁家的赘婿
5.周 扬:令人讨厌的汉子
6.巴 金:祖籍浙江的老乡
7.成仿吾:抡板斧乱砍的黑旋风
8.聂绀弩:写小说的“金元爹”
9.宋庆龄:同一阵营的同志
精彩书摘
许寿裳:拖在身后的“老虎尾巴”许寿裳摇着芭蕉扇从北边的嘉荫堂出来的时候,鲁迅已经在槐树下的石桌旁坐了好一会儿了。他不停地抽着烟,淡淡的烟草味道正好驱除了树荫下多得成把抓的蚊子。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两盏茶,一盏是他自己的,一盏是许寿裳的——这样的饭后茶聚对鲁迅来说是每日的老习惯。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与许寿裳的弟弟许寿昌都不会露面打扰,这也是他们的老习惯。两个弟弟都知道两个哥哥关系很铁。哥们儿关系铁到这种程度,对于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非常难得。这绵延一生的友谊的形成事出有因:首先他们都是绍兴老乡,在少年时代又同赴日本留学。坐过一样的乌篷船,吃过一样的梅干菜,也许还戴过同样的乌毡帽,家门前也许还都有一棵乌桕树吧?发小加同乡,乡党加同窗,这样的乡谊在两个绍兴男人之间竟然维持了漫漫三十五年,这就是命中注定。用许寿裳的话来说:“这三十五年间,有二十年(我们)是朝夕相处的。”“同舍同窗、同行同游、同桌办公、联床夜话、彼此关怀、无异昆弟”——人生难得一知己,这样的友谊虽说不是“鲜血凝成”,起码也是“肝胆相照”,照到最后就剩下兄弟间的默契,如同这样一个平淡的清凉的夏夜,一个守着清茶在等候着另一个。也没什么可谈,那就听听虫鸣、看看星空吧,这样也是好的。这是每天必须要经历的一道程序、一个过程,不这样坐一会儿,晚上肯定睡不好觉。
许寿裳在鲁迅对面坐下来,谈话照例都是他先开口:“明天休假,是去广和居吃饭还是到琉璃厂淘书?”鲁迅说:“你说呢?”许寿裳不置可否地笑笑:“北平胡同里有一种老房子叫‘老虎尾巴’,莫非你也是我的‘老虎尾巴’,老头子?”鲁迅不到四十岁,但是官场失意、婚姻失望让他内心颓废、心如止水,一直自称“老头子”。听着许寿裳的话,他不置可否地苦笑了一下。许寿裳说:“老头子枯坐终日,极其无聊。”鲁迅答道:“是啊,四十岁上头,一事无成,做了十几年佥事,眼看着走马灯似的换了三四十任教育总长,都是些官僚游士,谁肯静下心来做几件实事?”许寿裳也长叹一声,然后问:“这几日又在抄哪位圣贤的书?”鲁迅答:“《沈下贤集》、《唐宋传奇》,还有《异梦录》。”许寿裳点点头,呷着残茶,任月光随同树影斑驳地照在青布衫上。
这样会客的地方实在有点简陋,但是在生性散淡的文人看来,可能别有一番幽情与诗意,尤其在这样一个夏夜。蚊子很多,时不时会在屁股上咬出一片红包,老鼠与尺蠖应该也不会少。对于从小在百草园长大的迅哥儿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或者将来都成为他的回忆。原来在院子一角长着棵开淡紫色花的苦楝,一场风雨后它被拦腰折断,补种了这棵槐树,也留下一个诗意盎然的名字——补树书屋,它是绍兴会馆的一部分,还有藤花馆与嘉荫堂。鲁迅后来写道:“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许广平在鲁迅去世后回忆,许寿裳与鲁迅的谈话范围很广泛,从新书介绍到古籍探讨、从欧美文学到东洋近作,无所不包。而两人间的人事交往、喜怒哀乐在对方面前从不隐瞒,直接坦露,这样的友谊在鲁迅、在许寿裳都是终生的唯一。不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许寿裳,鲁迅的一生该是什么样子?许寿裳说鲁迅是他的“老虎尾巴”,确实是很准确的比喻。只是鲁迅这根“老虎尾巴”并不是高高翘起来,而是像个大扫帚似的一直拖在他身后。当初还在日本同读弘文学院时,两个人班级相邻却从不来往。后来因为一场剪辫子风波将两个身处异乡的少年一下子变得志同道合,男人脑袋上盘着个蛇一样的大辫子,许寿裳和鲁迅都烦得不得了,剪去烦恼丝痛快一下吧!他们一拍即合。不久,许寿裳接编刊物《浙江潮》,第一个便向鲁迅约稿,因为他早在鲁迅抽屉里发现他读过的大量书籍。鲁迅不客气、不推辞,第二天就交来一稿《斯巴达之魂》,借斯巴达的故事来激励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隔了一天,鲁迅又交来一文《说镭》,此时居里夫人刚刚发现金属元素“镭”,鲁迅借此事说明科学研究的伟大与重要。
同乡之谊演变成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两个人渐渐变得形影不离,常常在一起讨论三件人生大事: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彻夜思考着这三大问题,开始有了弃医从文的念头,因为他认定医治一个人的心灵比治疗他的身体更紧迫、更重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没有一个健全的心灵,这个人同样也是废物。他的看法深得许寿裳的认同。那时候,许寿裳虽然与鲁迅都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但是他已从弘文学院毕业,正在补习德文,计划前往欧洲留学。那是1908年春天,他在东京西片町租到一个绅士的住宅,绅士搬到大阪去了,将那片华美的豪宅租给了他。他带着鲁迅去看房,两个人都惊呆了,那片漂亮得不得了的房子还拥有一个遍种奇花异草的庭院,仅仅是篱笆上的牵牛花就有几十种颜色。更何况那个漂亮的宅子就在东京帝国大学的隔壁,那一片老街区家家鸿儒、户户博士。可是仅凭许寿裳和鲁迅两人的财力根本租不起,他们又邀请了三个同学一起租下。在大门楣上挂上一盏红灯笼,上书“伍舍”。
那一段美好的日子后来成为许寿裳与鲁迅最美好的回忆,鲁迅这根“老虎尾巴”从此就缠上了许寿裳。一起去上野看樱花、尝清茶与樱饼,一起去神田淘旧书。因为学费无着落,许寿裳的欧洲行中止了,回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务长。鲁迅对他说:“你要回去,我也要跟你回去。作人尚未毕业,我不能不先出来工作。”结果许寿裳四月份回国,鲁迅六月份就到两级师范学堂当老师。两年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许寿裳帮忙,草拟各种规章制度,每日不分昼夜地忙碌着,许寿裳心里始终惦记着在杭州的鲁迅。终于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对蔡总长说:“我向先生推荐我的同学周树人。”蔡元培一听,马上点点头,说:“其实我早就慕其大名,正打算驰函延请。现在你正好提起此事,那么就请你代为邀请,请他早日来京。”许寿裳喜出望外,当天连着发了两封信给鲁迅,说明蔡元培先生的揽才之意。教育部随北洋政府北迁北平,鲁迅与许寿裳重新聚首,他们的命运便又捆绑在一起——是一对蚂蚱,也是一对苦瓜。由两肋插刀的好友成为生死之交的莫逆,这其中的一个主要事件就是震惊全国的“女师大风潮”。
“女师大”全称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许寿裳当过校长,凡他的好事绝对少不了鲁迅的份儿,鲁迅也在这里做客座教授,与许广平的师生恋就在这里萌发。杨荫榆做校长后,他不顾一切解散学生自治会,动用军警进行镇压。鲁迅同情这些女生们,成立了以他为首的“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与教育部对着干。教育总长章士钊一怒之下开除了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许寿裳不开心了,在教育部,谁都知道许寿裳与鲁迅好得换裤子穿,哥们儿鲁迅被开除,许寿裳不干了。日日在走廊里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他就是不开口说出,而是将事情捅到了媒体上,根本不给章士钊留面子。在几天后的《京报》上,许寿裳发表了《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宣言》:“署教育总长章士钊,本一轻薄小才,江湖游士,偶会机缘,得跻上位。于是顿忘本来,恣为夸言,自诩不羁,盛称饱学,第以患得患失之心,遂辄现狐狸狐滑之态。近复加厉,本月十三日突将佥事周树人免职,事前既未使次长司长闻知,后又不将呈文正式宣布,秘密行事,如纵横家,群情骇然。寿裳自民元到部,迄于今至,分外之事,未尝论及。今则道揆沦丧,政令倒行,虽在部中,义难合作,自此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
这样的宣言也可以看作是决裂书与辞职书,为了鲁迅,许寿裳断掉自己的后路。后来经过打官司,他与鲁迅的职务得到恢复,但如此是非之地爷们显然不可久留。鲁迅当时正与许广平搞婚外恋,像一座上百年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忽然又失了火,烧得劈里啪啦的,救也没得救。他们先是去了厦门大学,接着又转赴广州的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鲁迅还兼教务主任,手中有一点实力,投桃报李,把许寿裳也请了来,铁哥们儿又开始了同吃同住的生活:“那时候,他(鲁迅)住在中山大学的最中央、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书桌和床铺,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内对角线的两端。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后来许广平来了,鲁迅搬出了中山大学,租住在白云楼,他依然带着许寿裳,两男一女在一起合居。这样的时间并不长,辞职后他去了上海。鲁迅一走,许寿裳在中山大学待着相当无趣,很快也追随他来到上海。
在上海的鲁迅已成为万众瞩目的文化英雄,但在经济上仍然不宽裕,此时的他说白了就是一介自由撰稿人,收入极不稳定。几年前兄弟失和买下阜成门西三条二十一号的房子,向许寿裳借了四百元一直未还。许寿裳为他心急,当时蔡元培创办大学院,对外邀请有一定声望的教授做特约著作员,相当于美国的驻校作家。许寿裳马上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事实上鲁迅既不驻校也没有为大学院写过什么著作,每个月却能领到三百元的补助费,并且一领就是好几年,这能让他心无旁骛地写着他想写的东西,让他攀着天梯,一步步上升到最后的如日中天。
不管鲁迅的名气有多大,他和许寿裳的友谊显然不受双方地位的影响,他们的相交始终是家常的和平常的,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发蒙读书,鲁迅做了他的“启蒙先生”。许寿裳的长女要结婚,鲁迅放下手头一应事务帮他操办。鲁迅在外面是匕首、是投枪,但在许寿裳这里,他始终是一条甩不掉的“老虎尾巴”。外人说起鲁迅的“骂人”,许寿裳替他护短:“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过称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哪能算是骂呢?”鲁迅逝世后,许寿裳回忆说:“那时候我在北平,当天上午便听到了噩音,不觉失声恸哭,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
失去了“老虎尾巴”的许寿裳去了台湾编译馆做馆长,后来在台北寓所意外惨遭歹徒杀害。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鲁迅的圈子》这个书名,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阅读冲动。我一直对“圈子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那个充满变革与思想激荡的民国时代。鲁迅先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巨人,他的思想影响了无数人,但我想,任何伟大的个体,也必然是生长在一定的土壤里的。他所处的“圈子”,无论是他的文友、学生、还是反对者,都必然在他的思想形成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非常好奇,这本书会如何描绘这些“圈子”?是围绕着他与当时几位重量级文人的交往展开?还是会展现他与更广泛社会阶层的互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揭示出鲁迅先生在人际交往中的真实状态,以及这些交往是如何反哺他的创作和思想的。它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充满个人魅力的背后,也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人际网络,而正是这些网络,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生态。
评分《鲁迅的圈子》这个书名,立刻勾起了我深入探究的兴趣。鲁迅先生,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思想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然而,我总觉得,一个思想家的形成,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息息相关。所以,“圈子”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它暗示着这本书将带领我走进鲁迅先生的社交世界,去了解那些与他有过交集的人物,去感受他们之间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甚至可能是矛盾与冲突。我迫切地想知道,在那些历史的洪流之外,鲁迅先生是如何在自己所处的“圈子”中,建立联系,分享观点,又如何影响他人,同时又被他人所影响。这本书如果能够细致地描摹出这些人物关系,挖掘出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或许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鲁迅先生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他在那个复杂时代中的生存智慧。
评分《鲁迅的圈子》这个名字,一听就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人文的温度。我一直觉得,鲁迅先生不单单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而“圈子”这个词,又恰恰捕捉到了这一点,它暗示着鲁迅先生身边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那些他交往过的朋友、知己,甚至是对手。我特别好奇,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鲁迅先生是如何在一个个小小的圈子里,激荡出如此巨大的思想火花?他与那些人之间的交流,是否如我们想象中那样充满碰撞与火花?还是有更温情、更细腻的一面?这本书如果能带领我走进鲁迅先生的社交世界,去感受他与周围人的互动,去了解那些被历史尘埃淹没的细节,那将是一次多么迷人的精神之旅啊!我期待着从书中窥见鲁迅先生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些在他宏大叙事之外,闪烁着人性光辉的片断。它或许会揭示出,伟大的思想是如何在人与人最寻常的交往中,悄然萌芽、生长、最终绽放的。
评分拿到《鲁迅的圈子》这本书,我立刻就被这个书名所吸引。鲁迅,一个我永远也读不透的人物,他的文字如同深邃的海洋,每一次阅读都仿佛能发掘出新的宝藏。而“圈子”二字,则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他的思想,必然是与他周围的人,与他所接触到的各种社会力量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本书如果能把鲁迅先生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拉”出来,让我们看到他如何在具体的社交场景中,如何与他所处的“圈子”互动,那么,这将会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解读。我期待着书中能够展现出鲁迅先生在不同人面前的不同面貌,他是否也会有温情的一面?他是否也会有困惑和无奈?他与那些同样活跃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墨客,他们的交往细节又是什么样的?这些细节,往往比宏大的理论更能触动人心,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的鲁迅。
评分我对于《鲁迅的圈子》这本书充满了期待,原因在于我对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模式非常感兴趣。我们通常接触到的鲁迅,是那个站在时代潮头、振聋发聩的斗士,他的文字犀利、思想深刻,但我们很少有机会去了解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是如何维系自己的人际关系的。他如何与同行者交流思想?如何在误解和攻击中保持自己的清醒?他又如何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交往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圈子”这个概念,恰恰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让我想象到,鲁迅先生是否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同盟,或者说,他是否在不同的圈子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本书如果能细致地描绘出这些关系网络,梳理出鲁迅先生与他所处的各个群体之间的联系,比如文坛巨匠、青年学生、甚至是普通的劳动者,那将是对鲁迅先生更立体、更全面的理解。我希望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人物介绍,而是能够深入挖掘这些“圈子”对鲁迅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展现出历史洪流中个体生存的智慧和力量。
评分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评分京东买书,买个放心!
评分很好的书啊!
评分不错
评分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赞
评分买了为了学习学习!!!
评分不推荐,很不客观的一本书,作者以裁判自居,拉偏架,认定鲁迅偏激,认定鲁迅的论敌都很“客观”,把很多不实传闻当事实写,把自己虚拟的对话当新闻纪实写,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这么自信的?我认为这类书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尽量少以个人的偏见来评论,更不能把自己幻想出来的对话当真实的对话来写,毕竟这不是小说,而是纪实体,何况写的也不像当事人说话的风格。
评分不推荐,很不客观的一本书,作者以裁判自居,拉偏架,认定鲁迅偏激,认定鲁迅的论敌都很“客观”,把很多不实传闻当事实写,把自己虚拟的对话当新闻纪实写,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这么自信的?我认为这类书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尽量少以个人的偏见来评论,更不能把自己幻想出来的对话当真实的对话来写,毕竟这不是小说,而是纪实体,何况写的也不像当事人说话的风格。
评分不推荐,很不客观的一本书,作者以裁判自居,拉偏架,认定鲁迅偏激,认定鲁迅的论敌都很“客观”,把很多不实传闻当事实写,把自己虚拟的对话当新闻纪实写,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这么自信的?我认为这类书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尽量少以个人的偏见来评论,更不能把自己幻想出来的对话当真实的对话来写,毕竟这不是小说,而是纪实体,何况写的也不像当事人说话的风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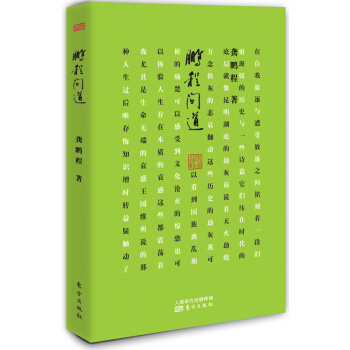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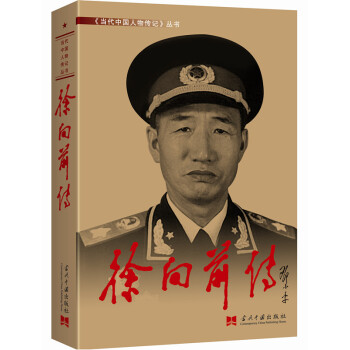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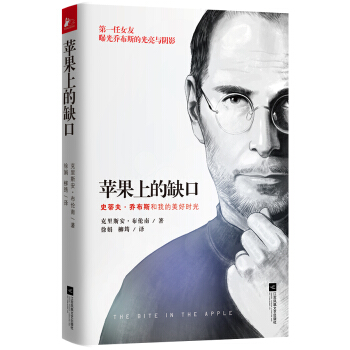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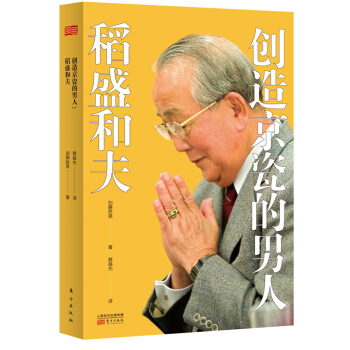
![汪精卫传 [A Biography of Wang Jingwei]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47603/569ddd3fN5aa6e56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