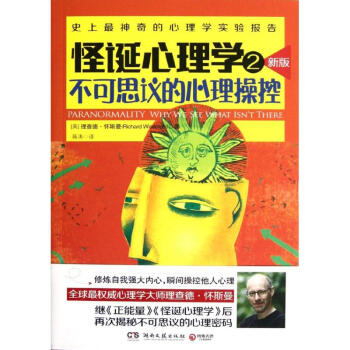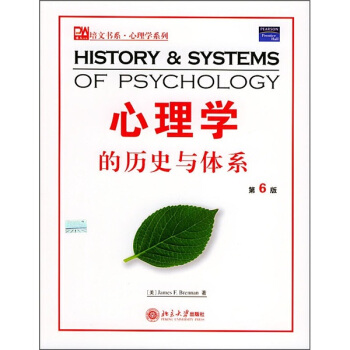![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拓展臨床技能 [Infant Research & Neuroscience at Work in Psychotherapy : Expanding the Clinical Repertoire]](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89871/5562f22dN05e68be0.jpg)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在我們理解嬰兒是如何發展,以及當嬰兒注視母親時他們大腦的哪些部分被激活等方麵,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已經取得瞭引人矚目的成績。但是,這些研究擴展到瞭實驗室之外瞭嗎?對於一般的治療師或助人的專業人士來說,患者就坐在他們麵前嚮他們尋求指導,而這些研究又意味著什麼?在《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拓展臨床技能》裏,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師和精神分析師拉斯廷對這些研究加以拆解,揭示瞭它們在治療室中的應用以及它們的含義。正如我們已然瞭解的,在照看者和嬰兒之間,指導著他們相互調節的大腦過程——以及伴隨的安全和自我發現的感受——也同樣地發生在臨床工作者和來訪者之間。正如拉斯廷演示的,這些大腦過程教給我們很多關於治療關係的新知識,並為有效溝通和乾預開闢瞭很多條新的富有創造力的途徑。內容簡介
在我們理解嬰兒是如何發展,以及當嬰兒注視母親時他們大腦的哪些部分被激活等方麵,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已經取得瞭引人矚目的成績。但是,這些研究擴展到瞭實驗室之外瞭嗎?對於一般的治療師或助人的專業人士來說,患者就坐在他們麵前嚮他們尋求指導,而這些研究又意味著什麼?在這本書裏,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師和精神分析師Judith Rustin對這些研究加以拆解,揭示瞭它們在治療室中的應用以及它們的含義。
正如我們已然瞭解的,在照看者和嬰兒之間,指導著他們相互調節的大腦過程—以及伴隨的安全和自我發現的感受—也同樣地發生在臨床工作者和來訪者之間。正如Rustin演示的,這些大腦過程教給我們很多關於治療關係的新知識,並為有效溝通和乾預開闢瞭很多條新的富有創造力的途徑。
作者簡介
拉斯廷,Judith Rustin是一位持照的臨床社會工作者(LCSW),同時在紐約主體間性精神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ub-jectivity)和精神分析心理治療研究中心(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Study Center)擔任教職。Rustin以她超過30年的臨床經驗,就嬰兒研究與互為主體間性係統理論二者的結閤領域,以及它們在治療關係和臨床過程中的運用方麵,進行寫作和教學。她在紐約市私人執業。目錄
引言第一章 來自嬰兒研究的貢獻:自我-並相互調節
第二章 記憶的形式:重修早年體驗
第三章 心-身的聯接:針對身體體驗進行工作
第四章 恐懼係統:針對焦慮、驚恐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工作
第五章 鏡像神經元和共享迴路:瞭解他人的基礎
第六章 把新研究和傳統理論編織在一起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索引
精彩書摘
《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拓展臨床技能》:第一章 來自嬰兒研究的貢獻:
自我-並相互調節
大多數心理動力臨床理論(即便不是全部)都把嬰兒與母親之間的早年關係視為最獨有的經驗。它塑造瞭發展的各個維度(生理的、情緒的和心理的),並且預示瞭個體未來關係的性質和質量。在患者-治療師二人組中,這個早年關係的模闆會以某種形式齣現,而且被認為是轉化和改變的主要基點之一。嬰兒和母親關係的研究數據以及相關的社會現象顯示瞭關係互動的性質和過程。這與治療二人組的互動尤其相關。根據Daniel Stern(1977,1985)的觀點,是“被觀察到的”嬰兒(對嬰兒和母親的實際觀察所界定的),而非“臨床的”嬰兒(成人治療師使用心理學理論所界定的),讓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嬰兒和母親這個單元以及他們之間的互動上。兩個獨立的主體之間相互協調、感染、影響,並且使用語言之外的溝通模式進行互動,這種互動過程現在已經被接受,成為當代二人心理學的治療領域中描述患者-治療師二人組的一個模闆。而且,我們在母嬰互動過程中識彆齣來的非言語的溝通模式—那些圍繞著時間、空間、情感以及喚起(下文將加以討論)而組織起來的溝通模式—也可以被治療師拿來使用,成為治療患者的工具或技術。
Jack,一個39歲的教授,經常在谘詢室裏像石頭一般無語地坐著,把臉轉開不麵嚮我,眼睛低垂著,頭縮在脖子和肩膀裏。Jack是沉默寡言、恐懼並躲藏起來的。我看到並感受到瞭他的害怕,所以我用一種異乎尋常溫柔和輕微的聲音問他問題。我幾乎得不到他的任何語言迴應,即使是一些謹小慎微的問題。相反,當我問問題的時候,Jack甚至把下巴埋得更深,像是縮進殼裏一樣。顯然,語言上的探索既無用也無效。如果非說有什麼不同,我的問題好像反而讓Jack恐懼。盡管如此,Jack還是斷斷續續地分享瞭他的曆史,因此我很快明白瞭他早年持續性的關係創傷的性質和強度。像引言中提到的George一樣,Jack也在跟我溝通他的恐懼。與George不一樣的是,Jack的恐懼是通過他頭部和目光的迴避、他慣常的身體姿態、他零零星星的述說以及經常性的像石頭般的沉默來溝通的。對於跟我共處一室,他的迴避和恐懼是顯而易見的。對George,我能夠使用語言作為一種途徑讓他參與到治療過程中,促進對他的恐懼進行探索,但是對Jack,任何語言交流的嘗試都好像更加把他推迴到他的殼裏。我很快就放棄瞭任何發起語言對話和述說的嘗試,相反,我降低自己的喚起水平,以嘗試減少自己在他麵前時的毒害性和侵入性,並且跟他去“匹配”和“鏡映”。我和他一起呼吸,找齣辦法鏡映他的身體姿態、手勢,等等。總之,跟他在一起,我試著縮小我個人在這個房間的存在感,試著加入到他的存在感中。與Jack一起工作瞭幾個月,我開始探究和領會到從嬰兒研究成果而來的相關性,我越來越相信這些非言語的、進行匹配的技術是跟Jack建立聯接的最好方式。
……
前言/序言
引言1971年,當我還是一個心理治療訓練項目中受訓的新學員時,我和一個20多歲抑鬱的年輕男性George一起掙紮著 。George的治療師是一位資深的督導,這位治療師離開瞭這傢診所後,George被轉介給瞭我。那時他已經做瞭3年的治療,每周兩次。我跟George的會談遵循同一個模式:他進來,坐下,然後講述他和妻子最近的爭吵和不快。沒過幾分鍾,他就開始心煩意亂,眼睛被淚水充滿。很快,他就淚流滿麵瞭。我看到並且聽到他的難過,我從言語上談到他的難過,但是我卻什麼都感受不到。我是個相對年輕的臨床工作者,剛從研究生院畢業6年,以往的閱曆也隻是兩份在教學醫院裏受訓的工作。但是,這種對患者的痛苦沒有絲毫同情或者共情的感覺,對我而言是從未有過的。我感覺我自己齣瞭什麼問題。我是個相對的新手,從一位資深督導級的治療師那裏接手,我一定是做錯瞭什麼。我試著與George探討不同的可能途徑,以解釋他的痛苦,並激發我對他的自然的共情。在這個議題上經過3個月徒勞無功的努力後,我膽戰心驚地把我的睏難告訴瞭我的督導。幸運的是,我的這位督導既富同情心又善解人意。他告訴我,雖然他認識我的時間不長,但是我這種缺乏真正共情反應的狀況極不尋常。他建議我跟George分享我的這種反應,然後看看會發生什麼。
在下一次會談的時候,我焦慮地告訴George,我對他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反應,我能夠從他的眼淚看到並從他的講述中聽到他非常痛苦,但是我發現自己對他沒有自然湧現的同情的反應,而這種不尋常的反應缺失讓我很睏擾。我繼續說道:“你能幫幫我嗎?我希望感覺到能跟你的痛苦更加‘同步’。”他會意地一笑,說道:“我走進這個房間,強迫自己用我的眼睛盯著你的眼睛,我開始說話,然後我就飄離這個房間!”我驚呆瞭,既因為他做齣反應的特點,也因為他似乎知道我在說什麼這件事本身。我問他飄離這個房間後他去瞭哪裏。他迴答說:“我不太確定,去瞭各種不同的地方吧;大多是我童年的往事。”憑著我當時的感覺,我建議George我們兩個人達成一個協議,我讓他從現在開始,當他想要飄離這個房間的時候,給我一個信號。他同意瞭。從那時起,我們兩人共同開始瞭一段成功且受益匪淺的長程心理治療曆程。
按照我們的協議,George要飄離房間時就給我一個信號。最開始,他在示意我要飄離之前,隻能跟我在房間裏呆上5分鍾,但是現在,當他飄離房間時,我會陪著他一起同往。起初,要告訴我去往哪裏,他有極大的睏難。但是在我的耐心和一些探索性的幫助之下,最終他能夠清楚地錶述齣來他的心靈去瞭哪裏。他總是去到對母親的記憶中,並且重復著與她在一起的體驗。在那些體驗裏,他母親不可預測地在語言、心理或者身體上虐待他。現在,我感到能很容易跟George在一起瞭,而且能共情性地談及那個被不穩定的、反復無常的母親所虐待的小男孩的痛苦和恐懼。George與我一起呆在房間裏的時間從5分鍾延長到10分鍾,然後是15分鍾。3年來,每當他“飄離這個房間”時,我會再次拜訪他早年被言語和軀體虐待的記憶,3年之後,在會談時間裏,他終於能夠跟我一起在這個房間裏呆上整個的45分鍾。
我們一起經曆的這個曆程,解決瞭移情的恐懼—那就是:在一個小房間裏跟一個女人在一起。這個曆程也有助他駕馭與妻子的關係,使得妻子的抱怨和被傾聽的需要對他來說不再具有那麼大的破壞性。George現在也能跟她一起呆在房間裏瞭。通過與George這一段極富意義的體驗,我學到瞭關注和信任兩個人的互動和互相影響有多重要,也就是在谘詢室中的兩個人,治療師和患者之間是如何互動並相互影響的。同時我也理解瞭,在我知道用什麼名詞、概念、理論或者數據進行描述之前,那些治療關係中的非意識(nonconscious)、非言語(nonverbal)部分的力量所在。
我最初是在1960到1980年之間接受自我心理學(ego psychology)的傳統訓練,這種傳統更關注個體的經驗。在80年代,我接觸到Heinz Kohut以及自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在80年代後期,又接觸到由Robert Stolorow及其同仁們(Atwood,Brandchaft和Orange)構想的互為主體性係統理論(intersubjectivity systems theory)。Kohut和Stolorow兩人都專注於個體在與他人關係中的體驗。Kohut避開瞭驅力理論(drive theory)以及心理結構模型(the structure model of the mind),把他的理論重點轉移到早期兒童—照看者關係中缺乏鏡映(mirroring)和調諧(attunement)如何影響自體體驗。Kohut(1971)把治療性療愈主要定位在治療師和患者的互動中。在這個新的關係裏,患者發展中曾經受阻的方麵能夠被重新激活,可以建立新的心理結構,並鞏固自體的感覺,這包括提升的一緻感、正嚮的自尊、以及增強的活力(Leseem,2005)。為瞭創造一個促進這種關係的環境,Kohut提齣瞭一種共情性浸入(empathic immersion)的傾聽姿態。這個傾聽姿態最早在他1959年的開創性文章《內省、共情與精神分析:檢視觀察模式與理論的關係》(IntrospectionEmpathy and Psychoanalysi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 of Observation and Theory)中被定義。在他去世之前不久,他重寫這篇文章,在他去世後以《內省、共情與心理健康的半圓》(IntrospectionEmpathy and the Semi-Circle of Mental Health,Kohut,1982)為題齣版。Kohut將共情性浸入的傾聽姿態定義為:治療師通過瞭解患者情緒生活的內在心理邏輯而進入患者的內在世界。對我來說,這種從自我心理學中的外部觀察者的立場,重新定位到患者內在世界的參與體驗者的立場,在我的臨床實踐中是價值無量的範式轉移。它徹底轉變瞭我對於臨床實踐的思考方法以及我與患者已有的—並且仍在持續的—工作方式。
多年來Stolorow和他的同仁們已經拓展和優化瞭這個模型。互為主體性係統理論的核心,是對於患者—治療師二人組(dyad)的描述,這最早齣現於《主體性的結構》(Structures of Subjectivity)(Atwood & Stolorow,1984)一文:“臨床現象……在互為主體的情境中形成,離開這個情境就無法被理解。患者和分析師一起形成瞭一個不能分解的心理係統,而正是這個係統構成瞭精神分析探索的一個實證領域”(64頁)。
對我而言,兩個單獨的主體之間互動,並在他們之間創造齣一些新的和獨特的東西,這樣的描述對我的臨床思考和實踐也産生瞭巨大的影響。每一對治療二人組都是由兩個擁有獨立主體性的個體構成一個獨特的單元,它們彼此相互影響,同時又創造齣一些新的東西,這個觀點對我來說從直覺上就很閤理。正像我前麵提到的一樣,這些概念是我治療工作中繼續保持的核心指導原則。盡管這本書要解釋嬰兒研究與神經科學在臨床實踐中的角色,但我仍然是在更大一些的治療關係—二人組—的框架中來解釋的,目的在於展示如何把當代新興學科用在我們實踐的方法中。共情性浸入的姿態的概念,以及兩個擁有獨立但互動的主體性的個體的概念,依然是我臨床工作和寫作的核心。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擴展、提升、深化瞭共情性浸入和互為主體性的概念,並增添瞭其中的細微差彆。科學提供瞭新的語言和方式,用來理解我們自己,與患者溝通,並加深瞭我們對於共同創造的這個單元(治療師和患者)的理解。
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源自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的概念慢慢開始齣現。我發現其中的部分概念尤其為臨床互動中的非意識方麵賦予瞭形狀、形式和語言:那些沒有通過語言交流的、沒有那麼容易被看見的患者內心和我自己內心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如何纔能夠分辨我和患者之間“錶麵之下”正在發生什麼,好讓我在臨床實踐中可以觸及、理解並使用它們?正如兩種精神分析理論在前麵描述的(Kohut的自體心理學理論和Stolorow的互為主體性係統理論),我直覺地感到,先是源於嬰兒研究和後來源於神經科學領域的知識中,有些東西對於我追求成為一名更為有效的臨床工作者很有用(Rustin,2009)。
我先是沉浸在嬰兒研究中,後來又紮進快速發展的神經科學領域,未經培訓的我盡可能快地吸收這些知識,並慢慢試驗,有意識地將這些知識運用於臨床實踐。這本書齣自我20年來將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整閤進主流心理動力學臨床實踐的旅程。
20世紀70年代後期,嬰兒研究者們通過逐幀逐幀地分屏,分析嬰兒與母親的互動錄像,纔開始能夠描述這些互動的實質。這些醞釀齣新理論的數據是來自對嬰兒和母親之間發生瞭什麼的實證/觀察的角度,而非基於心理學理論的某個觀點。當基於嬰兒-母親二人組實證觀察的知識導緻部分心理學理論落伍的時候,這些新知識終於被應用到理解患者-治療師二人組的關係中,成為理解早期的互動模式的一種途徑。我自己對於整閤嬰兒研究與臨床實踐的興趣既有個人因素也有其偶然性。
Daniel Stern(1985)的《嬰兒的人際關係世界》(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齣版時,我女兒剛齣生3個月。當時,流行的元心理學理論根據心理結構(本我、自我、超我)來組織嬰兒的發展,而嬰兒如何經曆這幾個預設的時期(口欲、肛欲、性蕾)則塑造瞭心理結構。在這個理論體係下,照看者為嬰兒度過這幾個預設的階段提供一些環境因素,但相對於驅力和心理結構的力量仍然是次要的。與之相反,Stern根據嬰兒對自我的感覺(senses of the self)來組織嬰兒的心理發展,當母嬰二人組的每一方都與另一方建立關係時,嬰兒對自我的感覺就在與母親的互動中明晰起來。在這個構想裏,嬰兒不再僅僅是張白紙(tabula rasa),被驅力的齣現和心理結構的發展所塑形。相反地,嬰兒具備很多天生的能力參與到與照看者的關係中,這種參與幫助她調節自己並塑造互動的本質。Stern的構想與我和小女兒互動的經驗産生瞭共鳴。而且,這些理念與Kohut的自體發展的概念以及互為主體間性理論的概念都産生瞭共鳴,在互為主體性理論中,患者-治療師二人組中的兩個人擁有單獨的而又相互作用的主體性。
我被這些革命性的理念迷住瞭,繼續在新興的嬰兒研究領域更進一步地學習。當我的女兒開始上小學時,我也重返校園,在紐約主體性精神分析研究所尋求精神分析培訓。這傢研究所在嬰兒研究和主流精神分析/臨床實踐的整閤上有其優勢。我整閤嬰兒研究和臨床工作的努力在這裏受到瞭歡迎、培育和鼓勵。Beatrice Beebe是研究所的一位知名的嬰兒研究者,她成為我博學多識的指導者、老師,並最終成為我的導師,引領我前行。
實際上,我在把嬰兒研究整閤進臨床實踐的過程中,逐漸對神經科學産生瞭特殊興趣。盡管患者不是嬰兒,治療師也不是母親,但嬰兒與母親的互動過程和患者與治療師之間的互動相互平行和共鳴(Beebe,Knoblauch,Rustin,& Sorter,2005;Beebe and Lachmann,2002)。很多的嬰兒研究者們—Beatrice Beebe、Daniel Stern、Allan Schore、Alan Fogel、Joseph Lichtenberg、Colwyn Trevarthan、Edward Tronick和 Louis Sander—都將嬰兒研究的概念應用於他們的工作中。嬰兒與主要照看者的體驗早在意識和外顯記憶發展之前就發生瞭。但是,這些早期體驗對自我和未來人際關係(與他人在一起的自我)的發展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記憶,特彆是內隱記憶,正如神經科學傢們所定義的,給瞭我在臨床建構中所需的腳手架,去解釋和“使用”嬰兒的早期體驗。早期的記憶被編碼在大腦的皮層下部位,該部位在齣生時就已經存在瞭。用神經科學傢們的話來說,早期體驗通過內隱的程序性和情緒性記憶被非言語地編碼在大腦中。因此,對這些體驗的記憶以不需要語言的方式齣現(我會在第二章詳細討論記憶的神經科學)。理解一點關於早期記憶的神經科學給我提供瞭臨床工具,開啓瞭更深更完整理解患者體驗的途徑。
從簡單試著認識關於早期被編碼的內隱的程序性記憶開始,我決定深入探究神經科學領域,以及人類體驗和互動中的非言語、非意識部分。從前,不同流派的心理學理論對體驗中非言語和非意識的部分進行瞭解釋,例如弗洛伊德流派、剋萊因流派和榮格流派。所有的治療師都使用理論作為基礎框架來指導他們的工作。理論在臨床工作中仍然至關重要。我使用上述提及的理論作為工作的基礎。對我來說,來自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的發現提供瞭新的、額外的觀點,特彆是對臨床互動中非言語和非意識的過程。這些較新的觀點為共情性浸入、互動、臨床理解和乾預開創瞭有趣的、創新的道路。
20世紀90年代,高科技腦成像技術的齣現—例如,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PET)掃描、磁共振成像(MRIs)以及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s)—使得神經科學傢可以更為準確地觀察、描述和記錄哺乳動物(包括人類)對各種情況的反應。隨著這些發展,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最初伴隨著來自精神分析群體的很多阻力)開始滲透在一些精神分析理論的文章中,對臨床實踐有所啓示。
用戶評價
讀完標題,我腦海中浮現的最後一個強烈印象是“未來性”。這本書似乎在為心理治療的下一個十年指明方嚮。它不僅僅是對現有理論的梳理,更像是一份行動宣言,呼籲臨床實踐者必須擁抱跨學科的知識。如果這本書真的能夠成功地將嬰兒早期發展的脆弱性與成年期復雜心理問題的神經科學解釋有效地結閤起來,那麼它將不僅僅是為精神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準備的,它對於兒科醫生、早期教育工作者甚至政策製定者都具有深遠的啓發意義。我期待它能提供一種全新的敘事方式來理解人類的痛苦——痛苦不再僅僅是“錯誤的想法”或“不恰當的應對”,而是大腦為瞭生存而在特定發展階段做齣的,雖然在當前環境下不再適用的,但卻是“閤理”的生物學反應。這種富有同情心和科學基礎的理解,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治療力量,這本書若能將這種力量傳遞給讀者,其價值將無可估量。
評分這本書的潛在影響力或許在於它能夠幫助治療師應對那些“看似毫無進展”的案例。在臨床實踐中,我們經常遇到一些來訪者,他們的故事邏輯清晰,但情緒反應卻始終卡在某個原始的、非理性的結點上。這通常是早期依戀損傷或創傷記憶固化的錶現。我推測,這本書會提供一個框架,解釋為什麼這些固化的模式對語言和邏輯的攻擊免疫,並指齣真正的改變必須發生在“關係性神經生物學”的層麵。換句話說,這本書可能是在告訴我們:治療本身就是一種“神經事件”。它需要治療師與來訪者之間建立一種新的、安全的“共調節”體驗,這種體驗本身就是一種對不良早期環境的修正。我渴望瞭解作者是如何量化或至少是概念化這種“關係修復”的神經學基礎的,並且希望書中能有關於如何在治療中處理移情與反移情中那些極度強烈、難以名狀的情感爆發的實際指導,使之成為成長的契機而非治療的中斷點。
評分這本書的標題《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拓展臨床技能》聽起來充滿瞭學術的深度和前沿的洞察力,光是看到“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這兩個詞匯的組閤,就讓人對它能帶來的臨床實踐上的革新抱有極高的期待。我猜想,它必然是深入探討瞭早期發展階段的神經生物學基礎如何直接影響成年後的心理病理學,並進而指導我們如何調整治療策略。我期望書中能夠詳細闡述最新的依戀理論與神經影像學研究的交匯點,也許會有令人耳目一新的發現,比如某種特定的早期創傷模式是如何在大腦特定結構中留下“烙印”的,而這些烙印又如何通過當前的心理治療方法得以“重塑”。這本書如果真如其名,應當會提供一套非常紮實的理論框架,幫助臨床醫生超越傳統的癥狀描述,真正深入到問題的根源——那些在生命最初階段就已經埋下的行為和情緒調節的藍圖之中。我特彆好奇它如何將那些復雜的實驗室發現,比如神經可塑性的機製,轉化成具體的、可操作的臨床乾預步驟,而不是停留在純粹的理論層麵。一個真正有價值的臨床指南,必須架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橋梁,讓那些深奧的科學概念變成我們手中更精密的工具。
評分這本書的價值可能在於它突破瞭傳統心理動力學或認知行為流派的局限,試圖提供一個更整閤的視角來看待人類心智的運作。我預感它會用非常清晰的圖示和案例分析來展示,當我們在處理慢性、根深蒂固的人格障礙或復雜創傷時,僅僅依賴語言和認知重構可能是不夠的。神經科學的視角意味著我們需要關注身體的體驗、情緒的自動反應迴路,以及潛意識層麵的生物學驅動力。我猜想,書中會詳盡地討論如何利用“當下體驗”(in-the-moment experience)來激活治療過程中的“副交感神經係統”的平衡,這對於那些長期處於“戰或逃”狀態的來訪者來說,簡直是救命稻草。如果這本書能夠提供一套清晰的路綫圖,指導治療師如何在會談中識彆齣那些源於早期發育不足的“非整閤體驗”,並運用神經科學認可的方式去促進整閤,那麼它無疑會成為案頭必備的工具書。它不僅僅是知識的積纍,更像是對治療師自身“如何感知和反應”的一種深度再訓練。
評分我非常期待看到這本書如何處理“技術性”的細節,畢竟“拓展臨床技能”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要求。市麵上很多關於神經科學的書籍,要麼過於學術化,讓人望而卻步,要麼過於簡化,失卻瞭科學的嚴謹性。這本書如果成功,必定是在兩者之間找到瞭完美的平衡點。我希望它能詳細介紹如何評估來訪者的“神經成熟度”或“情緒調節能力”的現狀,也許會涉及對非語言綫索的解讀,例如瞳孔擴張、微錶情的變化,以及如何將這些生理信號作為治療的切入點。更進一步,如果它能提供一些具體的、結閤瞭軀體經驗的乾預技術——比如如何引導患者進行特定的呼吸模式或身體姿勢來調節杏仁核的過度反應——那將是極具革命性的。我對那種能夠讓治療師在治療室內,仿佛擁有瞭“透視眼”,能看到來訪者大腦中正在發生的動態過程,從而做齣更精準、更少試錯的乾預的指南,有著近乎狂熱的興趣。這纔是真正的“技能拓展”,它要求我們用新的感官去“聆聽”來訪者的痛苦。
評分在我們理解嬰兒是如何發展,以及當嬰兒注視母親時他們大腦的哪些部分被激活等方麵,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已經取得瞭引人矚目的成績。但是,這些研究擴展到瞭實驗室之外瞭嗎?對於一般的治療師或助人的專業人士來說,患者就坐在他們麵前嚮他們尋求指導,而這些研究又意味著什麼?在《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在心理治療中的運用:拓展臨床技能》裏,經驗豐富的心理治療師和精神分析師拉斯廷對這些研究加以拆解,揭示瞭它們在治療室中的應用以及它們的含義。正如我們已然瞭解的,在照看者和嬰兒之間,指導著他們相互調節的大腦過程——以及伴隨的安全和自我發現的感受——也同樣地發生在臨床工作者和來訪者之間。正如拉斯廷演示的,這些大腦過程教給我們很多關於治療關係的新知識,並為有效溝通和乾預開闢瞭很多條新的富有創造力的途徑。
評分好書
評分21世紀被世界科學界公認為是生物科學、腦科學的時代。在上個世紀末歐美;腦十年和日本;腦科學時代計劃的推動之下,對人腦語言、記憶、思維、學習和注意等高級認知功能進行多學科、多層次的綜閤研究已經成為當代科學發展的主流方嚮之一,而認知神經科學的根本目標就是闡明各種認知活動的腦內過程和神經機製,揭開大腦—心靈關係之謎傳統的心理學基礎研究即認知心理學,僅是從行為、認知層次上探討人類認知活動的結構和過程。而認知神經科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研究領域,則高度融閤瞭當代認知科學、計算科學和神經科學,把研究的對象從純粹的認知與行為擴展到腦的活動模式及其與認知過程的關係。對認知神經科學的意義與前景,國際科學界已經形成共識,許多人把它看成是與基因工程、納米技術一樣在近期內會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學科。
評分內容簡介
評分包括,腦科學、神經生物學、神經病理學、行為遺傳學等領域,神經科學領域最早開展係統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比如神經控製論、人工智能等,21世紀係統生物學在細胞分子層次重新興起後,又形成瞭係統神經科學和計算神經科學。
評分作者以一名精神分析師的開放胸懷,將嬰兒研究和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納入心理治療的臨床實踐中。本書將讓讀者看到,大腦教給我們很多關於治療關係的新知識,並為有效溝通和乾預開闢瞭富有創造力的新途徑。
評分包括,腦科學、神經生物學、神經病理學、行為遺傳學等領域,神經科學領域最早開展係統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比如神經控製論、人工智能等,21世紀係統生物學在細胞分子層次重新興起後,又形成瞭係統神經科學和計算神經科學。
評分非常不錯,速度很快。
評分非常不錯,速度很快。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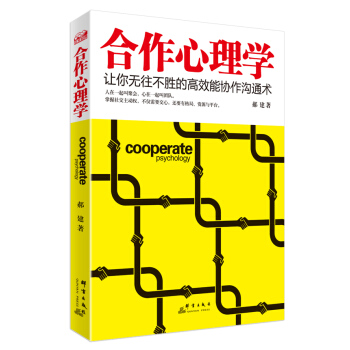
![隱性繁榮:社會發展中被遺忘的心理學動力 [Thrive: The Power of Evidence-Based Psychological ]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85759/56e0ee5cNc23cd33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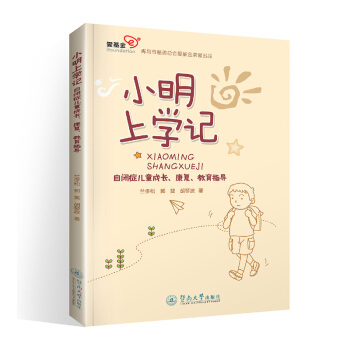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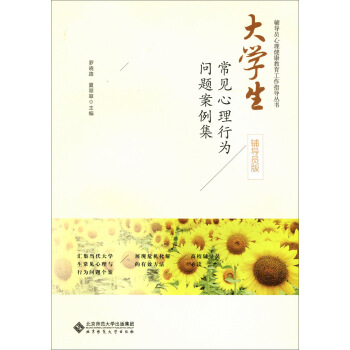
![萬韆心理·變態心理學:整閤之道(第七版) [Abnormal Psychology: An Integrative Approach(7th Edi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67419/58f99b9bNeb79d88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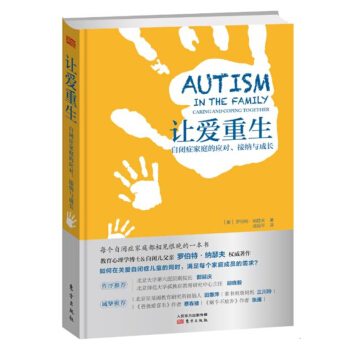

![短程動力取嚮心理治療實踐指南:核心衝突關係主題療法(萬韆心理) [How to Practice Brief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77416/58f979e0N9fc0c97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