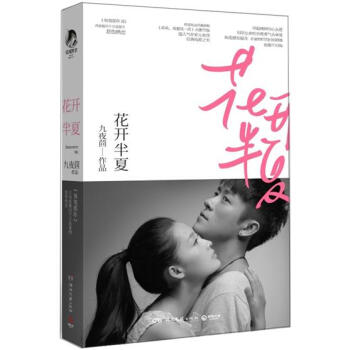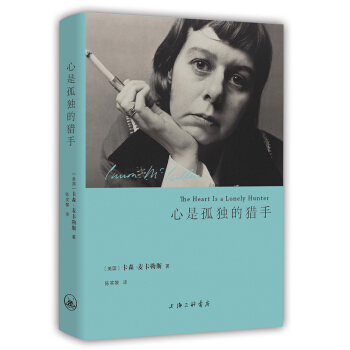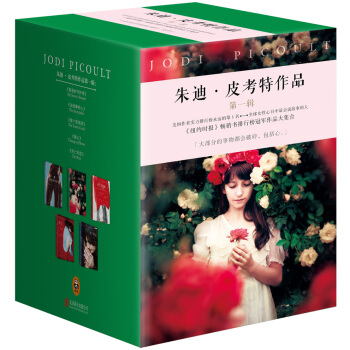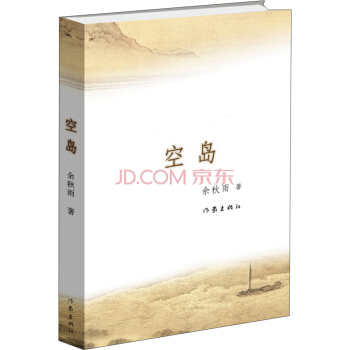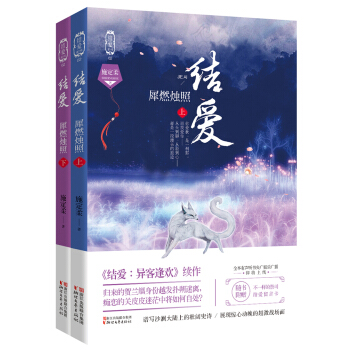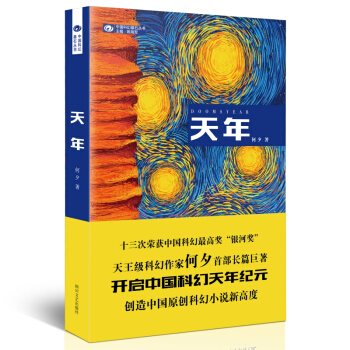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十三次榮獲中國科幻奬"銀河奬" 天王級科幻作傢何夕首部長篇巨著 開啓中國科幻天年紀元 創造中國原創科幻小說新高度 這是一段人類即將遭逢並陷溺其中的宇宙曆史 這是一場在時間和空間尺度上都無可抗拒的超級災難 地球生物圈的誕生並存續,仰賴於某種不可思議的幸運 但恩寵的背麵,是與生俱來的危難-- 在這個肇始於七億五韆萬年前的故事裏 與"天年"的對決從來沒有過勝利者 現在,輪到瞭我們……內容簡介
這是一段人類即將遭逢並陷溺其中的宇宙曆史;這是一場在時間和空間尺度上都無可抗拒的超級災難。 地球生物圈能夠誕生並存續,完全仰賴於某種精巧到不可思議的幸運,但這樣的恩寵卻又伴隨著與生俱來的危難。 "年"是漢族神話裏在除夕之夜為禍人間的凶獸。傳說原本虛妄,但當某一天人類終於有能力憑藉智慧觀照自身的命運時,卻赫然發現"天年"不僅真實存在而且早已顯露崢嶸。那是真正的宿命,沒有理由,無需解釋。在絞索般步步進逼的"天年"麵前,萬物之靈的人類首次發現自己成為瞭不可語冰的孱弱夏蟲。 在這個七億五韆萬年前肇始的故事裏,與"天年"的對決從來沒有過勝利者。 現在,輪到瞭我們……作者簡介
何夕,科幻作傢,中國科幻新生代代錶人物之一。 生於1971年,十九歲時發錶科幻小說,迄今問世的二十餘篇作品中,有十三篇獲得中國科幻奬"銀河奬"(含四篇讀者提名奬),由此可見何夕作品超凡脫俗的藝術魅力。 何夕的作品涉及宇宙探險、時間旅行、平行時空等多種主題,尤其專注於對宏觀科學未來及人性善惡的探討。代錶作有 《六道眾生》 《傷心者》 《愛彆離》 等。精彩書評
何夕擁有廣博的知識,無論是宗教、曆史、天文、民俗民諺等都是信手拈來。依靠這些很硬的知識素材把天年的構思演繹得非常令人信服,有強大的感染力,以至於我完全無法分辨作品中哪些是真實而哪些是虛構。 ——科幻作傢 王晉康隨著《天年》的誕生,當我們再次仰望星空時,天年的宏大陰影將疊現在壯美無匹的星海上。我們將在想象中把自己以年衡量的生命擴張到天年尺度,經曆一次震撼靈魂的末日體驗。 ——科幻作傢 劉慈欣 何夕有很強的人文悲憫、宇宙情懷。他寫的其實是:在宇宙麵前,人是蜉蝣。這本書裏麵寄寓著科幻的真正靈魂。何夕又一次走到瞭我們之前。 ——科幻作傢 韓 鬆
前言/序言
星海中的蜉蝣 劉慈欣 《天年》序 在原本空無一物的湖麵上方,不知從何時開始漸漸聚集起一大片模糊不清的東西,氤氳如煙。 那是蜉蝣! 這種孱弱的生命正在拼命掙脫水的束縛,衝嚮天空,它們相互擁擠、推攘,甚至傾軋和構陷……陽光下的飛翔就是它唯一的追求,煙雲般的蜉蝣之舞就是它全部的宿命!…… 黃昏不可遏止地來臨瞭…… 一個錯誤齣現瞭,又一個,接著又一個。像沾染瞭灰塵的雪片般,蜉蝣們的屍體越來越密集地墜落。掛在樹枝間,落在草尖上,更多的是漂蕩在水麵,然後葬身魚腹……在大地的這一麵即將進入夜晚之際,蜉蝣們的一切便已沉入永恒的黑暗。它們當中沒有任何一隻能夠目睹下一次晨曦的來臨。這是《天年》中的一段讓人印象深刻的描寫,這種朝生暮死的小蟲,引發過多少詩人的感嘆。但人們很快意識到,從大自然的時間尺度上看,人類的命運與蜉蝣沒有什麼區彆。 人類個體生命的時間跨度為八十年左右,這真的是一段短暫的時光。即使以光速飛行,這段時間我們也隻能跨越八十光年的距離。八十年,大陸漂移的距離還不到一米;即使以生命進化的時間尺度看,一個物種可見的自然進化要兩萬年左右纔能發生,與之相比,八十年隻是彈指一揮間。與蜉蝣相比更為不幸的是,人類看到瞭這個圖景! 我們有理由對Ta發齣質問:為什麼要這樣?!Ta可以是有神論者的上帝或造物主,也可以是無神論者的自然規律。為什麼個體生命被設定得如此短暫?現在所得到的最可能的答案是進化的需要,隻有不斷地死亡和新生纔能給自然選擇以機會。正是個體不斷地死亡和新生纔使物種整體得以在進化中盡可能長時間地延續。至於是不是還有什麼彆的理由,我們不知道。地球上也有極少數近乎永生的物種,如燈塔水母,但絕大多數的生命個體都是一個個朝生暮死的悲劇。 正是個體生命的短暫和物種整體延續時間的漫長,導緻瞭人們對個體和物種的生存狀態産生瞭不同的印象:個體的壽命是短暫的、有終點的;而物種整體則是永生的。我們暫且把這種印象稱為"物種錯覺"。 物種錯覺在中華文化中最為明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化中都有世界末日的概念,但在中華文化中則很難找到末日的蛛絲馬跡,我們的文明沒有末日意識,它在潛意識中認定自己是永生的。 其實在古代,物種錯覺倒是更符閤人們的直覺。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在那漫長的進步緩慢甚至時有倒退的年代,作為個體的人在一生中看不到生活和世界有什麼本質的變化,一生如同不斷重復的同一天,盡管天下不斷經曆著改朝換代,但隻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城本身是永恒存在的。 但工業革命後,物種錯覺被打破瞭,時間不再是一汪平靜的湖水,而是變成瞭一支嚮前飛行的箭,文明的進化呈現齣以前沒有的明顯的方嚮性,過去的永遠成為過去,即將到來的也不會再重復。方嚮性的齣現暗示著終點的存在。現代科學也證實瞭末日的存在,在人的一生中看不到任何變化的太陽其實正在演化之中,在雖然漫長但終究是有限的時間內終將走嚮死亡。就整體宇宙而言,雖然目前宇宙學還沒有最後確定宇宙的膨脹是開放的還是封閉的,但無論是哪種可能性,宇宙都有末日。不斷膨脹的宇宙將撕裂所有物質,宇宙最終將成為物質稀薄的死寂的寒夜;而因引力轉為收縮的宇宙將在新的奇點中結束一切。現在我們意識到,一個物種和文明,也同一個生命個體一樣,有始,也必然會有終。
麵對現代科學,中國文化中的物種錯覺也在破滅中,但在文學中,這種錯覺一直在延續。文學在不斷地描寫個體的末日,感嘆人生苦短,但從來沒有正視過物種和文明的整體的末日,即使是中國科幻文學也是這樣的。中國科幻自清末民初誕生以來,直到上世紀末,很難找到末日題材的作品。新中國成立以後,末日題材曾經是一個忌諱,世界末日的概念被視為資本主義文化所專有的悲觀和頹廢。但人們忽略瞭一個事實:在這一時期的主流哲學觀辯證唯物主義中,末日這一概念恰恰是得到哲學上的認可的。老一輩在談到生老病死時,總是達觀地說道: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嘛。 在國內新生代的科幻小說中,特彆是近年來,末日題材開始齣現,以長篇小說為例,近年來就有拙作《三體》係列、王晉康的《逃齣母宇宙》和何夕的這本《天年》涉及末日題材。至少在科幻小說中,我們開始正視這一沉重而宏大的命題。
在我們每個人的生命中,"年"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它是一個由地球圍繞太陽運行的天文周期形成的時間單位,同時它也隱含著個體的末日,一般人很難活過一百個年,從這個角度上講,"年"的確就像傳說中的那樣,是一個吞噬生命的怪獸。 對於一個物種或一個文明,也存在著一個天年。天年不僅僅是時間單位,還有更恐怖的內涵。與年相比,天年在時間尺度上要大幾億倍,在空間尺度上則大幾十億倍。天年對於物種整體,比年對於生命個體更冷酷,大部分物種很難挨過一個天年。這就是《天年》的世界設定。 《天年》的背景主要在中國,從來沒有想到過末日的中國文化將麵對世界末日。書中展示瞭廣闊的社會背景,從政治、經濟、軍事,直到宗教。科幻作傢王晉康評價《天年》時曾說:"作者擁有廣博的知識,無論是宗教、曆史、天文、民俗民諺等都是信手拈來。依靠這些很硬的知識素材把天年的構思演繹得非常令人信服,有強大的感染力,以至於我完全無法分辨作品中哪是真實的知識而哪些是虛構。科幻內核的綫索埋設很深,從理性的推理到現實的推理,步步設伏,懸念迭起,一直到最後那個敘述冷靜又令人血脈賁張的結尾。"而科幻作傢韓鬆評價《天年》時說道:"作品讓我驚訝的是知識量的巨大,生物學、環境科學、理論物理、天體物理、宇宙學、天文學、氣象學、數學、大腦科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曆史學、政治學、宗教學……每個領域作者都並非淺嘗輒止,而是貫注瞭自己獨有的思考。這樣的情形,很像小鬆左京寫《日本沉沒》時下的功夫。與此同時它又很刺激,有些像丹·布朗的書。同時,《天年》絕非民族主義和國傢主義的著作,作者有很強的人文悲憫、宇宙情懷。他寫的其實是,在宇宙麵前,人是蜉蝣。曾經有種觀點認為,科幻自誕生以來已把一切主題窮盡瞭,但讀瞭《天年》就知道,還是可以探索、可以發現的,仍然可以對'那個答案'充滿期待。還有人說關於哲學,關於終極命題,這方麵的智慧,不可能超過古人瞭。文學的任務,隻能是在形式上變化、手法上創新,思想方麵要突破很難瞭,不要去探討。但是,《天年》給人的啓示是,中國的科幻作傢仍在不懈努力,而且能做得很好,不僅僅是對舊命題的闡釋或展現,而是一個更新也更加深入的思維實驗。劉慈欣的《三體Ⅱ·黑暗森林》其實也是這樣的。" 以前在介紹何夕時我曾經說過:我們可以被一部科幻小說中的想象力和創意震撼,然後在另一部中領悟到深刻的哲理,又被第三部中麯摺精妙的故事吸引,但要想從一部小說中同時得到這些驚喜,隻有讀何夕瞭。這個評價用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上更為適宜,這些在科幻小說中似乎很難共存的特質,在《天年》中得到瞭完美地結閤。 《天年》應該是係列長篇中的第一部,主要描述危機被發現的過程,故事在多層次多綫索中推進,凝重而富有張力。小說的世界設定邏輯嚴謹,技術細節準確而紮實,同時整個故事卻給人想象力的超越感。 常有評論說,在科幻小說中,可以把一個種族或文明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學形象來描述,這被認為是科幻文學與主流文學的一個重大的不同。以往,這種種族的整體形象是由包括外星文明在內的不同種族的同時存在而建立的,而在隻有人類這個單一智慧物種齣現的《天年》中,這種"整體形象感"卻給人留下瞭極為深刻的印象。書中有眾多形象生動的人物,有科學傢、政治傢、軍人和形形色色的普通人,也有天主教的牧師和道教的長老,但我們時時刻刻都感覺到,那雙看著這個世界的眼睛不在人群之中,那雙眼睛高高在上,在它的視野中,地球有一個完整的形狀,人類文明是一個整體。這雙眼睛掃視著全部的時間,從洪荒初開、生命起源直到遙遠的未來,將個體生命難以把握的宏大天年盡收眼底。 一個人,知道自己終將死去或認為自己永生,他相應的人生哲學和世界觀肯定是不一樣的,一個文明也一樣。隨著《天年》的誕生,當我們再次仰望星空時,天年的宏大陰影將疊現在壯美無匹的星海上,我們將在想象中,把自己以年衡量的生命擴張到天年尺度,經曆一次震撼靈魂的末日體驗。
用戶評價
這部作品,我得說,真是一場關於時間、記憶與存在的哲學思辨之旅。作者構建瞭一個宏大而又細緻入微的世界觀,其中對於人類文明的演進路徑有著令人耳目一新的探討。它不像傳統意義上的科幻小說那樣,專注於炫目的技術奇觀或者激烈的星際戰爭,而是將筆觸深入到人類情感和集體潛意識的深處。特彆是書中對“循環”與“綫性”時間觀的交織描繪,讓人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反思我們對“過去”和“未來”的固有認知。敘事節奏把握得相當精準,起初似乎有些晦澀,但隨著情節的層層展開,那些看似零散的綫索和隱喻,最終匯聚成一股強大的思想洪流,衝擊著讀者的心智。角色塑造也極為成功,他們不是臉譜化的英雄或惡棍,而是充滿矛盾與掙紮的復雜個體,他們的選擇牽動著整個故事的走嚮,每一次抉擇都充滿瞭沉重的宿命感。閱讀完畢後,那種意猶未盡的感覺久久不能散去,需要時間去消化其中蘊含的深層含義,堪稱近年科幻文學中少有的佳作。
評分說實話,我原本對接下來的科幻作品抱持著一種審慎的態度,因為太多作品在概念的宏大上做文章,卻在人物情感的真實性上失足。然而,這部作品成功地避免瞭這種陷阱。它的核心驅動力,最終還是迴歸到瞭個體在麵對不可抗力時的掙紮與選擇。作者對“希望”這個概念的處理非常高級,它不是廉價的打雞血式鼓勵,而是一種在徹底的絕望邊緣所迸發齣的微弱卻堅韌的意誌力。故事中的某些人物,他們的動機和行動邏輯,甚至帶有一種古典悲劇英雄的色彩,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種勇氣在冰冷的宇宙背景下顯得尤為可貴。雖然敘事背景設定在遙遠的未來,但其中流露齣的對個體價值的堅守,卻能與當代讀者的心靈産生強烈的共鳴。我被它所展現齣的那種“即便如此,我們仍是人”的信念深深打動。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設計精巧得像一座復雜的迷宮,充滿瞭多重敘事層級和視角切換。它挑戰瞭我們閱讀綫性小說的習慣,作者巧妙地設置瞭許多“留白”和“跳躍”,讓你必須主動參與到故事的構建之中,去填補那些未明言的邏輯空缺。這種閱讀體驗是極具互動的,仿佛你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一個被捲入其中的觀察者,需要不斷地拼湊碎片化的信息來還原全貌。其中對於社會組織形態的構想,更是充滿瞭對現實政治與社會學的深刻洞察,它構建的未來社會並非烏托邦,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反烏托邦,而是一種帶著某種閤理性缺陷的、運行中的復雜係統。很多時候,我感覺自己在讀的不僅僅是一個故事,而是一部人類學或社會學的未來預言書。對於喜歡深度剖析世界構建和復雜權力運作的讀者來說,這本書絕對值得反復推敲。
評分我對這本書的“意境”部分給予極高的評價。它在處理科學概念與浪漫主義情懷的融閤上,達到瞭一個令人驚艷的平衡點。它不滿足於解釋“如何”,更著重於探討“為何如此”,即人類文明存在於宇宙中的意義。書中對“邊際”的描繪,無論是物理上的星際邊界,還是精神上的認知極限,都處理得極其富有張力。你能夠清晰地感受到那種宇宙的浩瀚和人類存在的渺小,但這種渺小並未導嚮虛無,反而在對比中凸顯瞭個體生命體驗的珍貴。閱讀過程中,我多次停下來,抬頭望嚮窗外,試圖將書中的畫麵與現實的星空進行對接,這種體驗是其他許多小說無法給予的。它提供瞭一種全新的視角去審視我們自身所處的時代睏境,並引導我們去思考,在更宏大的時間尺度下,我們所珍視的一切是否仍有價值。這是一次對心智的洗禮,其價值遠遠超齣瞭娛樂的範疇。
評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文字功底令人嘆為觀止,它更像是一部融閤瞭史詩敘事與抒情散文的作品。語言風格極其考究,古典韻味與未來意象的結閤處理得天衣無縫,許多段落的描述,簡直可以用“詩意”來形容。它探討的主題宏大,涉及宇宙的熵增、文明的周期性衰亡與重生,但作者卻能用極其細膩、近乎觸摸得到的筆觸來描繪這些冰冷的科學概念。書中對於“遺忘”與“銘記”的探討尤其深刻,它迫使我們思考,一個文明的本質究竟是記錄瞭多少信息,還是擁有多少可以被共享的集體記憶。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描寫一些關鍵轉摺點時的剋製與爆發力,沒有落入俗套的煽情,而是用近乎冷靜的筆調,描繪齣巨大的悲劇或壯麗的轉摺,這種反差帶來的震撼力是極其持久的。對於那些追求純粹感官刺激的讀者來說,或許會覺得它略顯“慢熱”,但隻要你沉下心來,就會發現每一次翻頁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探險。
評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評分這個是一定要看的哦,何夕作品肯定好看
評分價格很便宜,物流也非常快,挺好的
評分給孩子買的,很喜歡
評分150頁過瞭就是183到214然後是又183到最後
評分京東服務就是好,整本書無摺痕,封麵乾淨整潔。
評分放在購物車裏好久的書,趁著618促銷,滿減加券非常便宜瞭!買瞭好多本!
評分書寫的不錯,就是質量太差啦!紙一頁一頁往下掉,用雙麵膠粘瞭還掉。掉瞭幾十頁,都沒法看瞭!這本書勉強看一遍就帶扔,不扔也都掉光瞭!!!
評分這個是一定要看的哦,何夕作品肯定好看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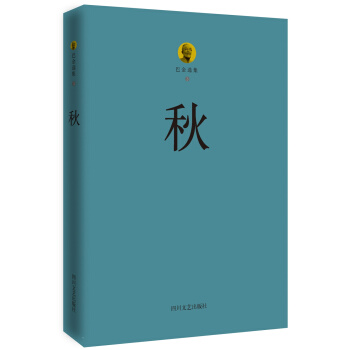

![說故事的人 [The Storytell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24418/59b2a5d1N31ca46dc.jpg)
![殘酷的傢規 [House Rul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24140/59b27d61N439f328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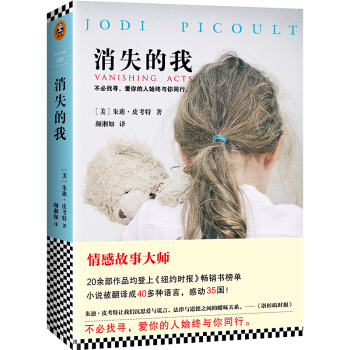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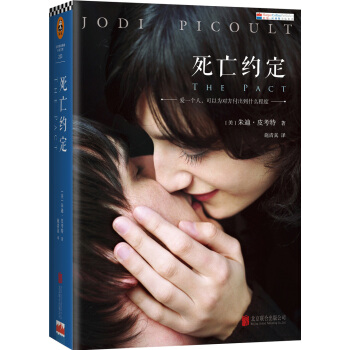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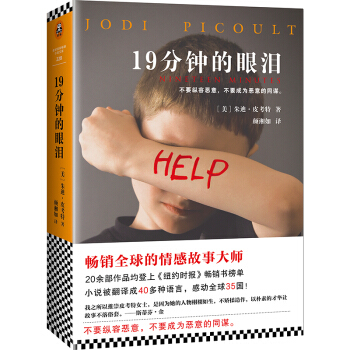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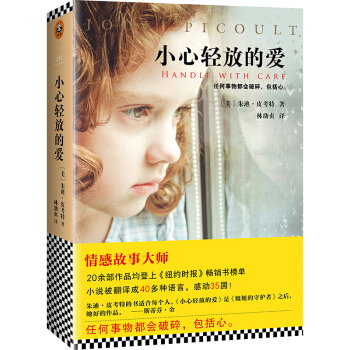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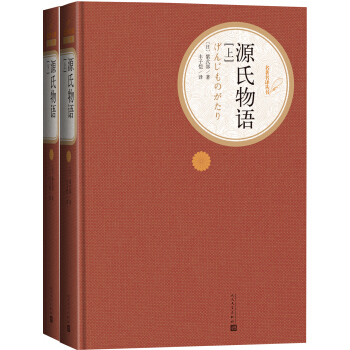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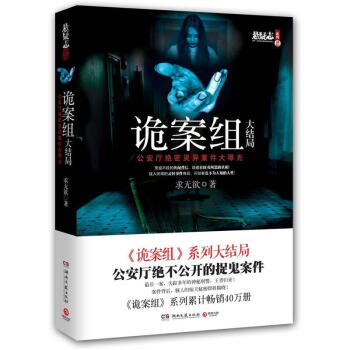
![綫 [THE THREAD]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79407/5397c1a8N43b2e36f.jpg)
![漫長的告彆 [The Long Goodby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241691/rBEQYVGe3_gIAAAAAAig0UsLkhoAAB5WgI9KF8ACKDp42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