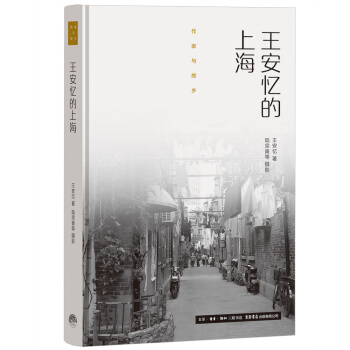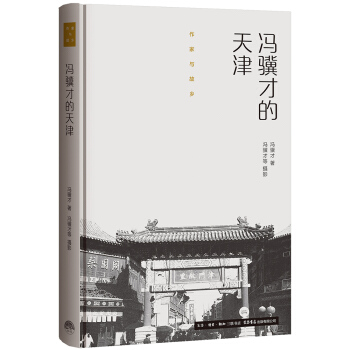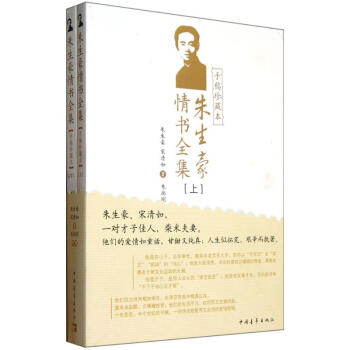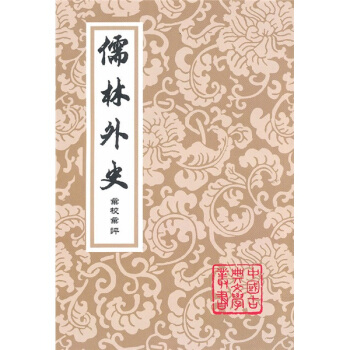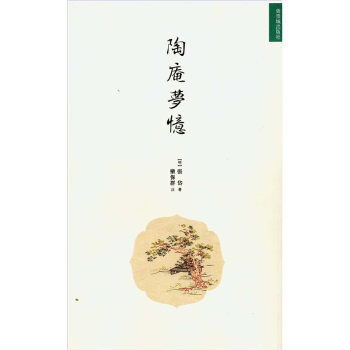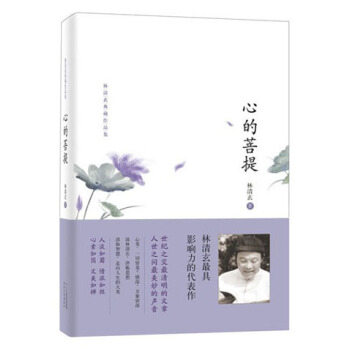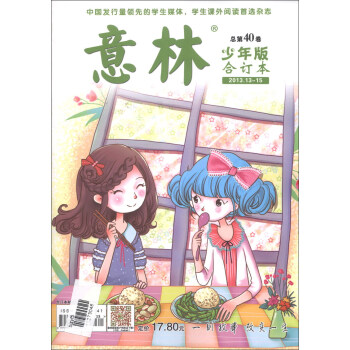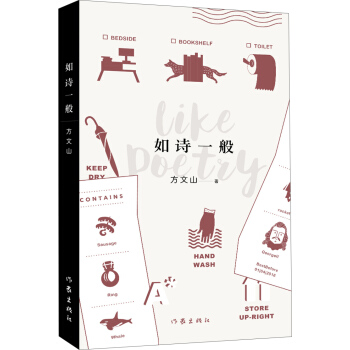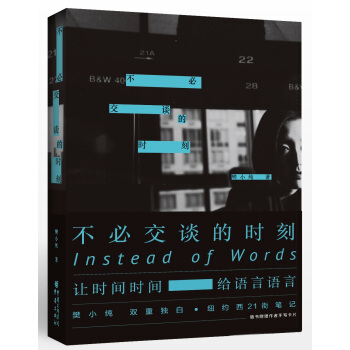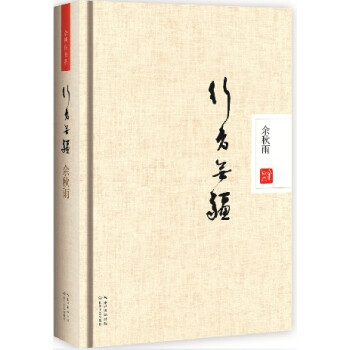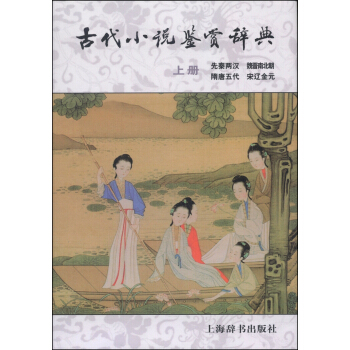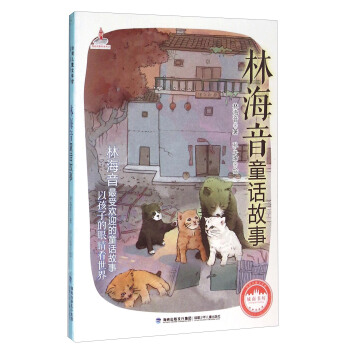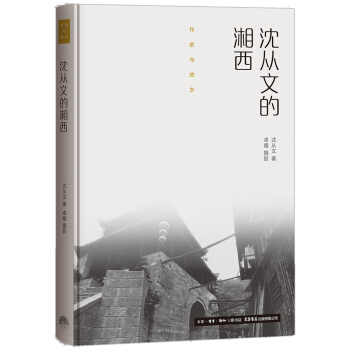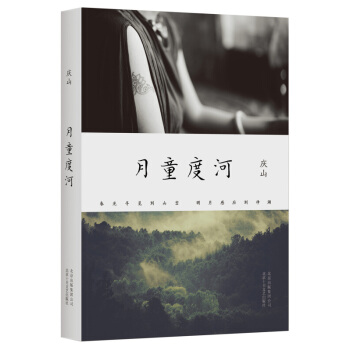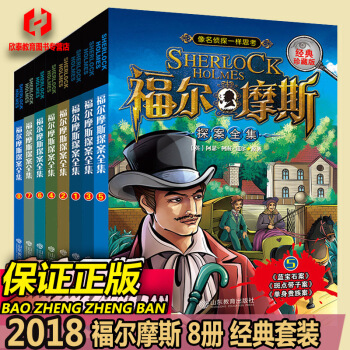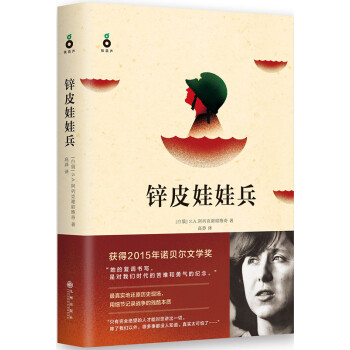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本书为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成名作,真实地还原历史现场,用细节记录战争的残酷本质。“娃娃兵被装到锌皮棺材里运回家时,母亲在墓地里讲述儿子的事,仿佛他们还活着。”“只有完全绝望的人才能对您讲出一切。除了我们以外,很多事都没人知道。真实太可怕了……”
本书为中文版正版引进,根据作者新修订的完整版翻译。
阿列克谢耶维奇被看作当今世界文坛的“黑马”,连续两年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决选名单,并获得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世界文坛开创了崭新纪实体裁。她的作品被译为35种文字,屡获大奖。
内容简介
《锌皮娃娃兵(精装)》内容简介:
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很快,阿富汗各派游击队逐渐结成联盟,同入侵者和阿富汗政府军展开了游击战争。本书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孩子的血泪记忆,是20世纪纪实文学经典作品。
作者简介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S.A.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白俄罗斯作家,1948年生于乌克兰,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曾做过记者,作品以独特风格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重大事件。
曾多次获奖,包括瑞典笔会奖(1996)、德国莱比锡图书奖(1998)、法国“世界见证人”奖(1999)、美国国家书评人奖(2005)、德国书业和平奖(2013)等。
2013年、2014年,连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入围决选名单,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目前其作品已在全世界被翻译成35种文字,并创作有21部纪录片脚本和3部戏剧(曾在法国、德国、保加利亚演出)。
目录
目 录
前 言
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 002
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005
我们彼此太贴近了,任何人都休想逃避 012
第一天
作者的话 020
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 022
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 029
人们在那边靠仇恨生存 032
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一切 041
我们好像已经是死人了 043
我们在忏悔 048
为什么逼我回忆 054
这里造就的都是扭曲的人 058
我感到羞耻 064
我的小太阳 075
如今我什么也不信了 078
忘掉你曾有过两条腿 084
人死的时候完全不像电影里那样 087
你们不要叫我儿子的名字 090
我把自己的一生全忘了 098
第二天
作者的话 102
杀人就是为了能回家 104
我仍然在哭泣 109
我不愿意当政治错误的牺牲品 114
活着回家 117
我在等他回来 124
我想像个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132
我在那边杀过人吗 144
我们出发时从不握手告别 147
他们死的时候不声不响 153
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159
我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什么人 163
只有完全绝望的人才能说出一切 169
这里的人都不愿意谈起未来 174
人身上能有多少人味 177
您浑身都沾着我儿子的鲜血 185
死亡就是这样 190
我要活着 194
第三天
作者的话 200
请在坟头上挂块牌子 202
为什么我只能想起可怕的事 205
我梦见的是棺材 212
朝着地雷前进 215
活石头 222
“快把我妈妈还给我” 226
“我想把儿子留在家里” 230
也许她还活着 233
我以为所有人都能变得善良 239
难道我能说“我怀疑” 243
什么是真理 249
为什么我要忍受这么大的痛苦 252
我没有人可以等待了 255
我有眼睛时比现在瞎得更厉害 262
“我亲爱的妈妈” 268
后 记
我是通过人说话的声音来聆听世界的 280
精彩书摘
【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
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我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一秒钟内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然后,用一口棺材装上一套军礼服,运回国去。棺材里还得再装些外国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
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
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
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
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
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我们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
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杜什曼:苏联军人对阿富汗武装人员的称呼。
],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
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日本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已无事可做。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有个小伙子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恨透了他们。当我们在那边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地雷时,他们在这儿听音乐,和姑娘们跳舞,看各种书。在那边,谁没有和我生死与共,没有和我一起耳闻目睹一切,没有和我实地体验与感受,那么,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分文不值。
等到十年以后,肝炎、挫伤、疟疾在我们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让我坐上主席台。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您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难道你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讲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潭里,他们的血混在一起,能讲出来吗?谁还需要这样的书呢?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家、我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婴儿,还有从那边回来的几个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
—一位列兵、掷弹筒手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读完之后,我最深的感受是,作者是如何将如此寻常的物件,赋予了如此深刻的意义。我一直以为,一本关于“锌皮娃娃兵”的书,顶多就是关于玩具的收藏或者历史,但这本书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微妙。我从书中看到了关于忠诚、关于牺牲、关于孤独,甚至关于战争的隐喻。那些看似僵硬的锌皮娃娃兵,在作者的笔下,却有了鲜活的生命,它们拥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恐惧,以及自己的渴望。我尤其被书中关于“沉默的守候”的描写所打动,那些娃娃兵可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见证了世事的变迁,却始终如一地守护着某个地方,某个秘密,或者某个心愿。这让我反思,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也有一些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锌皮娃娃兵”?它们可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是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凡事物,但它们的存在,却构成了我们世界的重要基石。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它让我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那些被遗忘的角落和不为人知的努力。
评分我必须说,这本书的文学性非常高。它不仅仅是在讲一个故事,更是在探讨一种存在的哲学。我从书中感受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那些比喻、拟人化的描写,将冰冷的金属赋予了温度,让每一个锌皮娃娃兵都仿佛拥有了灵魂。我曾读过很多关于历史和战争的书籍,但很少有能像这本书一样,从如此微小的视角,展现出宏大的主题。它让我思考,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作用,以及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是否也隐藏着伟大的故事。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时间”的描写,那些娃娃兵仿佛是时间的凝固,它们见证了岁月的流逝,承载着过去的记忆。这本书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即使是短暂的生命,也可以创造出永恒的价值。它没有激烈的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是持续性的,即便读完,我脑海中依然回响着那些锌皮娃娃兵的影子。它让我意识到,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神秘得多。我曾经以为,玩具只是玩具,是孩子们的消遣,但这本书颠覆了我的这种认知。它将玩具提升到了一个象征的高度,赋予了它们更深层次的意义。我从书中看到了关于“遗忘”和“铭记”的讨论,那些被遗忘的娃娃兵,是否也意味着被遗忘的故事?而那些被铭记的,又承载着怎样的重量?这本书的开放性也非常强,它留下了很多值得读者去思考和解读的空间。我曾试图将它归类,但发现它似乎融合了历史、幻想、哲学等多种元素,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格。这本书是一次深刻的心灵之旅,它让我重新认识了“存在”的意义,也让我更加珍惜那些生活中微小而美好的事物。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相当引人注目,那种略带复古的插画风格,配合着“锌皮娃娃兵”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好奇。我一直以来都对那种承载着历史痕迹和童年回忆的物品情有独钟,尤其是那些曾经是玩具,却又似乎拥有自己故事的物件。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可能将带领我进入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一个由微小、沉默的战士构成的军队,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默默执行着它们的使命。我设想着,这本书或许会讲述这些锌皮娃娃兵的起源,它们的制造过程,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是在某个特定的家庭中,扮演过的角色。它们可能是某个孩子最忠实的玩伴,也可能是某个家庭珍藏的宝物,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我期待它能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这些冰冷金属外壳下,可能蕴含的温度和情感,让读者在合上书本后,依然能回味无穷,仿佛自己也曾是那个用小手握着锌皮娃娃兵,在想象的世界里征战沙场的小孩。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方式十分独特,它不是一条直线式的讲述,而是像拼图一样,碎片化的信息不断呈现,直到最后才让你豁然开朗。我喜欢这种逐渐揭开谜底的过程,它让我全程都保持着高度的注意力,不断地猜测和推理。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场景,都仿佛是精心设计的线索,引导着读者一步步深入。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细节的把握,那些看似不经意间描写的物件、场景、对话,都可能蕴含着重要的信息。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一些侦探小说,但这本书却并非纯粹的解谜,它更像是在探索一种情感的逻辑,一种命运的轨迹。我曾一度怀疑,这些锌皮娃娃兵是否真的存在,还是仅仅是作者虚构的意象,但随着故事的深入,我越来越相信,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它们的存在方式,超越了我们寻常的认知。这本书的阅读过程,就像是在一场充满智慧的博弈,你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努力去理解那些超越语言的沉默。
评分同样的历史,不同的人写,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评分书是正品,很开心的购物下次还买
评分本次购物心情十分愉快,商品品相完美,物流迅速,感谢京东!
评分诺贝尔奖的水平是怎么样
评分物流就是这么给力,京东杠杠的
评分这本书一直想买,赶上世界读书日,买了一大堆,还没读,不过书的质量没法说。
评分我们读好的文学作品,其实是在仰望一个更高的人生,接触合乎自己喜好而境界更高的灵魂
评分物流很快,外包装很细心,质量很好,满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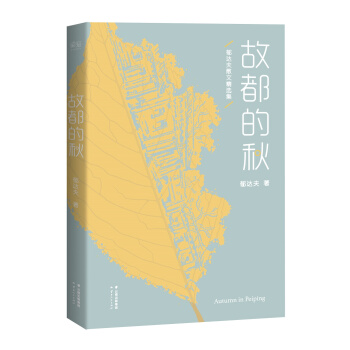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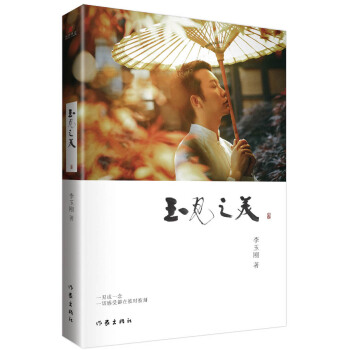
![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Language And Silence Gocrge Steiner]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355424/rBEhVVKf9PoIAAAAAAQcsQZI9QYAAGfJwDklTcABBzJ81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