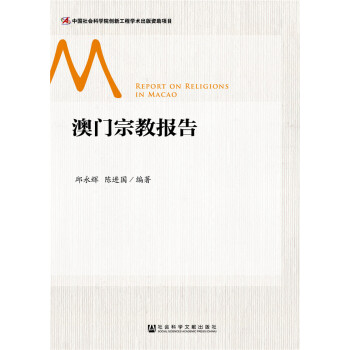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2013年10月在澳门召开的“宗教与可持续社区”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文集。书中展示的是宗教研究所发生的“范式的转变”,即更多注意宗教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书中特别关注巴哈伊教的社区建设经验。在各种宗教与可持续社区关系研究中,巴哈伊信仰的可持续社区理念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在全世界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也值得总结和借鉴。作者简介
邱永辉,女,1961年4月生,籍贯四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当代宗教发展态势研究”创新工程项目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南亚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当代宗教和印度宗教文化研究。1978年2月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2年初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2年初开始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研究生阶段学习,主攻方向为印度史,至1984年底毕业,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史学硕士学位。从1984年底至2001年7月,就职于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研究范围包括当代印度政治、社会和宗教文化。其间,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社会学系和印度尼赫鲁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进修访问。1986年12月始任助理研究员,1993年晋升为副研究员。2000年7月晋升为研究员,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亚基地政治社会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2001年9月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陈进国,男,1970年生,福建永春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1989-1996年厦门大学哲学系哲学学士、硕士,1998-2002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2002-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后。1996-2002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合著《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2002),专著《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2005)、《隔岸观火:泛台海区域的信仰生活》(2008)等。《宗教人类学》辑刊主编。
目录
中国宗教团体及其社会管理 (代序)【卓新平】/1导 论 澳门的宗教治理与宗教生态【陈进国】/1
上编 澳门宗教团体的治理——法律架构与治理实践
澳门基本法与宗教信仰自由【骆伟建 江 华】/15
澳门宗教团体的管治架构初探【郑庆云】/26
澳门佛教团体的弘法活动和管理模式【贾晋华 白照杰】/35
“石破花开”:澳门基督新教教会的治理与发展【游伟业】/49
天主教修会的革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对修会的训道及实践【叶家祺 陈玉叶】/65
培养宗教团体的治理能力——澳门巴哈伊的若干经验【江绍发】/81
探讨澳门巴哈伊团体廉正理念【陆 坚】/101
下编 澳门宗教调研报告——新兴宗教与民间信仰
巴哈伊教的慈善理念及其在澳门的实践
——以“巴迪基金会”为个案的研究报告【邱永辉】/123
一贯道在澳门的传播与发展——以发一崇德的活动为例【陈进国】/173
澳门地区民间信仰管窥【叶 涛】/189
后 记/232
前言/序言
中国宗教团体及其社会管理 (代序)卓新平
卓新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探究宗教团体的治理,重要且必要的关联就是分析、研究中国宗教团体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内在关系或关联。在中国社会处境及文化氛围中,人们很容易发现中国宗教团体在组织建构上的特色,以及其社会存在和社会作用的特点。然而,这些显而易见、与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宗教团体的不同,却未曾得到系统、认真的梳理和解读。其界说之难不仅在于中国宗教团体的构建本身,更在于其与中国社会政体的关系。这种政体本身,以及政教关系的与众不同,使我们对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管理问题不能简单与他者类比,而必须找出中国自己的特点,以此说明中国独有的特色。
一 中国的宗教团体与中国的政教关系
对于宗教团体的治理问题,取决于我们对宗教本质及其社会存在与作用的基本认知和评价。也就是说,宗教团体的管理只是手段,它势必反映这种治理的目的,即究竟是要推动宗教的发展,还是要限制宗教的存在;是要扩大宗教的社会影响,还是想减少、削弱这种影响;是要对宗教加以思想、政治、社会、法律层面的掌控,还是使宗教更加自由、自然地生存与发展。所以说,宗教团体的治理问题是“工具理性”的问题,它反映且也必然服从于关涉宗教的“价值理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宪法保障了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各种宗教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获得巨大发展,但是,尚有几个最为根本的问题仍未解决,人们对之分歧较大、解说众多,很难达成共识。
其问题之一即是对宗教的评价问题。这种对宗教的价值判断、基本定义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大陆还未能将以基本法、上位法的方式来解决宗教立法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其根本原因就是对“怎样看宗教”没有达成共识,故而影响到对宗教“怎么办”的具体立法和政策管理等举措,人们对这种“立法”究竟是“保护宗教”还是“限制宗教”认识不清、分歧颇大,所以立法机构只能对宗教立法问题加以暂时“悬置”,其结果是影响到我们从根本上思考、讨论、实施如何“依法管理宗教”的问题。人们由此提出了是否有“法”可“依”,“法”是什么性质之法,以及如何对之实施等疑问,需要我们进一步澄清和说明。
其问题之二即“宗教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有无区别及如何关联。中国大陆社会谈得较多的是“宗教信仰自由”,而对“宗教自由”的表述则颇为谨慎。个中原因在于“宗教信仰”主要是在“思想”层面,任何社会制度和管理举措很难从根本上真正限制人的“思想自由”,也就是说,这些制度和举措很容易管到人们之“行”和“言”,却很难限制其之“思”和“想”。而“宗教自由”则不仅包括其思想信仰层面,也包括其社会行动层面。所以,不少人认为“宗教信仰”有着绝对的思想自由,而宗教包括的社会组织团体及其言行则只有相对的自由,因为其社会机构及言行有着社会制度、秩序、法律和政策等制约,并不是绝对自由所能表达的。其中“宗教自由”的空间及限度,则依赖于相关宗教的社会存在及其公共秩序对它的要求。这里既涉及宗教可能获得的自由,也涉及宗教与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关联及由此而必须具有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法律的制约。
其问题之三即政府如何管理宗教,如何处理好多层面的政教关系。人们谈到政教关系时一般会论及“政教合一”“政教分离”“政教协约”这三种模式。政教关系的模式不同,也势必影响到其政治权力和社会管理机构在对待宗教团体上的管理方式之不同。在“政教合一”的关系中,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实质上是一种内涵式管理,即对所谓“国教”的提倡、推崇,以及管理。由于这种一体、合一,政府对宗教的管理即内部管理,属于其体制内、机制内的事务。其社会建构的一致,以其意识形态、价值核心的一致为前提。但在“政教分离”的关系中,宗教团体则“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 因此,这种政教关系中对宗教团体的管理是一种外延式管理,即只能在社会公共层面上对宗教的“言”与“行”,及其社会组织形式加以外在的、虽有限却有效的管理。这也只能是一种社会层面的管理,特别是以与其他社团相类似的方式来实施对宗教社团的管理。在此,宗教管理即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宪法、政策法规等来对宗教的社会存在方式及其行为方式进行管理,而不涉及其内在的教派之分、正邪之辨等。对宗教团体的管理就是把宗教视为一种社会团体,以宪法、法律和相关行政法规来规范宗教、掌控宗教的社会存在及其行为方式,保持宗教的社会服从及社会服务,而不使之出现挑战公共秩序等越轨、越线、越界的现象。而在“政教协约”的关系中,宗教通过与政治权力的“协商”来保留一部分权利或自由,同时亦不得不接受政权对之实施的社会管理。由于它反映出政教关系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过渡,政教之间故有一定的张力或权力博弈,需要政教之间有某种协议、协商或协调,以应对其社会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及困难。
但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来看,上述政教关系的这三种模式都不太符合中国的历史及国情。例如,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中国乃“政教合一”的国家,儒教为其国教,实施“神权政治”和“国教统治”。皇帝作为“天子”乃政教合一的领袖,负责主持“祭天”这种儒教中最高级别的大礼。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一直乃“政教分离”的国家,儒教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不是宗教,而乃国家意识、世俗文化哲学,并以此曾形成与宗教的抗衡,使佛、道等宗教不可能进入国家主流意识。按这后一种观点,“在古代中国文化的核心——政治层面上,宗教从来没有取得过统治地位”,而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人伦和权术,绝对是非宗教的。所以古代中国政治层面的‘天’‘神’也是非宗教化的”。 这样,中国的宗教就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化”的状态,受到社会政治的全面管理。从上述两种对立的见解可以看出,以西方话语模式的政教关系很难说清中国的政教处境及其关系。
如果跳出上述三种政教关系模式来看中国,那么在中国自古至今“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及其传统中,较能真实反映中国政教关系的就应是“政主教从”或“政主教辅”的模式,即以“政”统“教”、以“教”辅“政”。其特点是宗教不能掌控、左右政治,有着“政教分离”的类似形态,但国家政权则严格掌控着宗教,把宗教纳入其整体的政治及社会管理之中,故而形成中国所独有的“准政教合一”现象。“这种管理强调宗教在思想、政治上对政府的服从,保持政教程度较高的一致。为此,政府会具体负责宗教人事安排,指导宗教教义思想的诠释,督查宗教组织的构建,并为宗教提供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援助和保障。这样,合法宗教则会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宗教’,在此之外的宗教则为‘另类’,处于‘非法’之状。”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宗教在历史上有着“正”“邪”之分,而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着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专门机构,“从中国古代‘掌僧道’的‘礼部’到今天的各级‘宗教事务局’,这种管理体制乃一脉相承,凸显了政府的权威”。例如,唐朝曾为各国“蕃客”设立“蕃坊”,后来逐渐成为穆斯林集中居住的社区,而其负责人——“蕃长”则由唐朝政府批准和任命。这是较早由中国政府挑选和任命宗教高层领袖之例。元朝政府有专管佛教事务的“宣政院”、专管道教事务的“集贤院”、管理基督宗教(也里可温)等事务的“崇福司”和管理伊斯兰教事务的“回回哈的司”等,而且政府管理部门已分出等级,有一品、二品等区别。明朝负责宗教事务的有掌管僧道的“礼部”,负责边疆民族宗教事务的“四夷馆”,与之相关联的还有“兵部”,以及基层管理机构“卫所”,而主管各种礼仪祭典的则有“鸿胪寺”等。清朝政府有“理藩院”及其下设机构管理宗教事务。而民国时期的“蒙藏委员会”同样也是负责宗教事务的政府机构。所以说,脱离“政主教从”的现实来谈中国政教关系和宗教团体的管理乃无的放矢,不得要领。今天,我们从宗教团体对主流政治的拥戴、对核心价值观及其思想意识的学习、服从,从国家对宗教领袖教内外“职务”或职位的实际任命、安排,以及从“中梵关系”因罗马教权与中国政权的抗衡而形成的紧张及不和等,就可体悟这种传统的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这也是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宗教团体及其社会管理的基点或基础之所在。
二 关于中国当今宗教团体之社会管理的思考
就当前中国政教关系的现状而言,对宗教的社会管理既体现出现代“政教分离”的相关管理理念,又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国历史传统中以政统教的“政主教从”模式的管理办法,还有“政府派员”进驻宗教社会团体、以“秘书长”身份来直接管理等现代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宗教社团管理各有利弊,但整体上仍都不太适应现代社会宗教团体的发展,以及政教关系变化的新形势。因此,我们有必要调整思路、加强研究,创新对宗教团体的社会管理,达到最佳管理效果。
以往,中国的社会管理以“单位”管理为主,所以对宗教的社会管理也基本上采取对“宗教团体”这种“准单位”的管理方式。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单位”的传统意义已经削减,新的“单位”形式则有其明显的流变性、短暂性,甚至随意性,让人把握不住,难以为继。同理,中国当代宗教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宗教团体也不是以往的宗教社团形式所能涵括的,其弥散性、草根性或“公民意识”性已经很难用传统的宗教社团来概括。这些宗教团体在社会管理上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既有“全球化”处境中具有国际性质的,也有国内因这种社会“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所导致的,二者复杂交织,促使我们必经认真面对,提出有效举措。
就我个人的初步、肤浅之见而言,加强对中国宗教团体的社会管理,可以考虑如下举措。
其一,“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应与“属地管理”密切结合。
虽然从当前中国国情出发,我们已不能走把社会管理的权力都集中到政府、由政府来统摄和包办的老路,也不可能完全放开、全面放弃。在此,我们必须汲取以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教训,有机、逐渐地过渡到新的管理模式上来。因此,为了适应以往“大一统”的宗教管理模式的惯性,我认为中国各宗教团体仍有必要建立其全国性的领导式协调机构,形成其相对联合又有着松散性、联谊性特色的宗教“共同体”。政府的社会管理可以通过这些“大一统”的宗教联合体、共同体来协调全国性宗教活动、处理好各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加强对宗教团体的“属地管理”,即根据宗教的地域性发展及其基层社团的状况来实施社会管理,由此引导宗教社团从宏观的政治关注转向微观、具体的宗教社会发展,注重其地域民族及文化等特色,发挥基层社区管理的作用,以便真正能够管实、管好。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就宗教团体的社会管理而言,这两种管理模式仍然是“一个都不能少”。
其二,社会管理的“顶层设计”与宗教团体管理的“基层举措”应积极沟通。
在整个中国社会大系统中,不能排斥或排除宗教社团的存在及参与,而应将宗教社团视为在整个中国社会构建系统中有机共构的子系统、分单元,以普遍管理社会组织的方式来对待宗教团体,而不应对之歧视,持有偏见,人为地将宗教社团推至“敏感地带”或打入另类。在中国整体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中必须有宗教的构成及参与,形成积极、良性的“顶层”与“基层”的沟通、互动。由此,我们应该尽快、尽早使宗教“脱敏”,实现宗教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的尽量一致或充分认同,让其成为我们自己的有机构成,即把宗教团体从社会存在、政治存在、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上都全面纳入我们当今社会存在的整体建构和一统体系,避免宗教再被误解、遭冷落、受歧视,防止宗教在我们的社会机体内“异化”、“他化”或“恶化”。因此,在社会管理综合考虑的“顶层设计”中,我们必须要有如下理念及考量:“当宗教作为政治力量时应该成为我们自己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当宗教作为社会系统时应该成为我们当今和谐社会的有机构建,当宗教作为文化传承时应该成为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积极因素,当宗教作为灵性信仰时应该成为我们重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构成。”只有这样,才能有管好宗教团体的有效“基层举措”出台,才不会以敌意、暴力来对待、对付宗教社会组织,处理宗教问题。只有当宗教在中国社会被视为“为我”的存在,才会真正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发展。
其三,加强法治建设,使“依法管理宗教”真正落到实处。
在中国当前法治建设、实现“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依法管理宗教”应该逐步推动,使之最终能落到实处,发挥真正作用。目前我国管理宗教事务的法规主要是政府行政法规和地方相关法规,缺乏一种基本法、统领法、上位法来指导、规范这些行政及地方法规。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推动“宗教理解共识”,由此才可能真正达到“宗教立法共识”,明确立法目标,扫清立法障碍。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可能制定的宗教基本法应该是体现“保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意向,而不是用各种条条框框来“限制”宗教、“打压”宗教。如果宗教社团的存在能在未来中国真正获得“法律上的尊严”,那么中国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也就可能很快得以实现。
其四,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使宗教社团的政府政治管理平稳过渡到社会法治管理。
宗教社团在中国社会政治的“大一统”体制中,应该逐步实现其社会定位的正常化和良性发展,达到其有利于社会的“自立”和“自办”。在中国社会的总系统中,宗教社团的负责人即领袖人物理应从制度上、程序上都受到政治、政党(执政党)、宗教等方面的系统训练和素质教育,成为在政治上可靠、对执政党忠诚、有渊博宗教学识和高深宗教修行的“实力型”领军人物、社团核心。这种高度“保持一致”是我国政治体制、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所必需的,至少在目前而言乃是一种“绝对命令”或“绝对要求”,不可能根本回避或放弃。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不断成熟及其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随着宗教团体在中国社会中真正地融入和形成一体,其管理亦有可能由“政治”转为“自治”。这也就要求宗教能在各宗教信仰之间、各宗教团体之间、同一宗教内部各派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和睦,其中当然也可能有相互制约或相互监督,同时亦要求各宗教团体与其他各种社会团体之间的和谐共在,对中国政体的适应,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参与,从中完善宗教团体自身的体制机制,培育出其创新型领袖人才,并符合积极、主动适应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种要求。只有当宗教团体能够有效地实行自我管理、协调好整个中国的宗教生态,纳入整个社会的有机管理体制之内,以往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管理才可能逐渐消减,并最终自动停止。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握得相当老道,它并非线性叙事,而是采用了多线交织、如同织锦般复杂的结构。有些章节如同在幽暗的巷陌中穿行,聚焦于某一个家族世代守护的某种仪式,描述极其详尽,字斟句酌,仿佛作者花费了数年时间,才终于被允许窥见那一幕幕私密的场景。而紧接着的下一部分,可能又会突然拉高视角,引入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用一种近乎史诗般的语调,梳理某个宗教思潮在数百年间的流变与渗透。这种张弛有度的切换,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探险的乐趣。我特别欣赏作者处理复杂议题时的克制,他似乎总是能找到一个巧妙的切入点,不预设立场,而是将各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并置,让读者自行去感受其中的张力。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因为一个不经意的历史典故而不得不停下来查阅,这显示了作者知识储备的深厚,以及他对材料的梳理和提炼的功力,绝非轻易写成的作品。
评分从文风上来说,作者的语言驾驭能力令人叹服。它兼具了学术的严谨和文学的优美,但更偏向于一种冷静而富有洞察力的散文风格。最难得的是,整本书下来,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信息密度极高,但阅读起来却毫不费力,这是一种高超的文字炼金术。书中穿插的访谈录片段,没有被生硬地嵌入,而是如同珍珠般巧妙地镶嵌在论述之间,为冰冷的分析注入了鲜活的人声和个体命运的悲喜。这些访谈对象的话语,充满了地方色彩和生活智慧,它们与宏大的理论框架形成了有趣的互文,让原本严肃的议题变得可亲近、可理解。这种叙事策略,有效地避免了将文化研究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理论说教,而是构建了一种平视的对话关系。
评分我通常对这类主题的作品抱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因为很多时候,所谓的“研究”往往会陷入一种猎奇或符号化的陷阱,将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化为几个易于传播的标签。但这本书明显避开了这种窠臼。它真正触及到了信仰的“温度”和“重量”。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社区祭祀活动的那几章,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记录仪式本身,而是深入探讨了这些仪式如何作为一种社会粘合剂,在现代生活的高速运转下,维系着邻里关系和身份认同。那些关于食物、香火、甚至是特定时间点的气味和光影的描写,都充满了感官的冲击力。这让我意识到,宗教活动远不止于殿堂之内的祷告,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是一种活生生的、不断被重塑的社会实践。那种对细节的执着,让我感觉自己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些熙熙攘攘的节庆现场,而非仅仅在阅读文字描述。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初看之下,那份沉稳的墨绿色调和烫金的字体,便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装帧的质感非常扎实,捧在手里有一种久经风霜的历史感。我原本对“报告”这类字眼有些望而却步,总觉得会充斥着枯燥的数据和晦涩的学术术语。然而,翻开第一页,那种预设的沉重感立刻被一种细腻的观察所取代。作者的笔触并非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带着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仿佛在描摹一幅幅流动的社会风情画。尤其是在描述那些小众信仰群体在城市变迁中的挣扎与坚守时,那种细腻入微的细节捕捉,让人不禁停下来,反复咀嚼。比如,某段关于旧城区庙宇修复过程中,信众与开发商之间微妙的利益拉扯与情感维系,写得简直如同小说一般引人入胜,既有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又不失微观个体的真实心跳。这绝非是泛泛而谈的概览,而是深入肌理的剖析,让人对这座城市的精神脉络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远超我对一般纪实文学的预期。
评分这本书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它所揭示的关于“变迁”的主题。它不是一本静止的“风土志”,而是一部关于“动态平衡”的记录。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全球化、城市更新以及代际差异这几股强大力量如何与根深蒂固的传统发生碰撞、磨合、甚至相互吞噬的过程。我能从中读出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深刻反思,但这种反思并非是悲观的宿命论,而是在承认流逝的同时,对那些顽强抵抗消亡的文化基因所表达出的敬意。例如,书中对年轻一代如何“挪用”或“重新诠释”传统仪式的描写,充满了启发性,显示出文化生命力的强大韧性。读完后,我对于如何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了一种更具层次感的理解框架,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复杂的共生与演化。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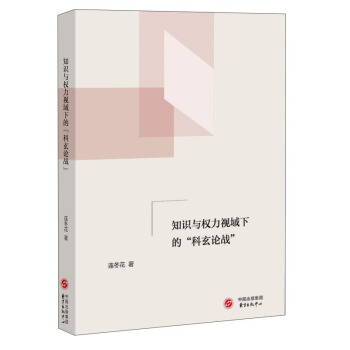



![价值理性批判:价值观念生成的先验程序和先验结构研究 [Critique of value reas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16344/59536941N2f99d0c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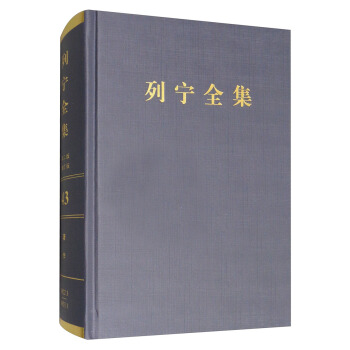
![老子道德经与神仙画(汉英) [Laozi Laws Divine&Human&Pictures of Deit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01110/5a694b97N552d281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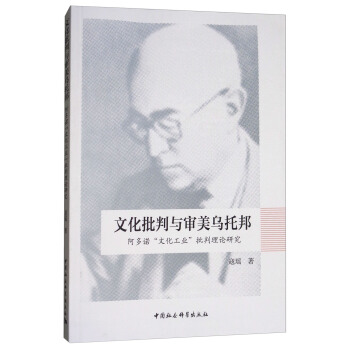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15)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62615/5b239ee0N5cfc50cc.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