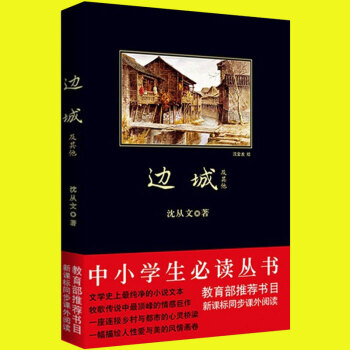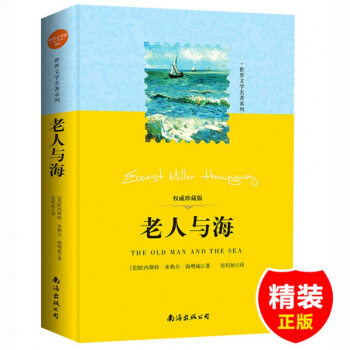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你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你想看清这个城市的什么?
唯有王城Z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然而,欲望无处可藏……
书写新北京的新阶层,直面新北京的新问题
不同于任何“京味小说”的新世相:雾霾之下,生存之中
看“京一代”继续《跑步穿过中关村》、在《耶路撒冷》跋涉
内容简介
这是70后实力作家徐则臣Z新的长篇小说,讲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的生活故事。海归导演余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巨大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步升级,先被家里的保姆罗冬雨洞悉,接着被罗冬雨的男友、快递员韩山发现;然后又被罗冬雨的弟弟,大学生罗龙河引爆……小说篇幅不长,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作家用一支成熟的笔,挑开了雾霾之下新北京的新世相,读者或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
“唯有王城Z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我们带着各自的过往,奔波在北京的大街上,奔向自己的未来。物质匮乏的时候,追逐物质;精神空虚的时候,寻求心安,然而,欲望无处可藏……
“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S侈品名品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
前言/序言
《王城如海》后记
徐则臣
这部小说是个意外产物。照我的写作计划,它至少该在三年后诞生。《耶路撒冷》写完,我就开始专心准备一部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的长篇小说。这小说既跟运河有关,运河的前生今世必当了然于胸,有一堆资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写作习惯,从南到北运河沿线我也得切实地走上一两趟,走过了写起来心里才踏实;小说的一条线在1901年,这一年于中国意义之重大,稍通近现代历史即可明白,这一年晚晴政府下令废止漕运,也直接导致了运河在今天的兴废,如此这般,二十世纪前后几年的中国历史也需要仔细地梳理一遍;凡此种种,有浩繁的功课要做,我是预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没想到大到如此,一个问题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一本书牵扯到另外一本书,笔记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资料和想法淹没之感。有一天我面对满桌子的书发呆,突然一个感觉从心里浮上来:有件事得干了。这个感觉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说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赶到前头了。这小说就是《王城如海》。
那时候它还叫《大都市》。在此更前它叫《大都会》。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写的的确就是从大城市看小城市里的事。写完了意犹未尽,想换个方向,让目光从小地方看回去,审一审大城市。当然是以北京为样本。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北京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人公写一部小说,跟过去写过的一系列关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说不同。区别在哪里?在“老书虫文学节”上,与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三位作家对谈城市文学时,我开过一个玩笑:很多人说我“北京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这次要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攥着博士学位的;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回要让他们高大上,出入一下主流的名利场;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出口转内销,沾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气,从世界看中国;过去的北京只是中国的北京,这一次,北京将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标里的北京。放言无忌的时候,这小说才刚开了头不久,但真要通俗、显明地辨识出两者的差异,这一番玩笑也算歪打正着。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从动笔之初它就没法叫《大都会》。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有个长篇小说叫《大都会》,写纽约的;有德里罗在前,且纽约之大都会称谓世人皆知,我只能避开。那就《大都市》?与《小城市》相对。和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先生聊及该小说,他以为“大都市”不好,听着与“耶路撒冷”不在一个级别上,过两天发来一条短信,苏东坡的一句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地敷衍,只说备用。没想透的事我不会贸然答应,尤其是小说题目。我是必须有了合适的题目才能把小说写去的那类作家。接下来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写在纸上,有空就盯着看。我让这四个字自由地发酵和生长,让它们的阴影缓慢地覆盖我想象中的那个故事,直到某一刻,它们巨大的阴影从容、开阔、自然地覆盖住了整个故事,好,题目和故事恰当地接上了头,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说才真正出现了。就它了,也只能是它。王城堪隐,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以我的经验,瓜熟蒂落的小说不能拖,拖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再也不会碰它。熟过头,你对它的好奇心和陌生感丧失殆尽,写作真就变成一个程序化的机械劳作,背书一样面对稿纸复述,写作让人着迷的寻找和探究的快乐荡然无存,这样的写作于我是折磨,宁可不干。所以,既然意外怀孕,那就当其时令,该生就生。
2016年1月1日上午,我坐到书桌前,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良辰吉日,就摊开习惯用的八开大的稿纸,在第一页的背面写下“王城如海”四个字,第二页的背面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句话:“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坡璃的破碎声响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余松坡的故事从此开始。
自元旦日始,到5月18日三稿毕,十万余字的小东西用了近五个月。我无从判断写作的速度快还是慢。有快的,长篇小说《夜火车》十来万字,一个月写完了;也有慢的,《耶路撒冷》四十万字,折腾了六年。但不论快慢,没有哪个小说比《王城如海》更艰难,很多次我都以为再也写不完了。写作《耶路撒冷》的六年里,横无际涯的时光如大海,我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往电脑上敲,也没有为一部小说的无力完成如此焦虑过。不是故事进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复调整,要一遍遍推倒重来——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从不为写作本身的问题如此焦虑和恐惧;只要耗得起,写作中几乎不存在过不去的槛儿,实在越不过了你就等,最终时间会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
多事之秋。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王城如海》的整个写作过程。在动笔之前祖父就进了两次医院,溶血性贫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体内相互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标像股票一样隔天就直线往下掉。本地医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溶血太厉害,血型都测不出来,只好转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多次尝试,血算是补上了,其他问题出来了。上年纪了,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医生让我把祖父想象成一辆老爷车,各个部件都处在报废的边缘,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抛锚的一种可能。当然,油上不去,将会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报废;而对一辆老爷车来说,哪个部件都报废不起。补过血,回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再四个小时的车躺着去那家医院。如此反复,祖父真折腾不起了,溶血性贫血在大剂量激素药的遏制下,成了威胁生命的次要因素,身体的其他部件揭竿而起,医生说,每一个脏器都可能随时说不。正是在众多的“不”声中,我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开始了《王城如海》的写作。千里之遥不能淡化任何一点担忧和焦虑,相反它在加剧和放大,你使不上劲儿,听风就是雨,你会为你使不上劲儿羞愧,自责你逃离了灾难现场,自责你因为距离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关口,我都觉得自己是帮凶。我使不上劲儿,连口水都不能端给祖父喝。
祖父是个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学校长,其后被责令当了多年的猪倌。平反时年纪也大了,离休终老,在乡村里也算大知识分子;闯荡过世界,毛病很多,见识也有,但在儿孙问题上还保留了老脑筋,最心疼我这个唯一的孙子。凡我的事,都有另外一套规矩办。从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书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说。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去镇上赶集,祖父骑着自行车,逢集就带上我,进了集市不管饿不饿,先给我买二两油煎包子。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包子。出门念书了,从一周回来一次到一个月回来一次到一学期回来一次,再到工作结婚后经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习惯从未改变:我离家之前一两个小时,他就会拎着马扎坐在大门口,听着我收拾行李的动静,我出门,他也站起来,拎着马扎一直沉默着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么劝都不回去,只说,“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从外面回来,祖父会提前几个小时坐到巷口的路边,就坐着,坐累了回家,抽根烟喝杯茶,过一会儿拎着马扎再去巷子口。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车晚点,到家已经半夜,八十多岁的祖父实在熬不动,上床睡了。父亲接我,用手电照着巷口至家门前的路,雪地里很多趟相同的脚印,把雪都踩乱了。父亲说,祖父一晚上就没干别的,一趟趟地走,跟他说也没用。那时候手机电话都通,我啥时候能到家早就通报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坚持摸黑往巷口去,嘴里还是习惯性的那句话:
“我就看看。”
那夜我到家,在院子里中说第一句话,就听见祖父在房间里说:“回来了?”
祖父从不讳言他对孙子的看重。他像一部上不了路的老爷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时,一度因为器官衰竭头脑出现了混乱,身边的人一个都不认识,听谁的名字他都茫然。小姑在电话里告诉我,只在听到我名字时,祖父突然清醒了,说:“那是我孙子。”
待在北京写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着多通类似的关于祖父病情的电话。最多的一天,我和家人来回通过二十多个电话。不通电话我焦虑,通过电话我更焦虑,真像蝴蝶效应,家人任何一点悲观的判断和情绪都能在我这里引起一场风暴。每一通电话之后,我都得坐在书桌前稳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书,让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静下来,直到下笔时心里能有着落。
工作之余我都尽量写一点,一天两百字也力图有所进展。完全停笔不动只在春节前后,我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医院,二十四小时守着祖父,一直到除夕前一天回老家。祖父坚持回家过年。有天早上醒来,他说我这是在哪里,为什么周围都是白的,房子连个屋顶都没有?医生说,天大的事也等过了年再说,别让老人有遗憾。这话说得我的心悬了整个年关,生怕祖父出什么意外。好在挺了过来,祖父又长了一岁。在老人身边焦虑的确是少了,我可以把祖父搀扶到阳光底下,可以端茶倒水,可以为祖父处理大小便问题,我使得上力气了。那段时间几乎不想《王城如海》的事,带回去的稿子停在哪句话上,离开老家时还在哪句话上,我甚至都没把稿纸打开,背回去的一堆空白稿纸原封不动地背回来。回到北京,坐下来,继续在书桌前的煎熬,跟之前有所不同的是,我时刻担心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确定性的消息。祖父的状况确实在每况愈下。医生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随时。我便在写作中随时提防那个“随时”,而这个“随时”让我的写作断断续续、举步维艰,让我觉得每一次顺利地接续下来都像是一场战斗。实话实说,半程之后的《王城如海》,我没能感受到丝毫的写作快感,我仿佛在和死神争夺一个祖父。
5月18日,三稿结束。6月24日,祖父在家中去世,该日故乡降下多年不遇的大雨。愿祖父在天之灵安息!
坏消息在这五个月里扎了堆。祖父尚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四姑胰腺上查出来有肿瘤,医生初步诊断是恶性,因为慎重,特从省城医院请来了主刀大夫。六个小时的大手术,一家人在手术室外掉眼泪。还好,切片结果,良性。我在电话里得到消息,觉得在生死之战中,终于胜了一局。四姑待我极好。在镇上念初中那会儿,学校没法给低年级学生提供床位,住不了校,我在四姑家住了很久。四姑炒得一手好菜,念大学了,我去学校之前经常绕道四姑家,先吃一盘四姑做的剁椒鸡蛋再去坐车。祖父的病情之外,电话内容里又多了一项,四姑的病情。
四姑术后不久,父亲脚腕处积水,严重影响了行动,服侍祖父都感到吃力,不得已也开了一刀,卧床数日。他们远在老家,我唯一可以接近的方式就是电话。我从来没有如此感激过电话的发明者,伟大的亚历山大·贝尔;我也从来没有如此痛恨过这个英国人,每当我坐在书桌前,心绪不宁、惊慌失措地面对《王城如海》的空白稿纸时,我就想,这个小说是永远也写不完了,我没有那么多的心力应付接踵而至的坏消息。
这些都不算完,看过小说的读者会发现,小说中花了不少篇幅写了北京的雾霾和一个叫余果的五岁男孩,他在故事发生期间正经历旷日持久的咳嗽;他的小嗓子对雾霾过敏,PM2.5稍微往上飙那么一点,在他那里就立竿见影。没错,写作这小说的过程里正值北京旷日持久的雾霾,也因为这雾霾,我四岁的儿子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咳嗽,他和余果一样,对雾霾过敏。刚治好了,雾霾来了,咳嗽又起;费了很大的力气再治,差不多了,雾霾又来,咳嗽再起。写《王城如海》的四个多月里,儿子前后咳嗽了三个多月。听见他硿硿硿的咳嗽声,我同样有种使不上劲儿的无力感和绝望感。那段时间,儿子清一下嗓子,我都会心惊肉跳。白天纠结他上幼儿园穿什么衣服,穿多了怕他上火,肺热咳,穿少了又担心着凉,肺寒咳或感冒咳;我睡得迟,睡前零点左右,看一次他被子盖得如何,凌晨四点钟左右还会醒来一次,看他是否蹬了被子,身上有没有微微的汗意。从早上起床到半夜突然醒来,一天要看挂在书橱上的温度计好多次。明知道气温变化不会大,还是认真地去数两个度数之间的一个个小格子,我要精确到半度、四分之一度、八分之一度、十六分之一度。
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正大踏步地走进我的中年生活:日常生活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男人。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三十出头,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豪言壮语,要努力进入宽阔、复杂、博大的中年写作,并为此很是认真地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不必刻意地想象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写,大约就不会太离谱。在小说里,我多次写到雾霾,与其说要在其中加入一个环保和批判的主题,毋宁说,我在借雾霾表达我这一时段的心境:生活的确是尘雾弥漫、十面霾伏。
当然,我肯定知道谁都不能永远都过开心的好日子,生老病死,聚散离合,乃是人生题中应有之义,圣诞老人也不负责每年都往你的小袜子里塞礼物。说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说多了就是自恋,招人烦,凭什么你遇到点事就吧啦吧啦磨叨个没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经结束,儿子的咳嗽早已痊愈,在小说里的那个霍大夫精心理疗下,小东西现在身体倍儿棒,两个小腮帮子上又有了婴儿肥的迹象。四姑康复良好,逐渐适应了腹腔内摘掉部分器官之后的空。父亲为脚腕处积水上了两次手术台,现在伤口完全愈合,回到了之前的健步如飞,只是在夜深人静时,还会慢慢寻找腿部皮肉和骨头之间曾有亲密无间的关系。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王城如海》是用笔写的,在高度发达的高科技时代,我给它找了一种古典的诞生模式。从2003年起,我就告别了稿纸,大大小小的作品都在电脑上敲出来。从前年开始,突然对纸上写作恢复了热情,喜欢看见白纸上一个个汉字顺次排列下去,甚至涂涂改改、东加西嵌的鬼画符似的修改方式都看顺眼了。一些小文章就开始断断续续用笔在稿纸背面写,写完了录入电脑,录入时顺便就修改。《王城如海》是我的电脑时代最长的一篇手写文章,第一稿就用了近两百页稿纸。纸是《人民文学》的老古董,八十年代杂志社通用的大开本,电脑来了,稿纸就淘汰了,剩下两箱子一直库存。前几年杂志社装修,地方变小了,用不上的东西都须清理,眼见两箱稿纸要卖废纸,我截了下来,竟派上大用。
过去出门出差,有稿子要赶,就得哼哧哼哧背上电脑,重不说,机场安检拿进拿出还得随身携带,太麻烦,现在出门扯下几张稿纸,对折,往包里一塞,走哪写哪,轻省简便,对日益膨出的腰间盘都是个贴心的福利。最主要的,不必在电脑开机关机的诸般仪式上浪费时间,还可以避开我的一个坏毛病:每次打开电脑都要把写好的部分从头到尾看一遍。工作忙了,日常也诸事烦扰,经常前面的万把字还没梳理上一遍,事就来了;下次坐到电脑前,又要重新来过,于是一次次温故却不能知新,家人都看不下去了:你这哪是写作,分明在复习迎考。
——那就稿纸,摊开来就写,一页六百字,再加两三页富余的以备写坏了撕掉,两千字的短文带五六张稿纸就足够了。极大提高了我出门在外和忙得只能见缝插针地写作的效率。
《王城如海》就是在一次次焦虑、无助、悲伤和恐惧平息之后,下一次焦虑、无助、悲伤和恐惧来临之前的间隙里,一页一页地写出来的。也因为携带方便,这部小说跟我走了很多地方,出门我把它折好放在一个专用的文件袋里,确保它平顺和整洁。但在印度,这小说差点流了产。一月份去新德里参加世界书展,从加尔各答飞德里,小说稿和与它有关的写作笔记,一个详细记录我的构思和点滴想法与部分细节的硬皮本,放在行李箱中托运,我人到了德里,行李箱丢了。看着空荡荡的行李传送带咣当一声停下,我的汗刷地就下来了。我极少重写,哪怕一篇短文,丢了就丢了;实在要重写,也得找到一条全新的路径,原样拷贝在我看来只是考验记忆力的体力活儿。还有那个硬皮笔记本,这小说构思了好几年,零散的想法都记在上面;你让我把笔记本合上,问里面都记了些啥,对不起,五分之一的内容我都想不起来,只有看到了,一个关键词我也能想起一大片的东西来。两样东西都丢不起,除非《王城如海》我不想要了。
与机场工作人员交涉。找不到。那也得继续找。别人的行李都在,我的就没理由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还是找不到。务请继续找。迷路了也得让我知道迷到哪条路上了。那天晚上工作人员快给我烦死了,从十一点一直忙到凌晨一点,来了消息:找到了。至今我也没搞清在哪里找到的、分拣行李时出了什么岔子,顾不上了,千恩万谢了一番,想的就是赶紧打开箱子,把小说稿和笔记本装进随身携带的双肩包里。走哪带哪心里才踏实。
我把《王城如海》的失而复得看作一个预言,在异国他乡都没丢掉,回到国内,在我手上更不能让它丢了:决不半途而废。疾病和坏消息席卷的几个月里,我的确多次感觉没力气把它写完了,甚至只剩下最后不足一万字时,我都动过撂挑子的念头;这些时候我就回想德里机场的那一夜,我执著地耗在行李传送带边,跟工作人员理论,旁边是一群宽慰和支持我的师友,他们陪着我直到柳暗花明的凌晨一点。在印度它没丢,说明它不想丢,那就不该丢。既如此,凡事都得过去,凡事也都能过去——我深呼吸,喝浓茶,铺纸握笔,继续写下去。
这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四十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王城如海》当是急管繁弦的断章。两者相近处:一是结构要尽量有所匠心,形式上要有层次感;二是小说中处理的绝对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周。
小说写完了,除去一直都在进行的边边角角的细部修改,主体工程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写作过程中,觉得就小说有满肚子话要说,写完了,放一放,那些话竟然给放没了。也好,表明都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2016/7/10,知春里1804
用户评价
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阅读门槛相当高,它绝不是一本可以“快餐式”阅读的作品。初读时,我感到有些吃力,因为信息密度实在太大,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作者似乎故意采用了非线性叙事手法,将时间线打乱重组,试图让读者亲身体验那种历史的迷雾感。但一旦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那种沉浸式的体验便会爆发出来。它强迫你调动所有的认知资源去构建自己的理解框架,这种主动的参与感,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成就感。等到故事的脉络在你脑中渐渐清晰,那些散落在各处的线索汇集成一张完整的网时,那种智力上的满足感是无与伦比的。它更像是一部需要做笔记、反复查阅的学术著作,但它又巧妙地用引人入胜的故事外壳包裹住了这一切,使得枯燥的分析过程变得充满张力。对于那些追求智力挑战和深度阅读体验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一座值得攀登的高峰。
评分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变化多端,令人目不暇接。在描写宏大场景时,它能展现出史诗般的磅礴气势,仿佛能听到战鼓声声,看到旌旗猎猎;而在描摹细腻情感时,笔触又变得极其温柔而内敛,用极简的句子勾勒出千言万语的情愫。我注意到作者对于意象的选择非常讲究,比如反复出现的“潮汐”、“铁锈”和“回声”,这些意象贯穿始终,每一次出现都带着不同的象征意义,构建了一个深层次的符号系统。这要求读者必须保持高度的专注力,因为错过任何一个意象的细微变化,都可能导致对后续情节深层含义的误读。这种精雕细琢的文字功力,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探索的乐趣。它不是一碗白粥,而是需要细细品味的珍馐,每一个词汇似乎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和推敲,力求达到音韵与意义的最佳契合点。
评分这本书的叙事节奏简直让人窒息,那种步步紧逼的压迫感,就像是身处一座古老、阴森的迷宫中,每走一步都感觉有无形的目光在身后窥视。作者对于环境的描摹极其到位,那些灰蒙蒙的、布满苔藓的石墙,空气中弥漫着的潮湿与腐朽的气息,都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主角的心理描写尤为精彩,那种在绝境中挣扎、在希望的微光中挣扎求存的复杂心绪,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代入其中,感同身受他的恐惧与无奈。读到一些关键转折点时,我甚至需要放下书本,深吸几口气才能平复心绪。这不是那种轻松愉快的故事,它像是一场漫长而又残酷的洗礼,对读者的耐心和承受力都是一种考验。它不急于抛出所有谜团,而是像一个老练的魔术师,总是在你以为要看清真相时,又抛出一个新的障眼法。这种高超的掌控力,让阅读过程充满了紧张感和期待感,让人欲罢不能,即便知道前方可能是万丈深渊,也忍不住想一探究竟。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绝对是近年来少有的佳作,值得反复回味那种深沉而又令人不安的美感。
评分我对这部作品的结构和世界观的构建深感震撼。作者似乎构建了一个极其宏大且逻辑严密的底层设定,即便故事的焦点聚焦在几个核心人物的命运纠葛上,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那个时代、那种社会形态的深刻洞察,让人不得不佩服其深厚的底蕴。它不像很多奇幻小说那样只是搭建一个漂亮的舞台,而是真正地赋予了这个“世界”历史的厚重感和内在的运行规则。我对其中对于权力运作的细致剖析特别感兴趣,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往往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博弈和潜规则的交锋。阅读时,我常常会停下来,对着书中某个精妙的设定进行揣摩,试图梳理出不同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网。这种智力上的挑战性,对于偏爱深度思考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它不是用华丽的辞藻堆砌出来的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扎实的思考和严谨的逻辑之上的艺术品。每当解开一个关于世界观的小谜团,那种豁然开朗的愉悦感,远胜过单纯的情节高潮。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欣赏的一点,在于它对人性灰度的精准把握。在这里,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每个人物都行走在道德的灰色地带,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基于生存的本能、环境的胁迫,或是被扭曲的信仰。即便是看似正面的角色,也潜藏着令人咋舌的阴暗面;而那些被定义为反派的角色,其行为逻辑却又有着令人同情的合理性。这种复杂性使得人物不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活生生、呼吸着、犯着错误的人。我尤其喜欢作者处理冲突的方式,矛盾的激化不是简单的善恶对抗,而是两种看似合理的需求之间的不可调和。每一次冲突的爆发,都像是历史必然性的一次体现,充满了悲剧色彩。这种对“人”本身的深刻挖掘,让整个故事超越了单纯的娱乐范畴,上升到了对存在意义的探讨。读完之后,我甚至会反思自己,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种持久的自我审视,才是真正好书的价值所在。
评分单位购书,一次性买了25本,同事们都很喜欢看。
评分我抄起椅子...放到你屁股后面,站累了吧,快坐下歇会。
评分很方便,京东商城购物方便又快捷
评分徐则臣是我校(东海高级中学)毕业的,这次请他回母校,于是买了一批他的书,放在阅览室,70后有实力的作家。
评分好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评分从爱上网购之后就喜欢在京东买东西,买的方便,买的开心,货到很快,最值得赞的是还送货上门,由于经常在京东买买买,就不一一评价了,此评语为好评!
评分帮朋友买的书,朋友说是正版的,没有错别字。
评分非常喜欢这本书,推荐朋友们看看这本书,值得拥有。
评分印刷质量不错。没有时间看,慢慢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双语译林:包法利夫人(附英文原版书1本) [Madame Bova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28856/57985b9dNc4fe0ef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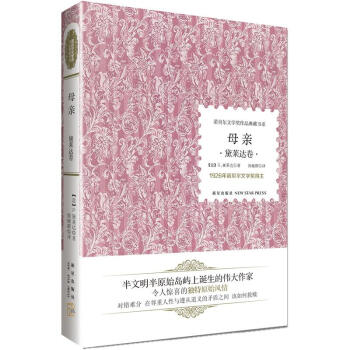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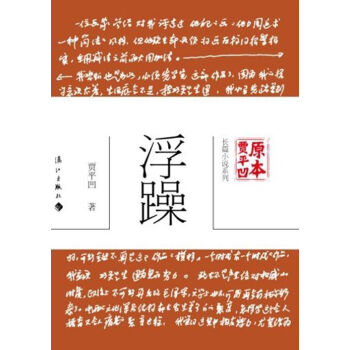
![民国秘事:被偷走的秘密 [The Secret Had Been Stole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43443/53cf27e0N0726d2ab.jpg)






![名家名译:包法利夫人(周克希译本) [Madame Bova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21923/56542f3eN2bf1ff1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