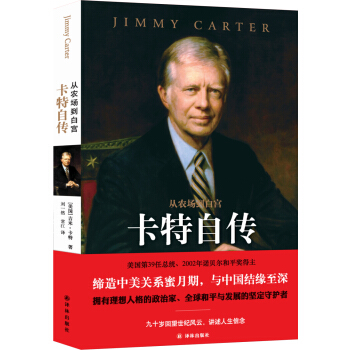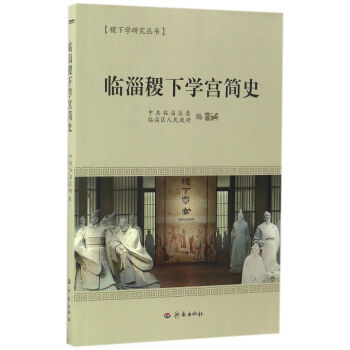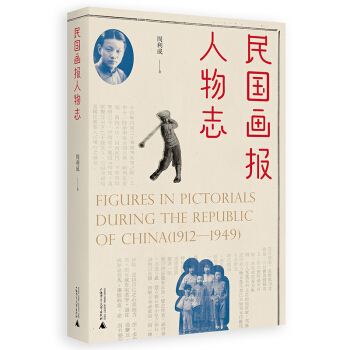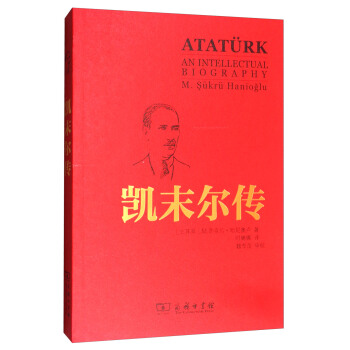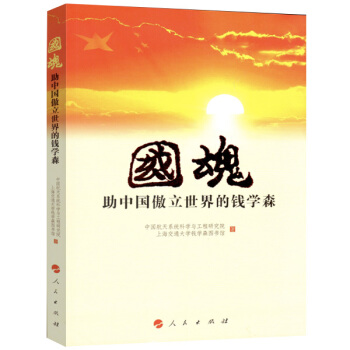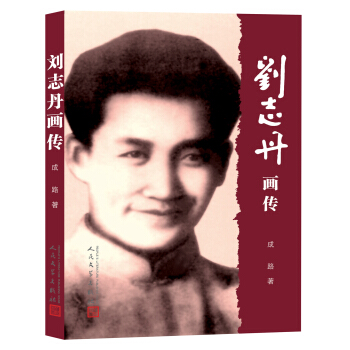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七月派”诗人、现年九十二岁的朱健先生的晚年自述,是一位与时代共命运的中国诗人的生命传奇。书中详细讲述了朱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故事与历史选择,折射了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百年时代风云变幻,也透视了“后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成长、独立精神与人文情怀。
作者简介
朱健,原名杨镇畿、杨竹剑,一九二三年生,山东郓城人,“七月派”诗人之一。一九八九年离休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著有诗集《骆驼和星》《朱健诗选》,散文随笔集《潇园随笔》《无霜斋札记》《逍遥读红楼》《人间烟火》《碎红偶拾》等。
目录
冉子故里杨村记忆
祖父科考脱贫
我的父母亲
辗转求学
五换小学
三换初中
感受宗教情怀
也算抗日少年
千里流亡
感受悲凉
汉江幸免于难
初见李广田
抵达罗江
罗江受业
小城罗江
“川北小延安”
秘密读书会
郧阳秘密出走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李广田
记罗江同学
西北诗情
兰州西北公路局当差
邠州车站的“中国特务老祖宗”
庙台子写诗
《青羊河小曲》本事
笔名的故事
从心里流出的《骆驼和星》
重庆风云
重返四川
初谒胡风先生
晏阳初先生和乡建学院
忆乡建学院的几位老师
“一六”大游行
“六一”大抓捕
与妻子一见钟情
动荡长沙
入党
迎接和平解放
三反五反打老虎
知识分子党员开始靠边站
因胡风案关进公安局
囚室恢复写诗
经历反右运动
留党察看期间两次当党委书记
正圆厂“过苦日子”
文革在牛棚
回铝厂当阳极工
在五七干校
静心养病读书
回归自我
多事之秋
修订辞源
绝意官场
再谒胡风先生
结缘《读书》
逍遥读红楼
订交彭燕郊
关于我自己
附录 朱健先生
后记
个挺拔的人
精彩书摘
初谒胡风先生1944年初冬,我当时已经到了四川,在五通桥永利公司谋生。由于胡风的指引和伙伴们鼓励,我在五通桥写出大量的诗,做了各种尝试。我记得重庆新华日的刊登了陶行知的《创造宣言》:“上帝创造天,创造地;人创造上帝,人是创造主”。巨大的气势和热情马上吸引了我。激动之中,我用全部摘引原文的方式把《创造宣言》改编成一首长诗,寄给胡风。他很快回信,表示了意见:很热情,很可惜被原作一些俗语拖累了,诗应当有自己的语言。以后,胡风在悼念陶行知的文章中提到有人把《创造宣言》改写成诗,大约指的就是这件事。神话,一直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但在灾难深重的年代,写一些脱离现实的题材,是否合适?我感到困惑,便向胡风请教。他回信明确表示:神话当然可以写。神话,是照亮黑暗天空的光电,是刺破腐朽人生的长剑,你应当写。但我却没有再写了。我在五通桥的时候,牛汉到西安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取名《流火》。“七月流火”,意思很明白,表示自己也是拥护胡风的。他这时和胡风还没有任何联系,写信给我转请胡风为《流火》写文章。我当然照办,胡风却是慎重的,回信说:写文章,以后看看再说吧。牛汉的刊物一期而终,胡风的文章自然没有写。胡风可能不愿意给不太了解的人。解放后,大约是1949年下半年或五十年代初,牛汉把他的诗集通过复旦他的同学,寄给胡风,才跟胡风联系上。1945年下半年我在邻水教书,假期到了重庆,按信上的地址,到张家花园去看胡风先生。第一天,是中华剧艺社的演员魏永秀带路。他认识也住在张家花园的陈白尘,而我则在陈白尘主编的报纸副刊上发表过几首诗。这次,陈白尘说,胡风出去了。我留下一张便条请他转交。送我们出来时,陈白尘指着一间东向的小屋说,胡风就住在这里,明天再来吧。
第二天,我径直走进了这间小屋。不顾屋子里正有别的客人,自报名姓。胡风正坐在西边窗下条桌与书架之间,面色黝黑,宽额秃顶,身躯伟岸,有点胖,他马上起身,目光炯炯,伸手相迎。这时坐在北边墙下一张大床上一位秀美的女性也站了起来,含笑连声:知道你要来,欢迎欢迎。我想这就是有着许多美好传闻的梅志了。他们两个人对我热情张罗时,那位客人起身告辞,用十分锐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飘然而去。胡风送客到门边回来对我说:“这是冯雪锋。”
我在冯雪锋的椅子上坐下来,对面是窗下侧身而坐的胡风。房子很小,整个下午,大约就是我手比指画滔滔不绝地信口开河。身心自在,无拘无束,因为感到始终有一双明亮清澈、兴味盎然、坦陈热烈的目光在注视着我,鼓励我倾吐一切。我到底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一直侧头微笑着听我高谈阔论的面影,还有偶尔的插话和提示:“看到《财主的儿女们》了么?怎么样?”我不假思索地说:“热情,非常热情。”
听了我的回答,他显得兴奋,立即说:“第二部更热情,快印出来了。”
谈着话,他突然转身从身后小小的竹书架底层抽出一本杂志,《希望》第四期。递到我手中:“刚印出来,有绿原的诗。”我不等他说完,便翻开来读,绿原的《终点,又一个起点》赫然在目,不禁忘乎所以地读了下去。直到我读完,他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坐在窗下看着我,读完,胡风问我:“你不是也写了一首长诗么?”他指的是我在邻水写的《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胡风淡淡地谈到《骆驼和星》,毫无奖饰之意,只是说:“一位朋友,在女子中学教高中,当教材给学生们读了,不知道反应怎么样?”梅志接过去说;“蛮好。反应蛮好。”我应声说:“我的一个朋友说这不是诗,是造谣,一个美丽的谣言”。胡风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大笑:“美丽的谣言,美丽的谣言。”除此之外,印象完全一片模糊了。以后我是否又到于一次张家园呢,也不记得了。因为我记不起《中国,什么是和平的代价》这首诗是在邻水寄给他的,还是这次见面带过去的。只记得他把诗稿交还给我的时候说:“太激动了,不行,太杂乱,仔细改一改,再寄给我吧。”我认真地改了这首诗,赶在他们离开重庆东下前又寄给了他。临行前他写信告诉我,稿子已交给了由何其芳主持的《希望》等四个刊物联合特刊。1946年春天,我在重庆覃家岗教书,何其芳把稿子寄还给我,说联合特刊篇幅有限,诗太长,没法发表。情况是确实的,并非推诿。在此之前,我一首歌颂毛泽东的短诗,也是胡风转给何其芳在联合诗刊发表,而且招来一位读者的直言批评,表示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写这种赞美个人的诗。在发表这首读者来信的同时,何其芳执笔为我辩解,文辞十分委婉温顺:也许作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人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用不着另外的说明和解释,便写了这样的诗。这场小小的风波当时并没有人注意。我的赞美诗也无助于解脱1955年迎面而来的困境。现在想起来,倒是能品味出一点历史的幽默感。
……
用户评价
当我看到“人生不满百”这个书名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种淡淡的,却又充满力量的哲学思考。人生短暂,十个甲子也不过百年,在这有限的时光里,我们总是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不满”,或是对现状的期许,或对未来的憧憬,亦或是对过往的追悔。而“朱健九十自述”则让我立刻将这种思考具象化,聚焦到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身上。这位老人,必然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见证了无数的风云变幻,他的九十年,或许浓缩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起伏,也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印记。我非常好奇,在这九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朱健先生所经历的“不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是时代的局限,是个人能力的不足,还是情感上的遗憾?我希望这本书能带领我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去理解他的人生哲学,去感受他对生命的态度。他或许会用一种平和而睿智的语气,讲述那些年轻时激昂的梦想,中年时奋斗的艰辛,晚年时对过往的回味。这本书,在我看来,更像是一本关于人生智慧的传承,一本关于生命厚度的解读。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就带着一种深刻的哲学意味。“人生不满百”,这句古老而充满智慧的箴言,点出了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也暗示了人类内心的不甘与追求。“朱健九十自述”,则将这份对生命的感悟聚焦于一位九十岁的老者身上,他的人生阅历必然饱满而厚重,他的回忆或许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抹印记,也可能是时代变迁中的一个缩影。而“开卷书坊第六辑”则表明了这本书的出版背景,这让我对它的品质和定位有了初步的期待,或许它会是一本能够引发深度思考,又具备一定文学性的读物。我非常好奇,在这九十载的人生长河里,朱健先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又积淀了怎样的智慧?他的“不满”究竟源于何处?是对命运的不甘,还是对社会的不平?抑或是对自身未尽心愿的遗憾?我期待着在这本书中,能读到他关于生活、关于情感、关于理想、关于奋斗的真实叙述,从中汲取力量,获得启迪,更希望能在他平静而深沉的文字里,找到与自己内心对话的共鸣。
评分这本书的名字,光是读起来就有一种岁月沉淀的厚重感。“人生不满百”,这句话本身就自带一种禅意和感慨,它提醒着我们生命的宝贵和短暂,也暗示了人类永恒的求索与不满足。而“朱健九十自述”则将这份沉思落到了实处,指向了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拥有九十年生命长度的人。我极度好奇,这位朱健先生,究竟是怎样度过他这不平凡的九十年的?他的人生中有哪些深刻的转折?有哪些让他至今难以忘怀的经历?他是否会像许多长者一样,在回忆中反思自己走过的路,感叹岁月的无情,或是对年轻人提出忠告?“开卷书坊第六辑”也让我对其内容有了初步的预期,这类书坊通常会选择一些有深度、有思想的作品,所以,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包含丰富的个人经历,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能够引发我关于生命意义、价值选择等问题的思考。我希望在这本书里,能读到一种历经沧桑后的豁达,一种看透世事后的平静,以及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与珍惜。
评分“人生不满百”,这四个字轻易地勾勒出一种苍凉而又充满张力的画面。它是一种对生命长度的慨叹,也是一种对生命质量的叩问。而“朱健九十自述”则将这份普遍的情感,锁定在了一个个体身上,一位已经走过九十年人生旅程的老者。这让我不禁想象,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云变幻,又沉淀了多少智慧与感慨。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读到他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独立而又深刻的叙事。他的人生,是否充满了跌宕起伏的传奇,还是平静中暗流涌动?他所经历的“不满”,是时代的洪流裹挟下的无奈,还是个体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必然?我希望他的文字能够带有强烈的个人印记,讲述那些鲜活的人物,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些改变他命运的重大抉择。我想象着,他或许会用一种饱含深情却又克制的笔触,描绘出他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理解,对事业、理想、信仰的坚守。这本书,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一次与生命智者的深度交流。
评分对于《人生不满百 朱健九十自述》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是它蕴含着一种沉甸甸的时间感。九十载的生命,足以沉淀出多少故事,多少感悟,多少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人生不满百”这句开篇语,虽然简短,却如同一记重锤,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有限,也激励着我们去思考如何活出生命的价值。我猜想,朱健先生的这九十自述,并非简单的年谱式记录,而更可能是一种对过往的回溯与审视,是对人生得失、喜怒哀乐的深刻剖析。我期待着,他能在书中分享那些改变他人生的关键时刻,那些让他铭记终生的深刻教训,那些让他由衷感到骄傲或遗憾的瞬间。或许,他会谈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谈到他所经历过的那些重要历史事件,更或许,他会深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以及在漫长岁月中,那些不变的情感内核。我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带来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话感,仿佛我正坐在朱健先生的对面,倾听他娓娓道来,感受他丰富而独特的人生轨迹。
评分几年前就想收一套的,那里刚买房,很紧张。虽然错过了一印,但是已经是欢欣无比了。感谢京东!
评分几年前就想收一套的,那里刚买房,很紧张。虽然错过了一印,但是已经是欢欣无比了。感谢京东!
评分开卷有益,卷卷有味,不错,值得推荐
评分第六辑都买了,但只看了2本,这个系列一直在买
评分开卷有益,卷卷有味,不错,值得推荐
评分几年前就想收一套的,那里刚买房,很紧张。虽然错过了一印,但是已经是欢欣无比了。感谢京东!
评分开卷有益,卷卷有味,不错,值得推荐
评分开卷有益,卷卷有味,不错,值得推荐
评分开卷有益,卷卷有味,不错,值得推荐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