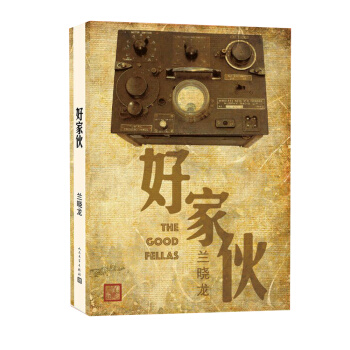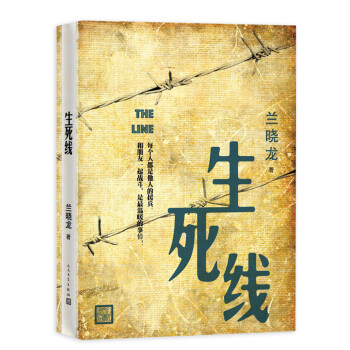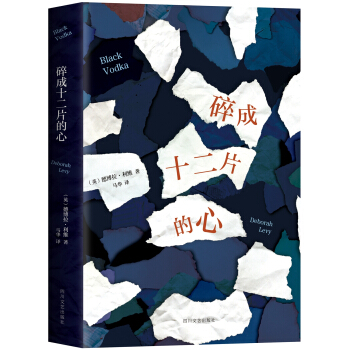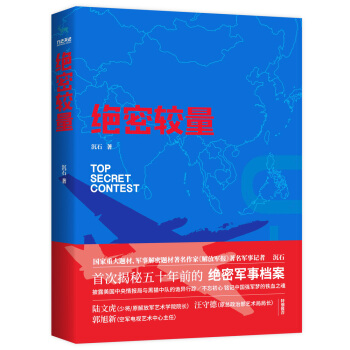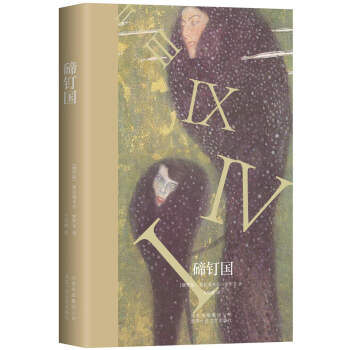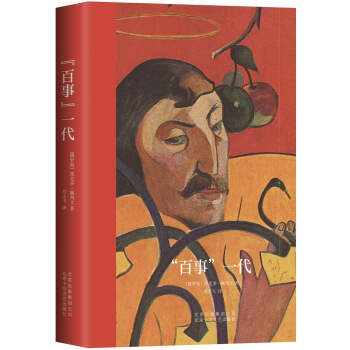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古船》是 一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小说,描写了胶东芦青河畔洼狸镇上几个家庭40多年来的荣辱沉浮、悲欢离合,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块土地的变化。它以一个古老的城镇映射了整个中国,以一条河流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以一个家庭的沧桑抒写灵魂的困境与挣扎。作者以细腻而饱含深情的笔触,勾勒众生,文本深厚而富有感染力。它是当代中国*有气势,*有深度的文学杰作之一,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古船》获得庄重文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精彩书评
《古船》是张炜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这部小说所展现的深远的背景、深重的苦难、深刻的命运,所蕴含的深沉的思想、深切的情感,经历了三十年时光的磨洗,依然清晰醒目,令人动容。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我们的土地上有过许多伟大的城墙。它们差不多和我们的历史一样古老。高筑墙,广积粮,被认为是上上之策。于是在黝黑的泥土上,在贫瘠的山岭上,就有了那么多崇高连绵的东西。每座城下都流过血,滋润出一簇簇青草。庄严的齐国长城西接济水,东临大海,曾把整个山东半岛横切为南北两半。像很多城墙一样,齐长城如今也毁掉了。《括地志》上记:“(齐)长城西北起济州平阴县,缘河历太山北岗上,经济州、淄州,即西南兖州博城县北,东至密州琅琊台入海。”沿着它指引的方向去寻找古城的踪迹吧,总还能够看到几处遗址。临淄故城就是齐都,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齐献公由薄姑迁入,直到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秦始皇灭齐,历经了六百三十多年。而秦汉时又完全沿用了齐故城,直到魏晋。齐国古城在一千多年的旷远历史中竟然一直不朽。芦青河发源于古阳山。古阳山地带也有一截城垣,是否属于齐长城就很难考了。有人在这一带多次勘查,结果不得而知。后来他们又沿河水北上四百里,来到中下游一座叫“洼狸”的重镇。那儿最触目的竟然还是一道城墙:整个大镇被一道很宽很矮的土墙围起来。墙基露着三合土,城是方的;拐角处陡然高大起来,并有包砖。砖的颜色已经像铁,最上一层的城垛还很完整。勘查者抚摸着砖石,仰视城垛,久久不愿离去。也就是这次北上,他们发现了一处极为重要的古都遗址:东莱子故城。遗址离洼狸镇很近,那儿有一座高大的“土堆”──仅存的一截夯土城垣。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镇上人已经用它烧了几辈子砖窑。砖窑自然马上被废止,并立起一块石碑,上面刻了金字,说明这个土堆是东莱子国的故城墙,属重点保护文物等等。洼狸镇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却从此知道自己的镇子曾坐落在东莱子国的都城里。事情再明白不过,大家都在“东莱子国”里过生活了。稍微展开一下想象,就依稀可见那在阳光下闪亮的甲胄,听到战马的嘶鸣。不过兴奋之余也多少有些遗憾:似乎古都城墙不该是那个“土堆子”,而活活就该是这镇子的高大城墙。
铁色的砖墙城垛的确也显示了洼狸镇当年的辉煌。芦青河道如今又浅又窄,而过去却是波澜壮阔的。那阶梯形的老河道就记叙了一条大河步步消退的历史。镇子上至今有一个废弃的码头,它隐约证明着桅樯如林的昔日风光。当时这里是来往航船必停的地方,船舶在此养精蓄锐,再开始新的远航。镇上有一处老庙,每年都有盛大的庙会。驶船人漂荡在大海上,也许最爱回想的就是庙会上熙熙攘攘的场景。老河道边上还有一处处陈旧的建筑,散散地矗在那儿,活像一些破败的古堡。在阴郁的天空下,河水缓缓流去,“古堡”沉默着。一眼望去,这些“古堡”在河岸一溜儿排开,愈来愈小,最远处的几乎要看不见了。可是河风渐渐会送来一种声音:呜隆、呜隆......越来越响,越清晰,原来就是从那些“古堡”里发出来的。它们原来有声音,有生命。但迎着“古堡”走过去,可以见到它们大多都塌了顶,入口也堵塞了。不过总还有一两个、两三个“活着”,如果走进去,就会让人大吃一惊:一个个巨大的石磨在“古堡”中间不慌不忙地转动,耐心地磨着时光。两头老牛拉着巨磨,在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的路上缓缓行走。牛蹄踏不到的地方,长满了绿苔。一个老人端坐在一旁的方凳上,看着老磨,一会儿起身往磨眼里倒一木勺浸湿的绿豆。这原来是一处处老磨屋。那呜隆呜隆的声音更像远处滚动的雷鸣。河岸上原有多少老磨屋,洼狸镇上就有过多少粉丝作坊。这里曾是粉丝最著名的产地,到了本世纪初,河边已经出现了规模宏大的粉丝工厂,“白龙”牌粉丝驰名世界。宽宽的河面上船帆不绝,半夜里还有号子声、吱吜吱吜的橹桨声。这其中有很多船是为粉丝工厂运送绿豆和煤炭,运走粉丝的。而今的河岸上还剩下几个老磨在转动,镇子上就剩下了几个粉丝作坊。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破败的老磨屋为什么在漫漫的岁月中一直矗立着?它们在暮色里与残破的城墙遥遥相对,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又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由一道城墙围起的这片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泥土上,一代代生息繁衍了这么多人口。矮矮的小屋,窄窄的巷子,表明了他们生活得多么拥挤。但人口再多再乱,只要从家族、从谱系上去看,就会清楚得多。血缘关系的纽带会把一些人执拗地连结在一起。他们的父亲、爷爷、老爷爷、太爷爷,再到儿子、孙子、曾孙子......图解起来像一串串葡萄。这个镇子主要由三大姓组成:老隋家、老赵家、老李家。老隋家的兴旺是其它两姓远不能比的。人们认为这与一族人的底气有关。在人们的记忆中,老隋家好象就是从粉丝工业上兴旺起来的,最早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作坊。到隋恒德这一代,老隋家到了最兴盛的时候。他们在河两岸拥有最大的粉丝工厂,并在南方和东北的几个大城市里开了粉庄和钱庄。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隋迎之,一个叫隋不召。兄弟两个先在家里跟一个老先生读书,后来隋迎之又被送到青岛读洋书。隋不召常到码头上闲逛,一直逛到哥哥读书回来。他扬言说总有一天要跟上大船到海上去。开始隋迎之不信,后来终于害怕起来,就告诉了父亲。隋恒德用一片乌木板打了小儿子的掌心,小儿子搓着手,死死盯住父亲。老人最后终于从这眼神上明白过来,知道管教也是枉然,说一声“罢”,也就扔了乌木板。一天深夜刮起了大风,雷声不绝,被惊醒的隋迎之爬起来看了看,弟弟不见了!
隋迎之为弟弟遗憾了多半辈子。父亲过世后,他一个人接过了宠大的家业,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也让孩子们读书,也偶尔使用一下乌木板。这时候渐渐到了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老隋家开始走下坡路了。隋迎之的结局很惨。只是在死前那一段,他才忽然羡慕起隋不召来了,但这会儿什么都晚了......隋不召在水上飘荡了半辈子,大哥过世的前几年才回到镇上。他不认得镇子,镇子也不认得他了。他走路晃晃荡荡,把洼狸镇的街道当成船板了吗?喝酒,酒沫子从胡须上流下来,直流到裤腰上。这哪里是老隋家的二少爷,干瘦干瘦,走路时两条小腿不停地交绊,脸色蜡黄,眼珠都是灰的。他一张嘴就胡言乱语,吹得没有边儿,说这些年可见了大世面,驾船到了南洋、西洋,领头的就是郑和大叔。他叹息道:“大叔可是个好人哪!”没有人信他的话。他讲海上生生死死的故事,倒有不少年轻人围上听。他说行船得按《海道针经》上来,那是一本航海的古书。年轻人不眨眼地听,他倒哈哈大笑起来,说南海沿那些姑娘好啊......镇上人断定:这个人注定这辈子完了。老隋家也注定完了。
隋不召回来这一年该记入镇史。就是这年春天,有一个巨雷竟然打中了老庙。半夜里庙宇烧起来,全镇人出来救火。大火映亮了整个洼狸镇,有什么在火里像炮弹一样炸着,老人们说那是和尚盛经的坛子烧碎了。古柏像是有血脉有生命的东西,在火焰里尖声大叫。乌鸦随着浓烟飞到空中,悬巨钟的木架子轰隆一声倒塌了。除了燃烧的声音,人们还仿佛听到一种低沉的呜鸣,忽高忽低,像是巨钟的余音,又像是从遥远的地方吹响的牛角号。令人震惊的是火焰就随了这声响忽高忽低。灼热的气流把围上近前的人烤得大叫,火舌就像红色的指头一样伸出老长,把试图冲上去救火的人一个一个按倒。他们哼哼着,爬起来就再也不敢上前了。老老少少呆若木鸡,鼻涕挂在嘴巴上。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场大火。天放亮时老庙也正好烧完,接着大雨浇下来。雨水冲涮着灰炭,黑色的水流像浓厚的墨汤一样在街上缓缓流动。全镇人都沉默了,鸡狗鹅鸭也缄口不语。天一黑,大家都赶紧上炕睡觉,要说话也只是互相看一眼。十天之后,有一条远道来的船在芦青河搁浅了。全镇人惊慌地跑到岸边:河心里停了一条三桅大船。河水分明是变得浅窄了,波浪微微地拍打着堤岸,很像是打着告别的手势。大家帮着拽那条大船了。
后来终于又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船搁浅。令人恐惧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河水越来越窄,最后是进不来船了。人们眼瞅着一个大码头在慢慢干废。
整个镇子都变得懒洋洋的。隋不召在街上蹿着,一对小灰眼珠流露出深深的悲哀。隋迎之的头发花了,常常叹气。粉丝工业特别赖水,河水浅下去,就不得不停下几个磨屋。最让他忧虑的还有世事的变迁,一颗心像被什么日夜绞拧着。至于这个从大海上归来的兄弟,也愈来愈令他伤心失望。有一次几个女工抬着一箩湿粉丝去晒粉场上,扔下箩筐就慌张地跑回来,说今天无论如何也晒不得粉丝了。隋迎之搞不明白,亲自到场上看了看。原来是隋不召一丝不怪地仰躺在细细的白沙上,舒服地晒着太阳。
隋迎之的大儿子隋抱朴当时已经长得天真可爱,到处跑动,人们见了都说:“老隋家的又一棵旺苗。”隋不召也特别喜欢这个侄子,常常把他扛在肩头上。他们最常去的就是那个干废的码头,望着变窄了的河道讲一些船上的故事。抱朴慢慢长高了,长得挺拔俊逸,隋不召不得不把他从肩上放下来,又去扛小侄子见素。抱朴这时候已经很懂些事情了,父亲悬腕为他书下几个大字: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他希望儿子将其当成座右铭。抱朴恭恭敬敬地收了起来。这一年的春夏秋三个季节无声无息地过去了。冬雪落在闪亮的河冰上,覆盖了河道,覆盖了河岸上那一个个古老的磨屋。雪天里有不少人跑去看老李家的一个和尚打坐。看着老人泛青的头顶,人们不由得就要去回想那座辉煌的庙宇;同时也想起停泊的帆船,欸乃之声不绝于耳。老和尚打坐完毕常常就讲起古来,大多数人却觉得像谶语一样费解。
齐魏争夺中原,洼狸人助孙膑一臂之力,齐威王才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秦始皇二十八年先到鲁南邹峄山,再到泰山,最后来到洼狸,修船固锚,访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孔子四方传礼唯独不来齐东,野人知礼。圣人尚有遗落未知之礼,派颜回、冉有来夷族求礼。他两人在芦青河上猎鱼,学圣人钓而不纲。有一洼狸镇人听墨子讲经十年,出自他手的飞箭能行十里,而且騞然有声。他磨一面铜镜,可以坐观九州。洼狸镇还有出名的僧、道。李安,字通妙,号长生;刘处玄,字长真,号广宁;皆洼狸人。万历年间飞蝗如云,遮天蔽日,人食草、食树、食人。镇上一高僧静坐入定已经三十八天,后经徒弟用铜铃引醒。高僧直奔城头,手搭晾棚道一声“罪过”,满天蝗虫收入袍袖,又被他抖入河底。长毛造反,四村八乡的百姓跑到洼狸城下,危急时城门大开,救了四村八乡......如净琉璃,内现精金,以前妙心,履以成地!
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大家还是十分激动。长时间来,全镇忍受着令人难堪的寂寞和无言的痛楚。河水消退了,码头干废了,听惯的行船号子也远远地消逝了。一种说不清的委屈在人们的心底泛起,渐渐化为愤怒。只是在这嗡嗡的讲古声里,有人才醒悟过来:老庙烧了,那口巨钟还在。岁月把雄伟的镇城墙一层层剥蚀,但还有完整的一截,余威犹存。大家似乎觉得:没有了那么多外地人来镇上搅闹,倒可以生活得更福气。儿子会更孝顺,女子会更贞洁。
河水无声地流淌着。窄窄的河道,水面上泛着苍白的颜色。一个个“古堡”似的老磨屋矗在河岸,渐渐有青藤攀上石基。大多数老磨屋沉默了,只有几个巨磨还在一天到晚地转动,发出“呜隆呜隆”的声响。牛蹄踏不到的地方,青苔越来越多了。看磨老人用木勺叩击着黑洞洞的磨眼,发出“(同:口匡;音:筐)(同:口匡;音:筐)”地声音。老磨缓缓转动,耐心地磨着时光。远处,那段高耸的镇城墙与岸边的老磨屋久久对视,沉默无言。
外面的人似乎把洼狸镇给忘掉了。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才有人重新记起她来。当然,外面的人首先记起的还是那一截镇城墙。当时我们的土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都在沸腾。人们完全有信心花上几年的时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外面的人就是在这时记起了镇城墙的,记起它的上面有好多砖。于是,一天清晨涌来一群人扒城取砖了。洼狸镇一下子呆住了,不少人激动得啊啊大叫。但扒城的人群手持一杆红旗,镇上人知道有些来头,就急急差人去喊四爷爷来。四爷爷当年不过三十出头,因为他在老赵门里辈分最高,所以人们也就这么喊。当时不巧他发疟疾,在炕上折腾了一天,实在没有力气爬起来。去的人是隔着窗户纸向四爷爷报告的。四爷爷听了,轻轻哼了一声,吩咐道:
“闲话没有,先把把领头那个人的腿砸断。”
镇上人抄起抓勾、扁担涌出了城门。拆城的人正在兴奋的时候,没想到一眨眼给围困起来。洼狸镇人挥起扁担就打。被打倒的人爬起来嚷:“讲不讲理?”举扁担的红着眼睛还一句:“鬼孙子,祖宗的城都敢扒,哪还有理!”说着扁担又从空中落下来。拆城的人被迫自卫,纷纷把手里的器具架在头上。有个打头!闷气憋了几十年,好哇,看家伙。洼狸镇人弓下身子,个个都机警地四下瞟着,猛然就平地跃起,挥起扁担,下手恶狠。拆城人慌了。正在这时突然传来凄惨的一声长喊,在场的人都不由得住手去看:原来是那个领头人的腿被打断了;一边正站立着一个镇上人,他嘴唇发青,颊肉微微抖动,头发一根根直立起来......明白了,这是恶手,不是唬人。洼狸镇大清早抖出了几辈子的凶气。拆城人不敢犹豫,抬起断腿的人就逃散了。一截城墙就这样保住;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动乱不止,但仅仅丢失了三块半老砖。
城墙骄傲地屹立着。也许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摇撼它,除非是它根植的那片土地本身会抖动起来。老磨呜隆呜隆地转着,耐心地磨着时光。那像古堡一样矗立着的老磨屋,青藤已经从基石攀到了屋顶,又在石墙上织成一面网。又是很多年过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片土地真的抖动起来──那是一个凌晨,土地抖动着,把全镇人都从沉睡中摇醒。接着就是沉闷的一声钝响,镇城墙塌下了一个城垛。
全镇人被深深地震撼了,一颗颗心都揪得紧紧的。大家不约而同地去回想老庙烧毁的日子,三桅船搁浅的日子。这次又毁掉了一个城垛,但这次是土地抖动了啊。人们(同:口丝;音:私)(同:口丝;音:私)地吸着凉气,极力去寻找其中的原因。后来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土地抖动以前是有过先兆的,只是大家都忽略了,以至于落下了永久的遗憾:有人看见无数条花花绿绿的蛇向芦青河岸上爬去;一头大猪一夜劳作,令人吃惊地在栏里掘了一个宽阔的大洞;母鸡在院墙上排起一行,一齐呼叫,一齐行走;刺猥坐在院子当心,像老头一样咳个不停。这就是土地抖动之前动物的异常反应。但镇上人认为令人不安的“先兆”还远远不止这些。半年多来,更深一层的忧虑和惊诧,就在折磨着全镇的人了。那是更深一层的忧虑和惊诧啊。
那时候,一个谣传像蝙蝠一样在镇城墙上飞动。全镇人都慌慌地议论着刚听来的各种消息:又要重新分配土地了;工厂,还有那些粉丝作坊,都要转交到个人手中经营。老天,时光真的像老磨一样又转回去了?没人敢相信会是真的。可是不久报上也印了类似的意思,接上镇子开起了大会,号召分地、把工厂和粉丝作坊转包到个人手里。洼狸镇惊呆了。有好多天,全镇没有一点声息,就像很久以前巨雷劈了老庙时的气氛一样。大人孩子都不说话,吃了晚饭互相盯几眼,赶紧上炕睡觉,连鸡狗鹅鸭也缄口不语。人们只在心里呼叫着:“洼狸镇哪,你这个背时倒运的镇哪,你还能走到哪里去啊?”......镇长和街道主任亲自领人丈量土地了,每丈量一块,就告诉大家一声:这叫责任田。后来剩下大大小小的工厂和粉丝作坊了。谁来承包呢?停了十几日,终于有人把那些工厂包下来。最后只剩下粉丝作坊了。再也没有人向它伸手。河岸上那一溜老磨屋神秘地沉默着,凶吉未卜。谁都明白:这些黑黝黝的破败的老磨屋简直就凝聚了洼狸镇的全部精气、全部晦气,活活连结着镇子的荣辱兴衰。谁敢踏进这阴暗潮湿、生满了青苔的“古堡”里,去充当它的主人呢?镇上人从来就把粉丝工业当成一个古怪行当。老磨屋、漏制粉丝的房子,都有难以言说的复杂和神秘。在粉丝生产过程中,水温、酵母、浆液、面糊......任何一个微小的关节出了毛病都会招致全局失败:淀粉突然不沉淀了!粉丝突然断成一截一截!......做粉丝的人把这种情况叫“倒缸”。他们惊呼着:“倒缸了!倒缸了!”却常常束手无策。不知有多少老师傅最后背着人跳进了芦青河。有一个师傅被人救起,第二天他又把自己悬在老磨屋的梁上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当。如今谁该当老磨屋的主人呢?老隋家几辈子都做粉丝工业,由老隋家的人出头承包不是更合适一点吗?终于有人鼓动起隋抱朴来了,结果这个四十多岁的红脸汉子连连摇头。他盯着河岸上那一溜磨屋,呜呜哦哦地咕哝着什么,满脸的慌蹙。
就在这个时候,老赵家的赵多多做出了惊人之举:出头承包了粉丝作坊。
整个洼狸镇沸动了。赵多多承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作坊改称“洼狸粉丝大厂”。人们见了面互相对视,都有些眼花缭乱了。大家好象突然明白起来:粉丝工业如今再不是洼狸镇的,它也不姓隋了,它是老赵家的了!天哪,老磨一天到黑呜隆呜隆转着,它要转到哪里去啊......全镇人常常望着那一溜磨屋发呆,他们觉得世事的变异奇怪得很,这一切的一切一点也不比母鸡在院墙上排队行走和刺猬大咳差到哪里去。“日子翻个个了”,镇上人都这么说。所以当土地在一天凌晨抖动起来的时候,只有人恐惧,没有人惊讶。
用户评价
说实话,《旧日低语》这本书一开始我差点就放下了,它的开篇节奏非常缓慢,充满了对一个偏僻小镇日常生活的冗长描述,各种家族间的陈年旧事被琐碎地铺陈开来。但是,如果能坚持读过前三分之一,你会发现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最后那场情绪的爆发。作者的叙事风格非常古典,像是在娓m描绘一幅缓慢晕染的水墨画,色彩由浅入深,最后定格在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剧性结局上。它探讨的核心是“时间如何腐蚀人心”以及“被遗忘的历史如何反噬现在”。镇子上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极为立体,每一个看似平凡的角色背后都藏着一段沉重的往事,他们的对话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暗流涌动,充满了未尽之意。这本书需要耐心,但回报是丰厚的,它教会你如何去品味那种“欲说还休”的东方美学。
评分《风语者的遗产》这本书,我只能用“磅礴大气”来形容。它是一部融合了民族史诗与奇幻设定的鸿篇巨制,世界观的构建之宏大,令人叹为观止。作者似乎倾注了毕生心血去描绘这个架空的大陆,从山川河流的地貌特征到不同部落的语言、习俗、信仰体系,都做到了详尽而富有想象力的铺陈。故事主线围绕着一场跨越数代的战争和一位被预言选中的人物展开,节奏把握得张弛有度,高潮部分的史诗级战斗场面,读起来酣畅淋漓,脑海中自动生成了电影般的画面。然而,它并非单纯的英雄赞歌,作者也着墨于战争带来的创伤和和平的代价,使得整个叙事拥有了厚重的历史感和人道关怀。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就像是在翻阅一本厚重的、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古老羊皮卷。
评分我最近读完的《代码之外的秘密》,简直是一本教科书级别的悬疑小说。它的厉害之处在于,逻辑推理构建得天衣无缝,每一条线索的抛出都精准无比,既能引导读者产生合理的猜测,又能在关键时刻用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彻底推翻之前的认知。作者似乎对犯罪心理学和侦查技术有着深入的研究,书中的专业术语和流程处理得极为自然,完全没有为了堆砌专业知识而显得生硬。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没有采用那种极度血腥或夸张的手法来营造紧张感,而是通过步步紧逼的心理战术,让读者自己陷入到一种无形的焦虑之中。每一次翻页都像是进行一次与作者的智力对决,你总以为自己抓住了凶手,结果下一秒就被作者带到了另一个死胡同。非常适合喜欢动脑筋、享受抽丝剥茧过程的读者。
评分这本《迷雾之海》读起来简直是一场对灵魂的洗礼。作者的笔触细腻得像描绘一幅油画,每一个场景都栩栩如生,让人仿佛能闻到海水的咸味,听到海鸥的鸣叫。故事围绕着一个失落已久的航海日记展开,揭示了一个关于勇气、牺牲和不为人知秘密的宏大史诗。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那些在极端环境下展现出的复杂人性,真实得让人心疼又敬佩。主角的挣扎、迷茫以及最终的自我救赎,完全抓住了读者的心弦。读到那些惊涛骇浪的描写时,我甚至能感觉到心跳加速,那种身临其境的体验是很多作品难以企及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冒险故事,更像是一面映照我们自身弱点与力量的镜子。书中的一些哲学思辨也十分深刻,关于命运与自由意志的探讨,让人读完后久久不能平静,需要时间去消化和反思。
评分我最近翻阅的这本《星辰坠落之夜》,给我的感觉是极其冷峻和疏离,但又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魔力。它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赛博朋克世界,霓虹灯下的阴影与高科技的冰冷并存,展现出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深刻洞察。叙事手法非常独特,大量运用了碎片化的叙事和意识流的描写,初读时或许会有些许晦涩,但一旦适应了这种节奏,便会发现其中隐藏的精妙结构和层层递进的线索。作者对“数据”、“记忆”和“真实”的定义提出了挑战,探讨了当技术发展到极致,人类的本质是否会被彻底重塑这一命题。这本书的氛围营造非常成功,那种压抑、疏离感透过文字直击内心,让人不禁思考自己所处世界的真实性。里面的技术设定细节考究,逻辑自洽,显示出作者在硬科幻领域的深厚功底。
评分包装很好,物流很快,非常满意。
评分书不错 正版,送货速度也非常快!好评!
评分包装很好,物流很快,非常满意。
评分包装很好,物流很快,非常满意。
评分年轻时读过的,怀念一下
评分装帧设计都合心意谢谢京东
评分书在3我身边,有空找我拿回来给我发信息给我发信息
评分名社名家,经典之作,喜欢
评分年轻时读过的,怀念一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