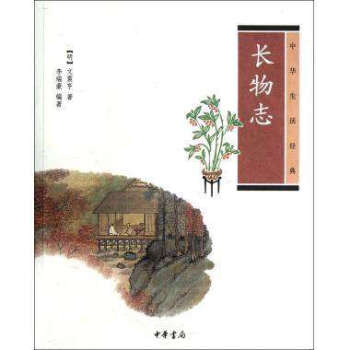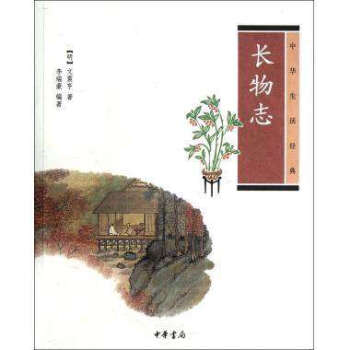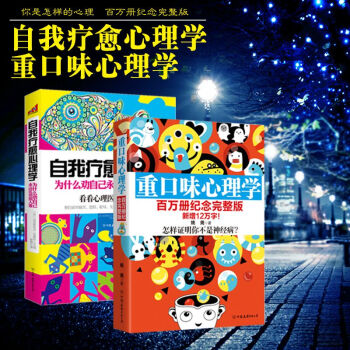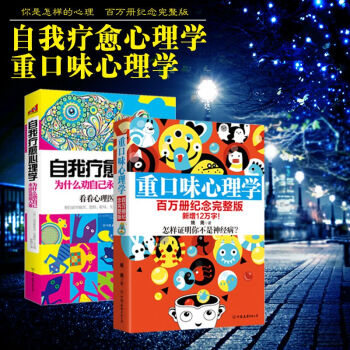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获央视评选2014年“中国好书”,第10届文津奖获奖图书。
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有趣、有料、有价值,是一本信息量很大的硬货。作者是科物理系研究院员,过硬的理科背景为本书的理性做了保障。正如副标题“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所言,这本书不仅抖了很多有趣的“反常识”知识,更重要的是“现身说法”,用客观、理性、逻辑的方法,加上广阔的视野,逐一分析了诸多案例。我想,介绍这种思维方法才是本书的核心,也是读者应该了解和学习的地方。无论在学习、工作、生活,甚至炒股,投资,创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书中大量案例也非常有趣。比如一个被媒体广泛传播的事件,伦敦奥运会为运动员准备的15万个避孕套在5天内被用完。当时很多媒体、公众人物发表了各自的观点,有说运动员花心,压力大等等。但没有人多问一句,这个数量级背后更合理的逻辑是什么?事实上有人把这些避孕套转手卖出。这些有趣的案例提醒读者,凡事多思考,客观看问题,而不是只停留在情绪共鸣。
——编辑艾丽萨
名人推荐
读这本书绝不像读某些流行读物那么畅快,它需要你时不时停下来,想几步,甚至,合卷后也未必能给你增加多少谈资——或者说,作者并不热衷于提供“有趣的知识”,他致力提供的是传说中的“科学理性思维”。他的野心是让“反常识思维”变成“常识思维”。
——姬十三(果壳网CEO)
你可以不同意这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但绝不能忽视作者所采用的,基于科学理性的思考方式,这才是这本书有价值的地方。
——土摩托(媒体人,《三联生活周刊》特约撰稿,著有《土摩托看世界》)
与同人于野一起寻找话题,堪称世界上有趣的事情之一,因为很少有人能把科学新知这块天地的魅力展现得如此清晰透彻。
——范致行(《新知客》、麻省理工《科技创业》前主编,读首诗再睡觉创始人)
这几年,我一直心甘情愿地被一个理工男“洗脑”,他就是万维钢。
——张明扬(《东方旱报—上海书评》执行主编)
同人于野即万维钢是我知道的善于用理科思维看社会问题的人,这本书只包括了一部分他历年写的文章,多数是关于个人的,例如一万小时定律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就像他在书中所写,这是一本值得马上读第二遍的好书。
——李淼(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物理学家和作家,著有(《越弱越暗越美丽》)
万维钢是少有的能与国外作者在视野、阅读量、写作方式与勤奋程度等方面一较高下的汉语写作者,无论对读者还是编辑来说,他都是一位理想的作者。我愿意向任何人毫无保留地推荐他的文集。
——郑诗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澎湃新闻思想版块编辑)
媒体推荐
读这本书绝不像读某些流行读物那么畅快,它需要你时不时停下来,想几步,甚至,合卷后也未必能给你增加多少谈资——或者说,作者并不热衷于提供“有趣的知识”,他致力提供的是传说中的“科学理性思维”。他的野心是让“反常识思维“变成“常识思维”。
——姬十三(果壳网CEO)
你可以不同意这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但绝不能忽视作者所采用的,基于科学理性的思考方式,这才是这本书有价值的地方。
——土摩托(媒体人,《三联生活周刊》特约撰稿,著有《土摩托看世界》)
与同人于野一起寻找话题,堪称世界上有趣的事情之一,因为很少有人能把科学新知这块天地的魅力展现得如此清晰透彻。
——范致行(《新知客》、麻省理工《科技创业》前主编,读首诗再睡觉创始人)
这几年,我一直心甘情愿的被一个理工男“洗脑”,他就是万维钢。
——张明扬(《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执行主编)
同人于野即万维钢是我知道的善于用理科思维看社会问题的人,这本书只包括了一部分他历年写的文章,多数是关于个人的,例如一万小时定律以及它的真正含义。就像他在书中所写,这是一本值得马上读第二遍的好书。
——李淼(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物理学家和作家,著有《越弱越暗越美丽》)
万维钢是少有的能与国外作者在视野、阅读量、写作方式与勤奋程度等方面一较高下的汉语写作者,无论对读者还是编辑来说,他都是一位理想的作者。我愿意向任何人毫无保留地推荐他的文集。
——郑诗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澎湃新闻思想版块编辑)
作者简介
万维钢,笔名同人于野,“学而时嘻之”博主。博文介绍为“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喜欢科学和政治,作品以理性思维见长。1999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新知客》、《新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特约撰稿人,天涯名博,在知乎、果壳、观察者、共识网等国内知名网站上设有专栏,在《麻省理工科技创业》、《商界评论》等报刊和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文章常引发大众思考,掀起诸多话题讨论。《流言时代的赛先生》及《十万个为什么》(新版)的数学分册和物理分册作者之一。
目录
Part One 反常识思维 1
“反常识”思维 2
别想说服我! 10
真理追求者 19
坏比好重要 23
简单概率论的五个智慧 27
一颗阴谋论的心 40
桥段会毁了你的生活 50
健康的经济学 55
核电站能出什么大事 59
Part Two 成功学的解药 65
科学的励志和励志的科学 66
匹夫怎样逆袭 73
练习一万小时成天才? 82
的想象力是不自由的 128
思维密集度与牛人的反击 133
上网能避免浅薄吗? 136
高效“冲浪”的办法 141
笔记本就是力量 145
用强力研读书 151
创新是落后者的特权:三个竞争故事 165
过度自信是创业者的通行证 172
夺魁者本色 177
打游戏的三个境界 186
穷人和富人的人脉结构 190
Part Three 霍金的答案 199
亚里士多德为何不数数妻子有几颗牙 200
物理学的逻辑和霍金的答案 205
怎样用统计实验检验灵魂转世假说 210
一个关于转世的流行病学研究 214
摆脱童稚状态 224
怎样才算主流科学? 232
科研的格调 240
喝一口的心理学与喝一瓶的心理学 244
医学研究能当真吗? 248
真空农场中的球形鸡 254
序言
序言
我和万维钢未曾谋面,但在网上神交已久,互为读者和粉丝。在模糊的记忆中,早似乎是通过刘夙给的链接发现了同人于野的博客,读过一篇之后便停不下来了。恰逢需要出差,灵机一动,利用一台贪便宜买来又没啥用的MP4的电子书功能,把他博客里的几十篇文章都下载到MP4里面,在动车上大饱眼福。其实旅程的无聊不算什么痛苦,毕竟有窗外的景色可看,知道有好文章却要在数日后方能有时间看,才足以令人牵肠挂肚,很不舒服。
从前听长辈说,人到老年,看书看皮儿,看报看题儿。我原以为,大概是因为老花眼看不清小字之故。或者是来日无多,学习的下降,学习欲望也就相应减退了。等到自己也到了这个年纪,就发现这两个原因固然都有,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东西多了就会发现,真正有价值,值得花功夫和精力认真去看的作品,少之又少。当然,对于年轻人而言,这种态度显然不对,年轻人看什么都新鲜,都未知,都长见识,不吃前两个烧饼,只吃第三个烧饼也吃不饱。不阅读很多糟粕,也没有能力发现精华。
微博上常看到推荐书目,也没兴趣点开看都推荐了些什么书,估计不外乎一些名著。提起名著,就想起一句名言:所谓名著,就是人人都说应该看,但谁也不看的书。我也多次看到本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作堆在书店里无人问津。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我不会推荐那些适合用来装X的名著,只会推荐一本书,就是这本尚未成名之著《万万没想到》。
推荐的理由就是:这本书真的有用,而且对大多数人都有用。
世上有用的书很多,例如各种专业书籍,你不读就进入不了这个行当,但是如果你并不想进入这个行当,专业书对你的用处就不大。而这本书就如同一部人生指南,只要想改善自己人生的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指导人生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其中有用的却如凤毛麟角。
本书值得一读的理由可归结为四点:
是新颖性。正如本书的书名《万万没想到》所示,本书所介绍的知识大多是与流行说法背道而驰的,可以改变我们很多固有的错误观念。我说本书有用也基于这个理由,毕竟,阅读一大堆老生常谈而不改变原来的想法,无异于浪费时间。
第二是科学性。本书的新颖,绝非信口开河的标新立异,而是由严谨的科学实验得到的结论。唯此才能有力地颠覆旧观念。这也是我认为本书很靠谱的理由。
第三是可操作性。本书不只是价值观的指针,更是行动的指南。有很多具体建议帮助你把领悟的道理付诸实施,这是很多类似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第四是深刻性。本书不仅提供了知识,更提供了获得知识的方法和判断知识是否可信的准则,即所谓“元知识”的内容。读过本书,对于今后接受和评判新知识具有指导意义。
此外,本书的可读性也是出类拔萃的。语言生动,引人入胜,捧起书就想一气读完。这当然是好作品的基本要求,毋庸赘言。
本书内容分为三部分。
部分谈的是人性。在文艺作品的评论中,常常可以看到说此作品深刻的刻画了人性。但是如果你想通过欣赏这些作品使你对人性有更深入或与众不同的看法,那你百分之百会失望。本书所谈的人性,都是通过认知科学的实验研究,得出我们自身的认知倾向。这些倾向并非十全十美,往往造成我们的错误认识。了解我们自身思考过程中的陷阱,可以有意识地避免很多常犯的错误,学会用理性审查直觉。
第二部分谈励志。如今励志书也属于畅销的一类,大抵是成功人士的自传,有些甚至宣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但是你真要想复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别人走过的路永远不会是自己能走的路。本书告诉我们励志也是有科学规律的,告诉我们如何以己之长克人之短。即使是读书一事,也有很多具体的技巧,更不用说要成为某项技艺的高手,科学的训练必不可少。至少在如何学习和训练以提升自己这方面,本书是介绍了很多实用诀窍的。
第三部分讲科学。科学的思想方法对人大有益处,起码可以大大减少受骗上当。特别是在信息爆炸的,缺乏科学精神会让脑袋里堆满垃圾。遗憾的是,现实中科学素养合格者在普通人群中只占不到百分之五。掌握大量的科学知识和从事科学研究也未必能使头脑中的科学精神同步增长,院士说蠢话也并不罕见。本书涉及具体的科学知识不多,但对于培养科学精神大有补益。我很希望文人们也来读一读这本书,不奢望他们会由此养成科学精神,即使能够由此了解一下“理呆们”如何想问题,也是一大收获。
如果说本书有何不足,那就是作者还有很多精彩文章未能收录,读者只能期待下一本书了。等不及的可以杀奔同人于野的博客,先睹为快。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
文摘
“反常识”思维
芦山地震,有人批评我国电视台的报道过于煽情。记者们有意刻画了太多哭泣和死者的画面,他们竟试图采访一个还在被废墟压着的人,甚至还想直播帐篷里正在进行的手术。你这是报道灾情呢还是拍电视剧呢?
但煽情是文人的膝跳反应。人们普遍反映日本NHK的灾难报道非常理性和专业,然而对绝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煽情是他们能听懂的语言。不煽情就没有高收视率。也许更重要的是,煽情可以获得更多捐款。
在2007年发表的一个研究中,几个美国研究者以做调查为名招募了若干受试者,并在调查结束的时候发给每个受试者5美元作为报酬。不过研究者的真正目的是搞一个决策实验。这个实验的机关在于,随着5美元一同发到受试者手里的还有一封呼吁给非洲儿童捐款的募捐信。而这封信有两个版本:
个版本列举了一些详实的统计数字:马拉维有三百万儿童面临食物短缺;安哥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四百万人,被迫远离家园,等等。
第二个版本说你的全部捐款会给一个叫Rokia的七岁女孩。她生活在马里,家里很穷,时常挨饿,你的钱会让她生活更好一点,也许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卫生条件。
研究者问受试者愿不愿意把一部分报酬捐给非洲。结果收到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1.14美元,而收到第二个版本募捐信的人平均捐了2.38美元。
据说是斯大林说的,“杀死一个人是悲剧,杀死一万个人是统计数字”。这个捐款实验证明统计数字的力量远远比不上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受试者对远在天边的国家的抽象数字没有多大兴趣,而他们对一个具体人物 -- 哪怕仅仅听说了她的名字和简单的背景,都更乐于出手相助。
在石器时代的几十万年里,甚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直到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世界中。我们的活动范围于自己所属的小部落或者小村庄,很多人一生去过的地方也不会超过的路程。我们熟悉每一个有可能打交道的人,而这些人的总数加起来也不是很多。这种生活模式对大脑的演化有巨大的影响。据英国人类学家邓巴估计,我们至今能够维持紧密人际关系的人数上限,也只有150个而已。 当我们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表情。在这些具体例子的训练下,我们的潜意识早就学会了快速判断人的真诚程度和事件的紧急程度:我们不会把钱借给一个嬉皮笑脸的名声不好的坏人,但是会借给一个窘迫不安的众所周知的好人。进化本能使我们毫不费力就可以通过人脸和情绪来作出判断。婴儿刚出生几天就能分辨不同的面部表情,六个月就能识别不同的人脸,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以相当高的准确度从两个政客的照片中找出更有能力的那个。
这种"具体思维"做各种选择的首要标准,是道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世代定居的传统中国社区本质上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做事不是靠商业和法治,而是靠道德和礼治。在这个体系中出了案子,首先关乎的是名声和面子,而不是利益。乡绅会"先照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这简直是丢我们村子里脸的事!你们还不认了错,回家去。"费孝通说乡土中国的高理想是"无讼",就好像足球比赛中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双方的规则,而犯规的代价不单是被罚,更是整个球队和指导员的耻辱。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的首要技能的不是数学计算,而是分辨善恶美丑。也许这就是文人思维的起源:针对每个特定动作的美学评价。有时候他们管这种评价叫“价值观”,但所谓价值观无非就是给人和事贴或好或坏的标签。文人把弘扬真善美和鞭挞假恶丑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低端文人研究道德,高端文人研究美感。他们的原始本能使他们热爱大自然,他们赞美花、赞美蓝天、赞美山水、赞美健康的动物和异性。这些赞美会演化成艺术。可是只有刚接触艺术的人才喜欢令人愉快的东西,审美观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就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感觉,改为欣赏愁苦了。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什么艺术,而现代社会却能让艺术普及,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统计表明过去几十年流行歌曲的趋势是感情越来越忧伤和含糊。所以美学是不可能客观的,每个人都在鄙视别人低端审美观和被别人鄙视,我们在审美观的鄙视链上不断移动。文人有时候研究病态美、悲壮美、失败美等等,也许更高境界则追求各种变态美。但本质上,他们研究美。
文人对事物的议论是感叹式的。有时候他们赞美,有时候他们唾弃;有时候他们悲愤,有时候他们呼吁。他们说来说去都是这个XXX怎么这么YYY啊!
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价值判断称为“常识”,因为这些判断本来就是从人的原始思维本能而来。
然而现代社会产生了另一种思维,却是“反常识”的。
现代社会与古代大的不同,是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还要娱乐和社交、学习和发展、以及随时对遥远的公众事务发表意见。我们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以一种不直截了当的方式影响他人,然后再影响自己。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基本的一个思想,就是好东西虽然多,你却不能都要。
你想用下班时间读书,就不能用同样的时间看电影。你不能又读书又看电影又加班又饭局,还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距离工作地点近的房子通常更贵,你不能要求这个房子又大又便宜又方便。长得帅的未必挣钱多,挣钱多的很可能没那么多时间陪你。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取舍,而很多烦恼恰恰来自不愿意或者不知道取舍。古人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能有一个选择就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了。
取舍这种思维,英文有一个可能更形神兼备的词:tradeoff。两个好东西我不可能都要,那么我愿意牺牲(off)一点这个,来换取(trade)一点那个。Tradeoff是"理工科思维"的起源。讨价还价一番达成交易,这对文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无语的情境!既不美也不丑,既不值得歌颂也不值得唾弃。斤斤计较地得到一个既谈不上实现了梦想也谈不上是悲剧的结果,完全不文艺。所以文人不研究这个。
Tradeoff要求我们知道每一个事物的利弊。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事情是"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所谓"帕累托改进",绝大多数情况下兴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无限大的。可是文人思维仍然停留在有点好东西就高兴的不得了的时代,习惯于无限夸大自己的情感,一边说金钱如粪土,一边说朋友值千金,一边说生命无价,一边说爱情价更高。做过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维要求妥协,而文人总爱戏剧性的不管不顾,喜欢说不惜一切代价,喜欢看动不动就把全部筹码都押上的剧情。理工科思维要求随时根据新情况调整策略,而撒切尔夫人说她"从不转弯"--可能是因为选民爱听这个,不过她的确不爱转弯。
对自己的事物搞不好tradeoff,生活仍然可以对付着过下去。但现代社会要求我们必须在整个社会的尺度上进行tradeoff。从美学角度看计划生育制度不但不美简直还灭绝人性,但是从社会角度人口暴涨的确有可能成为灾难。历史上很多国家因为人口太多而发生生产和社会退化,十八世纪的日本甚至连牛马都不用了,什么都必须用人,甚至打仗都不用枪炮直接退回到原始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计划生育这个动作的美学,我们得计算这个动作的后果。而且这个计算必须随时修正,比如现在就很有必要考虑是否应该继续保留这个制度。但文人却喜欢用一个动作的"美感"来说服别人。万历皇帝想收商业税,东林党反对,而他们给出的反对理由不是收税这个动作的输出后果,而是"天子不与小民争利"!当然有人认为东林党其实代表利益集团,是故意拿道德作为借口,但这种不重知识重姿势的谈话氛围仍然令现代人震惊。
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一书,把人脑的两套思维系统称为"系统1"和"系统2"。前者自动起作用,能迅速对事物给出一个的很难被改变的印象;而后者费力而缓慢,需要我们集中注意力进行复杂计算,甚至我们在系统2工作的时候连瞳孔都放大了。系统2根本不是计算机的对手,没人能在百万分之一秒内计算111.61872的平方根。然而系统1却比计算机强大得多,直到2012年Google用了1.6万块处理器,才让计算机学会识别猫的脸——而且它肯定还不会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分辨表情。系统1这么快,显然是因为它在漫长的进化史中非常有用的缘故。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不会算数,甚至不会清晰地逻辑推理的人只要知道谁对他好谁对他坏,靠本能也能在草原上生活的不错。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他才会有大麻烦。文人思维显然是系统1的集大成者,而理工科思维则是系统2的产物。
Tradeoff要求量化输入和预计输出,这也是理工科思维的根本方法。但人脑天生不适应抽象数字。伦敦奥运会组织者给运动员准备了15万个避孕套,竟在开幕仅仅五天之内被用完。腾讯请来梁文道、蒋方舟和阎连科三位文人对此事发表了意见。这三位都是高端文人,根本不计较道德,专门谈审美,甚至还要做一番技术分析。梁说他从来都是公开支持性产业和性工作者。蒋说拥有基因就会花心。阎说中医认为以毒攻毒,性可能也是一个疏通渠道。三人说的都挺有意思,可他们怎么就不算算一万运动员五天用掉15万个,这是每天六次的水平!真正合理的解释是大部分套被运动员拿走当纪念品了。据运动员说,奥运村还真没到性晚会的程度。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听作文的不如听论文的。以下这四件事,每个文人都想要:(1)用方法种植的有机农业;(2)保护环境;(3)取消人口控制;(4)让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可是这四件事不可能同时做到,你必须放弃一个。有机农产品上的农药残余的确更少,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有机农业的低产量,其生产一单位食物所消耗的水和地都比化肥农业高很多,综合起来的结果是有机农业更破坏环境。产量低是个致命缺点。事实上在没有化肥的时代,人类养活不了很多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再怎么大声疾呼有机农业也没用。
"好吧,"这时候有个文人说,"我有钱我自己吃有机食物,这总可以吧?"可以。但根据2012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表在《内医学年鉴》的一份针对过去几十年两百多项研究的总结报告,有机食物甚至并不比普通食物更健康。
现在到了用理工科思维取代文人思维的时候了。传统的的文人腔已经越来越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上,一篇正经讨论现实问题的文章总要做点计算才说的过去。
本文引用了几个的研究结果,但这其实是一篇一百年以前就能写出来的文章。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至今我们喊了近百年赛先生却仍然没搞清楚赛先生是干什么的。赛先生远不止是“鬼火是磷火”之类的少儿科普。他是常常违反常识,甚至可能变来变去,可是你却不得不依靠他来做出决策的硬知识。他更是有时候简单到tradeoff的一种并不“自然”的思维方式。
别想说服我!
霍金写《时间简史》和《大设计》二书,都有一个被所有人忽视了的第二作者,列纳德·蒙洛迪诺。这两本书能够畅销,我怀疑霍金本人的贡献也许仅仅是他的名气,因为公众其实并不真喜欢科学知识——哪怕是霍金的知识。而霍金也深知“每一个数学公式都能让这本书的销量减少一半”。如果真有读者能在这两本"霍金的书"中获得阅读上的乐趣,很可能要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功于蒙洛迪诺。从他独立完成的Subliminal(《潜意识:控制你行为的秘密》)这本书来看,蒙洛迪诺真的是个非常会写书的人。他完全了解读者想看什么。
看完《潜意识》,我也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了。在书中蒙洛迪诺讲了个很有意思的笑话。说有一个白人天主教徒来到天堂门口想要进去,他跟守门人列举了自己的种种善行,但守门人说:"可以,不过你还必须能够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哪个单词?”“上帝。”“GOD.你进去吧。”
一个犹太人来到天堂门口,他同样被要求正确拼写一个单词才能进。守门人考他的单词仍然是“上帝”。这个单词非常简单,所以他同样拼写正确,于是也进去了。
故事一个黑人来到天堂门口,他面临同样的规则。但是守门人让他拼写的单词是,“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笑话的寓意是像我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接收信息都有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的我们根本不看。我的门槛就相当高,谁想向我说明一个什么科学事实,我一般都要求他出具学术论文。比如作为一个爱国者,我对中医的存废和转基因的好坏这两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特别关注相关的论文。然而就算是论文也有好有坏,要知道有的论文根本不严谨。所以一篇论文质量好坏,我也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达到我的标准才算得上是严谨的好论文:
如果这篇论文是说中医有效的,我就要求它拼写"上帝"。如果这篇论文是说转基因无害的,我就要求它拼写“捷克斯洛伐克”。
你不用笑我,你也有同样的毛病。蒙洛迪诺说,人做判断的时候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科学家机制",先有证据再下结论;一种是"律师机制",先有了结论再去找证据。世界上科学家很少,你猜绝大多数人使用什么机制思考?每个人都爱看能印证自己已有观念的东西。我们不但不爱看,而且还会直接忽略,那些不符合我们已有观念的证据。
有人拿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做了个实验。研究者根据某个容易引起对立观点的议题,比如是否应该禁枪,伪造了两篇学术报告,受试者随机地只能看到其中一篇。这两篇报告的研究方法乃至写法都完全一样,只有数据对调,这样其结果分别对一种观点有利。受试者们被要求评价其所看到的这篇报告是否在科学上足够严谨。结果,如果受试者看到的报告符合他原本就支持的观点,那么他就会对这个报告的研究方法评价很高;如果是他反对的观点,那么他就会给这个报告挑毛病。
去年方舟子大战韩寒,双方阵营都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寻找证据,写了各种"论文",来证明韩寒的确有代笔或者的确没有代笔。有谁记得看到过有人说本阵营的论文不够严谨的么?都认为对方的论文才是胡扯。这远远不是可怕的。如果我反对一个结论而你支持,那么当我看一篇支持这个结论的论文就会不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去看,就会认为这个论文不行;而你,因为支持这个观点,则会认为这个论文很好 -- 如此一来我不就认为你是弱智了么?于是两个对立阵营都会认为对方是弱智。一切都可以在潜意识发生。
认为别人弱智和被别人认为是弱智,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媒体也参与到观念的战争之中。
如果人已经被各种观念分成了阵营,那么媒体就不应该追求什么“客观中立”,因为没人爱看客观中立的东西!媒体应该怎么做呢?技术活动家Clay Johnson在 The Information Diet (《信息食谱》)这本书里,给我们介绍了美国收视率高的新闻台 Fox News (福克斯新闻)的成功秘密。尼克松时期,媒体人Roger Ailes有感于当时媒体只知道报道政府的负面消息,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拥护政府的新闻系统"。然而事实证明Fox News 的成功并不在于其拥护政府 -- 它只拥护共和党政府 -- 而在于Ailes有的新闻理念:(下面事例换字体)
,有线频道这么多,你不可能,也没必要取悦所有观众。你只要迎合一个特定观众群体就可以了。
第二,要提供有强烈主观观点的新闻。
给观众想要的东西,比给观众事实更能赚钱。观众想要什么呢?娱乐和确认。观众需要你的新闻能用娱乐的方式确认他们已有的观念。福克斯新闻台选择的观众群体,是美国的保守派。每当美国发生枪击事件,不管有多少媒体呼吁禁枪,福克斯新闻一定强调拥枪权 – 他们会找一个有枪的采访对象,说如果我拿着枪在现场就可以制止惨案的发生。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福克斯新闻一定持强硬的支持态度,如果有谁敢提出质疑,他就会被说成不爱国。哪怕在其网站上转发一篇美联社消息,福克斯新闻都要做一番字词上的修改来取悦保守派,比如《选民对经济的担心给奥巴马带来新麻烦》这个标题被改成了《奥巴马跟白人妇女有大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知识分子一定不喜欢福克斯新闻。的确没有哪个大学教授宣称自己爱看这个台。就连我当初物理系毕业典礼,系里请来的演讲嘉宾都说物理学有什么用呢?至少能让你学会判断福克斯新闻说的都是什么玩应儿。可是如果你认为福克斯新闻这么做是为了宣传某种意识形态,你就错了。他们的目的是赚钱。
比如修改新闻标题这件事,其实从技术角度说并不是网站编辑的选择,而是读者自己的选择。很多新闻网站,比如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使用一个叫做 multivariate testing(也叫A/B testing)的技术:在一篇文章刚贴出来的时候,读者打开网站首页看到的是随机显示的这篇文章的两个不同标题之一,网站会在五分钟内判断哪个标题获得的点击率更高,然后就统一使用这个标题。事实证明在读者的选择下胜出的标题都是耸人听闻型的。
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在美国于其他新闻台。因为CNN在北京奥运传递火炬期间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很多人认为CNN是个有政治色彩的媒体,其实CNN得算是相当中立的——这也是为什么它的收视率现在节节败退。据2012年《经济学人》的报道,倾向自由派的MSNBC现在收视排名第二,CNN只得第三,而这两个台的收视率加起来也比不上福克斯。乔布斯1996年接受《连线》采访,对这个现象有一个非常好的评价: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看着电视就会想,这里面一定有阴谋。电视台想把我们变傻。可是等你长大一点,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视台的业务就是人们想要什么它们就给什么。这个想法更令人沮丧。阴谋论还算乐观的!至少你还有个坏人可以打,我们还可以革命!而现实是电视台只不过给我们想要的东西。
美国人玩的这一套,中国也有人早就玩明白了。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有各种观点鲜明的文章和报道,它们或者骂得特别犀利,或者捧得特别动人,观众看得畅快淋漓,十分过瘾。但是这些文章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有?说过什么能够修正我们现有思想的新信息没有?它们只是在迎合和肯定人们已有的观念而已。因为它们的生产者知道他们不需要取悦所有人。他们只要能让自己的粉丝基本盘高兴就已经足够获利的了。他们是"肯定贩卖者"。政治辩论?其实是一种娱乐。
王小波写过一篇《花刺子模信使问题》,感慨中国人(主要是领导们)听不得坏消息,一旦学者敢提供坏消息就恨不得把他们像花刺子模的信使一样杀掉。我想引用乔布斯的话:王小波说的太乐观了。真正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所有国家的所有人都有花刺子模君王的毛病,而且他们的做法不是杀掉坏消息,而是只听"好"消息 -- 那些能印证我们观念的消息。
这个毛病叫做“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如果你已经开始相信一个什么东西了,那么你就会主动寻找能够增强这种相信的信息,乃至不顾事实。这样一旦我们有了某种偏见,我们就无法改变主意了。《信息食谱》说,Emory大学教授Drew Westen实验发现,对于那些已经支持强烈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学生来说,如果你给他们关于其支持的党的负面新闻,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会显示这些人大脑中负责逻辑推理的区域关闭了,而负责感情的区域却激活了!换句话说他会变得不讲理只讲情。因为他们感到受到了威胁。这个受威胁的感情会让你把相反的事实用来加强自己的错误信念。社会学家Brendan Nyhan甚至发现了一个"逆火效应":你给一个保守派人士看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的文章之后,他居然反而更相信减税可以带来经济增长。
在确认偏误的作用下,任何新证据都有可能被忽略,甚至被对立的双方都用来加强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枪击事件之后禁枪派和拥枪派都变得更加强硬。另一本书,Future Babble(《未来乱语》)讲了个更有意思的实验。实验者给每个受试学生发一套性格测试题让他们做,然后说根据每个人的答案给其各自分析出来了一份"性格概况",让学生评价这个概况描写的准不准。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这个说的就是自己。而事实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概况"都是完全一样的!人自动就愿意看到说的跟自己一样的地方,并忽略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有人以为只有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才会陷入确认偏误,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客观判断。事实并非如此。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思想越容易两极分化。
一个有意思的议题是变暖。过去十几年来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变暖的科学报道和专家评论,这些报道可以大致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变暖的罪魁祸首,如果不采取激烈手段限制生产,未来气候就会不堪设想;一派则认为气候变化是个复杂问题,现有的模型并不可靠,二氧化碳没那么可怕。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你根本就不会被这些争论所影响。而《信息食谱》告诉我们,对变暖的观点分歧大的人群,恰恰是那些对这方面有很多了解的人。调查显示越是文化程度高的共和党人,越不相信变暖是人为原因造成的;越是文化程度高的民主党人,则越相信这一点。
如果谁想看看这个争论严重到什么程度,可以去看《经济学人》近一篇报道的读者评论。这篇文章说尽管过去几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不顾气候学家警告而继续增加,可是地球平均温度却并没有升高,远低于科学模型的预测。文章下面的评论水平跟新浪网足球新闻的评论不可同日而语,敢在这说话的可能没有高中生。评论者们摆事实讲道理,列举各种论文链接和数据,然而其观点仍然鲜明地分成了两派。就连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够不够合理,都有巨大的争议。
观念的两极分化并不于政治,人们可以因为很多事情进入不同阵营,而且一旦选了边就会为自己阵营而战。你的手机是苹果的还是安卓的?这两个阵营的人不但互相鄙视,而且有时候能上升到认为对方是邪恶势力的程度。人们对品牌的忠诚似乎跟政治意识形态没什么区别。我们看苹果新产品发布会,再看看美国大选前两党的集会,会发现二者极为相似,全都伴随着狂热的粉丝关注和激动的专家评论。
也许因为手机已经买了或者政治态度已经表过了,人们为了付出的沉没成本而不得不死命拥护自己的派别,也许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也许是为了寻找一种归属感。但不管是什么,这种阵营划分肯定不是各人科学推理的结果。根据诺贝尔奖得主 Robert Aumann 1976年的论文“Agreeing to Disagre”,说如果是两个理性而真诚的真理追求者争论问题,争论的结果必然是二人达成一致。那么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认知科学家 Hugo Mercier 和 Dan Sperber 2011年的一篇论文,“Why do humans reason?”,甚至认为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本来就不是用来追求真理的,而是用来说服别人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都是律师思维,我们的大脑本来就是个争论设备。这也许是因为进化总是奖励那些能说服别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发现真理的人吧。
互联网很可能加剧了人们观念阵营的划分。在网上你连换台都不用,推荐引擎自动根据你的喜好提供信息。我相信气候学家对变暖的预测大大言过其实,我认为决不可以废除死刑,我使用苹果手机,我还要求豆浆必须是甜的豆腐脑必须是咸的——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从来不跟人开玩笑。如果微博上有人发出违背我理念的言论我怎么办?我果断取消对他的关注。我们完全有权这么做,难道有人上微博是为了找气生么?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接收符合自己观点的信息,甚至只跟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交流,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回音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人们的观念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有鉴于此,Johnson 号召我们改变对信息的消费方式。他提出的核心建议是Consume deliberately. Take in information over affirmation.
要主动刻意地消费,吸收有可能修正我们观念的新信息,而不是吸收对我们现有观念的肯定。
这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要做到这些,我们必须避免那些预设立场的说服式文章,尽可能地接触手资料,为此甚至要有直接阅读数据的能力。可是有多少人能自研读各项经济指标再判断房价是否过高呢?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房价是高是低只与一个因素有关:他是不是已经买了房。
我建议把上面那两句英文刻iPad上。不过我发现的一系列针对社交网络的研究显示,也许回音室效应并不存在。有人对Facebook的朋友关系研究发现人们并没有只跟与自己政见相同的人交朋友。我们在网上辩得不可开交,生活中仍然可以跟对方辩友"隔着一张桌子吃饭"。哪怕在网上,统计表明人们的关注集群也不是按照政治立场划分,而更多的是按照视野大小划分的。更进一步,我们也许过高估计了对方阵营的极端程度。有人通过调查统计美国两党的支持者,发现如果一个人对某个政治方向有强烈的偏好,那么他对对方阵营的政治偏好,往往会有更高的估计。可能绝大多数人根本没那么极端,可能互联网本身就是个极端的人抒发极端思想的地方。对Twitter的一个研究表明其上的言论跟传统的民意测验相比,在很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问题)上更加偏向自由派。一般人并没有像Twitter上的这帮人那样拥护奥巴马,或者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互联网不是一个调查民意的好地方。
但不论如何,确认偏误是个普遍存在的人类特性,而且有人正在利用这个特性牟利。错误观点一旦占了大多数,正确的做法就可能不会被执行。既然改变那些已有成见的人的观念如此困难,也许双方阵营真正值得做的只有争取中间派。2013年的Nature Climate Change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说,虽然不可能改变那些已经对变暖学说有强烈看法的人的观点,但是可以用身经历来影响那些对气候变化并没有什么成见的人,而这些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的75%。一个策略是可以告诉一个中间派,你爱去凿冰捕鱼的那个地方,现在每年的冰冻期比十九世纪少了好几个星期,来吸引其注意力。
这个真不错。当然在我这个坚定的变暖学说质疑派看来,那些看见自己家门口的池塘不结冰了就认为变暖的人纯属弱智。
用户评价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读完这本书的感受,那大概是“豁然开朗”。它没有贩卖焦虑,反而是提供了一套应对焦虑的工具箱。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最稀缺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筛选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本书就集中火力攻克了这一点。它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去剖析那些充满温情脉脉的社会现象,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提供一个更清晰的观察视角,让我们能够跳出情绪的漩涡,看到事情更本质的运行轨迹。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对年轻人的价值尤为突出,它能帮助他们尽早建立起一套稳固的认知框架,避免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太多基于情感冲动的选择。那种对真理的尊重和对清晰逻辑的追求,是这本书留给我最深刻的烙印。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给我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感,那种深邃的蓝色调和充满几何感的排版,一下子就把我拉进了一个思考的迷宫。我记得当时是在书店里随意翻阅,目光就被它牢牢锁住,仿佛它有一种魔力,能穿透那些花里胡哨的营销辞藻,直击核心——理性的光芒。我当时想,这绝不是一本泛泛而谈的鸡汤读物,它一定蕴含着某种底层逻辑的构建方式,一种能让人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迅速抓住本质的“钥匙”。那些关于如何用结构化的思维去拆解日常现象的描述,读起来就让人热血沸腾,好像突然间,那些困扰已久的问题都有了新的观察角度。它不只是在讲述知识,更像是在教授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论,一种能让你的思考变得更清晰、更有力量的底层操作系统。这种感觉,就像你一直用模糊的滤镜看世界,突然有人递给你一副高清眼镜,所有细节瞬间锐利起来。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布局非常巧妙,仿佛是精心设计的一座迷宫,每走一步,都有新的发现,但每一步又都遵循着清晰的地图指引,让你既不迷失方向,又能体验探索的刺激。我特别喜欢它在不同章节之间建立起来的隐形联系,你会发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理学概念,竟然能和商业策略产生奇妙的共振。这种跨学科的融会贯通,体现了作者深厚的知识储备和高超的整合能力。我个人认为,衡量一本好书的标准之一,就是它能否让你在合上书本后,依然能持续地进行思考,并且能将书中的方法论灵活迁移到生活的其他领域。这本书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它不是那种读完就束之高阁的“背景知识”,而是像一把瑞士军刀,随时准备为你解决生活中的“疑难杂症”。
评分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那种“感觉派”的决策者,凭直觉行事,虽然偶尔也能蒙对,但长期来看总是在重复犯错。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他们后,有一个朋友反馈说,读完后感觉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但却是那种清醒的冷水。他提到,以前很多事情他都是从“我觉得”出发,现在开始习惯性地问“有没有数据支持?”、“这个结论的边界在哪里?” 这说明这本书的价值已经超越了纸面,开始真正改变人们的思维习惯。它不仅仅是理论的普及,更是一种思维习惯的重塑工程。我特别欣赏作者那种勇于挑战传统认知的态度,他不只是罗列事实,更是在引导读者去质疑那些约定俗成的“常识”,去探究事物背后的逻辑链条,这对于一个渴望独立思考的人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巨大滋养。
评分说实话,我拿到这本书后,第一个晚上就熬夜读完了将近一半,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很久没有在阅读中体会到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不屑于那些故作高深的术语堆砌,而是用极其生活化、甚至略带幽默感的案例,来阐释那些看似高不可攀的科学原理。比如,它分析某个社会现象时,会巧妙地引用概率论或者博弈论的观点,但绝不生硬,反而让人觉得“原来如此,我怎么没想到!” 这种“啊哈!”的瞬间,是阅读体验中最大的乐趣所在。我感觉自己仿佛在跟随一位极其聪明的朋友,他一边陪你闲聊家常,一边不动声色地帮你升级大脑的运算速度。这本书的行文节奏把握得极好,有张有弛,让你在享受思维乐趣的同时,又不会感到过度疲劳,简直是认知升级的绝佳伴侣。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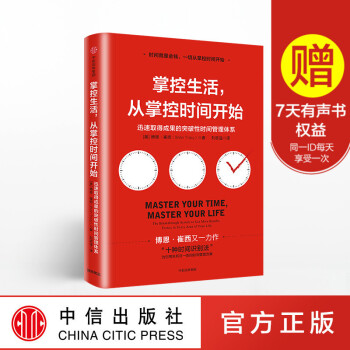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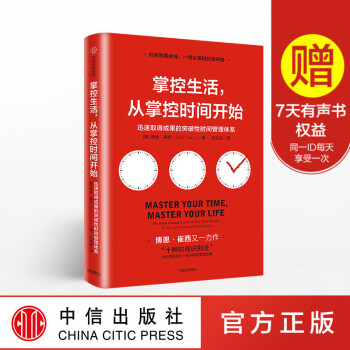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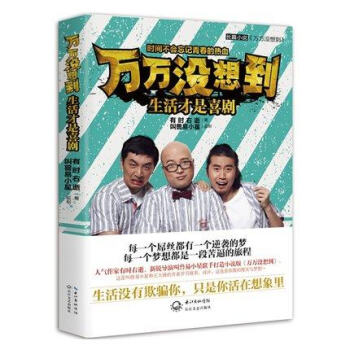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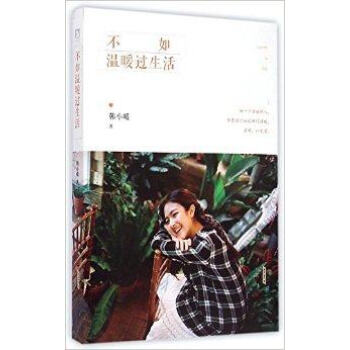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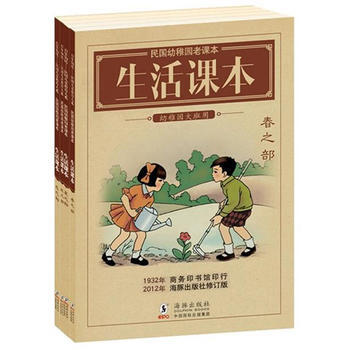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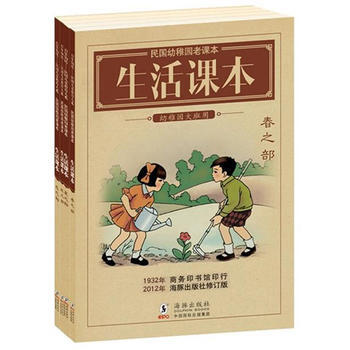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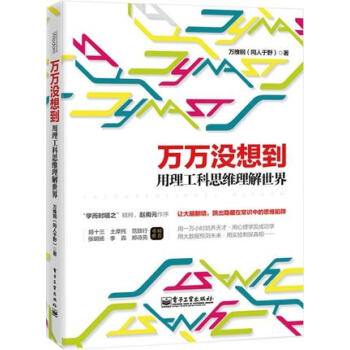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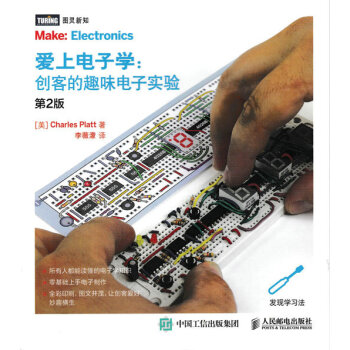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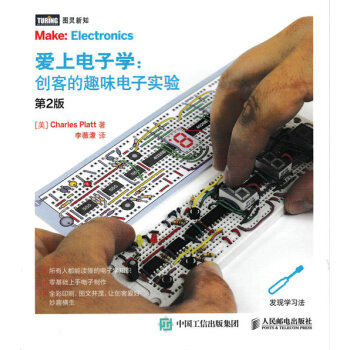
![FR [北京发货] 行政办公管理工具大全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30270022821/5ab5449cN00826e2b.jpg)
![FR [北京发货] 行政办公管理工具大全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30270024794/5ab5449cN00826e2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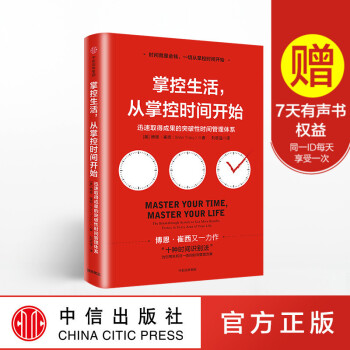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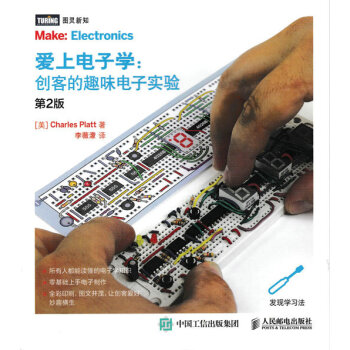
![FR [北京发货] 行政办公管理工具大全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30270560210/5ab5449cN00826e2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