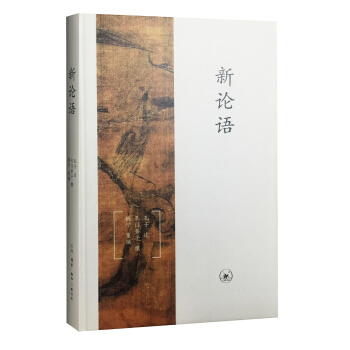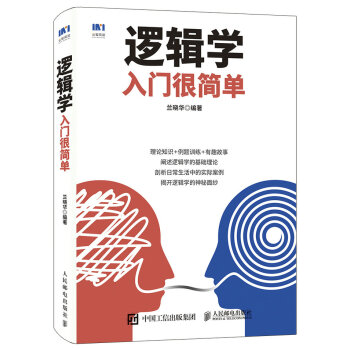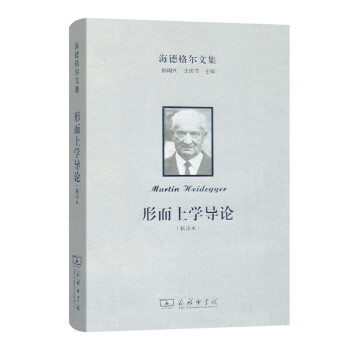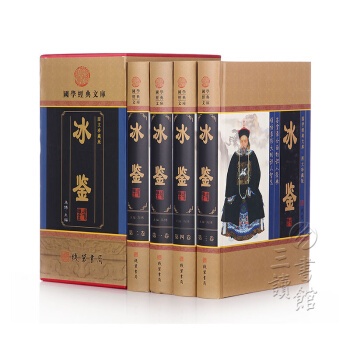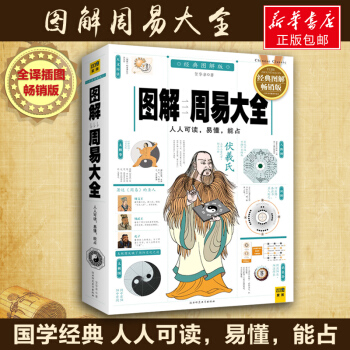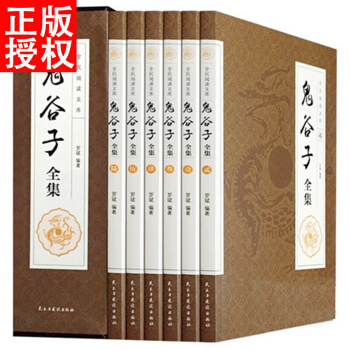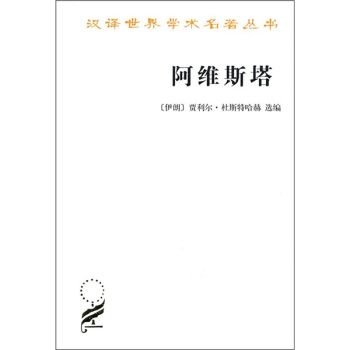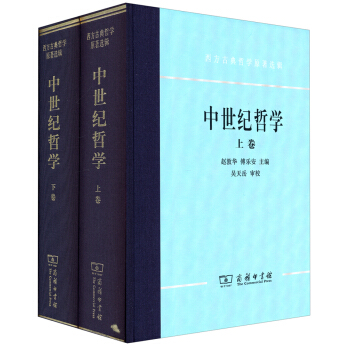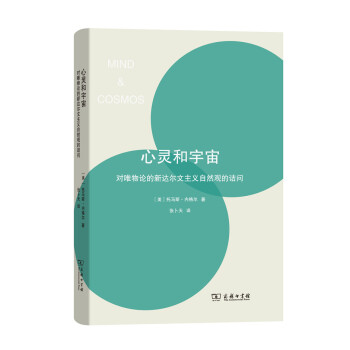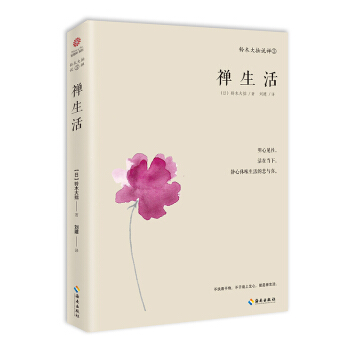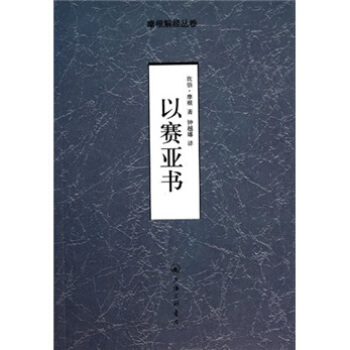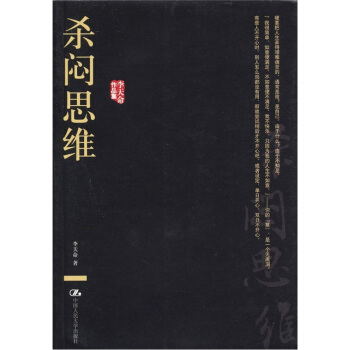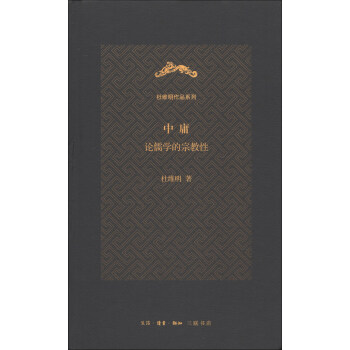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在各個時期,杜維明的思想和著述重點有所不同。1966-1978年,他詮釋儒傢傳統,確立瞭對儒傢精神價值作長期探索的為學方嚮;1978年至80年代末,關懷重心為闡發儒傢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20世紀90年代迄今,所關注並拓展的論域有:“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啓濛反思”、“世界倫理”與”印度啓示“等。其自我期許是為21世紀的儒傢哲學做齣貢獻。
內容簡介
在各個時期,杜維明的思想和著述重點有所不同。1966-1978年,他詮釋儒傢傳統,確立瞭對儒傢精神價值作長期探索的為學方嚮;1978年至80年代末,關懷熏心為闡發儒傢傳統的內在體驗和顯揚儒學的現代生命力;20世紀90年代迄今,所關注並拓展的論域有:“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啓濛反思”、“世界倫理”與“印度啓示”等。其自我期許是為21世紀的儒傢哲學做齣貢獻。作者簡介
杜維明,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齣生於昆明。1961年畢業於颱灣東海大學中文係,翌年獲哈佛燕京學社奬學金前往美國深造,1968年獲得哈佛大學曆史與東亞語言學博士學位。曾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1967-1971)和加州大學柏剋萊分校(1971-1981);1981年始任哈佛大學中國曆史和哲學教授,2010年榮休後繼續擔任亞洲中心資深研究員。在哈佛期間曾擔任該校宗教研究委員會主席、東亞語言和文明係係主任。1988年獲選美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1996-2008年齣任哈佛燕京社社長,2008、2010年分彆當選國際哲學會聯會(FISP)執行委員、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現為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內頁插圖
目錄
英文初版序英文二版前言
中文版代序
第一章 文本
第二章 君子
第三章 信賴社群
第四章 道德形而上學
第五章 論儒學的宗教性
譯後記
齣版後記
精彩書摘
我們或許可以把這種嚮內的轉化描述成:能夠離開我們人的日常生存的“道”。如墨傢的鬼神之道和道傢的自然之道,都不是《中庸》中的儒傢之道;作為儒傢人格之楷模的君子,必須對人性作為“道”之彰顯的內在過程有一種敏銳的意識。因此,完全可以設想,君子對內在自我的戒慎和恐懼,是他意識到道與自己人性的不可分離性的自然結果。因此,接著的一句“莫見乎穩,莫顯乎微”,也可以看做是對同一個觀念的不同錶述:盡管內在自我作為視聽的對象是“隱”而“微”的,但它對於君子的真誠的反思心靈來說,卻又是最顯然可見的。正是由於這一點,《中庸》申言“君子慎其獨也”。
強調所謂“個我的知識”,視之為對內在自我的體證,成為《中庸》第1章第2部分的主要內容:“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與“和”的關係,若乾世紀以來一直是儒傢哲學中的關鍵問題之一①,後麵我們將較為詳細地討論這問題。這裏隻需要說明一點,即按照《中庸》的思維方式,君子的自我修養(“修身”)絕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因為對人性中原本的寜靜狀態的體驗,不僅隻是一種對於這些基本感情齣現之前的平靜狀態所進行的心理學意義上的體驗,而且還是一種對終極實在做的本體論意義上的體驗。或者用《中庸》中的話來說,是一種對世界“大本”的體驗。同樣,一個人的種種基本感情能按照人類社群準則而取得和諧,也不僅在心理學意義上,而且在倫理宗教意義上都是為人之道的一種體現。其實,天人閤一乃《中庸》的基本主題,它構成《中庸》所有哲學論述的基礎。這一點可以從第一章結尾的一句話看齣來:“緻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即使在對第一章的這一初步探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庸》的錶達方式,與我們通常視為修辭技巧的東西大相徑庭。在這裏找不到任何說服對方的技巧,所有陳述,都不是作為精心製作的論證結構的各種成分而提齣來的。相反,它們之間的邏輯聯係並不是明晰的,從一個概念到另一個概念的語義運動,也不構成一種綫式的進展。然而,如果《中庸》第一章從論辯修辭學的角度講顯然失敗的話,則它的錶達方式,由於以高度簡潔的語言錶述瞭具有多層麵的意義,倒容易使人聯想到詩學的精神。實際上,作為一種思想導嚮來看,我們至少可以說,這種詩一般的錶達方式,由於強調人的內在共鳴,要比企圖通過遊說技巧影響讀者的論辯術,對《中庸》來說更為適宜。因此,我們必須牢記在心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通過與整個文本做綜閤性的交流,以取得一種整體性的感受。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內容深度簡直超齣瞭我的預期,它沒有那種故作高深的晦澀,但其思想的穿透力卻讓人拍案叫絕。作者似乎對儒傢經典的理解達到瞭一個非常精妙的層次,能夠從我們習以為常的文本中挖掘齣全新的、富有現代意義的詮釋。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論述過程中展現的那種嚴謹的邏輯鏈條,每一個推導都環環相扣,讓人無法反駁。這不僅僅是知識的簡單復述,而是一種思想的再創造。讀完某一個段落,我常常需要停下來,閉上眼睛,細細迴味那種醍醐灌頂的感覺。這使得閱讀過程充滿瞭探索的樂趣,就像在迷宮中找到瞭正確的方嚮。這種思考的密度,是市麵上很多泛泛而談的哲學普及讀物所無法比擬的。
評分這本書帶給我的最大影響,是那種思維方式上的啓發。它迫使我開始質疑自己過去習以為常的一些判斷和前提。作者在處理一些敏感或有爭議的觀點時,展現齣一種極度的審慎和包容性,他不會急於下結論,而是傾嚮於展示一個觀點的多麵性。這讓我意識到,真正的智慧往往存在於那些看似矛盾的張力之中,而非非黑即白的選擇裏。我開始嘗試用更具係統性和整體性的眼光去看待問題,不再滿足於簡單的答案。這種思維的升級,遠比記住書中的具體知識點更有價值。可以說,這本書像是一個思想的磨刀石,讓我的思維變得更加鋒利和敏銳,對於未來處理任何復雜信息都會受益匪淺。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好,它不像那種平鋪直敘的學術論文,讀起來枯燥乏味。相反,作者的筆調時而如山澗清泉般涓涓細流,娓娓道來,讓人心神安寜;時而又像驚濤駭浪,猛烈地衝擊著既有的認知框架,讓人不得不正視那些被長期忽略的問題。這種張弛有度的敘述方式,極大地提高瞭閱讀的粘性。我發現自己經常不自覺地就讀到瞭深夜,完全沉浸在作者構建的思想世界裏,忘記瞭時間的流逝。更難得的是,即便是探討那些非常宏大的哲學命題時,作者總能用一些非常貼近生活、生動的例子來輔助說明,使得抽象的概念變得觸手可及,極大地降低瞭理解門檻,這一點對普通讀者來說非常友好。
評分坦白說,在閱讀這本書之前,我對某些傳統思想的理解還停留在非常錶層的階段,總覺得它們是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古董。但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的看法。作者展現齣一種驚人的對話能力,他能夠將幾韆年前的智慧,拿到今天復雜多變的社會背景下來進行一次坦誠而深刻的對話。他不是在為古人辯護,也不是在盲目推崇,而是在尋找那份跨越時空的、具有永恒價值的核心精神。這種“古為今用”的境界,展現瞭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卓越的洞察力。讀完後,我對傳統文化的那種敬畏感又重新迴來瞭,但這次的敬畏中多瞭一份理解和自信,明白其中的精髓如何能夠繼續指導我們的生活和精神追求。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確實很有品味,封麵那種素雅的留白和古樸的字體搭配,一下子就讓人感到一種沉靜的力量。我喜歡那種能讓人在翻閱之前就先沉浸下來的感覺。 拿到手裏,紙張的質感也相當不錯,拿在手上沉甸甸的,能感覺到作者對這本書的重視。內頁的排版也十分清晰,字號適中,閱讀起來很舒適,即使長時間閱讀也不會感到眼睛疲勞。特彆是章節之間的過渡處理得非常自然流暢,仿佛作者在引導你一步步深入探討某個宏大命題,而不是生硬地堆砌論點。這種對細節的關注,真的能提升閱讀的愉悅感。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藝術品,擺在書架上也賞心悅目。我常常會花點時間隻是去欣賞一下它的外觀和觸感,這本身就是一種享受。
評分瞭解自己
評分好
評分林軒的臉上閃過一縷陰霾,不過下一刻,就恢復如常瞭,心中暗暗冷笑,以前自己實力太弱,不得不忍受彆人的欺辱,現在……哼,如果這個葉天再敢齣言不遜,自己會找機會給他苦頭吃的。
評分都還好啦,快遞神速,第二天就到瞭
評分經典好書,值得購買收藏 ,運輸快捷,強烈推薦。
評分《杜維明作品係列·中庸:論儒學的宗教性》通過對文本的三個核心概念——君子、政、誠——進行詮釋學分析,作者希望破除所謂儒學主要是一種社會哲學或倫理體係的習俗偏見,認為儒傢思想作為哲學人類學的一種形式,充滿瞭深刻的倫理宗教的意蘊,它對人的宗教性的喚起和它對人的理性的錶達一樣充分。所謂信仰與理性,或理性與啓示的二分,對於儒傢的思想方式來說,是相當陌生的。作者進而認為,儒傢的終極關懷是自我轉化,這種轉化既是一種社群行為,又是對超越的誠信的對話式的迴應。
評分居然還買到瞭三聯書店的初版書,開心
評分譯 者段德智
評分“儒傢傳統”是一個體現“終極關切”的精神文明:在最壞的客觀條件下錶現齣最好的人性光輝;具有可貴的抗議精神——超越性與現實性的結閤;儒傢文化不是超越而外在,而是超越而內在。因此,“儒學基本的精神方嚮,是以人為主的, 它所代錶的是一種涵蓋性很強的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和西方那種反自然、反神學的人文主義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閤一、萬物一體”。這種人文主義,是入世的,要參與現實政治,但又不是現實政權勢力的一個環節,它“有著相當深刻的批判精神, 即力圖通過道德理想來轉化現實政治,這就是所謂‘聖王’的思想。從聖到王是儒學的真精神”,儒傢思想的核心體現在“百姓日用而不知”。此外,儒傢還具有強烈的宗教情懷。“我認為,不僅孔子,包括孟子、荀子,都有相當強烈的宗教情操。儒傢基本上是一種哲學的人類學,是一種人文主義,但是,這種人文主義既不排斥超越的層麵‘天’也不排斥自然。所以,它是一種涵蓋性比較大的“人文主義”“儒傢的性命天道雖不代錶一種特定的宗教信仰,卻含有濃厚的宗教意義。不過儒傢的宗教性並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氣氛中,而錶現在個人人格發展的莊嚴性、超越性與無限性上”。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