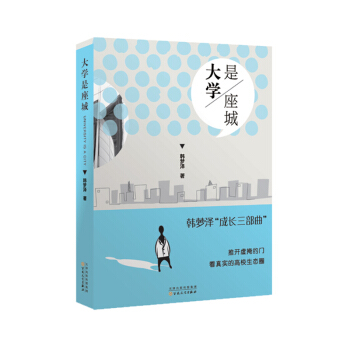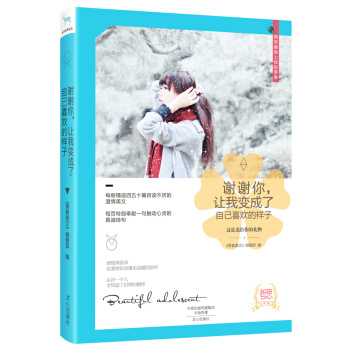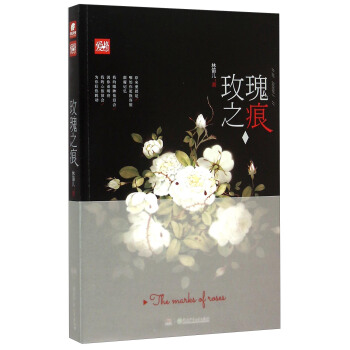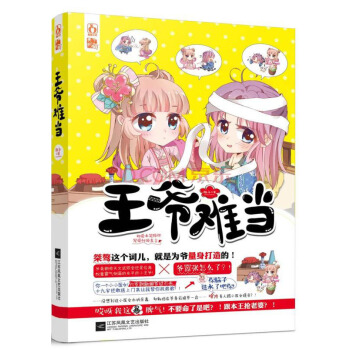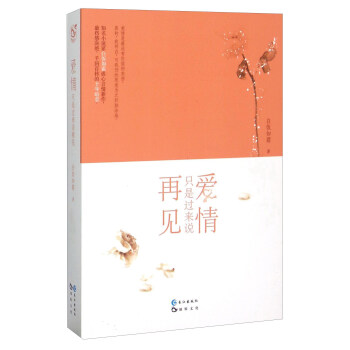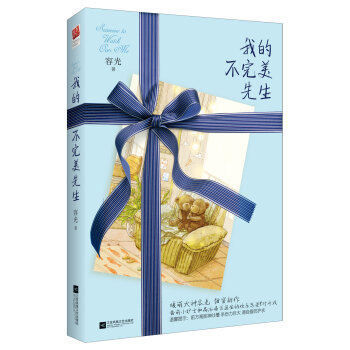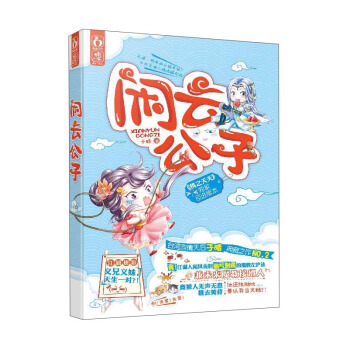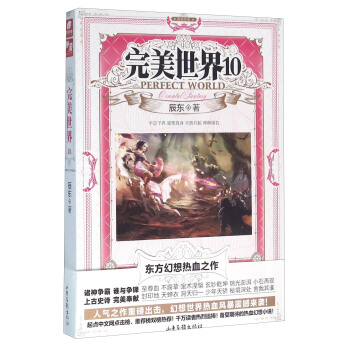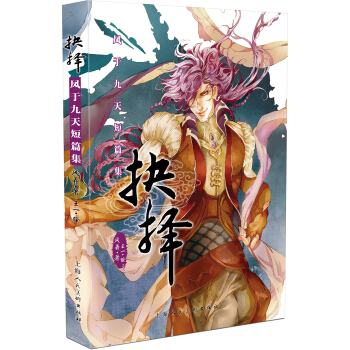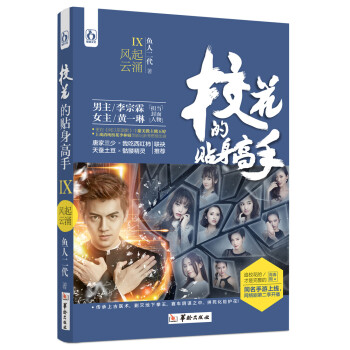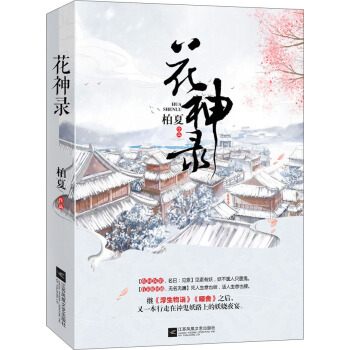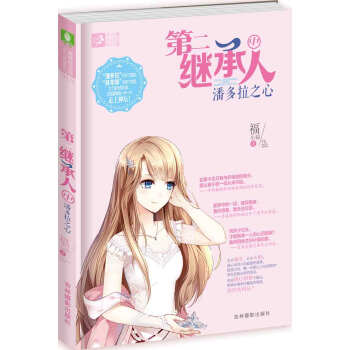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藤井树的小说,凄楚而又唯美,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套系列书描写虽是青年学生的故事,但其中不仅涉及爱情、友情,更涉及了人生况味。建立在现实人生理解的基础上,所描写的爱情友情真实感人,反映出的人生感触耐人寻味。作者简介
藤井树,台湾时尚文学的首席代表人物,畅销天王。《我们不结婚,好吗》让他一炮走红,随后,《猫空爱情故事》等长时间占据台湾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的纯情小说。内页插图
精彩书摘
001.十九号的月亮她站了起来,快要下山的夕阳像是站在海上舍不得离开一样,那橙色的光把她的脸照得好亮、好亮。
“那如果..我这辈子都不想离开高雄,你会不会留下来?”
她说。
夕阳橙光从她的发隙中穿过,刺痛我的眼睛。
075.渴爱
曾听说过,每个女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女孩,原本对这句话并没有太多感觉,却在年纪愈来愈大之后发现,我心里好像也有个小女孩,而她好像真的长不大。可爱的是她,渴爱的是我。
121.情签
从今天起,我再不会在博客里,为你写下我的感情了。
这些日子,我对你的感情虽然让我感觉到深深的寂寞,却也很高兴自己有过这一段。
至少我现在能诚实地面对自己,并且写下来,不让这份爱留白。
179.痕迹
失败的恋情会让自己很快地长大。
我体会了什么是失败的恋情,也知道什么是很快地长大。
只是,这滋味不好受,而且很伤..
目录
Contents
十九号的月亮
「当年你可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
「多喜欢?」
「喜欢到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念同一所大学,然后一起毕业,一起去工作,
.如果可以,我希望就这样不要变了。」她说。
「不要……变了?」
「对呀,我希望就这样不要变了。」
01
台北车站的设计真的会让人迷路。
四方形的建筑,四个方向都还各有三个一模一样的门,要不是我在台北待过一段时间,我还真不知道到底哪一边是哪一边。
在高雄搭上捷运往左营的途中,我看见车厢里有一对母子,妈妈正专心地看着报纸,而那看起来大概五岁的孩子则坐在妈妈身边,一边吃巧克力棒一边睁大眼睛瞪着我。
“小朋友,捷运上不能吃东西的,你知道吗?”我微笑着说。
他的妈妈一听见,视线立刻离开报纸,她先看了我一眼,然后赶紧把小孩手上的巧克力棒拿走,“我刚刚有没有说出捷运站才能吃?有没有?有没有?”她很凶地骂着那个孩子。
而那个孩子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妈妈,他的表情似乎在说着:“你根本就没讲……”
那个妈妈一直向我点头说抱歉,说她孩子不听话。
我笑着点点头,又看了那个孩子一眼,他竟然对我吐舌头。
“你真是没礼貌!快说叔叔对不起!我以后不敢在捷运上吃东西了。快说。”他的母亲拉着他的手说。
“叔叔对不起……”
那孩子话才刚出口我就插嘴了,“没关系,别说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噢,是捷运的规定噢,下次记得就好。”我说。
然后那个妈妈转头拾起报纸继续看着,那孩子又对我吐了个舌头。
但这次我的注意力不在孩子身上了,而是在那个妈妈身上。
那个妈妈的眼睛跟眉毛,跟月玫有相当神似的地方。
如果不是打扮,身高跟身材,还有那凶巴巴的个性差很多,若光是看见那双眼睛,我可能真的会认错人。
“如果我跟月玫早个几年……那孩子应该也这么大了。”
我心里这么想着。
高铁真的拉近了台湾南北的距离。
只要九十六分钟,就能从高雄到台北,而且安全安静又舒适,高铁上的服务小姐还都长得很漂亮,每个都很有气质。
刚走出台北车站就感觉到寒风刺骨,我从背包里把更厚重的外套拿出来穿上,抬头看着大楼顶部的显示器,它写着:“11℃”。
每一道寒流来袭的时候,台北总是又湿又冷。
像是挡在最前线的第一道门,寒流一到,台北马上就变成狼狈的落汤鸡。
所谓的大陆冷气团,所谓的东北季风,其实都只是气象学里面的专有名词而已,那对生活在一座爱下雨的都市里的人们来说,就是烂天气。
就是烂天气,没别的名字了。
台北啊,烂天气、烂交通,真是一座讨人厌的城市,却有六百万人住在这里。到处阴雨蒙蒙,十天里有八天天空都是灰色的。那细得会随风飘忽不定的雨下得跟雾一样的轻,那冷得会让人猛打哆嗦寒战的气温,还有那车塞得会令人情绪大坏的每一条马路。
而月玫就住在这里。
其实我在台北短暂地待过两年半的时间,在货运物流公司当最基层的送货员,那是大学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
两年半的时间对我来说一点都不短暂,但对佑哥来说却很短。
所以“短暂地待过两年半”这句话是他说的,我一点都不这么认为。
“你知道我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他拍着胸膛一脸骄傲地说。
“我知道,是公司大老板的特助。”我说。
“那你知道我几岁开始做那份工作吗?”
“我知道,十六岁。”
“那你知道那份工作我做了多久吗?”
“我知道,你做了九年。”
“整整九年的时间我才真的把特助这份工作学到透彻你知道吗?”
“知道。”
“所以每一份工作都有非常专业的部分,这是需要时间去慢慢体会与了解的,知道吗?”
“知道。”
“所以你在送货界才短短的时间,这一点都不长,明白吗?”
“是,我明白。”
佑哥是我的“帕呢”,这两个字是他说的,来,跟我念一遍,“帕呢”。
帕呢其实就是partner,伙伴的意思,不过佑哥很显然完全不知道,因为他说帕呢就是兄弟的意思,就是感情很好的两个人,这样。
我尝试过跟他解释帕呢是伙伴,不是兄弟。
但是他说伙伴当久了就是兄弟了,一边说还一边挑眉,我听完觉得怪怪的,但好像又没办法反驳什么。
佑哥似乎总有他的一套道理,又或者该说是歪理。
他结婚好多年了,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不过他太太嫌他脑筋不好又赚钱慢,两个人协议离婚,女儿一人一个。三岁的跟妈妈,五岁的跟佑哥。
他讲话带点严重的台湾喑,对英文有很大的兴趣,但是又学不好。
他有一天问我:“哇铐是一句英文对不对?”
我说不是啊,就是一句很口语化的小脏话。他听了有点吃惊:“那是脏话?”我歪着头想了一下,“呃……也不是很脏啦。”我说。
“小脏?”
“比小脏再小一点吧……”
“小小脏?”
“这……它有多脏很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女儿前一阵子问我什么是哇铐,我说是一句英文,说别人很厉害的意思。”
“……这……”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结果昨天她的安亲班老师送她回来的时候跟我说她最近整天都在哇铐哇铐,要我注意一下她的言行。”
“……那你应该快点跟她说你讲错了。”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耶,哈哈哈哈,”他大笑了起来,“昨天晚上我泡面给她吃,她说她们安亲班有一个同学唱歌很哇铐,哈哈哈哈!”
都四十岁的人了,大笑起来像个孩子。
我们常一起送货,就连住的地方都只是隔壁巷子,他虚长了我几岁但总是以一副老大哥的样子在教我做人处事的道理,于是每当 我跟他说:“佑哥,我觉得我应该要换工作了,一直送货好像没什么前途。”
然后他就会说:“你知道我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吗?”
然后我就会回答:“我知道,是公司大老板的特助。”
然后他又会说:“那你知道我几岁开始做那份工作吗?”
然后我就会回答:“我知道,十六岁。”
接下来的对话就不需要再重复了。
只是我曾经问过他,那位大老板到底是什么样的大老板?竟然让一个国中刚毕业的毛头小朋友去当他的特助。
他说:“我家那个村子里最有钱的一个大老板,是开印刷厂帮人家印东西的。”
“噢?听起来好厉害!”我说。
“那当然!”他很骄傲地扬起下巴。
“那印刷厂里一共几个人?”
“就我跟大老板两个人。”
“……果然是特助……”
“那当然!”他继续嚣张着。
在台北那两年半的时间里,我试着喜欢这座城市,但屡试不爽,是真的不爽,越试越失败。
明明就三不五时在下雨,结果三不五时在限水,说水不够用。
明明就是台北,路应该很平,结果路又够烂而且三不五时在挖马路。
一样都是同一个品牌的手摇饮料店,开在台北就要比别县市贵十块。
一样都是百货公司停车位,在台北停一小时最贵要一百六十块(半小时八十元)。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一百六十块。
其他县市一百六十块可以停多久?停到你忘记车子停在哪里那么久。
当然我这么说是夸张了点,但也点出了某些不合理的地方,对吧?
但佑哥说我这样叫作自己找自己麻烦。
“你这样只会让自己活在痛苦中。”他说。
“我没有很痛苦啊,我只是觉得这种状况不合理而已。”我说。
“你这就叫标准的愤世嫉俗。”
“我这样就愤世嫉俗?有那么严重吗?”
“愤世嫉俗的人都会活得很痛苦,你必须学会佛祖说的“放下,目空一切”,人遇上任何事情都要心平气和地面对,不管它有多么让你不高兴或是难过。”他说。
这时有个机车骑士在车缝中穿梭,经过我们的货车时他的安全帽撞歪了我们的后照镜。
“干你妈的会不会骑车啊!给我回来说对不起!”他指着那个已经扬长而去的骑士说。
……
在台北那段时间,其实心里有另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能遇到月玫。
不过月玫没有遇到,却遇到了月如,而且还三次。
月如跟月玫都是我的高中同学,不过我跟她们不同班。
请别因为她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就误会她们是姐妹,其实她们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第一次遇见她是在我公司楼下的全家便利商店,我认出她,却没叫住她,因为她一脸浓妆,比起以前瘦了、漂亮了许多,我担心会认错人。
第二次还是在同一家便利商店,她认出我,我傻笑,她说我变了很多,我又傻笑,然后她说她赶时间,转头就往便利商店门口跑去,她的道别被自动门的铃声淹没。
第三次依然在同一家便利商店,这时我才突然想问她:“为什么我总是在这里遇到你?”
“因为我公司在对面啊!”她说,指着马路那边的大楼。
“咦?这么近?我公司在楼上耶!”我指着天花板说。
“你公司是干吗的?”
“物流啊,我是送货的。你呢?”
“律师事务所。”
“你是律师?”我吃惊地问着。
“我只是总机。”她说。
我本来很想再问她为什么总机要浓妆艳抹,但是问到一半话哽在喉头,心里念头一转,“……那……你有跟月玫联络吗?”我说。
“大学的时候还有,到了大四就变少了,毕业之后几乎就断了联络,如果不是在路上碰巧遇见她,我可能真的就跟她断了联系了。”月如说。
“你遇见她了?她好吗?”我兴奋地说。
“她很好啊!气色好,而且变得好漂亮噢!”
“所以,你有她的电话号码?”
“有啊!你要吗?”
“我……可以要吗?”
“我问问她愿不愿意给你,然后再跟你说,好吗?”月如说。
“好,”我点点头,“你把我电话记一下吧,0936……”我说。
记得高中的时候,第一次跟月玫一起翘了放学后的辅导课,两个人骑着脚踏车到西子湾看夕阳。
当时她问我说:“哎!你会不会想离开高雄啊?”
我连想都没想就回答:“想!超想!非常想!如果可以,我明天就想离开……噢不!今晚……噢不!现在!”
看,都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当时我是怎么回答她的。
可见我有多想离开高雄,可见我有多不喜欢高雄,可见我们家附近那条臭到会让人得忧郁症的前镇大水沟到底有多臭,可见那些打开家里窗户就能看见的工业区大烟囱到底让我们吸了多少废气。
“为什么这么不喜欢高雄?”她接着问。
“就是不喜欢,而且我觉得一定要到外面去看看!”我说。
“是……吗?”
“是啊!”我说。
“那你想去哪里?”
“台北!我想去台北!那边一定很好玩!不然花莲也可以,风景一定很漂亮!”
“是……吗?”
“是啊!其他地方一定都比高雄好!不管去哪里都好,只要离开高雄!”我说。
然后月玫站了起来,快要下山的夕阳像站在海上舍不得离开一样,那橙色的光把她的脸照得好亮,好亮。
“那如果……我这辈子都不想离开高雄,你会不会留下来?”
她说。
夕阳橙光从她的发隙中穿过,刺痛我的眼睛。
“不会……吧。”我突然觉得心有点痛,像是要失去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一样,“我也不知道……”我真糟糕,被她这么一问,想离开高雄的念头就不那么坚定了。
“噢……”她点点头,转过身去侧面对着海。
“那………你,跟我……一起走,好不好?”我问。
“你以为离开高雄就像我们现在逃学一样吗?说走就走?”
“有什么不行?”我自以为这样回答很帅。
她回头看着我,因为背光,我看不清她的脸。
“你们男生,真的很幼稚。”
“最好是……”
“当然是!”你伸出手指碰着我的额头,“尤其是你!”你说。
“我很成熟了!”
“你超级幼稚!”
“你才幼稚又三八!”
“你幼稚低级又无聊!”
……
月玫啊,你知道吗?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天西子湾海风咸咸的味道;你被汗水给湿透的白色制服里透出的内衣颜色;旁边烤香肠小贩子的叫卖声;那些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引擎声;那颗很快就沉到海里看不见的太阳;因为那天逃学回家后被爸爸发现挨揍的巴掌声;你脸上那一点一点我说很可爱的小雀斑;还有我们不停地在斗嘴的幼稚。
还有我说我很成熟的但你幼稚又三八的……
十七岁。
那年。
夏天。
幼稚,低级,又无聊的那年,我们最快乐。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开篇就以一种近乎催眠的笔触,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时间仿佛停滞的夏日午后。那种光影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潮湿泥土与青草混合的气味,细腻得让人几乎能感觉到皮肤上的微风。作者对于环境的描摹,绝非简单的背景交代,而是将场景本身塑造成了一个有生命的,会呼吸的角色。主角的心绪波动,似乎总是与窗外的天气、树叶的颤动紧密相连,读起来让人不禁放慢了自己的呼吸节奏,仿佛生怕惊扰了这片刻的宁静。故事的推进非常缓慢,但这种慢不是拖沓,而是一种雕琢,每一个词语的选择都像是经过了精心的打磨,带着一种老电影胶片特有的暖黄色调和颗粒感。它探讨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情感冲突,而是那些潜藏在日常对话和眼神交汇下的、难以言喻的“懂得”。特别是其中关于“等待”的描写,那种明明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的心理距离,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读完后心里会留下一个长长的,带着惆怅的尾音。如果你期待的是快节奏的叙事或者强烈的戏剧性反转,这本书可能不适合你;但如果你喜欢沉浸式地体验一种情绪的氛围,享受文字如同音乐般流淌的韵律感,那么这本书绝对能提供一次久违的心灵漫游。
评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非常巧妙,它采用了多线叙事,但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这些线索并不是为了制造复杂的谜团,而是像几条平行的溪流,各自流淌,偶尔在某一个相似的意象或对白处产生共鸣,然后又各自散开。这种结构带来的阅读体验是碎片化的,却又在合上书本的那一刻,所有的碎片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重新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图案。我特别喜欢作者在不同章节间切换视角时的那种冷静和克制,他从不强迫读者去同情某一方,而是将叙事的焦点放在“事件本身如何被不同的人感知”这一母题上。这让读者获得了极大的思考空间,我们既是局外人,又是潜在的参与者,不断地在不同角色的立场间摇摆、权衡。这种多维度的审视,使得故事的深度远超于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范畴,它开始触及到记忆、时间流逝以及个体经验的不可复制性。读完后,脑海中回荡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对“视角”本身的敬畏。
评分从主题层面来看,这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探讨的“真情”并非是那种至死不渝的绝对承诺,而是一种更接近于“理解的宿命”的哲学命题。它暗示了,有些人,无论经历多少岔路口,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被彼此的生命轨迹所吸引、触碰,这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种宇宙间能量的必然汇合。书中对于“错过”的描绘尤其令人心痛,那不是因为双方不爱,而是因为在特定的时间点,他们缺乏了对方所需的那个“密钥”来开启下一扇门。随着故事的推进,读者会意识到,很多时候,遗憾不是源于外部的阻挠,而是源于个体成长的时间差。这本书仿佛在温柔地提醒我们:生命中的某些美好,注定只能停留在“可能性”的阶段,但这种可能性本身,就已然构成了永恒的一部分。读罢,心中涌起的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对人生复杂性的释然与接纳。
评分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简直是诗歌与散文的完美结合体。它的句式长短错落有致,时而是那种古典小说中才有的,严谨工整的排比结构,充满了文学的厚重感;时而又突然切换为极其口语化、甚至有些破碎的短句,像是角色在极度情绪激动时脱口而出的真言。这种节奏上的巨大反差,极大地增强了文字的表现力。它没有使用任何浮夸的形容词来标榜自己的“深刻”,所有的力量都蕴含在动词和名词的精准选择中。例如,描述一次告别,它不会说“他心碎了”,而是描绘“他将车钥匙放在桌上的动作,带着一种仿佛在告别一件易碎古董的慎重”,这种将抽象情感具象化的能力,令人赞叹。全书读下来,像是在欣赏一件雕刻精美的工艺品,每一个转折,每一处留白,似乎都经过了深思熟虑,目的是为了引导读者进入一种近乎冥想的状态,去感受语言本身作为载体的力量。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在人物刻画上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尤其是在处理“非语言沟通”方面。很多时候,角色们并没有用大段的独白来宣泄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一些极其微小的动作——比如整理袖口时指尖的轻微颤抖,递送物品时指尖不经意的触碰,或者是一个在别人看过来之前迅速移开的目光——将他们复杂纠结的情绪展露无遗。这些细节,细微到如果不是全神贯注地阅读,很容易就会被忽略,但正是这些被捕捉到的瞬间,构筑了人物关系的全部张力。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站在玻璃墙外的观察者,能清晰地看到角色们在做什么,却又无法真正触及他们内心深处那团摇曳的火苗。这种疏离感,反而加深了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它模仿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本质:我们永远只能触及对方的表象,而核心的秘密往往被小心翼翼地藏匿起来。尤其欣赏作者处理“遗憾”的方式,它不是用一个明确的事件来定义,而是让遗憾成为了一种伴随角色呼吸的背景噪音,轻微,却从未消失。
评分还不错的说,物流也挺快的
评分不错,女朋友很喜欢,给个赞。
评分还行,起码包装书面什么的还可以,商周授权的简体字版本
评分好看,好书好书,看了还想看,醉了
评分我就是喜欢京东购物,方便快捷还便宜
评分书是好书,就是这一版的封面不太好看
评分质量好,速度快,服务好,非常满意。京东可以的。看完了的
评分看完了,一口气看完了。
评分喜欢喜欢。很不错。买很多次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