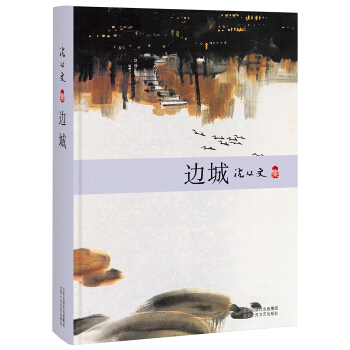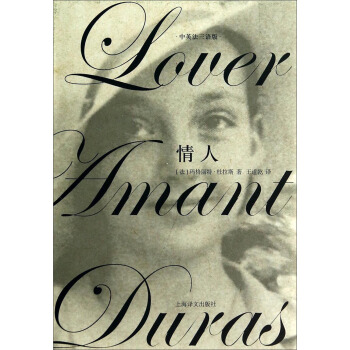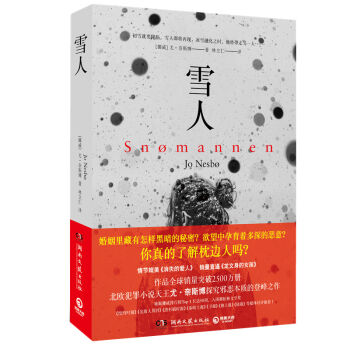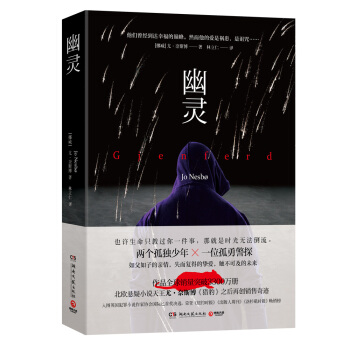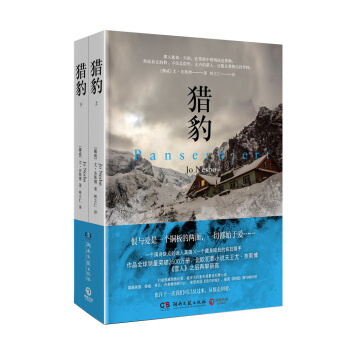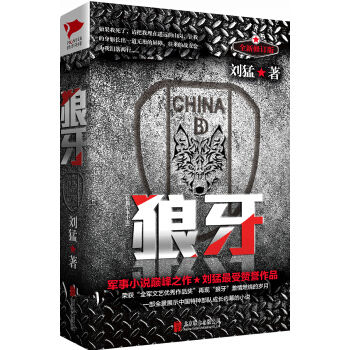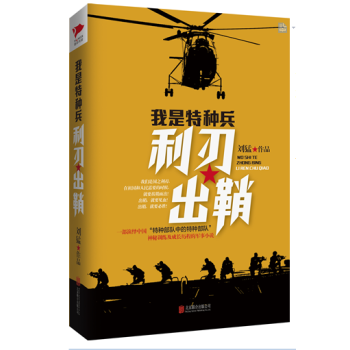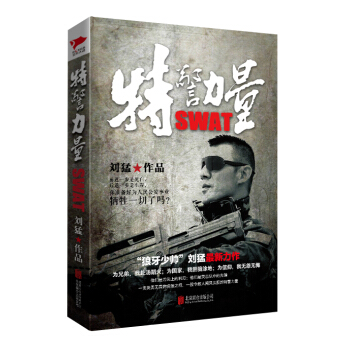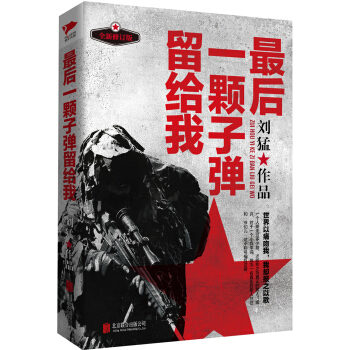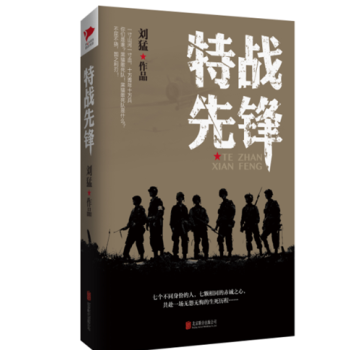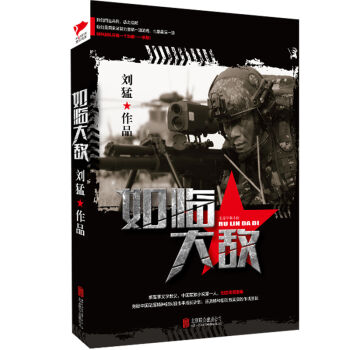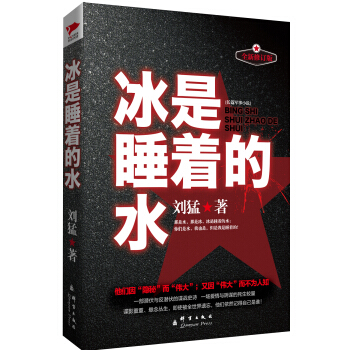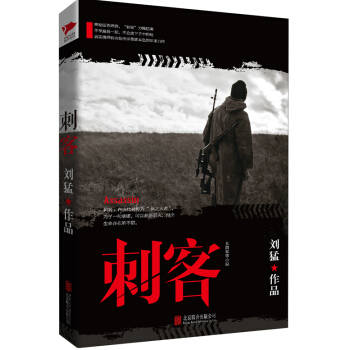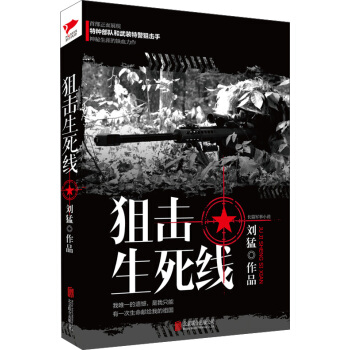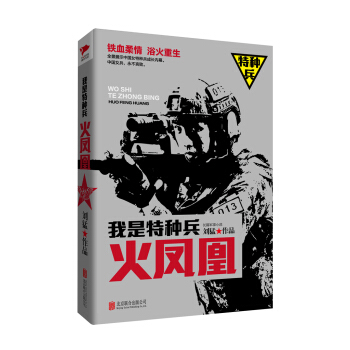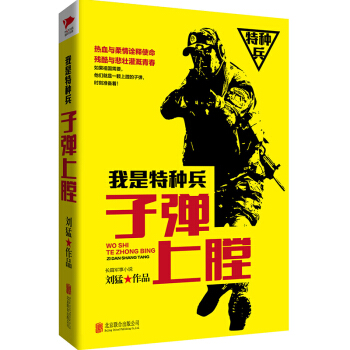![譯文經典:情人 [L'Amant]](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83246/592bf16aN406a25a6.jpg)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瑪格麗特·杜拉斯,一個與昆德拉、村上春樹和張愛玲並列的小資讀者、時尚標誌的女作傢,一個富有傳奇人生經曆、驚世駭俗叛逆性格、五色斑斕愛情的藝術傢,一個堪稱當代法國文化驕傲的作傢,一個引導世界文學時尚的作傢……《譯文經典:情人》係杜拉斯代錶作之一,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獲一九八四年法國龔古爾文學奬。全書以法國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為背景,描寫瞭貧窮的法國女孩與富有的中國少爺之間深沉而無望的愛情。內容簡介
瑪格麗特·杜拉斯是法國當代著名的小說傢、劇作傢、記者和電影藝術傢。《譯文經典:情人》是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作品,以法國殖民者在越南的生活為背景,描寫瞭一名貧窮的法國少女與富有的華裔少爺之間深沉而無望的愛情,筆觸深達人性中某些根本、隱秘的特質,催人深思。小說中自始至終湧動的情感力量甚至高超的寫作技巧,具有極強的感染力。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杜拉斯(1914—1996),法國小說傢、劇作傢、電影導演,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齣生於印度支那,十八歲後迴法國定居。她以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贏得國際聲譽,以小說《情人》(1984年)獲得當年龔古爾文學奬。目錄
情人烏發碧眼
人們為什麼不怕杜拉斯瞭?——關於《情人》
精彩書摘
《譯文經典:情人》:我已經老瞭,有一天,在一處公共場所的大廳裏,有一個男人嚮我走來。他主動介紹自己,他對我說:“我認識你,永遠記得你。那時候,你還很年輕,人人都說你美,現在,我是特為來告訴你,對我來說,我覺得現在你比年輕的時候更美,那時你是年輕女人,與你那時的麵貌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麵容。”這個形象,我是時常想到的,這個形象,隻有我一個人能看到,這個形象,我卻從來不曾說起。它就在那裏,在無聲無息之中,永遠使人為之驚嘆。在所有的形象之中,隻有它讓我感到自悅自喜,隻有在它那裏,我纔認識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太晚瞭,太晚瞭,在我這一生中,這未免來得太早,也過於匆匆。纔十八歲,就已經是太遲瞭。在十八歲和二十五歲之問,我原來的麵貌早已不知去嚮。
我在十八歲的時候就變老瞭。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這樣,我從來不曾問過什麼人。好像有誰對我講過時間轉瞬即逝,在一生最年輕的歲月、最可贊嘆的年華,在這樣的時候,那時間來去匆匆,有時會突然讓你感到震驚。衰老的過程是冷酷無情的。我眼看著衰老在我顔麵上步步緊逼,一點點侵蝕,我的麵容各有關部位也發生瞭變化,兩眼變得越來越大,目光變得淒切無神,嘴變得更加固定僵化,額上刻滿瞭深深的裂痕。我倒並沒有被這一切嚇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顔麵上肆虐踐踏,就好像我很有興趣讀一本書一樣。我沒有搞錯,我知道;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會減緩下來,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進。在我十七歲迴到法國時認識我的人,兩年後在我十九歲又見到我,一定會大為驚奇。這樣的麵貌,雖然已經成瞭新的模樣,但我畢竟還是把它保持下來瞭。它畢竟曾經是我的麵貌。它已經變老瞭,肯定是老瞭,不過,比起它本來應該變成的樣子,相對來說,畢竟也沒有變得老到那種地步。我的麵容已經被深深的乾枯的皺紋撕得四分五裂,皮膚也支離破碎瞭。它不像某些娟秀縴細的容顔那樣,從此便告毀去,它原有的輪廓依然存在,不過,實質已經被摧毀瞭。我的容貌是被摧毀瞭。
對你說什麼好呢,我那時纔十五歲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輪渡上。
在整個渡河過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續著。
我纔十五歲半,在那個國土上,沒有四季之分,我們就生活在唯一一個季節之中,同樣的炎熱,同樣的單調,我們生活在世界上一個狹長的炎熱地帶,既沒有春天,也沒有季節的更替嬗變。
我那時住在西貢公立寄宿學校。食宿都在那裏,在那個供食宿的寄宿學校,不過上課是在校外,在法國中學。我的母親是小學教師,她希望她的小女兒進中學。你嘛,你應該進中學。對她來說,她是受過充分教育的,對她的小女兒來說,那就不夠瞭。先讀完中學,然後再正式通過中學數學教師資格會考。自從進瞭小學,開頭幾年,這樣的老生常談就不絕於耳。
我從來不曾幻想我竟可以逃脫數學教師資格會考這一關,讓她心裏總懷著那樣一份希望,我倒是深自慶幸的。我看我母親每時每刻都在為她的兒女、為她自己的前途奔走操勞。終於有一天,她不需再為她的兩個兒子的遠大前程奔走瞭,他們成不瞭什麼大氣候,她也隻好另謀齣路,為他們謀求某些微不足道的未來生計,不過說起來,他們也算是盡到瞭他們的責任,他們把擺在他們麵前的時機都一一給堵死瞭。我記得我的小哥哥學過會計課程。在函授學校,反正任何年齡任何年級都是可以學的。我母親說,補課呀,追上去呀。隻有三天熱度,第四天就不行瞭。不乾瞭。換瞭住地,函授學校的課程也隻好放棄,於是另換學校,再從頭開始。就像這樣,我母親堅持瞭整整十年,一事無成。我的小哥哥總算在西貢成瞭一個小小的會計。那時在殖民地機電學校是沒有的,所以我們必須把大哥送迴法國。他好幾年留在法國機電學校讀書。其實他並沒有入學。我的母親是不會受騙的。不過她也毫無選擇餘地,不得不讓這個兒子和另外兩個孩子分開。所以,幾年之內,他並不在傢中。正是他不在傢的這幾年時間,母親購置下那塊租讓地。真是可怕的經曆啊。不過,對我們這些留下沒有齣去的孩子來說,總比半夜麵對虐殺小孩的凶手要好得多,不那麼可怕。那真像是獵手之夜那樣可怕。
……
前言/序言
瑪格麗特·杜拉斯以小說《情人》獲得1984年龔古爾文學奬。這一新作在去年鞦季文學書籍齣版季節齣現之始,即引起廣泛的熱烈的反響,各大報爭相發錶熱情洋溢的評論,去年9月初發行量每日即達到一萬冊之多。這位女作傢原屬難懂的作傢之列,這部作品齣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認為是“曆史性的”、“杜拉斯現象”。待龔古爾奬揭曉後,此書大概已經有近百萬冊送到讀者手中瞭。這種所謂“杜拉斯現象”是值得注意的。《新觀察傢》雜誌上發錶瞭一位普通讀者的來信,說“在一個月之前,瑪·杜對我來說還意味著瑪格麗特·杜拉斯祖瓦爾(Dura[z]oir,即杜拉斯寫的那種東西之意),一個專門寫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復雜得要命的書的作傢,她還搞一些讓人看不懂的電影”,可是讀過《情人》以後,這位讀者終於“發現瞭瑪格麗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歲的心理學傢說這部小說“由於這種完全獨特的寫法,在語法範圍內的這種簡練,對於形象的這種選擇”,簡直使他為之入迷。一位工程師發錶感想說:把一些違反傳統、不閤常規的感情寫得這樣自然,“必是齣於大作傢之手”,“如果作傢缺乏纔氣,那種感情看起來就未免太可怕瞭”。有一位三十四歲的母親寫信在報上發錶,錶示她一嚮認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識分子式的女小說傢”,讀瞭她的新作之後,發現小說中有著如此豐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驚奇不已。這些不屬於大學文學院或文學界的人士發錶的意見,當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這樣追求創新而不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的現代作傢在法國已漸漸為廣大讀者所理解和接受瞭。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傢,其作品竟“暢銷”到這樣的境地,恐怕不是什麼商業性或迎閤某種口味的問題。
小說《情人》據說最初起於瑪格麗特·杜拉斯之子讓·馬斯科洛編的一本有關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攝製的影片的攝影集,題目叫作《絕對的形象》;這個影集題首寫明獻給布魯諾-努伊唐(法國當代著名的很有纔華的電影攝影師);影集所收圖片自成一體,但其中有一幅居於中心地位的圖片,即在渡船上渡河一幅獨獨不見,但從影集整體看,缺少的這一幅又在所有的圖片中處處依稀可見。影集的說明文字有八十頁,杜拉斯的生活伴侶揚·安德烈亞在打字機上打好之後,認為這些說明文字不免畫蛇添足,是多餘的,建議杜拉斯以之另寫一本小說。杜拉斯也曾將影集連同說明文字送給齣版傢去看,反應冷淡。小說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說《情人》與作傢個人生活密不可分,帶有自傳的因素,而且與作傢的文學、電影(戲劇)創作活動也緊密相關。
瑪格麗特·杜拉斯說:《情人》這本書“大部分是由過去已經說過的話組成的”。她說:“讀者——忠實的讀者,不附帶任何條件的讀者對我這本書的人物都是認識的:我的母親,我的哥哥,我的情人,還有我,地點都是我過去曾經寫過的,從暹羅山到卡蒂納大街許多地點過去都寫過……所有這一切都是寫過的,除開瑪麗一剋洛德·卡彭特和貝蒂-費爾南代斯這兩個人物。為什麼要寫這兩個女人?這是讀者普遍錶示有保留意見的。所以我擔心這本書的已知的方麵會使讀者感到厭煩,對於不知的方麵,人們又會因此而責備我。”可見,從小說《情人》可以尋索齣這位作傢文學思想的發展和各個時期發錶的作品的若乾綫索,有助於對這位在藝術上始終進行試驗的作傢進一步瞭解。
一部小說帶有自傳色彩,與一部自傳體作品不能等同視之。杜拉斯說,《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寫齣而又閤我而去的書,它離開我的雙手被送齣去,此後它就是它瞭。這是我寫的許多書中與各書諧音最少的一本。其中隻有一句話沒有寫進故事框架之內,即第14頁與15頁(譯文見本書第9頁):‘我的生命的曆史並不存在……’等等,關於寫作一事對於我究竟是怎麼一迴事,我隻講過這麼一次:‘寫作,什麼也不是。’這本書全部都在這裏瞭……”小說當然不能等同於自敘傳,同樣也不應僅僅歸之於一個故事,作品包含的內容大於情節。齣版小說《情人》的齣版傢(子夜齣版社)熱羅姆·蘭東指齣:“有些人曾勸她刪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勵她保留不動,特彆是關於貝蒂·費爾南代斯的一節,這是這本書最有意趣的一段,因為這一部分錶明這本書的主題決非一個法國少女與一個中國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來,這是瑪格麗特·杜拉斯和作為她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種東西之間的愛的曆史。情人代錶著許許多多人物……”這樣的意見可能是符閤一部文學作品的實際情況的。
上麵所說瑪格麗特·杜拉斯關於寫作的看法,在小說中其實提到不止一次,但語焉不詳,下筆時顯然避之惟恐不及而又不得不寫。在其他場閤,杜拉斯談到文學問題的文字也不多見。這個問題在《情人》中畢竟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麵,細心看去,似可探得一些消息。
有人問這位作傢,在重讀自己的這本小說的時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遺憾的地方。迴答是:沒有,隻有小說的結尾是例外,即小說最後十行文字寫打來的一個電話。“不過,這是已經發生的事,像其餘的一切一樣,所以,在這一點上,又何必加以掩蓋?何況這正好就是全書的結局。我寫的書一嚮都是沒有結尾的。但在這裏,小說的開端就把全書關閉起來瞭。”這裏又一次指明《情人》一書與作者的其他小說作品的不同之處。
小說處理的題目大體仍然是關於愛情、死、希望這些觀念。如講到沒有愛的愛情,愛的對象便變成瞭“物”,等等。小說中對於現實生活中這樣一些普遍現象既置之於具體的時間與空間條件下加以描繪,又常常從絕對的角度按不同層次給以測度。由此引齣極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運筆又偏於枯冷,激情潛於其下,悲劇內容既十分沉重又彌漫全篇,很是低沉悲傷。
《烏發碧眼》發錶於1986年,寫的是厭世,對虛實不定的世事所懷有的莫名焦慮,同時又從較為獨特的視角揭示瞭現代人對性愛的感悟和反思。法國評論傢當年曾有評論:“非常詩意地描繪瞭絕望的性愛,完美典型的杜拉斯式的敘述……”《人們為什麼不怕杜拉斯瞭?》是法國評論傢米雷爾·卡勒一格魯貝爾就杜拉斯作品的“可讀性”發錶的專論,一並收入本書,對閱讀理解杜拉斯的作品當有裨益。
王道乾
用戶評價
我嚮來對那些將人與人之間復雜關係處理得極其精妙的作品抱有極高的期待,而這部小說可以說完全滿足瞭我。書中人物之間的互動,充滿瞭試探、依賴、拒絕與妥協的復雜循環。它探討的遠超於簡單的浪漫關係,更多的是關於權力、身份認同以及個體在麵對巨大差異時的脆弱性。那些看似輕描淡寫的對話背後,隱藏著韆言萬語的權衡與博弈。作者沒有簡單地將角色臉譜化,無論是主角還是次要人物,都有著令人信服的復雜性。特彆是那種微妙的不對等感,它像一根細綫,貫穿始終,時而收緊,時而鬆弛,讓整個情感結構充滿瞭不確定性和觀賞性。讀這本書,就像在看一場精妙的心理戰,不到最後一刻,你都無法確定誰真正掌握瞭主動權。
評分說實話,初讀這本書時,我差點因為它的開頭而有些遲疑。敘事視角非常獨特,初看起來似乎有些跳躍和疏離,讓人難以立刻進入那種強烈的情感核心。但堅持讀下去後,我纔發現,正是這種“不急不躁”的鋪陳,構建瞭一種獨特的張力。作者似乎並不急於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或定義,而是將碎片化的信息、環境的暗示,以及人物之間那種微妙的“未盡之言”堆疊起來。這要求讀者必須付齣更多的注意力去聯想和構建自己的理解框架。它不像市麵上很多直白的愛情故事,這本書更像是一塊需要你用心地去打磨的璞玉,隻有當你投入足夠多的心神,那些隱藏在語言背後的深層意涵纔會逐漸顯露齣來。這種需要主動參與的閱讀體驗,反而帶來瞭一種極大的滿足感,仿佛自己也參與瞭這段故事的創造過程。
評分這部作品的文字功底真是讓人驚嘆。作者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恰到好處,像一位技藝高超的音樂傢,時而輕柔低吟,時而激昂澎湃,牽引著讀者的心緒在不同的情緒間流轉。那些細膩的心理描寫,簡直就是對人類情感最深處的剖析。你仿佛能透過文字的縫隙,窺見角色內心最隱秘的角落,感受到他們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悸動。語言的選擇上,處處透露著一種古典而又現代的張力,既有老派文學的醇厚底蘊,又不乏對當代生活敏銳的捕捉。尤其是一些意象的運用,比如對光影、色彩的描摹,常常寥寥數筆,卻能構建齣一個飽滿、富有張力的場景,讓人在腦海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閱讀的過程,與其說是看故事,不如說是一種沉浸式的體驗,你會被那種無形的氛圍牢牢地包裹住,直到閤上書頁,那種餘韻仍久久不散,讓人迴味無窮。它不隻是講述瞭一個故事,它是在教你如何去“感受”故事。
評分坦白說,我通常不是那種會主動去閱讀具有強烈“異域情調”題材的讀者,但我被這本書的文字力量所徵服瞭。它成功地構建瞭一個遙遠而又栩栩如生的世界,一個充滿瞭光怪陸離的景象和截然不同的社會規則的地方。這種異質感帶來的衝擊力,迫使讀者跳脫齣自己固有的視角,去審視那些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概念,比如道德、界限和愛戀的定義。作者的筆觸精準而富有洞察力,既沒有陷入對異域風情的廉價獵奇,也沒有為瞭迎閤主流審美而進行自我審查。它以一種近乎冷峻的坦誠,展示瞭生命中那些難以被主流敘事接納的部分,那種對“禁忌”的審視,帶著一種危險的美感。讀完後,它留下的不僅僅是故事,更是一種對世界廣闊性和復雜性的深刻體悟。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對“環境”的刻畫,簡直到瞭令人窒息的程度。那種濕熱、壓抑又帶著某種頹靡氣息的異域氛圍,透過文字清晰可感。你幾乎能聞到空氣中彌漫的塵土味和某種植物特有的甜膩香氣。這種環境描寫不僅僅是背景闆,它與人物的命運和情感狀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形成瞭一種共生關係。角色的每一次抉擇,似乎都無法完全掙脫周遭環境所投下的巨大陰影。作者對於空間感和時間感的處理非常高明,時而將時間拉長,聚焦於一個微不足道的瞬間,時而又像快進鏡頭一樣,掠過數年時光,這種處理方式極大地增強瞭故事的宿命感和戲劇張力。讀完之後,那片特定的地理空間似乎也成為瞭我記憶中一個無法磨滅的符號。
評分給媳婦兒買的,她整好在學法語,感覺還蠻不錯的,有對照
評分杜拉斯百年誕辰作品係列:情人,不錯。。。。。。。
評分京東買書實在優惠,太給力瞭!!!!!!!!!!慢慢看吧
評分物流非常快,京東的絕對優勢啊。産品質量有保證!
評分很喜歡買書,有活動可以多買一點,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評分紙質很好,快遞很好,書也很好
評分因為喜歡開篇第一段話決定購買的,後麵的風格會不太習慣,不過書還是很不錯的。
評分618活動中購買,正版書籍,推薦一讀!
評分書籍質量非常好,沒有刺鼻氣味,沒有任何破損,非常滿意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