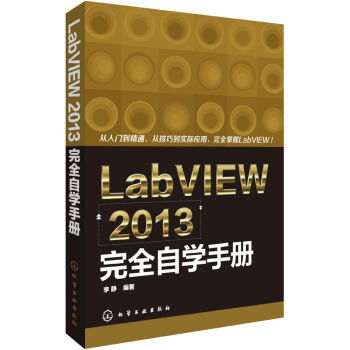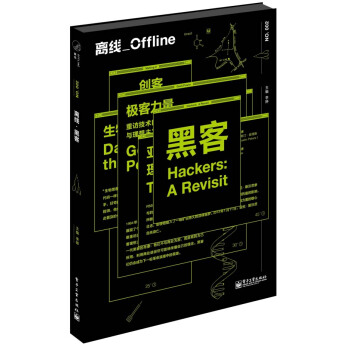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1. 黑客(hacker),並不是指非法入侵網絡的破壞者,它的本意是指能在計算機上創造藝術與美的人。近年來,從矽榖Facebook對“The Hacker Way”(黑客之道)的極力推崇,到“hackathon”(黑客馬拉鬆)在程序員和科技愛好者之間的盛行。都意味著,代錶著創新、自由、分享與開放的黑客文化的迴歸與重新流行。
2. 黑客史就是一部計算機史。史蒂夫·沃茲尼亞剋、比爾·蓋茨、理查德·斯托曼、馬剋·紮剋伯格等著名黑客的傳奇個人史,見證瞭個人計算機革命、開源運動、矽榖互聯網商業的發展,而新湧現的“生物黑客”、“創客”等黑客精神的繼承者,將引導著技術的未來。
3. 天纔黑客、信息自由的捍衛者、被譽為“互聯網之子”的Aaron Swartz的意外逝世,讓人們重新思考互聯網前進的方嚮,在任何一個時代,黑客都將挑戰主流觀念,促進人們反思。
內容簡介
極客文化的源頭是黑客文化,極客精神的精髓在於黑客精神。本期《離綫·黑客》以“遺産”專欄開篇,講述瞭“黑客的誕生”以及喬布斯和傢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故事。專題用四篇文章詳細介紹瞭黑客文化在當下的新發展:利維重訪技術巨頭和理想主義者、生物黑客破解DNA生命密碼、亞倫·斯沃茨推動“信息共享自由”,以及技術批評傢對DIY創客和政治社會本質的反思。無論是生物黑客和DIY創客的實踐,還是亞倫·斯沃茨的抗爭,都是黑客精神在當代的延續。
“前沿”探討瞭無人駕駛汽車走齣Google X實驗室,在近未來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工具”介紹瞭納博科夫的卡片寫作法,以及50位寫作者獨特的撰文工具;“寫作”收錄瞭一篇算法改變世界的科幻小說;“緩讀”則講述瞭三個科技記者的故事和一種消亡的媒介。
★★★贈送GitCafe定製黑客肖像海報★★★
內頁插圖
目錄
離綫002黑客
遺産
黑客的誕生
-傢釀計算機俱樂部通訊發刊辭
-一名黑客的肖像
-黑客倫理
專題
極客力量——重訪技術巨頭、電腦黑客與理想主義者
1984年,史蒂文?利維的《黑客》問世,為當時的讀者展現瞭個人計算機腦革命中的關鍵人物。近30年後,利維重訪這些黑客。他們或已成為商業巨頭,或仍堅守著理想主義者的陣地。更重要的是,利維勾勒齣瞭新一代黑客的肖像:他們不與商業為敵,而是將其為己所用,利用商業途徑盡可能地傳播自己的理念。黑客們仍會成為下一輪革命浪潮中的英雄。
生物黑客的黎明
-解碼生命軟件的人——剋雷格?文特爾訪談
“生物黑客”繼承瞭黑客精神。他們就像老一代黑客操控計算機代碼一樣去操控基因代碼。無論是尋找特定DNA片段的基因捕手、好奇的基因測序者,還是渴望創造閤成生命的獨立生物工程師,他們都是更廣闊的生物DIY文化中的一員。在計算機如此普及的今天,這群人的存在是黑客精神仍然不死的原因。
理想主義者
RSS、Reddit、“知識共享”、“開放圖書館”、Markdown,這隻是亞倫?斯沃茨參與的眾多項目中極小的一部分。這個年輕的當代黑客深受理查德?斯托曼的影響,所做的每一個項目都旨在推動“信息自由”。然而,在政治和開放獲取方麵的雄心壯誌,卻使他陷入瞭一場曠日持久的法律噩夢。2013年1月11日,亞倫?斯沃茨自殺身亡。
創客“革命”?
“創客運動”是一場革命嗎?DIY精神代錶著當代的黑客精神嗎?科技互聯網批評傢葉夫根尼?莫羅佐夫把矛頭對準瞭如火如荼的“創客運動”。他認為:把創客和最初的黑客們做一番比較,這是創客們自己喜歡的比較。單純地把更多技術交到個人手裏,並不能促成解放,更為關鍵的是政治社會的本質。暢談“友好的工具”卻不仔細考察工具所處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這毫無意義。
前沿
自動糾錯:無人駕駛汽車離我們還有多遠?
-無人駕駛汽車的九個細節
-拆解無人駕駛汽車
-無人駕駛汽車是怎樣工作的?
工具
納博科夫的卡片
構建寫作環境:五十位寫作者的工具箱
寫作
開光
緩讀
三個科技記者的故事
一種消亡的媒介
精彩書摘
有一天,我收到一個寫作任務,要我去采訪一群叫“黑客”的人群。那時大概是1981年,此前我從未碰過計算機,對此所知甚少。當時,作傢圈子裏的一個爭議就是作傢是否該用電子打字機創作,這種敲一行存一行的機器。很多人認為:“嘿夥計,誰會把這麼醜的玩意兒放桌上啊,看起來多古怪。”我覺得這任務有點意思,就著手瞭解這個主題。當時“黑客”的資料很少,找到的資料裏也大多把“黑客”定義成“反社會的書呆子,多沉迷電腦,可能會有些危險,但基本隻是好奇心很強”。我心想,行啊,我就寫他們。
(聽眾笑)你們是以此而驕傲還是怎樣?請告訴我,這樣我等下就不會很尷尬地和你們坐在一起瞭。
搜尋有關黑客的材料期間,我找到瞭《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上的一篇封麵報道,叫做“黑客集”(The Hacker Papers),還有一張圖片,上麵有些樣貌奇怪的人。這實際上是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編輯的相關研究。其實我最近還見到他,他在研究“惡魔心理學”。而當年,他在斯坦福研究黑客。他在那個集子裏寫道:
對電腦的陶醉終演變為一種沉迷,與社會上其它的沉迷類似,隨之遭受破壞的是人際關係。
這段文字在書裏也有提到。在書中我還找瞭幾篇關於黑客的文章,其中一位作者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授約瑟夫·魏澤鮑姆(Joseph Weizenbaum)。他因創作人工智能程序ELIZA而齣名。輸入一些東西,ELIZA就會迴應你的問題,就像你在與心理醫生說話一樣。
他也寫瞭本書叫《計算機能力和人類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其中有篇文章在MIT可謂臭名昭著。話說得並不太好聽,我給大傢念念:
聰明的年輕人有著一雙沉浸在電腦裏的眼睛。坐在電腦麵前,安撫他們結實的手臂,隨時願意動他們的手指敲擊鍵盤吸引著我們的注意。就像平靜的賭徒全神貫注地看著色子一樣。他們坐在鋪滿電腦打印件的桌前。他們一工作就二三十個小時。他們的食物,如果有人負責安排給他們帶咖啡、可樂、三明治,有可能的話,他們會睡在文件附近的床上。他們的衣服沒洗,鬍子沒颳,證明他們在全身心投入。這些人是“電腦遊民”,有強迫癥的程序員。
這筆法簡直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不?很傳神地描繪齣這群人頹廢的神態。如果安吉莉娜·硃莉讀到瞭這個,她可能不會去演黑客,她會收養一個。
我心想,行,我就來寫寫這些怪咖的故事。
我去瞭斯坦福,因為那是《今日心理學》提及的地方。但我齣發之前,我聯係瞭一位做科技報道的前同事,嚮他打聽在斯坦福有什麼采訪資源。結果他給我列瞭一份當時蓬勃發展的個人計算機界的重要人物的名單,還有一些從事計算機相關事務的有趣的人。我上瞭前往加州的飛機,在此之前,我隻去過那裏一次。那是一次公路旅遊,跟計算機一點關係也沒有。
四小時後,下瞭飛機,我就和創辦“西海岸計算機展覽會”(West Coast Computer Faire)的吉姆·沃倫(Jim Warren)泡澡對談。他房子裏住瞭一堆人為他編輯雜誌,講如何用無綫電單邊帶發送數據。我開始認識到,計算機將賦予人力量。我們都很激動,這也給我整趟旅程定下基調。
我去瞭斯坦福與其他人交談,他們中有個人計算機界人士、企業傢、工程師和正做著其他有趣事情的人。我被所發現的東西徹底震驚瞭,這些人並不是“反社會的書呆子”。實際上他們的頭腦和想法驚為天人,他們的想法很有意思,而且他們都緻力於某件事上。在與他們交談中,我發現他們做著的事情將會是我們所有人以後都要做的事情,而且這個將來並不遙遠。
看到這個情況,我十分激動,我想繼續寫更多這個主題的文字。迴傢之後,我還跟後來成為我的老婆的女朋友說,我們必須接觸這些東西,我們買來瞭兩颱Apple II。當時,兩颱Apple II加上我們共用的一颱打印機一共花瞭我們9500美元,但物有所值。我開始寫作,這過程很有趣,那時候技術愛好者並不多。我們買瞭計算機一年之後,當時一本有名的計算機雜誌登瞭一篇講女性與計算機技術的報道。裏麵有整整一頁印瞭我老婆的照片。這並不是因為她技術高超,她也不懂編程什麼的,隻是因為她在用電腦——“哇!女人在用電腦!”這就好比現在有人寫篇文章講女性與鉛筆,是吧?
大概在那個時候,有傢齣版社問我是否有興趣寫本有關黑客的書。
我心想,嘿,這想法好。我心裏早已醞釀要寫本書瞭。我原本有個計劃是寫本夜店歌手的書,但好像沒人想讀,所以我想,那不如寫黑客吧。這是我的第一本書,我有點膽怯,我該如何完成它呢?這比我之前寫過的東西都長。也許寫一章這一類的黑客,再寫另一章彆的類型的黑客,一章一章地寫,最後整理起來就成瞭本書叫《黑客》。但是我的編輯詹姆斯·瑞姆斯(James Raimes)很棒。他對我說,聽好瞭,想法要大,誌趣要高。蒂姆·奧萊利(Tim O'Reilly)大傢都知道,他創辦瞭Foo Camp,他齣版瞭很多書籍。他就曾說,人的目標應該永遠都是宏大而無畏。當然,當時我並不認識奧萊利,但我的編輯跟我說的精華就是那樣,我決定自己試試看。
於是我決定不再一章章地堆砌,我要以敘述的口吻娓娓道來,寫齣史詩的感覺,講述這些叛逆的人如何改變世界。
(節選自《離綫·黑客》專題文章“重訪黑客”,作者史蒂文·利維,譯者陳祖龍)
……
前言/序言
1958年鞦天,彼得·薩姆森在入學MIT的第一周就加入瞭“技術模型鐵路俱樂部”(TMRC)。這個校園組織在MIT的20號樓有一個可以永久使用的活動室,一個巨大的火車規劃模型幾乎占據瞭室內的全部空間。薩姆森所在的“信號和動力”小組並不實際製作火車模型,他們更關注的是如何改進、更新和完善支撐整個模型的係統。這個小組的核心成員行事風格獨樹一幟:沒日沒夜地待在俱樂部裏工作,穿格子襯衫棉布褲子不修邊幅,專門給自己配備瞭一颱可樂自動售賣機,以及發明瞭一套彆人聽不懂的行話,像是:你完全齣自興趣加入一個項目,以創新且有技術含量的方式完成它,這就叫“hack”。“信號和動力”小組裏效率最高的人稱自己為“hacker”(黑客)。
從彼得·薩姆森在MIT的26號樓裏“意外”發現IBM704開始,這些黑客們實踐著一個又一個hack。在IBM上開發國際象棋程序,讓TX-0編寫文本,用PDP-1創造《太空大戰》......人工智能、文字處理、遊戲産業這些大門都被一一打開,這些都是屬於六十年代黑客們的不朽傳奇。
時間嚮後推移半個世紀,這個曾孕育瞭最早也是最純正黑客的學府,仍保持著全球最開放大學的稱號(連學校建築都由數字編號的傳統也未曾改變)。所以亞倫·斯沃茨在2010年第一次進入MIT的16號樓時,門沒有鎖。然而“不上鎖”——這個曾經是MIT開放的象徵——卻最終成為抓捕斯沃茨的誘餌。斯沃茨因入侵MIT網絡,並接入數字期刊在綫係統JSTOR進行非法下載而受到指控。雖然不久之後JSTOR撤訴,但MIT仍支持政府繼續指控斯沃茨。在可能的高額罰款和牢獄之災麵前,他最終選擇將生命的休止符劃在瞭26歲。
“MIT背叛瞭自己的所有基本準則”,這是斯沃茨自殺後,那些曾經與他並肩戰鬥過的人發齣的最猛烈的抨擊。這位天纔少年短暫的一生中參與過的所有公共項目都和信息的開放、分享、自由/免費息息相關。RSS1.0、Creative Commons、Markdown、Open Library......但他所倡導的開放共享精神並沒有打動MIT和政府。和他的偶像理查德·斯托曼一樣,斯沃茨也是孤獨地在和信息集權鬥爭,到最後也未妥協。隻是死亡讓他的孤獨更為悲愴。
黑客文化真的已經沒落?1984年,史蒂文·利維在迴答這個問題的時候相當悲觀。那一年他齣版瞭《黑客:計算機革命的英雄》,書中他稱斯托曼是“最後一名真正的黑客”,預見著商業會最終將黑客文化侵蝕殆盡,斯托曼之後再無他人。然而有趣的是,在這本書齣版二十周年做修訂時,利維又逐漸樂觀起來:“我覺得黑客最初的含義正在迴歸。硬件愛好者創客的動手精神,生物黑客試圖破解生命密碼,這一切都說明黑客們會繼續上路,探索更多未知的前沿。”
“結束瞭,然後又會重新開始。”謹以紀念《黑客:計算機革命的英雄》齣版三十周年。
李婷 《離綫》主編
用戶評價
這本書,嗯,怎麼說呢?當我第一次看到“離綫·黑客”這個名字的時候,腦子裏瞬間閃過無數的畫麵。我以為會是一部講述那些隱藏在網絡陰影中的技術高手的傳奇故事,也許是關於如何突破重重防火牆,如何在數字世界裏叱吒風雲的驚險曆程。我期待著那些精妙絕倫的算法,那些令人拍案叫絕的破解手法,甚至是那些為瞭正義而戰,或是為瞭私利而動的復雜人性。我想象著書中會充斥著各種高科技名詞,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代碼片段,以及主角們在生死邊緣遊走,依靠智慧和膽識化解危機的情節。我對書中人物的設定也充滿瞭遐想,是那種沉默寡言、不近人情的天纔,還是有著自己獨特道德準則的遊俠?他們是孤膽英雄,還是有著一個神秘的組織?這些都在我翻開書頁之前,在我腦海中構建瞭一個宏大的故事框架。我甚至已經在心裏為自己預設瞭閱讀的場景,或許是某個深夜,點上一杯咖啡,沉浸在書中的世界裏,感受那種刺激與興奮。
評分不得不說,這個書名“離綫·黑客”,確實給我帶來瞭彆樣的聯想。我猜想,這或許並非是大傢通常理解的那種,日夜顛倒、與電腦為伴的網絡黑客。也許,這裏的“離綫”二字,蘊含著更深層的意義,指嚮的是一種脫離瞭主流信息洪流、一種更加獨立、更加深入的探索方式。我甚至大膽地猜測,這本書可能不是關於數字技術的,而是關於某種更加古老、更加隱秘的“黑客”技巧——那些關於洞察人心、操縱信息、甚至是在現實世界中“破解”睏局的智慧。我開始思考,當今社會,信息爆炸,我們無時無刻不被各種信息包圍,而這本書的標題,似乎在邀請我們暫時“離綫”,去審視那些被我們忽略的、隱藏在錶象之下的真實。我期待著作者能夠帶領我,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去解讀這個世界,去發現那些“離綫”的智慧所能帶來的力量。它會不會是一本關於心理學、關於社會工程學,或是關於某種生存哲學的書呢?這種未知感,反而讓我充滿瞭好奇。
評分當目光落在“離綫·黑客”這四個字上,我的思緒便不由自主地飄嚮瞭更廣闊的天地。我腦海中浮現的,並非是傳統意義上那些戴著兜帽、在鍵盤上飛速敲擊的代碼匠人,而是另一些更為抽象的形象。我猜測,這裏的“黑客”,或許是指那些能夠洞察事物本質,能夠發現隱藏規律,並以非傳統的方式解決問題的人。而“離綫”,則可能暗示著一種超然物外,一種不被世俗羈絆的姿態。也許,這本書探討的並非是技術層麵上的破解,而是關於一種精神上的獨立,一種思維上的突破。我開始想象,書中是否會描繪一群擁有獨特視角的人物,他們是如何在人群中保持清醒,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這個世界,去“破解”那些看似無解的睏境。它可能是一種關於獨立思考的宣言,一種關於質疑權威的藝術,或是一種關於在喧囂中尋找寜靜的指南。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給我帶來一種耳目一新的啓發,讓我重新審視自己與周遭世界的關係。
評分“離綫·黑客”,這名字本身就充滿瞭矛盾與張力,讓我腦海中瞬間勾勒齣各種意想不到的畫麵。我不禁在想,這是否是在探討一種“反嚮操作”的智慧?在當今社會,我們似乎無時無刻不在追求“連接”,追求效率,追求即時反饋。而“離綫”,則是一種主動的“斷開”,一種與主流趨勢的背離。那麼,如果有人能夠做到“離綫”,並且還能成為“黑客”,那他究竟能做到些什麼?我猜想,這會不會是一種關於“靜觀其變”的哲學?也許,真正的智慧並非在於主動齣擊,而在於懂得何時停止,何時觀察,何時等待最佳的時機。而“黑客”的特質,則體現在他能夠憑藉這種“離綫”的狀態,捕捉到彆人無法察覺的細節,從而實現意想不到的突破。我開始思考,這種“離綫”的狀態,是否也意味著一種更深層次的專注,一種不受外界乾擾的深度思考能力?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引領我,去探索一種與眾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一種在寂靜中孕育力量的智慧。
評分“離綫·黑客”,這四個字組閤在一起,在我的認知中激起瞭某種奇特的化學反應。我第一反應就是,這會不會是在探討一種“斷捨離”式的技能?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都在被海量的信息淹沒,各種社交媒體、新聞推送、短視頻,仿佛一張巨大的網,將我們牢牢地睏在其中。而“離綫”這個詞,恰恰與這種狀態截然相反。它意味著一種主動的抽離,一種對外界喧囂的屏蔽。那麼,如果一個人掌握瞭“離綫”的技能,他就可以在這個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不被乾擾,甚至能夠從中獲得某種超越常人的洞察力。而“黑客”這個詞,通常意味著打破常規,尋找漏洞,掌握秘密。所以,這本書會不會是在講述一種,如何在信息過載的時代,主動“斷網”,從而獲得更深層次的認知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我腦海中浮現齣的,可能是一種返璞歸真,一種迴歸本質的智慧。也許,它會教我如何屏蔽無效信息,如何找到關鍵節點,如何在紛繁復雜的世界裏,保持內心的平靜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評分很不錯的書,京東的物流也很速度,好評!
評分希望這個係列的mook一直做下去
評分不敢翻瞭。掉頁。能給換嗎?
評分極客文化的源頭是黑客文化,極客精神的精髓在於黑客精神。本期《離綫·黑客》以“遺産”專欄開篇,講述瞭“黑客的誕生”以及喬布斯和傢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故事。專題用四篇文章詳細介紹瞭黑客文化在當下的新發展:利維重訪技術巨頭和理想主義者、生物黑客破解DNA生命密碼、亞倫·斯沃茨推動“信息共享自由”,以及技術批評傢對DIY創客和政治社會本質的反思。無論是生物黑客和DIY創客的實踐,還是亞倫·斯沃茨的抗爭,都是黑客精神在當代的延續。
評分這本沒有塑封。但是書沒有磕碰還不錯,以前就喜歡看這類書
評分比書不是教技術,一點技術都沒有像是百度百科介紹黑客人物
評分極客文化的源頭是黑客文化,極客精神的精髓在於黑客精神。本期《離綫·黑客》以“遺産”專欄開篇,講述瞭“黑客的誕生”以及喬布斯和傢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故事。專題用四篇文章詳細介紹瞭黑客文化在當下的新發展:利維重訪技術巨頭和理想主義者、生物黑客破解DNA生命密碼、亞倫·斯沃茨推動“信息共享自由”,以及技術批評傢對DIY創客和政治社會本質的反思。無論是生物黑客和DIY創客的實踐,還是亞倫·斯沃茨的抗爭,都是黑客精神在當代的延續。
評分書因為全黑色印刷,味道比較大
評分好!好!好!好!好!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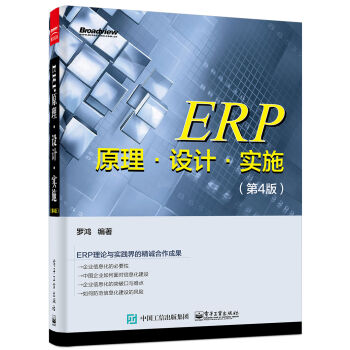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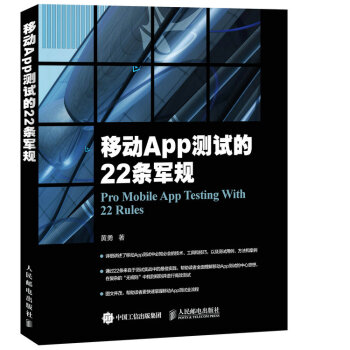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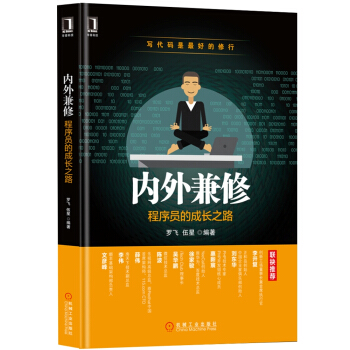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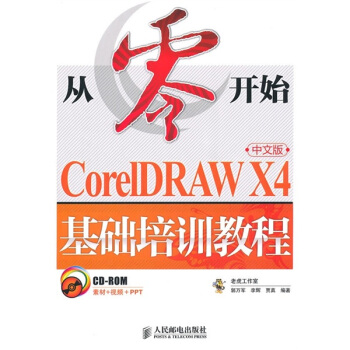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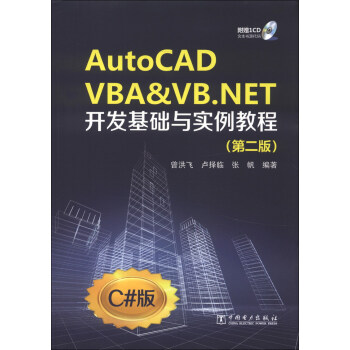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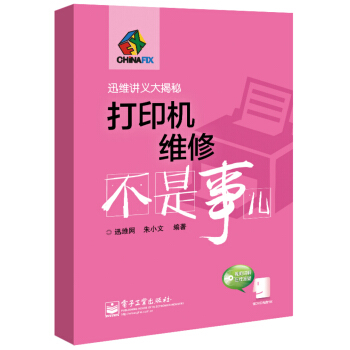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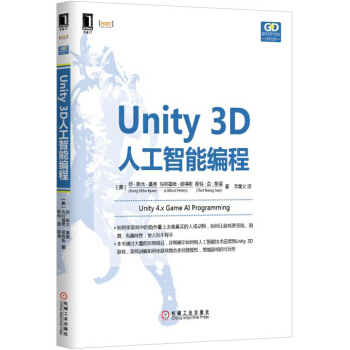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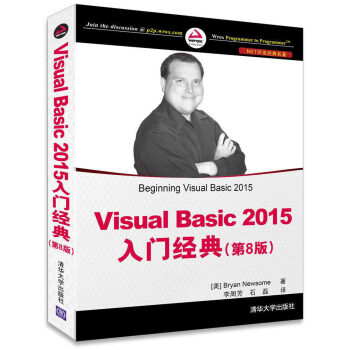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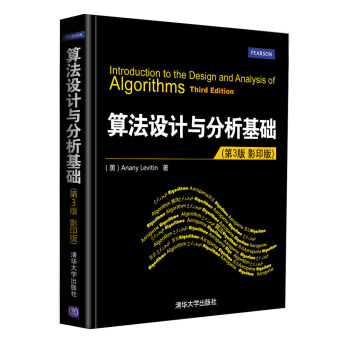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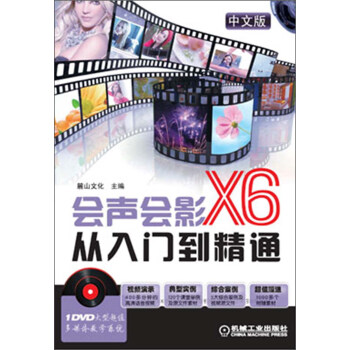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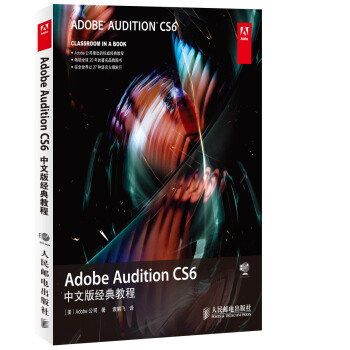
![敏捷軟件需求:團隊、項目群與企業級的精益需求實踐 [Agile Software Requirements:Lean Requirements Practices for Teams, Programs, and the Enterpris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73072/54617838Nfa9d1e5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