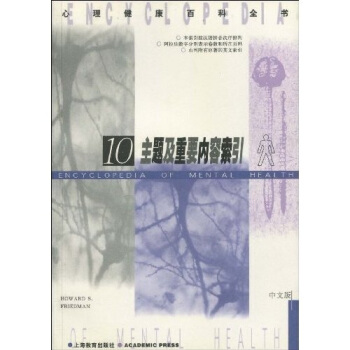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作者非学院派心理学家;作者擅长心理分析;
如果你对现实的社会人生感到苦闷难受无奈无解以致愤恨;
那么,读读这3卷,对你不无益处。
作者简介
李毅强(笔名,李沫来),曾在上海社科院工作。留学日本六年。专攻荣格派心理学,学习成唯识论。读书终生,理解他人,反省自己,充实自己,体味人生;言行一致,将心比心,我之外皆我师。精彩书评
★阅读是一门快要失传的艺术。在这个思想不能集中的时代,书籍仍旧是重要的,但作为曾经的出版人,我可以坚定地说,这不是一本畅销书,尽管相亲节目都配备了心理专家。这是一本普及性书籍,一本科普自助书籍。你可以不知道李毅强,但不能不知道这套《心理学散论》。好书改变人心。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遇到这套书。请阅读此书。独自阅读。你知道,那是一场内心的盛宴。
对《心理学散论》,诸位如未读懂,亦请对作者心存敬意。
——乔木
目录
第一辑 记忆与思想之间——隔雨望红楼笔记摘抄前记 从北京归来
听傅聪先生的访谈
Tobe与Tohave
附录:消夏杂记:Tobe与Tohave
小说作法及其周边
站在信仰的门槛上
语言(Logos,Wort)
从实际生活中开拓的地盘越大,所获得的Eros情感也越丰盛
附录:夏日杂记:关于荷马的成语
许思园先生与许思园现象
附录一:夏后杂记:“开口求人难”,李太白毕竟了不起!
附录二:“开口求人难”(续),黑格尔与歌德
许思园先生的议论
附录:脸谱的变化
“意义”是一种人类不能须臾离之的“疾病
罗杰斯的人际交往学
男性因素与女性因素
附录:消夏杂记:《浮士德》中的几句诗
写作中”自我“的重要性
附录:消夏杂记:陆九渊的”田地清净“说
勒本的著作与观点
写文章只需”自圆其说
尼采点滴:时代错误、历史感、创作
宗教的生理与心理基础:大脑与太阳神经丛
他人焦虑症:人我未分的混沌状态
结束语:春华秋实
第二辑 精神病理学点滴
读佛心得:“人际关系中毒症”解剖
“人际关系中毒症”释义及其他
“献身性”的病理——对日本某文学家的精神分析
“白痴一念——对太宰治”他人指向“的精神分析
关于太宰治
购书事情
自杀论
自杀论(续)
关于”境界型人格障碍
克莱恩女士
太宰治与酒
自恋性人格障碍症
关于井伏鱒二
读诗感怀两则
第三辑 生死观的觉悟
生死观的觉悟——围绕“死亡”的散记
遭遇儿子
后记
前言/序言
前记 从北京归来长期住在上海这个四季特征不太明显的城市中,几十年下来,只是对于夏日与冬天,感觉比较鲜明,其他的日子,好像一晃就过去了。北方的季节感却是要比南方来得明显。春夏秋冬的感觉截然分明,故宫护城河里冰水才融化,什刹海岸边的柳枝便抽出新芽,垂柳依依,远远看去仿佛给明媚的湖水,添了许多谦卑的侍者,送往迎来,参差不齐地站在那里,一副煞是殷勤的模样。
夏日的感觉,便是炎热,不过到了晚间,暑气似乎消得蛮快。只要红日西下,我去皇城根遗址一带去散步,便觉得非常凉爽了。那么北京夏日的特征是什么呢?可以举出的例子应该不少吧!不过如果让我来说的话,我想得起的,只有这什刹海杨柳树中“千啭不穷”的知了之声了。因为,我有过一次在什刹海边听知了叫的经验。
———那是一天下午,从前海郭沫若纪念馆(前海西街18号)走出来,心中颇有感慨,拐弯处就是什刹海,信步走去,望着那一片青青的垂柳,宛如云烟,不由想起了老杜的诗句:“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人的生命有时真是敌不过这送往迎来的柳树呢?这后海的柳树,郭沫若生前何尝不是天天看见,如今郭公已矣,而什刹海却风景依旧。
蓦然间注意到知了的叫声。突然脑海中闪过一句类似诗的句子:
啊,诗人的箜篌终于停歇了罢,
那古声古色的‘筑’亦无人敲击了罢
———听啊,那长夏中的知了却仍在欢叫呢!
如果熟谙日本俳句的话,那5 7 5的音节便可以容下我的感慨了,因为这里有了俳句所必须要有的“季题”(关于季节的感触,是俳句必不可少的要求)。这三段的句法也与俳句接近,可它不是俳句!———俳句当更加浓缩、更加精微,更加细密,其艺术韵味也更高!如果我也勉强写得浓缩一些,不知是不是应该这样:
箜篌久不作,
唯闻———
什刹海蝉叫声声……(访郭沫若纪念馆有感)
诗人走了,他也不带去一片云彩;却留下无数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其实,这知了也是叫不了多久的,等萧瑟的秋风一起,黄叶飘零,蝉的生命也就结束了。生物的生命总是要给画上句号的,可生命所发挥的能量,所留下的影响却是长久的。郭沫若先生,不管怎样,总是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表人物吧,他的去世也就意味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吧!
诗人生前使用过的书房与卧室,开放了让人参观。那栋古色古香的房子固然有些豪华,但并非如传说中所说是某位王公贵族的府邸,尽管那样的府邸北京城中到处都是。它原是北京城的达仁堂的一位老中医,行医半辈子,用自己的积蓄所建。郭老入住前,曾经做过蒙古的大使馆和宋庆龄的居所,尽管也曾经是达官贵人的所在,但确实并非王府(原先我也看到有的资料说,郭沫若住的是恭王府,而恭王府的前身就是和珅(1750—1799)的府邸。云云)。那是两个放大的四合院,通过回廊连在了一起。于是中间便有了两个很大的庭院,其中种满了花花草草。
夏天,尽管天气很热,在这样的四合院里,却是非常阴凉的。诗人的卧室很小,一张单人小床,靠床里的墙壁上放着一个二十四史的书柜,床前放着一双布底鞋子。想当年,诗人就是穿着这双鞋子在这个院里走进走出的。
是啊,诗人走了!什刹海的知了仍然在叫!
我这次在北京过的春节,原以为吃了团聚的饺子以后,便可以回江南去了。不料有一种令全世界的人都惊吓不已的疾病,在北京登陆,使北京成了一个人人谈虎色变的危险地区。只要听说你是从北京来的人,便要对你分外地当心,害怕你传染疾病。我也一下子给搞得动弹不得了。我本是好端端的人,一到上海就要被当作隔离对象,据说还要被“圈养”起来,那是我万分不情愿的事情。
我同学请我回去吃喜酒,本来我也兴致勃勃地要回上海的。可也去不成啦!
我小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沈玲丽),当年插队落户去了农村,结婚特早,当我还躲在上海的弄堂里———屋檐下,对卿卿我我的爱情生活抱着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的时候,她已经抱了孩子,在一次探亲返沪的时候,约了另一位女同学(陈美娣)一起来看我了。
前两年翻阅旧书,看见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有我写的字,什么“仰超”啊,“崇复”啊之类的词组,后来我回想起来了,这就是当年的女同学特意抱了孩子来让我起一个名字,她们认为我老是在看书,应该有文化。我便开始瞎想了起来。当时我刚买了一套《饮冰室文集》,还常常阅读严复(1854—1921,翻译家、教育家)的译著,对梁任公(1873—1929,思想家)和严几道真是崇拜得无以复加,才想出上面那两个不伦不类的名字来,最后,我的那位同学当然也没有采纳,因为她搞不懂我为什么老是要在“超”啊、“复”啊当中兜圈子。我向她介绍,那是近代史上的两位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她听我说了,虽然也觉得很应该尊敬那两位前辈,但她觉得跟自己的儿子没什么关系,似乎不必牵涉在一起。
我这个人缺乏想象力,不会取名字,可常有朋友来找我为他们的子女取名字,取了几次,都不见采纳。这样的结果也很伤我的自尊心,但也无奈。研究所时代,也许20年前吧,我有个同事姓“尔”,他跟香港的那位电影演员尔冬升(1957— )是堂兄弟,也找我取名。记得他生了个儿子,我便跟他说,那就单名一个“雅”字吧!“尔雅”是一部古代辞书,知道这个出典的人,联想起来觉得这个孩子似乎学富五车,蛮博学的,没什么不好。不知道的人,只觉得这是一个雅致的名字,也还可以。我跟他说了以后,也不知道他有没有采纳。估计也没有采用,因为后来就不见他提起这件事情了。上海社科院时的朋友金秀才,叫我给他儿子取名,我一下子给了他三个:进士、解元和状元,也不知道他最后取了哪一个名字。
我很佩服写小说的人,他们编的故事情节曲折姑且不论,光凭他能够取出五花八门的人物姓名来,我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啦!不过有的小说,为了使人物带有普遍性的色彩,故意不取名字,或者简化为“符号”:F、K 之类,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那当然不是取不出名字,而是故意不取。我还是从中窥出起名字的困难性来了,因为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带有典型色彩,这取决于作者对于人物塑造的功力,并不在于他有没有名字,或者用不用代号。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对于人物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姓名还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取名字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想不到当年在襁褓中的孩子,如今已经28岁了。这位本来或许要叫做“仰超”或者“崇复”的男孩,在今年的5月要结婚了。他母亲特意打电话到北京来,通知我去上海赴宴。接到电话的当时,我感慨万千,惊诧于岁月如电光火石,一闪而已,怎么已经28年过去了?我答应了她,说你儿子的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的,这是孩子一辈人当中的首次结婚,我一定要去祝贺的。这个孩子如今在一家大公司中任职,跟梁任公与严几道似乎不相干———我也不知道今天的现代化气氛是否就是两位当年的追求,如果是的话,那小朋友便活在两公当年追求的理想国中了。如果不是,那真正毫无关系了。
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他母亲身穿一件蓝色的上装,用一块红丝绸做成的襁褓包裹着婴儿。当时我还在里弄的服务站工作,没法招待她们坐,请她们坐到对面的食堂里去。我趁着传呼一个电话,溜出来,跟她们聊了半天。怎么一下子这个婴儿已经是个成熟的社会人了,居然也要结婚了———我的感慨真是很多!
可是当我买好了车票,隔天就准备返沪的时候,却又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说由于“非典”的缘故,婚宴取消了,你也不必回来了。回来据说还要给扣押!———这对兴冲冲的我来说,不啻迎头泼来了一桶冰水。随后我打电话到上海征求亲朋的意见,似乎都不赞成我的归来。我北京的家人自然不赞成我走,害怕我在途中、车上给传染上疾病。如果我母亲还活着,我可以肯定,她一定毫不犹豫地让我赶快回上海,到她的身边。因为做母亲的永远认为,在自己的膝边才是孩子最安全的地方。
我是在北京两个禁令解除(6月25日)以后,才回上海来的。6月25日那天晚上,我跟小关去王府井大街散步,不料给封路了。正好还有些小雨,我们便随意折了回来。后来看电视节目才知道,原来那天那里在举行庆祝双禁令解除的露天演出活动。
因此整个“非典”期间,我都在北京。在那段日子里,除了学会每天不停地规规矩矩洗手之外,我还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我还开始散步了。不仅仅洗手,也开始练练脚劲儿了。
每天散步,从皇城根遗址公园,一直往前走,走到长安街然后向左拐弯,过了北京饭店,就是王府井大街,有一段路是“步行者天堂”,过了灯市口,才可以通行车辆。刚开始是每天早上出去散步,开始只是走几步路便回来了,可后来越走越远,连晚上也出去了,有时我竟兴致勃勃地走过长安街,到了对面的马路。过街后的直马路叫做“正义路”,而横马路便是大名鼎鼎的东交民巷了。从王府井回来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有名的建筑,比如商务印书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隆福寺、美术馆,灯市口西街上的老舍故居,也是我散步天天路过的。东交民巷那里自然有许多过去的使馆旧址,如今都成了别的机关。有一所法国邮政局的旧房
子,门面非常典雅,如今是一家川菜馆了。走过去几步便是当年的法国大使馆,奇怪的是,并不是洋房,它是一座中国的王府,门口有石狮子,大门很壮观宏伟,每次走过都是晚上,所以也看不清现在是什么单位了。北京的机关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我所住的沙滩皇城根那一带,几乎走几步路,便是一个什么部级的办公大厦。
开始走的时间不多,路也近。后来自己渐渐加码,到最后,我每天一次的散步便有两三个小时之久,如果早上去了,晚上兴致好再出去,也有两个多小时。路程一般是5站路,来回等于10站路左右。刚回上海时,我甚至雄心勃勃准备从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北郊步行到人民广场去呢!
我面前的这条五四大街,历史也很悠久了,我看了一下路牌上的介绍,在元朝的大都(也就是马可·波罗称为“汗八里”的)时期,已经有了这条马路了。踏在这条路上,不难想象790多年前,元朝官兵的肥马从这里风尘仆仆疾驶而过的情形。
朝前走两三步便是故宫的后门,景山公园的前门了。有一天我偶尔往那里走了一圈,也是有所发现的。我发现了京师大学堂的旧址,原来就在我所住的红旗大院的后门。
“非典”期间,我除了散步,白昼的时间用来翻译一部有关人类意识活动的书籍,每天几千个字,等到禁令解除,我回上海的时候,那本书我也翻译完了,20余万字。
一回上海后,各位老朋友便到我家中来聚会。前天,收到W 兄的来信。他就像当年的菊治宽(1888—1948)为《文艺春秋》而催促稿子一样,向我约稿。可是我实在没什么准备,在北京期间,只顾了散步与翻译。现在我一边翻阅我在北京所写的《隔雨望红楼笔记》,一边想从中挑选一些稍微有些意思的话题出来,可惜没有成为正规的学术论文。我原是有学术情结的人,自己做不了学问,却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写出像样的学术文章来。幻想归幻想,W 兄如此催促,我还是只能把一些笔记不加修饰地端出来。我的笔记,几乎也就是日记,基本上是每天读书感想的记录,有时仅仅只是摘录或翻译一些材料,有时则随意勾勒一些大概的思路。
好在我素来没有写过正规的大块文章,别人对我也没有那样的期待。那就再来一次素面朝天吧!
2003年7月26日写于上海北郊一树斋之西窗下
用户评价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思考和探究事物本质的人,所以,《心理学散论(第三卷)》的出现,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及时雨。我之所以如此期待,是因为前两卷已经为我打开了通往心理学世界的大门,并且,它们所提供的见解,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记得在阅读第二卷的时候,关于“自我效能感”的讨论,让我深刻理解了自信心对于一个人达成目标的重要性,并且,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去培养自己的这种能力。因此,我非常好奇第三卷会继续深入哪些新的领域,是否会探讨关于“拖延症”的心理根源,又或是关于“情绪智力”的培养方法。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实践指导,让我不仅能够理解理论,更能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我的生活和工作中,从而实现真正的成长。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够继续带给我那种“原来如此”的惊喜,让我对“人”的理解,又迈进了一大步。
评分这本书我期待了好久,毕竟《心理学散论》前两卷带给我的惊喜和启迪实在太多了。当我拿到《心理学散论(第三卷)》的那一刻,心情是无比激动和好奇的。第一卷让我对人类行为的根源有了全新的认识,第二卷则深入剖析了各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进行一场思想的探险。我总是在想,这一卷又会带我走向何方?是否会揭示更多关于意识、潜意识、情感、认知以及社会互动的奥秘?书中那些引人入胜的案例分析,精妙绝伦的理论阐释,总是让我忍不住反复推敲,甚至会在深夜里辗转反侧,思考书中所探讨的关于“自我”的本质,关于“人性”的边界。我记得在阅读第二卷时,书中关于“认知失调”的章节,彻底颠覆了我对某些行为模式的理解,让我开始审视自己和周围人的决策过程,也更加理解了为何人们有时会做出看似不合逻辑的选择。因此,我对第三卷充满了极高的期待,希望它能延续这份深刻与洞察,为我打开一扇通往更深层心理世界的大门,让我对“为何我们如此”这个问题,有更丰富、更立体的回答。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到这本书的阅读之中,去感受作者的思想火花,去探索那些尚未被触及的心理疆域,去收获属于我的那份知识的馈赠。
评分《心理学散论(第三卷)》的封面设计给我一种沉稳而引人深思的感觉,与前两卷一脉相承,让我对接下来的阅读充满了信心。我一直以来都对人类内在的运行机制抱有极大的兴趣,而这两卷的阅读,已经让我在心理学的海洋里遨游许久,收获颇丰。我记得在第二卷中,关于“习得性无助”的案例分析,让我对一些消极行为的产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开始反思自己在某些困境中的应对方式。我渴望在第三卷中,继续找到能够帮助我更好地认识自己,也更能理解他人的深刻见解。我好奇书中是否会触及“自我控制”的奥秘,或是关于“共情能力”的培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继续给我带来那种“拨云见日”的明朗感,让我能够更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也更从容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扇不断打开的窗户,让我得以窥见更广阔的内心世界。
评分收到《心理学散论(第三卷)》,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仿佛又回到了与前两卷相伴的那些时光。我总是喜欢在宁静的夜晚,伴着一盏昏黄的灯光,静静地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作者的文字有一种魔力,总能轻易地触动我内心最深处的思考。我记得在阅读第二卷时,关于“认知偏差”的章节,让我对自己在判断事物时常常出现的盲点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学会了如何去挑战自己的固有思维。我喜欢这种能够让我不断反思和成长的阅读体验。我期待着第三卷能够继续给我带来这样的深度和启发,或许它会深入探讨关于“动机的深层心理机制”,又或是关于“压力与应对”的有效策略。我希望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更多能够帮助我理解人生百态,提升自我认知的智慧。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纸页上的文字,更是通往内心深处的一条小径,每一次的探索都让我收获满满。
评分当我拿到《心理学散论(第三卷)》时,一种久违的期待感瞬间涌上心头。我一直认为,理解人类的行为模式,是认识世界的基础,而前两卷,已经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尤其欣赏作者在书中对复杂心理现象的拆解和分析,总能让我茅塞顿开。我记得在阅读第二卷的时候,关于“锚定效应”的阐述,让我对自己在购物时的一些决策有了新的认识,也学会了如何去识别和规避这种效应。这种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生活挑战的知识,是我最渴望从书中获得的。我期待着第三卷能够继续拓展我的视野,或许会涉及“睡眠的心理学意义”,又或是关于“人际吸引的规律”的探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继续给我带来那种深刻的启发,让我能够以更智慧的方式去生活,去与他人相处。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我不断反思和成长的催化剂。
评分《心理学散论(第三卷)》的纸张触感和装帧质量都非常棒,让人一看就知道是经过用心制作的书籍。我一直以来都对人类心理的奥秘充满好奇,前两卷也确实满足了我这份探索的欲望。我喜欢作者那种抽丝剥茧的分析方式,总能将复杂的问题变得清晰易懂。我记得在阅读第二卷时,关于“社会认同理论”的讲解,让我对群体行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我更加警惕那些看似合理的集体盲从。我期待着第三卷能够继续深入我的思考,或许会关注“非语言沟通”的微妙信号,又或是关于“记忆的重构与遗忘”的机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顿悟”时刻,让我能够以更敏锐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以更理性的态度去处理问题。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次阅读,更是一次精神的旅行,一次对自我认知边界的拓展。
评分我一直对人类思维的复杂性着迷不已,而《心理学散论(第三卷)》无疑是满足我这种好奇心的绝佳选择。我记得在阅读前两卷时,书中关于“情绪调节”和“动机理论”的章节,曾让我深思许久,也尝试着将书中的理论应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中,效果斐然。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经历一场心灵的洗礼,让我对“我”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我喜欢作者的笔触,总是那么的流畅自然,不堆砌华丽的辞藻,却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我常常在想,书中会不会涉及到关于“创造力”的心理学机制,亦或是关于“学习效率”的更深层次的探讨。我的职业生涯也与人打交道息息相关,因此,对于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他人,改善沟通方式的内容,我总是格外关注。我希望这一卷能够继续提供给我这样富有实践意义的见解,让我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加游刃有余。我期待着书中那些精彩的案例分析,能够再次点亮我思考的火花,也期待着作者能够带我走进更广阔的心理学天地,让我看到更多未曾见过的风景,获得更深刻的领悟。
评分《心理学散论(第三卷)》的外包装就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那种低调而内敛的设计,总能引起我的注意。我喜欢在工作之余,翻开这本书,让我的思绪暂时远离尘嚣,进入一个更加纯粹的心理世界。前两卷已经为我构建了一个相当扎实的心理学基础,我从中学会了如何去观察和分析自己及他人的行为,也更加理解了许多社会现象背后的心理动因。我尤其喜欢作者在阐述一些复杂概念时,所使用的那些生动形象的比喻,让原本晦涩的理论变得易于理解。我记得在阅读第二卷时,关于“依恋理论”的讨论,让我对亲子关系和人际关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开始反思自己在关系中的模式。因此,我非常期待第三卷能够继续在我已有的认知上进行拓展,或许会探讨关于“幸福心理学”的积极力量,又或是关于“时间感知”的奇妙机制。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继续给我带来那种“豁然开朗”的惊喜,让我能够不断地自我完善,也更加善于与他人建立连接。
评分当我捧起《心理学散论(第三卷)》时,一股熟悉的宁静感便油然而生。前两卷如同指引我探索内心迷宫的地图,每一次阅读都让我对“人”这个复杂的生物有了更清晰的认知。我最欣赏的是书中那种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分析方式,它既有严谨的学术逻辑,又不失对人类情感的深刻体察。我常常会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书中的理论与自己的亲身经历相结合,那种“原来是这样”的豁然开朗,是阅读的最大乐趣。我记得第二卷中关于“成瘾行为”的探讨,让我对许多社会现象有了全新的解读,也让我更加理解了某些个体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我期待第三卷能继续带给我这样的深度和广度,或许它会触及关于“社会认同”的微妙之处,又或是关于“决策偏差”的隐秘诱因。我渴望在书中找到更多能够武装我的思想,提升我认知能力的工具,让我能够以更成熟、更包容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能力的提升,一种对生命理解的深化。
评分这本《心理学散论(第三卷)》的封面设计就透着一股沉静而睿智的气息,和前两卷一脉相承,让我瞬间就进入了那种专注思考的状态。我翻开书页,一股淡淡的油墨香扑鼻而来,这种熟悉的触感,总能勾起我过去的阅读回忆。我总是喜欢在闲暇的午后,泡上一杯热茶,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然后慢慢地品味书中的每一字每一句。我常常会被书中那些看似平凡却饱含深意的观点所震撼,作者总是能用一种非常贴近生活的方式,来解释那些抽象的心理学理论,让我觉得心理学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尤其喜欢作者在分析具体心理现象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细腻和敏锐,仿佛能够穿透表象,直达事物的本质。我记得在阅读第二卷的时候,有一个关于“归因错误”的章节,让我对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出现的一些误解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学会了如何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我希望第三卷能够继续给我带来这样的启发,让我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他人,也更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本读物,更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引领我不断探索内心深处的风景。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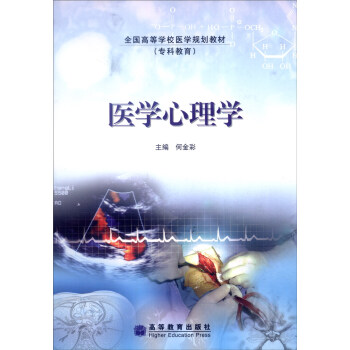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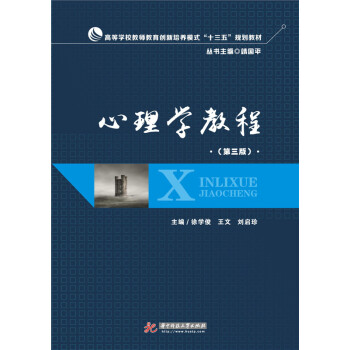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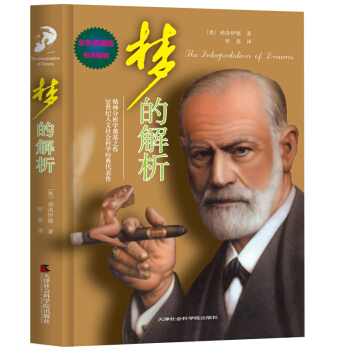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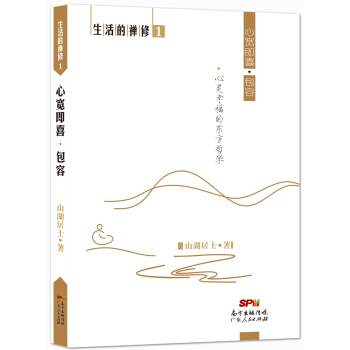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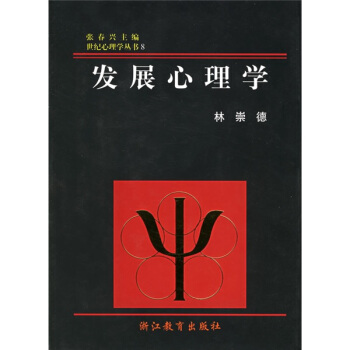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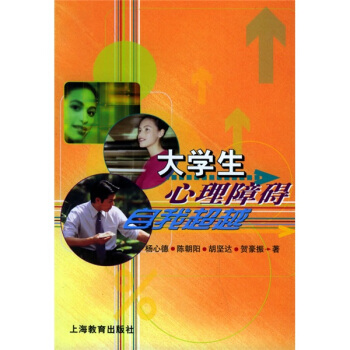
![健康理念卷(中文版) [ENCYCLOPEDIA OF MENTAL HEALT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293100/c72d8be1-ee66-45ea-9724-19e8402eae1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