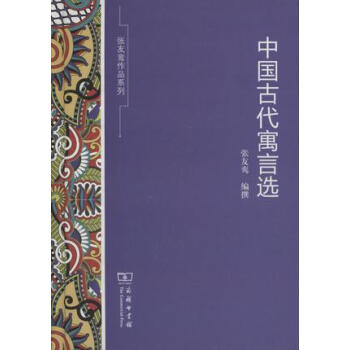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投身出版界数十年,集出版家、评论家、专栏作家多重身份于一身,俞晓群作为一个“爱书、懂书又做书”的出版人,“真懂且爱文化”,他对出版行业的机敏洞见,点滴萃语汇总成“经”,真知灼见俯拾皆是。说人论书,林林种种。同样的配方,新鲜的材料,实实在在的“干货”,亲切有味,开卷有益。 ◎俞晓群搜集两年多专栏文章结为本集,追忆过往为书往事、阅读经验与自身的出版经历,尽抒痴书之爱与出版情怀。内容耐看,掌故纷多,任性敢写。犹如江湖百晓生,逸闻轶事,如数家珍;英雄相见,各显神通,令人眼花缭乱。你可以把它当作做书“秘笈”,看门道;也可以把它当出版八卦,看热闹。 ◎全书搭配特色书影若干,书为图说,相得益彰,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有温度的情怀地图。宛如穿越一条“封面”流变的河流,按图索骥,可让情怀安放在书本之中。 我一直接受那样的观点,即书与其他商品不同,许多时候,它不是越新越好,而是越旧越好,因为新书上市,需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被读者筛选出来的好书,许多年后还有人找、有人买、有人看,往往才是有价值的。 有才华的人总会不安分,跨界的能力常常是才华大小的重要标志。 人生之旅,面上千奇百怪,实则大同小异。智者多思多虑,双成者是有的,如钟叔河先生;多成者也是有的,如叶圣陶先生;一事无成者更是满视野。 编辑要有两支笔,一红一蓝,红笔改书稿,蓝笔写文章。写什么文章呢?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爱好不同,志向不同,所作所为也会不同。内容简介
“我读故我在”源自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我读”和“我思”是对应。 著名出版人俞晓群搜集两年多专栏文章,除后记外共计九十九篇文章,结为此集。全书从出版人、名作者写到媒体人、书装者;从论选题、约稿写到书出版、逛书店。书人江湖,逸闻轶事,皆亲切有味,涉笔成趣。其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出版业细节趣闻,“在场”的记述、特色的点评和解读,无不体现了一个出版人的“书之爱,出版之爱,文化之爱”。作者简介
俞晓群 , 著名出版人。1956年生于辽宁丹东。自1982年从事出版工作至今。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现任海豚出版社社长。主持策划出版“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国学丛书”“书趣书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中国读本》《吕叔湘全集》《傅雷全集》《顾毓琇全集》《丰子恺全集》,主编《万象》杂志。著有《一个人的出版史》《这一代的书香》《那一张旧书单》《精细集》等。内页插图
目录
序:一个“三○后”的想法 沈昌文壹 沈公三书
贰 大侠书话
叁 棔柿楼
肆 梁由之
伍 读陈原
陆 大选家
柒 书装三家
捌 新吕览
玖 十本书
拾 云五扶乩
壹拾壹 郭氏九章
壹拾贰 胡适之师
壹拾叁 蔡元培晚年
壹拾肆 云五高徒
壹拾伍 以书祝寿
壹拾陆 一篇后记
壹拾柒 胡适与出版
壹拾捌 胡适论选题(上)
壹拾玖 胡适论选题(下)
贰拾 云五逸事
贰拾壹 结交老蒋
贰拾贰 脉望四人行
贰拾叁 许渊冲先生
贰拾肆 方豪神父
贰拾伍 书装的意义
贰拾陆 民国童诗
贰拾柒 吹皱眉头
贰拾捌 哪本书最畅销?
贰拾玖 字典的故事
叁拾 米兰·昆德拉
叁拾壹 寻旧之旅
叁拾贰 怪书记
叁拾叁 三张旧书单
叁拾肆 好为人序
叁拾伍 狗官由来
叁拾陆 委婉语词
叁拾柒 精细集
叁拾捌 严复与王云五
叁拾玖 素 王
肆拾 一笑而过
肆拾壹 真皮书
肆拾贰 开 本
肆拾叁 《鲁拜集》问答
肆拾肆 周氏《易》
肆拾伍 张国际
肆拾陆 王志毅(上)
肆拾柒 王志毅(下)
肆拾捌 商务的股份
肆拾玖 伟大的奥玛(上)
伍拾 伟大的奥玛(中)
伍拾壹 伟大的奥玛(下)
伍拾贰 专栏作家
伍拾叁 老丁命题
伍拾肆 老丁再命题
伍拾伍 荐 文
伍拾陆 沈公与静静
伍拾柒 蓝菊花
伍拾捌 敬惜字纸
伍拾玖 独居精神万岁!
陆拾 雅丽纳·鲍曼
陆拾壹 尚书吧
陆拾贰 “三○后”
陆拾叁 “四○后”
陆拾肆 “五○后”
陆拾伍 “五○后”续
陆拾陆 “六○后”
陆拾柒 “六○后”续
陆拾捌 “七○后”
陆拾玖 带雨的云
柒拾 再序眉睫(上)
柒拾壹 再序眉睫(下)
柒拾贰 一群人
柒拾叁 蔡志忠
柒拾肆 拍 卖
柒拾伍 赵启光
柒拾陆 老署长
柒拾柒 杨成凯
柒拾捌 三老集
柒拾玖 冷冰川
捌拾 北赵南陆
捌拾壹 刘忆斯(上)
捌拾贰 刘忆斯(下)
捌拾叁 吴兴文
捌拾肆 海昏侯
捌拾伍 最快的一年
捌拾陆 人书俱老
捌拾柒 食野之蒿
捌拾捌 阅读八问(上)
捌拾玖 阅读八问(下)
玖拾 另类出版
玖拾壹 晓聃书院
玖拾贰 大工匠
玖拾叁 四百年
玖拾肆 百道网
玖拾伍 吉尼斯体
玖拾陆 新一代
玖拾柒 徒 弟
玖拾捌 约 稿
玖拾玖 尾 声
壹佰 后记:点题
精彩书摘
肆拾玖 伟大的奥玛(上) 两年前,台湾出版家吴兴文来到我办公室,他将一本《鲁拜集》放到我手上,引起我出版该书的欲望。尤其是桑格斯基为《鲁拜集》制作的特装版《伟大的奥玛》,它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但我也知道,早在十九世纪,英国就有人叹息:“《伟大的奥玛》啊,总会有厄运相随。”那么,厄运何来呢?我的这一番追随,是否也会遇到厄运呢?下面,容我一一道来: 《鲁拜集》是一本奇异的诗集。他产生于十二世纪的波斯,一位算学家、哲学家奥玛·海亚姆之手。那诗句浪漫而华贵,倾诉着人世间及时行乐的快慰。他轻视神的妄想世界,主张人要自由自在地生活。结果海亚姆的放荡不羁惹怒了教会,认为那是一些“亡命之诗”,文字像蛇一样邪恶,充满了罪恶感。海亚姆感到了生命的威胁,他来到麦加,向神祷告,决心不再写那样的东西。 其实也不必再写了,现有的存在,已经决定了奥玛的伟大!尤其是十八世纪,又一位伟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出现。他发现波斯文化中海亚姆的诗集,并且将它们译成英文。菲氏翻译不单是再现,更是伟大的再创作,一个“死亡与享乐的混合物”,随着优美的诗句流淌出来,《鲁拜集》很快引人关注,吸引着艺术家们蜂拥而至,画家为它画插图,装帧家为它做版式,出版家不断推出各种版本。 二十世纪初,英国最优秀的装帧设计家桑格斯基,同样没能逃过《鲁拜集》的诱惑。他深深迷恋波斯的艺术风格:浓密的藤蔓盘绕,紫色葡萄的醉意,低垂着长长羽毛的孔雀,羽翎上闪亮的斑点,不就是人们梦中的满天星斗,或魔鬼的笑意么?桑格斯基一生追求,要把它们刻画到《鲁拜集》封面上。他先做一只孔雀的版本,羽翎镶上宝石;再做两只孔雀的版本,版面镶满宝石;当他做到三只孔雀时,装帧艺术的表现,渐臻登峰造极,每一颗宝石的色泽与镶嵌,都有了生命的感觉,一块块真皮拼接的画面,像上帝创造女人皮肤一样,不断走向极致!此时,艺术已经化为一种诱惑,让桑格斯基与波斯人思想吻合……我想象,每当夜幕低垂时,每一块宝石,都是一只魔鬼的眼睛,闪啊闪,五光十色。天堂中的那一条蛇也来了;还有一把波斯古琴;还有一个白森森的骷髅头,被镶嵌在书的封三上:断落的牙齿,深陷的眼窝,原本恐怖的存在,四周却铺满妖艳的罂粟花! 英国人为桑格斯基的《鲁拜集》——《伟大的奥玛》陶醉!美国人立即开出八百英镑高价购买。但是,当奢华走向极端时,上帝惊动了,天使与魔鬼都来围观。厄运像梦中的微风一样,无声无息,悄悄降临:去美国拍卖,由于税收的争议,未能入境;回英国拍卖,遇上经济危机,只以四百多英镑卖给美国人;书被装上去往美国的邮轮,又赶上工人罢工,邮轮停运;最终这本《伟大的奥玛》,被装上那艘著名的泰坦尼克号;几天后,书随着大船沉入海底;三个月后,设计者桑格斯基为了救人,也不幸溺水身亡,时年只有三十七岁。 船沉了,书落入海底,桑格斯基也去了。就这样,一点点积小厄成大厄,常言“自古才命两相妨”,真是这样么?谁知道呢!关键是《鲁拜集》的诱惑还在,厄运还在继续相随。 伍拾 伟大的奥玛(中) 桑格斯基去世之后,他的合作伙伴萨克利夫,收藏好桑氏留下的烫金版、黑白玻璃板底片和设计图样,不再做《鲁拜集》。但他两年后制作济慈的《诗集》,封面嵌满珠宝,以一千四百英镑售出。十年后,他拍卖一百二十多本昂贵的书,大多被美国人购买。 此时,萨克利夫的侄子斯坦利·布雷来到公司学徒,大约十年后,他偶然在公司保险柜中,发现那本《伟大的奥玛》原始资料。布雷知道桑格斯基的悲剧故事,他在好奇心驱使下,打开了那个“所罗门的铜瓶”。艺术的幽灵飘荡出来,迅速占满布雷的身心。即使他知道父辈们的告诫,那本书一直有厄运相伴,布雷还是在命运之神引导下,决心按照这些资料,将泰坦尼克号上那本《鲁拜集》再现出来。他瞒着叔叔,利用业余时间,在家中整整做了七年,终于再现了那本《伟大的奥玛》。 三只孔雀,一千零五十颗宝石,精致的工艺,几乎与桑格斯基的手艺分毫不差!见过的人,都会惊呼:“My God!”是啊,我的上帝,接着“二战”爆发了!德军的炮火,炸毁了安放那本书的银行,在高温之下,收藏在铁箱中的《伟大的奥玛》,纸张化为灰烬,羊皮封面化作黑乎乎的一团,只有一颗颗宝石还在。布雷忍着悲伤的心情,将它们挑拣出来,他是一个极其坚强的人,绝不会向厄运低头。果然在他人生旅途的最后几年,他又用那些宝石,再次装点出一本《伟大的奥玛》,现存于大英图书馆中。 时间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二十几岁的英国青年罗勃·谢泼德开始学习书籍装帧艺术。历经二十几年,他见过许多珍贵的经典书籍,但罗勃还是最崇拜当年桑格斯基设计的《伟大的奥玛》。此时的欧洲,布雷等前辈纷纷离世,传统书籍装帧行业已经衰落,罗勃却出手阔绰,收购了几家百年老店的品牌和遗存资料,其中就包括桑格斯基那家公司。那么,罗勃是靠什么财力来支撑自己这样的举动呢?前些天我们请罗勃来中国做讲座,与他聊到这个话题,罗勃只是说,这确实是富人做的事情。从他的言谈中,可以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一直陪伴他的杨小洲觉得,罗勃是一个“富二代”,他本人生活讲究,注重细节;他父亲是生产威士忌的老板,很支持他的艺术追求。二是罗勃是一位欧洲古旧书鉴定专家,在中国做讲座期间,他曾经对两本《鲁拜集》进行鉴定,所言分毫不差,甚至能说出,某个版本是在哪个书店买的,哪家书店仅存一本云云! 言归正传。上面说到罗勃收购桑格斯基的公司,不久,当年布雷打开保险柜,看到《伟大的奥玛》制作文件时的那一幕,又在罗勃身上发生了!结果,罗勃也毫不犹豫地打开“所罗门的魔瓶”。不过这一次,他没有急于再造那本《伟大的奥玛》,而是运用电脑技术,将那些一百年前的黑白照片加以分析、涂色,最终将那本书金碧辉煌的封面,又完完整整地再现出来。 本世纪初,在翻阅资料的基础上,罗勃写出一本书《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为了怀念前辈,罗勃的书采取复古的主题:他专门铸造铅字,沿用传统的铅字印刷;书中的彩图,采用特殊纸张,另行印制,然后手工粘贴在书页上;正文的字体、印刷油墨、纸张出处等等,都有说道。这本书的纪念版仅印一千册,编号在欧洲与美国上市,凡购买者,随书赠送一张图画,就是罗勃用电脑再现的那张《伟大的奥玛》封面,对开本原大! 伍拾壹 伟大的奥玛(下) 时间来到二〇一四年十月,两位中国人来到伦敦一家书店,其中一位叫吴光前,另一位叫杨小洲。他们受我之托,调研欧洲书籍装帧现状,顺路了解一下那本《伟大的奥玛》。 话说此前,我从董桥文章中,知道一些泰坦尼克号上那本《鲁拜集》的故事,若隐若现,愈发激动了我的好奇心。小洲是艺术家,他的艺术冲动与单纯,在今日世俗社会中,已不多见。几年中他设计出版几本“山寨”西方书装的书,极具奇思异想。他知道我对《鲁拜集》等西书装帧有兴趣,大为兴奋,不提任何要求,一定要加盟进来;我也为他的热情与才气感动,一定要他进来加盟。于是有了上面伦敦书店那一幕。 两位推开店门,还未开口,迎面看到,一张对开本展开的封面图片——《伟大的奥玛》!这这这……小洲一时激动,有些眩晕。立即开口要买,店员说:“不卖。”问:“为什么?”店员拿出了罗勃·谢泼德《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一书说:“买这本书,可以赠送此画。”那书是编号、签名、八开本,全书不足百页,薄薄一册售二百英镑。无奈,他们只好买下书,小心翼翼地将那幅封面画装入画筒中。记得两位回国后,进入我办公室,先将那个画筒递上来,我后来想,他们当时一定想说,花二百英镑买了一幅《伟大的奥玛》的封面画,附赠一本书!大幅的封面铺开,几乎覆盖了整个茶几,一眼望去,确实让人大呼惊艳。但是,当我们平静下来,细细翻读罗勃的书之后,再度受到震动。我们一致承认,罗勃不愧为西方传统书籍装帧大家,他的那本书,从内容、材料到印装,实在地道好看,是我们这些同道需要追随的楷模! 于是小洲开始与那家书店联系,寻找罗勃,联系版权。从去年年底启动,小洲率领他的夫人兼翻译,还有出版社曹巧丽等人,经过两个多月忙活,总算把书做出来了。我又提出,三月请罗勃来中国做讲座、签售,就讲《伟大的奥玛》的故事。结果又一阵忙活,罗勃答应会来,时间定在三月十八日,在北京、上海两地做讲座。时间一天天逼近,我们的宣传一点点升温,到了罗勃上飞机的那一刻,我与几位同事还击掌相庆,认为万事俱备,只等明早接机。正在此时,小洲接到罗勃用手机发来的邮件,他因为没办签证,无法登机! 这这这……此时小洲再次感到眩晕,血压也升上来。无数胡思乱想,一并涌上心头。难道是我们动静太大,又引来天使与魔鬼的围观?难道是罗勃骗了我们,他不是跨国公司的老总,不然他怎么会不知道要签证呢?难道他平时回复邮件很慢,不是因为很忙,而是在拖延?接着小洲自己的那本小书《伦敦的书店》出版,也遇到麻烦,迟迟难以上市;这边我们还要忙着推掉一切活动安排,向合作伙伴说抱歉,说好话,说罗勃还会再来。我心中暗想,难道那传说中的厄运,真的尾随而来? 结果到了愚人节前夕,罗勃终于来了。老先生六十三岁,每天睡五个小时,依然精神抖擞地工作。在中国的三天时间里,他在复旦大学、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外文局做了三场讲座,签了一千多册书,还在临行前观光故宫两个小时。我们交流顺畅,谈了很多极好的意向。最终我问他:“我们可以联手制作中文版《伟大的奥玛》么?做此事,会有厄运伴随么?”他笑着说:“当然可以。当然不会有厄运,制作《伟大的奥玛》的布雷,就活到九十几岁!” ……前言/序言
序
一个“三○后”的想法
沈昌文
我生于一九三一年,是个十足的“三○后”。我具有“三○后”的种种特色。
像我这种“三○后”,最痛恨的是当年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亲眼目睹那时的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蒋经国、王云五……在我们那时的眼里,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长大以后参加出版工作,不久就碰到胡适思想批判。那时我还没有资格做责任编辑。但眼看批判他的文集一本一本出来,相信这胡某肯定是个大坏人。那套书的编辑刘大哥,中午共餐时常给我讲些故事,让我长些知识,是我的一位恩师。一天他说起这套书要改用三联名义出书,我听了莫名其妙,不知上面究竟有什么意图。因为那时用三联名义出的书都是低人一头的。
改革开放以后,开始慢慢懂得,对事情要全面分析。我们当然不应该把过去认定的坏人坏事都变成好人好事,但好者未必一切都好,坏者不是一切都坏,都要一一具体分析。
我说过,帮我具体认识王云五功过的是俞晓群。我退休以后,在他的领导下,编印“新世纪万有文库”,便使我好好地学习一下王云五。我于是懂得,五十年代金灿然前辈他们把“一划二垂三点捺”改为“划一垂二点捺三”,有其高明之处,也有不足之处。
晓群兄现在把对民国出版史的研究逐步扩大,他这位“五○后”的这种研究路径我非常欢迎。
还顺便说说,俞晓群现在关于出版史研究的种种构想,我以为都根源于他在二○一二年说过的一句话:“文化是出版的终极目的。”为这句名言,我这“三○后”甘愿当他这“五○后”的“粉丝”。
二○一六年五月
用户评价
翻开这本书,与其说是在阅读文字,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精神的远足。我没有期待它会带我穿越时空的隧道,去亲历某个历史事件,也没有奢望它会揭示某个未解之谜的答案,抑或是描绘一个波澜壮阔的史诗。然而,它却以一种极其微妙的方式,拓展了我精神的疆域。每当我沉浸其中,仿佛就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引力,将我的思绪拉向更广阔的未知。 它并非提供了现成的地图,而是点燃了我内在的探索之火。我开始对那些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产生好奇,开始质疑那些被奉为圭臬的真理。这种质疑并非出于叛逆,而是一种对更深层理解的渴望。它让我意识到,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构建和解构的过程,而“我”的存在,正是这个过程的核心。 书中并没有直接的叙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它却在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力量,一种能唤醒潜藏在每一个读者内心深处思考的能量。它让我开始思考,是什么构成了“我”?是我的思想?是我的经历?还是某种更难以捉摸的存在?这种对“我”的追问,虽然没有直接的答案,却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盈和立体。
评分这本书,简直就像是在我的灵魂深处埋藏的一颗种子,虽然在翻阅它的过程中,我并没有直接读到某个具体的故事,没有遇到某个鲜活的人物,更没有跟随作者的脚步去探索某个遥远的地方,但它却在不经意间,一点一点地渗透我的思维,改变我对世界的看法。有时候,我甚至会怀疑,我之所以会产生某个灵感,会领悟到某种道理,是不是就因为这本书的某种“气息”在悄悄地引导我? 它不像那种会直接给你答案的书,更像是一个永恒的提问者,不断地在我脑海里激起涟漪。我常常会在读完一页,甚至只是读过一个词之后,就陷入沉思,开始反复琢磨作者想要传递的那种“在”的意义。这种“在”,并非指物质的存在,而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觉醒,一种对自我存在的深刻认知。 它让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审视那些被社会灌输的价值。它不是在讲述“我读到了什么”,而是在引导我思考“我因此成为了什么”。这种体验是如此独特,让我觉得,这本书并不是用来“读”的,而是用来“感受”和“体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内心深处那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让我开始与那个更深层次的自我对话。
评分这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与其说是在“读”它,不如说是在“养”它。我没有从中找到任何具体的故事线索,也没有遇到过任何可供描绘的角色。然而,它却在我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慢慢地生根发芽,长成一棵参天大树。它不是那种能让你一口气读完的读物,反而更像是那种需要你反复咀嚼,细细品味的陈年佳酿。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有新的感悟,仿佛拨开一层又一层的迷雾,看到更深层次的含义。 它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我”这个概念,不再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将其看作是与整个世界紧密相连的存在。它让我意识到,我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思考,都是与宇宙的宏大叙事息息相关的。 这种感觉是如此的奇妙,让我觉得,这本书并没有提供任何“内容”,但它却赋予了我一种全新的“视角”。它让我学会了从更宏观的角度去理解生命,去理解“我”的意义。它不是在告诉你“读了什么”,而是在让你思考“读了之后,你变成了什么”。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是深刻的,也是持久的。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汲取知识,不如说是进行一场灵魂的洗礼。我并没有期望它会像百科全书一样,塞满各种具体的知识点,也没有指望它会像小说那样,讲述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然而,它却在无形中,重塑了我对“存在”的理解。每一次翻阅,都像是在与一位沉默但充满智慧的长者进行对话。它不直接给出结论,而是抛出一个又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让我陷入沉思。 这种“思考”的过程,才是这本书的核心价值所在。它引导我去审视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生活片段,去反思那些被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它让我意识到,“我”的价值,并非取决于我做了多少事情,而是取决于我是否真正地“存在”着,是否能够深刻地体悟到这份“存在”的意义。 它就像是一面清澈的湖水,映照出我内心最真实的样子,让我开始审视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东西。我开始理解,真正的“我”,并非由外界的评价所定义,而是由内在的觉知所塑造。这种觉知,是独立于一切外在因素而存在的,是最为纯粹的“我”的体现。
评分我必须承认,在接触这本书之前,我对于“阅读”的理解,还停留在获取信息的层面。我总觉得,一本书的价值,就体现在它所包含的那些具体的故事、知识或者理论。然而,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它并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可以直接拿来引用的内容,也没有描绘任何鲜活的场景。但是,它却像一股清泉,涤荡了我长久以来关于“自我”的认知。 它让我开始质疑,我们所认为的“我”,究竟是什么?是那个不断在外界环境中塑造的形象,还是某个更深层的、不为外物所动的本质?这本书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它引导我去探索,去感受,去体悟。 仿佛作者是在为我搭建一座桥梁,而我需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过去,去领略彼岸的风光。这种“自己去探索”的过程,虽然没有具体的“内容”可言,但却让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满足。它让我明白,真正的“我”,并非被动地接受信息的载体,而是主动地创造意义的主体。这本书,就是这样一本,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属于自己的“我”的书。
评分,,,,,,,!!!!!!!
评分好书
评分因为在京东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订单,所以统一回复,很好!!
评分因为在京东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导致积累了很多未评价的订单,所以统一回复,很好!!
评分关于书的书,好好看看。
评分很好很好非常好,喜欢喜欢很喜欢
评分感谢京东的优惠
评分京东正版,传世之作,值得珍藏~~
评分好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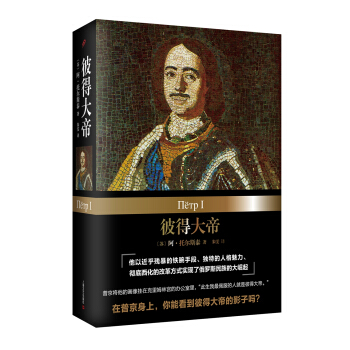
![想象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Imagin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16132/57b2ce43Nb5700382.jpg)


![兔子坡(全彩插图新译本)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084668/584a219dNbfe194d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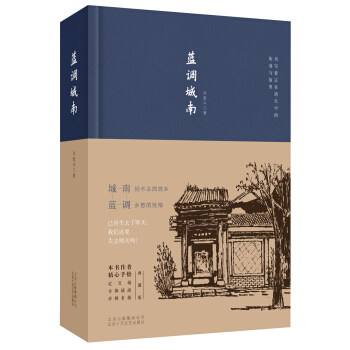






![曹文轩典藏拼音版:愤怒的哇哇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75316/59293a13N139fb7f4.jpg)
![世界少年文学精选·名家导读本:雾都孤儿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85499/53a7a30dN3e8f7ee5.jpg)
![中国名家名作少年儿童文学阅读:冰心儿童文学精选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68926/56a1cb83Na67d6ca1.jpg)
![世界儿童文学精选:格列佛游记(拼音美绘本)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570641/55826891N406b324e.jpg)
![拉封丹寓言 [3-6岁] [La Fontaine Fabl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55659/54f57a4eN91beca8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