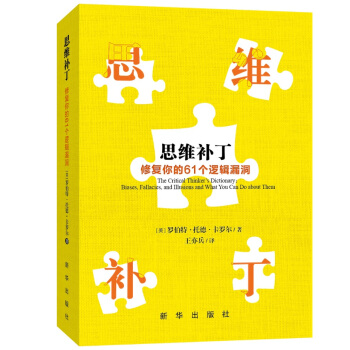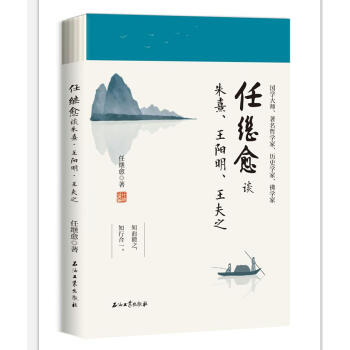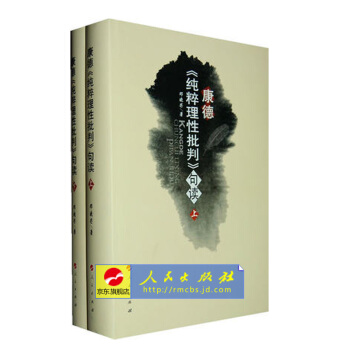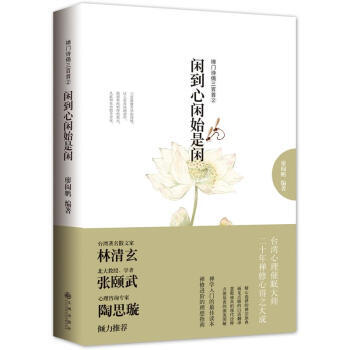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古代经注(卷三)》汇集了古代(公元1-8世纪)非常富有盛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安波罗修、奥古斯丁、俄利根、德尔图良等)对古代经典的解说和诠释,这些注释经由多位专家学者耗费数十年,从浩如烟海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中挑选整理翻译出来,真实反映了西方古代社会和思想的原貌,再现了古代的经文辨析和释经传统。内容简介
古代经注丛书由多位学者集十数年的精力编辑校订而成。本卷收录了包括奥利金,哲罗姆,希波的奥古斯丁,德尔图良,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内多位中世纪大思想家对《圣经·旧约》中《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和《创世记》一起,通常被称为《摩西五书》)的释文,时间跨度从公元二世纪到八世纪。释文除了取自耳熟能详的著作之外,还取自各种讲道集,书信集等等,涵盖了大量中世纪作者和作品。此书的出版将对圣经研究,中世纪哲学和宗教思想的研究提供崭新的资源和材料。书后附有大量的目录文献,可资读者做进一步研究查考之用。《古代经注(卷三)》的体例为,先列出圣经原文(中文本分别列出《和合本》及《思高本》相应的译文),然后在原文之下列出各位教父对本段经文注解。书后列出详细的关键词索引,每一位教父的生平和主要著作介绍,以及教父活跃的时间轴图表。对研究者相当有意义和参考价值。相信本书出版后,可以为圣经研究,基督教会史,以及中世纪哲学研究等等学科领域引入新的思想资源和参考资料。
作者简介
总主编 托马斯·奥登(Thomas C. Oden),美国新西泽州麦迪逊德鲁大学教授,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哲学、基督教神学等,已出版20多部重要学术著作。本卷书由美国福德汉姆大学的神学系教授约瑟·林哈德主编辑录,林哈德教授目前担任福德汉姆大学中世纪研究课程的教席。
丛书的中文版主编 黄锡木,南非普勒陀利亚大学文学博士,主修希腊文,并曾为美国俄利根大学访问学者,是资深的神学教育工作者,中英文编著逾半百。本卷编审黄嘉樑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圣经科副教授。
翻译者 吴轶凡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经济学学士
目录
《古代经注》╱1英文版丛书总序╱1
使用指南╱3
缩写表╱7
自出埃及记到申命记的导言╱1
注释
出埃及记╱1
利未记╱229
民数记╱287
申命记╱381
附录
本书引用的早期基督信仰作家和引用的文献╱475
教父生平概述及佚名作品简介╱486
图表
人物及佚名作品时间图表╱517
参考书目/525
索引
作者和作品索引╱541
主题索引╱543
中文索引╱555
圣经经文索引╱562
精彩书摘
自出埃及记到申命记的导言从基督教会诞生的第一天,即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开始,基督教会已经有了一本圣经──也就是犹太人的圣经。但是,基督徒并不按犹太人诠释圣经的方式来理解这些书卷,而是根据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作为来解释圣经。因此,基督徒看这部圣经不如犹太人那样;犹太人认为律法书(Torah)具有绝对的权威,但对基督徒来说,基督是最终的权威。
最早的基督徒是一些归信基督的犹太人。他们在犹太圣经中,找到了证明他们新信仰的确据。例如,马太福音开篇的几章经文,以及约翰福音在描述耶稣受难而死的章节中,都再三引用旧约;并加以解释说,“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语”。
然而,对基督徒来说,这本圣经并非十全十美。他们在犹太圣经里发现几十处经文,可以看作是关于基督的预言,甚至是对基督一生中某件事情的预言。但是,这些经文只占旧约圣经的一小部分。在基督徒看来,大部分的旧约经文与他们没有关系,尤其是五经中的仪式律例,更是篇幅冗长。至于其他部分,他们认为仍然有一定的价值:诗篇很快便成为基督徒的祷告手册;历史书阐述义人得奖赏,恶人受惩罚,其中的例子启迪人心;智慧文学包含道德教训,可以用来教导愿意归信基督的异教徒;先知书常常斥责犹太人的形式主义,这也正是耶稣所做的。
尽管如此,有关圣经的难题仍然没有解决。新的教会究竟应当在甚么程度上将犹太圣经视作上帝的道呢?保罗曾经警告基督徒,不要回到犹太人解释圣经的老路上,所以至少有一部分的旧约经文,不能再根据字面来理解其中的含义。
早期基督徒对犹太圣经持三种不同的基本态度:圣经是律法;圣经是预言;圣经对基督信仰没有意义。保罗勇于面对圣经的难题,他的态度最激进:旧约圣经的确是律法,是上帝的律法;这律法本是良善的。但是,律法只是暂时的,借着恩典,律法已被基督取代。希伯来书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旧的约再三重复律法,可见律法本是不完全的,惟有在基督里,这律法的的确确得以完成并且实现了。相比之下,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以及其他早期基督徒作品,比如游斯丁的《护教书》,则将旧约视作预言。第三种可能性就是,犹太圣经似乎对基督信仰完全没有意义。这种态度在新约的若干书卷中有所暗示,它们从未引用“圣经”。一些基督徒作家,如安提阿的伊格那丢的作品中,这种态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基督徒对犹太圣经的态度有所转变。最早的基督徒是犹太人信徒,他们早已接受犹太圣经,而后又从犹太圣经中发现他们对基督信仰的确据。后来的基督徒是从异教归信基督的。他们首先接受对基督的信仰,然后才面对深奥难懂的犹太圣经。这种情况最终引发了一场危机,确切地说,是一场圣经诠释的危机。
在这场有关圣经诠释的危机中,出现了两种最极端的诠释方法,分别见于西奴泊的马吉安(Marcion of Sinope)的作品和《巴拿巴书信》,两者的成书时间都在140年左右。
马吉安主张根据字面来理解圣经,并且只认定字面的含义。他认为,圣经的每一个词语都具有真实的字面含义,而且只有字面的含义才是真确的。犹太圣经将上帝描述成无知的上帝,祂不知道,所以才问亚当:“你在哪里?”这位上帝出尔反尔,变化无常。祂先是禁止摩西雕刻偶像,后来又吩咐他制作蛇的形像。祂优柔寡断,像摩西这样的凡人也可以说服祂改变主意。更有甚者,犹太圣经竟然声称上帝会后悔。祂还是一位邪恶狠毒的上帝;祂下令实行可怕的大屠杀,连妇女和婴孩也不放过。马吉安认为惟一可能的结论就是,教会必须摒弃这些圣经经卷,因为它们与耶稣基督的圣父,那位慈爱的上帝完全不相配。
《巴拿巴书信》的作者则持相反的看法,他完全只用寓意的方法来理解犹太圣经,并且下结论说,犹太人从未明白圣经的含义。他的理论是,从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十诫,到他下到山脚,摔碎法版为止,上帝和犹太人所立的约只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效。后来,一位邪恶的天使来到犹太人中间,引诱说服他们从字面来解释圣经。
简而言之,马吉安只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圣经,结论是教会必须抛弃犹太圣经;巴拿巴只用寓意的方法解经,结论是教会必须脱离犹太会堂对圣经的理解。
但是,教会既排除了马吉安的主张,也没有接纳巴拿巴的理论。最终,教会决定维持犹太圣经的原貌,同时认为这些圣经经卷在某些方面具有双重的含义。圣经具有真实的字面含义:上帝的确向古代的族长显现,并借着众先知说话;上帝的确曾与以色列立约。然而,基督赐予基督徒一把新的钥匙,让他们用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些古老的圣经经卷。字面的含义不再是惟一的含义。在基督的亮光中,这些古老的圣经经卷揭示出更深刻的意义。
里昂的艾雷尼厄斯构建出一个理论来解释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创下了先河。在艾雷尼厄斯的时代,即公元190年左右,教会已经明确要设立一部新约──也就是一套由基督徒撰写的圣书结集,与犹太圣经具有同等的权威。与此同时,犹太圣经被称为“旧约”;尽管艾雷尼厄斯没有采用这个词语。在艾雷尼厄斯看来,整个救恩历史好像一个椭圆,围绕着两个焦点:亚当和基督。旧约和新约构成了一幅壮观的图画:从亚当开始,人类堕落离开上帝的恩典,直到在基督里面才同归于一,有新的开始。
虽然有了理论,但教会仍然缺少相关的实用工具,就是一套基督徒对旧约圣经的逐卷注释。罗马的希坡律陀(卒于公元235年)首先尝试填补这个缺欠。他对但以理书的注释是现存最古老的基督徒旧约书卷注释。他还撰写了其他一些注释,大部分已经散佚;大概这些注释对当时的基督徒帮助不大。
奥利金(约公元185-254年)确立了旧约在基督教会中永久的地位。为此他写了大量的圣经注释和几百篇讲章,几乎涵盖所有的旧约书卷。从奥利金的时代开始,基督徒建立了旧约的释经原则;圣经注释作品和讲道集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一个文库,供人查阅。后来,许多解经家不认同奥利金的看法,甚至反对他的解经方法。但是,我们说奥利金对教会释经史有深远影响,亦绝不为过。奥利金的大部分作品已经散佚,我们无法全面检视他对其他作家,尤其是希腊作家的影响。奥利金存留下来的作品,大部分是拉丁文的译本。安波罗修、哲罗姆和其他许多教父都在相当程度上借镜奥利金的作品,有时他们过于倚赖奥利金的注释,以致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几乎就是对奥利金原文的翻译。
艾雷尼厄斯和奥利金为解释旧约圣经的理论和实践奠下了基础。犹太圣经成为基督信仰的旧约,惟有借着基督的亮光,才能完全理解犹太圣经的意义。这是以信仰为基础的解经原则,而这信仰亦在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信经(Creed of Constantinople)中得到确定。在君士坦丁堡信经中,基督徒承认“基督照圣经所说,在第三日复活”,并承认圣灵“曾藉众先知说话”。后面这句话说明教会最终摒弃了马吉安的说法,确定是上帝独一的圣灵,用同一个声音,在新约和旧约中说话。
理论和实践都有了,然而前面的任务依然艰巨。教会需要带着信心和盼望思考上帝的道,更完全地理解圣灵藉众先知所说的话语。
教父读的是旧约的译本,至少那些说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父是如此。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称为《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简称LXX)。这个名字起源于一个传说。照犹太人的说法,有七十位长老把律法书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照基督徒的说法,他们把整部旧约都翻译成希腊文。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确有一批不知名的犹太翻译者将犹太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堪称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翻译项目。在翻译的同时,他们也把犹太圣经转变成另一个思想模式的语言。希伯来文具体的表述变成了抽象的希腊文概念;其中最关键,或者说最贴切的翻译,是在出埃及记三章14节,翻译者把希伯来文“我是自有永有的”这句短语译成“我是那自有永有的”,由此为希腊人对上帝即“存在”之本的苦思开辟了出路。但是翻译也带来了重大的改变:希腊人认为存在是中性的,而犹太翻译者使用了男性的词语,这就表示虽然犹太圣经中的上帝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存在之本,但这位自有永有的上帝,远远超出了希腊人的想象,祂是有位格的。
《七十士译本》是早期教会最主要的圣经译本。奥古斯丁等教父认为,《七十士译本》和希伯来圣经同样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当然也有教父持不同的意见。众教父还知道其他一些希腊文译本,也都是犹太人翻译的。当基督徒接纳《七十士译本》为他们的圣经后,犹太人却舍弃这个译本,认为它太偏向意译。《巴比伦他勒目》有这样的评论:“在多利买王(Ptolemy)的要求下,五位长老把五经翻译成希腊文。这一天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痛苦的日子,就好比造金牛犊的日子那样,因为他们无法准确地翻译五经。”此后,犹太学者又提供了至少三个希腊文译本,每一个都比《七十士译本》更忠于字面意义,其中至少一个译本太过于直译,以至于几乎读不懂7。
如果说《七十士译本》是一部由不同翻译者的作品组成的结集,那么所谓的《古拉丁文译本》就更加复杂了。从二世纪末开始,拉丁语基督徒开始将《七十士译本》逐卷译成拉丁文。一些翻译者对希腊文的掌握尚未炉火纯青,少数翻译者不太精通拉丁文。尽管如此,直到五世纪为止,许多的拉丁文旧约圣经注释都是以《古拉丁文译本》为依据的。这个《古拉丁文译本》也就是《七十士译本》的拉丁文译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部由许多译者的作品组成的结集。
拉丁语基督徒也留意到这个问题。384年左右,圣哲罗姆开始对拉丁文圣经进行修订。经他修订后的拉丁文圣经被称为《武加大译本》(Vulgate),其中一部分是对希伯来圣经和(新约)希腊文圣经的重新翻译,一部分是对从前译本的修订,另一部分则未经哲罗姆的处理。从四世纪末开始,直到九世纪,《武加大译本》逐渐取代《古拉丁文译本》,成为西方拉丁语世界的标准圣经。
与此同时,犹太人致力于保存圣经的希伯来文本。在五至九世纪之间,马所拉学者(Masoretes)编订了一个最终的希伯来文本。一些现代的圣经译本,譬如《修订标准译本》(RSV),都是以这个希伯来文本为底本的。但是,我们不能过于简单,以为马所拉经文(Masoretic text)一定比《七十士译本》好;其实,这可说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首先,《七十士译本》显示了古代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文本的理解。有时候,《七十士译本》所反映的版本比马所拉经文更古老,更接近原来的文本。看看《修订标准译本》的脚注,就会发现马所拉经文存疑的经节为数不少,为了重整经文的意思,《修订标准译本》借用了希腊文译本及其他版本的圣经。
从实际的角度来看,就这本古代基督信仰的圣经注释书来说,可以有这样的结论:当教父诠释圣经的时候,他们采用的圣经文本不外乎这三种:《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古拉丁文译本》和《拉丁文武加大译本》。在某些情况下,他们采用的文本比《修订标准译本》更接近希伯来文本圣经。总而言之,众教父都是对自己所用的圣经版本进行注释,并且我们应当相信,他们是严谨地按照这些文本来诠释圣经的。
几乎在教父的所有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他们对圣经的注释。我们很难找出有哪一部早期教父的著作,其中没有引用圣经的话语,或是对圣经的解释。
在诠释圣经的文学作品中,讲章和注释是两种最常见的体裁,前者是讲坛的作品,后者是研经的作品。另一种用来解释圣经的文学体裁是希腊哲学家熟悉的问答式文体8。很少有教父专门为五经中某一卷或某几卷书撰写连贯的注释,而这少数的作品与现代的圣经注释也不尽相同。具体来说,现存有关五经的早期教父作品出自七位教父,包括四位拉丁教父,三位希腊教父。这些作品对圣经经文的注释并不平均,这几乎是必然的。我们很轻易就可以收集厚厚一本早期教父对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注释,相反,对于那些列举名字或单单记载详细仪式律例的章节,教父的注释很少,甚至没有注释。教父对圣经经文的注释不平均的情况,必然在这本注释书中有所体现。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希望看到的是一种超越传统注释学范畴的创新。市面上关于古代经典的注释本汗牛充栋,真正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那些敢于挑战既定范式、或者开辟了全新研究方法的作品。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对待那些已经被前人反复解读,被视为“定论”的部分的。他是否提出了新的证据链,或者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诠释了这些经典?如果只是对已有成果进行整合和润饰,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涉猎过相关领域的人来说,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我期待的是那种能够激发我重新审视自己既有知识结构的“智力冲击”。这本书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哪怕只是在某一个章节、某一个细微的注脚中,展现出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么它在我心中的分量,就会远远超过其厚度本身。
评分从阅读的整体感受来说,我更看重的是作者在构建整体框架时的宏大叙事能力。这部书涵盖了公元一到八个世纪的漫长历史,这段时间恰逢帝国兴衰、宗教更迭的剧烈动荡期。因此,经注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的考据上,更需要与当时的政治、社会、乃至地理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立体化的解读。我希望作者能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这些注释文本是如何在特定历史压力下被塑造和选择的。例如,某个重要的教义注释,是否受到了当时宫廷权力的影响?某个哲学术语的流行,是否与新的贸易路线开辟有关?如果本书能将文本的微观分析,成功地嫁接到宏观的历史变迁中去,形成一种有机的整体,那么它就超越了一般的文献汇编,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层面。
评分这部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那种泛黄的纸张质感,配上古朴的字体排版,瞬间就把人拉回了那个遥远的时代。拿到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翻开看看里面的内容究竟如何。当然,作为一名对古代文献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我最期待的还是那些深邃的文本解读。我希望能看到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脉络有一个清晰的梳理,尤其是在公元一到八世纪这个关键转型期,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与融合是如何体现在这些经注之中的。我一直好奇,在那个信息传播相对缓慢的年代,学者们是如何吸纳前人的智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批判的。这本书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深入挖掘那些被主流史学忽略的细节,那才算得上是一部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著作。毕竟,经注本身就是历史的活化石,它承载的不仅仅是文字的意义,更是当时社会的精神风貌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挣扎。
评分说实话,我对这种专注于“经注”的研究读物总是抱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我渴望知识的精准和深入,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过于专业的术语和晦涩的论证会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我希望这套书在保持其学术水准的同时,也能在行文的流畅性上下功夫。比如,如果能在关键的转折点用一些清晰的小标题或者总结性的段落来引导读者,那就太棒了。我尤其关注的是,作者是如何处理那些文本的“歧义”部分的。古代文本往往不像现代著作那样逻辑线条分明,其中充满了模糊地带和多重解释。一个优秀的注释者,不仅要指出哪种解释更为主流,更要探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及其历史语境。如果这本书能在这方面展现出高超的驾驭能力,能够把复杂的学术争鸣梳理得井井有条,让读者在迷雾中找到清晰的路径,那么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了。
评分初读这卷书的目录,我立刻被其中涉及的文献广度所震撼。它似乎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的经典文本,而是横跨了多个重要的知识领域,这让我对作者的学术视野充满了敬意。我尤其关注那些关于特定术语的考证部分,因为在古代文献的解读中,一个词语的细微差别往往能导致整个论断的偏差。如果作者能够提供详实的比对和多语种的参照,那无疑是对研究者极大的帮助。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些“耳目一新”的视角,而不是对既有观点的简单重复。真正的学术著作,应该敢于提出挑战,哪怕只是在脚注中轻轻地质疑一下前人的定论。那种严谨到近乎偏执的求真精神,才是我们这些后学应该追随的旗帜。这本书如果能在这份“偏执”中找到一种平衡,让阅读体验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那它无疑就是佳作。
评分东西很好 快递服务一流
评分期待已久的好书,得好好读读。只可惜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啊?
评分质量不错,价格实惠!个人喜欢!不错哦
评分质量不错,价格实惠!个人喜欢!不错哦
评分期待已久的好书,得好好读读。只可惜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啊?
评分很好
评分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
评分很好,很仔细很清楚,很有帮助。
评分搞活动!囤货!你们懂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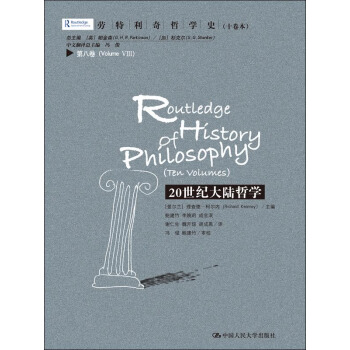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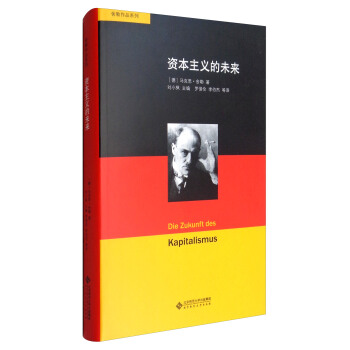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Series of Research on the Basic The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Research on Marxist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131947/5988332eNd8bf4dab.jpg)


![希腊神话的性质 [The Nature of Greek Myth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12394/594a0823N45fdb8e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