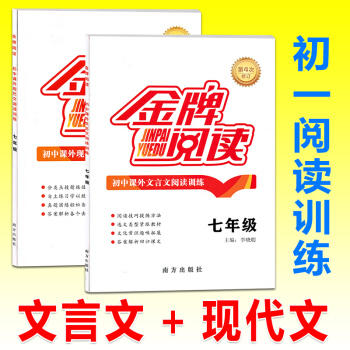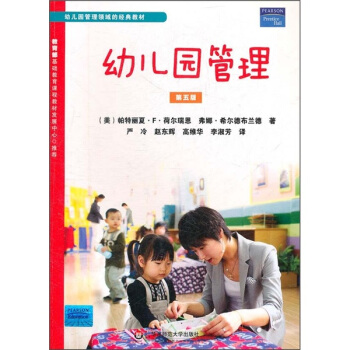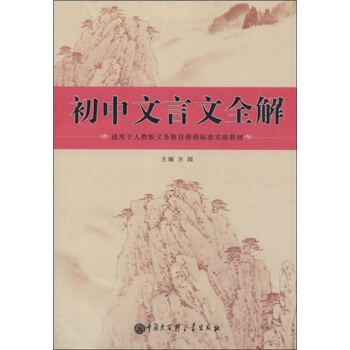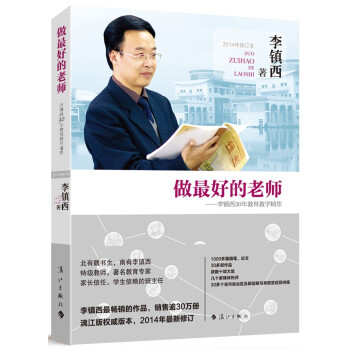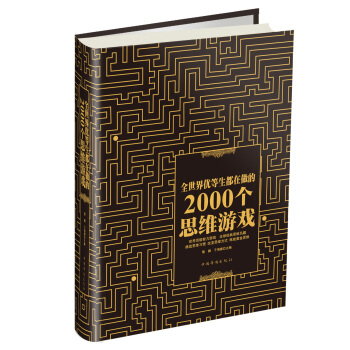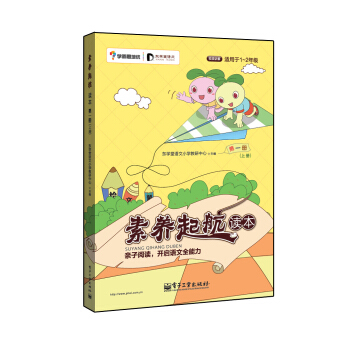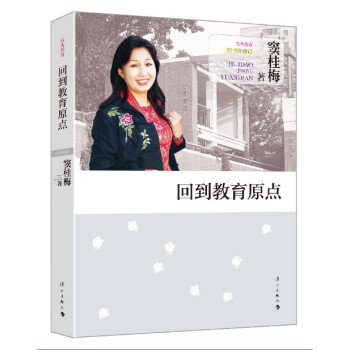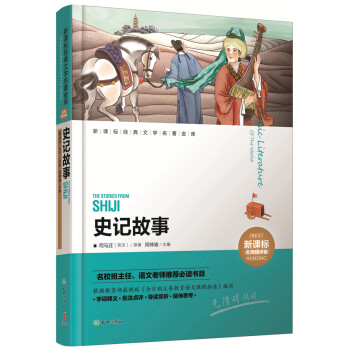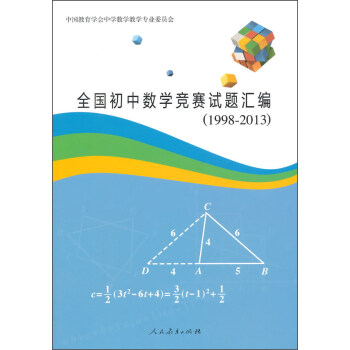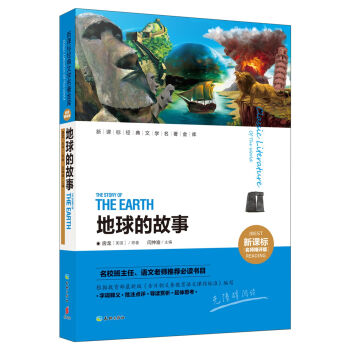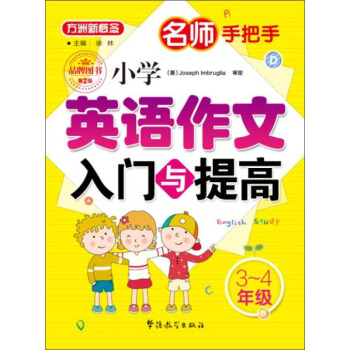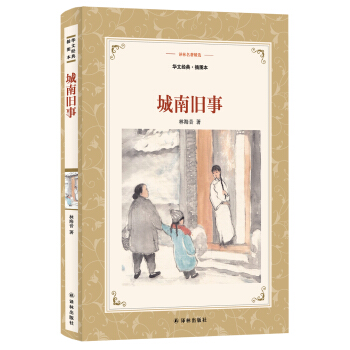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的经典作品,被教育部列为《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推荐书目。林海音以她超逸的文字风格,通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多少年来,《城南旧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除了再版无数次的小说外,1985年,《城南旧事》还被搬上银幕,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佳故事片大奖金鹰奖章”、第十四届“贝尔格勒国际儿童电影节*佳影片思想奖”等多项大奖。内容简介
《城南旧事》是文坛名家林海音女士的自传体小说集。小说透过童年英子的双眼,描述了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文字朴实温馨,故事生动起伏。读她,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孩子,看北京,看大人,看周遭的幸与不幸。作者简介
林海音(1918—2001),小说家。原名含英。台湾苗栗人,生于日本大阪。五岁随父母定居北京。1948年到台湾,任报社编辑,后主编《联合报》副刊。1967年创办和主编《纯文学》月刊。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城南旧事》、散文集《冬青树》等。内页插图
目录
城南旧事(代序)惠安馆传奇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冬阳 童年 骆驼队(后记)
作者大事略
前言/序言
城南旧事(代序)差不多快十年了,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抄写在这里:
我的生活兴趣极广泛,也极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要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着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些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最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便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便会挨挨蹭蹭地跟进来,北平的土话这叫作“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地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安在话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白:“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摩擦出吱吱扭扭的声音,嗞嗞啦啦地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是熟主顾,最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乱哄哄地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便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坐(包厢例外)。有时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最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入睡,坐在她们(母亲或是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着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了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有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地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地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最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的文章,便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他过早离开我们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还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以及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的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地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害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便可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最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地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的花盆都搬出来。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最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施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得咧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有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最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地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的程度,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是有连贯性的,读者们别问我那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地愚騃而神圣吗?
林海音
一九六〇年七月
用户评价
这本书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画,勾勒出老北京城南的温情与哀愁。从孩童的视角,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也瞥见了那个年代里形形色色的人物。那些鲜活的面孔,仿佛就站在我眼前,他们的笑声、哭声,他们的喜怒哀乐,都随着文字流淌进我的心底。我尤其喜欢书中对小女孩英子的描写,她的纯真、她的好奇,还有她面对离别时的懵懂和无助,都让我感同身受。那些曾经以为会永远存在的人和事,都在岁月的长河里渐渐模糊,只留下回忆的碎片,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读这本书,就像是在和一位老友聊天,听她娓娓道来那些久远的往事。每一个章节,都像是一个小小的故事,独立又相互关联,共同织就了一幅斑驳陆离的人生画卷。我常常会停下来,想象着那个年代的街景,那些老旧的院落,那些穿着长衫的老人,还有那些在胡同里追逐嬉闹的孩子。这本书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种情怀,一种对逝去岁月的深深眷恋。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在最平凡的叙述中,触动人心最深处的情感。英子,这个小小的灵魂,用她稚嫩的眼睛,观察着成人的世界。她看到了善良,也看到了无奈;她感受到了爱,也经历了分离。那些书中出现的人物,每一个都像一颗被时间遗忘的珍珠,在岁月的洪流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祥子,那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他的命运令人唏嘘;秀贞,那个被误解的女人,她的故事令人心酸。作者并没有刻意去美化或丑化任何一个人,而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展现了他们各自的人生。这本书让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成长?也许,成长就是经历,就是懂得,就是在那些失去和得到中,逐渐清晰地看到生命的纹理。它像一阵微风,吹过心田,留下一抹清新的痕迹。
评分刚拿到这本书时,就被它的封面设计所吸引。那是一种古朴而典雅的风格,仿佛能将人瞬间带回那个遥远的年代。翻开书页,迎面而来的是一种淡淡的墨香,伴随着字里行间流淌出的乡愁。英子,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用她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旧日北京。我尤其喜欢书中对童年场景的描写,那些槐树的浓荫,那些巷子里的叫卖声,那些邻里间的闲谈,都仿佛还回荡在耳边。这本书没有太多复杂的故事情节,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传递,一种对逝去时光的缅怀。英子的成长,伴随着她对生命中许多事情的理解,从最初的懵懂,到后来的懂得。她与父亲、母亲、奶妈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朋友们的交往,都展现了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喜怒哀乐。读完这本书,心中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却又夹杂着一丝温暖。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在一个老旧的照相机里翻看泛黄的老照片。每一张照片里,都定格着一个时代的片段,一段被遗忘的时光。英子用她那双清澈的眼睛,观察着身边形形色色的人。有卖豆汁儿的张老伯,有疯疯癫癫的祥子,还有那个神秘又善良的“疯”女人秀贞。他们都是那个时代里的小人物,他们的生活艰辛,却又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读到秀贞的故事,我为她的遭遇感到心痛,为她与女儿的分离而感到悲伤。作者对人物的刻画非常细腻,即使是寥寥数笔,也能勾勒出一个鲜活的形象。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深刻的哲理,它只是静静地讲述着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却在不经意间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残酷,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美好。它像一首低沉的歌,在心头回荡,久久不能平息。
评分初读这本书,便被它那独特的叙事风格深深吸引。作者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将看似平淡的生活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跌宕起伏的冲突,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淡淡的疏离感和宿命感。英子和小伙伴们的童年游戏,在大人眼中或许是无忧无虑的,但在孩童的世界里,却承载着许多他们尚不能理解的悲欢离合。读到那些关于“惠安馆”的故事,看到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物,心中不禁升起一股复杂的情感。他们的人生,像风中的蒲公英,飘零无依,却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作者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多的评判,而是用一种包容的视角,展现了他们各自的命运轨迹。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成长”这个概念,它不仅仅意味着年龄的增长,更意味着经历世事后的成熟与懂得。那些曾经的懵懂,终将成为回忆,而那些在生命中留下印记的人,也会在岁月的尘埃中,化作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评分无损,听说蒲隆的译本是最好的,看了序和首篇,感觉不错。
评分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评分东西不错的东西不错的东西不错的东西不错的东西不错的
评分与三联版的瓦尔登湖是相同的译者,翻译质量不错
评分这个课外阅读是我买过最实用的,贴近实际,与孩子平时测验考试的题型一致。粗细条,题材是那个时代的风格,没看头。黑白的,绘画还可以。以下是凑数文字: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今天的打脸,让我们的读者错过一波打赏的行情。这次监管事故,我们都付出了打脸、早套的代价,但是汇贬股涨的行情没有变,甚至今天还多了一波,那就是我们必然会看到的“打脸行情”。
评分习如何设计一套个性化的瑜伽练习 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保证自己的安全 接下来 你将学习如何进行深度放松 这是消除慢性肌肉紧张 降低疼痛敏感度 减缓压力和焦虑的关键 最后 你将学习一些冥想技巧 每种技巧都是针对一种特定的慢性疼痛的 例如 你将学习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疼痛发作 也将学习如何把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情绪 放松 和 冥想 都有助于身体实现自然愈合 也有助于你重新找到内心的喜悦 介绍完各种瑜伽练习方法后 我们将探讨如何让瑜伽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 你将学习如何的为人、她的号召力,成为联接大陆与台湾文学之间的桥梁。城南旧事是她早年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佳作。城南旧事主要讲述了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发生的故事书中内容包括人力资源规划,员工招聘管理,员工面试与甄选,员工录用管理,员工绩效管理,员工薪酬管理,员工培训管理,员工晋升与离职管理,劳动合同管理,员工档案管理,办公用品管理,办公设备管理、办公费用管理,印章、证照、文件资料、档案管理,会议、提案、行政事务、法务管理,员工考勤、出入、假务管理,员工出差管理,车辆管理,招待与接待管理,宿舍食堂管理,环境与安全管理共21项日常管理工作,涉及多个行业的企业制度范例以及大量拿来即用的模板、量表。人力资源与行政后勤工作执行流程为人力资源与行政后勤管理工作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管理范本,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人力资源与行政后勤工作执行流程适合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企业人力资源部、行政部、后勤保障部、综合管理部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培训和管理咨询。它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无孔不入。阅读《洗脑术:怎样有逻辑地说服他人》,你将获悉:怎样快速说服别人,让人无条件相信你?如何给人完美的第一印象,培养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如何走进他人的大脑,控制他们的思想?怎样引导他人的情绪,并将你的意志灌输给他们?如何构建一种信仰,为别人造梦?…… 全球最高端隐秘的心理学课程,一次彻底改变你思维逻辑的头脑风暴!白宫智囊团、美国FBI、全球十大上市公司总裁都在秘密学习!以及适宜的身体活动量。为了适应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发展需要,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人才,我国的许多高校开始在课程教学中实施双语教学。由于英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通用语言,国际上重要的科学技术成果大多首先以英文出版,因此,加强在专业课程中的英语学习,对于较快地学习和掌握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适应学生走向国际化的进程是必要的。由于学生外语水平的参差不齐,环境配套设施、教材以及师资的因素,对如何实施双语教学一直有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是第一位的,不能一味强调英语授课的比重,这可能最终以降低或损伤学科教学质量为代价。作为双语教学诸多方法中的一个层次的尝试,我们认为教学过程中汉语的讲授是必要的,需要尽可能地营造英语的氛围,使程度高的同学能借助这一平台达到更高的水平,而程度较差的同学也能通过这一过程感受到外语的环境,感受到颇有风度。多读书,可以让你多增加一些课外知识。培根先生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不错,多读书,增长了课外知识,可以让你感到浑身充满了一股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激励着你不断地前进,不断地成长。从书中,你往往可以发现自己身上的不足之处,使你不断地改正错误,摆正自己前进的方向。所以,书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多读书,可以让你变聪明,变得有智慧去战胜对手。书让你变得更聪明,你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困难。让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你又向你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迈出了一步。多读书,也能使你的心情便得快乐。读书也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的方式。读书可以调节身体的血管流动,使你身心健康。所以在书的海洋里遨游也是一种无限快乐的事情。用读书来为自己放松心情也是一种十分明智的。读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知识和智慧。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为我们以后的人生
评分为了京豆才给好评,京东快递越来越节俭了,一个破塑料袋都磨的有洞洞了,然后买的精装书书皮都皱了
评分简奥斯丁,最灿烂的一部。
评分学校推荐的中学生必读书目!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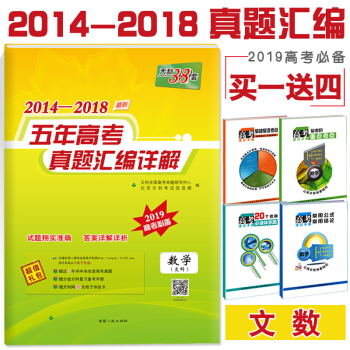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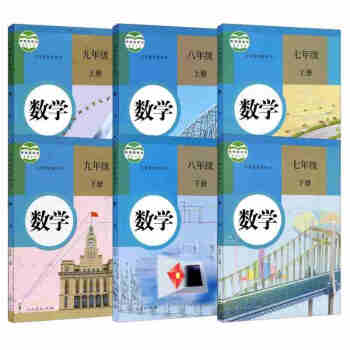
![2019版高中物理全能新课堂 课堂导学与针对训练(第三册) [含解答或提示] 高考总复习使用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92665920/5b2c9ba1N7bacfc7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