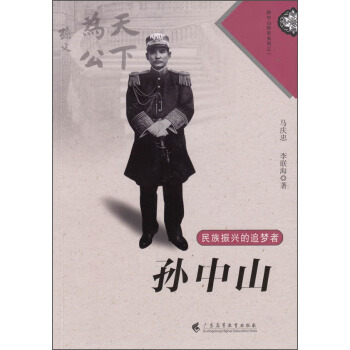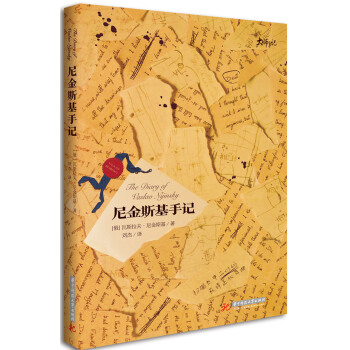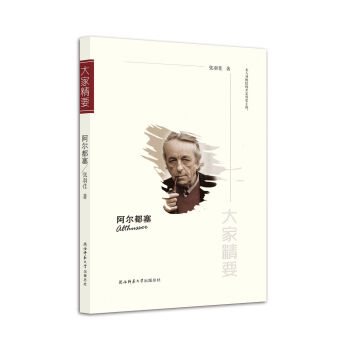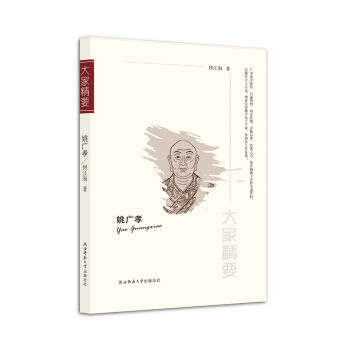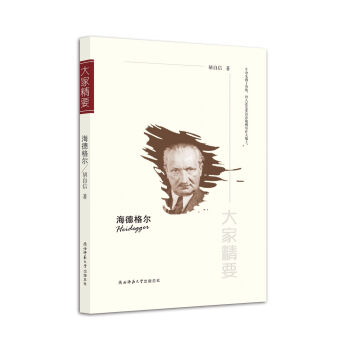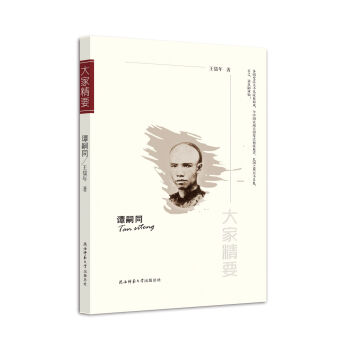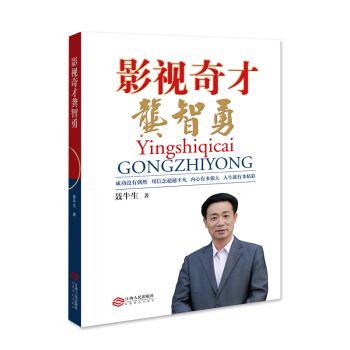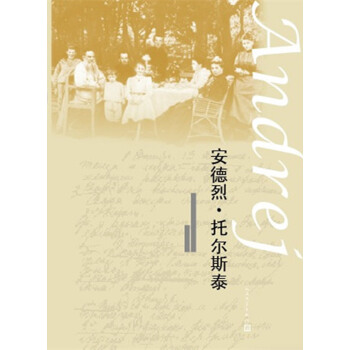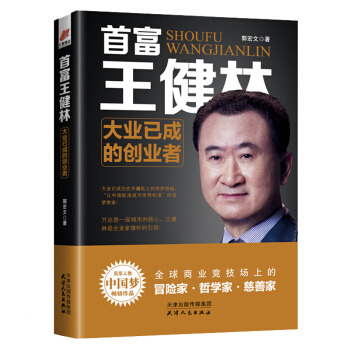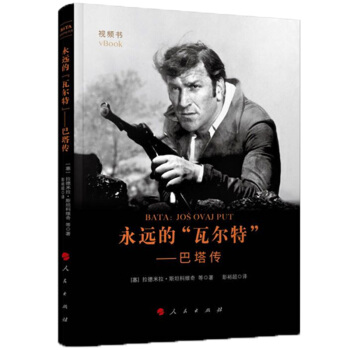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文坛硬汉”欧内斯特·海明威遗作一部融合自传与虚构的东非游猎回忆录
在非洲,di一道曙光下真实存在的事物到了正午就会成为假象。
内容简介
本书原是海明威1953年至1954年东非游猎归来后在古巴所写的一部无题手稿,写作过程几经中断,终未能完成。1999年“海明威百年诞辰”之际,这部长达八百页的手稿才由他的儿子帕特里克整理出版。海明威的密友“老爷子”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猎人,在海明威第二次来到非洲后,他让海明威接管了游猎营地。此时,几支部落间剑拔弩张,传闻一群逃脱拘留、宣誓加入茅茅运动的坎巴人威胁要袭击海明威的营地。海明威一方面肩负着领导者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得协助妻子在圣诞节前追捕一头狮子。
在非洲,di一道曙光下真实存在的事物到了正午就会成为假象。后来,那群坎巴人号称要发起的攻击,也如曙光照耀下的晨雾一般消散了。
作者简介
海明威(1899-1961),美国作家、记者,出生于芝加哥郊区的奥克帕克。一生感情错综复杂,先后经历过四段婚姻,本书的女主人公即他的第四任妻子。海明威是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海明威素以文坛硬汉著称,是美国的精神丰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授予银制英勇勋章;1953年,以《老人与海》一书获得普利策文学奖;1954年,《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太阳照样升起》与《永别了,武器》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20世纪100部zui佳英文小说”。
精彩书评
他会欣赏这个地球上我所爱的东西:天气、枪支、猎狗、赛马、爱与恨,以及看似艰难却可以被富有勇气和献身精神的人转变为有利条件和辉煌胜利的不利处境。——拉尔夫·埃里森
精彩书摘
在非洲,第一道曙光下真实存在的事物到了正午时分就会成为假象。对于这样的事物,你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就好像你不会相信在骄阳炙烤的盐碱地上有一泓晶莹剔透、灌木环抱的湖泊一样。曾经,你在上午时分穿过盐碱地,知道那里并没有这样的湖泊。而现在,它却是那么真实地存在着,无限美好,根本不像是假象。她从来没有躺在我们家乡山区山口顶部的树带界限之上的杜松树丛底下,手握.22步枪,等着鹰来吃一匹死马。那匹死马是熊的饵料,现在熊被杀死了,它又成了鹰的饵料,以后还会再次成为熊的饵料。你刚看到鹰的时候,它们都飞得很高。天还没亮你就在树丛下匍匐而行,当在太阳的照耀下,山口对面的山峰显出轮廓时,你看到鹰从阳光里飞出来。那座山峰就是一座长满草的高地,山顶上是一块露出地表的岩石,山坡上是散布的杜松树丛。那片区域的地势都很高,一旦你到达了如此的高度,便能很轻松地四处游览。那些鹰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要到雪山去。躺在树丛下可看不见那些雪山,得站起来看才行。天上飞着三只鹰,它们在风中盘旋飞行、扶摇攀升、轻盈滑翔,你看着它们,直到阳光照得眼睛刺痛。然后你闭上双眼,太阳还在,你的眼前是一片红。你再次睁开眼,从遮阳棚的边缘望出去,看见它们展开的翅膀和扇形的尾巴,能感觉到它们那长在大脑袋上的双眼在注视着前方。清晨的天气很冷,你看着外面的那匹马,它那以前你一直都要掀开嘴唇才能看见的老牙现在就在外面露着。它的嘴唇看起来和善而有弹性。当你把它带到这个地方来杀掉,解下它身上的缰绳时,它就按照你平时教它的方法站在那里。当你抚摸着它黑色的头上长着灰色长毛的那一块发亮的区域时,它低下头用嘴唇在你的脖子上夹了一下。它低头看了看你拴在树林边上的那匹配着马鞍的马,好像在疑惑,它在这干什么?又有什么新游戏了?你想起了它在黑暗中的视力总是很好,想起那时候你们走在那一条条小道上,旁边长着树木,路就挨着悬崖,而你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你把熊皮铺在马鞍上,手则紧紧地抓着它的尾巴。它的判断总是正确的,也能理解所有的新游戏。
于是你五天前就把它带到这里来了,因为这件事总得有人来做,而你即使做不到温和也能让它感受不到什么痛苦,但是这对结果能有什么影响呢?问题是,最后它觉得这是个新游戏,开始学习。它用它那有弹性的嘴唇吻了吻我,然后看了看另外那匹马的位置。它知道自己的蹄子开裂了,你不能骑它,但这是个新游戏,它想要学会。
“再见了,老凯特,”我说,然后握住它的右耳,轻轻抚摸它耳朵的根部。“我知道你也会对我做同样的事的。”
当然,它不会听懂我的话,正当它想要再吻我一下,告诉我一切都好的时候,它看到了我举上来的枪。我觉得我可以不让它看到,但它还是看到了,它的眼睛认出了枪,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身体瑟瑟发抖。我把枪打在它两对斜对的眼睛和耳朵的连接线的交汇处,它立即四肢跪地,全身倒下,变成了熊的诱饵。
我现在趴在杜松树丛下,悲伤尚未褪尽。我对老凯特的感情永生都不会变,或者说,我那时是这么想的,然而我还是看着它的那已经被鹰吃掉的嘴唇,看着它那已经被叼去的眼睛,看着它的身体被熊撕开的地方已经凹陷了,看着那块被熊吃掉的肉。我打断了熊对它的蚕食,继续等着鹰飞下来。
终于有一只飞了过来,它落地的声音就像是一颗炮弹飞过来然后爆炸的声音。它的双翼向前伸着,腿和爪子上都长满了羽毛,它奋力向前撞击着老凯特,仿佛要把它杀死似的。然后它傲慢地围着尸体转了几圈,开始啃它的伤口。又来了几只鹰,它们的动作更轻柔一些,翅膀也显得笨重一些,但是和前面那只鹰一样,它们的翅膀上都长着长长的羽毛,脖子都很粗,都长着硕大的脑袋、弯下去的喙和金色的眼睛。
我趴在那里,看着被我杀死的我的朋友、伙伴的身体被它们争相啄食,我想它们还是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比较可爱。既然它们也活不长了,我就让它们多吃了一会,它们争吵着,踱来踱去,把啄到自己嘴里的内脏细细嚼碎。我希望我手里有一把霰弹猎枪,但是我没有。于是我最终拿起那把.22曼彻斯特枪,小心翼翼地射中了一只鹰的头部,又在另一只鹰的身上开了两枪。它扑扇着翅膀想要飞走,但是飞不起来,平摊着翅膀落在了地上,于是我不得不爬上高坡去追它。几乎所有其它鸟类和野兽在受伤时都会往山下逃去,但是鹰会往山顶跑。我追上那只鹰,抓住它那用来抓捕猎物的爪子上面的双腿,用我穿鹿皮鞋的脚踩住它的脖子,用手把它的一对翅膀抓在一起。这个时候它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仇恨和蔑视,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动物或鸟类像它一样盯着我看。它是一只金鹰,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个子大得可以抓住年幼的大角羊,把那么一只鹰握在手里真的是很大。我看着那些鹰和珍珠鸡一起进食,想起它们是不屑于与其它动物为伍的,这时候我不禁为玛丽小姐的悲伤而感到难过。但是我不能告诉她那些鹰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能告诉她我为什么杀死了那两只鹰(最后那只是被我在树林里的一棵树上砸烂脑袋才死的),也不能告诉她我用它们的皮在保留地的跛脚鹿镇上买了什么。
……
前言/序言
序——帕特里克·海明威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至少对于我来说至今都还有着重要意义。我在东非度过了我成年时期的前半段,曾广泛阅读了在那里生活了两代半的英国和德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学。如果不解释一下北半球1953年到1954年冬季肯尼亚发生的事,本书的前五章在今天可能会很难理解。
乔莫·肯雅塔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游历甚广的非洲基库尤族黑人。在英国居住期间,他娶了一位英国女人做太太。根据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说法,乔默回到故乡肯尼亚,发动了一场被称作“茅茅运动”的黑人农奴起义,将矛头对准占有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是从欧洲迁移过来的,基库尤人认为这些欧洲农民窃取了他们手中的土地。正如《暴风雨》中卡利班的抱怨:
这岛是我老娘昔考拉克斯传给我,
而被你夺了去的。你刚来的时候,
抚拍我,待我好,给我
有浆果的水喝,教给我
白天亮着的大的光叫什么名字,
晚上亮着的小的光叫什么名字:
因此我以为你是个好人,
把这岛上一切的富源都指点给你知道
什么地方是清泉盐井什么地方是荒地和肥田
茅茅运动并不是在四十年后最终为大部分非洲黑人赢得了整个撒哈拉以南统治权的泛非独立运动,而基本上是基库尤族的人文历史上所特有的事件。一名基库尤人要成为茅茅战士,必须立下渎神之誓,从此停止正常生活,成为打击从欧洲移民来的农场雇主的神风突击队式的肉弹。全国最常见的农具在斯瓦希里语中被称为panga,这是一种厚重的单刃刀具,用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钢板冲压打磨而成,可用来砍柴、挖洞,在适当的时候,它还会成为杀人的屠刀。几乎每个农场工人都有这样一把刀具。我并不是人类学家,我所做的描述也许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但这就是从欧洲移民而来的农场主以及他们的妻儿眼中的茅茅运动。令人悲哀的是,在应用人类学的这段小插曲中,最终被屠戮和残害的并非茅茅运动所指向的从欧洲移民来的农耕家庭,而是拒不立誓却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基库尤人。
欧洲人为了进行农业殖民,专门留出了一块保护区,这在当时被称作“白色高地”。和坎巴族人的传统耕地相比,它的海拔更高,灌溉条件更好。基库尤人感到,这块土地是从他们的手中窃取的。坎巴族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尽管说着一种和基库尤人相近的班图语,但是他们必须狩猎和采集更多的事物,以弥补他们收成不太乐观的耕地,而且和他们的基库尤族邻居比起来,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更不容易就地取材。两族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微妙,要想充分理解这种微妙的差异,通过把共同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比较便可知。我们大多数人都很了解这两个国家,所以明白为什么在其中一国行得通的事对另一国却毫无吸引力可言,茅茅运动也是如此。在大多情况下,茅茅运动对于坎巴族是行不通的。这对海明威夫妇,欧内斯特和玛丽来说,确实是幸事,不然他们很有可能在睡梦中被他们十分信任并且自认为理解的仆人活活砍死。
一群逃脱拘留、宣誓加入茅茅运动的坎巴族人在威胁袭击海明威游猎营地之后不久,他们就如温暖的晨光照耀下的晨雾一般消散了。这之后发生的故事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有幸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在我的童年晚期和青少年时期我和父亲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父亲先后与玛莎·盖尔霍恩和玛丽·威尔士成婚。记得我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无意中走进父亲的卧室,那是在玛蒂为他们俩人在古巴找到的房子。当时,他们俩正在以一种婚姻幸福指导手册上推荐的激烈方式做爱。我立刻退了出来,我想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但当我写出眼下这个故事时,以及读到父亲把玛蒂描述成模仿大师那一段时,那一幕便在我遗忘了五十六年之后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她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模仿大师啊。
海明威的这部无题手稿长达二十万字左右,显然并不是一本日记。在这本书中,你将读到的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我希望玛丽不要因为我保留了关于戴芭的许多描述而生气。戴芭只是个黑皮肤的实体,而玛丽才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妻子。最终,这位真正的妻子进行了二十五年之久的慢性殉夫自焚,只不过燃料不是檀香,而是杜松子酒。
虚构和事实之间模糊的对位法构成了这部回忆录的核心。在许多段落中,作者大量运用了这种手法,这无疑会为所有喜欢这种写作手法的读者增添乐趣。我曾在基马纳的游猎营里度过一段日子,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通体红色的人。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这让我想起了1942年夏天在比拉尔号渔船上发生的事。当时我和弟弟格雷戈里还是孩子,在船上和临时充当海军后备队员的出色船员们度过了一个月时间,就像格兰特将军十三岁的儿子弗莱德在维克斯堡的时候一样。船上的无线电发报员是一名职业海军陆战队士兵,曾一度驻扎在中国。在那个搜索潜艇的夏天,他得空第一次读了《战争与和平》,因为他基本上白天黑夜都在待命,每天只需工作很短的时间,而这本书是船上的藏书之一。我记得他说这本书对于他的意义比其他人更大,因为他在上海时认识了那里所有的白俄。
海明威在写这部手稿的第一稿也是唯一一稿时曾被利兰德·黑沃德和其他拍摄《老人与海》的剧组人员打断,所以他不得不去秘鲁帮他们捕捞一条供拍摄用的枪鱼。这个故事中提到了利兰德,他当时娶了一个只能每天和他用长途电话联系的女人。苏伊士危机的爆发致使运河关闭,让父亲再度东非之行的计划落空,这也可能是他再未继续这部未完成的著作的一个原因。从故事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怀念“当年”的巴黎,而他中途辍笔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发现自己写巴黎可以比写东非更得心应手。尽管东非景色如画,激动人心,但是这种美好只持续了几个月他就遭了大罪,第一次是因为得了阿米巴痢疾,第二次是因为遇上了坠机。
如果拉尔夫·埃里森还在世,我就会让他来为这本书作序,因为他在《影子与行动》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你还要问为什么对我来说海明威比莱特更重要吗?并非因为他是白人,或更为读者所‘接受’。而是因为他会欣赏这个地球上我所爱的东西:天气、枪支、猎狗、赛马、爱与恨以及看似艰难但却可以被富有勇气和献身精神的人转变为有利条件和辉煌胜利的不利处境。而莱特却因为太急躁、贫困或稚嫩而无法理解这些。也因为他把每天的生活过程和技术写得细致入微,因而通过按照他描述的猎鸟,我和我的兄弟得以在1937年的大萧条中活了下来;因为他了解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差别,以及对于作家来说二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真正关系。也因为他写的所有东西都透着一种超越于我在家中所感受到的悲剧之上的精神,这一点很重要。这种悲剧很接近蓝调的感觉,而这可能是美国人所能表达的悲剧精神的极限了。”
我十分确信海明威读过了《看不见的人》,这帮助他在两次让他和玛丽差点丧命的坠机事故后重新振作起精神。当他在五十年代中旬开始继续写他的这部关于非洲的手稿时,这激励他重新开始创作的非洲之行已经过去了至少一年。在他的手稿的草稿中,他在评价作家们相互剽窃这件事时,脑中想到的可能是埃里森,因为埃里森小说中的描写疯人院中的疯子那一段像极了《有钱人和没钱人》中描写基韦斯特岛上的酒吧中的老兵们的那一段。
埃里森是在六十年代初写下这篇文章的,而海明威就在不久前的1961年夏天去世。当然,埃里森没有读过这部未完成的关于非洲的手稿,我在这里把它塑造成了一部作品:《曙光示真》,希望这不是最糟糕的样子。我把我父亲在早晨写的东西进行了一番加工,就像苏维托尼乌斯在他的《名人传》中所描述的:
“据说,弗吉尔在创作《农事诗》的时候,他习惯口述大量他在早晨创作的诗句,然后花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把它们删减到很少的几句,他诙谐地说他改诗的方式就像是母熊那样把它们‘舔’出模样来。”
只有海明威本人才能把他未完成的手稿“舔”成一只有模有样的灰熊。我在《曙光示真》中所呈现的只不过是一只孩子的玩具熊而已。从现在开始,我将每天带着它上床,躺在床上,我祈祷上帝保管我的灵魂,假如我在醒来前死去,我会祈祷上帝将我的灵魂带走。愿上帝保佑您,爸爸。
用户评价
这本《远行译丛: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实》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绝非一本轻松的读物,而是那种需要你沉下心来,仔细揣摩、反复品味的“硬菜”。从封面那充满象征意义的光影变幻,我就能感受到作者想要传递的某种超越表象的深度。我向来对那些能够挑战固有认知、迫使我跳出舒适区的作品充满敬意。我猜测,这本书可能是在探讨一些关于“真实”本身的定义,它是否是客观存在的,还是由我们主观意识所构建?又或者,作者会带领我们一同踏上一场心灵的远行,去探寻那些隐藏在生活表象之下,被我们忽略或遗忘的本质。我很期待书中是否会引用一些哲学、心理学,甚至是神秘学的理论,来支撑其观点。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让我对某些困扰已久的问题豁然开朗。读完这本书,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更敏锐的洞察力,能够以一种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视角去审视生活。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远行译丛: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实》就足以让我心生好奇。我一直在思考,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实”?它是否如同黎明的第一缕阳光,稀薄却充满力量,能够穿透黑暗,驱散迷雾?这本书的装帧精美,纸质也十分考究,给人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感觉。我推测,作者或许在书中探讨了关于意识、认知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等宏大命题。它可能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需要读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其深层含义。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能够跳出日常琐碎的烦恼,去思考那些更加根本性的问题。也许,它会挑战我一直以来对世界的看法,让我对“真实”有了一个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我希望,读完这本书,我能够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与力量,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姿态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充满了哲学意味,深邃的蓝色背景,隐约可见一丝金色的光芒从地平线升起,仿佛预示着一种觉醒和新生。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精装本给予人一种坚实可靠的感觉,触感细腻,装帧考究,让人立刻对其内容产生了莫大的期待。我一直对那些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作品情有独钟,尤其喜欢那些能够引导读者进行深刻自我反思的书籍。从书名“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实”来看,它似乎预示着一种摆脱蒙昧、直面真相的过程,而“远行译丛”的标签则暗示了其思想的深邃和跨文化的视野。我猜想,这本书或许会涉及一些关于人生意义、存在价值,甚至是人类意识边界的探讨。作者会不会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剖析人性的复杂,抑或是以一种充满诗意的语言,描绘那些不为人知的内心风景?我渴望在字里行间找到共鸣,获得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难以察觉的智慧启迪,能够帮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这个世界。这本书,绝对是我近期最期待的阅读体验之一,我相信它不会辜负这份等待。
评分《远行译丛: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实》,单单这个书名就充满了引人入胜的魅力。我总觉得,每个人都在内心深处渴望着追寻某种“真实”,一种能够让我们感到心安、感到踏实的本质。而“曙光”则暗示着一种启示,一种拨云见日的时刻。这本书的精装版本,给人一种庄重感,让我觉得它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智慧。我猜想,作者可能会通过一些深刻的寓言故事,或者是一些对人生哲学、存在主义的独到见解,来引导读者进入对“真实”的探索。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一种精神上的洗礼,让我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或许会揭示出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渴望,或者让我们看到一些被我们忽略的生命真相。我希望,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能够拥有更加清晰的自我认知,能够更加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内心所认定的“真实”。
评分拿到这本《远行译丛: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实》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我对“曙光”这个词有着特别的情感,它总是代表着希望、新生和突破。而“真实”则是我一直在追寻的那个永恒的命题。这本书的精装版本,厚实而有质感,无论是作为收藏还是作为日常阅读的伴侣,都显得尤为珍贵。我非常好奇作者会如何描绘这“第一道曙光”的到来,它会是突如其来的顿悟,还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求索?它会揭示怎样的“真实”,是关于个体存在的孤寂,还是关于宇宙万物的联系?我期待作者能够用一种独特而深刻的笔触,描绘出那些触动人心的瞬间,那些让我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自己的时刻。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我精神旅途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我照亮前行的道路,让我能够更加坚定地走向属于自己的“真实”。
评分好书,最近天气好正好看书
评分一直非常喜欢这类书籍,继续支持
评分现在的书真贵啊 活动还不错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远行译丛总的还不错。
评分现在的书真贵啊 活动还不错
评分这次大促买了好多书,够读一阵子了。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评分很喜欢这个作家的作品,值得一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