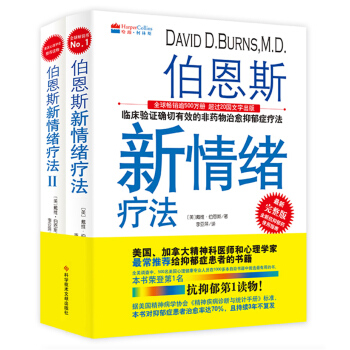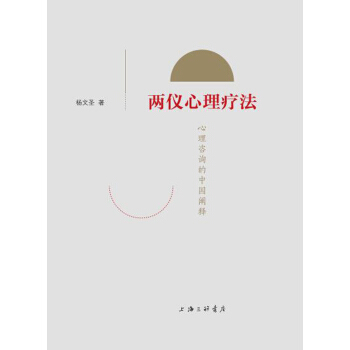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在心理分析学中,催眠是一种宽广、敏感的醒觉,它的实践可以成为一门生活的艺术,并意味着一种学习,这种学习不存在任何深奥的东西,只需要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可能性就已足够。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催眠研究的经验总结,观点鲜明独特,即使对今天的相关研究而言也依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内容简介
《什么是催眠》译自法国当代哲学家、著名心理学家、催眠治疗师弗朗索·鲁斯唐于1994年出版的一本名为《什么是催眠》的心理哲学随笔。在心理分析学中,催眠方法已应用多年,它可以有助病人释放自身的压力,让医生进入病人开放的意识,而本书的特别之处则在于指明“催眠”不仅是一种医疗方法,更是一种深度休憩的艺术,一种每个人都能付诸实践的生活方式。作者认为,催眠绝非被动,它使我们通过想象来预期和改变我们的举止和行为,同时,催眠还可以激发我们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对建立我们与他者以及我们所处环境之间关系的位置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催眠是更为宽广、更为敏感的醒觉,它的实践可以成为一门生活的艺术。作者简介
作者 弗朗索瓦·鲁斯唐(François Roustang,1923—2016),法国当代哲学家和催眠治疗师。他起初是耶稣会会士,曾从事心理分析师工作二十余年,后放弃心理分析,转而投身催眠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著作有《拉康:从模棱两可到穷途末路》、《什么是影响》、《结束抱怨》、《一个姿势就够了》、《懂得等待》、《苏格拉底改变生活的秘密》等。译者 赵济鸿,浙江绍兴人,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先后获得法语语言文学学士、硕士学位。现为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法语系副系主任,已出版《身体的历史》等多部译著,发表论文多篇。
译者 孙越,安徽合肥人,曾就读于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先后获得法语语言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南京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已在《法国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数篇。
目录
引言第一章 前提条件(Préalable)
第二章 预期(L’anticipation)
第三章 支配
第四章 改变(modification)
第五章 行动
部分术语和主题索引
人名索引表
精彩书摘
一个南非农场主的小男孩儿被毒蛇的毒液喷到眼睛。他马上就要失明了。家里的厨师,一个黑人,跑到大草原里寻来一些草嚼烂,敷到小男孩受伤的眼睛里。孩子最终得救。故事传到了隔壁的城市。得知此事的那些医生是怎样才会做到相信如此无稽之事?他们决定亲赴实地,采摘存在疑问的草本植物进行研究分析,或者确切地说是为了证明这些草药的治愈功效子虚乌有。那位厨师心知肚明;他肯定地说已经不知道在哪儿找到这些草药的。但他又改变了主意,带着这些先生们在越升越高,越来越闷热的大日头底下转来又转去。在远离农场的地方,当他看出来这些医生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他才承认无法找到他们想要证明的无医药功效的那些草药。这便是催眠。在我们的文化里,它看上去荒诞无稽,所以我们把它当成巫术魔法的遗毒来排斥。就像那些完全不担心闯入催眠师领域的白人医生,我们确信在听到催眠能告诉我们的那些话之前我们便有了答案。虽然为了能够有所评判,我们被建议亲身一试,但对于接受另一个时期的一种做法,我们还是非常抵触的,并且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治疗手段都会自诩某种功效。那么,这种功效是否有所验证,我们还仍然没有对此现象的解释。然而,我们需要这个解释,因为我们不可以拒绝理解,我们想要用我们的语言按照我们的标准将它表述出来。那些催眠师们可以自由行使他们的这项艺术,但是如果他们想要被世人理解,他们就应该既不影响那些成见也不干扰已有的确定性。
虽然在野草方面颇有认识,但面对医生们的自信傲慢,催眠术变得审慎并自我防卫。于是它会主动向我们呈现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歪曲夸张的行为又或是为了配合我们在这方面的空白认知而表现出一些消极做法。对它的各种假想让我们感到害怕。《黄色标记》(La marque jaune)里的塞普蒂默斯医生借助它的光环,将正直的公民变成了能上天遁地,挑衅伦敦警务处总部的罪犯。虽然像这般的能力从来都只存在于小说或电影之中,但是古怪与恐怖的混合体在如此的推波助澜下,其神秘色彩就会愈加浓烈,并且避开一些并不想了解其面貌的目光。此外,当身体失去自我般僵住不动,变成听从指令的机器人,感受或用手势来表达对他们做出的指令之时,催眠会表现出无害的一面,但又如此令人难以琢磨。又或是它会披上一件更为端庄的外衣,在我们风俗习惯里开辟出一条道路。事实上,这就是催眠,它通过让那些麻醉药物变得无用或不再那么得被需要,逐渐为医学所承认。催眠与慑人的迷惑力不可割裂,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最为显而易见的是它始终游走在对我们若隐若现之间。通过所有这些巧妙手段,它成功地将我们控制在它的投影中,让我们对其奥秘触不可及。
这是否危险?确切地说是令人难以理解。18世纪末,在吕米埃兄弟令欧洲为他们的发明赞叹不已之时,麦斯麦(Mesmer)则对催眠冠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动物磁气”(magnétisme animal),但他的说法又遭到国王派出的委员们的推翻。他们以极致的精确性和实验的创造性证明了这种不具有任何物质形态的磁流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种想象,当然,这是一种与现实相割裂的想象,它是精神失常和错乱的前奏。他们说得颇有道理,以致于那些动物磁气疗法施行者们都采纳了他们的观点。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们的确做出了让步,从与身体相对的精神中寻求庇佑,那里后来便是支配心理的现实之地。这一退却被某些人认为是一项胜利或是进入了希望之乡,事实上它是一种失败,它留给了对方外部世界的自由领域,用那些实验的自然科学手段排斥一切看不见又不可检验的神秘事物。
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后,这个领域仍然无法得到光复,因为仍然必须用科学的外衣来掩盖这件无法言明之事,或者至少也必须套以一个有着威胁力和说服力的所谓的科学名号。精神分析学(psychanalyse)曾经就是那根空心竿子,家蚕在那里面从一个世纪被输送到另一个世纪,而那些傲慢严苛的海关人员对此却丝毫不起疑心。此外,这样的偷运行为只是为了那些盲人所为。的确,弗洛伊德在催眠方面从来不曾忘记承认从中的受益,无论在关于其实践的思考中还是在其理论之中,他从来没有力图抹去显示其发现的具有输入痕迹的那些制作标记。虽然唯科学主义的法则冷酷无情,但是催眠的经验就这样没有被阻断过。因为弗洛伊德在一个世纪里用他的权威和才华促进了它的发展,从此,在科学之树得以充分舒枝展叶,终于可以思索它的内在严密性的时候,并且也是在催眠再也不必认真地打着科学的名号找到一席之地的时候,催眠就将可以正大光明地表现自己了。
但是在今天,催眠是什么样子呢?或者它表现得怎么样呢?它表示它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建立了一些学科,成功地且自由地付诸实践,病患们也因此对它感激万分。这一切都是那么不错。但是如果缺乏理论上的证明,这些大量的实践操作迟早都会变成不知所云的东西。把米尔顿?艾瑞克森的那种没有得到理论化的实践做法像避雷针一样拿来强调提出,这明显是在愚弄大家。首先,谨慎与大胆、智慧与简朴、力量与遵守之间的这种无法模仿的联合,谁敢于简单地将之独占己有?然后,美国的实用主义能够满足于此,这是它的事情。欧洲人是以其文化上的历史为代价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相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欧洲人在文化方面的经历迫使他们处于不同的文化之间。最后,如何无视在我们这里统治着我们这块领域的绝对霸权?对于我们的那些同时代人而言,关于心理现象、心理疾病、人类关系、社会关系,只有一种唯一有效的阐释:这就是精神分析学所做的理论化的阐释。任何类型的心理疗法必须在其影响范围内或根据它已经得出的或建议的内容来被设想。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催眠的任何理论化的论文就不会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它既不是一朵能够盛开的鲜花,也不是一个能够在西方个人自由的土壤里生长成熟的水果,西方个人自由的精神分析学是最后的变形。就像精神分析学那样,催眠并不以神经官能症的研究为依据,它不建立在任何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之上,并且不受疯狂(folie)的迷惑,有人说疯狂是天才的根源所在。在我们曾经称之为与它有关的心理现象中,催眠也并不研究有关它自己的人类主题,因为它只是通过或在它的周围状况中,通过或在与其世界的关系中来控制人;因此相较客观,它并没有更为主观,相较集体性,它并没有更为个体性。此外,它没有感到任何求助过去的必要性。它使用的所有方法都旨在让一些直到那时都无法想象的潜在能力(potentialités)突然出现在现时(le présent)中。因此它的实际做法是一种治疗措施,一种手术,一种效用。这就是为什么它总是一点都不关心阐释部分,即给一些显得反常的现象冠以或加注一种意义。它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会这样”,而是“如何贴合和改变情绪和定位”,总之,意义就在事物本身之中。因此应该从中推断出“催眠是一种变革的现象学,它与我们所有的理论知识都是背道而驰的”。由于我们的学识和固执,造成的失误甚至可能会让我们在对于神秘和无知的津津乐道之中裹足不前。例如,富兰克林?劳斯基(Franklin Rausky)在为了纪念莱昂?切尔托克的一卷书中引用了后者,并就1989年提出的关于催眠现象的一个定义做了长长的一番评注:“这是机体的第四种状态(état),目前不具可客观化(与其他三种状态相反:醒觉(veille)、沉睡(sommeil)、做梦(rêve)):一种自然的潜在能力,一种在动物催眠中都已经根深蒂固的天生装置(dispositif),它的特征为表面上有关孩童的先语言的依恋关系的一些表现,并且这些表现发生在个体在其与环境的关系中受到干扰的一些情况之下”。不过,自这卷纪念性的书籍做过阐述之后,关于这条定义的评注便提前失去了影响:切尔托克他自己会觉得这条定义“有点儿愚蠢”。因此,一切就好像出于对催眠的尊重而不该给出一个答案。这个理由明显是与此相矛盾的,那些对催眠感兴趣的认识论专家们就被困于这个矛盾中。一方面,他们希望的是只有当催眠能够遭受到科学性的莫大侮辱(但是哪一种?)时它才在我们的文化中得到认可,同时他们又否认在这里科学性还有些地方有待研究,因为催眠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并且应该依然是一个去不掉的“恋己癖创伤”。
只要我们仍停留在这类问题之上,那我们肯定停滞不前。诚然,这种赋予人类的特殊能力只是在科学时代才戴着催眠的名号呈现于世。但是对此的理解若止步于此就显得颇为短视了。人类的这件陈年旧事之前就存在过,与科学无关。即便它的这些早期表现被追溯到萨满教方面,我们也无法在那方面来观察一个古老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当前的,因为它经历的岁月和人类的一样久远,即使它所呈现的形式留下了那些时代和文化的烙印。比如,我们的个人主义神话强调了催眠经验的隔绝状态;这曾经一点都不是必然的,因为它所具有的力量是所有联系的根源所在。不管怎样,虽然今天催眠看上去像是自然科学无法纳入的一个剩余,但是这并不是就可以对它弃置不管的时刻,相反,这是提议对其进行思考的契机,以使得我们的同辈人们能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
催眠的现象学在实验科学领域中与我们所有的理论学识背道而驰,因为它并不像它们那样建立在反射作用的模式之上,即自动模式或机器模式。反射作用仅单向发生,它只能从要求(通常叫作刺激)到反应。保罗?瓦勒里先是为这项发现感到赞叹不已,他很快便领会到人类的精神有着相同的情况,并且因此它能够逆向地走完这个路程。但是他希望这第二个反射的方式是第一个的延伸。这是个必然会有后患的错误,出于不脱离我们的知识领域的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这个想法是否最不会具有最多的引发效果?始终必须以一个来自外部的刺激为前提条件的反射作用,它是如何能够具有自我形成的能力?必须求助于另一领域、另一逻辑水平的一种能力(pouvoir),以使得一种“可能性的领域(univers de possibilité)”能够从第二个反射模式中突然出现。这个同样的错误,同样也是我们的知识的故步自封,它支配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化,因为这个理论化经历的就是受到数个连续的决定性因素(déterminismes)支配的那个过程(histoire),而这些决定性因素的方向总是从因(cause)到果(effet)。这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化建议回到童年来发现导致神经官能症的那些原因。回到初始也是徒劳无功,得到的结果只能是重复而已。虽然精神分析疗法对于一个个体的存在进行了某些改动,但是这不能够成为其理论所强调提出的那些理由。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与催眠的现象学背道而驰,还是存在一些与之相符的知识。这就是神经系统科学(neurosciences)的情况。它已经证明存在着一种可遗传的物质成分,被称为基因,是“有机体、其结构(plan)发生全面变革的原因”。然而——这是最重要的——,即使这个物质成分受到其机体的影响,但是它仍然与后生部分(part épigénétique)泾渭分明,也就是说它是历史的,与这个组织中的环境所起到的作用相协调。因而这就是一种使得我们能够摆脱反射作用的统治的范例。如果我们确实打算通过让其反向运作来摆脱束缚,也就是说发生方向变为从反应到要求,那么这个反应就将必须变成一种要求。但是既然进程(histoire)中所有的力量从质量上看都是均等的,只是在强度上有所变化,人们就总是在同一份记录中进行操作,并且只能强调冲突,双重性,对立面之间的抗争。若不想再受到反射作用所强加的形式束缚,就必须求助于一种脱离了先前性规则(règle de l’antériorité)的非历史性的成分。然而这正是一个今天的遗传医学所提议的此类型的范例,而遗传医学也不是通过对结果即症状起作用,而是对结构(plan)具有的那些畸形起作用,结构让这些症状变得具有可能性。
如果根据同样的范例,并且仅仅通过将此当作范例,催眠能够进入人类的组织能力(pouvoir organisateur)之中,那么这就再也不必为其所谓的魔术般的技巧而感到惊讶了。接受外科手术时不会有任何感觉,可以放一块硬币在手臂上制造出一个烫痕,行走在火炭之上却不会对皮肤产生损伤,这些事情应该不再令人感到意外。我们的感官系统的组织能力能够决定不同于平常那样起作用,在一定限度内让我们失去感觉,因为它能够切断与我们有关的任何输入(afférence),或者相反能够以一定比例以及根据一些新的标准来联合刺激(stimuli)。遗传医学所开启的这些观点让我们感到惊叹或惊吓。催眠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能够令人着迷或害怕:我们影响了这个组织能力。因此催眠治疗(hypnothérapie)之于其他的精神疗法(psychothérapie)就是遗传医学之于表观遗传医学(la médecine épigénétique)。
那些催眠治疗师们或许并不是不承认这些假设。作为证据,所引用的定义稍早了一些。切尔托克用这种方法曾经试图弄清楚有关催眠的那些著作的情况,并且对欧洲和美洲研究者们的各种共同的研究方向进行总结。重新采用这条定义里的那些术语,加入某些修改,对这些术语进行整理和分等级,这就足以提供给我们一种不错的有关催眠现象的研究方法。
那么首先,把催眠视为人体的第四种状态,这没什么愚蠢之处。在第一章里我们就会看到催眠状态被赋予与异相睡眠(sommeil paradoxal)相对应的名字“异相醒觉”(veille paradoxale),这并不是一个滑稽的假设,另外在异相睡眠时做梦活动非常频繁。关于催眠本质的这场漫长的争论应该会具有其意义和结果:醒觉的状态还是睡眠的状态?如果催眠是一种异相醒觉,那么所有的主要角色都能够被认为是有理的。既然催眠将被催眠者与输入的那些刺激分离开来,那么它就具有某些睡眠的特性,但是另一方面它表现出一种扩大的醒觉状态(vigilance),这种状态能够考虑到生命的全部参量,这是一种全面醒觉状态(vigilance généralisée),它包含并超越了我们所熟知的平常生活中的那种受限制醒觉状态(vigilance restreinte)。
而且,就像异相睡眠影响着晚间做梦与否那样,催眠释放出一种固有的能力,即在白天酝酿世界(le monde)。通过催眠状态,要恢复的不是一种前语言关系,而是一种潜在力量,它自诞生之日起便显示出来,并将终其一生支配着与世界的联系。动物磁气说时代的那种普遍确信将会因此受到同化,也就是说催眠是一种想象力(imagination)的产物。这并不是想象力扩张造成催眠,除此之外,确切地说这就是催眠状态,即异相醒觉,它可以让人施展想象力从而改变我们与有生命体和无生命物(les êtres et les choses)之间的关系。人们之前已经明白催眠和想象力之间的联系,但是并不清楚想象力只是这种天生便能组织我们这个世界的能力的另一个名讳或另一种表现。
一旦这些理论基础得以建立,那就应该——这是第二章的内容——回归到如我们所认知的催眠的实践,以及对我们将之命名为催眠引导(l’induction hypnotique)的那些各个不同的片刻进行描述。有多少这样的片刻就将表现出多少催眠的特征。诱导是以中断平常的感知(perception)为开始,比如固定一个物件,把它孤立于其环境之外。最初阶段,往往是判断的唯一关注点,这使得人们在催眠中看到的只是一种具有魔力的现象。然而这个最初阶段只是一段过渡。它导致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对于有关于有生命体和无生命物的确定被悬置。不确定性(indétermination)产生一种混乱的感觉。第三阶段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可能,因为从与那些构成我们生命之物的成分有着过于紧密和明显的联系中,我们已经解脱出来了。对于那些实验室里的催眠学家们而言,这是能够制造幻觉(hallucination)的时代。目标还有待于完成,也就是说这还有待于在混乱和想象力方面获得那样的潜在性(potentialité)。这种潜在性既表现为个体的也表现为集体的,因为我们行为的设想完全可能在构成的同时又得到传递。
如果人们强调催眠引导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其现实化而言具有必要性的那些方式方法,那么人们就能够同意伯恩海姆的观点了,他把催眠视为一种“习得行为(comportement appris)”,一个“角色游戏”,一种“得到暗示的表现”。因为它确实要求得到传递,并且它真的必须以一种传授为前提。和许多其他的理论一样,伯恩海姆的理论在其作出的肯定方面是真实的,否定部分则是错误的。按照刺激-反应(stimulus-réponse)的方式,催眠能够诱导一些行为,这并不意味着一贯如此,也并不是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虽然实施催眠的人对此有一定的适应,但是冒出来的潜在的意外总是令他的步骤被打乱。所以如果一些行为、角色、引导可以被设计创造出来的话,那么为了对此有所了解就必须借助一种能力,并且为了得以运用,它将需要参考机体的独特状态。
有些人,尤其是在艾瑞克森的领域中,他们认为催眠状态并不存在,那都只是一些“状况(situations)”,“过程(processus)”或“态度(attitudes)”。且相互之间并不排斥彼此。尤其在美国,催眠治疗师们(hypnothérapeutes)的关注在于坚信那些可观察到的事实。因为他们确实看到治疗师们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可以运用某些程序的状况。这不禁让人思忖这种状况和这些过程是根据什么来发生和建立的。当还是这些人终于谈到了态度的时候,他们开启了另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就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他们从治疗的那个保留领域中脱离出来,从而对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方式(manière d’être au monde),一种出现在生命中的方法(façon de se poser dans l’existence),一种机能的形态(modalité de fonctionnement)投射出兴趣。第三章就旨在把支配(disposition)当作态度来进行描写,后者同时准备和继续在治疗中实施的作业。
第四章不难证明改变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坐标体系都被搁置,并且只有依靠想象力,这才会变得具有可能。因为它代表着与生俱来的和非历史性的能力,所以它经受得住搁置,并拥有足够的活力来确立一个新的力量对比,一个新的未来计划,后者既更具现实性也更具有未来。但是这项新的计划必须具备某种合适性才能够得以执行。于是,在实现计划的时候,人的自由就好像是一种战略必要性。
最后一章将大致勾画出催眠的基本特征。催眠必须经过如此去繁留简,才能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效且朴素的组成部分,一种生活方式。今天之所以催眠重获关注,这一切或许都是因为西方个人主义疲态尽现。为了凸显自己,为了使我们与众不同,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我们尽了一切之能事。但是我们已经对关注自我感到厌倦。那个组织(tissu)如今已经四分五裂,我们身处其中,曾经想要让自己的细微差异变得清晰可见,自主性已经变得缺乏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孤立的个体出发,重新找到那个持续不断的本质,曾经我们在这个本质的基础上勾勒出个体的轮廓。因为倒退回去并相信仍然存在着一些群体,我们在那里可能需要从容地占据一席之地并各司其职,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e)应该走得还可以更远一些,它应该经历那些云雾遮眼和充满焦虑的境遇,发现一些隶属关系,而它们的那种极致单一性可在另一个范畴中获取。
用户评价
当我看到《什么是催眠》这本书名时,一股抑制不住的好奇心涌上心头。催眠,这个词语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和吸引力。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浅出地揭示催眠的运作机制,它究竟是如何绕过我们的意识防御,直达潜意识的?我期待作者能够用科学的视角,解释催眠状态下的大脑活动变化,以及它与正常清醒状态有何不同。这本书是否会探讨催眠在表演艺术中的应用?比如,那些舞台上的催眠秀,它们是真的能够影响人的行为,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暗示的技巧?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界定,帮助我理解其中的奥秘。此外,我也对催眠在解决童年创伤方面的潜力感到好奇。许多心理问题的根源可能深埋在童年时期,而催眠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去触及和疗愈那些被遗忘的伤痛。我希望书中能够包含一些相关的案例研究,让我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催眠的治疗力量。同时,我也关注催眠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提升自我认知。当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潜意识时,是否就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本书能否提供一些引导,帮助我进行更深刻的自我反思?
评分当我看到《什么是催眠》这本书名时,一种莫名的冲动油然而生。催眠,这个词汇在我脑海中总是与神秘、力量、甚至一丝神秘感联系在一起。我渴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催眠的真正含义,它究竟是一种科学的实践,还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催眠与人类感知觉之间的关系。例如,在催眠状态下,我们的感官是否会变得更加敏锐,或者对某些刺激的反应会发生改变?书中是否会涉及催眠在缓解疼痛方面的应用?我曾听说过一些关于催眠止痛的案例,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更科学的解释和更多的证据。同时,我也对催眠与个人成长之间的联系抱有浓厚的兴趣。它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内心的障碍,例如自我怀疑、不安全感,从而建立更强的自信心?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 practical 的建议,让我能够将催眠的原理应用于自我提升。此外,我也关注催眠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例如,增强同理心,或者更好地理解他人的需求。如果这本书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启示,那将对我个人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评分这本书的标题《什么是催眠》让我一开始就充满了好奇。我一直对人类意识的边界和我们潜意识的力量感到着迷,而催眠无疑是探索这些领域的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切入点。翻开书页,我期待的不仅仅是关于催眠术的技巧或历史,更是对它背后深层心理学原理的解析。我希望作者能够带领我深入了解,是什么样的机制让一个人能够进入那种特殊的意识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被唤醒和引导。比如,当一个人被催眠时,他的大脑活动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某些区域变得更加活跃,还是某些区域的连接方式发生了改变?又或者,这是一种集体潜意识的共鸣,还是个体经验的独特投射?这本书是否会提及催眠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在某些传统仪式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类似催眠的状态,那些吟唱、重复的动作,是否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催眠过程?作者是否会从神经科学、心理学、甚至人类学等多个角度去阐述催眠的本质?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催眠是否真的能够触及那些被我们遗忘的记忆,或者说,它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记忆系统的?是仅仅调动了储存在大脑深处的片段,还是在重塑和创造新的叙事?我希望作者能够以一种既学术严谨又不失趣味性的方式,来解答这些我长久以来萦绕心头的疑问。如果这本书能够让我对人类心灵的奥秘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那么它的价值将远远超出我最初的期待。我期待的不仅仅是一本关于“是什么”的书,更是一次关于“为什么”和“如何”的探索之旅。
评分《什么是催眠》这个书名,瞬间勾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好奇心。我一直对人类的潜意识以及它所能带来的奇妙力量充满兴趣。这本书似乎承诺要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让我得以一窥其究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探讨催眠的工作原理,不仅仅是那些表面上的指令和暗示,而是它如何绕过我们理性思考的屏障,直接与潜意识进行沟通。这本书是否会提供一些关于催眠技术的基本介绍?例如,引导语的设计、语速的控制、甚至是一些非语言的暗示,它们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期待作者能够用清晰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心理学概念转化为读者能够理解的内容。同时,我也对催眠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或者风险感到一丝担忧。是否存在一些人并不适合接受催眠?又或者,催眠是否可能导致一些负面的心理影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对这些潜在的风险进行客观的分析,并给出相应的预防措施。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发我对于自我潜能的思考。催眠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发掘自己被压抑的天赋和才能?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自我提升的工具?如果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利用催眠来增强自信、改善专注力,甚至激发创造力的思路,那将是极大的收获。
评分当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催眠》这本书名时,一股难以言喻的冲动驱使我去了解。我一直认为,催眠是一种神秘而又充满力量的存在,它似乎能够解锁我们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本书的标题直击核心,让我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了期待。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深入浅出地剖析催眠的本质,它究竟是一种科学的治疗手段,还是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艺术?或者,它两者兼具?我期待作者能够详细阐述催眠的理论基础,比如,它是否与我们的大脑节奏、神经递质的释放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否会有章节专门探讨催眠在临床心理治疗中的应用?例如,它如何帮助患者克服恐惧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戒除不良习惯?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具体的案例研究,让我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催眠的力量,以及它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此外,我对于催眠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也相当关注。催眠师的责任是什么?被催眠者的权利又如何得到保障?是否存在被滥用的风险?如果作者能够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或建议,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将会大大提升。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关于催眠的权威解答,消除我对它的一些误解和偏见,并对人类意识的潜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评分当我看到《什么是催眠》这个书名时,我立刻被吸引住了。我一直对人类心理的复杂性和深度充满好奇,而催眠无疑是探索这些奥秘的一扇窗口。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关于催眠的最权威、最深入的解读。它是否会详细解释催眠与意志力之间的关系?被催眠者是否会完全失去自己的意志?还是说,催眠只是改变了意志力发挥的方式?我期待作者能够用清晰的逻辑,解答我心中长久以来的疑惑。同时,我也对催眠在提升艺术创作灵感方面的应用感到兴趣。许多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都会遇到瓶颈,如果催眠能够帮助他们打破思维定势,激发新的灵感,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我希望书中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如何运用催眠来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建议。此外,我也关注催眠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接纳自己。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忽略自己的优点,放大自己的缺点。如果催眠能够帮助我们建立更积极的自我形象,那将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本书,我希望它能带给我一次关于自我发现的深刻体验。
评分当我瞥见《什么是催眠》这个书名时,我的大脑立刻开始运转。催眠,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魅力,它既让人向往,又让人心生敬畏。这本书是否能真正解答“它究竟是什么”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希望它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现象描述,而是深入到催眠的心理学根源。这本书是否会介绍催眠的历史发展?从古代的巫术仪式到现代的心理治疗,催眠是如何一步步演变至今的?我尤其想了解,在催眠状态下,人的思维和情感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意识的边界模糊了,还是某种特殊的注意力模式被激活了?书中是否会探讨催眠与梦境、冥想等其他意识状态的异同?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一些科学的解释,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轶事和传说。我对于催眠在解决成瘾性行为方面的应用也颇感兴趣。比如,它如何帮助人们摆脱烟瘾、酒瘾,甚至赌瘾?是通过改变潜意识中的渴望,还是通过建立新的行为模式?如果书中能包含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案例,那我将感到非常有启发。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提醒读者,催眠并非万能,也并非全然没有风险。它需要专业的知识和负责任的操作。
评分《什么是催眠》这个书名,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我一直对人类意识的潜能感到着迷,而催眠似乎是其中一个非常特别的领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从更宏观的视角,阐述催眠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是否曾经在宗教、哲学或者艺术领域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期待作者能够提供一些历史性的视角,让我能够理解催眠的演变过程。同时,我也对催眠在提升运动表现方面的应用感到好奇。许多运动员会利用各种方法来激发自己的潜能,而催眠是否也能成为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我希望书中能够介绍一些催眠在增强自信、克服比赛紧张、甚至提高反应速度方面的案例。此外,我也关注催眠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一项新的技能。无论是学习一门外语,还是掌握一种乐器,效率的提升总是令人期待的。如果催眠能够提供一些辅助方法,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催眠本身,更是一次关于人类潜能的探索。
评分《什么是催眠》这个书名,就像一个巨大的问号,牢牢抓住了我的注意力。我一直对人类心理的深层运作机制充满了好奇,而催眠无疑是其中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领域。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带我进入一个关于意识、潜意识以及它们之间微妙关系的探索之旅。这本书是否会详细介绍不同类型的催眠技术?比如,渐进式放松法、意象引导法,或者其他更具创造性的方法?我期待作者能够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这些技术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了解到催眠在提升学习效率、增强记忆力方面的潜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更有效地吸收和利用知识,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果催眠能够提供一些解决方案,那将是令人振奋的。此外,我对于催眠与创造力的关系也充满好奇。是否能够通过催眠来释放我们被压抑的想象力,或者激发我们解决问题的独特视角?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让我能够尝试着去探索和发掘自身的创造潜能。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知识的获取,更是一次自我探索的契机。
评分《什么是催眠》这个书名,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我对人类意识的奇妙之处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催眠无疑是打开这扇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清晰地阐释催眠的核心概念,它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情绪和行为的?这本书是否会探讨催眠与暗示之间的关系?暗示是如何起作用的?它是否能够真正改变人们的信念系统?我期待作者能够用严谨的态度,剖析催眠的科学依据,并纠正一些普遍存在的误解。例如,关于被催眠者是否会失去意识、失去控制,或者是否会泄露秘密的疑虑。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清晰的解答,让我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催眠。同时,我也对催眠在改善睡眠质量方面的潜力感到好奇。许多人深受失眠的困扰,如果催眠能够提供一种安全有效的解决方案,那将是巨大的福音。我希望书中能够介绍一些促进深度睡眠的催眠技巧,以及它们背后的原理。此外,我也关注催眠是否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压力和焦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有效的压力管理至关重要。如果催眠能够成为一种辅助手段,那将非常有意义。
评分不错,很好,很快就收到了,就是没活动价格有点高。
评分京东价格优惠,送货快捷,一般会选择!
评分挺不错的文丛
评分不错,很好,很快就收到了,就是没活动价格有点高。
评分轻与重,最好的一系列书
评分帮别人买的,京东速度还是很快的,北上广深都可以当天到
评分很好的书。作為丛书类书籍,從設計至印刷均相當精致,值得收藏!
评分很卡亏测具体开幕式阿我最退款咯屋里
评分很好的系列,活动优惠,谢京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中学生心理辅导 [Psychological Guidance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1971/5a74348eNd75a2e0e.jpg)




![爱的艺术 [The Art of Lov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2185/5a338dcbN8e651500.jpg)






![健全的社会(弗洛姆作品系列) [The Sane Societ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52681/5a5d9f49N0c842bd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