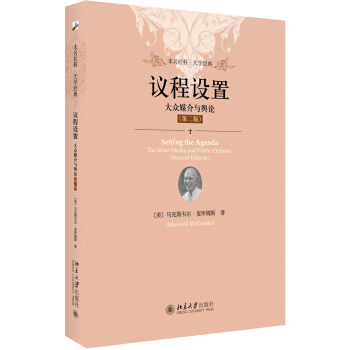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新闻传播领域的重要著作,系统介绍了议程设置理论及其实证研究。内容简介
议程设置理论描述了大众传播如何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的关注。近年来,这个理论逐渐扩展,又融入了许多新的命题,如关于产生这些效果的偶发条件、塑造媒介议程的力量、媒介信息中具体因素的影响以及议程设置过程的各种结果。《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既有对议程设置理论各个研究侧面的归纳概括,又涵盖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成果,同时具备理论和实践的价值。这一理论是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本书适合作为这些学科的入门参考书。
作者简介
作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教授,多年来致力于议程设置的研究及推广。译者郭镇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广播电视史、传播理论、国际传播与文化间传播;徐培喜,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网络安全、草根媒介。
目录
目录序言
第一章 影响舆论
第二章 现实与新闻
第三章 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第四章 议程设置为何发生
第五章 议程设置如何起作用
第六章 议程设置的结果
第七章 塑造媒介议程
第八章 大众传播与社会
结语 媒介议程设置和受众议程融合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美国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喜欢在他的讽刺性政治评论的开头说这么一句话:“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是从报纸上读来的。”这句评论是对我们所拥有的关于公共事务的大部分知识与信息的简洁概括,因为我们关注的这些事件与产生的许多担忧大多数都与个人的直接经验无关。很久以前,沃尔特·李普曼就在《舆论学》中指出:“那个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政治世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也想不到。”在罗杰斯与李普曼的那个时代,日报是人们获知公共事务的主要来源。今天,虽然我们已具备极大扩充了的系列传播渠道,但是核心的问题依然不变。对于公众议程上的几乎所有的事情,公民接触的只是二手现实,这种现实是由记者对这些事件与局势的报道建构的。
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同样简练地描述了我们与新闻媒介的这种关系,以令人信服的语言概括了新闻的信号功能。新闻每天告诉我们大环境中那些我们无法亲身经历的事件与变化。但是新闻媒介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告知重大事件与议题的范围。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筛选与展示,新闻工作者使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影响我们对当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件的认知。新闻媒介这种确认关键议题和话题并影响它们在公众议程上显著性的能力,后来就被称作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
报纸提供大量线索,体现各种话题在每日公众议程上的相对显著性。头版头条报道、与内页相对的头版报道、报道标题的大小甚至报道篇幅的长短,都能传达某种话题在新闻议程上的显著性。网站上也有诸如此类的线索。电视新闻议程的容量十分有限,因此,即使只是被电视晚间新闻简要提及,也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足以表示某个话题的显著性。其他线索还包括新闻在播报中的位置,以及报道时间的长短。对于所有传播媒介来说,日复一日地重复某个话题,是凸显这条消息重要性的最有力的证明。
公众利用这些来自媒介的显著性线索去组织他们自己的议程,并决定哪些是最重要的议题。时间长了,新闻报道中强调的议题就成为公众认为最重要的议题,新闻媒介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公众的议程。换句话说,新闻媒介在很大程度上设置了公众的议程。将某个议题或者话题置于公众议程,在公众中建立这种显著性,使之成为公众关注、思考甚至可能采取行动的焦点,这是形成舆论的初始阶段。
对舆论的讨论通常围绕观点的分布进行,多少人赞成,多少人反对,以及多少人还没有做出决定。这是新闻媒介以及很多受众对民意测验感兴趣的原因,在政治竞选时期尤其如此。但是,在思考观点的分布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哪些话题位于舆论的中心。人们对许多事情持有观点,但是对他们而言真正重要的话题只占少数。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便是影响某个议题在相当一部分公众中的显著性,这种影响能让很多人决定这个议题是否重要,是否值得自己关注,自己是否应对此议题持有观点。虽然许多议题都在竞争公众的注意,但是只有少数议题最终成功地获得了关注。而新闻媒介对我们的感觉——什么是当今最重要的议题——发挥了重要的影响。这不是一种故意的、有心栽花的影响,不是那种“要有一个议程”的计划,而是一种无心插柳的无意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新闻媒介在报道中必须选择并突出几个话题,并将它们设定为当前最重要的新闻这种需要。
新闻媒介对议题显著性的影响与新闻媒介对有关这些议题的具体观点的影响之间存在差别。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曾观察到并概括了这种差别,他指出,新闻媒介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方面可能并不成功,但是它们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则异常成功。换句话说,新闻媒介可以为公众思考与讨论的话题设置议程。有时,媒介所做的要超出这一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后面的章节中扩展科恩令人信服的观察。但是首先,让我们更细致地思考舆论形成的初期阶段:抓住公众的注意力。
前言/序言
序言如今,当人们讨论政治与舆论时,议程设置已经成为一个常用词语。什么是公众应该关注并采取行动的核心问题?“议程设置”一词概括了所有社群就这一问题的持续对话与辩论——这些社群可以小至地方邻里,也可以大到国际舞台。在大多数关于这些话题的对话中,新闻媒介都发挥着重要的,有时是具有争议的作用。南非最大的日报《索韦托人报》的总编辑就注意到在南非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传媒对全国议程的设置作用。他说:“我们强烈主张,在南非这样的国家,不能任由一个少数族群通过控制媒介的方式继续设置公众议程,这种做法肯定不对。”在英国,《卫报》也曾发表与此类似的评论:“75%以上的英国报业被三个右翼人士所牢牢控制,任意为国家政治话语设定议程,这是严重的功能缺陷。”
对于新闻媒介这种持久而广泛的作用,如果有人还存在疑问的话,那么可以再参考一下《纽约时报》对英国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男爵的描绘。比弗布鲁克被描绘成“一个和首相们一道用餐并为国家设置议程的人”。还可以参考《纽约时报》前主管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对自家报纸的描绘:它是那些最聪明、最有才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的“内部刊物”,这些人处于美国权力的顶层。虽然人们可能会轻视或批驳其专栏作家与评论家的意见和观点,但是他们不能抛弃这份报纸的每日新闻套餐。这些新闻设定了美国严肃人士的智慧与情感议程。
这些大众媒介机构的急剧增长与快速扩张是20世纪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成为当代社会不容置辩的一个特征。19世纪主要孕育了大批的报纸与杂志;20世纪则增添了电影、广播、电视与有线电视,使得媒介交叉重叠,无处不在;20世纪末又迎来了互联网以及各种传播技术的多变组合,使得各种媒介及其内容之间的传统界限日益模糊。这些新的渠道重新定义了大众传播,并扩大了它在社会中的议程设置作用。大众传播曾经意味着大规模地扩散相同的消息,特别是通过报纸、电视和广播;而新的传播渠道,例如Facebook、Twitter和Blog,在使用它们的人数量众多、比例甚大的意义上,仍属大众规模的传播,但就消息的流通而言,这些渠道却是个人化的。
虽然现在人人都在谈论新千年里涌现出的这些技术的冲击,但是,与近几波横扫全球的技术扩散相比,大众传播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显而易见。在《制造总统,1972》一书中,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将大众传播为公众注意力设置议程的能力描绘为“一种在别的国家只有暴君、牧师、政党以及官僚才享有的权威”。自从怀特发表了这番令人信服的洞见以来,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家已经详细阐述了新闻媒介及其不断扩张的传播渠道对我们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议程各方面的影响。
在有关这种影响的学术图谱中,最著名且记录最完备的成员之一便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理论,这也是本书的主题。很少有理论刚刚诞生就羽翼丰满。理论通常始自一种简明扼要的洞见,然后经过各种探索者和调查者的多年耕耘,对这一智力领域进行不遗余力的细化和说明,才逐渐清晰起来。议程设置理论的形成正是这种情形。这个理论始自一个简单的假设——关于大众传播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的关注的效果。由此,这个理论逐渐扩展,又纳入许多新的命题,如关于这些效果的心理过程、塑造传播议程的影响因素、媒介信息中特定消息的冲击,以及这种议程设置过程的各种结果。这样,议程设置理论便超越了传统的新闻媒介的效果研究,成为描绘公共事务信息通过不断增加的过剩传播渠道持续流动并产生效果的一张详细图谱。
现今这种理论形式的议程设置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在1967年初的某日,研究者对《洛杉矶时报》头版新闻报道编排的不经意观察。那一天有三条重要新闻:国际新闻,是在英国郡议会选举中工党出人意料地败给了保守党;国内新闻,有一条关于华盛顿政界的丑闻浮出水面;地方新闻,是大洛杉矶地区主持一项联邦资助的全国重点扶贫项目的主管被解职。毫不奇怪,《洛杉矶时报》将地方新闻放在头版头条,而将其他两条国际和国内新闻置于不那么显要的头版次席。如果没有其他两条新闻,这三条新闻中的任何一条都能轻易地登上头版头条。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几位年轻教员的探讨。在世纪广场酒店大厅的周五下午“青年教师会议”上,我们边喝边聊。我们猜测:如果某条新闻被安排到一个不显眼的位置,那么这个事件的冲击会不会因此而降低?这种猜测来自先前在大众媒介对公众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各种分散的观点与经验研究的结果,它们种下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种子。
关于议程设置思想的正式说明开始于1967年秋天,当时我转到北卡罗来纳大学查普希尔分校,在那里遇到了唐·肖(Don Shaw)。从此我们建立了45年以上的友谊与专业上的合作。我们对议程设置思想进行正式调查的最初念头完全基于在洛杉矶时关于新闻报道编排的那些猜测。我们尝试对实际存在的报纸根据同一条新闻完全不同的编排方式,设置一次实验。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观察家报》是一份广受尊重的报纸,它一天之中要出一系列不同的版本,早间各版针对距离夏洛特远近不同的地点,最后一版为本市居民提供新闻。这种多个版本的设计方式会造成一种结果,即某些新闻在一天中的早些时间可能占据头版的显要位置,在接下来的版本中可能退居头版的次要位置,有时会完全退出头版。我们最初打算利用这些版本之间的差异作为实验的基础。但是后来发现,新闻编排上的这些变化毫无规律可循,无论是在题目上,还是在其位置的变化上,因此,我们无法系统地比较它们对公众感知所产生的影响。
尽管遇到了这种挫折,但是理论的想法却仍然迷人,我们决定尝试另外一种方法:对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进行一次小规模的调查,同时,对这些选民经常接触的新闻媒介如何编排选举中的重大事件进行内容分析。选择那些犹豫不决的选民作为样本是基于下列假设:相对于广大选民而言,这些对选举感兴趣却还没有做出决定将选票投给谁的人,可能最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这就是“查普希尔研究”(Chapel Hill Study),即现在公认的议程设置理论的起源。
查普希尔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议程设置”这个词语本身,它使关于媒介影响的这个概念立即在学者中流传开来。查菲(Steve Chaffee)回忆到,在1968年新闻教育协会的年会上,当我第一次向他介绍议程设置研究时,虽然这个新词还很陌生,但他马上就理解了我们研究的焦点。
因为肖学过历史,所以人们预料我们会记下创造“议程设置”一词的准确时间,诸如“8月初的一个周二的下午”之类。然而,无论是我还是肖都没有记住我们想到这个名字的具体时间。1967年我们从美国广播主协会(NAB)申请到一笔小额资金,用于对我们调查的部分资助,在申请书中我们并没有提到“议程设置”这个词。但是我们在1969年向这个协会提交的有关查普希尔研究结果的报告中,却使用了这个词,就好像这个词一直在使用似的。“议程设置”这个词出现在1968年的某个时间。无疑,除了直接参与查普希尔项目的那些人之外,查菲是最早认识到其用处的“裁判者”之一,恐怕他正是第一人。第一章叙述了查普希尔调查的细节以及在查普希尔研究与洛杉矶讨论之前有关这种思想的知识前辈。
套用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话来说,1968年查普希尔调查成功之后,游戏显然就开始了。关于大众媒介对舆论的精确效果,人们发现了充满希望的先导,至少能够撩开这个神秘面纱的一角。接下来,许多“侦探”开始追踪这些线索,力求解释媒介如何影响公众的注意与感知,解释媒介、媒介内容以及媒介受众的各种特点如何调节了这些效果。福尔摩斯的侦破案例被整理成厚厚的九大卷宗。与此非常类似,在议程设置的知识网络中,人们也记录下各种线索与联系。然而,因为传播研究中的观点市场非常自由放任,所以,对于大众媒介议程设置作用的详尽阐释并没有采取一种整齐有序的系统方式。多年里,许多“侦探”在各种地理与文化背景中对许多案例进行研究,这里增加一点,那里增加一点,积累了许多证据;说明议程设置思想的新理论概念也在这个知识网络中不断出现,一会儿在这一部分,一会儿在那一部分。
许多年来,研究的主要重点都是公众议题议程。特别是,作为流行的方式,新闻媒介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通常被人们视为舆论。议程设置理论产生于描述与解释新闻传播就当时议题对舆论产生的影响。这种研究经常采用盖洛普民意调查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使用的一个开放式问题:“什么是这个国家当前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基于这个问题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积累了公众回答的几百个议题,数十年来一直吸引着公众与民意测验专家的关注。
议题议程之外,议程设置理论也包括了公众对政治候选人及其他公众人物的意见,尤其涉及这些人在公众中的形象以及大众媒介在塑造这些公众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些更大的话题议程既包括公众议题,也涉及公众人物,标志着一种重要的理论延伸——从开始时的传播过程,即媒介与公众关注并认为重要的话题,转移到下一阶段,即媒介与公众感知与理解这些话题细节的方式。这第二阶段又为勘察媒介在态度、观点和行为方面的议程设置效果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更近的几十年间,对议程设置效果及其结果的调查已经延展到公共事务的领域之外,也在探索各种不同的事务,如体育、宗教和企业经营中的议程设置作用。所有这些媒介对于公众的效果都在本书的记录范围内。本书将不仅以理论的方式,而且以世界范围内经验证据的方式展示这些效果。
自从1968年创始性的查普希尔研究以来,我们关于议程设置的知识在理论方面的演化过程非常琐碎。但与此相反,下面各章将努力系统有序地展示我们在这些年里学到的理论,力图整合各种不同的大量证据——无论是历史与地理场景的多样,还是媒介与话题的混杂,抑或调查方法的复杂,都体现出研究的多样性。这本书的核心目的就是介绍这个整合的图画。用约翰·帕夫利克(John Pavlik)的话说,就是建立一个议程设置理论的《格雷解剖学》。构成这幅图画的大部分证据来自美国,因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创始人——肖、韦弗(David Weaver)与我——都是美国学者,并且大部分实证调查都是在美国进行的。但是读者也会看到来自英国、德国、西班牙、日本、韩国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大量证据。议程设置理论的优势之一就在于这种证据的地理与文化多样性,它验证了传媒影响社会的最主要方面。
除了对我最好的朋友与长期的研究伙伴肖与韦弗不胜感激之外,本书的成果还要归功于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他们创造了记录于此的不断积累的文献。作为“健忘的教授”,我下面所列的名单可能会遗漏一些做出重要贡献的人,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特别感谢长期以来与我共事的下列诸位:埃斯特万·洛佩斯-埃斯科帕(Esteban Lopez-Escobar)、克雷格·卡罗尔(Craig Carrol)、迪克西·伊瓦特(Dixie Evatt)、萨尔玛·加尼姆(Salma Ghanem)、郭蕾(Lei Guo)、斯皮罗·基欧瑟斯(Spiro Kiousis)、多米尼克·拉索拉萨(Dominic Lasorsa)、保拉·波因德克斯特(Paula Poindexter)、竹下俊郎(Toshio Takeshita)、塞巴斯蒂娜·瓦伦苏埃拉(Sebastina Valenzuela)、武洪(Hong Vu)、韦恩·万塔(Wayne Wanta)和祝建华(Jian�睭ua Zhu)。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詹姆士·迪林(James Dearing)与艾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以前写过《议程设置》一书,这是关于议程设置研究历史与基本思想的必读书。特别感谢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和安德列亚·德鲁甘(Andrea Drugan),他们耐心等待本书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完成。我个人还想感谢下列教授:杜兰大学的沃尔特·威尔科克斯(Walter Wilcox),他引导我去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在斯坦福大学,奇尔顿·布什(Chilton Bush)、里查德·卡特(Richard Carter)、内森·麦克比(Nathan Maccoby)、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指导我一步步沿着理论途径进行探索。更近一点,我要感谢墨西哥大学的伊萨·卢纳(Issa Luna),以及西班牙潘普洛纳的纳瓦拉大学、智利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与迭戈波塔利斯大学的同事,他们对议程设置理论在拉丁美洲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是一幅仍然处于演化中的学术图谱。虽然本书重点讲述的内容是建立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并以媒介为中心研究有关大众媒介在形成舆论方面的已知作用,但是后面几章也讨论了媒介发生影响的更加广阔的背景。对于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这座宝矿,学者们虽然已经开采了超过45年,但它的许多财富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然而,即便是现有的学术图谱,也已经确认了令人振奋的新的探索领域,而当代公众传播系统的流动也创造了细描这幅图谱的无穷新机遇。在评价当前政治传播的新时代时,英国学者布拉姆勒(Jay G. Blumler)与卡瓦纳(Dennis Kavanagh)这样写道: 这种形势对研究而言极有希望,但也需要用想象力来进行裁剪,使其适应这些张力与新的条件……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范式中,议程设置可能是最值得追求的。
本书的目标是展示有关传播媒介在塑造舆论方面所起作用的一些基础思想,并陈列一些支持经验证据的代表性样本。这些知识开启了理解公众传播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路,能够指导未来的理论制图者的探索。
即便在最初的舆论领域内,除了描述与解释大众媒介如何影响我们对公共事务的观点之外,仍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思考。对于记者来说,我们现在讨论的现象,即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就应该推进何种议程而言,还是一个严肃而涵盖广泛的伦理问题。提供“公众需要知道的”新闻是新闻业的一个永恒梦想。然而媒介议程真能反映公众需要知道的事务吗?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节目《夜线》的执行制片人曾经产生了片刻的怀疑,他问道:“我们是什么人,竟认为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设置议程?是什么让我们似乎比周围的人更聪明?”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讲故事的传统,但是,好新闻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讲述那些对公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故事。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作用将新闻及其讲故事的传统与舆论领域联系了起来。对社会而言,这是一种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关系。媒介格局的变化与新闻和政治传播的演变提出了一种关于公众意见形成的重大问题。
用户评价
读完前几章,我发现这本书的叙事风格带着一种近乎冷静的批判性视角,它毫不留情地揭示了权力结构如何利用媒介渠道来构建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共识。我印象最深的是它对“新闻价值”这一概念的解构过程,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传统的新闻学定义上,而是深入探究了政治经济因素如何渗透到日常的新闻选择标准之中。例如,书中对特定议题在不同媒体间的曝光率差异的统计分析,简直令人不寒而栗——那些被刻意边缘化的声音,其缺失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塑造。这种深入骨髓的洞察力,让这本书读起来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它强迫读者跳出自己习惯性的信息茧房,去审视那些每天被我们视为“事实”的报道,其背后可能潜藏的倾向性。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理解现代政治传播和公共舆论形成过程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其坚实且不容置疑的理论基石。它不是一本提供轻松阅读体验的书,但它提供的思考深度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吸引人眼球,封面色彩搭配沉稳又不失现代感,摸上去质感也相当不错,让人忍不住想立刻翻开阅读。我一直对那些宏大的社会现象背后运作的机制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尤其关注信息是如何被筛选、被塑造,最终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认知和判断的。翻开扉页后,排版清晰,字体大小适中,阅读起来非常舒适,即便是长时间沉浸其中也不会感到视觉疲劳。作者在引言部分就抛出了几个极具挑战性的观点,直击当代社会信息洪流中的痛点,这立刻吊起了我的胃口。我尤其欣赏它对于理论框架构建的严谨性,那种层层递进、逻辑缜密的论述方式,让人感到作者对该领域有着深刻且全面的把握。这本书似乎不仅仅是在罗列现象,更像是在搭建一个分析工具箱,教人如何从纷繁复杂的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动态中,抽丝剥茧地找出那些“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没有采用那种空洞的口号式论述,而是用丰富的案例作为支撑,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这对初学者和资深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福音。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学术化,但又不失其作为大众读物的可及性,这平衡掌握得非常巧妙。作者在阐述复杂的概念时,习惯于引入多个学派的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这种多维度的审视方式,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相关理论的理解边界。我特别喜欢它在讨论媒介机构的商业利益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张力时所展现出的那种细致入微的笔触。书中详尽地剖析了广告收入、所有权集中化对新闻报道自由度的制约,这些内容对于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媒体生态至关重要。它不像某些理论著作那样晦涩难懂,而是通过大量的历史案例和现实观察,将理论融入到鲜活的叙事之中。这种叙事策略,让原本枯燥的理论讨论变得引人入胜,仿佛在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进行一次深度的田野考察。这本书更像是一份详尽的“舆论地图绘制指南”,标注了权力流动的关键节点和信息传播的隐形路径。
评分从整体结构来看,本书的逻辑衔接流畅自然,每一次理论的提升都建立在前文扎实的基础上,给人一种步步为营、坚实可靠的阅读体验。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元认知”的能力,即关于“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这种反思。它不仅仅停留在批判媒介表象的层面,而是深入挖掘了影响媒介生产的深层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根源。书中对特定历史时期媒介环境变迁的梳理,展现了作者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历史洞察力。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对照自己日常接触到的信息流进行反思,这种即时的知识迁移和应用,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粘性和有效性。这本书的重量级,在于它敢于挑战那些被我们视为“自然”或“中立”的传播现象,并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将其还原为社会建构的结果。它无疑是理解现代社会信息生态不可或缺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评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在方法论的探讨上尤其出色,它不仅指出了问题,更尝试提供了一种审视和分析问题的框架。作者对“框架效应”的阐述极为精妙,通过对比不同新闻报道如何对同一事件进行“定性”和“定调”,清晰地展示了媒介建构现实的强大力量。我个人的体验是,在阅读完相关章节后,看新闻时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是被动接受信息,而是主动探究信息背后的“叙事选择”。这种主动性的提升,是任何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学术专著能够给予读者的最大馈赠。书中的图表和模型设计得非常直观,辅助理解那些原本比较抽象的社会学概念。对于那些希望将理论应用于现实分析的学生或从业者来说,这些工具性的内容简直是如获至宝。总而言之,这是一部结构严谨、论证有力的作品,它成功地将深奥的学术理论普及化,同时保持了其应有的专业深度。
评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将讨论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或不会做的各种事情。当一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时,池们通常总会想要了解这个人的情况,或调用他们已掌握的有关这个人的各种信息。他们会对他的一般社会经济地位、他的自我观念、他对他们的态度、他的能力、他的可信赖性等等产生兴趣。获得个体的信息,有助于定义情境,能使他人预先知道该个体对他们寄予什么期望,以及他们或许可以对该个体寄予什么期望。
评分还要超过10个字评论,10个字好多呀
评分还要超过10个字评论,10个字好多呀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评分经典专业书,好好学习
评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将讨论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或不会做的各种事情。当一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时,池们通常总会想要了解这个人的情况,或调用他们已掌握的有关这个人的各种信息。他们会对他的一般社会经济地位、他的自我观念、他对他们的态度、他的能力、他的可信赖性等等产生兴趣。获得个体的信息,有助于定义情境,能使他人预先知道该个体对他们寄予什么期望,以及他们或许可以对该个体寄予什么期望。
评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将讨论个体在普通工作情境中向他人呈现他自己和他的活动的方式,他引导和控制他人对他形成的印象的方式,以及他在他人面前维持表演时可能会做或不会做的各种事情。当一个人出现在别人面前时,池们通常总会想要了解这个人的情况,或调用他们已掌握的有关这个人的各种信息。他们会对他的一般社会经济地位、他的自我观念、他对他们的态度、他的能力、他的可信赖性等等产生兴趣。获得个体的信息,有助于定义情境,能使他人预先知道该个体对他们寄予什么期望,以及他们或许可以对该个体寄予什么期望。
评分东西不错,发货也很快。
评分此用户未填写评价内容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牛津社会语言学丛书·语言神话与英语历史 [Language Myths and the History of Engslish]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94375/5aa797f2N49cf7f97.jpg)
![牛津社会语言学丛书·交际界位研究:社会语言学视角 [Stanc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94417/5aa797f2Nc0fb783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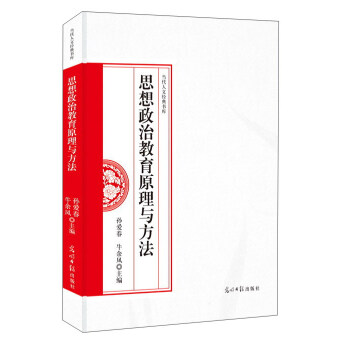












![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17 附光盘) [China Statistics Yearbook on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297676/5a717fecN8baf2e9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