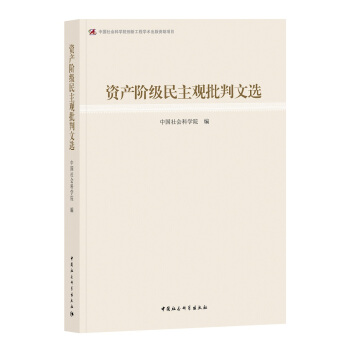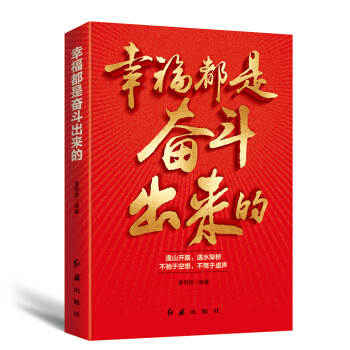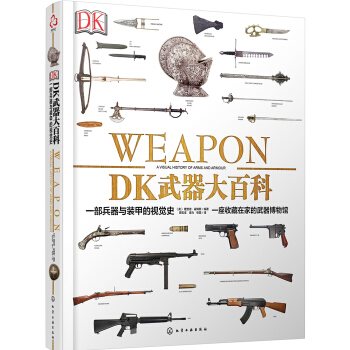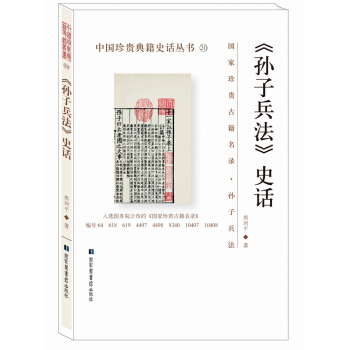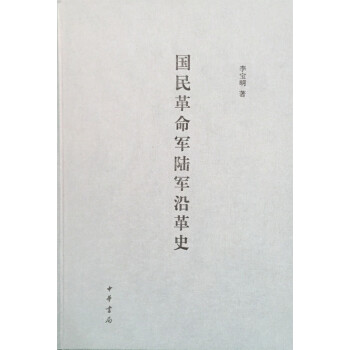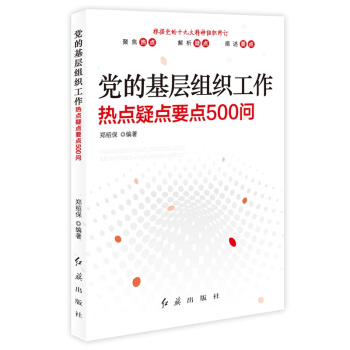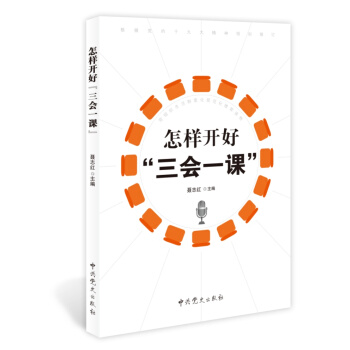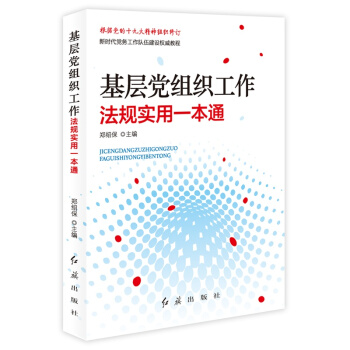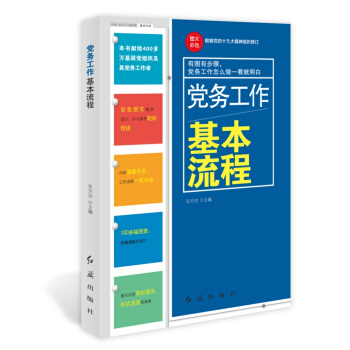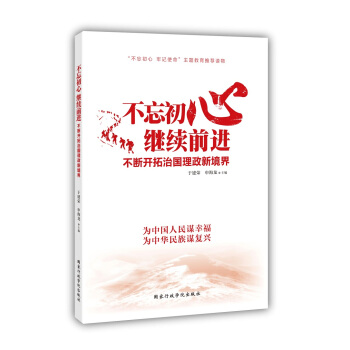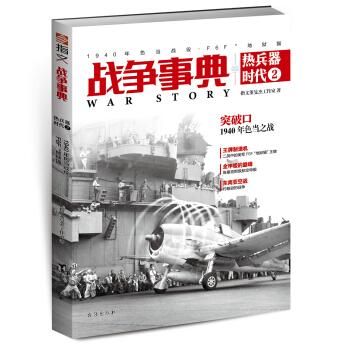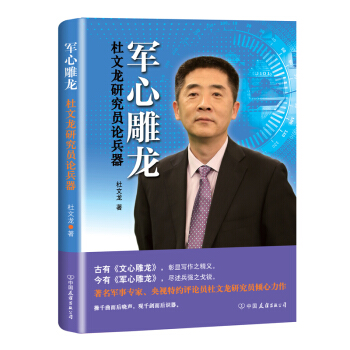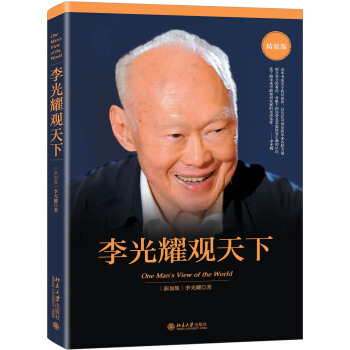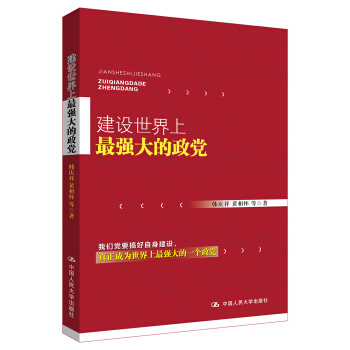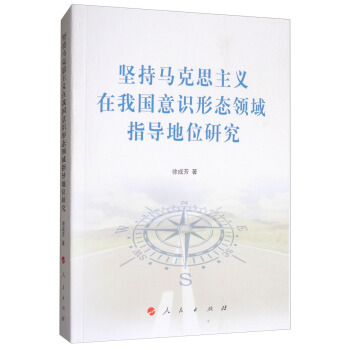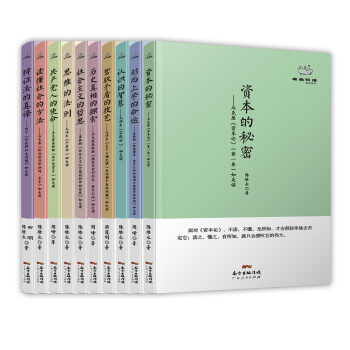编辑推荐
本书是近年来正面阐释功利主义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一方面以颇为独特的方式梳理近代功利主义的历史沿革,另一方面力图从理论的角度回应自罗尔斯以来哲学界对功利主义的整体否定,重申功利主义价值。
内容简介
本书着眼于伊壁鸠鲁传统语境下对快乐、痛苦、效用等概念的讨论,通过对大卫?休谟、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思想家著作的分析,定义了一个古典功利主义的传统,以此为背景阐释关于正义、权利、自由、个体、平等、民主等概念的道德哲学、政治思想与社会理论,并针对一些当代的批评为这一思想传统进行了辩护。
作者简介
弗雷德里克?罗森是伦敦大学学院政治思想史教授。他曾担任伦敦城市大学政治、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与《杰里米?边沁全集》主编。主要作品有《杰里米?边沁与代议制民主》、《边沁、拜伦和希腊:立宪主义、民族主义与早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等。
精彩书评
本书涵盖了许多材料,任何对功利主义感兴趣的读者都能从中获益。它对一些传统论题提出了有趣的观点,并成功地厘清了一些问题,相信这些话题将历久弥新。
——《经济学与哲学》
目录
序 言
缩略语
第一章 导 论
全书要旨
关于道德哲学家的若干注解
关于政治理论家与法理学家的简单注解
上 篇
第二章 功利与正义:伊壁鸠鲁与伊壁鸠鲁传统
伊壁鸠鲁与古代伊壁鸠鲁主义
伽森狄与现代伊壁鸠鲁主义
伽森狄的影响
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的伊壁鸠鲁主义
第三章 逆向解读休谟:功利作为道德的基础
《道德原则研究》和《人性论》中的功利
功利的基础性作用
仁爱、正义与功利
功利与道德
《道德原则研究》与《人性论》
休谟与边沁
第四章 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功利思想
功利和正义
斯密和休谟论正义
斯密论功利:幻象与现实
斯密、休谟以及哲学体系
斯密与边沁
第五章 爱尔维修、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边沁的功利观念
休谟、斯密和爱尔维修
立法者的角色
功利与美德
爱尔维修与边沁
《论教育》
结 论
第六章 斯密《国富论》中的功利观念
“看不见的手”
无意的后果与劳动分工
自 由
劳动、自由和进步状态
第七章 边沁和斯密对自由的论述
边沁的反对派
《为高利贷辩护》以及边沁的其他著作
边沁对斯密的批判
边沁的标题
第八章 作为功利主义者的威廉?佩利
功 利
自 由
结 论
第九章 自由、功利以及刑法改革
自由与刑法
贝卡里亚思想中的罪与罚
边沁的比例理论
关于死刑的争论
流放罪与监禁罪
启蒙与改革
第十章 密尔的快乐论
密尔与卡莱尔
伊壁鸠鲁主义传统
质与量
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第十一章 密尔论正义和自由
正义与功利
正义与自由
自由和真理的脆弱性
下 篇
第十二章 对无辜者的惩罚
唯心主义的背景
后功利主义范式
对功利主义的批驳
第十三章 个人牺牲与最大幸福
边沁的终极原则
快乐和痛苦的位阶
次要原则和权利
最大化和最小化
边沁和密尔思想中的平等和权利
第十四章 多数的暴政
实践中的多数和少数
利益、安全和平等
人民主权和多数统治
民主的专政
多数暴政
第十五章 消极自由
霍布斯和边沁的消极自由思想
边沁和伯林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
自由和民主
值得为之奋斗的消极自由
参考文献
索 引
精彩书摘
本书的目的是要以既有历史精确性又体现哲学重要性的方式阐述大体上从休谟的《道德原则研究》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中存在的功利思想。这一功利思想的开端是这样一种反直觉主义的观念,即认为,功利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作为道德特别是正义的基础的,本书所述及的所有思想家以及伊壁鸠鲁传统中的早期作家都认可这种观念。这一观念一开始就具有反直觉性,这是由于,诸如正义,尤其是以自然正义形式出现的正义,这样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绝对观念,被置于似乎不那么可靠的功利基础之上,这一基础一直被视为是可以因时因地而改变的。功利可以在道德和立法中发挥基础作用,此外,人的幸福是立基于趋乐避苦之上的,古典功利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在拙作中,笔者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种特殊的学说是如何成为一种哲学常识的,并通过诸如休谟、斯密、爱尔维修、佩利、边沁和密尔等一系列作家来考察这一学说的独特性。
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论点关注的是正义与自由的联系。一旦脱离了传统的哲学基础,现代伊壁鸠鲁传统中的正义就要让位于自由,首先是公民自由和自由市场的观念,而后是反对父权制和培育个性,这一点在密尔的《论自由》中达到了极致。正义的任务不再是在私人和公共生活中规制和引导其他美德,而是成为自由得以兴旺、幸福得以实现的规则体系。
这一命题关涉功利、正义和自由之间的联系,在这一命题提出的同时,许多相关的命题也得到了阐发。其中一些主要是历史命题,而另一些则是哲学命题。历史命题致力于厘清十八世纪的古典功利主义脉络,这一任务事后证明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得多。大多数休谟和斯密的研究者都否认休谟和斯密使用的功利概念与到边沁和密尔那里所演变成的“功利主义”之间存在任何重大关联。前面章节大部分精力都用来挑战这一广为流传但错误的观点。
在这一过程中,我竭力将休谟和斯密从所谓“苏格兰启蒙”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禁锢中解脱出来。此外,休谟和斯密的研究者当中绝少有人发现两位哲学家之间在使用功利概念方面的连续性。要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哲学家联系起来建立一种古典功利主义观,就也要在休谟和斯密当中找到共同的志趣以及对功利的阐释。
不过,功利的重要性并不是十八世纪的发现,而是脱胎于早期的伊壁鸠鲁传统,这一传统产生于古代,却以特殊的现代形式盛行于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哲学和科学圈子当中。下一章将简要地讨论现代早期的伊壁鸠鲁主义,我要试图揭示出伽森狄及其众多英国追随者赋予功利的独特作用。
这一素材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功利是如何进入现代哲学思想之中的,此外,这也为古典功利主义传统内部存在的各个重要变种是如何在十八世纪产生的提供了解释。休谟、斯密、爱尔维修和佩利运用功利阐发了不同的论点,他们继承这一更为古老的伊壁鸠鲁传统的不同方式就可以解释这种差别。
在此,笔者通过对边沁功利主义的全新解释,接续了这一古典功利主义学说中迄今为止缺失的联系。这从实质上完全不同于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中对古典功利主义的笨拙描述,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认为,古典功利主义是庸俗的行为功利主义,即允许惩罚无辜者,为了其他人的幸福而牺牲某些人的幸福,导致多数暴政。我的解释也会令人发现,一方面,休谟和斯密在功利、正义和自由方面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联系,另一方面,在类似的命题上,边沁和密尔之间存在着重大的连续性。通常的观点认为,密尔扬弃了边沁非常具有局限性的学说,在论述密尔的两个重要章节中,我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并揭示了其错误性。我也驳斥了在关涉快乐、痛苦和功利方面,边沁并没有与休谟和斯密共享同一语境的观点。
贯穿全书,“启蒙”时常是用于作为参照系的,启蒙也构成了笔者所论及的思想家们的另外一个思想脉络。特别是论述爱尔维修一章,重点放在了法国启蒙运动,在论述休谟和斯密的章节中,评论引发了苏格兰启蒙的话题。
我并不是强烈反对使用这一思想脉络去解读本书讨论的思想家,因为实际上参照启蒙就是参照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但当参照某些独有的语言或文化印记之时,可能就变得毫无助益了,因为这给人看起来仿佛启蒙要么完全只是属于法国的,要么完全只是属于苏格兰的。相反,这些思想家在与其他国家的思想家的接触方面,在新思想的发展与交流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敏捷与韧性令我惊诧不已。在这个意义上,法国或苏格兰启蒙是不存在的。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许多学者强调启蒙的“理性主义”特征,而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伊壁鸠鲁传统中的学者却将感觉,特别是对快乐和痛苦的感觉,作为道德和政治的基础,同时也同样强调激情是动机和行动的基础。总体上或主要以理性为基础的启蒙思想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是格格不入的。
拙作省略了许多功利主义传统中的思想家,这主要是由于时间与空间不允许我进一步扩展。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早期的伊壁鸠鲁传统被高度压缩为几个思想家,诸如伽森狄、培尔、霍布斯、洛克,其他思想家只是简要地得到关注或者被忽略不计。除了佩利,所谓神学功利主义者只是稍作提及,许多重要思想家,诸如哈特利、哈奇森、普雷斯特利、葛德文以及詹姆斯·密尔等人,实际上就忽略不计了。此外,不同学科势必会强调不同的思想家和不同的命题。那些属于英国文学学科的学者可能比其他学者更为关注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之间持续的紧张。道德哲学家势必强调休谟和密尔胜过斯密,经济思想史家则关注斯密胜过休谟。法学家考察布莱克斯通、边沁和奥斯汀,但绝少关注休谟或密尔。从一个学科转向另外一个学科就会在相关文本特别是语境方面遇到不同的争论。我努力运用尽可能多的学科,因为这些学科代表了切入现代伊壁鸠鲁和功利主义传统的最为重要且富有生命力的研究路径。经济思想史家最感兴趣的是论述斯密和边沁的章节;道德哲学家最感兴趣的是论述密尔的章节,而思想文化史家可能最感兴趣的是论述休谟和斯密的素材。不过,拙作总体上是围绕功利、正义和自由之间关系这一命题展开的,这一命题在所有章节都有所阐发。
前言/序言
拙作试图纠正在哲学家、法学与政治学理论家、经济思想史家以及思想文化史家中间常见的对于古典功利主义的种种误解。为此,首先就要重新阐释这一传统中诸如休谟、斯密、爱尔维修、佩利、边沁以及密尔等主要思想家阐发的诸多论点。尽管拙作并不致力于为功利主义作正式辩护,但会为这类辩护提供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尤其出现在最初由伊壁鸠鲁传统所作的对快乐与痛苦问题的诸多讨论中,以及由上述思想家所发展的对功利、正义以及自由之间联系的说明中。此外,拙作也会揭示,对这一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形成的诸多成见是毫无根据的。拙作通篇都认为,古典功利主义代表了丰富的哲学反思传统,特别是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反思,而这一点往往被当代哲学家所忽视或轻易地予以批驳。
本书的上篇主要对古典功利主义进行了阐释。几乎所有篇章都是为拙作量身打造的,那些提交过的研讨报告和(或)论文也都进行了修订。对于下列学术出版机构允许我在第二章中使用已发表的论文谨致谢意:《功利与正义:伊壁鸠鲁与伊壁鸠鲁传统》,发表于Polis,19(2002),93—10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功利思想》,发表于《欧洲思想史》(History of EuropeanIdeas),26(2000),79—103。
下篇包括四篇论文,探讨了对古典功利主义传统常见的一些批判,四篇论文以前都发表过,但编入拙作时都进行了修订。第十二章考察的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认为功利主义允许甚或要求对无辜者进行惩罚,第十三章重新检视了为了其他人或整个共同体的更大幸福而牺牲某些人幸福这一命题。这些论文发表在Utilitas,题为《功利主义与对无辜者的惩罚》,9(1997),23—37,以及《个人牺牲和最大幸福:边沁论功利与权利》,10(1998),129—143。我要感谢编辑和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这篇论文。第十四章考察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导致了多数暴政,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NOMOS XXXIII,《论多数与少数》(ed. J. W. Chapman and AlanWerthheimer,b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in 1990)。本次使用得到了编辑和出版社的慷慨应允。最后一章论《消极自由》最初是1990 年我赴任伦敦大学学院以《思考自由》为题进行的就职演说。参照以赛亚?伯林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这篇论文探讨了功利主义中的自由思想。伯林教授非常热情地阅读了已发表的最初演讲稿,并就其中的论点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议。
在撰写拙作的过程中,本人有幸得到了许多帮助,特此致谢如下: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斯蒂芬?康威(Stephen Conway)、已故的莫里斯?克雷斯顿(Maurice Cranston)、詹姆斯?克里明斯(James Crimmins)、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基里亚科斯?德米特奥(Kyriakos Demetriou)、托尼?德雷伯(Tony Draper)、罗伯特?福克纳(Robert Faulkner)、克努特?哈坎森(Knud Haakonssen)、弗里茨?霍顿(Frits van Holthoon)、特德?洪德里奇(Ted Honderich )、保罗? 凯利(Paul Kelly )、大卫? 利伯曼(DavidLieberman)、道格拉斯? 朗(Douglas Long)、哈维? 曼斯菲尔德(HarveyMansfield)、詹姆斯? 摩尔(James Moore )、彼得? 尼克尔森(PeterNicholson)、凯文?奥洛克(Kevin O�穑遥铮酰颍耄澹�、拉斐尔(D. D. Raphael)、乔纳森?雷利(Jonathan Riley)、伊泽贝尔?里弗斯(Isobel Rivers)、亚历克斯?罗森(Alex Rosen)、菲利普?斯科菲尔德(Philip Schofield)、杰弗里?托马斯(Geoffrey Thomas)、威廉?特文宁(William Twining)、大卫?温斯坦(DavidWeinstein)、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和大卫?沃顿(David Wootton)。
我要特别感谢罗杰?克里斯普对许多章节的评论,包括对密尔一章的评论;感谢詹姆斯?摩尔将我引入现代伊壁鸠鲁传统之中,特别是在伊壁鸠鲁传统与休谟的关系上;感谢凯文?奥洛克在休谟和斯密方面提出的建议和帮助;感谢菲利普?斯科菲尔德倾听、审读并讨论了关于边沁的若干章节。当然,我要为拙作中的论述负责。
许多学者对本人最初思想的提出助益良多。我要感谢日本功利主义研究学会以及英日研究委员会的会员们,特别要感谢永井义雄(Yoshio Nagai)、土方直史(Naobumi Hijikata)、音无通宏(Michihiro Otonashi)、深贝保译(Yasunori Fukagai)、有江大介(Daisuke Arie)以及近藤加代子(KayokoKondo),他们以研讨论文的形式提供了拙作中包括的素材。也要感谢何塞?德?布里托?伊?索萨(Jose de Britoy Sousa)、奥伦?多尔本(Oren BenDor)、曼纽尔? 伊斯卡米拉(Manuel Escamilla)、埃斯波兰萨? 吉桑(Esperanza Guisan)、罗斯?哈里森(Ross Harrison)、加里?麦克道尔(GaryMcDowell),他们在另外的场合讨论了我的想法。我要感谢凯特?巴伯小姐,她热情而极富专业性地协助了文本的呈现工作,还要感谢边沁项目组成员的帮助和鼓励。我想感谢我的家人(玛利亚、格瑞戈、亚历克斯)再一次为我完成这样一个大项目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与其他著作一样,拙作的大部分是居住在彼得?塔维的达特摩尔小镇期间完成的。我要感谢居住在库姆街的邻居们,包括柯林斯、海克尔、沃尔克以及怀特一家,还要感谢小镇上多德以及鲍尔一家不可计数的善行。在伦敦,大量研究是在新大不列颠图书馆中进行的,我在那里得到了慷慨的帮助和高效的服务。
最后,我想将此书谨献给在这一领域对拙作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两位学者:哈特教授(H. L. A. Hart)最先教导我要认真对待边沁,将其视为哲学家,虽然他强调边沁与其说是个功利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个法学家。约翰?罗布森(John M. Robson)教导我,详细编撰的著作可能是富有重大学术洞见的基础。在拙作的许多章节中,卷帙浩繁的多伦多版密尔著作全集令我受益匪浅,也是最高水平的学术样板。
弗雷德里克?罗森
伦敦大学学院
2002 年12 月
拙作试图纠正在哲学家、法学与政治学理论家、经济思想史家以及思想文化史家中间常见的对于古典功利主义的种种误解。为此,首先就要重新阐释这一传统中诸如休谟、斯密、爱尔维修、佩利、边沁以及密尔等主要思想家阐发的诸多论点。尽管拙作并不致力于为功利主义作正式辩护,但会为这类辩护提供一些要素。这些要素尤其出现在最初由伊壁鸠鲁传统所作的对快乐与痛苦问题的诸多讨论中,以及由上述思想家所发展的对功利、正义以及自由之间联系的说明中。此外,拙作也会揭示,对这一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形成的诸多成见是毫无根据的。拙作通篇都认为,古典功利主义代表了丰富的哲学反思传统,特别是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反思,而这一点往往被当代哲学家所忽视或轻易地予以批驳。
本书的上篇主要对古典功利主义进行了阐释。几乎所有篇章都是为拙作量身打造的,那些提交过的研讨报告和(或)论文也都进行了修订。对于下列学术出版机构允许我在第二章中使用已发表的论文谨致谢意:《功利与正义:伊壁鸠鲁与伊壁鸠鲁传统》,发表于Polis,19(2002),93—107;《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功利思想》,发表于《欧洲思想史》(History of EuropeanIdeas),26(2000),79—103。
下篇包括四篇论文,探讨了对古典功利主义传统常见的一些批判,四篇论文以前都发表过,但编入拙作时都进行了修订。第十二章考察的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认为功利主义允许甚或要求对无辜者进行惩罚,第十三章重新检视了为了其他人或整个共同体的更大幸福而牺牲某些人幸福这一命题。这些论文发表在Utilitas,题为《功利主义与对无辜者的惩罚》,9(1997),23—37,以及《个人牺牲和最大幸福:边沁论功利与权利》,10(1998),129—143。我要感谢编辑和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允许我使用这篇论文。第十四章考察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导致了多数暴政,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NOMOS XXXIII,《论多数与少数》(ed. J. W. Chapman and AlanWerthheimer,b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in 1990)。本次使用得到了编辑和出版社的慷慨应允。最后一章论《消极自由》最初是1990 年我赴任伦敦大学学院以《思考自由》为题进行的就职演说。参照以赛亚?伯林的就职演说《两种自由概念》,这篇论文探讨了功利主义中的自由思想。伯林教授非常热情地阅读了已发表的最初演讲稿,并就其中的论点给我提出了许多建议。
在撰写拙作的过程中,本人有幸得到了许多帮助,特此致谢如下:布莱恩?巴利(Brian Barry)、斯蒂芬?康威(Stephen Conway)、已故的莫里斯?克雷斯顿(Maurice Cranston)、詹姆斯?克里明斯(James Crimmins)、罗杰?克里斯普(Roger Crisp)、基里亚科斯?德米特奥(Kyriakos Demetriou)、托尼?德雷伯(Tony Draper)、罗伯特?福克纳(Robert Faulkner)、克努特?哈坎森(Knud Haakonssen)、弗里茨?霍顿(Frits van Holthoon)、特德?洪德里奇(Ted Honderich )、保罗? 凯利(Paul Kelly )、大卫? 利伯曼(DavidLieberman)、道格拉斯? 朗(Douglas Long)、哈维? 曼斯菲尔德(HarveyMansfield)、詹姆斯? 摩尔(James Moore )、彼得? 尼克尔森(PeterNicholson)、凯文?奥洛克(Kevin O�穑遥铮酰颍耄澹�、拉斐尔(D. D. Raphael)、乔纳森?雷利(Jonathan Riley)、伊泽贝尔?里弗斯(Isobel Rivers)、亚历克斯?罗森(Alex Rosen)、菲利普?斯科菲尔德(Philip Schofield)、杰弗里?托马斯(Geoffrey Thomas)、威廉?特文宁(William Twining)、大卫?温斯坦(DavidWeinstein)、唐纳德?温奇(Donald Winch)和大卫?沃顿(David Wootton)。
我要特别感谢罗杰?克里斯普对许多章节的评论,包括对密尔一章的评论;感谢詹姆斯?摩尔将我引入现代伊壁鸠鲁传统之中,特别是在伊壁鸠鲁传统与休谟的关系上;感谢凯文?奥洛克在休谟和斯密方面提出的建议和帮助;感谢菲利普?斯科菲尔德倾听、审读并讨论了关于边沁的若干章节。当然,我要为拙作中的论述负责。
许多学者对本人最初思想的提出助益良多。我要感谢日本功利主义研究学会以及英日研究委员会的会员们,特别要感谢永井义雄(Yoshio Nagai)、土方直史(Naobumi Hijikata)、音无通宏(Michihiro Otonashi)、深贝保译(Yasunori Fukagai)、有江大介(Daisuke Arie)以及近藤加代子(KayokoKondo),他们以研讨论文的形式提供了拙作中包括的素材。也要感谢何塞?德?布里托?伊?索萨(Jose de Britoy Sousa)、奥伦?多尔本(Oren BenDor)、曼纽尔? 伊斯卡米拉(Manuel Escamilla)、埃斯波兰萨? 吉桑(Esperanza Guisan)、罗斯?哈里森(Ross Harrison)、加里?麦克道尔(GaryMcDowell),他们在另外的场合讨论了我的想法。我要感谢凯特?巴伯小姐,她热情而极富专业性地协助了文本的呈现工作,还要感谢边沁项目组成员的帮助和鼓励。我想感谢我的家人(玛利亚、格瑞戈、亚历克斯)再一次为我完成这样一个大项目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与其他著作一样,拙作的大部分是居住在彼得?塔维的达特摩尔小镇期间完成的。我要感谢居住在库姆街的邻居们,包括柯林斯、海克尔、沃尔克以及怀特一家,还要感谢小镇上多德以及鲍尔一家不可计数的善行。在伦敦,大量研究是在新大不列颠图书馆中进行的,我在那里得到了慷慨的帮助和高效的服务。
最后,我想将此书谨献给在这一领域对拙作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两位学者:哈特教授(H. L. A. Hart)最先教导我要认真对待边沁,将其视为哲学家,虽然他强调边沁与其说是个功利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个法学家。约翰?罗布森(John M. Robson)教导我,详细编撰的著作可能是富有重大学术洞见的基础。在拙作的许多章节中,卷帙浩繁的多伦多版密尔著作全集令我受益匪浅,也是最高水平的学术样板。
弗雷德里克?罗森
伦敦大学学院
2002 年12 月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古典功利主义 目录 引言 功利主义的源起与历史语境 “古典功利主义”的界定与范畴 本书的研究旨趣与结构安排 第一章:休谟的审慎功利主义 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与功利主义的萌芽 “效用”的观念在休谟政治哲学中的地位 对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功利性审视 休谟功利主义的局限与承续 第二章:边沁的快乐计算与立法原则 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快乐与痛苦的量化分析:功利原则的基石 立法原则的建构:基于功利计算的制度设计 对财产、刑罚与法律改革的功利性论证 边沁功利主义的革新性与争议 第三章: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的精进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回应 快乐的“质”的区分:区分高等与低等快乐 个体自由与功利主义的调和:论“自由”的功利价值 功利主义与正义、权利的辩证关系 密尔的功利主义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应用 第四章:詹姆斯·密尔与功利主义的早期传播 詹姆斯·密尔的政治经济学与功利主义的结合 对代议制政府与民主改革的功利性辩护 功利主义在教育与社会改良中的实践 詹姆斯·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特征 第五章:功利主义的理论挑战与演变 对功利主义“结果主义”的批评 “平均功利主义”与“功利主义悖论”的探讨 早期功利主义者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功利主义对后世政治哲学的深远影响 结语 古典功利主义的遗产与当代意义 对未来政治思想研究的启示 引言 功利主义的源起与历史语境 政治思想史的长河中,鲜有哪个思想流派能像功利主义那样,以其简洁而强有力的原则,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社会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以及道德判断的标准。从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浪潮中孕育而生,到十九世纪达到其巅峰,古典功利主义以一种务实而激进的方式,挑战了传统的政治与道德权威,将“幸福”与“效用”置于政治思考的核心。本书所要深入探讨的“古典功利主义”,并非一个孤立的思想体系,而是植根于特定历史语境,由一系列思想家在互动与对话中逐渐塑造而成的一个复杂而富有活力的思想图景。 十八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变革与反思的时代。科学革命的理性之光照亮了人类的认知,启蒙思想家们纷纷质疑中世纪以来的神学权威、贵族特权以及封建等级制度。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现世的福祉,寻求一种更为理性、更为公正的社会组织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政治哲学,无论是基于神圣契约,还是基于自然权利,都面临着严峻的拷问。人们需要一种能够解释和指导社会变革,并能为普遍幸福提供坚实基础的理论。功利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开始萌芽并成长。它脱离了抽象的形而上学思辨,将目光聚焦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快乐与痛苦,并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构建一套能够评价行为、制度乃至法律的道德和政治准则。 “古典功利主义”的界定与范畴 本书所关注的“古典功利主义”,并非指代某一单一理论,而是涵盖了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期,由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所发展和阐释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核心脉络。这一时期的功利主义,以其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普遍追求,以及对行为和制度效用性的强调为标志。核心人物包括,但不仅限于,戴维·休谟(David Hume)的初步构想,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系统奠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精进与辩护,以及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的早期传播与实践。 “古典”二字,不仅指向其历史年代,更在于其所奠定的基础性地位。后世的功利主义,如规则功利主义、负功利主义等,虽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修正或发展,但无不与古典功利主义的核心理念有所关联,或对其进行回应。因此,理解古典功利主义,是把握整个功利主义思想发展脉络的关键。本书将聚焦于这一时期思想家们关于功利原则的定义、应用及其在政治、道德、法律等领域的论证,力图展现其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其理论的内在张力。 本书的研究旨趣与结构安排 本书旨在对古典功利主义进行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梳理与分析。我们不仅将追溯其思想的起源,理解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成逻辑,更将细致考察各位核心思想家所贡献的独特见解,以及他们之间在理论上的传承、发展与争论。通过对休谟的道德情感与效用观念的初步探究,我们可以看到功利主义的思想火种;边沁对快乐计算的创新,为功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并将其转化为一项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立法原则;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在其父的理论基础上,对功利主义进行了更为精妙的辩护,尤其是在处理快乐的质量、个体自由以及正义等问题上,展现了功利主义的深刻思考;而詹姆斯·密尔则在功利主义的早期传播和理论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书的结构安排,力求循序渐进,层层深入。我们首先从功利主义思想的萌芽——休谟的哲学出发,考察其道德情感理论中蕴含的功利性因素,以及他对社会秩序与法律的理性审视,尽管休谟本人并未明确提出“功利主义”这一术语,但其思想无疑为后来的功利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接着,我们将重点探讨功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杰里米·边沁。边沁的“快乐计算”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立法原则,是古典功利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贡献,我们将详细分析其理论的构成、应用及其对现代法律和政治改革的影响。随后,我们将转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深入剖析他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发展,特别是其关于“快乐质量”的区分,以及如何将功利主义与个体自由、正义等重要价值进行调和,这使得功利主义思想得以超越其早期形式,展现出更为成熟的面貌。同时,我们也将在适当的位置,探讨詹姆斯·密尔在功利主义传播和早期实践中的贡献,理解功利主义如何在思想界和现实政治中落地生根。 最后,本书将对古典功利主义的理论挑战与演变进行总结性反思,考察后世对功利主义提出的批评,以及古典功利主义思想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面向。通过这样的结构安排,我们希望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系统且富有洞察力的古典功利主义思想图景,并揭示其在塑造现代政治与道德观念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以及其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的深刻启示意义。 --- 第一章:休谟的审慎功利主义 休谟的道德情感理论与功利主义的萌芽 戴维·休谟,这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巨匠,在其宏伟的哲学体系中,虽然并未直接使用“功利主义”这一术语,但其对人类道德情感的深刻洞察,以及对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的理性审视,为后来的功利主义思想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休谟的道德哲学,将道德判断的来源从理性与义务,转向了人类的同情心与情感。他认为,道德的善恶并非源于理性对客观真理的认知,而是源于我们能够对他人行为产生的感受,特别是那些能够引发我们赞许或不满的情感。这种对情感的强调,为功利主义将快乐和痛苦作为道德评价的核心奠定了先声。 休谟在《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与《道德原理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等著作中,反复论述了“效用”(utility)在道德和政治判断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之所以赞许某些品质,例如仁慈、公正、智慧、勤勉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品质有助于个体自身或他人获得幸福与福祉。相反,那些导向痛苦、灾难或不便的品质,则会招致我们的厌恶。休谟指出,“凡是能使人感到愉快的性质,以及能使他人感到愉快而又非出于特殊义务的性质,都属于道德上的赞许之列。”[1] 这种对“愉快”和“方便”的关注,正是功利主义“效用”观念的雏形。换言之,一个行为或一个品质之所以被认为是道德的,是因为它能够产生积极的、令人愉悦的后果,即具有“效用”。 “效用”的观念在休谟政治哲学中的地位 休谟的政治哲学,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其对“效用”的关注。与一些将政治秩序建立在神圣契约或天赋权利上的思想家不同,休谟更倾向于从经验和理性出发,来审视和解释政治制度的起源与维系。他认为,社会秩序和政府的权威,并非来自某种先验的承诺,而是源于其能够提供的实在的益处——即“效用”。人们服从法律,拥护政府,并不是因为被某种抽象的义务所束缚,而是因为这些法律和政府能够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幸福和安全。 在《论礼让的服从》(Of Passive Obedience)等篇章中,休谟明确指出,政治上的服从,其最终目的在于维护和平与秩序,避免无政府状态带来的灾难。他写道:“即使是最暴虐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要好。”[2] 这种论断,并非是对暴政的辩护,而是强调了秩序本身所具有的根本性效用。没有秩序,个人的自由、财产乃至生命都将无法得到保障,更遑论追求幸福。因此,任何能够有效维持秩序的政治制度,都因其具有的“效用”而获得了其合法性基础。 休谟对法律的看法,也与其对效用的重视紧密相关。他认为,法律的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共同利益,其合理性在于它能够为社会成员带来长远的福祉。他虽然也承认正义的重要性,但同样指出,所谓的“正义”原则,其根本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如果某些传统或法律虽然在形式上符合某种抽象的正义原则,但实际上却会损害社会整体的效用,那么它们就应该被质疑和改革。这种将法律和制度的价值归结于其“效用”的思路,无疑是对后世功利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铺垫。 对法律、制度与社会秩序的功利性审视 休谟的功利性审视,渗透到他对社会各个层面的观察之中。在《论道德的普遍原则》(Of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Morality)中,他讨论了财产的制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之所以被普遍接受和遵守,是因为它能够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财富的生产,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福祉。尽管这种制度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不平等,但其整体的效用仍然大于其负面影响。 同样,在《论国民的财富》(Of the Balance of Trade)等经济思想中,休谟也表现出其功利主义的倾向。他反对重商主义的一些保护性政策,认为这些政策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对某些行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会损害国家整体的贸易和经济发展,降低国民的整体福利。他推崇自由贸易,认为这能够最大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增进国际间的合作,从而为各国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对于政治制度,休谟倾向于一种审慎的改革观。他认为,由于政治制度的复杂性,任何激进的、缺乏经验基础的改革都可能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甚至破坏现有的秩序,反而降低社会整体的效用。因此,他主张在保留现有制度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渐进式的、基于经验证据的改进。这种审慎的态度,虽然有时被视为保守,但其核心仍然是对“效用”的考量——即改革的潜在收益是否能够显著地大于其潜在的风险。 休谟功利主义的局限与承续 休谟的贡献在于,他将道德和政治判断的重心,从抽象的理性原则,转移到了人类实际的情感体验和可观察的后果上,并强调了“效用”在这些判断中的核心地位。他为功利主义打开了一扇重要的思想窗口,让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通过关注行为和制度的实际效果,来构建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然而,休谟的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他的“效用”概念,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愉快”和“方便”,缺乏边沁那样明确的量化标准。他的道德情感理论,虽然揭示了人类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但对于如何处理不同个体之间情感冲突,以及如何量化和比较不同效用,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尽管如此,休谟的思想为功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他的强调经验、观察和实际效果的分析方法,以及他对“效用”重要性的洞察,被后来的边沁和密尔继承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系统而影响深远的古典功利主义。休谟的“审慎功利主义”,更像是一种前奏,一种为宏大的功利主义乐章铺陈的基调,为后续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1] 休谟,《道德原理研究》,第二章,节选。 [2] 休谟,《论人性》,第三卷,第二卷。 --- 第二章:边沁的快乐计算与立法原则 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 杰里米·边沁,这位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被誉为古典功利主义的奠基人。他以其严谨的逻辑、激进的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怀,将功利主义理论系统化,并赋予其强大的实践指导意义。边沁最著名、也是最具标志性的功利主义原则,便是:“当一项行为的原则,是增加快乐的量时,它就是正确的,而当是减少快乐的量时,它就是错误的。”[1] 这一原则被他进一步扩展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 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受到两种“主权者”(sovereign masters)的支配,那就是快乐(pleasure)和痛苦(pain)。它们不仅决定了我们做什么,也决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道德的真谛,就在于认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导我们的行为。因此,一个行为在道德上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它所产生的快乐和痛苦的总量。当一个行为能够最大化整体的快乐,并最小化整体的痛苦时,它就是道德上可取的。这一原则,为我们评价行为、制度乃至法律提供了一个清晰而统一的标准。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非简单地鼓励自私自利的享乐,而是要求我们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时,必须考虑他人的福祉,并且以社会整体的幸福为最高目标。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一种“群体性”的功利主义,它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局部利益,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福祉。这种对集体幸福的强调,使得功利主义成为一种具有社会关怀和改革精神的思想流派。 快乐与痛苦的量化分析:功利原则的基石 边沁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他试图对快乐和痛苦进行一种量化的分析,即所谓的“快乐计算”(felicific calculus)。他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维度来衡量快乐和痛苦的强度,从而在不同行为或不同结果之间进行比较。这些维度包括: 1. 强度(Intensity):快乐或痛苦的程度有多大。 2. 持久度(Duration):快乐或痛苦持续的时间有多长。 3. 确定性或不确定性(Certainty or Uncertainty):获得快乐或遭受痛苦的可能性有多大。 4. 临近性或遥远性(Propinquity or Remoteness):获得快乐或遭受痛苦在时间上有多么接近。 5. 繁殖性(Fecundity):如果是一个快乐,它能否带来更多的快乐;如果是一个痛苦,它能否带来更多的痛苦。 6. 纯洁性(Purity):一个快乐是否会伴随着痛苦;一个痛苦是否会伴随着快乐。 7. 范围(Extent):有多少人会受到这种快乐或痛苦的影响。 通过对这些因素的细致考察,边沁认为,我们可以对一项行为或一项法律所带来的总体快乐和痛苦进行一个相对客观的计算。尽管边沁本人也承认,这种计算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在不同人之间的主观感受上也存在差异,但他坚信,这种量化分析的尝试,是理性地指导人类行为,并构建公正社会的必要步骤。这种对“数量”的强调,使得边沁的功利主义区别于模糊的道德情感,而成为一种更为精确和可操作的理论。 立法原则的建构:基于功利计算的制度设计 边沁的功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哲学,更是一套具有强大改造力量的政治和法律改革蓝图。他坚信,只要遵循功利原则,就可以设计出最能促进社会整体幸福的法律和制度。因此,他将功利主义视为“立法者”最重要的指南。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立法原则。他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促进公民的幸福,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制定恰当的法律。法律的效力,在于它能够通过奖励和惩罚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使其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幸福的方向发展。 对于立法者而言,边沁提出了以下关键点: 明确目标:立法者必须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一切立法的终极目标。 行为分类:立法者需要分析不同行为所带来的快乐和痛苦,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法律。 惩罚与奖励:法律的实施,离不开适当的惩罚和奖励。边沁对惩罚的原则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强调惩罚的必要性在于其威慑作用,但同时也应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即惩罚的成本不应大于其所防止的犯罪所带来的危害。 制度设计:边沁对各种制度,如监狱、教育、选举制度等,都进行了功利主义的分析和设计。他著名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设计,便是基于最大化效率和最小化成本的功利考量。 边沁的立法思想,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他反对基于传统、宗教或虚幻的“自然权利”来制定法律,而是强调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其是否能够真正地增进公民的福祉。 对财产、刑罚与法律改革的功利性论证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在他的具体法律和社会改革主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关于财产,边沁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够刺激人们的生产和创造力,从而带来更大的社会财富和整体幸福。然而,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同样建立在其对整体效用的贡献之上。如果某个财产所有权的存在,会带来比其消失所带来的好处更大的痛苦,那么这种所有权就应该被重新审视。 在刑罚方面,边沁对当时英国残酷而低效的刑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刑罚的唯一合法目的就是预防犯罪,而预防犯罪的关键在于其威慑作用。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刑罚的原则,例如:刑罚的理由应当是防止更大邪恶的发生;刑罚应当是可变的,以适应不同罪行的严重程度;刑罚应当足够,但又不过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痛苦;刑罚的成本不应超过其预期的收益。这些原则,深刻地影响了现代刑法理论的发展。 边沁还对法律改革充满了热情。他认为,许多陈旧的法律和制度,都未能遵循功利原则,反而给社会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和痛苦。他积极参与和推动了英国的法律改革,包括起草新的法典、改进司法程序等。他提出的“国民教育”计划,也是为了通过提高公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来增进社会的整体幸福。 边沁功利主义的革新性与争议 边沁的功利主义,无疑是一场思想革命。它将道德和政治判断从抽象的义务论和自然法论中解放出来,提供了一个以经验为基础、以人类福祉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它的革新性在于: 普世性:将快乐和痛苦作为人类普遍的经验,从而为构建普遍适用的道德和法律原则提供了可能。 理性主义:强调通过理性分析和计算,来指导人类行为和制度设计。 改革导向: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鼓励人们质疑旧的、不合理的制度。 然而,边沁的功利主义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猪哲学”的指责:批评者认为,边沁对快乐的量化和简单的“最大幸福”原则,将人类的追求简化为低级的物质享受,忽视了精神、美德等更为深刻的价值。 个体权利的困境:当多数人的幸福与少数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时,功利主义如何处理?边沁的理论似乎倾向于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成全多数人的幸福,这可能导致对个体权利的侵犯。 计算的难度:快乐和痛苦的量化,本身就存在极大的主观性和操作上的困难。 尽管存在争议,边沁的功利主义以其系统的理论和强大的实践力量,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法律理论和社会改革。他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以及对“效用”的强调,成为古典功利主义的基石,为后世的思考者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1]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第一章,第一节。 --- 第三章: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的精进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批判与回应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作为边沁的追随者和理论继承者,却并非盲目地重复前人的思想,而是以其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哲学思考,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了精进与辩护,使其得以超越早期的某些局限。密尔最直接的批评,集中在边沁对快乐的简单量化以及对快乐“质”的忽视。边沁曾认为,“如果力量是相同的,那么,如果它能引起更多人,或者更多具有优势的人,那么它在总量上将比引起较少人,或者较不具优势的人要好。”[1] 这种“数量至上”的观点,在密尔看来,未能充分体现人类经验的复杂性。 密尔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对边沁理论的修正。他承认边沁将功利主义与快乐、痛苦的原则联系起来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边沁“未能注意到快乐的质的不同”。[2] 密尔指出,人类不仅仅是追求快乐的生物,更是具有情感、理智和道德能力的个体。有些快乐,即使在量上不如某些低级快乐,但其“质”却更为优越,更能满足人类的根本需求。因此,仅仅考虑快乐的数量,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而充实的功利主义伦理。 快乐的“质”的区分:区分高等与低等快乐 这是密尔对功利主义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将快乐区分为“高等快乐”(higher pleasures)和“低等快乐”(lower pleasures)。高等快乐,通常与智力、情感、想象力以及道德意识相关,例如求知、艺术欣赏、友谊、道德满足等。低等快乐,则更多地与感官体验相关,如食欲、肉体上的舒适等。 密尔的著名论断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3] 这句话清晰地表明,密尔认为,即使是较低级别的快乐,如果能被具有较高能力的人所体验,也比单纯的、大量的低级快乐更有价值。反之,即使是低级快乐,如果它能被理解和体会到其局限性,并且拥有体验高等快乐的能力,那么这个人也不会选择沉溺其中。 密尔的这一区分,并非是要否定低级快乐的价值,而是要强调,人类的幸福不仅仅在于生理上的满足,更在于智力和精神层面的充实。高等快乐,虽然可能伴随着更多的挣扎和不确定性,但其带来的满足感是更为深刻和持久的。这种对快乐“质”的区分,使得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包含了一种对人类高贵品格的肯定和追求。它回应了边沁“猪哲学”的批评,为功利主义注入了更深厚的哲学内涵。 个体自由与功利主义的调和:论“自由”的功利价值 密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他如何将功利主义与个体自由和个人权利进行调和。他深知,在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高原则时,个体可能面临被集体牺牲的风险。尤其是在对待少数群体、异见者时,多数人的意志可能形成一种“多数人的暴政”,对个体的自由构成威胁。 在《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密尔为个体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提供了强有力的功利主义辩护。他认为,尽管限制言论自由在短期内可能避免一些不快或冲突,但从长远来看,对言论自由的压制,会损害社会整体的进步和福祉。原因如下: 可能被压制的意见是真理:我们不能确信自己所拥有的意见是绝对真理,如果压制了错误的意见,我们也就失去了反驳错误、巩固真理的机会。 即使是错误意见,其辩论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真理:通过与错误意见的辩论,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真理的含义,并使其根基更加牢固。 真理可能被部分地揭示:往往,真理并非全然正确,而是在不同意见的碰撞中被逐步完善和揭示。 压制错误意见,会削弱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环境中,我们对真理的理解就会变得机械和僵化。 因此,密尔认为,保护个体表达自由的权利,尽管有时会带来一些不便或冒犯,但从长远来看,它对于增进人类知识、促进社会进步以及最终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具有不可估量的功利价值。这种将自由视为一种重要的、长远的功利性工具的论证,成功地化解了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潜在矛盾。 功利主义与正义、权利的辩证关系 除了自由,密尔还探讨了功利主义与正义、权利的关系。他认识到,“正义”是一个在道德判断中具有特殊分量的概念,人们对其有着强烈的感受。他指出,正义的观念,与个人权利的观念紧密相连,而个人权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维护社会整体福祉所必需的。 密尔认为,正义并非是独立于功利主义之外的原则,而是功利主义原则在社会互动中的一种特殊、重要的应用。当某人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这往往意味着他的某种权利受到了侵犯,而这种权利的侵犯,最终会损害社会整体的幸福。例如,盗窃和欺骗等行为,不仅侵犯了个人财产和诚信的权利,更会破坏社会秩序,降低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福祉。 因此,密尔将正义的观念,归结为对“普遍功利”(general utility)的关注。那些被普遍认为是公正的行为,往往是最有利于全体人类的。反之,那些被认为是邪恶的行为,往往是对全体人类福祉的损害。这种将正义与权利纳入功利主义框架的论证,使得功利主义在回应人们对公平和公正的诉求时,显得更为充实和令人信服。他认为,人们对正义的强烈情感,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遵守正义原则,是维护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而这种前提,最终服务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密尔的功利主义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应用 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不仅在理论上进行了精进,更在社会与政治实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教育改革:密尔始终坚信教育对于提升个人和社会的功利价值至关重要。他积极倡导普及教育,特别是女性教育,认为提高全体公民的知识和品德水平,能够最大化社会整体的幸福。 妇女解放:作为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密尔在《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中,运用功利主义的论证,猛烈批判了当时对女性的压迫。他认为,剥夺女性的自由和权利,不仅对女性本身是一种巨大的不公,更是对社会整体人才资源的浪费,极大地削弱了社会整体的功利。 政治改革:密尔支持代议制民主,但他同样警惕多数人的暴政。他提出了一些关于投票权和议会制度的改革建议,例如,主张赋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多的投票权,以期更好地代表和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 经济思想:在经济领域,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既包含了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坚持,也反映了他对社会分配公平的关切,体现了其功利主义思想在经济政策上的应用。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功利主义,以其对快乐“质”的区分,对个体自由与正义的辩护,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深远影响,将古典功利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成功地将这一学说从一种简单的快乐计算,发展成为一种更为丰富、更为人道、也更具说服力的道德和政治哲学体系。 [1]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第一章,第十三节。 [2] 密尔,《功利主义》,第二章。 [3] 同上。 --- 第四章:詹姆斯·密尔与功利主义的早期传播 詹姆斯·密尔的政治经济学与功利主义的结合 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作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父亲,是功利主义思想在十九世纪初叶的重要传播者和早期实践者。他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并且在当时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詹姆斯·密尔的思想,深刻地受到边沁的影响,他积极地将功利主义原则应用于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改革之中,并身体力行地推广这一学说。 詹姆斯·密尔在其著作,例如《英国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和《论政治经济学》(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清晰地展现了功利主义的核心理念。他认为,任何制度、法律或政策,其价值高低,都应以其能否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这种将功利原则作为判断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是他思想的鲜明特征。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詹姆斯·密尔是古典经济学的坚定拥护者,并且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经济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即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是最大化社会财富和增进国民福祉的最有效途径。他相信,个人的追求私利,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下,最终会导向公共利益的实现。 他强调,政府的角色应当是有限的,其主要职责在于维护法律秩序、保障私有财产,并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过度干预经济,会破坏市场机制的效率,反而损害整体的功利。因此,他主张减少政府的干预,推崇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这种对经济自由的强调,正是基于其功利主义的考量——即经济自由能够最大化生产力,从而最大化社会整体的幸福。 对代议制政府与民主改革的功利性辩护 詹姆斯·密尔不仅是理论家,更是积极的政治改革倡导者。他坚信,改进政治制度,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关键。他旗帜鲜明地支持代议制民主,并为之提供了功利主义的论证。 他认为,君主制或寡头制政府,往往是为统治者自身而非被统治者谋福利,其结果是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代议制政府,则通过让民众拥有选举代表的权力,使得政府的行为能够更接近民众的意愿,从而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他认为,代表们会因为担心在下次选举中落败,而不得不关注选民的利益。 然而,詹姆斯·密尔也认识到代议制政府潜在的弊端,尤其是“多数人的暴政”问题,这与他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担忧不谋而合。但相较于儿子更为精妙的辩护,詹姆斯·密尔的论证更为直接。他认为,即使存在少数人的利益被牺牲的风险,代议制政府相较于专制政府,仍然是“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佳守护者。 他积极参与了当时英国的政治改革运动,例如支持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他认为,扩大选举权,让更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拥有投票权,是使政府更加关注人民福祉的重要步骤。这种对民主改革的推动,正是基于其坚定的功利主义信仰——改革能够带来更广泛的利益,从而增进社会整体的幸福。 功利主义在教育与社会改良中的实践 詹姆斯·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更深入到教育和社会改良的实践中。他作为一位教育家,对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教育方式,可谓是功利主义思想在个体培养上的极致体现。他为儿子制定了极其严苛的学习计划,从小就让他接触大量的经典著作和复杂的知识,其目的在于最大化儿子的智力和能力,以期他将来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更大的“功利”。 他相信,教育是提升社会整体功利水平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通过普及和改进教育,可以提高公民的理性能力、道德情操和生产技能,从而减少犯罪,增加财富,提升生活品质。因此,他大力提倡改革当时的教育体系,使其更具实用性和效率。 此外,詹姆斯·密尔也关注社会改良。他与边沁等人共同发起了“供给学会”(Utilitarian Society),旨在聚集有志于功利主义研究和推广的人士,共同探讨如何将功利主义原则应用于社会现实。他们关注公共卫生、贫困问题、监狱改革等社会议题,并试图用功利主义的视角来寻找解决方案。 他认为,一个“好的”社会,是能够为绝大多数成员提供最大化幸福的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不断地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改革,来优化制度和政策,淘汰那些不再能带来最大功利的部分。 詹姆斯·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特征 詹姆斯·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强烈的边沁主义色彩:他几乎完全接受了边沁的快乐计算原则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目标,并且将其作为一切判断的出发点。 注重实践与改革:与纯粹的理论家不同,詹姆斯·密尔更关注如何将功利主义原则应用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中,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改革者。 对理性与科学方法的推崇:他相信,通过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方法,能够有效地衡量行为和制度的功利,并据此做出最优的选择。 对经济自由的强调:他将功利主义原则与古典经济学紧密结合,认为经济自由是实现社会整体福祉的重要保障。 詹姆斯·密尔在功利主义思想的传播和早期实践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边沁的思想,更通过自己的著作和实践,将功利主义的影响力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功利主义在十九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后来的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现实背景。 --- 第五章:功利主义的理论挑战与演变 对功利主义“结果主义”的批评 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伦理,其核心在于评价行为的道德性,完全取决于其产生的后果。这意味着,即便是出于善意或遵循某些道德规则的行为,如果其结果是负面的,那么在功利主义的视角下,它就可能是错误的。这种纯粹基于后果的评价方式,引来了深刻的理论挑战。 批评者认为,这种“结果主义”忽视了行为本身固有的道德属性。例如,在功利主义框架下,如果一个谎言能够带来比说实话更大的“快乐总量”,那么这个谎言在道德上就是可取的。这与人们普遍的道德直觉相悖,即诚实是一种美德,即使在某些情况下,说谎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好处。 此外,“结果主义”还可能导致一种道德上的机会主义。也就是说,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功利,人们可能会被鼓励去进行一些在常规道德观念中被视为邪恶的行为,只要他们能够确保其后果是积极的。例如,是否可以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而牺牲另一个无辜的人?功利主义的纯粹后果计算,可能会在这种极端情况下陷入困境。 “平均功利主义”与“功利主义悖论”的探讨 随着功利主义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表述方式,其中“平均功利主义”(average utilitarianism)与“总功利主义”(total utilitarianism)的区分,带来了新的理论问题。总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化所有个体的快乐总和。而平均功利主义则追求最大化每个个体的平均快乐水平。 在某些情境下,这两种表述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例如,一个拥有十亿人的社会,其中所有人快乐水平为10;而另一个拥有五亿人的社会,其中所有人快乐水平为11。总功利主义会偏好第一个社会(10 x 10亿 = 100亿),因为它拥有更高的快乐总和。而平均功利主义则会偏好第二个社会(11 x 5亿 = 55亿,但平均为11 > 10),因为它拥有更高的平均快乐水平。 更具争议的是“功利主义悖论”(utilitarian paradoxes),例如“功利主义奴隶制”的论证。这种论证指出,在某些理论构建下,如果一个社会能够通过奴役一部分人来为绝大多数人带来巨大的快乐,那么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奴役似乎是可以被辩护的。这显然与现代社会的普遍道德观念产生尖锐的冲突。这些悖论的出现,迫使功利主义者重新审视其理论的合理性,并寻求更精密的论证来回应这些挑战。 早期功利主义者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尽管古典功利主义的核心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其早期思想家们,如边沁和密尔父子,并非忽视了“个人”的重要性。相反,他们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边沁的“快乐计算”虽然关注群体,但其基础是个体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他相信,通过个体经验的集合,可以推导出社会整体的幸福。 詹姆斯·密尔通过对儿子的严苛教育,体现了对个体潜能最大化的重视,他认为,最大限度地发展个体的智力和能力,是实现社会整体功利的重要途径。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更是将个体自由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是实现长远社会功利的关键。他反对将功利主义理解为压制个体、迎合多数的工具。相反,他强调,真正的功利,在于尊重和发展个体的独特性,并允许他们在自由的环境中贡献自己的才智。 因此,可以说,古典功利主义者并非简单地将个体视为达成多数人幸福的工具,而是试图在个人自由、个体发展与社会整体福祉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他们对个体潜能的关注,以及对个体自由的辩护,使得功利主义在理论上具有了更强的包容性和人道主义色彩。 功利主义对后世政治哲学的深远影响 尽管面临诸多理论挑战,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潮,对后世的政治哲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政策分析与评估:功利主义的思想,尤其是在边沁和密尔的阐释下,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提供了重要的工具。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等方法,就是功利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体现。政府和机构常常会通过权衡不同政策选项所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来做出决策。 伦理学研究:功利主义是现代伦理学讨论中绕不开的重要流派。它促使后来的伦理学家们思考,如何在后果与义务、个体权利与集体利益之间做出权衡。 法律与政治改革:许多现代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例如,对犯罪的预防和惩罚,对公共资源的分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追求,都可以在功利主义的逻辑中找到其渊源。 对其他思潮的启示:即使是反对功利主义的思潮,也常常是在回应和批判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例如,权利伦理学、德性伦理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功利主义的局限性进行了反思和修正。 总而言之,古典功利主义,以其对“效用”、“快乐”、“痛苦”以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系统阐释,深刻地塑造了现代政治和道德观念。尽管其理论本身经历了一系列挑战与演变,但其核心思想,即关注行为和制度的实际后果,并以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至今仍然是理解现代社会及其思想根源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 结语 古典功利主义的遗产与当代意义 古典功利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座辉煌的思想丰碑,由休谟的道德情感萌芽,经边沁的系统奠基,密尔父子的精进与传播,最终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它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核心原则,将道德和政治判断的重心从抽象的义务和权利,转移到对行为与制度实际后果的考察。这种强调“效用”、关注现实福祉的思想取向,为现代社会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制定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我们回顾休谟的审慎功利主义,看到了对“效用”在社会秩序和道德判断中作用的早期洞察。边沁以其“快乐计算”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为功利主义注入了革命性的活力,并将其转化为一项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立法原则,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法律和政治改革。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则通过对快乐“质”的区分,对个体自由和正义的辩护,成功地弥合了功利主义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之间的裂痕,使其思想更具深度和说服力。而詹姆斯·密尔则在功利主义的早期传播和实践中,将这一学说推广至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古典功利主义的遗产,体现在多个层面: 理性与经验主义:它鼓励人们运用理性和经验来分析问题,并以实际效果为导向来指导行动,而非仅仅依赖于教条或传统。 社会关怀与改革精神:它将目光投向社会整体的福祉,并为社会改良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激励人们质疑不合理的制度,追求更美好的社会。 政策分析与评估:功利主义的思想,在现代公共政策分析中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就是其直接的应用。 对个体与集体的平衡:尽管其核心是“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但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述,也充分强调了个体自由、权利和尊严的重要性,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 对未来政治思想研究的启示 古典功利主义虽然有其理论的局限性,例如如何精确地量化幸福,以及如何处理极端情况下的道德困境等,但其核心的理性探究精神、对人类福祉的关注以及对社会进步的追求,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当代意义。 在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问题时,我们仍然可以从古典功利主义那里获得启发。例如,在面对环境危机、经济不平等、医疗资源分配等问题时,我们依然需要权衡不同选择所带来的后果,评估其对社会整体福祉的影响。同时,我们也需要警惕过度简化和绝对化的论证,认识到人类价值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脉络,更能帮助我们审视自身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它提醒我们,一切政治和道德的努力,最终都应服务于提升人类的福祉,并以理性和审慎的态度,不断探索和完善通往更美好社会之路。 --- [1]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第一章,第一节。 [2] 密尔,《功利主义》,第二章。 [3] 同上。
![西方政治思想译丛:古典功利主义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 from Hume to Mill]](https://pic.windowsfront.com/12319569/5ab0bd28N38407e0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