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马岛 [Duma Key]](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006228/820a8f18-6d06-4f8b-91bb-30b2656e32ad.jpg)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斯蒂芬·金迄今辉煌的作品!囊括《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邦诺书店、美国独立书商协会、《丹佛邮报》、《洛杉矶时报》溜达畅销排行榜冠军!关于肉体与心灵、爱与伤害、困境与破局、毁灭与救赎……
我会永远爱那个小女孩,不管她已让我付出了多少。
我必须爱。我没有选择。
一次非凡的阅读体验,一个惊人的恐怖故事,一轮深入的人性探索,一场震撼的道德救赎。
内容简介
埃德加·弗里曼特是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建筑商,美国成功人士的代表,事业有成,在业界享有良好声誉,并拥有爱妻、两个可爱的女儿和四千万身家。然而,他的完美人生被突如其来的一辆十二层楼高的起重机压得粉碎——建筑工地一场交通事故令他身受重伤,并失去了右臂。在经历了痛不欲生的恢复期后,埃德加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匆匆告终。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他搬到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荒僻小岛,租住在一座粉红色的大房子里。在岛上,他结识了睿智的前律师怀尔曼,神秘的房东伊丽莎白,同时他自己开始出现无法抑制的绘画冲动——开始只是画素描,接着是油画——他以惊人的速度画着,作品充满奇诡的想象,而他的创作似乎还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埃德加在杜马岛上绮丽多彩而又惊心动魄的人生画卷由此徐徐展开……
作者简介
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一九四七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波特兰市,后在缅因州州立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毕业后因工资菲薄而走上写作之路,自一九七三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魔女嘉莉》后,迄今已著有四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二百多部短篇小说。其作品是近年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还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有超过百部影视作品取材自他的小说。他因此被誉为“现代惊悚小说大师”。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遭遇严重车祸,侥幸大难不死。在康复后,他又立刻投入写作。二○○三年,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其后又先后获得世界奇幻文学奖“终身成就奖”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爱伦-坡奖”的“大师奖”。在斯蒂芬金的众多作品中,以历时三十余年才终于完成的奇幻巨著“黑暗塔全系列”(共七卷)最为壮观,也最受金迷推崇,书里的人物与情节,散见.于斯蒂芬‘金的其它小说中,堪称他最重要的作品。《杜马岛》是其○○八年出版的新作,被评选为第二届黑色羽毛笔奖“年度暗黑小说”,并获得恐怖小说界最高荣誉——斯托克奖。目前斯蒂芬·金与妻子居住于缅因州。
译者简介:
于是,自由作家、翻译作者。著有《六翼天使》、《同居笔记》、《事后》、《自恋时殴》、《一只黑猫的自闭症》、《夜在窗外》、《避孕》。翻译作品有《迷失男女》、《红颜》、《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乐透彩》、斯蒂芬金“黑暗塔全系列”之七《黑暗之塔》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无法用寥寥数语概括斯蒂芬·金这部新作里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悬念和惊悚,我只能说,《杜马岛》……是斯蒂芬·金迄今辉煌的作品。(除了“黑暗塔”,之外,那个系列里的每一部都堪称他的高峰之作。)《杜马岛》如商《肖申克的救赎》一样有着丰富的内涵与价值,并完美地呈现了金大师一贯的营造恐怖氛围的非凡功力。那些一直对斯蒂芬·金的作品跃跃欲试却不知该从哪本开始的读者不妨翻开《杜马岛》读上几页。——网上书店
精彩书摘
一 我的上辈子1
我的名字是埃德加·弗里曼特。曾经是建筑承包业界的大人物。那是在明尼苏达州,在我的上辈子里。我是从怀尔曼那儿学到“上辈子”之说的。我很想把怀尔曼的事儿告诉你,但还是让我们先了解明尼苏达州的那部分吧。
要说的是:我的光辉历程走的是堂堂正正的美国男子汉之路。先进了一家公司站稳了脚跟,等到节节攀升到了头,我就辞职了,开始自己创业。离开那家公司时,老板嘲笑我,说我不出一年就会破产。我猜想,每当有精明强干的年轻员工自立门户时,大多数老板都会这么说。
我呢,卓有成效。当明尼阿波利斯的圣保罗一带繁荣起来时,弗里曼特公司也兴旺发达了。时局萧条时,我从不逞强,一向谨慎从事。但我确实会在直觉上押宝,大多数时候,直觉都会帮到我。到了五十岁时,我和帕姆的身家值四千万美元。而且,我俩感情甚笃,多年不渝。我们有两个女儿,等我们的黄金岁月到头时,伊瑟在布朗大学,梅琳达在法国教书,那是她身为外国交换生的一个兼职。要是事情有什么不对劲,我和太太就会飞过去看看她。
我在某处施工现场遭遇了意外。事情倒是很简单:敝篷小货车和十二层楼高的起重机亲密接触时,输的永远是小货车,哪怕是会铃声大作的道奇公羊也没辙。我的右侧颅骨仅是开裂之伤。左侧狠狠撞上公羊的车门支柱,导致三处骨折。也可能是五处。我的记忆力比伤后好多了,但相比于受伤之前仍有天壤之别。
医生说,我受到的脑损伤叫做“对冲伤”,通常会比冲击伤带来更深远的伤害。我的肋骨断了。右臀粉碎性骨折。虽说右跟的七成视力保住了(要是天气好,还能看得更清楚),却永远失去了右臂。
我本会送命的,但我活了下来。理论上,对冲伤会引发精神性损伤症状,一开始确实是,但慢慢消退了。差不多算消退了。等我的精神有所好转时,太太却走了,那可不是差不多,而是完完全全地走了。我们结婚有整整二十五年,但你也知道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我想,那也不要紧;走了就走了吧。了结就了结吧。有时候,完结是好事情。
我所说的精神性损伤是指一开始认不出别人是谁——甚至不认得我太太——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疼。现在,四年后的我已记不得那种疼痛的实感了。我知道自己在忍、在熬,那是能把人撕裂、把人疼死的痛,但现在说来好像只需动动口舌。当时的痛可不是口头说说的。当时就像身处地狱,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下了地狱。
你先是怕死,然后怕自己死不掉。这是怀尔曼说的,他一定是知道的;曾身处地狱的他很有发言权。
每时每刻,每一处都在疼。脑袋里好像总有钟在敲,敲得我头痛欲裂;全世界最大的钟表行好像开在我的脑壳里,并永远关在漆黑深夜里。由于我的右眼被撞伤了,只能透过一层血膜看世界,而我几乎不知道身在阴阳何界。所有东西都没了名字。我记得有那么一天,帕姆在房间里——我还在病房里——她站在我的床边。我气急败坏,因为她本该站在另一边,另一边有个像板条的东西,可以把屁股蛋子放上去。
“搬个朋友来,”我说,“坐在朋友上。”
“埃德加,你这是什么意思?”她问。
“朋友啊,就是伙计呗!”我大喊,“把他妈的伙计拿过来,你臭婊子!”头痛得能直接把我干掉,而她哭了起来。我讨厌她哭哭啼啼的。她根本没理由哭,她又不是在笼子里的倒霉鬼,她又不需要隔着模糊的血红色看世界。笼子里的猴子不是她。接着,我的火气蹿上来了。“把小伙子拿过来,病倒!”我在乱成一团的脑瓜里找不到椅子,朋友算是最挨近的一个词儿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发火。照顾我的有两个老护士,我称其为“老菜皮一号”和“老菜皮二号”,好像她们都是色情片《苏斯大夫》里的角色。还有个志愿者担当护士助理,我叫她“菱形尿不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但这昵称同样有性联想。至少,我有。等我有点儿力气了,就开始攻击别人。有两次,我企图刺伤帕姆,其中有一次得手,尽管用的只是一把塑料餐刀,但她的小臂上还是要缝几针。还有好几次,他们必须把我捆牢在床上。
关于我的上辈子,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昂贵的康复病房里都快待足一个月时,有天下午很燥热,昂贵的空调机坏掉了,我被捆在床上,电视里在放肥皂剧,脑袋里有成千上万只午夜大钟在敲,右侧身体疼得火烧火燎,消失不见的右臂痒得很,消失不见的右手手指在抽搐,复方羟氢可待因止痛剂隔一阵子要停用一会儿(我不知道是多久,计算时间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一个护士从血红视野里浮上来,又一个凑到笼子前看猴子的生物,她说:“你想现在见你太太吗?”我答:“除非她带把枪来崩了我。”
你不会相信那种蚀骨的痛会消退,但它真的会。接着,他们把你运送回家,再用肌体复原的那套把戏制造的痛苦代替原先的疼痛。血红色开始从我的视野淡化。有个专攻催眠疗法的心理学家向我露了两手,教我如何处置幻觉中的疼痛、痒死人的失去的右臂。那就是卡曼。也是卡曼给我带来了瑞芭。当我跌跌撞撞走出上辈子、走进我现在居住的杜马岛时,我只带了寥寥可数的家当,瑞芭就是其一。
卡曼医生说:“在制怒心理疗程中,这是不允许的。”其实,我怀疑他在此事上说了谎,只是为了让瑞芭对我更有吸引力。他告诉我,我必须给她一个充满恨意的名字,于是,虽然她长得酷似露西·里卡多,但我想起了小时候只要看到我没把胡萝卜吃光就拧我手指头的瑞芭姑妈。拥有她还不到两天工夫,我就把这名字忘了。我只能想起男孩的名字,每—个都会让我更愤怒:兰道尔,罗素,鲁道夫,该死的凤凰河。
那时候我已经回家住了。帕姆端着早餐进来时,准是看到了我的表情,因为我听得出她克制的语气,她不想让自己爆发。不过,就算我记不起心理医生给我的红色布片制怒娃娃叫什么名字,我还能记得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使用它。
“帕姆,”我说,“给我五分钟,控制情绪。我办得到。”
“你肯定——”
“是,就现在,带着火腿出去,用它补补你的妆。我办得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控制情绪,但理论上我就该那么说。我记不起该死的娃娃叫什么,可“我办得到”这话还记得清清楚楚。明知办不到,明知自己被毁了,被加倍地毁了,就像倾盆大雨中的倒霉鬼,可我还口口声声不停地说我行、我可以,很明显,那段生活就算走到头了。
“我行的。”我说这话时的表情只有天知道,因为她一声不吭地退出去了,托盘还在她手里,可茶杯像在跳踢踏舞般撞出响动。
等她走了,我把玩偶举到面前,死死看进它愚蠢的蓝眼睛里,与此同时,深深掐进那愚不可及的软绵绵躯体里,大拇指几乎都看不见了。“你叫什么,蝙蝠脸的小婊子?”我冲着它大吼一声。我从没想过,帕姆和日班护士就在厨房里用内部电话收听我的一言一行。跟你这么说吧:就算内部电话不管用,她们隔着门板也照样听得到。那天,我嗓子不错。
我把玩偶前前后后摇个不停。它的脑袋怦然落下,《我爱露西》剧集里经久不衰的发式、也就是人造头发飞起来。大大的蓝色卡通眼珠子好像在说,“哦哦哦,你个死男人!”活像古老动画片里的贝蒂娃娃,你至今还能时不时在有线电视里看到呢。
“你叫什么,婊子!叫什么啊,贱货!烂布头骚货!你到底叫什么?快说出你的名字!跟我说你叫什么?再不说我就挖出你的眼珠子,割掉你的鼻子,剥掉你的——”
就在那时,混乱如麻的神智交错碰撞,直到现在——四年后,我在墨西哥山路易斯州坦马祖卡勒小镇过着埃德加·弗里曼特的第三幕人生戏时——还会时常这么跳接思路。就在那个瞬间,我好像又坐在了货车里,硬夹写字板和放在副驾座脚垫上的铁皮午餐盒相碰,嘎啦嘎啦直响,(我怀疑自己是准一带午饭盒去上班的美国千万富翁,但你说不定能数出一打来)苹果电脑放在我身旁的座位上。收音机里有个女人带着传福音者般的激情尖声高唱,“……红色的!”只有三个字,但足够了。那首歌唱的是,有个可怜的女人发现漂亮的女儿当了妓女。歌名叫《异想天开》,演唱者:瑞芭·麦克英泰尔。
“瑞芭,”喃喃自语的我将玩偶揽在怀里。“你叫瑞芭。瑞芭一瑞芭一瑞芭。我再也不会忘了。”结果还是忘了——隔一星期就忘了——但不再变得如此暴躁。不。我抱着她就像抱着亲爱的爱人,闭起眼睛,在车祸中毁于一旦的小货车也在幻想中重现。我在幻象中看到铁皮午餐盒和写字板上的铁夹子磕磕碰碰,也听到收音机里再次传出那歌声,以同样福音歌般的激情高唱道,“红色的!”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接近尾声,故事的气氛变得异常凝重,但同时又有一种奇异的、近乎宗教般的平静降临。作者似乎在用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来收束所有的挣扎与迷失。这不是一个简单地给出答案的结局,而更像是一种对“接受”的探讨。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生命中那些无法抗拒的力量,并从中找到一种新的生存平衡。我特别在意作者对于“遗留物”的描写,那些留在场景中的物件,不仅仅是道具,它们仿佛成为了某种精神能量的载体,承载着过去所有的重量与意义。这种对细节的坚守,让整个故事的结局拥有了回味无穷的层次感。读完之后,我感到了一种长时间的沉浸后才能体会到的疲惫与满足,仿佛自己也一同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深度洗礼。那种对环境、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描摹,让我久久无法从那个遥远的海岛中抽离出来。
评分随着故事的深入,我开始被那种逐渐渗透的“异化感”所深深吸引。主角周遭的环境,包括那些看似友善的邻里关系,都染上了一层不真实的薄雾。作者非常擅长使用环境细节来烘托人物的内心不安,比如对特定光影的反复描摹,或者对某些重复出现的、似乎毫无意义的自然现象的捕捉。这种处理方式,非常考验读者的耐心,因为它要求你放慢速度,去感受那种缓慢堆积的、令人不安的预兆。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对话和观察,在回溯时会显得格外意味深长。我特别喜欢这种叙事策略——它不急于解释,而是将所有的谜团像鱼线一样缓缓放出,让读者在迷雾中自行摸索。这种对悬疑感的营造,是建立在对人性深处弱点洞察之上的,而非廉价的惊吓。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知道危险就在拐角处,却又忍不住好奇地想知道它究竟会以何种形态显现,这是一种既抗拒又沉溺的阅读状态。
评分这部小说的开篇,那种缓慢而又无可阻挡的沉重感就紧紧抓住了我,仿佛置身于一场无法逃脱的命运漩涡之中。作者在描绘主人公的心灵转变时,展现出了惊人的细腻。一开始,那种职业生涯戛然而止后的茫然、失落与自我怀疑,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不禁反思自己生活中那些突然被剥夺的支柱感。接着,场景的转换,从都市的喧嚣直接跳跃到那个孤僻的海岸地带,那种环境上的巨大反差,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空气仿佛都变了质地,潮湿、咸涩,混合着一种未知的、古老的宁静。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创造”这一主题的探讨,那种从虚无中试图重建意义的挣扎,读起来让人心潮澎湃。每一次笔触的落下,都像是主人公在用新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也重新审视他与周遭世界的联系。尽管故事尚未完全展开,但那种潜藏在平静水面下的暗流已经清晰可见,预示着一场深刻的、可能带有超自然色彩的蜕变即将发生。这种铺陈的手法,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直接抛出冲突,而是让读者和主角一同呼吸着那片土地特有的、略带压抑的气息,耐心等待着那层神秘的面纱被揭开。
评分后期的情节发展,那种近乎宿命的追赶感,让我的心跳频率明显加快了。当那些隐藏的线索开始汇集,指向一个不可避免的终点时,那种感觉是震撼的。作者对“纠缠”这一主题的处理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仅是人与人的纠缠,更是过去与现在、现实与幻觉之间的紧密捆绑。我欣赏作者对道德模糊性的刻画,在这里,善恶的界限变得如同海边雾气般飘渺。你无法简单地将任何一个角色归类为纯粹的受害者或加害者,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阴影和无法磨灭的印记。这种复杂性,使得人物的最终抉择充满了悲剧性的力量。而且,叙事风格在这里发生了明显的转向,从内省式的独白,转变为更加动态、更具冲突性的场景交锋。那种从内向到外放的爆发力,处理得既猛烈又不失克制,显示出作者对情节高潮控制力的强大掌控力。
评分读到中段,我发现作者的叙事节奏开始出现一种奇妙的波动,时而如夏日午后的慵懒海风,舒缓到几乎令人昏昏欲睡;时而又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带着一股原始的、不可名状的力量猛烈袭来。这种张弛有度的控制,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期待感和不确定性。最引人入胜的是他对“艺术与疯癫”之间那条模糊界限的探究。主角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近乎痴迷的状态,让人不禁思考:真正的灵感是否总是需要以某种程度的自我牺牲为代价?书中的某些段落,描写起那些灵感的迸发,那些色彩的幻象和声音的重叠,简直是视觉和听觉的双重盛宴。它们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描述,而更像是直接投射到读者脑海中的印象派画作,色彩浓烈,笔触狂放。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巧妙地融入了当地的民间传说和历史的碎片,这些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主角当下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共振,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现实。这使得整个故事不仅仅停留在个人心理层面,更拥有了某种地域性的、史诗般的厚重感,仿佛那片土地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记忆的实体。
评分跨越千年的悠悠岁月,漫步纷纷扰扰的红尘俗世,只为寻找一份恩情回报过后的释然,殊知上苍竟在此时贸然介足,给予了一份别样的礼物,只是不知得到这意料之外的馈赠是幸还是不幸,但已无暇顾及,因为,自古至今都无人可以抵挡住爱情的诱惑,虽然本质为灵长类,但可惜的是拥有着同于人类的情感。凡拥有七情六欲者,皆无一幸免的落入情感的蛛网,而世间万物皆有情。
评分编辑本段
评分只是船员罢了。听到这话,红色的暴怒如潮退般在我心田骤灭,即便右手将再次消隐无影。但在右手彻底消失之前……在我失去愤怒、也失去该死的瓷桶之前……
评分斯蒂芬·金1947年出生于美国缅因州一贫困家庭。在州立大学学习英国文学。毕业后因工资菲薄而走上写作之路。70年代中期声名渐起,被《纽约时报》誉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自80年代至90年代以来,历年的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他的小说总是名列榜首,久居不下。他是当今世界上读者最多、声名最大的美国小说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好莱坞制片商的抢手货。1979年,在他32岁时,成为全世界作家中首屈一指的亿万富翁。
评分只是船员罢了。听到这话,红色的暴怒如潮退般在我心田骤灭,即便右手将再次消隐无影。但在右手彻底消失之前……在我失去愤怒、也失去该死的瓷桶之前……
评分有一次性的塑封 但是纸张有点薄 会透出背面的字 还行
评分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遭遇严重车祸,侥幸大难不死。在康复后,他又立刻投入写作。二○○三年,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颁发的“杰出贡献奖”。其后又先后获得世界奇幻文学奖“终身成就奖”和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爱伦-坡奖”的“大师奖”。在斯蒂芬金的众多作品中,以历时三十余年才终于完成的奇幻巨著“黑暗塔全系列”(共七卷)最为壮观,也最受金迷推崇,书里的人物与情节,散见.于斯蒂芬‘金的其它小说中,堪称他最重要的作品。《杜马岛》是其○○八年出版的新作,被评选为第二届黑色羽毛笔奖“年度暗黑小说”,并获得恐怖小说界最高荣誉——斯托克奖。目前斯蒂芬·金与妻子居住于缅因州。
评分-- 44
评分就是个好,好的很,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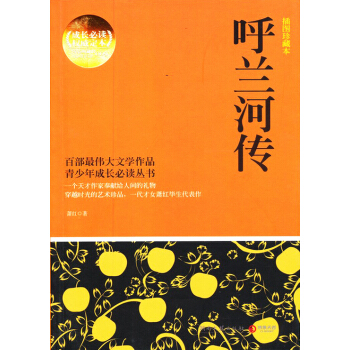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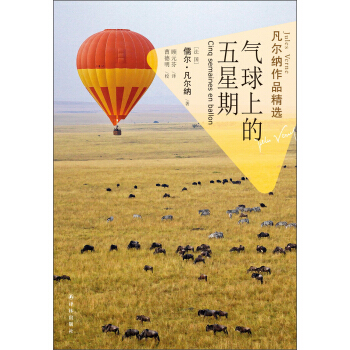

![异乡人 [Snow Hunter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92159/53b10012N5bc4dcd0.jpg)

![第二十二条军规 [Catch-22]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640665/54c21b18N3819429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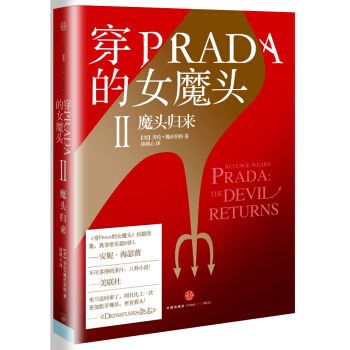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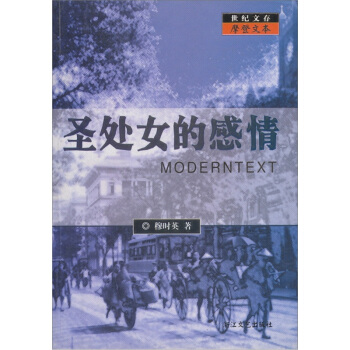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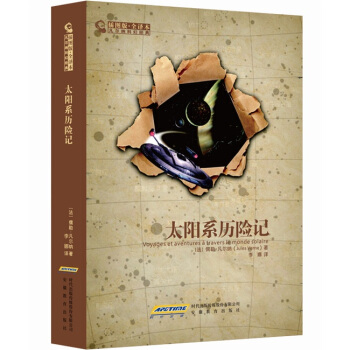



![终点人 [ENDER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67953/55efb899N61b2f1bf.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