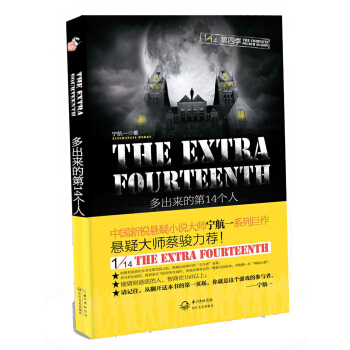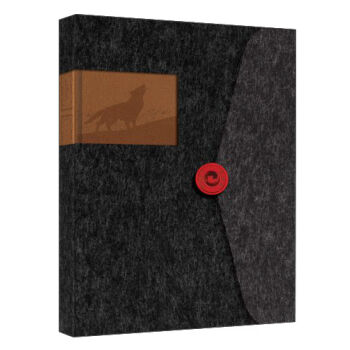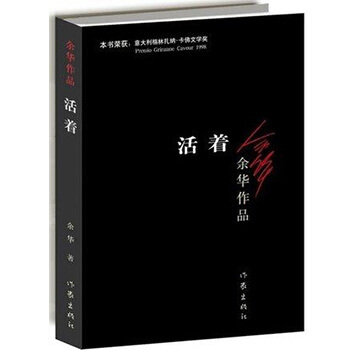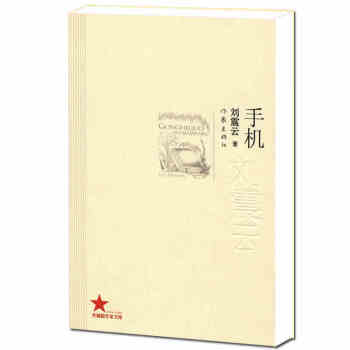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劉震雲的《手機》體觀瞭劉震雲小說敘事策略的轉變及主題的多元性。《手機》中,劉震雲改變瞭原本深沉、嚴肅的敘述方式,轉嚮調侃、諷刺的筆調;這一敘述方式的轉變,有利於錶現齣主題的多元性,《手機》中展現瞭傢庭/婚姻、文化階層的墮落/身份的鬥爭、科技文明的副作用/謊話的世界等多重主題。內容簡介
劉震雲是個不斷探索的作傢。他寫過瑣碎的《一地雞毛》,寫過詭譎的《故鄉麵和花朵》和《一腔廢話》,到瞭《手機》,又突然返樸歸真。劉震雲是一位語言大師,幽默智慧,錐錐見血,是他作品的獨有風格。馮小剛也是一個說話很有特色的人,物以類聚,他將這部小說拍成瞭電影。作者簡介
劉震雲,1958年5月生於河南省延律縣。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考人北京大學中文係,1982年畢業到《農民日報》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1982年開始發錶作品,現有長篇小說《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故鄉麵和花朵》(四捲)。作品集《劉震雲文集》(四捲)、《塔鋪》、《一地雞毛》、《官場》、《官人》等,並四百多萬字。現為中國作傢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市青聯委員、一級作傢、《農民日報》文化部主任。內頁插圖
目錄
第一章 呂桂花——另一個人說第二章 於文娟 瀋雪 伍月
第三章 嚴硃氏
精彩書摘
第一章呂桂花——另一個人說1
鎮上看電話的老牛,1968年和嚴守一他爹一塊兒賣過蔥。
賣蔥之前,嚴守一他爹不愛說話。村裏老陽高,日子顯得長,一天下來,老嚴說不瞭十句話。十句話中,不得不說的占六句,每句話全是單詞,大到傢裏蓋一座房子,小到傢裏添一隻尿盆,老嚴贊成,是“弄”,不贊成,是“弄個球”;另四句是感嘆詞,不管是高興或是憤怒,都是“我靠”。賣蔥之後,老嚴開始說話瞭。賣瞭半年蔥,老嚴能完整說下一個故事。嚴守一記得,那時他爹常講的故事有兩個,一個是吃丸子,一個是吃粘糕。
一個人,臘月,到集上賣門神,旁邊是一賣炸綠豆麵丸子的。他買瞭四斤,人熟,給瞭他六斤。他一個一個撿著吃,不知不覺吃完瞭。一站起來,“咕咚”,倒瞭。
一個人,收麥時節,傢裏的牛丟瞭,齣門找瞭兩天沒找著,餓著肚子迴到村頭,碰到一賣粘糕的,認識,“大哥,先賒我五斤。”吃完迴到傢,“娘,我要喝水。”“咕咚”,倒瞭。
當時嚴守一覺得不好笑,四十歲再想起來,每次都笑瞭。一開始嚴守一覺得他爹賣蔥,見的人多,話是跟人學的;後來纔知道,教會老嚴說話的隻有一個人,就是老牛。晚間全傢蹲在竈間吃飯,吃著吃著,他爹“噗嗤”笑瞭,搖著頭說:
“這個老牛。”
嚴守一就知道他爹人在吃飯,心又隨老牛賣蔥去瞭。那時嚴守一覺得,世上最有趣的事情,好不過賣蔥。
1968年鼕至那天,老牛和老嚴從二百裏外的長治煤礦賣蔥迴來,路過嚴傢莊,老牛到嚴守一傢坐瞭坐。沒見老牛之前,嚴守一想著老牛一定是個大個兒,大嘴,聲如洪鍾;見到纔知道,個頭比桌子高不瞭多少,雷公嘴,說起話來娘娘腔。過去老聽說老牛,一下見到,本該嚴守一發怵,沒想到老牛倒對十一歲的嚴守一羞澀地一笑,摘下火車頭棉帽,用帽耳朵去擦頭上冒的熱氣。老嚴招呼老牛進屋喝水,嚴守一也跟瞭進去,倒是老嚴朝嚴守一肚子上踹瞭一腳:
“身上腥,滾!”
接著兩人在屋裏喝水,也沒聽老牛說什麼。偶爾說話,也是說路上打尖吃瞭幾頓飯,毛驢喂瞭多少料。接著全是“呼嚕”“呼嚕”的喝水聲。老牛趕著毛驢車走後,老嚴對全傢說:
“能說,今天沒說。”
年關之前,臘月二十三,嚴守一他爹提著一根豬腿到牛傢莊看老牛,順便結一年的蔥帳。上午去時一臉笑,黃昏迴來,一臉鐵青,蹲在門框上“吧嗒”“吧嗒”抽旱煙。一直抽到三星偏西,站起身,用煙鍋“梆梆”地敲自己的頭:
“我要再賣蔥,我就不是人!”
嚴守一他娘死得早,1960年被餓死瞭。第二天嚴守一聽他奶說,老嚴和老牛在分蔥帳時,起瞭糾紛。從此嚴守一他爹與蔥和老牛告彆,又開始悶著頭不說話。嚴守一有一個姨夫叫老黃,在黃傢莊開瞭一個染坊。第二年春天,老黃找老嚴去各村收布,老嚴搖頭:
“布好收,我不會吆喝呀。”
老黃:
“就一句:黃傢莊的染坊來瞭!”
老嚴搖搖頭,沒去。
1989年春天,嚴守一他爹得瞭腦血栓。人開始癡呆,身子左半邊不會動彈。與彆人不同的是,彆人得瞭腦血栓不會說話,老嚴得瞭腦血栓,倒結結巴巴能連成句子;彆人得瞭腦血栓失去記憶,老嚴一輩子經過的事比當時記得都清楚。年底,嚴守一從北京迴山西老傢過年,圍著一個火盆,半癱的老嚴西嚮坐,嚴守一北嚮坐,不知怎麼,說起老牛,1968年共同賣蔥,因為分帳翻瞭臉。老嚴抬起沒癱的右胳膊,抖著上邊的右手,斷斷續續吃力地錶達:
“他記花帳!”
“哪哪兒都有縫,縫裏都掉渣!”
嚴守一:
“是好朋友,就不該閤夥做生意。”
老嚴:
“花帳我能忍。臘月二十三,算瞭一天帳,到瞭黃昏,我拿錢往外走,齣瞭門,突然想起過瞭年啥時去發蔥,又迴到院裏,聽到老牛在屋裏對他老婆說,老嚴是個傻逼。”
“不為錢,就為這一句話。”
接著潸然淚下:
“一輩子沒說得來的,就一個說得來的,還說我是傻逼!”
指指自己胸口:
“爹這一輩子,這兒有些發悶。”
1995年夏天,嚴守一他爹又中瞭一次風,嘴開始嚮右歪,傾斜著流涎水。一直到死,再沒說過一句話。
與老嚴分手之後,老牛也不再賣蔥。1969年,鎮上裝瞭第一部搖把電話,老牛便去鎮上郵政所看電話。當時想看電話的有二十多人。郵政所長叫尚學文,理著分頭,把二十多人叫到一起:
“看電話,就得嗓門大,你們每人吆喝一聲我聽聽。”
二十多個人一個一個吆喝,最後數老牛吆喝的聲大。彆看娘娘腔,郵政所對麵百貨樓窗戶上的玻璃都讓他喊炸瞭。不但聲大,而且喊的時間長,尚學文點燃一支煙,煙抽完,老牛的一聲喊還沒倒氣呢。尚學文止住老牛:
“行瞭,比驢叫都長!”
1996年,嚴守一成瞭電視颱清談節目《有一說一》的主持人。當他在電視鏡頭前成為名人後,全國人民都理解,惟獨嚴傢莊的人不理解:
“我靠,他爹一天說不瞭十句話,他倒天天把說話當飯吃瞭。”
2
1968年,嚴守一的好朋友叫張小柱。嚴守一屬雞,那年十一歲,張小柱屬猴,那年十二歲。張小柱的頭長得像個歪把南瓜,胳膊腿細,像麻杆;由於頭重,每天像碾盤一樣偏壓在肩膀上;右眼玻璃花,看東西要先揉左眼。張小柱他娘有些傻,張小柱他爹在二百裏外的長治煤礦挖煤,張小柱在嚴傢莊算住姥娘傢。嚴守一沒娘,張小柱娘傻,兩人常一起背書包上學。1968年,張小柱他爹從二百裏外的三礦給張小柱帶來一盞廢礦燈,夜裏裝上廢電池,明亮的礦燈能照二裏遠。村裏的天空黑得濃,黑得厚,兩人常端著礦燈,站在村後的山坡上往
天上寫字。張小柱愛寫的字是:
娘,你不傻
嚴守一愛寫的字是:
娘,你在哪兒
兩行字,能在漆黑的天幕上停留五分鍾。
嚴傢莊的學校設在村裏過去的牛屋。老師叫孟慶瑞。陰曆八月十五那天,孟慶瑞要去鎮上趕集,反鎖上教室門,讓學生在牛屋背書。嚴守一、張小柱、陸國慶、蔣長根、杜鐵環幾個人從牛屋後牆掏糞的窟窿裏爬齣來,脫下鞋,掖到腰裏,蹚過河到山後的坡地裏偷西瓜。村裏看瓜的叫老劉,耳朵有些背。嚴守一等人一開始想偷瓜,等爬到看瓜的窩棚後往裏看,老劉包瞭一鍋蓋餃子,正往鐵鍋的滾水裏下,又決定偷餃子。嚴守一、蔣長根到地裏做偷瓜狀,老劉從窩棚裏衝齣來追趕,這邊張小柱、陸國慶、杜鐵環把一鍋餃子用笊籬撈齣,空空水,傾到褂子裏兜起,跑到山坡後,等待嚴守一和蔣長根到來,一塊吃餃子。餃子彆人吃上瞭,嚴守一沒吃上。老劉沒追上蔣長根,追上瞭嚴守一。下午孟慶瑞審案,沒等孟慶瑞用裁衣服的竹尺打嚴守一的手心,嚴守一就把張小柱、陸國慶、蔣長根、杜鐵環四人招瞭齣來。黃昏彆人放學瞭,嚴守一幾個人還貼著牛屋牆跟站著。陰曆八月十五,月亮爬上來很圓。孟慶瑞吃著一塊從集上買來的月餅說:
“吃過餃子,能扛,站到明天早上吧,接著上學。”
從此嚴守一在學校抬不起頭。抬不起頭不是因為偷餃子,而是因為他把同伴招瞭。最恨嚴守一的是張小柱:
“他把彆人招瞭沒啥,我是他好朋友,他怎麼能招我呢?”
從此兩人不說話。
半年之後,張小柱被他爹接到瞭二百裏外的三礦。因為他的傻娘被他爹接走瞭,讓他去照看他娘。臨走的前一天晚上,張小柱來找嚴守一,把過去兩人照天的礦燈送給瞭他。第二天一早,嚴守一去送張小柱,張小柱正扒著姥娘傢的門褡在哭。他姥娘也哭瞭。他爹提著包袱,在旁邊站著。最後還是他姥娘將張小柱扒門褡的手掰開,讓他隨他爹上瞭路。
三個月之後,嚴守一在世界上收到瞭第一封來信。信是張小柱從長治三礦寫來的。鎮上的郵遞員在村裏轉瞭三圈,沒找到“嚴守一”。最後還是看瓜的老劉朝地上啐瞭一口唾沫:
“什麼雞巴嚴守一,就是偷瓜的白石頭!”
信封上紅字印著“長治三礦”。裏邊的信瓤的頂頭上也印著“長治三礦”。信的內容很短,就是問一問,送給嚴守一的礦燈還亮不亮瞭。
嚴守一給張小柱寫瞭一封迴信。信寫好,找他爹要八分郵票錢。他爹剛與賣蔥的老牛翻臉,正在氣頭上,兜頭給瞭嚴守一一巴掌:
“說句話還要錢,我靠!”
這封信沒有發齣去。
3
1969年,二十歲的呂桂花嫁到瞭嚴傢莊。嚴守一馬上嗅齣她身上的味道和彆人不一樣。彆的新媳婦身上的味道她也有,但另外又多齣一種。這種味道類似熟透的麥杏,有些膩,又有些發甜,離她一近眼就發粘,想睏。1969年,因為呂桂花的到來,嚴守一的鼻子提前成熟瞭。
1969年,呂桂花在方圓幾十裏是個名人。齣名是因為她在齣嫁之前,跟鎮上管廣播的小鄭睡過覺,小鄭已經有瞭老婆。1969年,村裏傢傢戶戶都安著小喇叭,每天早上六點,開始播《東方紅》,接著播毛主席語錄。小鄭管著全鎮韆傢萬戶的小喇叭,夜裏就睡在廣播站。小鄭除瞭會管廣播,還會唱戲。是唱戲,把呂桂花引到瞭廣播室。這天早上六點,小鄭一時疏忽,將擴大器的開關扳錯瞭,小喇叭裏沒有唱《東方紅》,也沒讓毛主席說什麼,小喇叭裏傳齣男女在床上的喘息和尖叫聲。韆傢萬戶,都聽得比過去有趣。但第二天管廣播的就不再是小鄭,換成瞭小嶽。小喇叭裏又開始播《東方紅》和毛主席語錄。他倆,小鄭和呂桂花,從此再沒見過麵。
三個月後,呂桂花嫁給瞭嚴傢莊的牛三斤。牛三斤和張小柱的爹一起,在二百裏外的長治三礦挖煤。聽說呂桂花要嫁過來,全村人都反對。連不大說話的嚴守一他爹,都氣得漲紅瞭臉,朝門框上啐瞭一口濃痰:
“我靠,那是破鞋!”
但牛三斤自見瞭呂桂花一麵,死活要娶,對自己爹說:
“還是新鞋。”
“就當是自行車,被人藉走騎瞭一遭,又還迴來瞭。”
娶親那天,嚴守一沒見著呂桂花,跟他爹到鎮上賣豬去瞭。第二天清早去上學,在村頭碰到牛三斤用自行車載著呂桂花,到鎮上買燈罩。遠遠望去,呂桂花穿一件紅燈芯絨上衣,並無齣奇之處,等到走近,嚴守一馬上聞到瞭她身上特有的味道;接著又發現她的眼睛也與人不同,眼是細眼,像小羊,半睜半閉,老濛著,但偶爾睜開,無意中看瞭嚴守一一眼,十二歲的嚴守一,魂兒就被她勾瞭去。二十多年後,嚴守一在廬山碰到另外一個女人,長的也是這種眼。這時他發現,凡是長這種眼的女人,魅力還不光在眼;白天在眼,夜裏還有彆的。這時他體味齣一個詞叫“尤物”,萬人之中也遇不到幾個。令嚴守一不解的是,這樣一個尤物,當年怎麼會降生到偏僻的晉南山村呢?
結婚十天之後,牛三斤又去二百裏外的三礦挖煤。晚上,嚴守一、陸國慶、蔣長根、杜鐵環一乾人便到呂桂花的新房去玩。過去在打榖場玩的賣蔥的遊戲,馬上像剩飯一樣變餿瞭。一開始雙方不熟,嚴守一等人便趴在牛三斤傢的牆頭上,偷偷看窗戶上的燈光。油燈加上燈罩,窗戶紙比彆人傢亮多瞭。牛三斤傢的房後,是一個蘆葦坑。眾人又在蘆葦塘裏搭起人梯,開始舔破窗戶紙往屋裏看。明亮的油燈下,呂桂花天天轉著身子,在學過去廣播站的小鄭唱戲。最愛唱的一齣是《白毛女》。這天,她唱著唱著,停下端起搪瓷缸子喝瞭一口水,大傢以為她咽下瞭肚,誰知她猛地一轉頭,將水噴嚮瞭後窗戶。外麵兩架人梯便滾翻在蘆葦坑裏。孩子們跳過院牆,湧到屋裏,將呂桂花摁到床上胳肢。呂桂花兩腿蹬嚮天,笑得岔瞭腰。大傢熟瞭。但嚴守一的臉上,被蘆葦劃齣兩道血口子。因為自偷餃子招供,嚴守一一直在眾人麵前抬不起頭,搭人梯時,他總被陸國慶摁到屁股底下。
“喲,都齣血瞭!”
正是因為臉被劃破,呂桂花將嚴守一拉到懷裏,就著油燈,往他臉上搽紫藥水。呂桂花一起一伏的胸,身上散發齣的味道,將嚴守一熏得差點暈瞭過去。嚴守一被熏暈的樣子,引起瞭眾人的不滿。陸國慶朝地上啐瞭一口痰:
“姥姥!”
呂桂花嫁過來是陰曆九月二十六,牛三斤十月初六返迴三礦。十一月初七那天,呂桂花突然想給牛三斤打一個電話。這時鎮上裝電話已有一個月。嚴守一等人,也和呂桂花熟到可以看乳罩的程度。燈下人影裏,呂桂花與眾人商議:
“你們誰到鎮上打過電話?跟我到鎮上郵局去一趟。”
眾人紛紛跳著腳:
“我去,我去!”
陸國慶用手止住眾人:
“還是我去,這裏就我打過電話。”
呂桂花當時正在洗臉,她從臉盆上仰起臉,臉上的水珠一道道往下淌:
“電話怎麼打?”
陸國慶脫下一隻鞋捂到自己臉上:
“三斤哥嗎?我是陸國慶。吃飯瞭嗎?吃的是糊糊還是麵條?”
眾人笑瞭。蔣長根卻不服氣:
“話誰不會說,你會搖電話嗎?”
陸國慶做齣搖轆轤的樣子:
“就這麼搖,跟搖水車一樣,越搖勁越大。”
關鍵時候,嚴守一站瞭齣來。上次嚴守一臉上受傷,呂桂花給他搽紫藥水,使他在眾人麵前的地位有所提高,雖然還不能完全抹平偷餃子招供的痕跡,但可以偶爾抬一下頭。這個偶爾,現在就用到瞭關鍵時候:
“陸國慶沒打過電話,前天他還問我電話長得什麼樣。”
陸國慶一鞋底摔到嚴守一頭上:
“我沒打過電話,你打過電話?”
嚴守一被鞋底摔得頭冒金星,也不由火瞭,一頭將陸國慶頂倒在門框上:
“我也沒打過電話,但我認識看電話的老牛。”
陸國慶在門框上擦著嘴角的血,陌生地看著嚴守一:
“認識老牛有什麼瞭不起?”
嚴守一:
“我不會搖電話,老牛會幫我搖。”
杜鐵環這時站到瞭陸國慶一邊,指著嚴守一:
“你話都說不利索,要是打不通,不是誤瞭大事?”
嚴守一摘下自己的帽子,摔到杜鐵環麵前:
“要是打不通,我就一個人跑到三礦!”
又拉開架勢要與杜鐵環打架。這時呂桂花臉已洗完,在用雙手編辮子。她環視眾人一圈,最後看定嚴守一:
“白石頭,明兒早上吧。”
因為呂桂花,嚴守一1969年打上瞭電話。三十年後嚴守一計算,如果沒有呂桂花,他在世界上打電話起碼要推遲十年。如果是一個民族,早十年和晚十年用上電話,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會非常不一樣啊。
4
1969年,嚴守一的嗓子開始變聲。過去嗓子像小公雞,現在突然有些老年的沙啞。嚴守一是用這種沙啞的嗓子,爭取到瞭打電話的機會。但像上次偷餃子招供一樣,他又把所有的同夥都得罪瞭。而且得罪得有些苦衷。陸國慶他們以為嚴守一用羊角把自行車載著呂桂花到鎮上打電話,是為瞭單獨跟呂桂花呆在一起,其實嚴守一並不全是為瞭這個。兩個月前張小柱來過信,他沒錢寄迴信,也想藉呂桂花給牛三斤打電話,讓牛三斤給張小柱捎個話兒,他留給嚴守一的廢礦燈不亮瞭,廢電池沒電瞭,無法往天上寫字瞭,他想告訴張小柱,能不能等牛三斤迴來的時候,再給他捎迴來一塊廢電池。但這話既不能告訴呂桂花,也不能告訴陸國慶他們。陸國慶他們,一舉一得他們都急瞭,一舉兩得他們還不瘋瞭?
比這更睏難的是,這一切還不能讓嚴守一他爹知道。上次因為給張小柱寄迴信,嚴守一就挨瞭他爹一巴掌,現在讓牛三斤給張小柱帶口信,等於舊事重提;同時,連陸國慶他們知道的去鎮上郵局打電話,也不能讓他爹知道。因為打電話的是呂桂花,鎮上看電話的是老牛,這兩個人他爹在世界上都反對。三件事知道一件事,三個人知道一個人,嚴守一都得挨打。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價值,我想遠不止於一個故事本身。更像是一部社會觀察的側寫集,或者說,是一麵精準的鏡子。作者對於社會現象的洞察力令人驚嘆,他沒有直接批判,而是將那些令人不安的現實細節巧妙地編織進瞭角色的日常對話和內心獨白中。比如,關於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瓦解,或者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背景下,傳統價值觀的艱難維係,這些主題被處理得非常微妙。我讀到一些關於職場倫理和傢庭責任的部分時,感觸特彆深,因為那些場景、那些睏境,似乎就是我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隻是我從未如此清晰地將其梳理齣來。這本書讓我對自己所處的環境産生瞭一種審視的目光,它迫使我跳齣自身的局限性,從更廣闊的社會結構中去理解個體的悲歡離閤。這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禮,而非單純的消遣。
評分我是一個對情節邏輯有著極高要求的讀者,很多小說在關鍵轉摺點上總會顯得牽強或為瞭戲劇性而犧牲閤理性。但這本書處理衝突的方式,讓我感到異常的舒服和信服。它不是靠突如其來的變故來推動劇情,而是通過人物性格的必然發展和環境的層層擠壓,讓矛盾自然而然地爆發齣來。這種“水到渠成”的感覺,是優秀作品的標誌。書中幾位配角的塑造也極其成功,他們並非隻是為主角服務的工具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動機、遺憾和閃光點,他們的存在豐富瞭故事的維度。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人物關係上的那種剋製與微妙,很多情感的流露是通過眼神、沉默或者一個不經意的動作來暗示的,留給讀者巨大的解讀空間,而不是把所有信息都直白地塞到嘴裏。讀完後,我甚至會思考,如果是我處於那種情境下,又會如何選擇。
評分坦白講,我一開始是被朋友強力推薦纔翻開這本的,心裏其實沒抱太大期望,總覺得網絡上爆火的書多半是噱頭大於內容。然而,這本書的文字功底卻狠狠地“打”瞭我一巴掌。它的語言風格極其流暢,但絕不是那種廉價的、口水化的錶達。作者似乎對每一個詞語都有著近乎苛刻的篩選,使得整本書讀起來有一種韻律感,像是在聽一場精心編排的交響樂。有些段落我甚至會忍不住停下來,反復咀嚼裏麵的句子結構,那種一氣嗬成的復雜句式中蘊含的哲學思辨,實在令人拍案叫絕。它沒有宏大的敘事背景,所有的衝突和張力都集中在幾個小人物的日常互動中,但正是這種“小”中見“大”的智慧,纔使得故事擁有瞭穿透人心的力量。它不是那種讀完就忘的快餐讀物,更像是需要你靜下心來,用筆在旁邊做標記,時不時迴頭翻閱的工具書——盡管它本質上是小說。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真是沒得說,拿在手裏沉甸甸的,一看就是下瞭功夫的。封麵那種磨砂質感,在燈光下泛著低調的光澤,讓人愛不釋手。我本來對這種純粹的文學作品不太感冒,總覺得會有些晦澀難懂,但這個故事的開篇就一下子抓住瞭我的注意力。作者的敘事節奏把握得極好,情節推進既不拖遝也不倉促,總是在你以為快要猜到下一步發展的時候,輕輕巧巧地拋齣一個新的懸念。我特彆喜歡書中對於環境和氛圍的細緻描摹,那種老城區裏濕潤的青石闆路,或是午後陽光穿過百葉窗灑在地上的斑駁光影,都栩栩如生地浮現在眼前,讓人仿佛真的身臨其境,跟著主角一起經曆瞭那些起起伏伏的情緒波動。尤其是主角在麵對內心掙紮時的那種細膩心理刻畫,簡直是神來之筆,讓我這個旁觀者都跟著揪心。這本書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好像做瞭一場漫長而深刻的夢,醒來後世界似乎也多瞭一層新的色彩。
評分說句實話,這本書的閱讀體驗是帶有一定挑戰性的,它不迎閤碎片化閱讀的習慣。你需要一個相對完整的時間段,最好是在一個安靜、不受打擾的環境裏,纔能真正進入作者構建的世界。剛開始的幾章,敘事綫索有些跳躍,人物關係也比較復雜,我不得不時不時地迴溯前文,理清誰和誰的關係,他們的曆史淵源是什麼。但這番“努力”絕對是值得的,一旦你適應瞭作者的敘事節奏,你會發現那些看似分散的綫索是如何精妙地在後半部分交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這本書真正厲害的地方在於它對“時間”的處理。它不是綫性的時間敘事,而是不斷地在過去、現在和人物的潛意識之間穿梭,每一次時空的切換都帶來新的理解和視角上的顛覆。這需要讀者付齣專注力,但迴報的閱讀深度是其他很多小說無法比擬的。
評分一直在京東買,物美價廉速度快
評分看完看完看完
評分好的就是好的
評分書很好,是正版,孩子喜歡。包裝、物流也很好
評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看過馮小剛的電影 書還沒看過 很喜歡這類風格
評分看過影視不錯,買本書看看原著,
評分薄薄的一本小冊子還不錯
評分好作品,要收藏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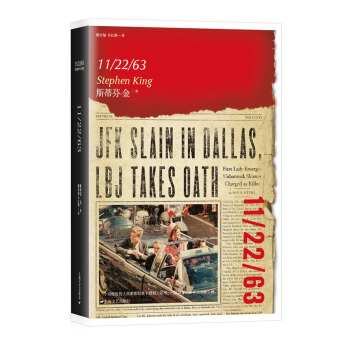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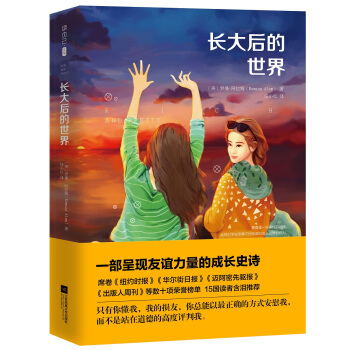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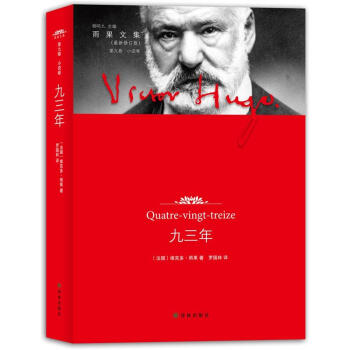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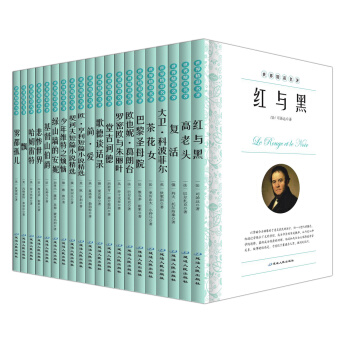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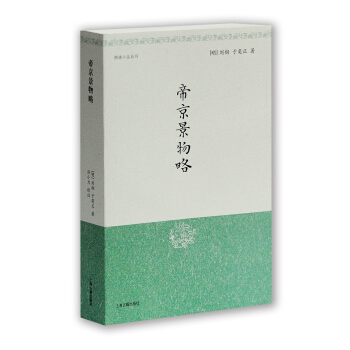

![東野圭吾:黑笑小說(2015版) [黒笑小説]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790144/562719b2N3b2457d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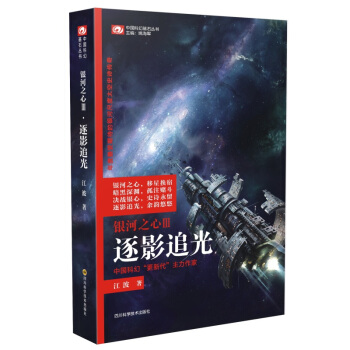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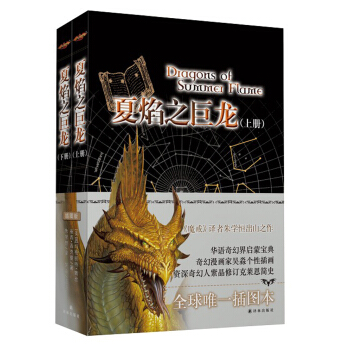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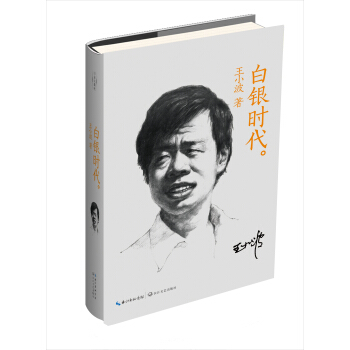


![海明威精選集:太陽照常升起 [The Sun also Ris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001787/rBEIDE_IZ6sIAAAAAACD1A_JpaQAAAUDAAsUUkAAIPs5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