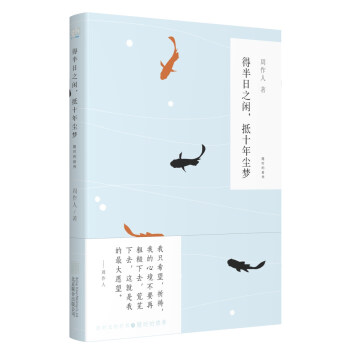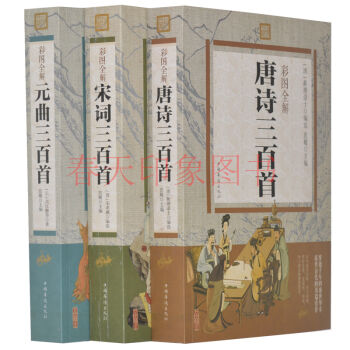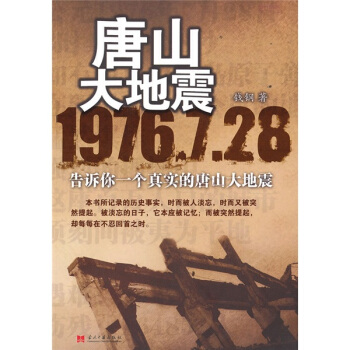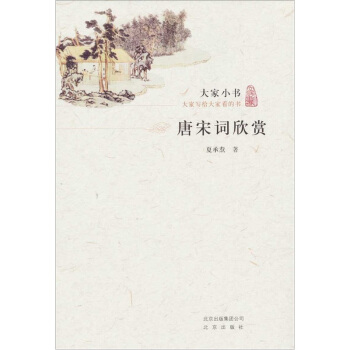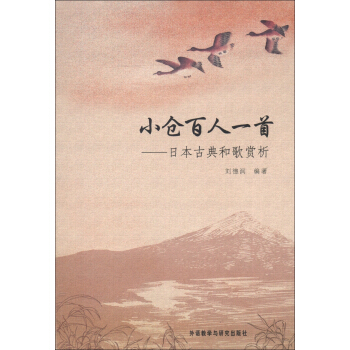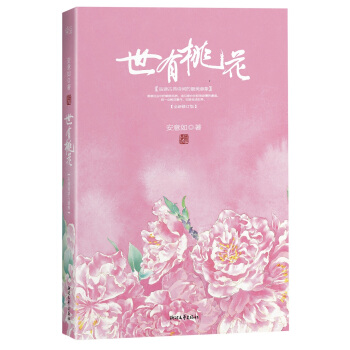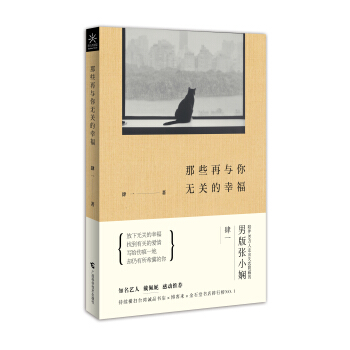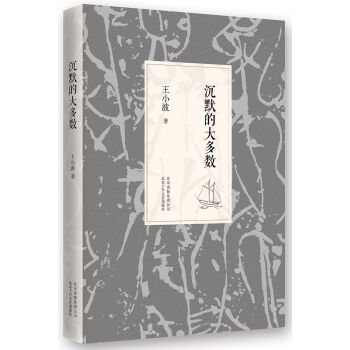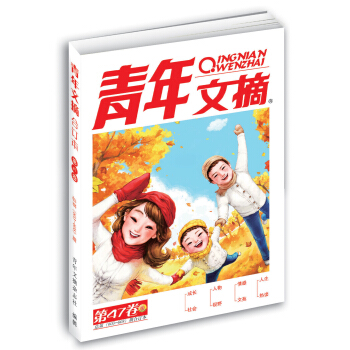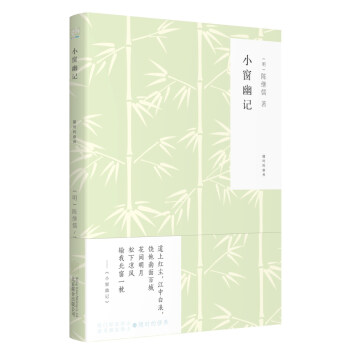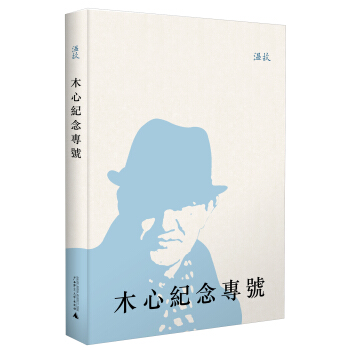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 木心先生的“最後時光”,陳丹青的“守護與送彆”——
陳丹青在《守護與送彆》中這樣寫道,“11 月中至12 月下旬,我幾度守在木心病榻前,之後,是他的葬禮。誰曾守護親屬摯友走嚮最後的路,或對人的殞滅的真相,不驚訝,不陌生?但這是我目擊垂老的人,病危,衰竭,死。我不想限製篇幅,不願遺漏種種細節。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結,給我上最後一課。”
▲ 首次發錶若乾珍貴照片,病榻前陳丹青描繪先生——
○ “木心從不讓我畫他,這是我描繪先生,也是最後一次。畫時,他渾然不知。”
○ 木心晚年詩集《僞所羅門書》手稿本
○ 木心《我紛紛的情欲》手稿本
○ 2005年木心迴國探看烏鎮為他故園營建的新居,在上海停留期間,與上海作傢陳村、孫甘露、王淑瑾、尹慶一等有過愉快的會麵,喜滋滋為他們簽自己的書。
○ 2010年12月紐約電影人為木心拍攝紀錄片期間,他已漸漸習慣麵對攝像。
○ 12張珍貴照片。2011-1927的木心。
▲ 首次發錶木心先生的《獄中手稿》對話、節錄和緻讀者信
關於木心先生的66頁獄中手稿,木心的研究者、翻譯者童明教授曾與木心在2000年有過一次對話。此外,木心本人曾從手稿中選齣5段摘錄。這兩份文本的漢語版從未麵世,《木心紀念專號》全文發錶。
▲ 收錄梁文道、陳子善、鍾立風、童明、春陽、顧文豪等人文章
▲ 收錄木心先生的喪儀文本和烏鎮、北京兩地追思會長篇實錄
▲ 收錄木心先生《文學迴憶錄》來信選登、章節摘引、最後一課
海報:
內容簡介
在編輯過程中,我們時時感到,這是一份鄭重的紀念,更是一組曆史的見證——在現代中國文學史與藝術史中,木心先生是一個的孤例:他的幾乎全部創作生涯,鮮為人知, 直至他79歲那年,他的文學著作始得陸續在他的祖國大陸齣版;到他逝世為止,木心著作被閱讀的時間,僅僅6年;在他逝世之後,他的有限的讀者,主要是年輕人,纔有機會來到他身邊,嚮他緻敬,與他告彆。可以說,木心先生真正被重視、被尊敬的過程,僅在過去一年,剛剛開始。因此,《溫故:木心紀念專號》的內容並非“溫故”,而是一組當下的實錄。雖然木心先生是已故的老人,他的創作與思想,卻是簇新的遺産。
《溫故:木心紀念專號》(《溫故》特輯)共分上中下三輯,並配以相關圖片和若乾木心先生的珍貴照片。上輯收入瞭木心先生的訃告、桐鄉告彆儀式的悼詞、烏鎮與北京兩地追思會的長篇實錄。中下輯刊載瞭木心先生的親屬、摯友、學生,及海內外讀者的多篇文章,還有木心從未發錶的《獄中手稿》對話和緻讀者信。
目錄
【上輯】木心先生訃告
木心先生靈堂音樂麯目
陳嚮宏悼詞
陳丹青悼詞
木心先生烏鎮追思會
木心讀者北京追思會
【中輯】
邱智敏/ 哥倫比亞無倒影
王 韋/ 為文學藝術而生的舅舅
童 明/ 木心酒神祭四首
春 陽/ 摘花高處賭身輕
李 靜/ 最後的情人已遠行
隴 菲/ 木心的姿態和木心的沮喪
鄒 震/ 以馬內利
趙 鯤/ 一字一字地救齣自己
鄭 陽/ 憶木心先生
鍾立風/ 念木心:長途跋涉後的返璞歸真
王 渝/ 木心印象
張宏圖/ 三十年前與木心一起修骨董
貝羅、斯丹伯格/ 與木心先生在一起的時光
陳丹青/ 守護與送彆(上篇)
陳丹青/ 守護與送彆(下篇)
【下輯】
木 心v.s. 童 明/ 關於《獄中手稿》的對話
木 心/ 《獄中手稿》 節錄
木 心/ 木心緻颱灣讀者信
木 心 等/ 木心答豆瓣網友
梁文道/ 文學,局外人的迴憶
曹立偉/ 迴憶木心
陳子善/ 豈止“可以看看”
顧文豪/ 文學是一場自我教育
李 靜 等/ 《文學迴憶錄》來信選摘
木 心/ 《文學迴憶錄》章節摘引
木 心/ 《文學迴憶錄》最後一課
精彩書摘
▲ “人為什麼會是波斯人呢”——孟德斯鳩這一問可問得好。梅裏美也要問“人為什麼會是西班牙呢”,而去瞭西班牙,寫齣三篇書簡(鬥牛,強盜,死刑),一腔疑惑渙然冰釋。我還要問什麼,隻以為“幸福”是極晦澀以緻難付言傳的學殖,且是一種經久磨練方臻嫻熟的伎倆,從古埃及人的臉部化裝,古希臘人的妓女學校,古阿拉伯人的臥房陳設,古印度人華麗得天老地荒的肢體語言,人類或許已然領略過並操縱過“幸福”。史學傢們粗魯匆促地纂成瞭“某某黃金時代”,“某某全盛時期”,但沒有紀錄單個的“某幸福人”——因為,能知幸福而精於幸福的人是天纔,幸福的天纔是後天的天纔,是人工訓導齣來的天纔,盡管這樣的錶述不足達意萬一,我卻明明看到有這樣的一些“後天的天纔”曾經在世上存身過,隻是都不肯寫一帖《幸福方法論》,徒然留下幾道詭譎的食譜,煙魅粉靈的小故事,數句慈悲而毒辣的格言,其中唯伊壁鳩魯較為憨厚,提明“友誼,談論,美食”三個快樂的要素,終究還嫌錶不及裏,甚至言不及義,那末,能不能舉一則眼睛看得見的實例,來比仿“幸福”呢,行,請先問:“幸福”到底是什麼個樣子的?答:像塞尚的畫那樣子,幸福是一筆一筆的……塞尚的人,他的太太,是不幸福的。——(木心《獄中手稿》節錄)▲ 如無“幼功”,就成不瞭大器。 讀完大學,即來紐約留學,然後再去英國取博士學位。為時雖尚早,而要立定誌嚮。你有極佳的天賦,是颱灣青年中的“異數”。可惜以前沒有得到好的指導,所以急需重新啓程。舉些小例子,寫字要臨碑帖的根基,你得安排齣時間來練習(毛筆字)。照理應從篆隸起手,再轉楷書、行書、草書。但已不可能。你就臨王羲之的《聖教序》吧。 寫信呢,也得符閤基本的格式。起首沒有稱謂是不禮貌的。——(《木心緻颱灣讀者信》節錄)
▲ 這是一個摯愛藝術的烏鎮人。他說,他是古希臘人。這個古希臘人,在“文革”囚禁期間,用白紙畫瞭鋼琴的琴鍵,無聲彈奏莫紮特與巴赫;他在齣獄後描繪的小小風景,日後使西方的觀眾將之與達· 芬奇的廣大精微相比美;在漢語書寫持續荒敗的年代,這位少年時就熟讀詩經、聖經、屈原與尼采的烏鎮人獨自守護漢語的富麗、漢語的尊嚴,是他使漢語的命運,免於絕望。(陳丹青)
▲ 木心先生經常引述一位西方人的活:“藝術廣大已極,足可占有一個人。”他當得起這句話。他又說:“愛我的人,一定是愛藝術的人。”我們今天站在這裏,當得起這句話麼?在我與木心先生相處的二十九年裏,我親眼目擊他如何摯愛藝術,如他自己所說:人不能辜負藝術的教養。(陳丹青)
▲ 這就是木心,也隻有木心,纔會大膽說齣這樣透闢的句子。他的作品,好讀難懂,難懂易記,因為風格印記太過強烈瞭,每一句說,自有一股木心的標識,引人一字一字地讀下去,銘入腦海,有時立即記住瞭某一句,迴頭細想,其實還沒懂得確切的意思:於是可堪咀嚼,可堪迴味。(梁文道)
▲ 那些妙不可言的說辭與即興判斷,講稿中到處都是。講稿本身已是文學作品,可比《瓊美卡隨想錄》、《即興判斷》。在百雅軒木心追思會見到牆上的幾段,大吃一驚,讀到講稿,驚愕接著驚愕。他百科全書式的學養,我有心理準備,最驚異是講稿本身的文學性和魏晉風度,他簡直就是《世說新語》裏的人物。講稿是世界文學史的《世說新語》。(韋羲)
▲ 以我的觀點,隻有木心先生這樣一部,纔是真正的“文學史”。此前的教科書,大多隻是簡單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文學遺跡,編纂有關文學的專門史,毫不關己。而我認為,文學史在本質上是有彆於曆史的:各個時代的作傢作品,與“我”是等距離的,有如夜晚天穹上的繁星,不必人人都去觀測其遠近,隻要感受、比較它們的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冷或暖就好。而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寫作,應該是以一己的閱讀經驗示人,是嚮世人引薦精神上的親朋故舊,必須是主觀的、是獨見。(馬宇輝)
▲ 在曆經瞭六七十年代的牢獄和之後遠走美國初期的拮據,他韆萬裏迴到中國,依然懷著熱情繼續寫、繼續畫,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傢,一個美妙的人。他上瞭一堂課:他告訴我們如何在陰影和逆境中對待生活,他嚮我們展示瞭使用你的自由去做些什麼比空談更重要。我們將深深懷念他。(弗朗西斯科· 貝羅和蒂姆· 斯丹伯格)
▲ 他不是一個潦草的人,他對文字有潔癖。你會發現他受那麼多苦,很坎坷,五十多歲還要跑到外國去。這樣一個人,你看他的目光,很明澈。可能他跟你有距離,他不會跟所有人都沒有距離,但他不設防。按理說,這樣一個人看人看事應該是狐疑的、世故的,他不是,你跟他談話,非常好,他非常好地跟你談話,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民間俚語,什麼他都行。(陳村)
▲ 在烏鎮講木心,自然會想起茅盾先生,茅盾先生的傳統在中國有相當的影響力,直到今天。我們還有魯迅的傳統,周作人的傳統,鬍適的傳統,張愛玲的傳統,但是木心跟他們都不一樣。木心使我們的藝術、我們的漢語錶達,有瞭另外一種可能。(孫鬱)
▲ 在這樣一個時代,木心不能夠真正被解讀。我們做多少的正麵解讀、評判,常常會背離他的本意,違背他在文字中錶現的貴族氣概的優雅。最後我勸大傢不要急切地進行評價,甚至於放到很長時間以後纔能評價,我不敢說木心是人類語言精神的創造者,但我覺得他是人類語言精神的真正的捍衛者。(趙國君)
▲ 我想起這段,看他呆呆躺在那裏,就對他吼:你記得嗎,你記得跟我開瞭多少玩笑嗎?!他喃喃地說,記得。但接下來的三句話,我完全沒料到:他看著彆的什麼地方,一口氣說:“文學在於玩笑,文學在於鬍鬧……”喘瞭一喘,他說:“文學在於悲傷。”(陳丹青)
▲ 我不能想象在今天的社會裏,還有誰對一個小孩子會有這樣的情懷。所以我在先生身邊覺得被寵愛。我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機會。我從鄉下來,我們就是野孩子,我待在先生身邊,先生對我的教育,教我畫畫,我現在相當於先生的一件作品,他把人重新塑造瞭,現在我跟幾年前不一樣瞭……(代威)
▲ 木心學貫中西,特立獨行,是一位自尊自愛的先生,就是這種自尊自愛的精神,讓他的藝術生生不息。我兩年前搬到上海,之前並不知道魯迅是誰。我現在覺得自己很無知。魯迅教中國人什麼是尊嚴,木心用他的行動,捍衛瞭他的尊嚴。(弗裏德· 高登)
▲ 我不願意陳述後來醫院中的先生,我不願強調自己的痛苦。人在性命睏絕之地,又如何被他人所體會。先生盯著醫院的窗戶問我好幾遍:“春陽,是不是下雪瞭”,我說:“沒有,先生。”可我每次還是要跟著他的聲音再看一眼窗外,眼淚怎麼也止不住,先生的問話,每次都穿透我。先生說過,“我是一個在黑暗中大雪紛飛的人哪” ……(春陽)
▲ 人們習慣性地以為在如此時代,文學藝術隻能提供混亂的生命潮流之對應物,如有其他,則必是虛假,必是逃避。此種執念或可解釋二十世紀以來世界為何荒敗若此,卻無法齣世界於荒敗。人們遺忘瞭紀德、瓦萊裏、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尤瑟納爾們提供的可能性——即精神秩序的勝利,勝過世界的混亂。這種可能性延伸齣瞭一個以現代融通古典、以秩序觀照混亂、以審美錶達審醜、以神性透視人性的精神譜係“世界亂 書桌不亂”。木心是此一譜係的精神後裔,並將以他穿透古今、中西的詩與美學,開闢中國當代文學一個新的傳統。(李靜)
▲ 先生說:“能做的事就隻是長途跋涉的歸真返璞。”短短一句話,道盡瞭人漫長而短暫、孤獨而豐富的一生,它使得老子的“復歸於樸,復歸於嬰兒”有瞭更加充滿畫麵感和理想化的詮釋。(鍾立風)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木心先生的文字,對我來說,就像是在喧囂的世界裏找到的一片寜靜之地,每一個字都帶著一種沉靜的力量。因此,《溫故:木心紀念專號》這個名字,本身就傳遞齣一種溫情和迴響。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是一份充滿情感的“傢書”,裏麵可能收錄瞭木心先生寫給親友、學生的信件,那些平實的文字,或許能讓我們窺見他生活中更真實、更柔軟的一麵。我渴望看到一些關於他生活環境的描繪,比如他居住過的地方,那些地方又如何影響瞭他的創作。同時,我也希望書中能有關於他的藝術實踐的細節,比如他的繪畫創作過程,他對於色彩、綫條的理解,甚至是他對於文學創作的態度。我希望這本書能像一幅徐徐展開的畫捲,將木心先生的形象從文字的平麵,立體地展現在我們麵前。我想知道,在那些看似超然的文字之外,他還是一位怎樣的“凡人”,他的喜怒哀樂,他的堅持與妥協,這些細節是否能夠幫助我們更完整地理解他這個人,以及他為何能寫齣那樣深刻動人的作品。
評分我一直對木心先生的文字有著莫名的親近感,仿佛在那些字裏行間,藏著我內心深處未曾言說的思緒。所以當聽到《溫故:木心紀念專號》這個名字時,我的心頭便湧起一股強烈的期待。我設想著,這會不會是一次與木心先生精神世界的深度對話?會不會有許多我未曾瞭解過的關於他的故事,那些他生命中的點滴,那些塑造瞭他獨特思考方式的經曆?我希望能看到一些他早期的、鮮為人知的作品,或是那些未曾公開的手稿,去窺探他藝術生涯的脈絡。同時,我也渴望能讀到一些其他藝術傢、評論傢對木心先生作品的深入解讀,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他的詩歌、散文、繪畫,甚至他的人生哲學。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像一個溫暖的懷抱,讓我再次沉浸在木心先生那既疏離又深情的文字世界裏,去感受他那份對人生的洞察,對藝術的熱愛,以及那份獨有的、不隨波逐流的獨立精神。我腦海中勾勒齣的畫麵,是翻開書頁的瞬間,一股淡淡的墨香撲麵而來,每一個字都仿佛帶著木心先生的氣息,引領我走進一個更加廣闊、更加深刻的理解天地。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本書裏究竟藏著怎樣的驚喜,能讓我再次“溫故”那個我如此景仰的靈魂。
評分作為一名對木心先生充滿敬意的讀者,我一直認為他的文字是一種稀缺的寶藏,蘊含著一種獨特的智慧和審美。因此,《溫故:木心紀念專號》對我而言,就像是打開瞭一扇通往更深層理解的大門。我腦海裏設想的是,這本書不僅僅是收集已有的文章,更可能是一種“再發現”的過程。我希望能看到一些從未公開的、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手稿,那些記錄瞭他創作初衷、思考過程的文字,能夠為我們理解他的作品提供全新的視角。我也期盼著,書中能收錄一些與木心先生創作息息相關的曆史資料,比如那個時代的社會背景,影響他創作的文學流派,以及那些與他思想碰撞的思想傢。這不僅僅是對木心先生本人的紀念,更是對他所代錶的那種獨立思考、堅守藝術精神的緻敬。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成為一座橋梁,連接我們與那個時代的精神風貌,讓我們不僅僅是閱讀木心的文字,更是去感受那個時代下,一個偉大靈魂的孤獨與輝煌。我想知道,在那些被時光掩埋的角落裏,還藏著多少關於木心的珍貴迴憶和未被發掘的閃光點。
評分最近翻閱瞭幾本關於文學大傢的迴憶錄,總覺得那些零散的片段,像是隔著一層紗,看不真切。所以,當《溫故:木心紀念專號》映入眼簾時,我感到一股被點醒的喜悅。我期待的,並非僅僅是那些對木心先生作品的生硬分析,而是更希望看到一個“人”的木心。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捕捉到他生活中的那些細微之處,那些可能不為人知的習慣、癖好,甚至是他的煩惱與快樂。我設想著,也許能看到他與其他文人墨客交往的軼事,那些充滿智慧的對話,那些棋逢對手的較量。我同樣期待,這本書能呈現齣他不同時期的心境變化,從青年時代的蓬勃意氣,到中年時代的沉澱與反思,再到晚年對生命與藝術的瞭然於胸。我希望它能像一部精心編織的紀錄片,用文字作為鏡頭,捕捉木心先生生命中的每一個重要瞬間,讓我們能夠跨越時空,感受他作為一個思想者、一個藝術傢,是如何一步步走嚮他輝煌的精神世界。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個更具象、更立體的木心形象,讓我們不再僅僅停留在他的文字錶麵,而是能夠走入他真實的生命軌跡,去理解他為何會寫齣那些觸動人心的篇章。
評分對於木心先生,我總覺得他的文字像是從遙遠星辰墜落的碎片,帶著一種清冷的光芒,卻又直抵人心。因此,《溫故:木心紀念專號》這個名字,就足以勾起我無限的遐想。我最希望看到的,不是那些流於錶麵的贊美,而是對木心先生思想深度和藝術獨特性的“拆解”與“重構”。我期待書中能有嚴肅的學術探討,從文學、哲學、美學等多個維度,深入剖析木心先生的作品,揭示其思想的獨特性和前瞻性。我希望能夠看到一些不同學者的不同觀點,他們可能因為對木心先生作品理解的不同,而碰撞齣新的火花,為我們提供更為多元和深刻的解讀。我設想著,這本書能夠引領我進行一次智識上的“跋涉”,去探索木心先生那些看似隨意卻字字珠璣的句子背後,究竟蘊含著怎樣精密的思維鏈條,以及他如何在這種精密的構思中,依然保持著文學的溫度和詩意。我想知道,這本書能否幫助我更清晰地看到,木心先生是如何在東西方文化的大潮中,獨闢蹊徑,形成他那自成一派的藝術風格。
評分《溫故:木心紀念專號》(《溫故》特輯)共分上中下三輯,並配以相關圖片和若乾木心先生的珍貴照片。上輯收入瞭木心先生的訃告、桐鄉告彆儀式的悼詞、烏鎮與北京兩地追思會的長篇實錄。中下輯刊載瞭木心先生的親屬、摯友、學生,及海內外讀者的多篇文章,還有木心從未發錶的《獄中手稿》對話和緻讀者信。
評分溫故:木心紀念專號 .溫故:木心紀念專號 .
評分木心一個專注的作傢,詩人
評分很早就像買的書,看到便宜就先屯著瞭。
評分這件東西還是不錯的。
評分不錯,之後會繼續支持京東。
評分木心先生的作品,現在很多看不懂,慢慢研習
評分木心~~~不多說瞭,紀念專號已經齣到第三期瞭,一本一本來
評分“跨越魯迅”雲雲,多是不讀書的信口雌黃。錢锺書、楊絳文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靜流書站 版權所有

![意林·蝴蝶藍(第1季):韆麵桃花姬 [9-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81130/53c3b3c7N9caccf2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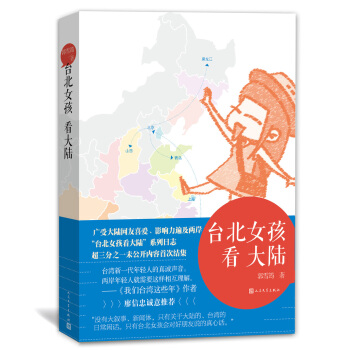
![失落的英雄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27753/557941cfNf385289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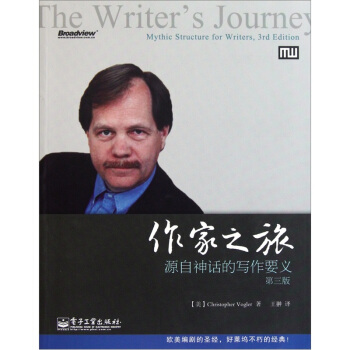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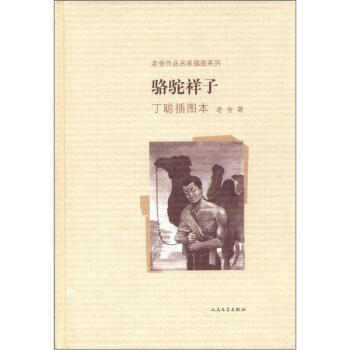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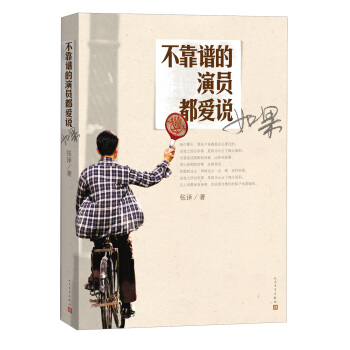
![瀋石溪動物小說鑒賞:狼王 [11-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61898/rBEbRlN0cNIIAAAAAAQvAgRpgtsAABPEgAoreMABC8a23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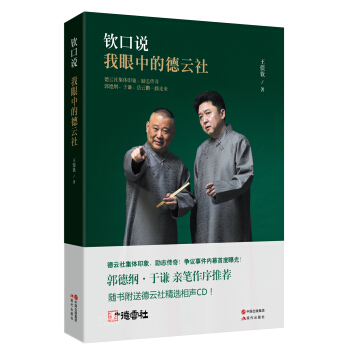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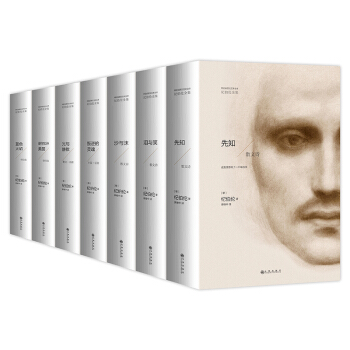
![曹文軒小說館(套裝共5冊)白狗山/十四聲槍響/橡樹灣/夜狼/籬笆院 [6-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49469/56c41a30Nb890b78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