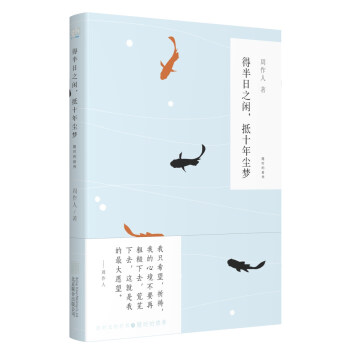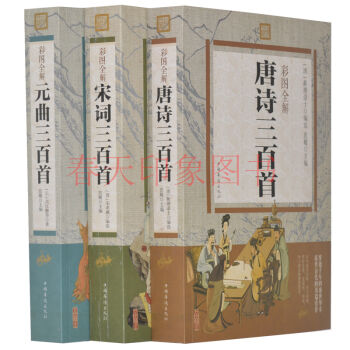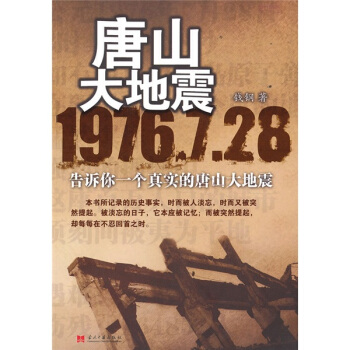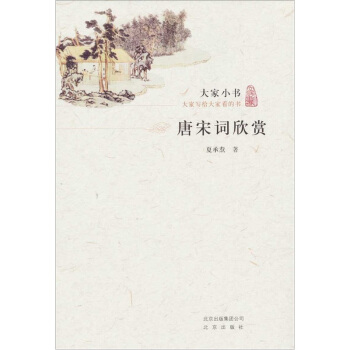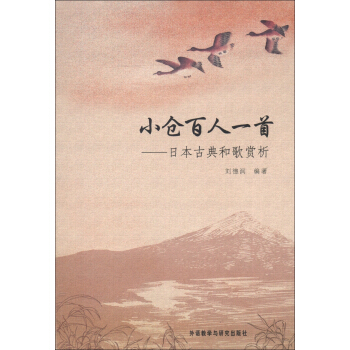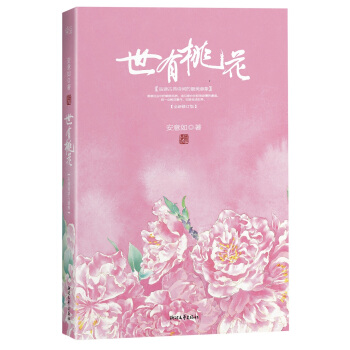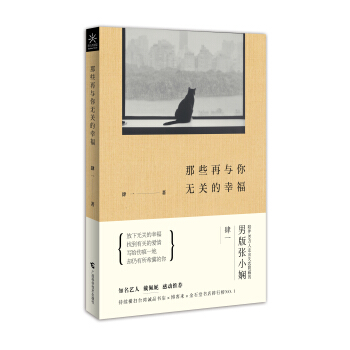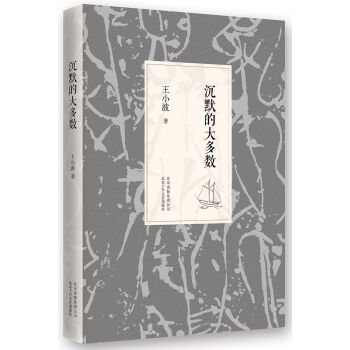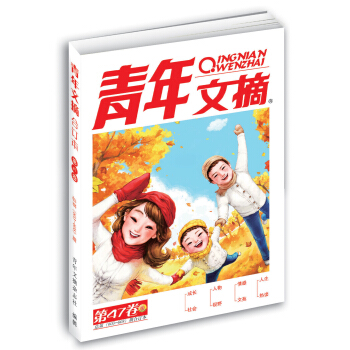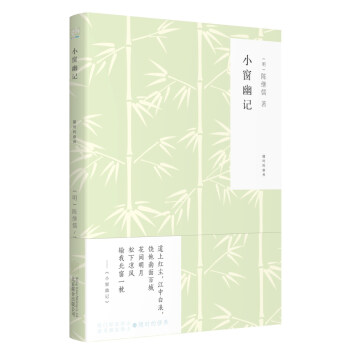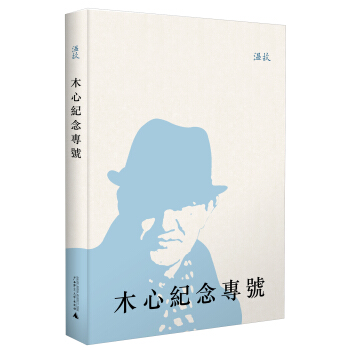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木心先生的“最后时光”,陈丹青的“守护与送别”——
陈丹青在《守护与送别》中这样写道,“11 月中至12 月下旬,我几度守在木心病榻前,之后,是他的葬礼。谁曾守护亲属挚友走向最后的路,或对人的殒灭的真相,不惊讶,不陌生?但这是我目击垂老的人,病危,衰竭,死。我不想限制篇幅,不愿遗漏种种细节。这是木心以自己的性命的完结,给我上最后一课。”
▲ 首次发表若干珍贵照片,病榻前陈丹青描绘先生——
○ “木心从不让我画他,这是我描绘先生,也是最后一次。画时,他浑然不知。”
○ 木心晚年诗集《伪所罗门书》手稿本
○ 木心《我纷纷的情欲》手稿本
○ 2005年木心回国探看乌镇为他故园营建的新居,在上海停留期间,与上海作家陈村、孙甘露、王淑瑾、尹庆一等有过愉快的会面,喜滋滋为他们签自己的书。
○ 2010年12月纽约电影人为木心拍摄纪录片期间,他已渐渐习惯面对摄像。
○ 12张珍贵照片。2011-1927的木心。
▲ 首次发表木心先生的《狱中手稿》对话、节录和致读者信
关于木心先生的66页狱中手稿,木心的研究者、翻译者童明教授曾与木心在2000年有过一次对话。此外,木心本人曾从手稿中选出5段摘录。这两份文本的汉语版从未面世,《木心纪念专号》全文发表。
▲ 收录梁文道、陈子善、钟立风、童明、春阳、顾文豪等人文章
▲ 收录木心先生的丧仪文本和乌镇、北京两地追思会长篇实录
▲ 收录木心先生《文学回忆录》来信选登、章节摘引、最后一课
海报:
内容简介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时时感到,这是一份郑重的纪念,更是一组历史的见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与艺术史中,木心先生是一个的孤例:他的几乎全部创作生涯,鲜为人知, 直至他79岁那年,他的文学著作始得陆续在他的祖国大陆出版;到他逝世为止,木心著作被阅读的时间,仅仅6年;在他逝世之后,他的有限的读者,主要是年轻人,才有机会来到他身边,向他致敬,与他告别。可以说,木心先生真正被重视、被尊敬的过程,仅在过去一年,刚刚开始。因此,《温故:木心纪念专号》的内容并非“温故”,而是一组当下的实录。虽然木心先生是已故的老人,他的创作与思想,却是簇新的遗产。
《温故:木心纪念专号》(《温故》特辑)共分上中下三辑,并配以相关图片和若干木心先生的珍贵照片。上辑收入了木心先生的讣告、桐乡告别仪式的悼词、乌镇与北京两地追思会的长篇实录。中下辑刊载了木心先生的亲属、挚友、学生,及海内外读者的多篇文章,还有木心从未发表的《狱中手稿》对话和致读者信。
目录
【上辑】木心先生讣告
木心先生灵堂音乐曲目
陈向宏悼词
陈丹青悼词
木心先生乌镇追思会
木心读者北京追思会
【中辑】
邱智敏/ 哥伦比亚无倒影
王 韦/ 为文学艺术而生的舅舅
童 明/ 木心酒神祭四首
春 阳/ 摘花高处赌身轻
李 静/ 最后的情人已远行
陇 菲/ 木心的姿态和木心的沮丧
邹 震/ 以马内利
赵 鲲/ 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
郑 阳/ 忆木心先生
钟立风/ 念木心:长途跋涉后的返璞归真
王 渝/ 木心印象
张宏图/ 三十年前与木心一起修骨董
贝罗、斯丹伯格/ 与木心先生在一起的时光
陈丹青/ 守护与送别(上篇)
陈丹青/ 守护与送别(下篇)
【下辑】
木 心v.s. 童 明/ 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
木 心/ 《狱中手稿》 节录
木 心/ 木心致台湾读者信
木 心 等/ 木心答豆瓣网友
梁文道/ 文学,局外人的回忆
曹立伟/ 回忆木心
陈子善/ 岂止“可以看看”
顾文豪/ 文学是一场自我教育
李 静 等/ 《文学回忆录》来信选摘
木 心/ 《文学回忆录》章节摘引
木 心/ 《文学回忆录》最后一课
精彩书摘
▲ “人为什么会是波斯人呢”——孟德斯鸠这一问可问得好。梅里美也要问“人为什么会是西班牙呢”,而去了西班牙,写出三篇书简(斗牛,强盗,死刑),一腔疑惑涣然冰释。我还要问什么,只以为“幸福”是极晦涩以致难付言传的学殖,且是一种经久磨练方臻娴熟的伎俩,从古埃及人的脸部化装,古希腊人的妓女学校,古阿拉伯人的卧房陈设,古印度人华丽得天老地荒的肢体语言,人类或许已然领略过并操纵过“幸福”。史学家们粗鲁匆促地纂成了“某某黄金时代”,“某某全盛时期”,但没有纪录单个的“某幸福人”——因为,能知幸福而精于幸福的人是天才,幸福的天才是后天的天才,是人工训导出来的天才,尽管这样的表述不足达意万一,我却明明看到有这样的一些“后天的天才”曾经在世上存身过,只是都不肯写一帖《幸福方法论》,徒然留下几道诡谲的食谱,烟魅粉灵的小故事,数句慈悲而毒辣的格言,其中唯伊壁鸠鲁较为憨厚,提明“友谊,谈论,美食”三个快乐的要素,终究还嫌表不及里,甚至言不及义,那末,能不能举一则眼睛看得见的实例,来比仿“幸福”呢,行,请先问:“幸福”到底是什么个样子的?答:像塞尚的画那样子,幸福是一笔一笔的……塞尚的人,他的太太,是不幸福的。——(木心《狱中手稿》节录)▲ 如无“幼功”,就成不了大器。 读完大学,即来纽约留学,然后再去英国取博士学位。为时虽尚早,而要立定志向。你有极佳的天赋,是台湾青年中的“异数”。可惜以前没有得到好的指导,所以急需重新启程。举些小例子,写字要临碑帖的根基,你得安排出时间来练习(毛笔字)。照理应从篆隶起手,再转楷书、行书、草书。但已不可能。你就临王羲之的《圣教序》吧。 写信呢,也得符合基本的格式。起首没有称谓是不礼貌的。——(《木心致台湾读者信》节录)
▲ 这是一个挚爱艺术的乌镇人。他说,他是古希腊人。这个古希腊人,在“文革”囚禁期间,用白纸画了钢琴的琴键,无声弹奏莫扎特与巴赫;他在出狱后描绘的小小风景,日后使西方的观众将之与达· 芬奇的广大精微相比美;在汉语书写持续荒败的年代,这位少年时就熟读诗经、圣经、屈原与尼采的乌镇人独自守护汉语的富丽、汉语的尊严,是他使汉语的命运,免于绝望。(陈丹青)
▲ 木心先生经常引述一位西方人的活:“艺术广大已极,足可占有一个人。”他当得起这句话。他又说:“爱我的人,一定是爱艺术的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当得起这句话么?在我与木心先生相处的二十九年里,我亲眼目击他如何挚爱艺术,如他自己所说:人不能辜负艺术的教养。(陈丹青)
▲ 这就是木心,也只有木心,才会大胆说出这样透辟的句子。他的作品,好读难懂,难懂易记,因为风格印记太过强烈了,每一句说,自有一股木心的标识,引人一字一字地读下去,铭入脑海,有时立即记住了某一句,回头细想,其实还没懂得确切的意思:于是可堪咀嚼,可堪回味。(梁文道)
▲ 那些妙不可言的说辞与即兴判断,讲稿中到处都是。讲稿本身已是文学作品,可比《琼美卡随想录》、《即兴判断》。在百雅轩木心追思会见到墙上的几段,大吃一惊,读到讲稿,惊愕接着惊愕。他百科全书式的学养,我有心理准备,最惊异是讲稿本身的文学性和魏晋风度,他简直就是《世说新语》里的人物。讲稿是世界文学史的《世说新语》。(韦羲)
▲ 以我的观点,只有木心先生这样一部,才是真正的“文学史”。此前的教科书,大多只是简单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文学遗迹,编纂有关文学的专门史,毫不关己。而我认为,文学史在本质上是有别于历史的:各个时代的作家作品,与“我”是等距离的,有如夜晚天穹上的繁星,不必人人都去观测其远近,只要感受、比较它们的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冷或暖就好。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以一己的阅读经验示人,是向世人引荐精神上的亲朋故旧,必须是主观的、是独见。(马宇辉)
▲ 在历经了六七十年代的牢狱和之后远走美国初期的拮据,他千万里回到中国,依然怀着热情继续写、继续画,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一个美妙的人。他上了一堂课:他告诉我们如何在阴影和逆境中对待生活,他向我们展示了使用你的自由去做些什么比空谈更重要。我们将深深怀念他。(弗朗西斯科· 贝罗和蒂姆· 斯丹伯格)
▲ 他不是一个潦草的人,他对文字有洁癖。你会发现他受那么多苦,很坎坷,五十多岁还要跑到外国去。这样一个人,你看他的目光,很明澈。可能他跟你有距离,他不会跟所有人都没有距离,但他不设防。按理说,这样一个人看人看事应该是狐疑的、世故的,他不是,你跟他谈话,非常好,他非常好地跟你谈话,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民间俚语,什么他都行。(陈村)
▲ 在乌镇讲木心,自然会想起茅盾先生,茅盾先生的传统在中国有相当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我们还有鲁迅的传统,周作人的传统,胡适的传统,张爱玲的传统,但是木心跟他们都不一样。木心使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汉语表达,有了另外一种可能。(孙郁)
▲ 在这样一个时代,木心不能够真正被解读。我们做多少的正面解读、评判,常常会背离他的本意,违背他在文字中表现的贵族气概的优雅。最后我劝大家不要急切地进行评价,甚至于放到很长时间以后才能评价,我不敢说木心是人类语言精神的创造者,但我觉得他是人类语言精神的真正的捍卫者。(赵国君)
▲ 我想起这段,看他呆呆躺在那里,就对他吼:你记得吗,你记得跟我开了多少玩笑吗?!他喃喃地说,记得。但接下来的三句话,我完全没料到:他看着别的什么地方,一口气说:“文学在于玩笑,文学在于胡闹……”喘了一喘,他说:“文学在于悲伤。”(陈丹青)
▲ 我不能想象在今天的社会里,还有谁对一个小孩子会有这样的情怀。所以我在先生身边觉得被宠爱。我没有得到过这样的机会。我从乡下来,我们就是野孩子,我待在先生身边,先生对我的教育,教我画画,我现在相当于先生的一件作品,他把人重新塑造了,现在我跟几年前不一样了……(代威)
▲ 木心学贯中西,特立独行,是一位自尊自爱的先生,就是这种自尊自爱的精神,让他的艺术生生不息。我两年前搬到上海,之前并不知道鲁迅是谁。我现在觉得自己很无知。鲁迅教中国人什么是尊严,木心用他的行动,捍卫了他的尊严。(弗里德· 高登)
▲ 我不愿意陈述后来医院中的先生,我不愿强调自己的痛苦。人在性命困绝之地,又如何被他人所体会。先生盯着医院的窗户问我好几遍:“春阳,是不是下雪了”,我说:“没有,先生。”可我每次还是要跟着他的声音再看一眼窗外,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先生的问话,每次都穿透我。先生说过,“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哪” ……(春阳)
▲ 人们习惯性地以为在如此时代,文学艺术只能提供混乱的生命潮流之对应物,如有其他,则必是虚假,必是逃避。此种执念或可解释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为何荒败若此,却无法出世界于荒败。人们遗忘了纪德、瓦莱里、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尤瑟纳尔们提供的可能性——即精神秩序的胜利,胜过世界的混乱。这种可能性延伸出了一个以现代融通古典、以秩序观照混乱、以审美表达审丑、以神性透视人性的精神谱系“世界乱 书桌不乱”。木心是此一谱系的精神后裔,并将以他穿透古今、中西的诗与美学,开辟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新的传统。(李静)
▲ 先生说:“能做的事就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短短一句话,道尽了人漫长而短暂、孤独而丰富的一生,它使得老子的“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有了更加充满画面感和理想化的诠释。(钟立风)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木心先生的文字,对我来说,就像是在喧嚣的世界里找到的一片宁静之地,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因此,《温故:木心纪念专号》这个名字,本身就传递出一种温情和回响。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是一份充满情感的“家书”,里面可能收录了木心先生写给亲友、学生的信件,那些平实的文字,或许能让我们窥见他生活中更真实、更柔软的一面。我渴望看到一些关于他生活环境的描绘,比如他居住过的地方,那些地方又如何影响了他的创作。同时,我也希望书中能有关于他的艺术实践的细节,比如他的绘画创作过程,他对于色彩、线条的理解,甚至是他对于文学创作的态度。我希望这本书能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将木心先生的形象从文字的平面,立体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知道,在那些看似超然的文字之外,他还是一位怎样的“凡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坚持与妥协,这些细节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更完整地理解他这个人,以及他为何能写出那样深刻动人的作品。
评分作为一名对木心先生充满敬意的读者,我一直认为他的文字是一种稀缺的宝藏,蕴含着一种独特的智慧和审美。因此,《温故:木心纪念专号》对我而言,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更深层理解的大门。我脑海里设想的是,这本书不仅仅是收集已有的文章,更可能是一种“再发现”的过程。我希望能看到一些从未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手稿,那些记录了他创作初衷、思考过程的文字,能够为我们理解他的作品提供全新的视角。我也期盼着,书中能收录一些与木心先生创作息息相关的历史资料,比如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影响他创作的文学流派,以及那些与他思想碰撞的思想家。这不仅仅是对木心先生本人的纪念,更是对他所代表的那种独立思考、坚守艺术精神的致敬。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连接我们与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不仅仅是阅读木心的文字,更是去感受那个时代下,一个伟大灵魂的孤独与辉煌。我想知道,在那些被时光掩埋的角落里,还藏着多少关于木心的珍贵回忆和未被发掘的闪光点。
评分最近翻阅了几本关于文学大家的回忆录,总觉得那些零散的片段,像是隔着一层纱,看不真切。所以,当《温故:木心纪念专号》映入眼帘时,我感到一股被点醒的喜悦。我期待的,并非仅仅是那些对木心先生作品的生硬分析,而是更希望看到一个“人”的木心。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捕捉到他生活中的那些细微之处,那些可能不为人知的习惯、癖好,甚至是他的烦恼与快乐。我设想着,也许能看到他与其他文人墨客交往的轶事,那些充满智慧的对话,那些棋逢对手的较量。我同样期待,这本书能呈现出他不同时期的心境变化,从青年时代的蓬勃意气,到中年时代的沉淀与反思,再到晚年对生命与艺术的了然于胸。我希望它能像一部精心编织的纪录片,用文字作为镜头,捕捉木心先生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瞬间,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感受他作为一个思想者、一个艺术家,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他辉煌的精神世界。我希望这本书能提供一个更具象、更立体的木心形象,让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他的文字表面,而是能够走入他真实的生命轨迹,去理解他为何会写出那些触动人心的篇章。
评分我一直对木心先生的文字有着莫名的亲近感,仿佛在那些字里行间,藏着我内心深处未曾言说的思绪。所以当听到《温故:木心纪念专号》这个名字时,我的心头便涌起一股强烈的期待。我设想着,这会不会是一次与木心先生精神世界的深度对话?会不会有许多我未曾了解过的关于他的故事,那些他生命中的点滴,那些塑造了他独特思考方式的经历?我希望能看到一些他早期的、鲜为人知的作品,或是那些未曾公开的手稿,去窥探他艺术生涯的脉络。同时,我也渴望能读到一些其他艺术家、评论家对木心先生作品的深入解读,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他的诗歌、散文、绘画,甚至他的人生哲学。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个温暖的怀抱,让我再次沉浸在木心先生那既疏离又深情的文字世界里,去感受他那份对人生的洞察,对艺术的热爱,以及那份独有的、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精神。我脑海中勾勒出的画面,是翻开书页的瞬间,一股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木心先生的气息,引领我走进一个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理解天地。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本书里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能让我再次“温故”那个我如此景仰的灵魂。
评分对于木心先生,我总觉得他的文字像是从遥远星辰坠落的碎片,带着一种清冷的光芒,却又直抵人心。因此,《温故:木心纪念专号》这个名字,就足以勾起我无限的遐想。我最希望看到的,不是那些流于表面的赞美,而是对木心先生思想深度和艺术独特性的“拆解”与“重构”。我期待书中能有严肃的学术探讨,从文学、哲学、美学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木心先生的作品,揭示其思想的独特性和前瞻性。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他们可能因为对木心先生作品理解的不同,而碰撞出新的火花,为我们提供更为多元和深刻的解读。我设想着,这本书能够引领我进行一次智识上的“跋涉”,去探索木心先生那些看似随意却字字珠玑的句子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精密的思维链条,以及他如何在这种精密的构思中,依然保持着文学的温度和诗意。我想知道,这本书能否帮助我更清晰地看到,木心先生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潮中,独辟蹊径,形成他那自成一派的艺术风格。
评分快递很给力,很好?
评分在书中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体验千种滋味,百态人生
评分帮同学买的,他很喜欢!
评分好书,可惜是平装版的!
评分四、开展活动进行阅读。在班级中开展有关活动,比如组织朗诵会、图书节、故事会等,组织学生填写“读书信息卡”、制作“读书书签”、与家长共同开展“亲子阅读”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为学生创设了有趣的多样的读书活动。使学生广泛地“读”,大量地“读”。
评分帮同学买的,他很喜欢!
评分非常愉快的购物体验,物美价廉,物超所值。
评分温故:木心纪念专号,喜欢陈丹青先生的书,他多次提到木心老人,所以,买来看看
评分对木心有了很好的了解。对继续阅读他的作品有很大的帮助。好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coffeedeals.club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流书站 版权所有

![意林·蝴蝶蓝(第1季):千面桃花姬 [9-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81130/53c3b3c7N9caccf2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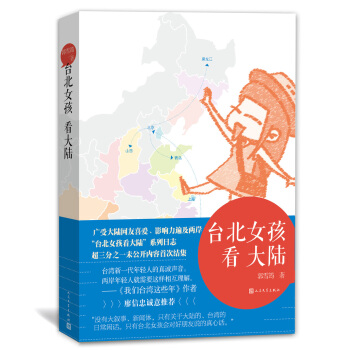
![失落的英雄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0827753/557941cfNf385289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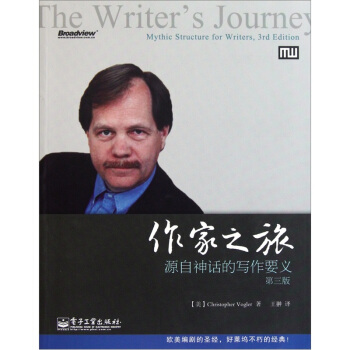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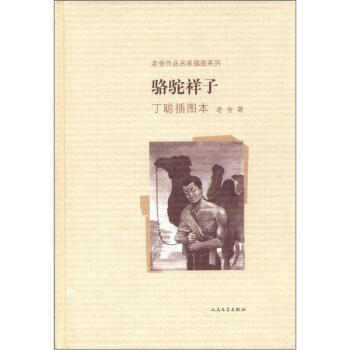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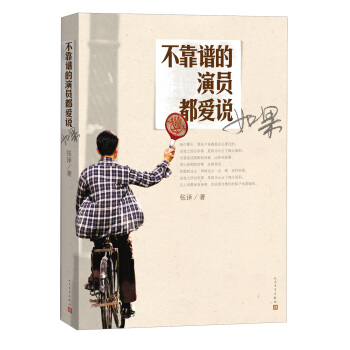
![沈石溪动物小说鉴赏:狼王 [11-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461898/rBEbRlN0cNIIAAAAAAQvAgRpgtsAABPEgAoreMABC8a23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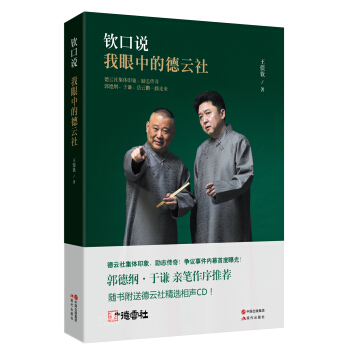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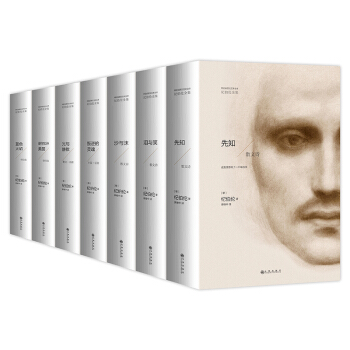
![曹文轩小说馆(套装共5册)白狗山/十四声枪响/橡树湾/夜狼/篱笆院 [6-14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windowsfront.com/11849469/56c41a30Nb890b78a.jpg)